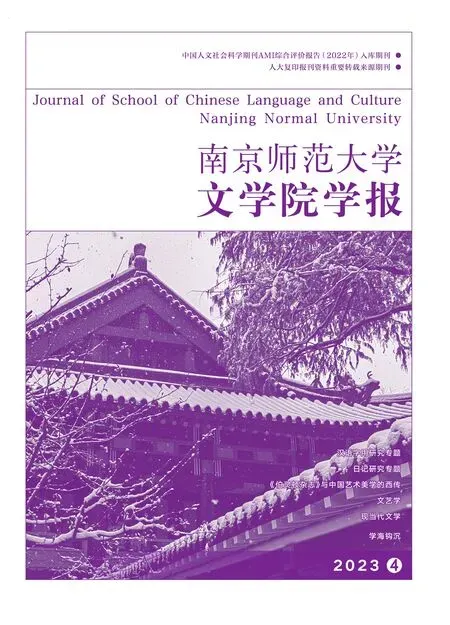论阿瑟·韦利对中国艺术哲学的译介和研究
—— 以《中国艺术哲学》系列论文为例
白薇臻
(南京工业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
在20世纪初期的英国汉学界,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可谓一颗耀眼璀璨的明珠。凭借着惊人的语言天赋和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满腔热忱,韦利在勤恳工作的数十年中,出版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化的译作与研究,为沟通中西文化搭建了坚实的桥梁。总体而言,韦利主要是以其对汉诗的出色英译而闻名于世的。他通过典雅、贴切的翻译风格和自然、独特的“跳跃节奏(sprung rhythm)”,精准把握了中国古典诗歌意蕴无穷的独特魅力,使其译作成为汉诗英译的典范,并推动了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中的远播,甚至在美国新诗运动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韦利在诗歌译介和诗文创作的巨大成就,最终让他于1953年获得女王诗歌奖(Queen’s Medal for Poetry)。基于此,国内外学界的诸多著述早已关注其中国文学译介的成果,从翻译策略、风格取向、译作影响等予以阐释。
然而,韦利不仅是中国文学译介的伟大实践者,还是悉心研究中国艺术,并推动英语世界关注和接受中国艺术的重要中介。特别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他先后出版包括《大英博物馆东方图片及绘画分部藏品之中国艺术家人名索引》(AnIndexofChineseArtistsRepresentedintheSub-DepartmentofOrientalPrintsandDrawingsintheBritishMuseum,1922)、《中国艺术研究概论》(A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ChinesePainting,1923)、《斯坦因爵士敦煌绘画目录》(ACatalogueofPaintingRecoveredformTun-HangbySirAurelStein,K.C.I.E.PreservedintheSubDepartmentofOrientalPrintsandDrawingsintheBritishMuseum,andintheMuseumofCentralAsianAntiquities,Delhi,1931)等在内的重要艺术论著,为西方社会打开通往中国古典艺术的一扇明窗。
可惜的是,当韦利汉诗英译的巨大成就遮蔽了其在中国艺术西传历程中的突出贡献时,国内外学界也因此忽视了对其中国艺术研究的梳理和论析,聚焦此论题的著述还较少。其中,吴云的硕士论文《他山之石——阿瑟·韦利对中国艺术的研究》(2015)爬梳了韦利有关中国艺术研究的全部论著,并逐一进行内容概述和要点翻译,文后还附上了韦利翻译董其昌《画论》的手稿,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1)吴云. 他山之石—阿瑟·韦利对中国艺术的研究[D].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15。。曹顺庆、任鑫的论文《阿瑟·韦利的中国绘画研究与汉学转折》(2018年)聚焦韦利中国艺术研究的成果、特色,及其对西方汉学转向、西方现代文艺发展的深刻影响(2)曹顺庆, 任鑫. 阿瑟·韦利的中国绘画研究与汉学转折[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5)。。国外重要的韦利研究学者格鲁希(John Walter de Gruchy)、鲁思·帕尔马特(Ruth Perlmutter)等对其中国艺术观的阐释亦散见于数部论著中(3)See John Walter de Gruchy. Orienting Arthur Waley: Japanism, Orientalism, and the Crea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 [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Ruth Perlmutter. Arthur Waley and His Place in the Modern Movement Between the Two Wars [D]. University Microfilms, Michigan: A XEROX Company, 1971.,为此论题研究提供有益参考。遗憾的是尚未有成果专论韦利的中国艺术哲学研究。因此,本文将以阿瑟·韦利20世纪二十年代发表于著名艺术评论杂志——《伯灵顿杂志》(TheBurlingtonMagazineforConnoisseurs)上的《中国艺术哲学》系列论文为研究对象,在梳理系列论文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探究其译介中国艺术哲学的特色和影响,以此揭示韦利对20世纪初期西方接受、理解、汲取中国艺术哲学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一、《中国艺术哲学》系列论文的刊发背景
作为推动英国传统汉学向现代汉学转变的“边缘者”与“颠覆者”(4)冀爱莲. 阿瑟·韦利汉学研究策略考辨.绪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第61页。,阿瑟·韦利热切拥抱中国艺术并非偶然,而是内外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韦利开展中国艺术研究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初期中国艺术在西方再次“复兴”的史实。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艺术史学家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所言,“中西美术的交流从1592年著名学者兼传教士利玛窦来到澳门才真正开始”(5)迈克尔·苏立文. 东西方艺术的交会.引言[M]. 赵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54页。。随着越来越多瓷器、屏风、纺织品等中国工艺品从遥远的东方运抵西方,同西方艺术风格迥然不同的充满异域风情、极具装饰价值的“中国风尚”(chinoiserie)于17、18世纪席卷欧洲,并催生了繁复华丽的洛可可风格(Rococo)。然而,即便中国艺术品已成为欧洲家庭的重要饰品,但“欧洲人对中国美术的兴趣基本上只限于工艺品和装饰性绘画”(6)迈克尔·苏立文. 东西方艺术的交会.引言[M]. 赵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101页。,不讲求三维透视、明暗法,以灵动飘逸、以形写神、笔精墨妙为特征的中国绘画对欧洲人而言十分陌生,中国画论更被长期忽视。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艺术的创作技法、美学观念、风格趣味才真正进入了西方主流艺术研究的视野,并在思想和技法两方面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施加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20世纪初英国再度出现的这股中国浪潮不应被单纯理解为历史性的风格复兴,而应该将其放置于文学诗歌、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时尚消费彼此交织流动的图景中,作为洞察现代主义思潮与实践的有效框架。”(7)汪燕翎,梁海育. 寻找“宋瓷”——20世纪初英国的现代主义中国风[J]. 艺术设计研究,2022(6)。而创刊于1903年的英国著名艺术评论杂志《伯灵顿杂志》见证并推动了这股“中国浪潮”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相互激荡与合流。在罗杰·弗莱的影响下,该杂志“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涵盖法国现代主义绘画、更多理论文章、诸如儿童艺术等非传统主题,以及包括中国等非欧洲艺术的宽广主题”(8)Ralph Parfect. Roger Fly,Chinese Art and the Burlington Magazine[A].Ed. Anne Witchard. British Modernism and Chinoiserie[C].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15, p.53.。其于20世纪初围绕中国、日本、印度等非西方国家集中刊发众多论文,一跃成为西方探讨东方艺术的重要阵地。韦利也自1917年起,在该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近20篇中国艺术的相关论文,集中呈现了其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和探究。
就个人因缘而言,大英博物馆的工作经历为韦利品评中国艺术品、梳理中国艺术史、引介中国艺术哲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和研究帮助。韦利的继任者、大英博物馆东方图片及绘画分部主任贝西尔·格雷(Basil Gray),就曾撰写《大英博物馆的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at the British Museum”)一文,饱含深情地回顾了韦利在博物馆勤恳工作的十数年。他认为韦利和博物馆互相成就,并各自受到了来自对方的形成性影响(9)Basil Gray. Arthur Waley at the British Museum [M]. Ivan Morris.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 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Ltd., 1970, p.37.,而作为英国最重要的艺术收藏场馆,大英博物馆自19世纪后期便接收了大量来自中国的艺术珍品,极大地充实了其东方艺术馆藏。1903年,被誉为“现存于世最重要的中国绘画品之一”(10)John Hatcher. Laurence Binyon, Poet, Scholar of East and West[M]. Oxford: Clarendon, 1995, p.166.的《女史箴图》入藏大英博物馆的历程,即是中国艺术珍宝在这一时间流散西方的一个历史缩影。因此,如果没有大英博物馆的工作经历,韦利就难以长期保持与中国艺术遗珍的亲密接触,并直接参与到斯坦因考古成果的整理工作之中,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出版《斯坦因爵士敦煌绘画目录》等重要论著。
在大英博物馆工作期间,韦利与对中国文化葆有热忱的同好们共事、交游,使他越来越着迷于挖掘古典中国深厚的文化意蕴。对韦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前辈兼上级——英国著名的远东艺术学者劳伦斯·宾庸(Laurence Binyon)。1910-1912年,在宾庸的精心组织下,大英博物馆在白翼馆举办了中日画展,《女史箴图》和斯坦因刚从中国西域带回的幢幡等是其中的重要展品。为此,1910年宾庸在《伯灵顿杂志》上相继撰文《大英博物馆的中国绘画(一)(二)》介绍了博物馆的中国藏品,并指出中国无疑存在可与西方比肩的真正成熟、伟大的艺术(11)Laurence Binyon. Chinese Painting in the British Museum-I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10(89).。英国著名的现代主义团体“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如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等都曾参观过此次展览。此次展览也深刻启迪了另一位著名的现代主义学者——埃兹拉·庞德(Ezera Pound)及其漩涡主义理论。因此,钱兆明在论著《中国美术与现代主义》中,将1909-1914年称作庞德的“英博时期”(British Museum era),并认为庞德的导师就是劳伦斯·宾庸(12)钱兆明. 中国美术与现代主义[M]. 王凤元、裘禾敏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第3页。。由此可见,宾庸是20世纪初英国中国艺术研究的先驱者,其有关中国艺术的演讲、著述甚至影响了英美现代主义学者,帮助他们从中国艺术中汲取所需的养分,从而完善现代主义审美理念。因此,在这样一位被韦利视作“理想的朋友和领导”(13)Arthur Waley.Introduction to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1962 edition) [M]. Ivan Morris.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 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Ltd., 1970, p.133.的引导和熏陶下,韦利从对东亚艺术知之甚少的年轻研究员迅速成长为中国艺术研究领域的重要专家,韦利之后出版的数部重要论著由宾庸作序,宾庸也从不吝啬对韦利工作的夸奖。1929年,当宾庸继任大英博物馆图片部主任时,还举荐韦利担任东方图片及绘画分部主任,但因韦利于同年辞职而未能如愿(14)冀爱莲. 阿瑟·韦利(1889—1966)汉学年谱[M]. 葛桂录. 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之旅——英国三大汉学家年谱:翟理斯、韦利、霍克斯.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第201页。。
综上所述,韦利的中国艺术研究既离不开特殊的时代背景,又得益于大英博物馆的工作经历,以及与宾庸、弗莱等知识精英的亲密互动和彼此影响。在此背景下刊发的《中国艺术哲学》系列论文,代表了韦利对中国艺术的初期探索,亦开启了他系统研究中国艺术的生涯,对相关论题的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中国艺术哲学》系列论文的主要内容
自1920年至1921年,韦利陆续在《伯灵顿杂志》上发表了共九篇题为《中国艺术哲学》的系列论文,大致按照中国朝代更迭的顺序,依次翻译和介绍了著名的中国画论名家及其代表观点,涉及谢赫(南朝齐梁)、王维和张彦远(唐)、荆浩(唐末五代)、郭熙(北宋)、倪瓒(元),以及董其昌、恽寿平和吴历(明)等,较清晰地勾画出这一时段中国画论发展的脉络。
首篇论文《中国艺术哲学之一:“六法”释义》(15)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 Note on the Six “Methods”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0(213).(“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 Note on the Six ‘Methods’”)发表于1920年12月,集中介绍了南齐谢赫及其重要的中国画论——“六法”。 文章伊始,韦利便强调谢赫“六法”在中国艺术史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它很大程度上为后继艺术批评奠定了基础,因此正确理解它是了解中国艺术的一把钥匙(16)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 Note on the Six “Methods”[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0(213).。随后,韦利将“六法”全部英译而出(17)韦利的译文为:(1)Spirit-harmony-Life's Motion. 气韵生动;(2) Bone-means-use brush. 骨法用笔;(3) According to the object depict its shape.应物象形;(4) According to species apply colour. 随类赋彩;(5) Planning and disposing degrees and places. 经营位置;(6) By handing on and copying to transmit designs.传移摹写。,从而更新了此前冈仓天心、翟理斯、夏德、布歇尔、泷精一、彼得鲁奇等人对这一重要艺术哲学术语的翻译。至于为何如此翻译,韦利在文中也做出了详细解释。他首先将“法”,也就是被他译为“methods”的这一术语,与佛教中的专有术语“Dharma”(18)音译为“达摩”或“达磨”,意译为“法”。具体释义参见:杜继文,黄明信主编. 佛教小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第322页.并置对比,认为二者表达的意义相同。但他又进一步认为“六法”更贴切的解释或为“六个组成部分”(Six Component-Parts),而绝不是六种原则或绘画方式。其次,针对彼得鲁奇在《远东艺术中的自然哲学》一书中强调“六法”所受到的道家学说影响,韦利则补充了谢赫画论中蕴含的儒家哲学,并认为其学说与西方19世纪学院派的艺术观念并没有很大不同。其中,“应物象形”“随类赋彩”指明画家要准确复制所描摹事物的色彩和形式;“经营位置”指最广义的构图;“传移摹写”最具中国特征,强调一件艺术作品必然包括过去的回音,因而,必然是“经典的”(classical)。
韦利把 “气韵生动” “骨法用笔”放在最后,重点探讨了他对“气”(spirit)、“韵”(harmony)、“骨法”(bone work)的理解。对于“气”这个颇具中国哲学意味的概念,韦利引用泷精一将之解释为儒家“天地之气”(spirit of heaven and earth)和《易经》“精气”(subtle spirit)的观点,指出“气”和“道”(way)显然不可完全对等,因为谢赫在品评陆探微时引用的正是《易经》中的评价(19)即《古画品录》中评陆探微“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原句出自郑玄《周易郑注》。。那么何为“气”和“韵”呢?韦利没有对它们分别做过多阐释,而是偏重描述“气韵”动态运用的过程,说道:“这种由气(spirit)推动世界现象发展的过程,就如由竖琴演奏者的手拨动着乐器的琴弦。”(20)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 Note on the Six “Methods”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0(213).在翻译“韵”时,韦利与前人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将“韵”直接译为“节奏、节奏的”(rhythme,rhythmic)等词汇是明显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原文没有设计的对称或“形式”的平衡这样的意思。因此,“气韵生动”指“气”和“韵”的“运作”产生了“生命的律动”(Life's motion),而这一过程是画家所必须呈现的东西。至于“骨法”则可直译为“bone-work”,但“法”在此并不是“规则”的意思,因此彼得鲁奇之前将其解释为“La loi des os au moyen du pinceau”是有误的(21)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 Note on the Six “Methods”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0(213).。最后,韦利也指出“六法”亦是评判一幅画的六个方面,“如果没有第一法,我们应该会断定谢赫有成为彩色摄像师的理想。但是,画家必须(先于其它方面)展示出‘气’(spirit)的运作,[产生]出‘生命的律动’”(22)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 Note on the Six “Methods”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0(213).。由此可见,韦利清楚了解“气韵生动”在“六法”中占据首要地位,且对中国画家的创作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921年1月,韦利发表了第二篇论文《中国艺术哲学之二:王维和张彦远》(23)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I. Wang Wei and Chang Yen-Yüan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1(214).(“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I. Wang Wei and Chang Yen-Yüan”)。在这篇短文中,韦利首先介绍了王维及其山水画论的主要观点,但对他的总体评价并不算高。他在文章伊始便评价道:“早期学者所构建的标准是关于人物画的,而他们的继任者勉强将这一标准移用到山水画上。据此,我们发现了王维,这个唐代山水画的代表画家,阐明了一些一般法则,满足于自己作为自然学者而非出于一个审美学者的恰当观察。”(24)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I. Wang Wei and Chang Yen-Yüan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1(214).为了佐证自己的这一评价,韦利随后翻译了王维《山水诀》《山水论》两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韦利对张彦远的评述则主要集中在对《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源流》《论画山水树石》部分重要内容的译介。1921年3月,《中国艺术哲学之三:荆浩》(25)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II. Ching Hao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1(216).(“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II. Ching Hao”)刊发。在这篇文章中,韦利高度评价了荆浩及其所代表的绘画风格,认为“正是荆浩在10世纪初开创了一种磅礴大气的、印象主义风格的画派,并成为历史悠久的南宗画派的开宗鼻祖”(26)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II.Ching Hao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1(216).。韦利还大段翻译了荆浩《笔法记》中的内容,其中包括绘画的“六要”论、“二病”说。1921年5月和7月,韦利发表了《中国艺术哲学之四:郭熙(一)》(27)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V.Kuo Hsi (Part I)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1(218).(“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V. Kuo Hsi (Part I)”)和《中国艺术哲学之五:郭熙(二)》(28)Arthur Waley.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V. Kuo Hsi (Part II)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1(220).(“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V. Kuo Hsi (Part II)”),从论文的篇幅上就不难看出韦利对这位中国学者的青睐和重视。韦利首先简要介绍了郭熙其人,随后带领读者步入由郭熙撰写的重要画论《林泉高致》)(TheSublimeinLandscapePainting)所构筑的山水世界中,试图挖掘以自然灵动、意境高远为旨趣的山水画,和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内在修为间微妙而令人着迷的关联。他从郭思的序言起,几乎逐句翻译了《林泉高致》的精华部分。后一篇文章是前文的承接,韦利几乎通篇翻译了《林泉高致》的《画意》部分,尤其是准确地翻译了原文中所引用的诗句。不过出色的译者在此仍犯了一个小错误,将杜甫的《客至》标注为《雪》(卢延让)。1921年8月,韦利的第六篇论文《中国艺术哲学之六》(29)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VI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1(221).(“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VI”)刊发,文章主要聚焦宋代画院的发展和画派的特色。他指出宋代的画派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赵孟頫为首的“复古”之风,其复古理论可从《松雪论画》中窥见;另一类是13世纪发展出的佛教和道教隐士们的速写水墨风格(rapid ink-style),在绘画中看到的只是他们转瞬即逝的情绪和狂喜的快速记号(30)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VI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1(221).。与他们风格类似的是所谓的“业余画家”,如倪瓒及其画论《云林论画》。
1921年9月和11月,韦利又陆续发表了第七篇《中国艺术哲学之七:董其昌(一)》(31)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VII. Tung Ch'i-ch'ang (1)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1(222).(“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VII. Tung Ch'i-ch'ang(1)”)和第八篇《中国艺术哲学之八》(32)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VIII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1(224).(“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VIII”),聚焦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前一篇文章伊始,韦利首先对中国和欧洲艺术的分类进行了有趣的对比。他写道:“如今,在欧洲存在两种艺术,一种是面向普通大众的艺术,另一种则面向被赋予艺术敏感度的少数人。”(33)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VII. Tung Ch'i-ch'ang (1)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1(222).而前一种艺术必须与其它艺术门类混杂起来才能被普罗大众所接受,戏剧在西方的流行正得益于此。虽然中国艺术也存在类似的分类,但中国的普通人比西方更容易接受“纯艺术”,音乐领域、文学领域皆是如此。因此,大多数中国人也可接受并懂得欣赏中国经典诗歌。其后,韦利简要介绍了董其昌在明代的声望和成就,并整段翻译了董其昌的《画旨》,还在文中提到了董其昌一直期待寻得一幅王维的真迹,但他的发现并不比现代人更多。而韦利在本文的脚注中指出,一幅由赵孟頫临摹王维《辋川图》的副本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宾庸曾在《大英博物馆的中国绘画(一)》一文中提及这幅画。
后一篇文章则承接前文,韦利以董其昌在船上无意中用手撞到张布的帆竹从而悟道的逸事,证明董其昌不仅如人们所期待的是正统的儒家学者,更在初年便已潜心禅学,甚至曾将利玛窦的评述与禅宗的要义相比较,展现出对基督教的了解(34)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VIII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1(224).。然而,在论及绘画时,董其昌便收回友好、开放的目光,坚守其形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主张。为证明这一点,韦利接着详细选译了《画旨》《画诀》《画源》等经典篇目的精华部分,让读者得以窥见董其昌的画论理念,例如其对文人画的推崇,对精雕细琢画风的摒弃,以及对前代绘画名家的评点等。
1921年12月,韦利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中国艺术哲学之九:结论》(35)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X(Concluded)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1(225).(“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X. (Concluded)”)。作为系列论文的最终章,韦利介绍了明代画家恽寿平、吴历的艺术成就,并对中国艺术哲学进行总结性评述。在韦利看来,别号南山的画家恽寿平,世人皆知其过着典范生活,有着高尚品格,算得上是中国、日本所有现代花鸟绘画之父,他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恽寿平重忠实描摹,而众所周知,那些持“所绘即所见”观念的画家更有可能比那些“皆以不似为妙”的画家达成更高的艺术成就(36)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X(Concluded)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1(225).。另一位是与恽寿平同期的画家吴历,韦利以吴历的生平经历和画论为例,阐述了当时中西艺术间的融合与影响。吴历曾与天主教徒交游甚密,并于1861年打算与比利时籍传教士柏应理一同前往罗马,但最终在澳门待了6年。也正因为此,吴历习得一些西洋艺术的诀窍,并将之与中国画相较,写道:“我之画不取形似,不落窠臼,谓之神逸;彼全以阴阳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工夫。即款识,我之题上,彼之识下。”(37)吴历. 墨井画跋[M]. 沈子丞. 历代论画名著汇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第133页。这点明中国画不以忠实描摹实物为旨归,而意在捕捉所画对象的神采和韵致,抒发画家个人情趣;西洋画则注重运用焦点透视、明暗技法等技法,意在栩栩如生地描摹实物,这是中西绘画理论和审美标准最大的区别。
在评述中国艺术哲学的特征时,韦利显然对中国艺术哲学所体现出的精妙、飘逸但难以言明的独特魅力有所感知,但又感到迷惑。因此,他做出如下评判:“中国艺术学者从未发展出一种理性的思想脉络,也没有寻求创造一种系统的艺术哲学。他们满足于随性的观察、交谈、逸事和观点。”(38)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X(Concluded)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1(225).这就让他在试图厘清文献、翻译原文和深入阐发观点时,陷入无法构建理性框架、梳理“凌乱”文献的困境。
随后,韦利将目光投向中国艺术与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关联。他引用了当时还未出版的《禅宗与艺术之关联》(1922)中的论述阐发艺术与禅宗无可分割的关联:“艺术被视作一种禅,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潜入佛陀,正如本杰明把约瑟夫的杯子放在麻布口袋里一样。通过禅,我们可以湮灭时间,并且看到宇宙不是分裂成无数的碎片,而是最初的统一体。”(39)Arthur Waley. Zen Buddhism and Its Relation to Art [M]. London: LUZAC,1922, p.21.自12世纪以降,中国文化已经越来越受到禅的浸润,即使是最纯粹的世俗艺术作家有关艺术的作品中也出现了禅宗的术语。然而,禅画这种在美酒、茗茶或自我催眠的激励下创作出的水墨速写,从未在中国受到重视。但它在移植日本之后获得了蓬勃发展,熟练的作画往往取代了灵感的迸发(40)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X(Concluded)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1(225).。由此可见,韦利早就关注到了中国绘画中独特的类别——禅画,并对其最终在日本大放异彩,且对日本绘画产生深远影响的历程颇为熟悉。他在1922年出版的《禅宗与艺术之关联》,正是对这一论题的集中阐释,也是西方了解和研究中日禅画的重要参考文献。
以上就是《中国艺术哲学》系列论文的基本内容。随着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愈来愈深入、全面,他将系列论文进行修改、完善及补充,纳入在1923年9月出版的代表论著《中国绘画研究概论》之中,从而充实了西方的中国艺术研究。
三、韦利中国艺术哲学研究的特色与影响
作为典型的学者型汉学家,韦利的中国艺术哲学研究严谨细致,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对侪辈和后辈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我们回顾《中国艺术哲学》系列论文的基本内容,不难发现韦利中国艺术研究的第一个突出特色即注重忠实翻译原文。韦利选译了大量重要的中国画论篇目,如谢赫《古画品录》、王维《山水诀》《山水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荆浩《笔法记》、郭熙《林泉高致》、赵孟頫《松雪论画》、倪瓒《云林论画》、王履《华山图序》、董其昌《画旨》《画诀》等,将中国艺术哲学以准确、流畅的英译文直接呈现给读者,不仅减少使用非一手资料所造成的误解,还为无法自如阅读中文文献的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持。这主要得益于韦利的语言天赋。在入职大英博物馆之前,韦利就已熟练掌握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荷兰语等多种语言,显示出极高的语言天赋(41)Basil Gray. Arthur Waley at the British Museum [A].Ed. Ivan Morris.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C].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Ltd., 1970, p.39.。自1913年入职大英博物馆后,出于工作和研究需要,韦利开始自学中文和日文,并很快运用自如,1916年便已自费刊印了首部汉诗译作《中国诗歌》(ChinesePoems)。出色的中文阅读能力无疑为他进行中国文化译介和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此外,韦利也匡正了现存译文的错译、误译,并进行重译,以保证原文的本意不被曲解。例如,在介绍郭熙及其画论《林泉高致》时,韦利便指出费诺罗萨在《中日艺术的源流》一书中的翻译主要来自其日本朋友的译介,但其中一些翻译极为错误,某些地方甚为荒谬。郭熙那些看上去在探讨花卉画的句子,被费诺罗萨弄得支离破碎,因为他是从日本的英译本中摘录这些句子的(42)Arthur Waley. 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IV.Kuo Hsi (Part I) [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1(218).。韦利在此指出了西方中国艺术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即主要依赖由日本人翻译的英译本,甚至习惯于透过日本学者的研究来审视中国艺术。事实上,自19世纪中叶起,日本版画在西方获得广泛喜爱和接受,此时的中国艺术却遭遇了在西方长达一个世纪的回落,其背后的原因既包括日本艺术恰好满足西方革新绘画传统理论和技法的需求,也包括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时代背景,以及西方对中国、中国文化一概贬低的总体倾向。无论如何,“在19至20世纪的一二百年间,西方人并非全然将中国艺术作为独立范畴来理解,而是作为远东艺术中的一类看待”(43)施锜. 19至20世纪西方鉴藏与研究视野中的中日绘画[J]. 艺术探索,2019(3)。。就中国艺术研究而言,日本学者也是较早英译中国画论,并将中国艺术理论介绍到西方的重要力量。正如邵宏所说:“中国古代画论被迻译成欧美书面语在西方传播肇始于1903年。”(44)邵宏. 东西美术互释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第213页。1903年,冈仓天心的代表作《东洋的理想》(TheIdealoftheEast)一经出版,便受到西方学界的瞩目,其中关于中国艺术的论述对宾庸、费诺罗萨等西方汉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创刊于1889年,着眼于东亚美术研究的日本著名美术杂志《国华》,又于1905年7月刊行其英文版TheKokka,成为西方了解中国艺术的重要中介。包括冈仓天心、泷精一、内藤湖南在内的日本学者,以及费诺罗萨等西方学者在该刊上发表了众多中国艺术相关的文章,且多数论文皆为日英双语,扩大了日本学者的影响力,并间接助推了中国艺术哲学在西方的早期传播。因此,邵宏在《中国画学域外传播考略》中写道:“在讨论中国画学的域外传播这一论题时,我们有必要大致地了解汉字及其承载的汉籍传播,以及由此在20世纪之前所构成的汉字文化圈。因为此前中国画学在这文化圈内的传播及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西语传播,都是以这个汉字文化圈所共享的艺术理论为文本基础的。”(45)邵宏. 中国画学域外传播考略[J]. 中国美术学院学报, 2009(1)。在此背景之下,西方的中国艺术研究无可避免地受到日本学者的英译本和研究观点的影响。因此,在评论《中国艺术研究概论》时,苏立文曾颇为遗憾地说道:“当然,韦利的这本书有其局限性。当他在写作此书时,几乎没有见过任何有质量的中国绘画。他从未身处远东,也从未见过出现在美国的重要藏品,尤其是弗利尔和波士顿美术馆的藏品。几乎所有他能接触到的材料都来自于平庸乏味的伦敦展览,或者出自日本期刊的复制件,例如《国华》等。”(46)Michael Sullivan. Reaching Out [A].Ed. Ivan Morris.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C].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Ltd., 1970, p.108.但不管怎样,韦利通过一手文献对中国画论篇目进行英译的实践,对前期研究存在的错译、误译等问题的纠正,以及对相关史实的梳理和介绍,事实上开启了西方学者直接接受、论述中国艺术哲学的历程。
韦利中国艺术哲学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色是注重将不同时期的中国艺术名家及其画论置于中国历史、思想史、哲学史的框架内予以阐释,不仅清晰呈现中国古典艺术发展的脉络和阶段性成果,还将其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广阔图景紧密融合,显示出韦利深厚的中国文化研究功底。例如,在第二篇介绍王维的文章中,韦利就明确指出其绘画与禅宗之关联,并在《中国绘画研究概论》中具体展开论析。以《王维和水墨画》为例,他首先介绍了王维的乐曲创作,并翻译了其诗作《阳关三叠》《菩提寺禁裴迪》,评价道:“王维是第一个既是伟大的诗人又是伟大的画家的人。他的诗歌反应了其天性的绝佳平衡。”(47)Arthur Wale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M]. New York: Grove Press,Inc., 1958, p.143.随后,韦利又将王维与李白、杜甫相比较,指出王维的诗歌技法纯熟,更具沉思、更加私人化,也不像李白的诗歌那么抒情。同时,他完全丧失了杜甫对政治的热情。接着,韦利从“摩诘”之名入手介绍了王维与禅宗的关系,并解读了佛教术语“色”。他还认为西方学者因误解而滥用了评价王维诗画的“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这一名言出自苏东坡对王维某一幅画,而非全部画作的评价,因此用它来总体概括王维诗画并不恰当。在探讨王维绘画风格的变迁之后,韦利颇具新意地将中国白描画的发展阶段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阶段相对应,认为王维的泼墨画对应着莎士比亚创作晚期无拘无束的风格;而将各种阶段的白描画风格熔于一炉的正是16世纪伟大的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董其昌(48)Arthur Wale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M]. New York: Grove Press,Inc., 1958, pp.147-149.。由此,韦利以王维的诗画创作串联起中国水墨画、白描画的发展阶段,并将中国悠久的诗画传统呈现给读者,解释了其相互依存、影响、转化的特征和表现。
诚然,韦利的学院派批评方法透露出他身为学者型汉学家的严谨的学术态度、扎实的学术素养和注重考据的学术倾向,从而成为西方以科学探究的态度,从考古学、民族学角度切入,对中国艺术进行科学溯源、辨析和论述的代表学者。彼时,《伯灵顿杂志》所刊登的文章大致存在两种研究倾向,一是将中国艺术吸收或纳入现代主义美学框架中,着眼挖掘中国艺术独特的形式之美和审美意味,尤以罗杰·弗莱和克莱夫·贝尔为代表;一是对中国艺术做“科学研究”,注重厘清“中国艺术的起源、分类、属性、民族志内容和历史背景”(49)Ralph Parfect. Roger Fly,Chinese Art and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A].Ed.Anne Witchard. British Modernism and Chinoiserie[C].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p.56.,代表则为韦利及其撰写的《中国艺术哲学》系列论文。两种不同的研究立场同时出现在《伯灵顿杂志》上,不仅帮助读者从“审美”和“科学”两种视角拓展对中国艺术的理解,也证明《伯灵顿杂志》在20世纪初为西方学者探寻中国艺术研究新途、交流研究心得、分享研究发现提供了重要阵地。
尽管弗莱和韦利探究中国艺术的视角并不相同,但韦利的中国艺术哲学研究,尤其是对谢赫“六法”的重新翻译,为弗莱的现代主义美学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不同于其他学者对“六法”的阐述,他在译介“气韵生动”时格外强调“气”(sprit)、“韵”(harmony)相协同运作,进而产生“生命的律动”(Life’s motion)的动态过程,由此揭示了充盈中国绘画的丰富、灵动、深刻的精神性元素。这一观点与弗莱及其所倡导的现代主义美学对人的“精神”“情感”的呼吁相契合,并引导弗莱从中“捕捉到了中国艺术美学讲求以简劲有力的线条勾勒,以唤起生命的律动感的精髓,与西方诗歌与音乐艺术传统中的节奏感结合到一起,发展出了对‘韵律’(rhythm)的独到追求,要求无论是语言文字艺术还是视觉艺术中的韵律,都要与人的生命节奏、人的情感变化同构对应,以表达人的心灵的律动”(50)杨莉馨,白薇臻. 论汉学家之于英美现代主义运动的意义——以阿瑟·韦利为例[J]. 中国比较文学,2020(4),第112页。。
诚如美国学者J.J.克拉克所言:“中国的思想及文化,一向被忽略甚至被蔑视,在西方浪漫主义时代衰落之后,再次重现光彩,这是由于阿瑟·魏理着手翻译的系列中国古诗被介绍进来。这些诗不仅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现代诗人,如叶芝和庞德,而且也赢得了西方学者和哲学家的再次青睐。”(51)J.J.克拉克. 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M]. 于闽梅、曾祥波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144页。事实上,韦利对中国艺术哲学的探究,同样将一个迥异于西方但又意蕴无穷的东方美学世界呈现给西方社会。当遮蔽的面纱被掀起,西方学者才惊异地发现,自己苦苦追寻的现代主义美学原则,原来早就蕴含在古典优雅的中国艺术之中。从此意义而言,韦利对中国艺术哲学的阐释有其深远的影响,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