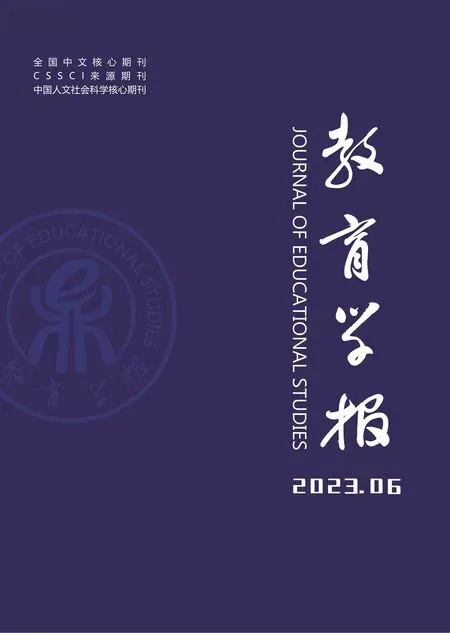孔子教师形象的欧洲汉学建构
杜 钢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37)
所谓汉学(Sinology),学界通行的一般观点即是指外国学者对中国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中国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哲学、宗教、文艺、语言、文字、文化与教育等诸方面问题所进行的研究。欧洲汉学乃是世界汉学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研究则历来是欧洲汉学研究中的一大要题,而孔子教育问题特别是孔子教师问题又是欧洲汉学孔子研究的重中之重问题所在。克实而论,欧洲汉学中的孔子教师形象是在一种历史建构的进程中形成和变化的。本文重点对欧洲汉学对孔子教师形象数百年的建构历程展开深入解读和分析,以期探明和揭示这一建构历程的演化表征与特质,并对其当下及未来发展变迁中的价值发掘和运用等问题进行审视和展望。
一、传教士汉学对孔子教师形象的原初建构与孔子学说西传
欧洲汉学的孔子研究肇端于十六世纪末的传教士汉学研究,迄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而欧洲汉学对孔子教师形象的原初建构也便始自于传教士汉学的孔子研究。1582年,作为西方对华传教活动的主要开创者和核心人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此后直至1610年去世,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从未离开过中国。利玛窦将孔子视作中国哲学家中最著名的一位,并对孔子通过著述、授徒和身教等方式来激励民众追求道德的行为表现印象颇为深刻。在其看来,孔子凭借自身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而塑成的道德榜样形象,在中国民众眼中远比其他国家的德高望重者们更具神圣色彩。而与其他异教哲学家相比,孔子这位中国的“圣哲之师”非但毫不逊色,反而超过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1]104利玛窦深知,孔子在中国士人群体中所受尊敬程度之高是超乎寻常的,其权威性是不容置疑和挑战的,而中国历代政府所给予孔子及其家族后裔的尊崇和恩荣亦是至高无上和无以复加的。[1]31-32基于此,利玛窦所采用的乃是一种相对随顺与务实的孔子研究方略和范式。艾田蒲(Rene Etiemble)认为,利玛窦为了说服中国人信仰基督教,不得不采用在外表上适应中国人的习俗与行为方式的灵活路线来传教,而利玛窦于中所做的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儒教主要人物孔子往自己的观点立场上拉,并以对自己传教有利的方式对孔子著作中一些模棱两可的东西做了解释。[2]241-242艾田蒲对利玛窦所做孔子研究的批判意见虽然自有其道理所在,但仍可说,正是基于对中国别具一格的历史传统与具体国情以及孔子于中所扮独一无二角色的深刻了解和洞察,利玛窦在对孔子教师形象进行建构时,尽管终极目的从未离开过服务自身宗教利益的价值取向所需,但在实际操作上,其所采用的则是一种灵活机动的对中国儒家文化的随顺和宽容方式,而非泥古不化地按照自身的宗教信仰和价值取向来一味盲目行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牵强附会地对孔子教师形象进行宗教意向上的过度解读状况的发生。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看似谦顺务实地对待儒家和孔子的传教姿态及其相应施为,并不能全然代表和统一来华传教士内部的所有意见,这种意见分歧也终于在来华传教士内部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1610年,利玛窦去世,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取代了其在华传教的领导地位,进而将利玛窦在世时便已显露端倪的“礼仪之争”问题进一步明面化和扩大化。“礼仪之争”所关涉的焦点问题即在于,中国基督教徒究竟还能否参加诸如祭天、敬祖和祀孔等本土传统礼仪活动,耶稣会士内部对此问题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利玛窦一派对此采取的是相对宽容的允许态度,但龙华民一派则对此持相左意见,明确反对中国基督教徒参加诸如此类的传统礼仪活动,两派之间也由此展开了一系列激烈论争。“礼仪之争”的事态不断扩大,1643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Morales)将利玛窦一派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过程中宽待和随顺中国传统礼仪的问题向梵蒂冈教廷上报,由此也引发了西方宗教界和中国政治界最高领导层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Innocent X)发布了宣告祭祖祀孔等为“异端”行为的通谕,禁止中国教徒参加诸如此类的传统礼仪活动,清康熙帝则在多次派使节与教皇就取消此一禁令的问题反复协调斡旋未果之下,开始制定禁教政策,雍正元年(1723年)这一禁教政策正式颁布实施,并一直延续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方才有所放松。
正是在“礼仪之争”的独特背景下,经由传教士的驱动和传布,孔子思想学说也开启了西传之旅,其意义和影响较之耶稣会士在中国本土所做的孔子研究活动更加深远和重大,由此所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传教士汉学孔子研究的接续而起,而这样一种转变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欧洲汉学对孔子教师形象建构的从服务于来华传教价值取向转为服务于欧洲思想启蒙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变化过程。1687年,《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us)一书在欧洲出版,该书由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与殷铎泽((Intercetta)等数位耶稣会士共同完成。全书内容主要包括一篇序言以及《孔子传》《大学》《中庸》与《论语》等的译文。该书中的《孔子传》一文由殷铎泽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译出,在这篇《孔子传》中,作者删去了其中一切可能将孔子误视为神的情节,而只强调孔子是学问家、教育家的一面。作者称赞孔子的声誉随时间之流逝而愈发显赫,达到了人类智慧所能企及之顶峰。并且,孔子以其个人具体体现了其著作及讲学中所宣讲之道德规范,以致于中国人至今仍视其为大师及帝国最具权威之学者。[3]68-70龙伯格(Knud Lundback)在谈到该书的影响时指出,孔子的形象由此书首次传到欧洲,并且在书中孔子被描绘成了一位全面的伦理学家。书中认为孔子的伦理和自然神学统治着中国,这样的写作逻辑也便支持了耶稣会士们对于归化中国人信教的希望。[4]艾田蒲对《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之于孔子学说西传欧洲所产生影响的评价意见则依旧保持着自己的一贯立场,他指出,尽管《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在欧洲的出版确实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也开启了欧洲思想界对孔子其人其说产生误导的先河。[2]208-209
总体来看,无论“礼仪之争”中不同传教士派别之间所持意见的相互龃龉程度究竟如何,在服务于来华传教这一价值取向方面,其实并无本质差异。“礼仪之争”对十七、十八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中可以看到以基督教文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西方文化在面对以儒家文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国文化时,彼此之间基于各自文化特质的差异在交流互动上所必然发生的碰撞与博弈,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势下,基督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开始大力推动中国思想文化西传的进程,欧洲思想界逐渐兴起了持续不断的“中国热”,而对以孔子学说为典型组成部分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关注则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的鲜明思想标志,欧洲汉学对孔子教师形象的建构也由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二、欧洲启蒙思想家对孔子教师形象建构的推进与深化
如若将十六世纪末的来华耶稣会士视作欧洲汉学对孔子教师形象建构的开路先锋的话,那么,伴随着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和演进而涌现出的一众欧洲启蒙思想家则是一股创进力量,其对孔子教师形象的建构是在耶稣会士基础上的推进与深化。
伏尔泰(Voltaire)称得上是欧洲启蒙思想家中在对孔子教师形象及其学说研究问题上关切度最高、影响力最大、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一位。就像艾田蒲所说的那样,伏尔泰身处那个世纪的中心,是最活跃、最惹是生非的人物,也是个最固执的“中国迷”。那个时代人们所关注的所有问题,以及当时人们认为参照中国即可解决的一切问题,伏尔泰无一不在其著作中提出。[2]201对于造成这一状况的深层原因,艾田蒲认为,那时的中国是时尚,任何有思想的人都必定参考有关中国历史、风俗和思想的发现。那又为什么偏要这位以其独特方式充当时代的“响亮回声”的伏尔泰,对其所处社会环境中那些有关中国的事情闭目塞听、不闻不问呢?[2]202此可谓明见,在那个欧洲思想界竞相以探讨中国思想为时尚的启蒙时代,像伏尔泰这样一位吹响着启蒙时代思想号角的中心人物,当然不会置身事外。伏尔泰说道:“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毫无迷信,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5]331又说:“西方的民族能够用什么格言什么规则来反对这样纯洁完美的道德呢?孔夫子在多少地方要人谦逊哪!如若大家都实践这种美德,人世上也就永不会有争吵了。”[5]282伏尔泰将孔子之律法得以施行的时代,视作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并认定孔子所享有的一切荣誉,并非是神的荣誉,因为神的荣誉谁也无法享有,孔子的荣誉实际上是一个人由于在神明的问题上,提出了人类理性所能形成的最圣洁的看法而受之无愧的荣誉。[6]253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时代,像伏尔泰这样的启蒙思想家,所追寻的既非神权掌控下的宗教道德,亦非君权专制下的封建道德,而是可以满足民众现实人权所需的世俗道德,这种世俗道德重在彰显人性的朴素光辉与呼唤理性的自然力量,并能够与普罗大众的现实生活有机结合,而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恰恰具备这样的特质,由此,伏尔泰对于孔子其人其说的向往与信从,也便是自然而然的了。伏尔泰指明,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孔子的弟子有数千计之多,他本可以成为强大的党派的领袖,但他宁愿来教育人,而不愿去统治人。[6]88而且,孔子也决不愿意说谎,并且从来不说自己有什么灵感,也决不宣扬一种新宗教,更不借助于什么威望。孔子根本不奉承他那时代的当朝皇帝,甚至都不谈论他。总之,孔子是举世唯一的一位不让妇女追随他的教师。[5]322伏尔泰视孔子为“理性之友、狂热之敌”,并对孔子所具的道德本位教师形象大加赞叹与推崇,这客观上虽是顺应启蒙时代历史潮流发展的必然选择,但主观上亦是伏尔泰本人与孔子之间深有精神投契的自然反映,诚可谓东圣西哲遥相呼应、千古同风。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将人类社会最大痛苦的根源归之于人类相互之间和平秩序的失守,在“人与人相互为狼”的现实情形逼迫之下,人类原本饱受自然灾害侵扰的艰辛处境则变得愈加苦难深重。莱布尼茨认定,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找到了更好地拯救人类苦难的解决之道。[7]莱布尼茨致读者:2-3莱布尼茨揭示和肯定了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所独具的特质与价值所在,但仍可看到,在莱布尼茨的思想本位上,其还是认定西方基督教文化乃是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莱布尼茨主张传教士应该为一切人而行一切事,并认为中国人对孔子的崇拜似乎并没有任何宗教崇拜的意味。由此,他对于耶稣会士通过随顺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方式来传教的行为乃是持赞同意见的,并强调耶稣会士的努力和功绩即便是在那些敌视他们的人们那里,也是需要得到承认的。[7]莱布尼茨致读者:61700年,莱布尼茨在致维利乌斯的信中写下了著名的《论尊孔的风俗》一文,其中就对“礼仪之争”中的最核心问题,即祭孔问题做了明确表态,指出其在给《中国近事》作序时,就相信中国文人的尊孔主要是一种民间礼俗而不是宗教礼仪。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收到一些反对派也许出于善意发表的著述,但他对此一直未予苟同。令人费解的是,莱布尼茨似乎同时也赋予了孔子形象以某种程度上的基督教宗教色彩,即如艾田蒲所言:“每当莱布尼茨提到孔夫子,他总是缩小基督教义与这位中国哲人的思想之间的差异。”[2]425事实确乎如此,莱布尼茨在针对龙华民指责中国古人和时人都是无神论者这一点所做的回应中,便曾结合其对孔子思想的解读表明了自己的这一调和取向主张。他强调,孔子认为天神、四时之神、山川之神以及其他无生命的东西的神等崇拜对象即是至上神、上帝、太极、理。实际上,莱布尼茨更加愿意孔子能阐明自己的宗教观点,但他也明白这种不探究鬼神的性质和活动方式不一定使人成为无神论者,因为在基督教中肯定也可以发现这种对鬼神和自然的不感兴趣。[8]在欧洲启蒙思想家所做的中国文化以及孔子研究中,艾田蒲对莱布尼茨的思想主张持有明确的赞赏和认可。就莱布尼茨本人而言,他是赞成耶稣会士对孔子其人其说的解读主张的,但有所蹊跷的是,这种赞成的态度在艾田蒲那里,反倒并未成为其对莱布尼茨的观点持有肯定式评价意见的阻碍。艾田蒲认为莱布尼茨一生都未失去在对中国游戏进行思考时的宽宏热情和清醒头脑,他始终坚信不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立起“光明的交流”。艾田蒲确认,在1700年前后关注中国的人之中,莱布尼茨无疑是最了解实情、最公平合理的一个,他的著作也是唯一一部我们今天还可以阅读的著作。[2]385
与莱布尼茨同为德国启蒙思想家代表人物的沃尔弗(Christian Wolf),对孔子教师形象的建构主张亦有其独特之处,具体包括如下几点。 其一,孔子所处的时代,中国正处于一派混乱不堪的景象之中。据此,沃氏强调,孔子的出现具有应时而起的天命所授性,孔子乃是以天命所系的道德君、大学士和先知先生等形象示现于世的。 其二,孔子未能做到政治上的得位行道,他本人并不处在君王之位,也便难以对国家治理的种种乱象进行有效干预和纠正,但他非常注意尽自己最大努力履行一位师长应尽的职责,因此,他尽管无法做到己欲之事,但却做到了尽力而为,无一遗漏地完成了理性要求他为尽职耀职所必须做的一切事情。孔子投身文教事业,并在自身的教师生涯中将中国传统治国理政与思想学术之智慧与精华教授给弟子门人,使之流传后世。 其三,孔子在中国人心目中所得到的尊崇程度历来便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崇尚孔子的程度不亚于犹太人之于摩西、土耳其人之于穆罕默德、德国人之于耶稣基督。尽管如此,沃氏依然认定,事实上,孔子并没有做到使廉洁朝政、敦厚风尚之花在中国常开不败,这是因为在孔子的生前死后,在一个世道多变的中国,历代帝王、师长乃至百姓在依循和践行孔子的主张和教诲方面,或是走上歧途,或是因缺乏孔子的那种理智和敏锐而永远也达不到这位伟大哲人的学说所具有的深度和广度,或是在行为举止上与谨小慎微的先师孔子的教诲相去甚远。[9]
艾田蒲认为,无论是十八世纪的培尔(Bayle)、孟德斯鸠(Montesquieu)、伏尔泰,还是杜尔阁(Turgot),这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对在中国发生的、思考的一切了解都很不正确。这是因为在无人或几乎无人懂得中文的情况下,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完全依靠多明我会或方济各会,特别是耶稣会士们有趣而有益的书信以及他们的回忆录和译作来进行。[2]183在艾田蒲看来,这种状况的形成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启蒙思想家自身偏见的影响所致,但更多还是他们受到了传教士的主观刻意误导,以及没有课本、拼音表、语法和字典等其他一些客观不利条件所限造成的,因此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2]195相较而言,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的主张则体现出与艾田蒲迥然相异的特点,他说道:“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通过耶稣会教士的翻译了解了中国思想后惊讶地发现,中国思想和他们的思想多么接近。然而难以理解的是,当他们如此努力地要抛开教条主义的信仰,而达到符合理性的伦理世界观,并努力地要在自己的时代实现它的时候,孔子及其后来者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实现了。”[10]98又说:“莱布尼茨、克利斯蒂安·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他们的同时代人和孔子的学说如此接近,因为他们自己也有着和孔子一样的信念。在他们生活的启蒙时代也终于达到了这样的伦理信念。”[10]108史氏认定,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立场和价值取向与孔子是有着天然相合的共同意趣的,这也使得他们在对孔子其人其说进行解读和阐释时,也便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某种与孔子学说“志同道合”式的思想表征。克实而论,启蒙思想家对于理性精神指导下的具有充分的道德反思能力与道德实践能力的自由人的养成是格外重视的,启蒙思想家这样的思想价值取向与孔子思想学说之间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天然契合性的,启蒙思想家对于孔子道德学说的偏爱,绝非是由于受耶稣会士思想主张下的误导所致,实质上乃是启蒙思想家进行思想自主选择的结果,而由此角度出发来审视和辨析启蒙思想家对孔子教师形象建构的本质特色方是正途所在。
三、现当代欧洲汉学对孔子教师形象建构的返本还原
当探讨关乎欧洲汉学对孔子教师形象建构的问题时,尤为重要的一点即在于能否有效还原孔子教师形象的真貌,这种诉诸于对孔子教师形象建构的返本还原的价值取向在十九、二十世纪以来的现当代欧洲汉学中更加凸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价值取向变化有助于跳脱出传教士和启蒙思想家基于宗教和启蒙取向上对孔子教师形象进行建构时的边界限定,而可以更多地从孔子其人其说之于世界思想文化整体发展演变进程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深远意义出发,来对孔子教师形象进行更具本真性和建设性的建构与呈现。
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虽对《论语》内容的全真性存有怀疑,但他依然认定通过《论语》来对孔子的形象加以解读是一种方便之举。他指出,《论语》中的孔子是一位在政治上志趣难酬,但却在教育上大获成功的为众多弟子所簇拥追随的精神导师形象,而且孔子的教学内容非常丰富,远超出当时一般性的教学课程内容范畴之外。[11]12同时,在葛氏看来,尽管《论语》中的孔子是一位教师,但孔子在其身后的若干世纪里首先是被看作一位伟人式的先行者,于是也便不可避免地成了后人不断添枝加叶的传奇的中心。[11]11在此种情形之下,对孔子思想特质的解读也便会屡遭曲解和误读。朴赖斯(Jonathan Price)认为,当人们试图将孔子的思想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有机的理论体系时,就可能导致对孔子不同思想主张的扬此抑彼现象的出现,从而形成一种在对孔子思想特质阐释中的矛盾重重的状况,以致于无法展现和揭示孔子思想特质的全貌和真貌,他强调,出现这种情况多因诠释者掺杂了自己的观点而非孔子本人的原意。[12]296-297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指出,汉代时期,国家权力与儒家学派实现了联姻和结盟,国家权力也便借助儒家精神获得了思想上的权威地位,受此影响,儒家学说成为了训练官员的工具。学派的体系成为了国家设置的教育体系,其目的是传授对国家制度整治与尊崇的学说。然而,此种时代情势的巨大变化,就其产生的动机和情形,对孔子本人来讲有些都是陌生的。由此可以推见,整个中国儒家思想的漫长演变过程实质上也便与孔子自身的根本思想之间有所出入和不同了。[13]150可见,不仅是学者们个人意见的掺杂会使得孔子思想特质的展现令人难辨真假,某些历史时期,国家权力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使得孔子思想特质的展现变得模糊不清。雅氏又指出,孔子的性格乐天知命、开放、自然。他是一个市井中人,也有他的弱点。孔子拒绝对他个人的任何神化,他只希望自己是一个人,因为他知道自己从来就不是圣人,但最终还是被奉为了神明,这真是一个令人深思的发展。[13]145-153需要指明的是,这种对于孔子形象和学说臆造添加的情况,不仅出现在中国本土,在西方学界,也亦非罕见。谢和耐(Jacques Gernet)便曾指出,“孔夫子主义”(Confucianisme,儒教)一词是西方人生造杜撰出来的,其范畴明显远超出孔子这位大圣人本人的思想范畴之外。[14]74此外,在雅斯贝尔斯那里,其对于真实孔子形象的解析,似乎是体现出颇为复杂矛盾的思绪状态。雅氏的这种看似复杂矛盾的思绪状态,实质上是强调在对孔子形象进行如实解读时要有所甄别和取舍。一方面,对于历史上关乎孔子形象的种种似是而非的状况,雅氏是明确主张要予以摒弃的,他认为,透过层层变化的传说想要描绘出历史上的孔子形象,似乎是不太可能的。[13]112-113另一方面,对于诸如《论语》中能够确认的来自孔子本人所提供的篇章丰富的原文资料,尽管在细节上仍有诸多不确定之处,雅氏则提示要对其加以充分利用,并确信是可以从中描绘和获得一个符合历史真实性的孔子的。[13]145孔子思想特质的形成有其自然的历史因果脉路,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道德社会的维系已然瓦解,道德教化和道德弘扬则成为恢复礼乐秩序的必然选择,孔子的思想前提正源于此。森格哈斯(Dieter Senghaas)即从这样的思想逻辑出发,将孔子定位为一个明理的现实主义者,这是孔子给人的一种基本印象,其思想主张是以正名和复礼为主要诉求的,并以此为实际行为指明正确和有效的方向。[15]而在谢和耐看来,孔子是将道德视作个人努力的结果,而并非贵族所专有的固定品质。孔子所倡导的是一种以德配位的思想主张,在这一主张之下,君子之位已不再是贵族世代相袭的专属品,而是要凭此来构建和实现个人修养与公共利益的等同关系。[14]74-75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孔子教师形象的真貌是含藏于其思想特质之中的,对孔子教师形象的还原应当是以揭示孔子思想特质的真相为前提的。葛瑞汉指出,诸如孔子等先秦诸子所全部思考的问题并不是西方哲学中的真理是什么的问题,而是道在哪里的问题,这个道就是规范国家与指导个人生活的道。[11]4朴赖斯也指出,孔子仅仅是一个想改变自己人生和周围社会的人。[12]183雅斯贝尔斯亦认为,孔子的关注点是人类及其所处的世界,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孔子在本质上所关心的都是人类及其社会。[13]130谢和耐也强调,孔子所关注的并不是一种关于人的抽象科学,而是囊括了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一种人生艺术。[14]75综上可说,解读孔子思想特质的必要理路要置放在一种人文主义视角下的世俗社会情境之中来展开,超脱于现实社会与世俗生活的纯粹致力于精神愉悦或形而上式的真理探求的思想特质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是无从寻觅的,抓住这一思想逻辑要点,才有可能实现对孔子教师形象及其学说解读和分析的返本还原。
朴赖斯认为,孔子是中国的第一位“职业”教师,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他首开先河,将课堂向任何人开放,而不论地位,不管能否交得起学费。[12]129朴氏强调,孔子天生就是当教师的材料,有人曾把他誉为举世闻名的哲学家或者圣人,其实这都是错误的,他既不是什么哲学家,也不是什么圣人,他本人也未曾承认过这些头衔,但他的确是有史以来举世无双的、最伟大的教师。[12]177朴氏将孔子之路视作是一条仁慈之路,并认为孔子从未强调创造这种理念就是为了迫使人们去探索和遵循。[12]349在朴氏看来,弟子们之所以衷心拥戴孔子,且永远不能把他忘记的理由,正是因为孔子唱响的是人们的心曲,而非不着边际的虚空说教。[12]180这体现出孔子的教师形象乃是构筑在自我道德实践本位的基础之上,而这一基础又是通过孔子本人以身作则和知行合一的方式来加以奠定的,这可以视作孔子教师形象本原面貌的核心表征所在。雅斯贝尔斯认为,孔子的学习并不仅仅是学习关于什么的知识,而是成为自己的知识,其目的是获得真理之道,而通过学习来获得真理之道的具体方式并不是要熟记它们,而是要从内心去领悟,从外部去实现。雅氏指明,在孔子那里,这一真正的“学习”入门是要借助于书本与学校的存在。书本方面,孔子从古代的文书、文献、诗歌、神卜、礼法及风俗规定中选取教材,并且以真理和实用作为尺度,校订成书。学校方面,是通过孔子所创立的私人学校来实现的,在这样的学校中,孔子要把弟子们培养成未来的政治家。[13]117在雅氏看来,理解孔子学习的外部实现方式,需要关注到孔子的教本、办学以及育人目标等角度上的相关问题。但这些角度上的问题主要关涉到的还只是处于基础和入门层面上的学习问题。内心深处的领悟方是对学习问题本质的触及,就孔子所理解的学习而言,弟子们如果没有伦理生活作为前提的话,是没法教的。弟子应当爱父母、爱兄弟,应当诚实、认真。如果谁的举止不良的话,那么他在学习中绝不可能触及到事物的本质。[13]118雅氏强调,孔子认为所有学习的意义在于实践,而内心的陶冶是在学习之中形成的。[13]119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自觉自主的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学习行为的切实展开,学生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自己”,而孔子真实教师形象的缔成实质上也正植根于此。朴赖斯指出,尽管孔子所办学校的规模很小,但这种新式兴学在当时却是一种社会革命,孔子所遵行的是一种普惠教育的原理,这也是他留下的宝贵遗产。孔子的招生条件仅仅是向学生收取一点力所能及的束修,他最看重的是学生对学习的喜欢和认真。孔子的这种“有教无类”的教育活动使得那些出身寒微的学生也能够有机会成为具有高贵绅士风度和品质的人,并由此实现自身的潜能以及家庭的梦想。[12]137-141如朴氏所言,广开门路兴办私学是孔子应时而起所做出的一大文教创举所在,孔子凭此创举奠定其在历史上的独一无二教师地位亦可谓是实至名归。朴氏认为,孔子在课堂上虽然偶尔非常严厉,但课堂气氛总体上还是轻松愉快的,不过这绝非就意味着孔子可以放任学生在学习中任意懈怠,并且像孔子这样伟大的教师正如其自身所主张的那样,他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学到的东西传授给了学生,孔子的教学也由此体现出鲜明的表里如一和言行一致的特色。[12]148孔子的课堂教学可谓深蕴非同寻常的教育智慧,且在孔子那里,为学与施教这两大教育行为之间因其所奉行的以身作则和知行合一的价值取向而有机融合为了一体,体现出鲜明的践行为本的笃实风格。在朴氏看来,孔子及其弟子之间的关系是亲如家人的,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甚至是在周游列国那段最为艰难的岁月中,孔子也总是笑对人生,他与自己所钟爱的弟子们一起度过的是一段“家一般”的幸福时光。同时,诸如孔子、子路、子贡、颜回等孔门师生,或为大师、或为斗士、或为儒商、或为雅士,他们每个人独具特点的人生都是一部传奇,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师生们为了追寻理想,浪迹天涯、不畏艰辛、矢志不渝,他们也由此成为了真实的传说,并已深植于民众心中,永难磨灭。[12]249-251
归根结底,现当代欧洲汉学对孔子教师形象建构的返本还原,是要在保持中西思想文化各自独有特色的前提下,努力创设一条将彼此价值取向、世界观、思维方式和思想特质达成有效融通的宽坦新路,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掘和运用孔子教师形象及其思想学说之于推动世界思想文化实现更好发展的独特价值。
四、结 语
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东西方文化接触推动了人类文明世界的发展,在这方面,以孔子为例,我们可以得到证明。[16]欧洲汉学在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几百年间对孔子教师形象的建构历程实质上也正是一个不断促进和加强中欧之间文化沟通与互鉴的历程,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全球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自二十世纪以来,彻底摆脱过去的文化霸权宰制和建构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世界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很多西方学者在看到自身文化发展危机的同时,也从他种文化寻求新路,特别是一些对中国文化素有研究的西方学者,也在试图从中国文化中寻求普世价值,以解决人类遭遇的共同问题。[17]汉学固然涵盖了中国文化的广泛内容,但对中国文化价值的研究始终是它的灵魂所在。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正逐渐再现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昔日辉煌。世界各国也在迫切关注并希望了解诸如中国要怎样影响世界、中国的价值观会给世界带来什么等等问题的答案,它关乎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18]从欧洲汉学的总体历史变革进程来看,现当代欧洲汉学对于孔子教师形象的研究愈加体现出中西融通和全球一体的变革特点,而在未来发展趋势上也必定会不断加强对孔子教师形象背后的中国思想文化价值的关切程度,并由此推进对中国思想文化价值的发掘与运用。
雅斯贝尔斯将孔子与苏格拉底、佛陀和耶稣并列为人类思想范式的四大创造者,并认为这些伟人虽然并不拥有俗世的权力,不具备民众领袖以及诡辩师的魔力,但他们却在灵魂上征服了民众。他们能容忍一切,并不执著于什么。雅氏断言,他们所具有的伟大人格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从未停止过。[13]186朴赖斯也强调,孔子作为一位公元前5世纪并不起眼的教师,能够在此后两千五百年中产生如此深远的历史影响,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他认为,唯一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理由就是孔子的“博爱和与人为善”的哲学理念乃是不朽的。[12]332
雅氏与朴氏所言可谓当矣!不过亦须看到,尽管作为教师的孔子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非凡意义和深远影响是举世公认的,但对其所独具价值的发掘和运用在当下乃至未来的西方世界却并非一片坦途,而是面临着相当程度的困境。
卜松山(Karl-Heinz Pohl)认为,我们不仅在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欧洲哲学家的思想里,而且在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中国哲学家的传统中,发现了具有全球性意义的思想。但同时,卜氏也指明,在西方知识分子那里,中国哲学家并没有受到充分的关注,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知识分子与东方知识分子在面对彼此思想文化传统时的熟悉程度并不对等,东方知识分子较之西方知识分子更加熟悉对方的思想文化传统,而西方知识分子的状况则恰恰相反,他们只熟悉自己的思想文化传统,对于对方的思想文化传统却所知甚少。由此,卜氏主张,在一个跨文化的语境中进一步追求一种普遍伦理的观念,并强调非西方价值中的普遍意义,特别是那些能够弥补西方个人自由和权利要求的义务观念,是十分恰当的。[19]
道姆(Ulrich Daum)的观点与卜松山有异曲同工之处,他指出,在欧洲人眼中,孔子一般性地乃是一种僵化的形象,但这种形象绝非其本来面目。他认为,西方批评家们习惯于指责孔子劝解人们盲目地相信权威,但这种肤浅的批评对孔子来说并不公正。孔子实际上并没有要求盲目地服从权威,而是对权威产生了怀疑。在道姆看来,孔子实质上是一位注重维护旧有道德规范和礼乐秩序的诚实教师,而并非一位把过去绝对化,进而阻止一切创新的反动思想家。孔子最重要的遗产恰恰是存在于不受时空限制的具有突出优先地位的道德之中,存在于由道德所塑造的人之中,而这种优先地位不是民主方法、法律的规则制度和目的理性所能取代的,有时能面对任何一种社会的重要的政治权威而发挥其作用。由此,道姆强调,孔子可以为现代化的中国和整个现代世界指出一条将西方追逐成功、个人主义同东方的集体主义思想、东方的人性、东方重视自然的思想相结合的道路,因此面对受西方影响的自私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时便会出现一条新路。[20]
无论如何,正如卜松山和道姆所冀望的那样,我们可以对孔子其人其说在西方世界的发展前途和命运保持理性而谨慎的乐观。在当下及未来欧洲汉学那里,对孔子教师形象的建构必将逐渐跳脱出西方批评家们习惯性思维下的僵化保守形象的困囿,而主要地表现为一个既具有批判精神又遵行道德法则的诚实教师形象。同时,孔子思想作为一种代表着人类思想文化精华的深厚历史遗产,也必将更好地展现出其基于中西思想文化有机协调和融通下的促进中西文化与教育发展进程,乃至促进中西整体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