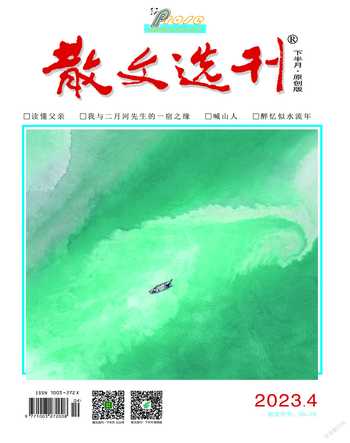我与二月河先生的一宿之缘

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1987 年 9 月 12 日,那天是周六。我从沈丘乘长途客车来到郑州我叔家。我叔于通是《河南日报》社的编辑,全家六口人住在纬五路路南的报社家属院 3 单元 4 楼。晚饭后,我叔要送我去与家属院仅一墙之隔的报社招待所,说比住家里舒服。来到招待所,所长听说我是于编辑的亲侄儿,很热情地喊一位女服务员来开 01 号房间的门。女服务员对我说,这房间已经入住了一位南阳客人,外出还没回来。
当年的《河南日报》社招待所是只有几排砖瓦平房的大院子。01 号,就是这院里第一排最东头的一个房间。小小的房间里很整洁,东西靠墙各有一张木床,两床中间有一书桌,桌上方悬挂着一个长长的大电棒管。我看西边床上放有衣物,就在东边床上坐了下来。
所长和我叔进屋聊了一会儿就走了,恰好那位南阳客人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我看他比我年轻,好像才三十多岁(其时我们都已年过四十)。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高大魁梧,站在小小房间里,像挺拔的青松,巍峨的铁塔。我仰脸望着他说:“看你这高大形象,你是哪个部队的大将军吧!”他把一个厚重的军用挎包放在桌上,笑着说:“你看得也准也不准,我在工程兵部队当过兵,没当过将军。”
话匣子一打开,我们就坐在各自床上聊了起来。当他听我说我是沈丘师范的语文教师名叫“于华”时,既惊喜又很敬重地说:“是于老师呀!我还读过你的一篇文章哩!《河南日报》1985 年第一个教师节的征文选登,你的那篇《一顿难忘的夜餐》,是跟叶文玲的散文排在一起的……”
说到叶文玲,南阳客人十分景仰。他说,叶文玲老家是浙江的,15岁上初中时就发表过小说。她哥哥叶鹏是复旦大学的高才生,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她受到牵连,高中没上成,1962 年来到咱这河南郑州,在市郊的一个工厂当工人。生活艰苦仍然坚持写作,发表作品越来越多,1979年调入河南省文联。1980 年,她创作的《心香》被评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成了有名的大作家!
我说,是的,三年前,在沈丘县党校礼堂,我听过南丁先生和她的写作讲座(沈丘县文联特邀的)。
南阳客人说,他 1978 年从部队转业到南阳宣传部。这几年业余写了个长篇,这次来郑州是来联系出版社的。我说:“咱俩都是业余作者呀!我看看你写的长篇吧……”他说:“您是师范老师,我是高中生,您也是我的老师,得请您指导。”我说:“不敢说指导,我只写过几篇短文。”
他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一大摞装订成本的文稿——每页400字的大稿纸,那一行行隶书体的深蓝色钢笔字,好像是一排排等待元帅检阅的士兵。首页的大标题是“康熙大帝·夺宫初政”,开篇的“楔子”写道:
顺治十八年正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刚过完年,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
我又往下翻了几页,上面写的是“第一回 开新篇纵谈天下事 辞旧朝忍抛骨肉情”。我惊叹说:“不简单!你这是章回体呀!《三国演义》的写法!这可不是一般作家能扛得起的。嗬!你不是一般的大将军,你是能管住皇帝的大将军耶!”
忽然,我看到大标题下边的署名是“二月河”。我说:“我还没问你尊姓大名哩!看你这署名,是笔名吧!”他说是,本名叫“凌解放”。听他这么一说,我这每天上语文课的职业病又发作了起来。我说:“你这笔名挺有诗意——凌的偏旁是两点水,是‘二。这冰凌呢,一到二月春暖花开,大块大块的冰凌都化开啦解放啦,哗哗哗就流成一条波涛滚滚的大河啦,就有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美好意境啦!”他笑笑说:“于老师您讲得还挺有理有趣!”
2009 年 3 月,我从新华网上看到一位记者采写的《二月河的军旅人生》一文,谈到“凌解放”的姓名与笔名,文中写道:
二月河的原名叫凌解放,1945 年农历九月出生于山西省晉阳县。当时人们正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和上党战役报捷、家乡获得解放的欢乐之中。于是,身为县武委主任的父亲凌尔文和战友们经过一番研究,集体给这个初生婴儿起了个名字,叫作“凌解放”。二月河是他年满四十岁正式出版《康熙大帝》第一卷时,才首次用的笔名。当时,他是这样考虑的:自己创作的是长篇历史小说,而自己的名字叫凌解放,一个历史,一个现代,有点不太协调,想用个笔名,于是就顺着“凌解放”三个字的意思找思路,凌乃冰凌也,解放者,开春解冻也。冰凌融解,不正是人们看到的二月河开的景象吗?就此,二月河的名字便应时应运而生。
读了这篇报道,我才知道自己虽已年过“不惑”却还是望文生义信口开河,而今回想仍感羞愧。那天夜晚,二月河还和我共同感叹了业余作者的艰难。我们二人特别有共鸣的是:白天上班忙,顾不上写,就算白天偶尔有点时间也不敢写,怕别人说你不务正业,只能夜里在家写。他还笑着补充说:“就这也有人说闲话哩,说我用公家的稿纸写自己的书。”接着,他又叹息说:“写书难,可谓千难万难!现在才知道,业余作者想出书,比写书还难!”
那时的我,只偶尔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散文,好像还不太难,所以,对他的这番感叹还理解不深。就问他:“你说出书比写书还难?看你这一大摞一大摞的一百多万字,先不说查找史料构思起草有多难,就算只叫我抄写一遍我也没这个胆!”他淡淡却又苦涩地笑了笑说:“于老师呀,我不怕您见笑,这一年多,我背着这老厚的书稿跑了好几家出版社啦!大编辑们一听说我只上过高中,随手翻了几下稿子,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啦!我真搞不清,到底写啥样才算达到出版水平?后来再去出版社,我就对编辑说,我是红学研究会的。这才算遇到一位愿意审阅我书稿的编辑……”
他说,他非常感谢中国红学研究会会长冯其庸先生。经冯会长推荐,他才有幸在《红楼梦学刊》发表了两篇论文。1982年,他才有幸以最年轻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红学”年会。
我看看手表 10 点多了,就说你也挺累的,咱休息吧。
房间里没有卫生间。我们一齐出门去了一趟公厕,回来就拉灭了电棒。
睡到下半夜,我起床要外出小解时,看见他手握钢笔,正伏在桌前的一个小台灯下聚精会神地修改书稿。映着灯光,他那刚毅而沉静的面容有明有暗,宛若石雕……三十多年了,二月河这样一幅灯下伏案改稿的画面还常常在我脑海浮现。
他抬头问我:“于老师,我影响您休息了吗?”我说:“你连大电棒都没拉,咋会影响我呢?看你这么熬夜,身体能顶得住?”他说:“我在家也这样,习惯啦!”他又抱歉似的笑了笑说:“忽然想起来有一段得改,不起来改,也睡不着。”
翌日晨,我就要和他告别了。他说,为了等候出版社的意见,还得在这儿住两天,他很希望我能在这儿多住一天帮他审审稿。我说明天周一上午我有两个班的语文课,今天不回学校不行呀!
他一直送我到大门口。临别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于老师您啥时候去南阳,一定到我家,咱俩好好拉拉家常话!”我连声说“好、好”。
嘴上说“好好”,可是,自从那天与他握手告别后二三十年里,虽然很想去他家“拉拉家常话”,却终归没去成。
没去成的原因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原因是:几年后,二月河的 4 卷本《康熙大帝》由郑州的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不久,有关二月河的新闻报道就好似星火燎原,继而蒸蒸日上如彩霞满天。先是荣获河南省优秀图书奖,河南省第一届优秀文艺成果奖。1994 年,根据《康熙大帝》第1 卷改编的14 集同名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放……1990 年至 1992 年,二月河又完成了《雍正皇帝》3卷共140余万字,由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96 年,他又推出了“帝王系列”第三部《乾隆皇帝》,获河南省第二届优秀文艺成果奖……他的一部部厚厚的书稿,再也不像 10 年前那样送到好几家出版社吃“闭门羹”了,而是好多出版社纷纷派编辑直奔南阳“三顾茅庐”登门求稿啦!
1998 年,根据“帝王系列”改编的 60 集电视剧《雍正皇帝》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起全国轰动……
匆匆 10 年岁月,开冻解放了的小溪哗哗哗地流成了大江大河,默默无闻的业余作者成了一鸣惊人的著名作家。想到他不分昼夜的写作之忙,想到他作为明星大家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的应酬之多,仍然是小小业余作者的我,怎么好意思去叨扰他呢?
我还想到,当年,一听说他是“只上过高中”的业余作者,就不屑于看他书稿的那些出版社编辑,而今后悔吗?
2011 年 6 月,从新闻报道中得知:二月河,这位没上过大学的高中生出任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
屈指算来,自从 1987 年在《河南日报》社招待所与他同宿一室之后,时光如水,年复一年,尽管时常想念,却再也没见过面。
没想到——30 年后的 2017 年,我竟然又见了他一“面”!
11 月 19 日那天是星期日,正在书房里写稿的我忽然被客厅里的一阵“哗哗哗”的掌声所吸引,不由得走了过去。只见电视屏幕上:在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主持人撒贝宁搀扶着一位老人走上讲台……全场观众坐下之后,从撒贝宁口中,我才听出这位老人就是二月河!我对着屏幕瞅了又瞅,啊!这样一位头发稀疏、圆圆胖胖、眯着两眼、满面含笑的慈祥老人就是二月河?
30年来,在我的记忆里,二月河一直是魁梧高大、如青松似铁塔的英俊军人形象,啊呀!这……差别也太大啦!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信。
更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一年后,报刊上一个触目惊心的讣告让我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2018年12月15日,著名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因突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时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3岁……
虽然我和他是“同龄人”,可若论出生年月,他比我还年轻。何况,在我的记忆里,中年时期魁梧的他可比我健壮得多,怎么突然就……
从报刊上几篇怀念二月河的文章里,我找到了答案:提及二月河的创作艰辛,了解他的人都说,古有头悬梁锥刺股,今有二月河的“烟炙腕”。每当深夜困顿难忍时,他就用烟头烫自己的手腕,如今,他手腕上全是烟烧伤痕。他天天通宵写作,晚上 10点开始,写到凌晨 3 点睡觉。写到深夜,手都僵硬得握不住笔了,就狠劲搓搓手,或把开水倒在毛巾上捂住手暖一暖再继续写。高强度的创作过程,严重透支着他的身体,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接踵而来……
我想起 30 多年前,他和我在《河南日报》社招待所同住一室的那天夜里,我原以为他是睡到半夜才起床改稿的。看了上述的那篇怀念文章,我才悟出——为了不影响我休息,他是在我 10 点多拉灭电棒之后“假寐”了一会儿,等我入睡后,他才悄悄地摁亮小台灯,仍然按照他“通宵写作”的习惯起床修改……长年熬夜、高强度创作……为了这 520 万字的“落霞三部曲”,二月河是在以命相拼啊!
那天夜晚,我曾说他是“能管住皇帝的大將军”。然而,可敬却又可悲的是——他这位“大将军”以超乎常人的能力创造出当代文学史上的奇迹,却没能管好自己的身体。
二月河呀!您怎么不向您景仰的叶文玲大姐学习呢?您怎么不向四川省作协主席马识途老先生学习呢?叶文玲是1942年出生的人,比您大 3 岁,从郑州回她家乡后担任浙江省作协主席,已出版著作 60 多本,今年 80 岁了还在从容写作。马老出生于1915年,比您大30岁。他70多岁那年学会了电脑写作,所以,他写书就不像您“爬格子”那样累,去年,106岁的他又出版了一大本《夜谭续记》。他们为什么能成为“文坛常青树”?因为他们写作虽然也很勤奋,却不像您那样“烟炙腕”式的长年熬夜!
而今,我后悔的是——20年前,假如我别有那么多顾虑,只管去南阳找您“拉拉家常”,我一定要下大力气劝您:“写长篇要从容,要沉住气,要把自己的‘青山放在第一位,您的‘落霞三部曲晚个几年再出版也没啥关系。”假如您接受了我的劝告,您就不会这样突然离去。
假如只能是假如,斯人已去,唯有怀念、痛惜!
责任编辑:刘筱雪美术插图:曲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