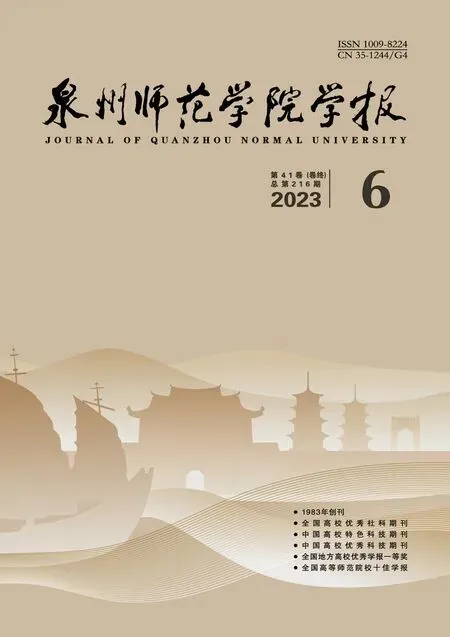论沈从文《边城》的企慕情境
陈良启,陈妍
(1.泉州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2.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一、企慕情境的由来及内涵
“企慕情境”这一美学范畴最早由被誉为“博学鸿儒”[1]“文化昆仑”[2]的钱钟书先生提出的。他在《管锥编》论及《诗经·秦风·蒹葭》和《管锥编·论宋玉〈高唐赋〉》时是这样描述的: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传》:“‘一方’、难至矣。”按《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附录》论之曰:“夫说之必求之,然维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益至。”二诗所赋,皆西洋浪漫主义所谓企慕(Sehnsucht)之情境也。古罗马诗人桓吉尔名句云:“望对岸而伸手向往 (Tendebantque manus ripaeulterioris amore)。”后世会心者以为善道可望难即、欲求不遂之致[3]208。
人生在世,情差思役,寤寐以求,或悬理想,或构幻想,或结妄想,佥以道阻且长,欲往莫至为因缘义谛[3]208。
钱钟书认为,《蒹葭》所创作出来的美学效果与西方浪漫主义所说的“企慕情境”美学思想一致,即“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可望而不即的企盼、憧憬之情境。在他看来,中外学者对“企慕情境”的看法是相似的,对于美好的事物,人们都充满欲望和不满足,会不断地追寻,充满期待。“企慕情境,它表现所渴望所追求的对象在远方,在对岸,可以眼望心至,却不能手触身接,是永远可以向往,但不能达到的境界”[4]23。在“企慕情境”中,企盼、憧憬的情思是“人类的共同的文化心理”[5],是“万千人生体验的常态之一,是普通存在于人类生存困境的一种表现形式”[6]。
综上,我们可以将“企慕情境”美学理念概括为以下四个层次意思。其一,企慕情境期待的对象是美好的。这种美好的事物能激发人的欲望,令人为之追索。其二,企慕情境是“难至”的。“伊人”永远“在水一方”,中间有着不可跨越的“阻隔”,即使可以看到,却难以到达。“阻隔”产生距离美,因而更加令人神往。其三,“难至”的程度。不可“求思”“泳思”“方思”,表面说的是追寻的难度巨大,其实反衬出游女企慕的境界非常人所及。其四,对“难至”的态度。“必求之”,说明“道阻且长”并不能阻断游女反复地追寻,反而更加坚定“求之”的信念。在钱钟书先生看来,企慕情境不仅表达男欢女爱的艳羡之情,还表达一种社会普遍心理,即让人为之倾情、憧憬且未能得偿所愿的情感。这种情感状态存在于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心理,并在作品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边城》的企慕情境
《边城》是一首“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7]18,是沈从文将“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7]18,“处处充溢着牧歌气息”[8]的作品。《边城》讲述的是翠翠与天保、傩送兄弟间的爱情纠葛故事。小说抒写如诗一般的山光水色、风土人情,以及善良、朴实、勇武的人性,让生活在诗情画意的翠翠与天保、傩送兄弟演绎着爱恋之情,“然而到处是不凑巧”[7]18,天保追求翠翠失败溺水而亡,傩送为寻找天保尸体隐忍情愫,翠翠谢绝一切帮助,守护着渡船等待“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9]293的那个人。尽管小说结尾令人黯然神伤,但是沈从文创设了“田园牧歌”式的人间仙境,抒写翠翠、天保、傩送对美丽爱情的追求和企盼,特别是一句“也许明天回来”,饱含着翠翠对爱情的热切企盼和执着追求,可以说是《边城》对企慕情境的直接诠释。
(一)翠翠生活的世界:企慕之境
古今中外,美的情境是人们向往的地方。《蒹葭》开篇给我们营造了梦幻式“蒹葭苍苍”情境,将读者带入一个企慕之境。这样的企慕之境,无疑增加了主人公对“伊人”的思慕情怀。
《边城》一落笔,描写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9]209。这无疑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牧歌气息”的环境——沈从文试图构建出一幅与自然合而为一的和谐世界。翠翠在自然山水的滋养下,心性浸染着“自然的文化”。
小说还着意刻画翠翠的生活世界周围,处处呈现美丽的心灵。与翠翠生活在一起的爷爷老船夫,一生守护着渡船,阅尽人世沧桑,然而始终保有一颗朴实无华善良的心,“管船人却情不过,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烟草……过渡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9]208。爷孙俩生活虽然简朴,但“老船夫闲暇时,便为翠翠快乐地唱起歌来”[9]215。船总顺顺,“事业十分顺手”,“为人既明事理,正直和平”,“闻名求助莫不尽力相助”,“为人公正无私”[9]216。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年纪长的,性情如他们的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年幼的……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9]216。翠翠生活的周边,生活着一群“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可以信任”[9]215的人。“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10]。沈从文构想“田园牧歌”境况,并不是纯粹如诗般的青山绿水。也就是说,沈从文构建的“企慕之境”,既包括自然美景,还必须拥有人性善的人情美、社会美,“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1]5。沈从文构建一个“蒹葭”式的境况,开启了翠翠们的追寻爱情之路,为翠翠企慕心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爱情:企慕之情
企慕情境所期待、所追求的对象是美好的,同时又被一种无形的东西“阻隔”着。《边城》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主要有两条线索。其一,翠翠与天宝、傩送兄弟间的爱情。其二,翠翠父亲和母亲的爱情。翠翠的爱情及父母的爱情,都因为“偶然”“不凑巧”[7]18而以悲剧告终。
翠翠父亲和母亲的爱情在小说的第一、七、十一、十二、十三、二十一章六次反复出现。可以说,翠翠父亲和母亲的爱情在小说中的存在,是对翠翠的爱情企慕心理的不断强化。小说第一章,作者“客观”叙述翠翠父亲和母亲在对歌中相爱的故事。男女对歌定终身,本是苗族的择偶方式,它赋予青年男女极大的爱情自主权。他们不太注重身份和钱财,追求的是富有浪漫情趣的爱情价值观。这样的爱情,就像一个令人神往的神话,冲击着翠翠的内心,埋下她对爱情企慕的种子。
小说第四章,翠翠初见二老傩送。翠翠误会二老。后来经老船夫说明,翠翠才知道二老傩送是“岳云”,不仅是女孩心目中的美男子,而且歌唱得好。“歌唱得好”“美男子”,正是女孩子心目中企盼的对象。翠翠“心里又吃惊又害羞”[9]225,“沉默了一个夜晚”[9]225。此时,二老傩送的形象已深深嵌入翠翠的内心,也确立了翠翠心目中理想的形象。第五章中,老船夫就大老天宝送鸭子一事问:“假若大老要你做媳妇,请人来做媒,你答应不答应?”翠翠则“着了恼”[9]228。第六章中,老船夫重提天宝送鸭子一事,“翠翠却微带着点儿恼着的神气”。这两章的描述进一步说明二老傩送在翠翠内心占据重要位置,大老天宝并不是她心中的理想形象。
小说第七章,翠翠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故事第二次出现在老船夫的思想意识里,“祖父明白这类事情对于一个女子的影响,祖父心情也变了些”。当大老过溪提到要为翠翠唱歌时,“祖父用微笑奖励这种自白”,进而大老提出“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得好”的请求时,老船夫温习大老的话,“实在又愁又喜”。第十一章,大老正式托媒,翠翠先是“不曾抬起头,心忡忡地跳着”[9]225,于是老船夫告诉翠翠“若欢喜走马路”,相信大老会“像杜鹃一样一直唱到吐血喉咙烂”[9]225。这时,祖父“便引到了死去了的母亲来了”,“翠翠心中乱乱的”,反复思索着“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谁更是好运气”。虽然老船夫意识到翠翠对爱情的追求,但是大老天保愿意“接过渡船”(“上门女婿”),因此他想方设法、旁敲侧击翠翠接受天保。老船夫的举动并没有打消翠翠对爱情的企盼,反而起到反作用。接着在第十二、十三章里,翠翠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故事连续出现,一次比一次清晰地指向翠翠对爱情的企盼,不断地强化翠翠的这一企盼。
叙述到这里,可以看出翠翠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故事在小说中的作用:形成翠翠企慕心理—强化企慕情感—恒定对爱情的企慕。关于翠翠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故事在接下的几章(一直到老船夫死去)中并没有出现,因为此时的翠翠已然形成“爱情企慕之境”。
另外,沈从文在小说中为了呈现企慕情境美学追求,还写老船夫“心境”的转变。小说第十二章,做媒的来探口气,老船夫“回头又同翠翠谈了一次,也依然得不到结果”,“隐隐约约体会到一件事——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9]257。于是,他希望大老能以“对歌”方式赢得翠翠的芳心。第十三章,老船夫“夜来兴致很好”,说出翠翠的父亲是“当地唱歌的第一手”,翠翠的母亲“如何爱唱歌,且如何同父亲在未认识以前在白日里对歌”[9]264。正是老船夫潜意识的转变,才有小说第十四章“张冠李戴”的一幕,以为是大老为翠翠“唱了半夜的歌”[9]265。第二天见了大老,老船夫“搓着手”夸他是“我们地方唱歌的第一号”[9]266,“走马路,你有分的”[9]266。两天后,不再听到对崖的歌声,“老船夫实在忍不住了,进城往河街去找寻那个青年小伙子”[9]270。从杨马兵口中得知大老“被水淹坏”后,连说“天意”,他细细回想翠翠的心思,明白“翠翠不讨厌那个二老”。于是,他急不可耐地转着弯试探二老,想促成二老与翠翠的婚事。甚至在二老过渡时,厚着老脸再次试探,二老却“不置可否、不动感情听下去”,“那点淡漠印象留存老船夫心上”[9]280。说明老船夫“明白”翠翠对爱情“企慕”心理后,误认为大老按着自己的意愿为翠翠唱歌,发生了误会,从侧面强化了翠翠对爱情(对歌)的企慕。
翠翠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故事最后一次复现是在小说的第二十一章,经由“暗恋”翠翠母亲的杨马兵口中叙述的。这一细节显得特别有意思。其一,杨马兵的亲身经历,美化了人们对神圣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为了爱情,杨马兵终身不娶。其二,父亲和母亲的凄美爱情故事坚定了翠翠对爱情的企盼。至此,翠翠对爱情的企慕就牢牢地扎根心中。
小说的结尾只有一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9]293。这是一个未定式不相容选择句,表示两个答案非此即彼,不能同时存在。然而,从故事的发展进程来看,“阻隔”在翠翠和傩送的“距离”随着天保的死越拉越大,是无法跨越的。因此,两个未定的选项指向的答案是“永远不回来”,即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是“难至”的。那么,“明天回来”就是作者留给人们对美好爱情的企盼、憧憬,是他对“美和善”“永远倾心”的企望。也就是说,翠翠经历人生的“起伏转折”后,更加坚定对美好爱情的企盼、憧憬,在她的内心深处——认定的东西,不管多么“难至”,终“必求之”。小说末尾,翠翠谢绝船总顺顺、杨马兵等的照料,毅然独自守护着渡船等待她心中的“他”,就是其坚定信念的表征。
三、企慕情境:沈从文的情感表征
企慕情境,是作者把内心强烈的企慕情感用艺术的形式形象地表现出来形成的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美学境界[12]。在《蒹葭》中,“伊人”代表企慕的对象,其“身份”是不确定的,是恋人、情人、友人,抑或指事业、功名、理想。“在水一方”是一种物象,一种阻碍追求企慕对象的因素,或高山大海,或习俗礼法,或命运际遇,或人为阻隔。王国维认为,“《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13]12。其中,“风人深致”,指的是该诗最能体现民间歌手的本色,即用强烈的情感歌咏民间对理想之境的企盼。《边城》对企慕情境的抒写,是沈从文作为一个苗族乡土作家创作情绪的表征。
(一)亲情之痛
沈从文在《边城·新题记》中写道:“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14]211母亲在沈从文心中的位置,远高于父亲,“我的教育得于母亲的不少,她告我认字,告我认识药名,告我决断——做男子极不可少的决断。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14]287。母亲出身于大家,知书达礼,对孩子管教甚严,对沈从文影响极大。1934年,母亲病危,沈从文匆匆赶回离开10多年的湘西。到家后又逼于当地的情形,母亲劝他返回北京,沈从文也不敢久留。不久,母亲就去世了,这给沈从文留下无法弥补的伤痛。《边城》写于“看望母亲”途中,完成于“母亲死去”之后,奠定其“充满悲伤”的基调。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沈从文与母亲、妹妹三人一直生活在一起。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将母亲送回湘西。如今,母亲去世,沈从文再也无法用现世去弥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只能用“作品能不死”来表达对母亲的爱和情。因此,《边城》是沈从文借“作品背后的悲痛”表达对母亲情感的企盼。
(二)爱情相思
《边城》创作期间,沈从文的个人感情是矛盾的。他创作《边城》是想将“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7]18,因为“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蚀它”[7]18,“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各式各样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7]18。上海公学教书期间,沈从文喜欢上该校学生张兆和,但张兆和并无此意思。沈从文痛苦地追求,害着单相思,甚至有自杀的念头。和张兆和结婚后,沈从文发现自己对妻子缺乏足够的了解,两人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性格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两人婚姻的调适期,“能破坏你幸福的幻影的‘偶然’”[7]19闯入他的情感世界。1933年,在熊希龄的西山别墅里,沈从文遇见让他“情感与理性陷入矛盾”的高青子,陷入了感情困惑矛盾之中。为此,他曾经寻找林徽因诉苦并寻求解决办法。在情感挣扎过程中,他明白了“生命的两面,用之于编排故事,见出被压抑热情的美丽处;用之于处理人事,即不免见出性情上的弱点,不特苦恼自己,也苦恼人”[7]22,最后,沈从文决定让“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压抑在心底”。同时,他寻找另外一种排泄心中郁闷的方式——任凭他肆无忌惮、天马行空地表达对爱情的憧憬。可以说,翠翠的等待和憧憬就是沈从文对爱情企慕的直接诠释。
(三)个人理想
湘西,是沈从文儿时生活过的地方,是他最为欢娱的地方,也是最为留恋的地方。湘西是沈从文创作的“一个想像的王国”[15]4。“湘西世界”是沈从文“展示人生境界的最集中概括”[16]。沈从文出身于湘西的一个军旅世家,幼年有不菲的家产,每年“还可收取租谷三百石”,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由于家道中落,他当过士兵、税务员,只能将小时候的“温情”“堆积于小小生命中深处”[17]9。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经历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和抵御外敌入侵的战争。沈从文生活在那个年代,深谙社会状况。1922年,沈从文“为了实现社会重造的理想”[18],接受“大学教育”“念书”[15]68,只身前往北京。然而,沈从文“既穷,又未上过新学,当然考不上大学”[15]69。希望一再落空,“求学既无可望,求职亦无可望,唯一是手中还有一支笔,可以自由处理一点印象联想和生活经验,来作求生的准备”[17]15。可以说,沈从文是在生活重压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这无疑对他的创作原貌产生重要影响。
沈从文的思想立场是随着经历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时期进入他视野的湘西世界是不一样的,呈现在他作品中的湘西世界也是不一样的”[19]。《边城》是沈从文创作第二阶段的作品,是“沈从文创作上完成了从简单的叙写自身经历到以文化视角来审视社会人生的根本转折,依照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对理想人性的追求,虚构了一个‘湘西世界’”[19]的作品。这一阶段,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生活、体验过,感受都市人间的冷暖。特别是上海,“残酷的现实击垮了他的信心与自尊,他处处感觉到自己与城市的对立与冲突”[20]。他的内心,对都市生活充斥着深刻的体悟和悸动,交织着痛苦、失落、失望。然而,都市又是他创作的源泉和生活的依靠,“我的文章是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的……只有上海,我才能够混下去”[21]143。
艺术家创造艺术,无以逃避“文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下的历史生活矛盾[22]。“正像所有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某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于原始事物的爱慕,以及一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更加热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23]38。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新的文明不免给人们带来新的束缚,造成人类痛苦和矛盾。这种痛苦和矛盾,却成为艺术家创作艺术的源泉。面对文明带来的苦痛,艺术家试图从“原始事物”中找到一丝依慰,作品不免烙上“对于原始事物的爱慕”和对原始“生活方式的热望”。在北京、上海这样的文明社会交织着痛苦、失望的沈从文,内心希望有一种美好的东西,可以带领自己走出困境。“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是罪恶,可是总不能令人愉快。我们活在这个现代社会中,被官僚、政客、银行老板、理发师和成衣师傅,共同弄得到处都是丑陋,可是人应当还有个较理想的标准,也能够达到那个标准,至少容许在文学艺术上创造那标准。因为不管别的如何,美应当是善的一种形式”[7]15。这是沈从文对生活和文学艺术创作的态度。因此,他将现实中的不如意潜藏起来,而“美和善”成为他企慕的对象。
总之,《边城》的创作,是沈从文多种情感交织的体现。正如他在回顾《边城》创作时说的,“这个作品原来是那么情绪复杂背景鲜明中完成的。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以及音乐和图画吸入生命总量,形成的互相激情,旋律和节度,都融汇而为一道长流,倾注入作品模式中,得到一回完全的铸造”[17]27。可见,《边城》是其“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的情绪表达。同时,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潜藏着对故乡“美和善”的向往。因此,他选用“音乐和图画吸入生命总量”去表达,“这个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料少,占地少,希望它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1]5,让“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交织在文字与形式里”[17]27。正是这样的创作思路,促成沈从文孜孜以求、充满期待地构建“希腊小庙”,去抒写“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1]5,以修复都市生活中的困境。
四、结语
沈从文是一个执着于生命信仰的人,“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7]33。他又是一个“耐烦”[24]的人,对美好的事物孜孜以求、饱含期待,他执着于“美好的人性”,执念于讴歌“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11]5。在他的《边城》中,“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7]18,“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10]。为了家乡、为了民族、为了心中的执念,“对于原始事物的爱慕”[23]38和对“生活方式的热望”[23]38,沈从文不断地抒写他的企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