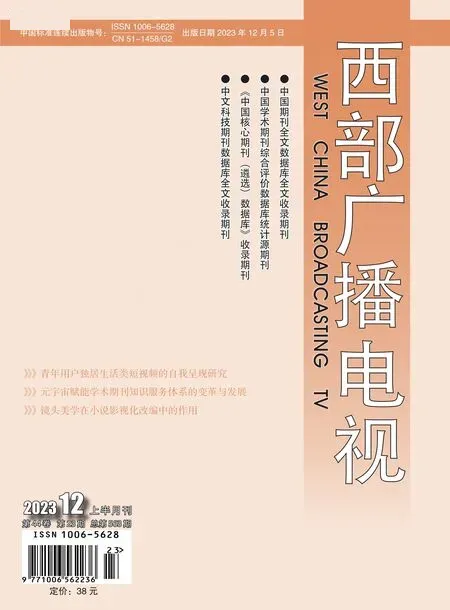武侠电影的反类型化
——浅析何平导演的《日光峡谷》
谭 苗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
武侠片是中国本土所特有的一种类型片,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特色和文化,也被世界电影艺术所接受。中国武侠电影几乎与中国电影艺术同时诞生,中国第一部武侠片来自天一影片公司的《女侠李飞飞》,这部影片已经基本具备武侠片应有的元素:飞檐走壁的武打动作设计,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等。身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观众需要一个英雄形象去缓解生活中的困苦和面对战乱引发的恐慌,武侠电影应运而生,成为解决社会精神困苦的一剂良药。此后,我国香港电影接过武侠电影发展的接力棒,使武侠电影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塑造了一批经典的武侠英雄,从黄飞鸿、方世玉那样行侠仗义、惩奸除恶的翩翩侠士,到张彻、胡金铨、楚原电影中塑造的快意恩仇、侠骨柔情的江湖儿女,香港武侠电影趋于成熟和完善。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武侠电影陷入瓶颈,20世纪90年代武侠电影开始彻底走向没落,各种商业的武侠大片,以及具有武侠外壳但丧失侠义的“泛武侠作品”的出现,表明武侠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武侠精神也日趋式微。
20世纪90年代初,何平导演以一部《双旗镇刀客》成为西部武侠的开创者。1996年,何平导演再推出一部西部武侠片《日光峡谷》,这部影片赓续了何平一贯的西部侠情,延续了西部武侠的地域特色。何平导演的西部武侠片不同于传统武侠作品,它兼顾着武侠片的可看性和西部电影的艺术性,具有天然的文化批判功能。《日光峡谷》同样也具有很强的艺术和哲思元素,呈现了对武侠伦理的反思,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和对人性的思考,值得在今天重新深入探讨。
1 另类英雄:中国西部最后一个刀侠武士
在拍摄完《双旗镇刀客》之后,何平就萌生了拍摄“中国西部最后一个刀侠武士”的想法,当这个社会已经不需要侠客,侠客又该何去何从。《日光峡谷》中黑牛对寻仇客说:“刀客这行档(当)已经不兴了,过时喽。现在来西北的,那都是挣钱,盘货,开商号,年景不同了。”电影聚焦在“后武侠”时代的刀客,完成了对“侠客”形象的去符号化,从传统的“侠”精神的宣扬上,转向“人”本身的情感,再上升至人文与精神层面,注重人道主义的关怀。片中的每位刀客都被情、理、欲所羁绊,俨然不似传统刀客般纵横江湖,潇洒恣肆。
1.1 “怕血”的刀客形象
寻仇客是一个具有极大悲剧性色彩的主角,影片以他刀客身份的瓦解和重塑为线索推动叙事,呈现了其认识的深化和精神的成长。寻仇客在幼年遭遇了灭门的悲剧,这使其背上了仇恨的重压,他常常会回忆起那梦魇般的屠杀,月光下刀面寒光凛然,鲜艳夺目的红色格外具有冲击感。仇人“一刀仙”带着一条红色头巾,身上染满鲜血,眼神凌厉无情,用一把镶嵌两颗蓝宝石的刀疯狂厮杀,两颗蓝宝石像一双眼睛一样凝视着他,将其拖入无尽的深渊,从此寻仇客便得了不能见血的“怪病”(创伤后应激障碍),受到鲜血的刺激便开始“发病”,见人就杀。武侠电影中的一位“怕血”的侠客,这样的人物设定天然存在着矛盾性和撕裂感,与传统武侠电影中嗜血残忍的形象大相径庭。影片完成了对侠客形象的去魅,消解了英雄人物的强大与崇高。
1.2 “弃刀修佛”的刀客形象
名震江湖、独步天下是每个侠客的心愿,武林中侠客常常为名利输赢不择手段,为活命自相残杀、尔虞我诈,但疯爷却说:“路遇强手被杀,这是福份(分)。”那个曾经被称为“快刀疯子”的传奇人物疯爷,最后却选择了弃刀修佛,自我救赎。影片重新定义了“侠客”的形象,侠者迟暮,创伤仍在,杀戮不只是表面的血雨腥风,也是精神上无法弥补的伤痕。电影中寻仇客第一次找疯爷借用磨刀石时,面对杀伐深重的寻仇客的请求,疯爷默不作答,而是径直走向了屋内,转着自己的经轮和佛珠走了出来,沉稳敛容的面孔带着历尽沧桑的冷静。从前对胜负的执着、对名利的追求造成如今深重的罪孽,疯爷妄图借助宗教信仰实现解脱和永恒的精神觉醒。电影中,疯爷前往马蹄寺的片段极具震撼力,冰天雪地下疯爷虔诚地跪拜朝圣,冬日高山上的阳光热烈明亮,疯爷一路叩等身长头,匍匐在地起身虔诚双手合十,抓起的白雪扬起,呈现晶莹的沙粒感,在人物轮廓上闪着耀眼、圣洁的信仰之光,给人洗涤心灵之感。直到他冻僵在冰雪之中,仍然面带着浅笑,走完了他精神上的修行之旅、救赎之路。
1.3 “双面”的刀客形象
“一刀仙”这一角色首次出现是在何平导演的《双旗镇刀客》中,与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相比,残忍暴戾的土匪“一刀仙”显然是一个反派角色。并且,在《日光峡谷》中,他屠杀了寻仇客无辜的家人,是杀伐深重、作恶多端的恶人形象。但在黑牛和红柳的叙述中,“一刀仙”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好大哥,武侠中重情重义的精神在其身上尽数体现。电影以敏锐的视角对人性进行深入的刻画,《双旗镇刀客》中他听到自己的兄弟命丧双旗镇后猛然起身,面露愠色,两泪纵横,这里没有激烈的情感输出和冗长多余的台词,但是观众可以感受到“一刀仙”的重情重义和侠肝义胆。在双旗镇与孩哥的决斗中,他虽技不如人但却武德高尚,面对孩哥面露敬佩之色,微笑着面对死亡的到来。从“一刀仙”身上,观众可以窥见人性的复杂性和人情的真实性,这同时也是对鲜明的善恶二元对立叙事模式的修正和消解。
2 叙事策略:反类型的创作倾向
武侠电影作为类型片,具有固定的叙事模式和主题,大多呈现江湖儿女的快意恩仇、仁人志士的豪情壮志,上演着笑傲江湖的传奇轶事。从何平导演的《双旗镇刀客》可以看出,西部这片土地天然适合呈现云谲波诡的传奇风云。西部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富有传奇性的美学特质,其沙子般粗糙的质感给电影带来了独特的视觉美感。“为了寻找这样一个景地,大约跑了一万两千多公里。在祖国的西北疆最终找到这么个地方。这么个海拔三千米以上的一片荒凉的峡谷的山口。”[1]日光峡谷,群山绵延、苍松挺拔,健壮的骏马四肢矫健,蹄如雷鸣,威武的马队扬鞭跃马疾驰而来。漫天的黄沙肆意张扬,但西部的土地总给人一种沉稳安定之感,壮丽苍茫的高原让人心生寂寥,这里是江湖的起点,也是江湖的终点。
2.1 去江湖化的叙事倾向
“江湖也泛指古代意欲挣脱掌权势力的控制指挥,逃避规矩的约束,从而畅意超脱的社会环境。”[2]在传统的武侠电影中,英雄会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用高超的功夫完成惩奸除恶的使命,然后潇洒离去。尽管寻仇客刀技高超,但是他显然不是以一个“救赎者”的身份来到日光峡谷的。电影中,寻仇客始终是痛苦的,他一直被仇恨的执念所困,在睡觉时也保持着警惕,稍有动静就会拔刀而出。在平日里也寡言孤僻且不易接近,他怕血的症结使他形成了这样的性格。寻仇客总是自觉回避争端,面对客栈客人的挑衅更愿意忍受欺辱,选择息事宁人。胡金铨导演的经典影片《大醉侠》中,侠女金燕子在客栈面对笑面虎的挑衅,以高超的武功和过人的智慧巧妙应对,让观众欣赏到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矛盾冲突是戏剧的生命力,武侠电影擅长使用激烈的矛盾冲突,形成具有冲击力的情节,呈现出人物的饱满与矛盾的对立。但《日光峡谷》却具有“去江湖化”倾向,跳出武侠片的常套和窠臼,不追求精彩的双雄对决,更愿意呈现个人的情感状态和思想境界,体现成长和救赎的主题。
2.2 回归家庭
影片的反类型化还体现在对情感的追求、对家庭的回归。传统武侠电影中,侠客始终是无牵无挂行走江湖的形象。在张彻的经典电影《新独臂刀》中,江湖豪侠封俊杰一人持双刀行走天下,与落难的雷力成为知己,后封俊杰中计被奸人所害,雷力选择不顾生死为其报仇。在电影中,雷力并没有直接接受芭蕉姑娘的示好,不会选择回归家庭和安定,他可以随时为了侠义之情抛弃这份感情。观众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就是,一个合格的侠客不应该在乎儿女情长,要以充满豪情侠义的大局为重,做一个潇洒自如的游侠客。在电影《日光峡谷》中,无论是寻仇客还是四处游荡的马贩子,都意欲回归家庭,渴望安定的感情。电影在解构武侠神话的同时,展现了人性中应有的对情和欲的渴望。电影中呈现了一个漫长的冬季,大雪封山的日光峡谷杳无人迹,往日熙来攘往的客栈如今只有三人,红柳温暖的房间蒸腾着烟火气,寻仇客放牛牧马、劈砍柴火、修理马棚,与沙枣相处融洽,俨然一副和谐的景象。影片中这种对田园牧歌式家庭生活的呈现,完成由“侠”转向“人”的叙事。
2.3 消解暴力
香港武侠电影自全盛时期开始,就聚焦于武打动作的设计上,采取“动作大于一切”的原则,追求视觉上的痛快酣畅和设定上的技巧,武侠电影开始陷入只会“打斗”的泥淖。《日光峡谷》中的打斗设计非常收敛,影片几乎没有多余的、与影片叙事无关的暴力情节,这延续了何平在《双骑镇刀客》中节奏张弛有度、武打虚实结合的武术美学,采用“写意”的武打设计,规避过多的暴力带来的纯感官刺激。《日光峡谷》中呈现了三次打斗,都是使用利落流畅的刀法一刀毙命。与同为第五代导演的张艺谋所拍的武侠片不同,“《英雄》里没有一场真正的以杀戮为目的、以生死较量为旨意的武打设计。影片中所有的武打场面几乎都是非对抗性的武舞表演”[3]254-256。何平更注重的是爆发力,招式简单直接,讲究速战速决,运用催石破金的绝世内力,产生了不亚于兵刃相接的打斗招式所带来的巨大震撼,产生精致极简的审美体验。
3 对中国侠文化中的“轻生重义”的质疑
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中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4]司马迁在书中列举了朱家、郭解等乡野平民出身的游侠,称其恪守诺言、义传千里,甚至不顾世人的讨论,选择为义而死。中国武侠电影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它集中展现了中国传统“侠文化”的精神,展示信诺忠义的侠客精神。侠客有自己信奉的人生哲学和判断是非曲直的道德标准,在其内心深处是深信不疑、从不动摇的,信守诺言成了古往今来所有侠客的信条。在何平导演的电影《双旗镇刀客》中,有两个出场不足一分钟的刀客让人印象深刻,两人追寻了“一刀仙”7年,凭借着信念的支撑一路追逐,人生仿佛只剩下了这一件事。漫长的7年已经磨掉了仇恨,在平常又普通的一天,双方展开的决斗平和且冷静,像完成任务一样,两人刀起刀落间就被结束了生命。坚定的信念感和契约感下,欣然赴死是一种崇高的选择。“豪侠义士都不是苟且偷生之辈,他们之所以面对死亡,并不是因为他们随意轻生,而是因为他们认定通过死能够获得比生更重要的意义。”[3]221这样的“悲剧英雄”使人感到震撼的同时,也会让观众重新思考传统武侠精神中“轻生重义”的价值所在。
在《日光峡谷》中,导演重新思索了生命的意义。电影中深谙行内规则和精神信仰的疯爷,却规劝寻仇客放下执念,挣脱枷锁。寻仇客说:“我找了他近二十年,这二十年怎么过的我都不敢想。要不,我找到他,要不我死。”而疯爷却觉得人生一世,为了给过去的事儿打个结,执拗于此并不值得,人世间的恩怨冷暖、喜怒哀乐都只是过眼烟云。疯爷看透了江湖的实质,走向了虚无。在他面对前来杀他的刀客时,不仅笑着迎接,两人还互相寒暄问候,熟稔得像老友重逢,毫无剑拔弩张的气氛。导演采用极为平静的方式呈现了对传统武侠精神的反叛。
“刀”是侠者身份的象征,彰显着侠者无坚不摧的信念和自由不羁的灵魂。电影《日光峡谷》里提到了两把刀,一把是镶嵌着蓝宝石像一双眼睛一样的仇人的刀,这是寻仇客梦魇的开始,另一把是寻仇客的斩千军之刃,这是他防身的工具。电影中,寻仇客对刀的态度转变,表明他一步步化解执念,挣脱仇恨的束缚,走出了那个自己曾经参与塑造的江湖。当寻仇客与红柳、沙枣培养出深厚的感情时,他打算放下仇恨回归家庭,将自己的刀交给了红柳,说:“拿去,放个地方。”当他发现了红柳的丈夫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仇人时,思索一整夜的他告诉红柳,把蓝眼睛的刀“扔了吧”。寻仇客对自己的刀说的是“放下”,对仇人的刀说的是“扔了”,这种递进的情绪展现了寻仇客内心的艰难抉择和无奈的情感矛盾,“扔”和“放”都是与侠客身份的割舍,对恪守的“信”的舍弃。天色将白,黑夜过去,寻仇客渐渐远去的背影,宣告着武侠片所塑造的英雄神话也随之消逝。
4 结语
《日光峡谷》延续了何平导演一贯的创作风格,尽管票房表现不佳,电影后续也无人问津,但作为一位具有类型意识的导演,这样的尝试在武侠电影的发展中是有必要的,同时也对武侠电影“无米下锅”的当下,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何平导演虽已逝去,但他始终“用电影的独特思维方式去思考、去表现、去不断地拓展电影艺术已知的和未知的魅力”[5]。何平导演给后人留下了非凡的艺术成就,他的作品扎根西部土壤,立足传统中国文化,为西部电影开创出新的武侠世界,也有助于重新打造武侠电影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