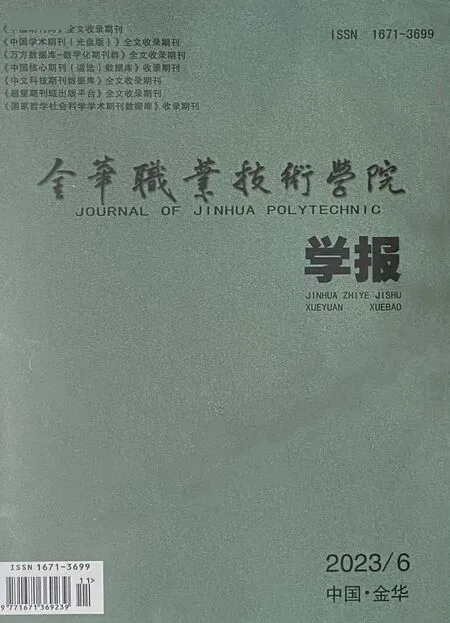《克拉拉与太阳》中的权力规训与自我救赎
路悦巍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 210000)
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克拉拉与太阳》于2021 年3 月出版,石黑一雄用一以贯之的精炼典雅、平实节制的文风刻画了在高度现代化的未来社会中、在机器人克拉拉视角下人类女孩乔西的成长经历。乔西从被权力规训到自我建构再到主体意识还原最后完成自我救赎的成长全过程,体现出作者对人性、情感和人类个体本身充满信心。《克拉拉与太阳》是石黑一雄创作的第八部长篇小说,前几部小说的人物在对世界的混沌认识和被遮蔽的自我意识中变得脆弱伤感,作者此次借助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等科幻题材,在相对可靠的叙述中完成了对人类独特性和社会性的闭环探索。
这部新作标志着石黑一雄在作品题材上取得了较大突破。还应注意的是,小说文本在塑造乔西的过程中,以儿童文学的书写模式隐含了丰富的文化寓意和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考——在模糊化的科学话语下,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人类究竟面临何种困境?作出了怎样的反思?未来社会的人类命运走向承载了怎样的话语机制?
1 被规训的身体
主人公乔西所处的成长背景为祛魅的未来世界。受高度发达的科技的影响,世界被客观化,等级秩序森严,阶级固化,不再具有神性和灵性。正如马尔库塞所言:“在现实原则的指导下,人类发展了理性功能……成了一个有意识的思想主体,并且做到了与外部强加于他的合理性步调一致。”[1]人们高度信任理性逻辑,在因果规律环中作出更为利己的选择。在这种世界中如何重建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成为小说中不同人物将面临的一道难题。其中不乏对理性逻辑的信奉者,他们试图用科学解释包括人类情感在内的世间万物。比如坚信人类能够通过科学技术予实现复制的科学家卡帕尔迪,当克丽西在让克拉拉代替乔西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时,他坚定地对克丽西说:“你需要的不是信心。只是理性。”[2]乔西的妈妈克丽西一心想给女儿最好的东西,如让女儿接受基因改造,有机会进入象征高层阶级的大学,甚至在乔西内心抗拒的情况下迫使乔西参加接受过基因改造的同龄人间的社交活动。克丽西谙熟社会秩序对个体的种种要求并以此要求女儿,企图让乔西在社会固有规则下过上上层阶级的生活。实质上,克丽西只是将女儿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完全无视女儿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应具有的独特性,这种对他人进行严格控制的行为方式和思维特征正体现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规训”。
“规训”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创造性使用的一个关键性术语,强调使身体变得“驯顺”并强制在肉体中建立能力增强与支配加剧之间的聚敛关系[3]156。这种规训意味着人们能通过一种新的“肉体—对象连结”[3]172与对象相互作用,在这样的过程中,身体不只是被开发,还受到强制性教导:“在肉体与其对象之间的整个接触表面,权力被引进,使二者啮合得更紧。权力造就了一种肉体-武器、肉体-工具、肉体-机器复合”[3]173。克丽西自身便是社会已有规训的接受者和认同者,她有着高级的职业、充沛的物质资源和良好的人脉关系,她深谙如何让女儿迈入大学、如何获得一份体面高薪的工作、如何过上自己心目中的“好日子”。虽然这一切出于母亲对女儿的爱,但在乔西看来,母亲以掌权者的姿态对她进行方方面面的压制,如让她接受基因改造,迫使她参加社交活动,让管家和克拉拉时刻监视在身边,禁止她出门旅行等。乔西生活在完全被设定好的世界中,生活中有无孔不入的监控,犹如新版本的“全景敞建筑”。全景敞视建筑在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被福柯看作“关于呈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图解”,是一种“权力的自动运作”[4]。在全景敞建筑中,乔西不仅从外在仪式和物质力量之中感受到权力,而且从内在精神中意识到权力的压制无所不在。乔西从小便渴望与里克携手相伴,但她在母亲的教育和社会的规训下被迫融入到社会话语体系中,她的心愿只能成为不能向外道的秘密。这一阶段的乔西生活在母亲和社会的话语机制和权力的支配之下,自我意识不明确,自我认知模糊。
乔西通过接受社会理性逻辑规训来建构对世界的认知,与其思维模式形成对照的是克拉拉对世界的认知方式。石黑一雄曾在采访中提及,自己正在试图捕捉的怀旧可以成为一个积极的事物,它是理想主义的情感对应物……是某种像伊甸园一样的记忆[5],克拉拉正是伊甸园一样的记忆的象征。《克拉拉与太阳》的书名、封面上的太阳图案及小说中对克拉拉信仰的大篇幅描写都明确指向了作者提出的另一种世界认知方式——太阳信仰。克拉拉的原始信仰不仅能作为乔西思维模式的对照,而且能以此透视作者的写作意图和价值选择。作为一个机器人,克拉拉的精神世界并非绝对的客观科学,她虽然一直在不断学习人类情感,但在遵守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之外,她始终保持着对自然世界中的神秘性的敬畏,以神秘、仁慈的太阳为信仰,由此建立了对世界价值体系的坚定认可。她以太阳为能量来源,在见证了乞丐人和狗死而复生后,她更加坚信太阳有能够带给万物滋养的神奇作用。第一次来到谷仓时,她看见“谷仓内部充盈着橙色的光芒,半空中漂浮着干草的颗粒,好似黄昏虫,他的图案洒遍了谷仓的整扇木门”[2]204。在这里,阳光变得可感知可触摸,夕阳的光芒投射在谷仓中的情形给克拉拉带来陌生化的审美感觉,由此使得克拉拉的信仰具有神秘性和崇高感。克拉拉相信在一天中太阳照耀谷仓的最后时刻,她能够在谷仓与太阳对话,能够向仁慈的太阳祈祷。在她的世界里,太阳犹如上帝,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犹如教堂,在这里能够完成宗教仪式的忏悔、祈祷,从而得到太阳的救赎。因此,相信太阳能给世界带来滋养构成了克拉拉精神世界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使得她和世界紧密连接为一个整体。
克拉拉对太阳的理解接近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在看到公牛时,她感到可怕、恐惧,“感觉仿佛是有人犯下了一个大错,竟然允许那个生物站在太阳的图案里”[2]126;第一次看到绵羊时,她感受到善意、温和,后来在谷仓中再次看见绵羊吃不到草的照片时,她又感觉到一些悲哀。弗莱曾在阐释原型批评理论时提及,原型是指“一种典型或重复出现的意象”[6]。作者数次态度鲜明地描写公牛的可怕和绵羊的温和,结合《圣经》及诸多文学作品,不由让人想到牛与羊的原型,从而将公牛与魔怪意象对应,绵羊与神启意象对应。富有宗教意味的动物意象深化了自然法则对应在人类社会中的残酷性:牛可被视为掌握权力者,吃不到草的绵羊则象征被权力规训者。由此可以发现石黑一雄的象征运用并非偶然,而是有机贯穿于克拉拉的信仰总体建构中,以此体现人类社会规则中生物进化般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总而言之,对太阳的信仰建立起克拉拉与世界形成某种联系的可能,折射出人类社会的严酷性。
2 游戏中的自我建构
以克丽西为代表的外部权力企图使乔西接受社会建构,并内化为在无意识中遵循的身体规训。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乔西努力将这种权力规训合理化、合法化,甚至以缺少“勇气”来说服自己去克服被规训过程中的不适感,但她始终无法与内心深处的自己和解。小说用大量篇幅描写乔西的生病状态,虽然作者没有说明具体病因、疾病名称以及治疗方法,但从含糊的言辞中能大致推断乔西的病与接受基因改造有一定关联。由此可见,乔西的病在此并非病理学意义上的疾病,而是对日常意识形态的批判,具有丰富象征和隐喻意义。乔西在患病后常常被禁锢在家中,出门须由母亲或管家批准并受到严密管控,可以说,乔西常常处于在家中“隔离”的状态。《疾病的隐喻》中,“一旦被隔离,病人就进入了一个有着特殊规则的双重世界”[7],乔西因病被隔离是权力结构作用的结果,也给她提供了在特殊规则中形成自我认知的契机。从这一层面看,乔西的病不仅仅是见证克拉拉太阳信仰的客体,更隐喻着理性与情感、权力规训与内心真实的交锋过程。权力规训作为病原体,引发了乔西的病,虽然她也曾与病原体和解,努力接受权力的规训,甚至一度以为接受权力规训是理所应当的正义明智之举,但这显然无法抑制病情的进展。乔西在两个时间节点过后病情明显加重,而这正是乔西完成自我重构的关键性时刻:第一个为克拉拉与克丽西摩根瀑布远足回来几天后,第二个为克丽西一行人进城为乔西“画像”归来十一天后。
乔西第一次生病卧床是在参加交流聚会和被母亲禁止去摩根瀑布后。在交流聚会中,有的孩子对没接受过基因改造的里克品头论足,也对克拉拉指手画脚。在克拉拉没有做出那些孩子们要求的指令后,他们开始讥讽克拉拉,乔西也随声附和自己原本讨厌的孩子们,言明自己确实应该要一个B3型号的AF。乔西渴望在群体中获得他人的认可并达到母亲对自己的期待,于是当里克和克拉拉受到他人伤害时选择保持沉默甚至附和,不知不觉成为了“平庸之恶”的一份子。正如石黑一雄在访谈中提及:“我想我们都有一种自然的本性,总是要找一个罪犯,一个有过失的人,而不是为整个文明的失误共同承担某种集体的责任。我觉得许多坏事发生正是因为有这些大事件的缘故,那些道德不好不坏的平庸的人成为促成这些大潮的因素,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其他什么皆然。还有,大多数人无能为力,只能随波逐流,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回顾20世纪时所意识到的诸多痛苦之一。”[8]乔西在交流聚会中所呈现的正是“平庸之恶”的实质,反思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在权力规训下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缺乏挑战群体话语权力的勇气以及介于这两种情况之间的认知模糊状态。从她生病卧床期间与里克进行泡泡游戏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乔西更偏重于最后一种情况。
小说花费大量笔墨细致描写了乔西与里克进行泡泡游戏的几次场景,对其进行分析可以较为清晰明了地透视乔西自我重建的过程。泡泡游戏始于乔西第一次因病情加重卧床休息,里克前来探望,游戏规则为乔西画画,并在一些人物旁绘制空白泡泡框,让里克凭借自己对人物的理解填上对应人物所想。在小说详细描述的第一幅眼球画中,里克并没有在空白泡泡中填写内容,他学得画中的女孩看起来乐意并希望眼球们盯着她看,乔西却坚决否定了里克的想法。不难看出,这幅画与乔西在交流聚会中的感受有关,画中的人物事实上就是她自己,描绘的正是她在其他孩子的目光中感到恐惧、紧张等不适感的真实心理状态。而里克描述的则是乔西在交流聚会中表现出的合群、乐于社交的一面,他对乔西说的话可视为他试探乔西内心的一种方式。从两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乔西在交流聚会上因内心恐惧而选择伪装,她的内心实际上是排斥社交。泡泡游戏中第二幅图片描绘的也是交流聚会上的场景,中间水滴形的小人是乔西,她在人群中显得极易被忽视,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形体,这体现出乔西对融入集体的渴望和对被孤立忽视的排斥。里克在泡泡中写道:“那些聪明孩子以为我没有形体,但是我有,我只是把它藏起来了,因为谁想让他们看见呢?”[2]156-157可见,他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带入其中,不愿一味迎合自己所不屑的权力关系构建的社会,而面对他人的冷眼和讥讽则摆出超然其外的姿态。第三幅图中写着:“真希望我能走出去,去散步、去跑步、去踩滑板、去湖里游泳。可我不能,因为我妈妈有勇气。所以,我就只能躺在床上生病了。对此我很高兴,我真的很高兴。”[2]164这几句话与画面格格不入,这是里克在两人意见出现分歧时写下的带有情绪化的话语。乔西看后,将不敢开车、没有社交的里克母亲海伦与自己不断向社会体制金字塔顶端一次次冲锋的勇敢母亲克丽西相比较,责备里克不努力考进大学。这让原本就排斥社会权力话语的里克彻底意识到乔西与自己的价值观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他感到失望、愤怒,并写下了第三幅图泡泡框中的语句,从此讽刺乔西被权力话语影响后主动选择自我改造的行为。
从图画中不仅可以清晰看出里克与乔西在自我认知方面的分歧,还可以看出乔西在被社会理性建构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不适感和对里克亲密情感的依恋。通过泡泡游戏,乔西在认知困境中尝试进行自我逻辑的建构,但是,哪怕她努力赋予权力规训下的异托邦以合理化的意义,她还是无法割舍内心对里克的真挚情感。因而在进行第三幅图的泡泡游戏时,她虽然在语言上贬抑里克和他母亲的行为和选择,但依然在画面中表达了与里克理想互动的情景。以泡泡游戏为契机,乔西渐渐意到到社会规训对情感的束缚和局限,在表达向里克道歉的画中可以看见乔西最终作出的价值选择——与里克共同面对尖锐社会,不改初心。乔西以图像式的游戏作为自我内心真实的表达方式,价值天平虽在权力结构和自我意识之间上下摇摆,但终究倾斜向了后者。在里克和克拉拉的辅助引导下,乔西在病中逐渐完成了对自我认知的重建。
3 主体意识的还原
作为现有社会秩序下的信服者和受益者,在乔西病重到弥留之际这段时期,克丽西一向以社会已有逻辑为价值依据进行人生命题选择的坚定信念发生了动摇。她与里克展开了一段关于“谁才是赢家”的重要对话,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两难境地下经受了内心的煎熬与拷问。克丽西质问里克:
“你真的相信在你俩当中,你才是最终的那个赢家?如果你确实这么认为的话,那就请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你到底赢了什么?看看吧。看看你自己的未来。”[2]354-355
克丽西认为里克没有接受基因改造因而“下了小注”,理应收益寥寥、未来惨淡;乔西接受基因改造,“下了大注”,如果能赌赢,收益便是“一个对得起她这般活力的未来”。两人交谈至此,可以说克丽西依然以物化、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现代性话语所倡导的社会领域丛林法则作为价值判断依据。面对深信金钱、权力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关键标准的克丽西,里克神情激愤,并转达了乔西希望他在合适时机带给她母亲的重要口信:
“她说,不管现在发生了什么,无论事情最后的结果如何,她都爱你,永远爱你。她非常感谢你能做她的母亲,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换一个母亲,一次都没有。她就是这么说的。她还说了些别的。关于接受提升的问题。她想要你知道,她不想要任何别的选择。假如她有能力从头来过,这回由她说了算,她说她会和你做出完全一样的选择,你永远都会是她所拥有的最好的母亲。”[2]355-356
听完这段话,克丽西原有的价值体系开始坍塌,在她震惊之时,太阳特殊的滋养也恰好来到乔西房间,从此乔西逐渐痊愈。可是乔西究竟为什么会奇迹般地痊愈?克拉拉信仰的太阳所提供的特殊滋养固然是一方面,但从内容的推进和时间的吻合度来看,更重要的原因是从乔西给母亲的口信中乔西终于完成了对自我主体意识的还原——她爱的是母亲本人而非她作出的种种决定,她对母亲的情感不会因社会规训的要求而改变,哪怕因为出于对母亲的爱。她接受社会和他人对她价值观的塑造,但真挚的情感和心灵隐秘处真实的自己将永远不会因权力规训而动摇。在病重之时,乔西终于意识到,在人生中究竟什么应被视若珍宝,什么当被弃如敝屣,什么能亘古恒久,什么是过眼云烟,从而最终形成了对理性与情感、荣誉与信念、才华与德行非单一评判维度的认知。乔西的痊愈和上大学前的秘密目标更加佐证了她内心的“真实”——即使她表现出与社会权力规训相一致的行为,但依然保持着清醒的主体意识和植根在情感基础上的对朋友和家人永恒的爱。
乔西上大学后,克拉拉被弃置在杂物间,最后被送到堆场,在这里她邂逅经理时说道:“母亲、里克、梅拉尼娅管家、父亲——我永远都无法触及他们在内心中对于乔西的感情。”[2]385人对待人与人对待机器人的本质区别正是感情上的差异:人与人间的真挚感情是永恒的,不因人外在形态或表现的变化而改变,人对机器人的感情更趋于对待商品一般,注重功用而非情感连结。小说至此,所有人物都完成了自我认知,也标志着作者对人类独特性的探索完成,文本到达了本体论层面的哲学命题探讨。石黑一雄以无数房间套着无数房间的房子喻指复杂而多样的人类情感,这与德勒兹的“褶子”理论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德勒兹认为,“连续体的分割不应当被看成沙子分离为颗粒,而应被视为一页纸或一件上衣被分割为褶子,并且是无穷尽的分割,褶子越分越小,但物体却永远不会分解成点或最终极。如同洞里有洞一样,总是褶子里还有褶子。物质的统一性,即迷宫的最小元素是褶子”[9]。无穷无尽而又在不断变幻改变的情感“褶子”,复杂且无法用理性认知,但这始终是我们生而为人独特于其他物种并应当珍视的部分。
《克拉拉与太阳》中,虽然科技及其所代表的理性思想无法指导对肉身化自我的认知,但作者在尖端科技面前仍对人性持有乐观态度,将人类包括爱、恐惧、孤独、勇敢等内在的情感表达,独立进行价值判断,选择的主体意识细腻地传达出来。同时,作者在权力话语中深层次地探讨人们对不同社会角色的认知与接受,将具有利他性的机器人置于人类社会中,探索二者的异同和社会定位:在未来社会中,科技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可能会致使人类自我真身和主体意识成为缺席者,人们展现在社会面前的是被话语规训过后的模样,真正的内心情感却被隐蔽起来,以致于自己都不再相信,甚至怀疑人心是否真实存在、人和机器是否有区别。
4 结语
石黑一雄在创作中一直关注国际化题材、人类生存状况和普遍人性。虽然《克拉拉与太阳》的叙事地点为美国,但其所讨论的是人类共同命题,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克拉拉与太阳》中,作者借助机器人克拉拉的视角,回忆式讲述了乔西的情感表达和自我认知形成的过程,并将宗教、环保、孤独等元素融入其中,探讨人类的生存困境,发出对生命意义的诘问。正如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那篇著名演讲《我的二十世纪之夜以及其他细小处的突破》中所言:“小说故事可以是娱乐,有时是教诲或争辩一个观点。但对我来说,最基本的就是情感沟通。”[10]不同于石黑一雄的首部科幻题材小说《别让我走》中对人类残忍不仁的剖析和对人性异化造成悲剧的失落,石黑一雄在小说《克拉拉与太阳》中以乔西为情感纽带的连结点,探索了处于权力规训下但依旧闪耀着光芒的人类情感。正如小说封面设计使用的红、黄、蓝三原色,它带给人们的是爱、希望和温暖。从乔西主体意识被权力规训、遮蔽到重建,再到最后完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工具理性”造成人异化的社会中,对“价值理性”的呼唤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我们无法打破现代化的铁笼,但我们可以真诚地去正视这一切,珍视人之为人才可能拥有的各种美好情感,并始终忠于自己,这是我们现代人能够去做,也应当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