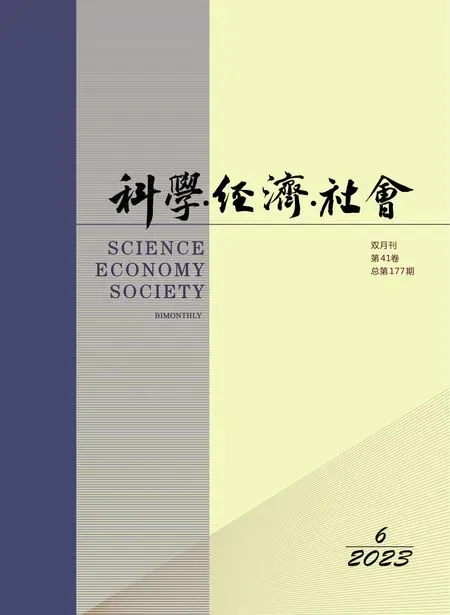后电影,奇点与创伤主体
姜宇辉
刚才李洋老师和蓝江老师都谈到,我们之间有一个“镜像关系”。其实我跟李洋更像是一种“手性关系”,我们对称但逆反,呈现出的是一种“inversion”。这两年,我们之间有一些地方是很相似的,尤其今年写的文章。马上还要出一本讨论电影的书,我把它叫作“Image Without Becoming”——没有生成的影像,来自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的文章《无生成的时间》(“Time Without Becoming”),从物性的角度来谈论时间。李洋刚刚还谈到了“digital touch”“digital index”,即从数字的角度能否重现影像与世界之间的索引关系,我在刚写完的一篇文章中恰好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刚才的讨论还谈到了“无物之像”,其实我认为它有一个更好的说法。去年,我在一篇讨论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和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的文章中①姜宇辉:《“姿势”的意义:技术图像时代的“无根基之恶 ”——从阿甘本到弗卢塞尔》,《文化艺术研究》2022年第6期,第1-16页。,运用了一个核心概念,即“无根基”(groundless),我认为“无物之像”更应该被称为“无根基的影像”或“无根基的图像”,而不仅仅是“无物”。“物”仅是一种存在方式,或者说“物”是一种对象。但是,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数字时代或数字元宇宙的世界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虚拟的数字世界是循环的、抽象的,在其中通过数字可以生成一切,也并不需要数字之外真实的实在世界,这首先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种世界/图像本身“无根基”的特性。图像不需要根基,图像可以自己生产自己、模拟自己,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核心状况。
其次,我们的讨论可以从“图像”的无根基状态转向“技术”,是技术把我们的时代推向了无根基状态,这也是阿甘本和弗卢塞尔提出的观点,分别对应“去本原”(anarchy)与“无根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无根基”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其实也使用了这一概念,即技术把我们推向了无根基的时代,它包括生命的无意义性和世界的无意义性。这也是我最近想去回应的一个问题:面对一个被技术抽去根基的世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回应它,是抵抗还是逍遥,是拯救还是逃逸?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所以,我们不应该单纯局限在“物”的范围内讨论,而应从哲学的高度展开。
我想从四个角度来回应这次的主题。
第一,关于“电影性”;第二,关于“奇点”的两种不同的时间性路数,一种来自阿甘本,另一种来自德勒兹;第三,对“主体性”问题的反思;第四,重点讨论图像在这个时代发生的变化,从“index”到“icon”再到“symbol”的演变过程。今天这个时代的图像实际上是“symbol”,它是循环的,自主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这样一种框架、座驾之中跳出来,重新找回图像的物性,找回图像与世界的连接。
第一,关于“电影性”。刚才在讨论有关电影性这一主题时谈到,“短视频是不是一种电影”,这个议题让我重新反思了“电影之为电影性的本性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在谈论任何东西的本性时,都涉及两个时间性维度,一个是过去,一个是未来。我们可以从过去的角度来说,这个东西从发端、起源的状态是这样,决定了以后的发展,亦即它的本质也是这样。比如说,电影在发端之处有两个起源,一个是“documentary”,另一个是“attraction”,前者是卢米埃尔兄弟,后者就是梅里埃。卢米埃尔兄弟所界定的电影是“记录”,即用摄像机对准外部的现实,记录火车进站、记录从工厂大门里面走出来的工人。相较而言,梅里埃创立的“吸引力电影”则是把电影变成景观,变成叙事,变成剧场。我们认为,这两个方面是界定“电影之为电影性”最初的两个源头。但到后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了,我们将它称为“essay film”,即“论文电影”或“散文电影”。“essay film”并不仅仅是一种风格或者类型,它建立起来的其实是“图像与思考”(image 与thinking/thoughts)之间的关系。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Alexandre Astruc)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电影的未来》(“The Future of Cinema”),他在开篇说道,电影最重要的功能并不仅仅在于记录或叙事,而是要用图像的方式来思考(thinking in pictures),只有在电影这一媒介之中,我们才能找到图像与思考/人类思维之间最根本性的关系。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对“essay film”感兴趣的原因。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哲学与电影之间的连接,找到影像与主体之间各种各样的连接。
我对电影的研究是从“后电影”(post-cinema)入手的,我列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拓展电影、电子游戏等,来看它们是否能够成为界定“后电影”的典型形态。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essay film”恰恰可以作为“后电影”——电影之未来,电影朝向未来的一种全新的可能性。电影的未来是什么?电影的未来不在于延续电影的过去和传统,而是要以思想的方式建立起电影与哲学之间的连接,把电影作为激发人类思考的一种面向未来的可能性,这才是电影真正的本性。蒂莫西·科里根(Timothy J.Corrigan)和劳拉·拉斯卡罗利(Laura Rascaroli)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essay film”的,他们认为,电影的本质还没有被实现,其本质在于它的未来,而未来在于它可以用影像的方式去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说,短视频或许可以作为电影性的一个全新形态。“essay film”让我们打开了更为开放的可能性,它的重点在于,电影创作者的思想要通过思考与不同的观众进行互动,从而建立起人与影像之间更为开放稳妥的关系。那么,从这个角度说,电子游戏和短视频都可以是电影的未来形式。
第二,关于“奇点”。蓝江和吴冠军经常会使用“奇点”,尤其冠军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示,他是将“奇点”作为德勒兹的概念来讨论的,同时还引用了阿甘本的“剩余的时间”概念。这两个时间其实并不一样,一个是肯定的,另一个是否定的;一个是连续生成的,另一个是断裂创伤的。阿甘本《剩余的时间》(The Time That Remains)这本书中最重要的两个理论来源,分别来自列维·施特劳斯的“漂浮的能指”和本雅明的“弥赛亚时间”。这两年我自己的研究开始慢慢转向了否定性的线索,我认为“奇点”可能也具有这两种不同的形态。“奇点”的第一个形态就是在德勒兹的意义上,它是发生转折、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practical moment)。《褶子》是德勒兹讨论“奇点”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德勒兹谈到,世界不是按照直线运动的,它是按照曲线运动的,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而曲线会展现出森罗万象的新鲜方向,同时,不同的曲线又纠缠在一起。但当直线变成曲线时,它必须有一个转折的时刻——变弯,而变弯是数学和物理意义上的,变弯的时刻会有力量积聚在那里,有各种各样新的东西在那个点上缠绕,以至于它不再按照原来的方向运动。
比如,原来直线是从A 点到B 点,但突然有一点开始向C 点或一个分叉点发生偏转,德勒兹在书中引用了一个经典的形象,就是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世界在每个点上都可能分叉,那个分叉点就是“奇点”,在分叉点上会有事件发生,有偶然性敞开,也具有多样性,会被不同的力量缠结在一起。因此,德勒兹所说的“奇点”是非常积极的,对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期望。按照德勒兹式的逻辑思维,技术的进化或人类的变革将没有任何悲观之处,因为生命总要转折,世界就是在转折的地方才拥有新生,才能有新的东西被生产出来。但如果我们回到阿甘本,回到本雅明,就完全不一样了。
本雅明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绝对的内在性”(immanent absolute),他讲的“奇点”不是在我们的生命或世界中打开可能性向度,而是绝对真理突入到历史中,并产生一种断裂。我更多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奇点”的概念。所以,“奇点”不仅仅是人类生命在技术的加持之下,生生不息地向前创造,而是在本雅明或列维纳斯的意义上来讨论,为什么它是一个创伤?我们会看到,当未来失控时,当物和技术变成一个“庞大之物”(gigantic)的时候,它其实是突兀进来的,它并不是我们内在生命的表达,也不是连续地、生生不息地创造。相反,我们时刻都会觉得外面有一种力量,它突兀到我们的历史中,打断了历史发展的过程,让我们感受到痛苦,让我们面对死亡的深渊,让我们认为所有连续的东西都是难以为继的。它就是一次“intrusion”,是“rupture”,是我们所说的“创伤”(trauma)。在这个意义上,这两种“奇点”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是“创造”(creation),但另一种是“创伤”。
第三,对“主体性”的反思。主体性问题对于德勒兹式的“奇点”而言并不重要,即谁成为主体是不重要的,因为生命永远在生生不息地创造和变化,它永远要打开新的维度。至于谁会成为主体,这个主体出现在什么位置,这些并不是关键性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要将生命不断向未来推进下去,要将其新鲜的形态展现出来。但如果我们回到阿甘本,回到列维纳斯,便会发现,在创伤之处,在否定性的地方,主体性问题逐渐凸显了出来。因为从生命创造的角度来说,变革可能是一个积极乐观、朝向未来的过程,但是,当生命的创造落实到每个个体身上时,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如何以一种主体性的方式呈现,或者说又如何承受这种创造?
很多后人类主义者都会从“体验”(experience)的角度来讨论主体性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主体性,谈论这些关于体验的东西?这是因为当我们从本体的角度来看,在生命生生不息地创造中并没有主体的位置,也不需要主体的位置。德勒兹思想中有一个概念,被称为“游牧主体”(nomadic subject)。但当游牧成为主体,当我们必须随着技术、物质性和网络不断去运动发展,每时每刻缠绕其中,无法选择自我的命运时,我们又何以能够将自己称作主体(subject)?所以,“游牧主体”本身是一个非常嘲讽的词,当我们游牧的时候,我们将不可能成为主体。但是后来像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这些后人类主义者,他们想从游牧主体的角度重建主体性的地位,就像谢亚洲老师刚才提出,在一个技术的体系里面,我们被卷入其中,但我们仍然还可以具有主动性,那么,这种主动性到底在哪里?布拉伊多蒂就是从“体验”的角度来论证的,她提出,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还在生存,并意识到技术在伤害我们,技术在推进我们,但当我们有意识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还活着,我们能够体验到自己的生命。
在此之前,我一直是从传统人文主义的立场来谈论主体性的问题,但这与我今天谈论的主体性从本质上来看是完全不同的。之前对主体性的谈论可能与康德的先验主体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为我还是想捍卫一个自律的、自主的、反思的、理性式的主体性问题,但在今天,我对主体性的讨论更多是放在体验、创伤与脆弱。我想引用一下德勒兹的一句话,即所有的主体在今天都是“受害者”(victim),齐泽克好像也使用过这个词,他说,我们思索主体性的起点不是将其作为能动者,而是作为一个受害者。我们通常是在被迫害的时候才会发现,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像康德一样勇于使用自己的理性来规定人类历史。今天有很多对“创伤”“脆弱性主体”的谈论是在女性主义思想脉络之中的,这是因为女性在历史上是最受迫害的一个群体。当然,儿童也受迫害,但儿童不会思考,儿童无法将自我表达为一个脆弱性的儿童主体,儿童要等待大人去诠释。所以,女性主义也成为我最近很多研究关注的一个重点,蓝江老师最近也翻译了很多关于女性主义的著作,比如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的著作。可能在座的诸位老师和同学没有注意到,晚近二三十年,最重要的哲学家基本上都是女性。
最后,回到图像的问题。李洋刚才谈到图像有两极——“文”和“画’,W.J.T.米歇尔也谈论过图像的两极,他认为,一极是语言,一极是物质性,我后来写过很多篇文章去讨论米歇尔理论存在的一些问题。因为皮尔士(C.S.Peirce)强调,“文”作为“symbol”与“图”作为“index”之间,其实还存在一极“icon”。这意味着,图像或者绘画是夹在两极当中的。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说,“index-icon-symbol”对应“摄影—绘画—电影”的演变过程,图像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生成为一个自我相似、自我指称、自我循环的体系。今天的数字时代也是这样,它越来越失去了与世界、与index 之间的关系。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也指出,今天的数据或后媒介伦理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可以被称为“计算+ data”,今天所有的艺术都是“data + computation”,意味着媒介自身的边界已经消失了,我们无法去界定绘画、文学、戏剧等各种艺术门类,所有东西都是数据处理的,包括绘画和电影。因此,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把“digital”和“index”重新连接在一起,让我们自身不再陷入数字宇宙之中,或陷入数字座驾之中,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数字角度出发,找到与世界之间的“index”,即索引的源头,或者生命的脐带。因为我们原来就从那里来,图像就是从那里来的,包括福柯所说的“大地书写”,以及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都在强调我们的“像”与“万物”之间是相连的。这也是昨天科林谈到的第一种文艺复兴的知识型,相似交感、互渗交织,“像”与“物”之间的交织就是图像的源头。《周易》中说道:“象也者,像也”,也是同样的含义,它是发生的事件,是发生在世界之中的。我们是通过对“像”的考察,比如对“画像”的考察去理解这个世界,以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趋势和变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赞同李洋老师未来的研究方向,但我认为可能并不仅仅停留在“物”,而是要停留在“物”与“图像”之间的对抗,既分离又连接的“手性关系”。
我先谈到这里,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