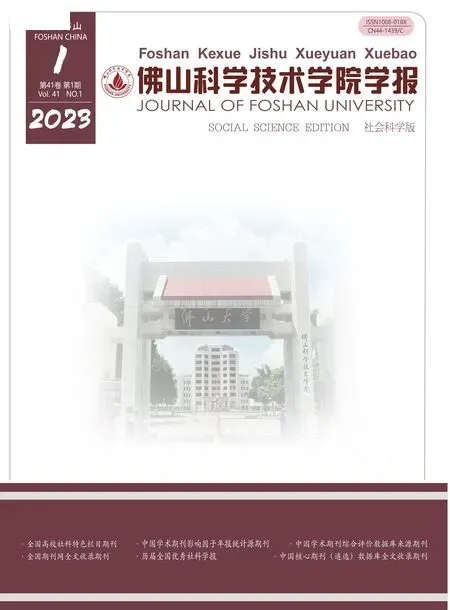走向他者的政治
——论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
胡良沛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安庆 541006)
韩炳哲作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尽管其以对数字信息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分析和批判闻名于世——《在群中》《倦怠社会》《透明社会》等著作无不以批判精神状况为主要任务,但这并不能说明,韩炳哲的思想仅聚焦于精神之类的无形之物。其实对精神状况的分析和批判最终还是对数字信息时代现实问题的思考,而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数字信息时代人类的精神状况,就充分说明了韩炳哲的批判具有的强烈社会现实感。《精神政治学》不仅表达了韩炳哲的数字精神政治思想,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出数字信息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病症。韩炳哲如何对数字信息时代的人类精神状况作一种政治解读?他的解读又有何意义?弄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韩炳哲的数字精神政治思想,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甄别当代社会人类精神状况的政治问题,并为解决问题提供新视野和新思路。
一、“精神政治”:一场“自我肯定”的骗局
韩炳哲对“精神政治”的批判之所以以人类的精神状况为切入点,是因为在他看来“各种精神疾病,如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边缘性人格障碍或疲劳综合征主导了21 世纪初的疾病形态。”[1]3所以,21 世纪的政治问题就必然不能断开与精神世界的关联。也就是说,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必然要从福柯的“生物政治”转向到“精神政治”。因而要想准确把握数字信息时代的政治,就必须关注人类的精神状况。
在韩炳哲看来,“精神政治”是在人的精神层面实施的一种极为隐蔽的管理方式。韩炳哲表示:“新自由主义政权的权力技术采用了一种微妙的模式。它并不直接掌控个体。确切地说,它要做的是让个体从自身出发,自己去影响自己,让环境威力法自发形成,同时,还会把这种法则诠释为自由。”[2]37简单来说,数字信息技术其实是利用大数据对人的心理进行画像,从而达到利用人的潜意识进行管理的目的。这与“生物政治”存在根本差别。“生物政治”通过对人的身体、生命进行控制、威胁或伤害以达到管理目的,即使按福柯所言,“生物政治”亦可对人的心理产生“规训”作用,但这种“规训”带有明显的强迫性。而“精神政治”并不以人的身体、生命为管理的直接对象,也不以控制、威胁或伤害身体为手段。“精神政治”的对象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手段主要是“引诱”,即引诱人们自觉去做某事。这种“自己影响自己”的方式看似节约了管理成本,但在韩炳哲看来,其实是一场骗局。
“精神政治”的独到之处在于其手段并非依托于一种异己的对抗力量来开展,而是通过“自我肯定”来实施。自己如何去影响自己?韩炳哲认为,这种方式的精髓就在于“点赞”。“点赞”—“Like-Button”,最早由Facebook 于2009 年推出,该功能一经推出,立刻让Facebook 用户暴增2 亿,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广告收益。随后,各互联网商家开始争相推出“点赞”功能。然而,“点赞”并非仅是一项单纯的技术创新。诚如韩炳哲所言:“‘点赞’就是以数字化的方式说‘阿门’。”[2]17
首先,“点赞”在技术上的设计极为巧妙。即我们可以对信息进行肯定,但却不能否定,譬如很少的App 有例如“差评”或者“不喜欢”的快捷按钮。也就是说,在数字信息时代,“肯定”是最主要的表达方式,而“否定”则用沉默替代了;其次,“点赞”虽然能肯定各类信息。但可以“点赞”或肯定的都是经过人为设计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尽管我们还可以“肯定”,但我们“肯定”的并非是来自“他者”的信息,而是“自我”的画像。可以说,数字信息技术的运转逻辑既不同于电视,也不同于互联网。电视主要是从“他”到“我”的单向传播,互联网则是由“我”及“他”的单向选择,而数字信息技术的运转逻辑却是技术与人对“同一性”的双向选择——因为数字信息技术仅为“我”推荐符合或相似于“我”个人“画像”的数据,而“我”也会选择符合个人喜好的信息展开交往。那么数字信息社会的交往其实就是一种“照镜子”的活动。所以,数字信息技术让我们遇到的“他者”,其实是一个无异质性的“同者”,而“我”在数字信息时代最主要的表达——“肯定”,也就是对我自己或者是我本来就一定认同的事物的肯定,即“自我肯定”。
在韩炳哲看来,“精神政治”的“自我肯定”之所以是一场骗局,因为其实质上是数字和资本的“把戏”。
第一,数字的骗局。在数字信息时代,世间万物都要被强行数字化,因为一切信息交流和技术运转都不过是“0”和“1”的电信号转化。这也是我们将这个时代称为“数字信息时代”的原因。“0”和“1”转化而成的数据正是当代社会中人们赖以生活和交往的基础。美国统计学家爱德华·戴明甚至声称:“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3]62如若不然,即如果与他人之间的交往或者从事的劳动脱离了数字技术这个必要的中介,或者是拒绝被数据化,那么个人的生产和生活就必定无法在数字信息时代展开,譬如当拒绝App 获取个人信息的要求时,App 也同样会拒绝人们使用它。如果长此以往,就不仅意味着人类将与这个时代“脱钩”,而且意味着人将脱离现实,这显然行不通。所以,被数字化或数据化就成了人类的一条不可抗拒之路。韩炳哲将这样一种万物皆被数字化的社会称之为“数字的全景监狱”或者是“透明社会”。因为“我们的每一次点击都会被保存下来,我们操作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追溯的。我们无时无处不留下数字痕迹。”[4]102这不仅意味着人类活动的每一步都可能受到监控,而且还使人类活动始终符合数字技术运转的逻辑成为可能。数字信息技术发展得越成熟,就越是要更多的人去使用它,而越多的人使用数字信息技术,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人类活动都在主动贴合数字信息技术的逻辑。这就是数字的骗局。
第二,资本的骗局。为何必须使一切事物都数据化?为何人类的每一步都要受到数据的制约和掌控。我们认为,这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技术要素问题,正如芬伯格所言:“社会意义和功能理性是技术不可分割的、交织在一起的两个维度。”[5]18所以任何技术,包括数字信息技术就必定会融入一定的社会因素,也就是人的因素。因而数据的骗局的原因也就只能到人的因素中寻找。按照芬伯格的观点:“利益是分析一切事物的出发点,因为它是历史发展中最明显、最有力和最持续的力量。”[6]21所以,数据的骗局就一定是缘于利益。这与韩炳哲的分析不谋而合。韩炳哲对数字信息时代的批判,最终也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在韩炳哲看来,“新自由主义”并未给人类社会带来真正的自由。韩炳哲表示:“资本的自由通过个体自由得以实现。自由的个体因此降级,成为资本的生殖(升值)工具。”[2]5因为在数字信息时代,个人越是自由,其在数字世界的活跃度就越高,活跃度越高就意味着会创造更多的数据。众所周知,数据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新型资本,因而数据越多,资本的积累就越多。所以,我们就不难知道,之所以要让这个时代的一切都数据化、之所以一切都要遵循数据的运转逻辑,本质上仍是为了资本积累的目的。
总之,“精神政治”在一方面通过将管理主体变为“自己”、将对象变为“精神”,并通过“自我肯定”的方式消除了对抗性,让不平等不合理的管理变得不明显,从而消除了人们对其行为的怀疑,也免除了政治应负的责任。然而,这场骗局终究要使人类陷入更深层次的危机之中。
二、自由的危机和剥削的加深
诚如唐·伊德所言:“没有技术的代价就是被封闭起来。”[7]14但“没有技术的生存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7]14所以从现实来看,技术必然存在,因而它的使命就必然要打破“封闭”,获得自由。可以说,追寻自由是技术与生俱来的使命。数字信息技术作为技术的一个种属,当然也应具备这项使命。然而,当今的数字信息技术却成了一种“枷锁”,其将人们锁定在数字终端背后,就像柏拉图的“洞穴”一样,使人沉迷于自由的假象。
韩炳哲认为数字信息时代的自由反而是一种强迫。在数字信息社会,虽然人人都可以在数字终端随意发言或展开活动,自由地获取自己喜好的信息,这看似是一种自由,但实际上,这些人类的活动大多是被数据和资本在不经意间强制引导的。可见,“人人都能发声”“畅游数字世界”之类的自由其实都是一场骗局。数字信息时代的管理不再依靠对身体的威胁、也不再取决于强烈的对抗,因为这里根本就无对抗,只有对管理对象在精神上的引导,使他们误以为自己也是管理的主体。这样,误认为自己是管理者的被管理者就乐于用“主人”的身份进行自我管理,甚至是“自我压迫”“自我剥削”。这就难怪韩炳哲会断言:“功绩至上的主体自认为是自由的,实际上却是一个奴仆,是没有主人强迫却自愿被剥削的绝对的奴仆。”[2]2-3
在韩炳哲看来,自由之所以会陷入更深层的危机,直接原因是由资本打造的数字信息技术让“他者”消失了。韩炳哲认为:“‘自由’原本意味着‘于朋友处’。”[2]3“只有在和谐幸福的共同关系中,我们才能感知到自由。”[2]4这其实想告诉我们的是:“自由”的关键不仅是洛克等人指的未受约束的状态,或者是康德和斯宾诺莎说的自主自觉自律的状态,又或者詹姆士等人指的“两可”的状态。更重要的是,“自由”的生成有其必要前提,这个前提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联合体”,即只有在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才有可能。于是我们可以知道,即使是个人自由,也非个人之事,个人自由绝对少不了与他人之间的交往。所以,真正的自由是“我”与“他”之间的相互成就。然而,数字信息技术却让“他者”消失了,那么自由又将如何产生?
自由在人们心中一直是一个神圣的名词,也是一切时代中所追求的价值,因为它意味着人类不再被强迫,可以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然而,为何在数字信息时代的今天,“精神政治”反而利用自由制造出了一场骗局?在韩炳哲看来,仅仅追问到“他者”仍不够,必须追问到“他者”为何消失,才算是找到最根本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就是“新自由主义”。诚如大卫·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判断:其“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8]22在韩炳哲看来,如果自由仅仅是经济精英为了扩大资本积累并恢复其权力而炮制出的口号,那么自由也就仅仅是一种形式、是一种假象。所以,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价值目标就必将陷入更深层的危机之中。
在韩炳哲看来,自由如果仅是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炮制出的口号,不仅不能实现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价值目标,而且还会将人类社会推向另一深渊,即加深剥削的程度。对韩炳哲来说,自由和剥削同属于政治的核心问题,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说明其对“精神政治”的批判是要反对剥削,而且是反对一种新型的剥削形式,即“自我剥削”。韩炳哲认为:“自由和剥削合二为一的权力技术,成了一种自我剥削的形式。”[2]38其实,人类在数字信息时代的任何活动,都可以说是一个劳动的过程。因为只要人们打开任何数字终端,就能即刻生产数据。众所周知的是,数据早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劳动产品,甚至是资本的新形式,只是其价值一般只在特殊团体中才能兑现罢了。所以,如果说,过去的劳动生产是被迫固定在特殊的时间和场所中,并将自己无差别的劳动凝结在对象中,那么数字信息时代的劳动生产就是劳动者在数字终端存在的任一空间内,主动将自己的剩余价值贡献出去。同时,如果说过去的生产是通过人与对象合作而生成的,那么今天的数据产品就是自我生成的。之所以说这样的生产模式会加深剥削的程度,一方面是因为生产数据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大减少,但是数据的价值却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自我剥削”大多是以一种娱乐的形式进行的,这意味着“自我剥削”这种行为具备一定的主观意愿,因此剥削的实质就很难被意识到。这种带有一定享乐形式的劳动就消除了人们在被剥削时的对抗性,那么剥削的阻力就会减少,因而剥削就更易开展。
三、走向他者:政治
在韩炳哲看来,“精神政治”的“自我肯定”消除了“他者”,这是一种无对抗性的政治,因而就可以通过引诱等方式,平和地实现管理。所以,要走出自由的危机和剥削,就必须要走向“他者”。
“他者”的概念由来已久,但从胡塞尔在认识论上提出“交互主体性”的概念之后,才正式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可以说,自“他者”的概念提出后,主体性就开始走向黄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者”会使“人”边缘化。其实,尊重“他者”反而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就指出:“对于我的存在,别人是少不了的”。[9]25“他者”的概念虽然强调“我”之外的他人、他事、他物,但实际上是对“我”与“他人”的共同关怀。因此,“他者”的意义实际上是促逼着人们走出主体性的狂妄自大,在与“他者”的交往中成就自己,也成就他人。韩炳哲的“他者”概念与此类似,但也略有不同。他曾用生物学上的免疫原理形容“我”与“他者”之间交往的意义,说正是:“自我抵御了否定性的他者,从而确立自身。”[1]7其实,这不仅强调了“他者”与“我”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也指出了“他者”的异质性和对抗性。
“他者”在韩炳哲看来,不仅是另一个人类主体或他物、他事。在《他者的消失》中,韩炳哲认为,人的交往应当设有门槛、要保持距离,甚至要让人们心生恐惧,这种在现代社会反人类的思想属实难以理解、匪夷所思,但这些却恰恰是必不可少的“他者”必然带给人们的结果。当然,韩炳哲绝非是要走向某种神秘主义,因为“他者”带来的门槛、距离,甚至是恐惧,对韩炳哲来说正是“事件”的发生。韩炳哲表示:“思考可以通往全然他者,它会使同者中断。其中蕴藏着它的事件属性。”[10]6“事件”意味着连续性的中断,而这种中断的出现就意味着过去那些被隐藏的问题将暴露出来,问题的暴露就是人类新认识的开始。在韩炳哲看来,数字信息社会的问题就是不会发生任何“事件”,因为每一个人的交往都体现了一种“固步自封”,这种“固步自封”使得“精神政治”的问题无法暴露,因而自由和剥削的问题就只会越陷越深。“他者”为何会产生“事件”?关键在于其与“我”的不同和对抗。诚如韩炳哲所言:“若没有‘对立’,人就会重重地摔在自己身上。”[10]63或者说,也只有异质性和对抗性的存在才意味着“他者”的存在。而“他者”的异质性,必然能形成与“我”的对抗,对抗一旦形成,就能够触发类似生命成长的免疫原理,就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带菌生活”:通过“带菌生活”才能刺激我们免疫系统发挥作用,也才能促进我们更好地成长发育。在免疫发生的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无论是“他者”战胜了“我”,还是“我”抵御了“他者”,其实都是创造性的发展自身。
然而,韩炳哲宣称:“他者的时代已然逝去。”[10]1因为诚如上文所言,今天的数字信息技术,是一个“自我肯定”的技术,这里并未让我们遇见更多的“他者”,我们只能遇见更多的“同者”。所以,韩炳哲断言:“如今的网络已变成一个特殊的共振空间,一个回音室,任何不同与陌生都被消除了。”[10]8这种将人类活动变为“独角戏”的行为,显然不合理。
在韩炳哲看来,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通过自我来实现其管理,以达到其剥削乃至资本与权力重构的目的,关键还是在于“我”,是“我”沉浸于一种自恋式的自我满足,才中了新自由主义的圈套。因此,“我”就成为让“他者”重现的关键。那“我”应该怎么做?韩炳哲认为,“爱欲”是关键,他表示:“唯有爱欲有能力将‘我’从抑郁中、从自恋的纠缠中解放出来。”[10]104因为人一旦具有了“爱欲”,就能“超越了工作绩效和能力的、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情态动词就是承认‘无能为力’。”[11]26而“只有承认‘无能为力,’他者才会出现。”[11]27也就是说,在韩炳哲看来,“他者”的消失是“我”不经意间在数据和资本的强制引导下,做出拒绝行为的后果,即是“我”无意识地拒绝了“他者”,因为数据和资本一直欺骗“我”,它们告诉“我”说:“我”无所不能。现在,只要“我”承认“无能为力”,“我”就能中断“我”在数字信息社会自恋式的满足,于是“我”就能自然地走向沉思,“他者”与“我”的交往也就消除了障碍,“他者”就会走进“我”。而“我”与“他者”之间的对抗就自然会打破“精神政治”的“独角戏”,数据和资本就再也不能“一意孤行”。
韩炳哲认为,一旦“他者”重现,那么“我”在与“他者”的对抗中就能反思数字信息社会的问题,数据和资本就不再能束缚我。就像“花儿之美归功于挣脱了经济束缚的奢侈”[12]77一样,“我”也就能不再束缚于数字技术的运转逻辑,因而我也就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政治也就能成为一种美的政治。
四、问题与意义
虽然韩炳哲的精神政治思想在理论上丰富了关于技术的政治批判理论,在现实上,“祛魅”了数字时代的管理模式,敲响了该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警钟。但遗憾的是,由于韩炳哲解决问题的方法存在巨大漏洞,最终也使其理论成为一种仅是停留在“解释世界”层面的“乌托邦”。
(一)问题:解决方法的乏力
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140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最大的问题是:虽然揭示了数字时代新管理模式以及该模式下人类社会,尤其是人类精神世界的问题,但在解决该问题的方法上却差强人意。
第一,解决方法既存有逻辑悖论又忽视现实。尽管韩炳哲曾表明“爱欲”是数字时代人类精神问题的救赎之道,但是,“爱欲”从何而来?在韩炳哲看来,必须要“我”承认了“无能为力”,这样“我”就只能依靠“他者”,“我”也将不再坚持“我”能做什么,而是让“他者”来帮助我。“他者”的重现将重启人的免疫系统,进而完成自我持存。但不能否认的是,“爱欲”仅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自我救赎。可以说,这种方法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现实。从逻辑上看,韩炳哲揭示的“点赞”模式正是文化上的一种自明性,这种自明性使“点赞”这种肯定性的模式是不可争议的、是理所当然的。既然如此,在当今文化的驱使下,人们又怎会承认“我”的无能为力?所以“爱欲”就不可能会出现,否则“点赞”的肯定性文化就不会像韩炳哲说的那样可怕。从现实上看,马克思表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3]152数字时代的现实生活,正是韩炳哲所批判的现实,也是在这个现实基础上,人类精神状况才出现了问题。如果不对这个现实做出改变,妄图直接改变由这个现实衍生出来的意识(精神),则无疑是一种“乌托邦”。
第二,解决方法偏重“他者”却忽视了“我”。韩炳哲提出的“爱欲”“安全距离”“门槛”“深度无聊”等概念,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呼唤出“他者”。由于韩炳哲提前预设了“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他者”对于“我”来说必定是具有“否定性”的,所以“他者”就天生能够打破数字信息时代的肯定性思维,那么该时代的精神政治就不再有效。然而,“我”与“他者”之间对立的前提本身就存在问题。试想,数字时代正是因为仅有“我”而无“他者”,所以才出现问题,那么同理,如果仅有“他者”而无“我”,也必定会产生新的问题。其实,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已经表示,人的自我持存,应当是在“我”与“他者”之间的斗争过程中完成的,“我”与“他者”是缺一不可的,只是在韩炳哲其他的著作中,似乎陷入到了他者消失的悲哀之中,致使他特别强调“他者”对“我”的意义,却忽视了“我”的不可替代性。这样,即使不考虑现实因素,在精神领域自身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成为一种片面之法。
(二)“数字精神政治”思想的意义
从理论上看,数字精神政治思想无疑丰富了关于技术政治批判的相关理论。该理论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图,其所提出的“哲学王”的概念就将技术与政治关联到了一起。长期以来,尽管也有例如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凡伯伦提出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等思想涉及了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但是这种必然的关系始终未能引起思想家们的足够重视,直到马克思提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3]222技术与政治的必然关联才被彻底揭示出来。随着这种必然关系被揭示,众多思想家也开始从不同维度研究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例如海德格尔对技术文化产生的权力的批判、福柯的知识权力批判、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芬伯格对技术设计中负荷的政治权力的批判、温纳对技术自主性的批判等。这些关于技术的政治批判理论无疑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然而,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问题。以往的思想家对技术的政治批判无疑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因而他们关于技术的政治批判或者是针对贵族,或者是针对传统的管理者,而在当今这个时代,这些批判就不能够应对当今这个数字时代的需求,因此,关于技术政治批判的理论也就需要不断推进。韩炳哲正是推进关于技术政治批判理论的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说,其提出的数字精神政治思想使其成为当今这个数字时代展开技术政治批判的领军人物。如果说,每一位展开技术政治批判的思想家的理论,都对其所处时代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韩炳哲的数字精神政治思想也必将对数字时代的政治大有裨益。
从现实上来看,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首先是对数字时代管理模式的“祛魅”。诚如上文所述,我们认为,我们在数字信息时代的一切行动都是“自愿”的,因此,我就是“自由”的。殊不知,这完全是一种假相。韩炳哲的数字精神政治思想正是对这一假相的揭露,数字信息技术引导的“自由”,其实是一种“枷锁”。如此,韩炳哲也敲响了数字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警钟。相信通过韩炳哲对数字精神政治的批判,人们将有可能构建更为健康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