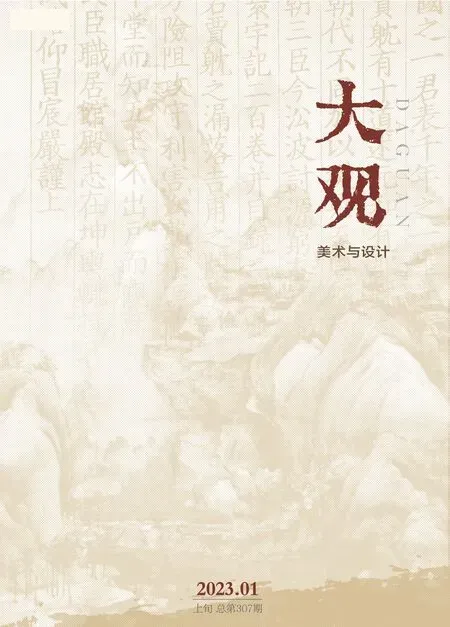中华原始图腾艺术视觉图式探析
——基于李泽厚《美的历程》第一章节
◇熊 净
一、关于视觉图式
关于视觉图式,首先需要将视觉和图式分开进行理解。“视觉”,即人眼组织通过光与物之间折射而产生的视线画面,并由大脑处理形成图像。“图式”一词,经查词典及各专业学者所著论文与书籍中可得两种解释,一是测绘地图上所用符号的样式、尺寸及颜色等地图形式和说明,二是经过历久蜕变所具有和展现的模式或样式。本文引用的解释为第二种。
在艺术领域和理论中,视觉图式即视觉感知下所接收到的视觉信息呈现,它源于西方现代视觉艺术理论的发展。艺术的探索离不开视觉艺术理论,即离不开视觉感知的发展。视觉感知对于视觉图式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从古至今,艺术创作不是简单的视觉图像再现或描摹,而是创作起始便构思好的构图、色彩搭配、点线面构成、造型设计等图式的组成,它们决定了作品的风格和样式,也蕴含了创作者的审美直觉、情感表达和文化意志。
二、中华原始图腾视觉图式解析
图腾(Totem) 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阿尔衮部落的方言,意为“他的亲族”,大约和氏族公社同时产生。在华夏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低下、劳动力不足,动物与植物不仅是部落家族的象征与记号,更成为后代繁衍生息的源头,而图腾的积淀和发展与先祖的庇护息息相关。为保护族群部落,他们把大自然神化,并赋予其超越人的精神力量。这种原始的宗教崇拜使得图腾不断发展壮大,因此在原始器具或人的皮肤上都能找到各类图腾的标志,同时这也意味着图腾开始具有视觉图式意味。中国原始社会时期,图腾作为一种艺术,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探索其演变过程与审美形式是了解图腾图式之美的必由之路。本文基于李泽厚《美的历程》第一章节中将原始图腾称为美的源头即“有意味的形式”进行思考,结合视觉图式理论知识,了解中华原始图腾图式的艺术美,以及演化中蕴含的文化意志和中华原始氏族对图腾的审美直觉、情感表达。
(一)中华原始图腾艺术视觉图式积淀过程
在我国的西北、西南、华北地区,早在距今6 000年左右,就已出现原始图腾文化。尤其是黄河下游的甘肃、宁夏、青海等地,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殷商时代,原始图腾文化一直是华夏文明特别是史前文化的重要特征。这些图腾图式特征主要表现为人形如虎,头似鹿。而在这种原始图腾形象的出现、发展,是原始部落对工具的合规律性的形体感受和在所谓“装饰品”上的自觉加工。例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这样描述:“上溯到旧石器时代,从南方的元谋人到北方的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虽然像欧洲洞穴壁画那样的艺术尚待发现,但从石器工具的进步上可以看出对形体形状的初步感受。”原始氏族对图腾图式的最初步展现即对美的第一次探索与运用,不论是早期遗存的旧石器时代蓝田人、北京人的无意识器具使用,中期遗存的丁村人早中晚期的石器,和晚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山顶洞人磨制石器、磨孔海蚶壳、钻孔兽牙,及用赤铁矿粉末与红色泥岩制作的染色材料,等等,这些对形体、色彩、事物的同一性的掌握,都表明原始氏族对劳动工具的物质使用与精神生产的最早的朦胧理解,是原始图腾艺术可以追溯的源头。直到“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原始氏族基于探索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表达的欲望,才使得图腾的视觉图式作用也开始逐渐显露并形成规模。
在前期工具的使用、观念的塑造及官能感受的积淀下,以远古神话为代表的图腾活动及巫术礼仪、原始歌舞等原始人的观念意识物态化活动开始蓬勃发展,原始图腾视觉图式所展现的原始人的审美直觉、情感表达和文化意志也相继显露。从中国传统神话传说中女娲“人首蛇身”的图腾图式,到《山海经》中的“人首马身”“鸟身人面”图式,以及原始歌舞图腾活动等,它们皆预示着中华大地上部落氏族、联盟以龙、凤图腾图式为代表的文明时代的来临。原始歌舞成为龙凤图腾演习形式的同时,也暗示着图腾视觉图式的运用巅峰即将到来。这些原始图腾作为观念意识活动的产物,既酝酿了一场盛大的视觉文化盛宴,也萌生出了前所未有的审美意识和史无前例的艺术作品。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表述,“……凝练在、聚集在这种图像符号形式里的社会意识,亦即原始人们那如醉如狂的情感、观念和心理,恰恰使这种图像形式获有了超模拟的内涵和意义”,“……也就是自然形式里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
随着图腾图式逐渐简化和抽象化成为纯几何形式的图式,图腾的积淀过程到达顶峰,内容积淀为形式,想象、观念积淀为感受。例如原始彩陶纹饰上的图腾图式,多数由动物演化而来,如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文化侧重于鸟、鱼图式,马家窑文化侧重于鸟、蛙图式等。图式的积淀与演变由早期的写实、生动、形象多样化逐步走向规律化、规范化。尤其从半坡期、庙底沟期到马家窑期的鸟纹和蛙纹,以及半山期、马厂期的拟日纹,陶器纹样图式的演变复杂且探索之路道阻且长,总体趋势和规律逐渐趋向“有意味的形式”。
(二)中华原始图腾艺术视觉图式审美直觉
1.仰韶半坡彩陶鱼纹线条之美
原始图腾的图式审美与原始图腾的积淀过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相辅相成、彼此包含,每一个积淀过程都代表着那一阶段的原始氏族以及彼时时代的意识元素、精神需求及审美直觉。如《美的历程》所述“半坡彩陶的几何形花纹是由鱼纹变化而来的,庙底沟彩陶的几何形花纹是由鸟纹演变而来的,所以前者是单纯的直线,后者是起伏的曲线……”它们在视觉图式上的美的形式便有着因袭相承、依次演化的脉络。
依据康定斯基点线面理论,可以发现任何艺术作品中空间的表达和视觉要素中图式的表现,都离不开点、线、面等基本要素,这些要素的美学特征使艺术作品图式生成新的面貌。图腾图式构成感及视觉符号要素与点、线、面不可分割,回顾中华原始图腾的积淀历程,其演化过程中最显著的审美变化即线条的变化——写实的线条变化与抽象的线条变化。
可以看到写实鱼形与写意鱼形是新石器时代仰韶半坡彩陶出土最多、最具代表性的鱼纹图式。不论是半坡单体鱼纹、半坡复体鱼纹还是半坡综合鱼纹,半坡鱼纹图式经过长期积淀演化,鱼的画法逐渐程式化,线条造型愈来愈规整、写实。以仰韶文化写实时期的半坡类彩陶人面鱼纹彩陶盆为例——这是一个儿童瓮棺棺盖,盆底稍平,腰部突出圆润,内壁光滑。作为翻唇阔口浅腹盆的代表,圆形的人面鱼身在内壁非常引人注目,黑色的人面纹图式被画出半圆柱的束发,古拙简洁而又典雅对称,整体大胆夸张。通过极富律动感的线条与黑色人脸块面的黑白对比,整个人面鱼纹图腾在视觉上充满了装饰性,图式效果自然而灵动。原始先民在有限的认知和视觉体验中,运用寥寥几笔写实的线条,便将人面冥思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人面鱼纹的视觉形象与图式特征充分显示了原始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才能,整体写实的手法也反映了渔猎生活与巫术在原始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有意味的形式”成为美的开端,更成为原始氏族对生活态度与情感的传达。
2.马家窑彩陶点、线、面之美
不同的图腾图式特征反映了不同的时代风貌,更体现出中华原始氏族对现实经验的美的不同直觉。如果说写实的仰韶人面鱼纹图式是半坡原始氏族表达对巫术和大自然的崇拜的初始手法,那么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旋涡纹尖底瓶则是新石器时代原始陶具创作中点、线、面运用与抽象写意线条的代表,也是中华原始氏族对自然与宗教情感更深层次的意识创作表现。马家窑型彩陶,主要分布在甘肃和青海地区,它晚于半坡型、庙底沟型,因而马家窑型彩陶的图腾图式非常丰富。作为渭水流域原始人民的生活陶具,它的图式主要有人形纹、动物纹、植物纹、几何圆点纹、斜扎纹等。例如,彩陶旋涡纹尖底瓶作为尖底瓶代表,兼具艺术美与实用价值。瓶子通身施彩,以黑色描绘流畅的旋涡纹,穿插黑白圆点,在写意自然的点与线的交错中,黑、白、灰的色彩对比愈发鲜明,流畅恣意的线条具有明朗、热烈、奔放的美感以及强烈的动感。瓶身上的旋涡线条并非无意义的单纯抽象图式,而是常居渭水流域的原始先民,将赖以生存并提供生命之源的黄河,借以旋转流动的线条作为替代抽象意识中水的表达。
河水翻卷的旋转线条在仰韶文化晚期更强烈地体现在了变形的鸟纹上,并促成了流体旋涡图式的出现。到马家窑文化早、中期,旋涡线条成为彩陶纹饰中最常见的图式之一,并且以点状展开,其为表现激流中的旋涡,一般以2个、4个或更多旋涡为中心连续展开。旋涡之间由数道水流连接,呈现出一派循环往复、汹涌澎湃、变幻无穷的气势。这些玄幻变化的旋动图式,表现了人与水的密切关系,仿佛使人看到远古时先民对自然的细致观察与依赖眷恋。而旋涡图式的中心最开始或为圆点,或为空白小圆圈,而后圆圈逐渐扩大,圈内多填以网格纹、十字纹、对三角纹、小圆圈纹、动物纹等,并以此不断衍生出新的纹路图式。点状图式的出现既是旋涡条纹图式的起始,也是整个瓶身的点睛之笔,线与点的相互纠缠、融合,使得整个图式不再局限于静止状态,而是给人以强烈动势,加之整个线条也并非瘦削的细线,而为规律整齐的黑色长块面,每个黑色块面被流畅地绘制在点状图式周围,使得旋转图式不再单一,逐渐宽窄相间,如同河流湍急处的形貌。而那些没有卷进旋涡的水流,则多以各种疏密相间的黑色色块表现——起伏高低错落,或密或疏,有时如绷直的琴弦,有时似风吹麦浪。这些均是原始先民为了表现河流湖泽,所做出的细致观察与无意识的艺术处理。
三、中华原始图腾视觉图式情感表达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用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历史初期,自然力在不同民族历经了不同的文化洗礼,以及在环境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变迁中不断反映成现实活动,这既有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也有对大自然的崇拜以及脑海中对幻想附于现实的反映。图腾就是一种打下了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双重烙印的意识活动。中华民族的图腾情感表达和其他民族不一样,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崇拜是单一的,是某一种动物或是一种植物。而中华民族的图腾由于不断积淀演化和再创作,开始由几种动物合成——有鹿的角、鹰的爪、蛇的身、狮子的毛、金鱼的胡须、牛的眼睛等等,最终融合为龙等具有强烈民族依赖的图式。中华图腾的凝聚力量因为动物以及自然力量被原始祖先掌握而逐渐壮大,再随着中华神话礼教发展,慢慢变成具有中式审美意味的最早样板和标本。中华原始先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视觉再现和单纯的意识崇拜,而是将积淀于感官中的大量观念、想象以及特定的审美情感毫无保留地展现在陶作器具上。图腾的各类图式成为人们生命的物化形式,它不再是纯粹的自然力的象征,也不再是无意识的美的展露,而是中华民族原始先民幻想中的自然崇拜偶像,是人的自我生命的二次展开。这样的情感既包含强烈炽热的对生活的持续的渴望,同时又附着在自然力上,变成规范化的形式美,无法用理智、逻辑、概念诠释清楚。
图腾作为中华原始先民生命力的象征,不仅展现出非一般的意识飞跃,更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过去一直危害着人类的自然力量,最终被中华先祖所战胜。至今,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量以及对大自然的敬佩和对美的感受,超越了对原始世界的权威神力的崇拜,也超越了对物质资本的依赖与屈服。中华原始图腾图式作为无可比拟的文化结晶,使中华儿女从心灵深处紧密联结,其在未来仍会继续发挥作用,给中华民族以无比的自信和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