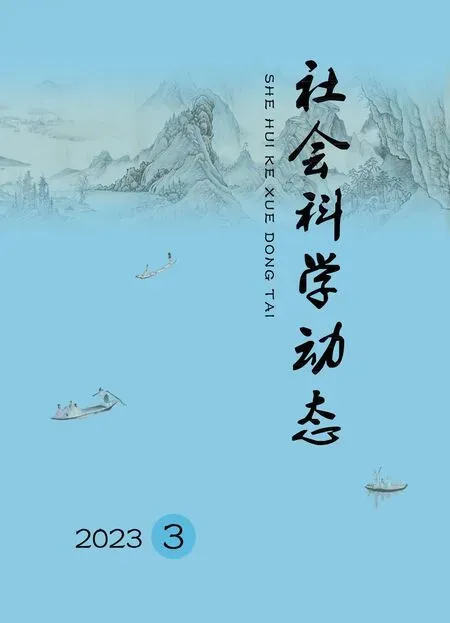我所接触的何其芳、蔡仪先生
——钱中文先生访谈
李世涛
编者按:钱中文,生于1932年,江苏无锡人。1959年肄业于莫斯科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荣誉委员,曾担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副主席、《文学评论》主编等职。主要代表作有《文学原理——发展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等;论著汇编有《钱中文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四卷)、《钱中文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五卷)等,译著长篇小说《现代牧歌》([俄]谢德林著,合译)等。先后主持主编《文艺理论方法论研究》《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文艺理论建设丛书》(7种)、《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36种)、《读世界》(6种)等;主编学术集刊《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中外文化与文论》,主持翻译出版《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14种,合作)、《巴赫金全集》(三版,七卷)。
李世涛(以下简称“李”):钱先生您好!近年来我就中国当代文论学术史做了一系列的访谈,希望通过当事人从史料的层面挖掘一些学术史的情况。据我所知,自20世纪50年代您从苏联留学回国迄今,就一直在从事文学理论的研究工作,见证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发生的重大变迁。而且,您一直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还一度担任《文学评论》主编。有些事情是您亲自经历的,有些事情是您知道的,可以由此反映出当时文艺界的一些情况。所以,我提请从您的学术研究经历谈起吧!
钱中文(以下简称“钱”):你的工作很有意义,我愿意接受你的采访,谈些我知道的情况。
一、我与何其芳先生的交往
李:在您长期的学习和学术研究生涯中,您曾经接触许多学者,或受过他们的领导,或与他们一起共过事。如今,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去世,这也是我国文论学界的重大损失。而且,他们的活动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论学术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希望您能谈一些你们之间交往的情况,这样既可以了解一些他们的情况,又可以从这些学术交流活动中一定程度反映当代文艺界的情况。您曾谈到自己是从批判何其芳、蔡仪的文艺思想转向文艺理论研究的,他们也是您当时的领导。我们不妨就从他们两位谈起?
钱:这个角度当然不错,那就先从我与何其芳先生的交往开始吧。
我开始认识其芳同志,是在1959年9月,那时我刚被分配到文学所。在国外学习时,我就很向往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现在幸运终于落到了我的头上,自然十分高兴。去文学所之前,先到科学院院部,张劲夫副院长接见了我们,大概说了些鼓励的话。到文学研究所不久,就要把我们分配到几个研究组去,开会征求我们意见,领导方面参加的有何其芳、蔡仪和叶水夫等先生。来之前,只知道何其芳是位诗人,也零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一到文学所,其芳同志就接见了我们。他简单介绍了一下文学所的情况,说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和意愿,选择自己愿意去的研究组。他希望我到文艺理论组去,说理论组要一些懂外文的人,蔡仪先生是理论组的组长,也表示欢迎。几位学习过美学的朋友就去了理论组,我则因为对文学理论并未系统学习过,不熟悉理论问题,心里无底,所以未敢贸然答应。叶水夫先生则欢迎我去苏联东欧文学组,我自然高兴前往了。这样我就到了苏联东欧文学组,主要方向是研究俄罗斯文学。虽然我没去理论组,但这第一个印象使我极为振奋,觉得其芳同志很开明、随和,没有架子。后来果然如此,比如在称呼问题上,不久我们看到文学所的年长同志和青年同志,都亲切地叫他“其芳同志”,连姓都不带,于是我们也就这么称呼他了,而见了面称他“何其芳同志”反而会不习惯;至于在研究人员中间,我从未听到有人称他为“何所长”的。
当时文学所正在搞“反右倾”运动,气氛神秘得很。文学所的几位领导,好像都去过庐山,为彭德怀同志帮过腔,都成了运动重点。后来得知,副所长唐棣华同志是黄克诚同志的妻子,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文学所如临大敌一般。看看“大字报”,只见“反”这、“反”那,如此这般。这还了得,光这些帽子就会把人吓死了。至于对其芳同志和蔡仪同志,则要我们几个刚到文学所的年轻人,查阅他们过去的著作,从中彻底揭发他们的“右倾”思想,等等。
我先读了他完成于1950年代前的《画梦录》《刻意集》和《夜歌和白天的歌》,读完一遍后,未发现其中违反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地方。不过这么一翻阅,倒引起我的兴趣来了。我看到了痛苦的诗人的他的另一面。读他的《论〈红楼梦〉》,觉得见解独到,论说新颖,文字如行云流水,显示出一个批评家的独特风格。其中关于典型“共名”说,富有创见,令人信服,但这一论点在“大字报”上其时是被当作“人性论”观点加以批判的。而我知道,一些新来文学所的年轻同志,都反复地阅读过这本书,作为自己学习写作批评文章的范本。
“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我印象中其芳同志总是没完没了地在做检讨。“反右倾”这次运动,上面整他整得很厉害,检讨做了三次才通过,听的人都听够了,而他也真有耐心,当然每次都要加码上纲。其实,其芳同志就管100多人,值得他费那么大的心力去写检讨么?只不过是他有些书生气,别人觉得他好对付而已。1962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其芳同志又做了检讨,检讨了自己跟不上形势,有“糊涂观念”“右倾思想”等等。历次检查,他都很认真,检讨内容都用道林纸写成详细提纲,并且像他写稿子一样,规规矩矩,字迹工整,这不知要消耗他多少精力和写作时间。有一年,有关领导要他写篇纪念《讲话》的时评。其芳同志回到所里对人说,他觉得很为难,由于他常常写这类文字,再写也没有新意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后来,他为此自然受到了批判。
作为历次运动中的一员,其芳同志不仅代人受过,同时也奉命批判别人。他多次说过,他最不喜欢写这类政论性文章,写不好,但又不得不写。他最喜欢写的是关于阿Q、《红楼梦》、诗歌创作研究、小说评论、论争性的文章,而且写了不少。可以看得出来,他处在一种矛盾的心态中。一方面,他无力超越运动的局面,在上级领导下搞批判,诚心诚意地干。因为对他来说,不这样做,就是“失职”,就要检讨,为此,他的虔诚使他吃了不少苦头。另一方面,他的身上始终存在着诗人的气质、理论家的真诚和勇气。他总认为文学研究所是搞学术研究的,要不断拿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东西来。因此,他尽量维护真正的文学研究,竭力为广大研究人员争取正常的研究条件。如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正是在他领导下抓出来的。他除了写批判文章外,同时还写了大量的理论性的研究文章。今天看来,这后一类文章中,不少是可以经受住历史的检验的。
李:我听刘锡诚先生谈到,“文革”期间,何其芳先生也被下放到河南农村改造,身心都受到摧残,严重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正常的领导工作。其实,这也是当时文学所许多学者的遭遇。您当时也被下放到河南信阳,你们的活动应该有交集吧?希望您谈些这方面的情况。
钱:十年动乱期间,下干校后,何其芳同志被分配去养猪。那时他已是快60岁的人了。我常在木工棚里,见他矮胖的身子肩挑两桶猪食时东斜西歪的艰难步履。后来更不行了,他就拄着拐棍挑东西了。小猪常常闯出猪圈,跑到田野里去。其芳同志发现后,就叫着“啰啰啰”、“啰啰啰”地到处去追寻。运动中间,虽然有些人互相摧残,但也有不少人自己虽被摧残过而始终不去摧残别人,其芳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他获得“解放”后,并未像有的人那样扩大着仇恨的心,而是对各类人都一视同仁、不存芥蒂,这需要宽厚的胸怀。不过,他对有的人却明显地怀有憎恶感。1975年,《红楼梦》等“研究”闹得不亦乐乎,文学所的大批力量闲得无事可干。在一次会议上,其芳同志很有情绪地说:“有人出于好心,劝我给姚文元写信,承认一下过去的错误,为文学所领点业务工作。笑话!我怎么会去干这种事!我向姚文元检讨什么,姚文元算什么?文学所跟他有什么关系?我是共产党员,党员有组织性,我们有党组织……”其芳同志对丑类的不满之情和蔑视,可以说溢于言表。大家怕他的话引起麻烦,就把话题岔开了。还在1973和1974年间,他在一些会议上心情极为不平地谈起了有人在北京图书馆做有关《红楼梦》报告时批判了他的“共名论”。他之所以极为不满,主要是当时他被剥夺了发言权、发表权,他的意见得不到申述的机会。他说这种做法不光明正大,他要辩论,要求有答辩的权利。但是直到“四人帮”垮台,他始终也未能得到这一权利。
李:粉碎“四人帮”后,何先生很快恢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领导工作,带领文学拨乱反正、走向正规。这时,你们应该还有接触吧?
钱:在何其芳同志去世前,我曾经在医院照料过他,对他去世的情况比较了解。
1977年7月,何先生因大量吐血被送进了医院。住院前几天,在文学所的一次会议上,他就运动中那些纠缠不清的事而发怒了。他说,所里的业务工作已荒废了10多年了,现在要赶快搞上去,怎么总纠缠那些事呢?接着他站了起来,生气地说:我们还要不要搞业务?谁愿纠缠过去的事,就让他继续去干吧,但这样的会我以后不参加了。大家劝他平静下来,而会议显然难以继续,只好不欢而散。
第二天就传来了不妙的消息。原来前一天会后回到家里,其芳同志一反常态,显得焦躁异常,难以休息。晚上坚持工作了一段时间,到半夜竟是大口吐血了。这忧伤的消息使文学所陷入了惶惶不安的气氛之中。行政方面安排所里同志去医院轮流看护病人。每逢这种情况,说明病人病情不轻。十分突然的是,这次其芳同志是胃癌出血。
我去看他时已在几天之后,轮到我值班。我进入病房时脚步很轻,但他听到了我和另一位同志的说话声音。见此情景,我赶忙向他打了招呼。他要我坐下。我忙说,你只管安心休息,有什么事,招呼我就是。过了一会儿,他说他很寂寞,所里无人理解他。我知道前几天的事仍萦绕于他的脑际,赶忙安慰他说不要去想这些事了,以后再说,现在养好身体最要紧。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支持你工作,你放心吧。说实在的,多年来没有一个领导人和我这样平等对话了。他的话感动了我,他在我面前没有掩饰,拿一副标准的、原则的脸给我看。因此使我的心为之一动,两眼突然湿润起来。他眼睛闭着,又继续对我说:我怎么能休息,我好些事还未做呢,我文章的清样不知来了没有?你们组里的工作……
我—面答应着一面打断他的话,劝他着急不得,等病好了再说。他大概感到有点累了,就不说话了。但是不到不到半小时,他突然招呼我,说屋里闷得很,让我开—下电扇。我赶忙说,电扇一直开着呢,是不是有点闷?我看了—下窗外,一片铅色,有如迷雾,湿热难忍。他接着说:我气闷极了,你快扶我坐起来。
我见他挣扎乱抓,就上前扶他的手和背,叫他轻轻地、慢慢地,不要动得太厉害。刚扶起一些,他突然“哇”的一声,大口大口地呕吐出深褐色的已经淤积了一个时候的血来,吐得床单和我左手手臂、衬衣左胸一边都是血。我吃惊不小,连忙拉起枕头扶他靠着,然后急忙叫来了护士。护士一见这等情景,立刻转身就跑,叫来大夫进行急救。
这时我感到一阵冷颤,一股痛楚的感觉紧紧地捆住了我的心。接着我打了电话,叫来了所里同志,后来家属也来了。以后其芳同志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有时清醒过来,就要家人把他的文章校样取来,说他要工作。等我再去看他时,他已完全昏迷……
其芳同志的逝世,使文学所呆木了许久。好些业务工作刚做了筹划,开了个头,可突然又中断了,失去了头绪。
李: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何先生这样的领导也难以幸免,真是令人感慨啊!他的遭遇也许与他强烈的诗人气质、学者气质很有关系。但从另一方面看,正是何先生的诗人气质、学者气质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与敬重,许多学者都表达了对他的尊重。现在,您是如何看待、评价他呢?
钱:我一直把何先生视为我的老师。由于工作关系,我常听到他关于研究工作的一些经验谈,它们至今给我启发,给我教益。
1959年其芳同志建议我去文艺理论室时我没有去。当时我想,我过去接触的主要是俄罗斯文学,其他文学虽也了解一些,但从未深入思考过,所以不敢贸然答应。前面讲到“反右倾”运动中,要我们一些年轻人从其芳同志和蔡仪同志的著作中寻找“右倾思想”。但这一阅读的过程,却无异是给我的一次理论补课,使我对文艺理论发生了兴趣。我觉得理论中的问题很多,研究它们,比以毕生的精力去研究几个作家有意思得多。于是我把这个想法向其芳同志说了,要求转一个专业。他十分支持我的想法。他接着像谈心一样,说一个人的兴趣十分重要,搞研究没有兴趣不行,至于理论研究就更是如此。他说他原来的兴趣是写作,至今犹跃跃欲试,但客观条件不允许,总未免觉得可惜。
其芳同志后来在别的场合又谈到,搞文艺理论研究要多读当前作品,要了解现实问题,开始时不要去钻研抽象问题,要多读作品,中外古今的文学感性知识越多越好,知识范围越广越好。如果要写东西,最好先搞一段文学评论,具体分析一些作品,这样一两年后,再研究理论问题,自然会深入下去。否则不需多久,写文章就会感到无话可说,结果就会在概念中转来转去,无法深入,这样做也容易脱离实际。他的这个意见,完全是一种经验之谈,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后来也给一些同志介绍过。
1960年代初的几年,不少同志写了稿子,总喜欢给其芳同志去看,有时打印出来,相互传阅,互提意见,以便精益求精。他对大家送去的稿子从不拒绝,也从不敷衍。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看稿中的问题,在一些小会上常常谈到研究、写作问题。他说写文章要抓住问题,抓住问题后要进行彻底的分析。他说要把理论文章当作艺术作品来写,要精雕细琢、字斟句酌,写得要有感情,要有起伏,要有气势,要有文采,切忌平铺直叙、言之无物,这样才会诱人去读。他一写长文章,就要请假,关起门来写。即使这样,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一天最多也就两千字,但是他写下的两千字,却是经得住时间的磨洗的两千字。
为了使自己的文章具有充分的说理性、科学性,其芳同志十分注意引文的准确性。在引用外国作家、理论家的文字时,他都要请人找原文加以核对,他说核对的结果还真会发现译文与原文意思弄反了的。在这方面,他完全做到了不耻下问。在他逝世前不久,一次他和我谈起文学的“人民性”问题,我把“人民性”的来龙去脉向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顺便提到马恩的论述中没有这个概念。可他说他好像在哪里见到过。我说我好久前也曾在马恩的不知哪篇文章中见到过,但和俄国文学理论中的“人民性”是两回事。一星期后,一天上午在所里,他来找我,手里拿了张卡片,我接过一看,上面摘录了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的一段话。我一看正是我过去看到过的那段文字,便对他说,这不是文学的“人民性”的人民性,但一时又说不清楚。他把卡片给了我,说有空再查查。于是我翻阅了马恩全集的俄译本,这里的“人民性”原是“人民特性”“人民特征”的意思,为了避免和文学的“人民性”的专门名词相混,似译作“人民特性”为妥。我把这个出处和原文意思同其芳同志谈后,他才释然,觉得我的解释有理。
其芳同志对青年同志十分和蔼,他对人平等,没有架子,即使在长幼之间,也很重情谊。1964年他的《文学艺术的春天》出版后,赠送了我一本,并在扉页上写有几行字:“送给钱中文同志,谢谢他对《托尔斯泰的作品仍然活着》一文提过许多意见。何其芳,1964年5月。” 读完题字我十分激动。原来1961年1月是托尔斯泰逝世50周年,苏联文艺界开会纪念,邀请其芳同志参加。1960年底,其芳同志写了初稿,让一些同志提意见。我阅读后,曾就论点、材料提出过一些意见,过后也就忘怀了。而其芳同志不仅记着,而且写到赠书的扉页上去了。后来我又阅读了其芳的这篇文章,它较之1961年发表的论文,实际上已做了重大的修改。大家都说,在文学研究所,其芳同志是不可重复的。
二、我与蔡仪先生的交往
李:看得出,您对何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在您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您对蔡仪先生也有着类似的情感。而且,您与蔡先生都研究文学理论,你们的业务往来应该更多些,也应该更了解蔡先生。请您介绍一些蔡先生的情况。
钱:1959年8月,我从苏联回国。9月,我就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一到所里,正逢所谓“反右倾”运动,文学所一派神秘、肃杀景象。
不几天,所里为了分配我们的工作,由所长何其芳先生召开会议,征求我们意见,确定专业方向,分入研究组(当时无“室”这一编制)。那次会议蔡仪、叶水夫先生也参加了。何其芳、蔡仪先生想加强文艺理论组工作,希望我们参加理论组,水夫先生则欢迎我们进苏联文学组工作,我因没有系统学过文学理论,就自愿进了苏联东欧文学组。
为了显示“反右倾”运动的深入,同时“锻炼”我们这些年轻人,领导要我们清查何其芳、蔡仪先生的著作,包括他们1949年以前出版的理论、散文著作和诗作在内,找出其中的“右倾思想”,好像1959年出现的所谓“右倾机会”思想,早在他们几十年前的著作中就有的了!
我先阅读何其芳的著作,接着我又开始阅读蔡仪先生的著作。一些“大字报”批评蔡仪先生的著作文字“晦涩难懂”“缺乏群众观点”,云云。我接触到蔡仪先生的著作后,则感到他文章的风格凝重厚实,逻辑性强,见解独到。没有丰富的文学史知识,没有一定的理论积累与思考,自然不容易读懂蔡仪先生的著作,那么,实际上何晦涩之有?这样找来找去,自然没有找出什么“右倾思想”来。阅读蔡仪先生的著作《新美学》《新艺术论》以及有关现实主义的一组文章,实在使我获益匪浅。我过去接触的是苏联读物,多而零星,对于一些问题的见解不成系统。蔡仪先生有关现实主义的五论,算得上是当时对这一问题相当完整的阐释了。阅读何、蔡二先生的著作,使我的兴趣转向了理论研究,这可算是我在“反右倾”运动中的最大收获。运动后,等我应约写完一部小册子的稿子后,我就正式向何其芳所长提出想去文艺理论组的要求。蒙他立刻答应,同时经他疏通,在征得蔡仪、水夫先生的同意后,我就去了文艺理论组工作。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我总把两位先生当作自己学术上的引路人看待,心里充满感谢和暖意。
李: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很长时间,您就与蔡先生一起在文艺理论组从事研究工作,后来也一直在同一个研究室工作。希望您谈一些他当时更详细的情况。
钱:20世纪50-70年代,是我国学术研究最受压制的年代,学术与政治几乎是一回事,而且是只能是几个人说了算。回顾1950年代的学术著作,能够保留下来的有几多?蔡仪先生的“现实主义五论”,即使现在读来仍不失其理论力量,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蔡仪先生也是不断遇到麻烦的。
60年代初期,领导布置编写《文学概论》。当时的要求是南北各写一本,南方由叶以群担任主编,北方由蔡仪担任主编。蔡仪先生写出提纲(这提纲我未见到),据说在天津会议上给领导否定了,于是这位领导自己拿出提纲,要别人按他的提纲写作。蔡仪先生只好照办,组织力量,勉力写成初稿。蔡先生平常沉默少言,不痛快的心情一般不轻易外露,但是有时在工作交谈中不免流露出来,认为此书已不是他的想法,有违他的初衷。70年代末,为适应当时高校教学的需要,《文学概论》初稿经修改后出版,成为大专院校采用的教科书,影响极大。这书既然写成于60年代初,自然受到当时“左”的势力干扰,部分观念已失去了其意义,所以在80年代就受到一些非议。出版社曾建议编者进行修改,蔡仪先生觉得除了少量提法可以改动,此书难以再改,要写就得另起炉灶,重搭框架。但当时他正在改写《新美学》,这是他的毕生精力所在,《文学概论》已无暇顾及,所以一任人们评说。而那位制造过无数冤案、横扫过不知多少人的领导,却对此事不置一字,摇身一变,举着一面过去被他践踏的人道主义大旗,又在呐喊了!但此事到现在未了。80年代被这位领导举荐的新秀,曾在文学所庆祝蔡仪学术活动60周年的纪念会上,大力表彰蔡仪先生如何开创学派,要营造尊敬卓有影响的老学者的学术气氛,提倡宽松、宽容,云云。而一离开会场就对蔡仪著作中的“认识论”观念进行歪曲,庸俗化一通,然后加以挞伐,并且一直进行到现在。对稍有不同意见的人就力加排斥,真是颐指气使,八面威风。而他在国内的朋友们,现在还与之呼应,发表文章,非欲把“认识论”除之而后快。其实,任何理论、体系,都有其长处与局限,你不满对方的理论,最好是拿出自己的货真价实、以理服人的新东西来,让读者在比较中自然明白。不要一会儿大倡西学,把它们奉之为神明,一会儿又举行与诸神告别仪式,像小儿游戏一般。要分清一般理论原则与“极左”和“左”的理论之间的界限,混而统之,或是把别人的理论庸俗化一通,就以为骂倒了对方、清除了对手,我们不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不然,何以一些人在大骂“认识论”,而另一些学者又在大写“文学认识论”或“认识论文艺学”呢?!不是他们没有见到被骂的危险,而是认为你骂得并不在理,骂不到点子上,说了好多的外行话,所以他们仍然我行我素,不予理会。要看看自己的东西,并非都是金科玉律,漏洞倒是不少的!
另一次是60年代初,那位名声显赫的文艺界领导,为了提倡“双百”方针,先让朱光潜先生批评蔡仪先生,然后让蔡仪先生进行反批评,这不是创造了一幅学术争鸣的繁荣图景吗?但是在朱先生发了第二篇文章后,蔡仪的反批评文章就不让发了,这自然是那位领导的“裁夺”,并要何其芳将蔡仪的第二篇文稿从《新建设》编辑部撤回。所谓“双百”云云,全是由一些人在调动、摆弄的,只有当权者的发号施令,哪有什么“百家争鸣”啊!我知道,蔡仪先生对此事一直感到不快,可又怎么办呢?这事就是连何其芳先生也感到不平、委曲啊,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呢?当然,朱先生在“极左”路线下也是身受其害的,甚至在他弥留之际,在其意识即将消逝的时刻,在回光返照之时,仍在发出“我要检讨,我要检讨”的胡话!要检讨什么呢?大概就是所谓“反动的唯心主义”吧!请看,那已是什么时候了?1986年了!可见其身心蒙受的摧残之深!但就这场争鸣来说,我们作为局外人,至今都深为蔡仪先生感到不平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蔡仪先生成了“文革”发动者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牺牲品。下放到干校后,蔡仪先生竟以65岁高龄被分配去干校厨房充当火头军,为几百人烧饭、烧水。在炉灶旁,他在沉思着,大概觉得周围的世界是荒诞而寂寞的吧。
李:当时,蔡先生的遭遇也很有代表性。现在,时过境迁,您是如何看待蔡先生的为人和学术研究的?
钱:蔡仪先生在美学上自成一派。他在20世纪40年代初出版的《新美学》中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美学后,一直未改初衷。有人说蔡仪先生的美学没有新东西,这自然是一种浅薄的见解。其实,40年代蔡仪提出的唯物主义新美学,就是美学中的重大的创新。他后来主编的《美学原理》,逻辑严密,学理清晰,自成体系。80至90年代的《新美学》改写本,极大地丰富了原著。他崇尚新思想,在一段时间里,在编辑《美学论丛》过程中,我常听他说,文章要有新意,或提出新的问题,或在讨论中有所深入,切忌老生常谈。所以他选稿极严,这给我的印象极深。
蔡先生为人,生活简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真正是位忠厚长者。他知道我的一些缺点和一些不同意见,但他决不像有的人通过“小小的政变”获得权力,立刻排斥异已,扶植亲信。1989年冬我因手术住院,术后一些年轻的同行都前来看过我。一天下午,蔡仪先生夫妇来到医院床前探望,使我心头为之一热。蔡仪先生是我前辈,而且其时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了。作为后学,我从未想到他会来看我,每想起此事,总是令我感动不已!
李:您的经历丰富,非常感谢您详细、生动地讲述了这些经历。今天的访谈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有价值、有意义的材料,帮助我澄清了很多疑惑,使我了解到中国文艺界、文论界的很多情况,也有助于了解我国建国以来的文艺、文论的历史,对于今后的研究工作也很有启发意义和史料价值。再次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祝您健康、高寿、永葆学术青春!
——兼及一类史料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