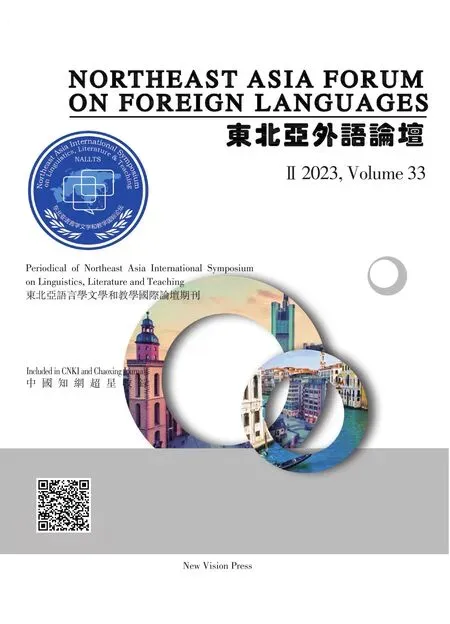身份的迷失与追寻:《望岩》中杰克的忧郁症研究
郭宇琦 刘 丹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 连 116044 中 国
一、引语
美籍华裔女作家伍慧明的小说《望岩》于2008年出版,与第一部在1993年出版的《骨》一样,该小说延续了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华人群体的生活故事。根据伍慧明父亲的真实经历,她借用父亲的真实姓名蔡有信,将有信作为《望岩》主人公杰克的真实名字。生活在广东农村的梁有信,以司徒金“契纸儿子”的假身份偷渡到美国。在旧金山的唐人街,梁有信以杰克·司徒·满的名字在大众市场做屠夫,并在当地恋爱、结婚、生女,在真实的岁月里度过跌宕起伏的人生。
在《哀悼与忧郁症》弗洛伊德认为,“哀悼通常是对失去所爱之人的反应,或者是对失去一些取代所爱之人的抽象事物的反应”(2009: 20),而“忧郁症的突出心理特征是深切的痛苦和沮丧,停止了对外界的兴趣,失去了爱的能力”(2009: 20)。在忧郁症中,“本我想要吸收爱的客体。并且,根据它所处的本能发展的同类相食阶段,本我想要通过吞噬客体达到一种状态”(2009: 25)。弗洛伊德将忧郁症描述为个人对失去迷恋之物、自由、自己国家和理想的一种病理形式的哀悼。从弗洛伊德的解读出发,郑安琳在《种族忧郁症》中提出弗洛伊德所解读的忧郁症是一种消耗和无尽的自我贫乏状态。“首先,忧郁症患者必须否认丧失的状态,以维持对占有的想象;其次,忧郁症患者必须确定‘爱的客体’将不再失而复得”(2000: 9)。此外,郑安琳还进一步指出遭受种族歧视的种族主体对这种排斥做出忧郁的反应,即被歧视种族的忧郁症,这是一种“规训和排斥的内化以及可感知的特定背景下的存在”(2000: 10),并且“对被歧视种族主体来说,这是一种长期的,既是排斥的象征,也是回应这种排斥的一种心理策略”(2000: 10)。
在研究美国少数种族对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忧郁反应时,郑安琳认为,“主流文化压迫的内化可能并不意味着被歧视种族的顺从或者屈服,而是指向了新的思维方式,即种族对于被剥夺客体的群体的含义”(2000: 21)。同时,穆尼奥斯也提出了弗洛伊德关于忧郁症的观点,他认为忧郁症是日常生活和生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机制,帮助我们重建身份的同时以我们的自身的名义和他者的名义进行各种斗争”(1999: 74)。根据上述阐释的忧郁症的观点,本文试图分析主人公杰克自身体现出的忧郁症得出,忧郁症一方面导致他身份的错位感,另一方面又鼓励他摆脱流离失所的生存状态,重构自我身份价值。
二、身份的错位与忧郁
1.原始家庭的分隔
在杰克来到美国之前,一直过着与原生家庭割裂的苦难生活。少不更事时便被贩卖给了司徒金一家,为司徒金患有不孕症的妻子延续家族血脉。杰克“被卖给了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那个村子很小,名字就是一个数字”(伍慧明,2008: 207)。在过去的贫苦生活中,一切皆可以金钱来换取,“人们卖人。儿子和妻子,女儿和狗。当时发生过的,现在仍然发生。只是现在,有了新的名字”(伍慧明,2008: 210)。儿童被列为商品,以不同的理由卖给他人,父亲杰克也是被贩卖的受害者之一。作为司徒金的“契纸儿子”,杰克从小与原生家庭分离,并长期生活在异国他乡。
家系纽带维系着家庭文化生活,“家庭是社会关系的首位,家庭是通过血缘关系形成的,血缘关系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决定了人们的生活”(王娜,2007: 23)。带着伤痛的阴影,成为漂泊的幽灵。杰克自小被家人抛弃,他的生活“没有关怀,没有目的,没有爱,没有奉献”(伍慧明,2008: 98)。身居异乡的他没有真正的家人,因而了却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愿景。长期的家庭分离模糊了他对自己真实名字“有信”的概念,对自己的身份倍感茫然。“在家庭中,这个名字让人感觉很亲切,就像玉石必须贴着皮肤佩戴,才能起到保护作用”(伍慧明,2008: 28),而他的假身份却时时刻刻让他觉得居无定所,谎言般的人生未曾给他丝毫安全感。
在唐人街里,杰克以“契纸儿子”的身份开始他的新生活,被动地接受着陌生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在这里,一切维持家庭关系的不过仅仅是所谓的“契纸父亲”和“契纸妻子”,大家彼此以虚假的身份共同生活在一起,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生活让杰克无法感受到自身的完整性,“我娶的那个女人不是我的妻子,她在纸上是我的妻子。在事实上,她属于司徒金。在债务方面,我也是属于他的,他也是我的父亲,契纸父亲”(伍慧明,2008: 3)杰克沉湎和挣扎于原生家庭的割裂之中。
2.身份错位的迷失
对于大多数美国华裔来说,最直接、最明显的歧视和不公正来自于美国政府。1882年《排华法案》的颁布使得中国在美移民生活陷入僵局。在此法案条例中,普通工人被禁止通过合法途径入境美国。“1882年的法律对中国人的家庭生活造成了严重和持久的伤害……1882年的法律进一步的将反华浪潮推向了顶峰”(Chen,2015: 301)。美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来核实美国华裔居住证。然而,1906年旧金山大火则烧毁了移民局所有在美中国居民的身份记录,中国移民趁机伪造了自己的美国身份,“通过他人证词来确定,这就为移民检查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漏洞,也就是后来的‘契纸儿子’计划”(Chen, 2015: 299)。
中国的一部分移民通过这种被迫反应方式成功进入美国境内,美国劳工市场也从未给辗转漂泊的移民们显露丝毫怜悯之心。他们忽视移民们的所有工作需求,并削减和剥夺他们的商业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没有机会冲破社会偏见和歧视,一度陷入困难求生的境地。美国社会完全阻止了移民同化的心愿,以至于他们从未真正意义上融入美国主流大环境。“这种无法将自我投射于新的客体之中的现象,就是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忧郁症的体现”(Eng & Han, 2000: 680)。以此看来,亚裔美国人将完全被主流大环境所排斥,无法同化的痛苦将使大部分人长期处于忧郁状态。
杰克的根从旧的传统文化中拔起,却无法深深扎根于新的土地。为了谋求生存,他辗转劳作在肉铺、澡堂、餐馆等社会底层场所,在唐人街挣取血汗钱来偿还“契纸父亲”的债务。“我就像是活在鸡笼子里的一个人,生活圈子从大众市场算起,也就只能往外拓展到几个街区”(伍慧明,2008: 9)。渴望开始新生活的梁有信,却只能在大洋彼岸的加州以“杰克’的假身份痛苦的生存下去。这种“同化过程悬而未决的概念能够契合到种族忧郁症的框架之中”(王卉,2019: 33)。忧郁症展现了同化过程中一个不稳定的过程,表现了亚裔美国人在经历痛苦的移民生活时却又永远无法同化到美国主流环境之中。
3.爱的渴求和追寻
面对白人社区对华人紧闭的大门,移民们不得不选择在一个类似于家乡环境的地区内群居。而以杰克居住的唐人街为代表的种族群居地实际上种族隔离的区域,它代表了中国移民过渡和适应美国社会的一种特殊方式。唐人街是一个封闭的和停滞的“飞地”,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一个地区(Cheung, 1996: 199)。在郑安琳对种族忧郁症的定义中,唐人街可以“作为一种被排斥的标志,同时也是对这种排斥做出反应的一种心理策略”(Cheng, 1999: 20)。在唐人街里,杰克被困在被贫穷和剥削编织的铁笼里,他没有过去,如今也没有自由,只有依靠一个虚假的身份勉强维持自己无奈和麻木的生活,但他心中却一直梦想着在这片新的土地过得幸福,他无尽的渴望着爱和追求爱。
杰克与乔伊斯的相遇点燃了他对爱情的希望。“我爱的女人叫乔伊斯·关,我相想跟她在一起,想保护她”(伍慧明, 2008: 5)。乔伊斯是杰克对家庭和美国新生活希望的一个具体化身,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离散者,心里最渴望的就是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差点就得到别人的爱了,爱情差点就在我这里成为现实了”(伍慧明, 2008: 6)。然而乔伊斯却无法回应杰克的爱,以此同时,杰克为了履行“契纸儿子”的义务,不得不遵从司徒金为他安排的“契纸婚姻”,拥有家庭的美梦再一次破灭,家和爱变得遥不可及。
无奈和愤怒之下,杰克选择了“坦白计划”。杰克是一个为爱而背叛法律的人,报复式“坦白”是他对难以喘息的生活的反击:
为了她,我参加了中国人的“坦白计划”。我想要做回我自己。为了爱情,我坦白了司徒是个假名字,我也因此失去了公民的身份。我跟自己打赌,乔伊斯会把我这种行为看作是对她忠诚的表示,但对我的牺牲她毫不领情。最终,我伤心欲绝,尝尽了热情、怨恨、后悔的滋味。(伍慧明,2008: 5)
杰克的坦白并没有得到乔伊斯的回应,反而遭到了司徒金的报复,被人砍掉了自己的一只胳膊。他不仅没有以“坦白”的方式获得自己理想的生活,反而终生生活在“坦白”的痛苦阴影下。身份的丧失、种族主义的排斥和隔阂,无法触及的爱让杰克长期处于忧郁的状态中。
三、反抗和身份的追寻
在忧郁症的框架中,“忧郁症描述了一个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爱的客体对自我来说至关重要,被自我所爱,以至于以自我牺牲的代价来维护它”(Eng & Han,2000: 695)。“自我的忧郁症坚持拒绝让爱的客体消失在遗忘之中……这种对受威胁的客体的保护可以看作是忧郁症自我的一种道德坚持”。杰克经历的迷失都来自于他流离失所的生活和对爱情的渴望,同时他也由自我的忧郁症心理去抵制失去爱的客体,也就是他的中国根和爱情。
1.中国根的记忆和追寻
因颠沛流离的生活和爱情而忧郁的杰克不断在失落中挣扎,在挣扎中徘徊,从被动去接受他者文化到最后主动去接受和学习外国文化,他一次次在寻求和失去的过程中重新定位自己。尽管和女儿维达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已经学会接收了美国的生活习惯,但他却从未忘记自己对中国根的追寻。
虽然杰克从小就被贩卖到司徒金家里,又远渡重洋来到美国,但他永远记得他的中国血脉带给他弥足珍贵的回忆和希望。每逢过年佳节,杰克会按照中国习俗去看望他的“契纸父亲”,正如杰克所说:“契纸父亲也好,亲生父亲也罢,我都尊敬。每年新年的时候,我都带着糖果和吉祥话给‘父亲’拜年。中秋节,我寄一盒十二块钱的蛋黄月饼给他。冬至的时候,我给‘父亲’带一袋橘子”(伍慧明,2008: 8)。而每当杰克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他总会想起他亲生母亲带着他过河的场景:那时,他们坐着船,正朝着一块刻有“向、我、来”的大石头划去,母亲的教诲在耳畔响起“要腾空你的心,把恐惧在岩石上摔碎……要面对恐惧,相信恐惧,向那块岩石驶去”(伍慧明,2008: 118)。尽管杰克身处他乡,在他者文化间遭到不公平对待,但他始终怀着故土带给他的记忆和爱去克服生活的压抑和负担,以超越种族和国界的爱和信念生活在新居。无论他生活在何方,飞向哪片土地,根的血脉流淌着祖辈带给他的爱和力量,让他在新的土壤中里扎根并茁壮成长。
2.他者文化的接受和包容
身份的迷失和不完整始终是杰克陷入痛苦的原因之一,但他也在漫长和压抑的生活中不断将自己投射在不同的爱的客体中,通过定义自己与情人乔伊斯、“契纸妻子”张伊琳和女儿维达的关系和感情中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曾经的真名“梁有信”已经逐渐被实实在在生活在当下的“杰克”所替代,这个假身份使得杰克在新的土地上有了新的人生故事。
杰克之所以能够最后在唐人街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归根到底在于他能够以善意和宽容去融入当地生活,以跨越国界的爱和信念去包容两种文化。面对新环境各种文化的交融,杰克并未选择仅仅以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来定义自己,而是将自己投射在不断变化的文化背景中来重塑自己的身份和责任。正如霍尔认为,移民并不是由不惜一切的代价去回归自己心目中所坚持的神圣家园获得的身份的完整定义,他们的集体经验也并不是他们的本性所定义的,而是在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接受过程中得到重塑的。杰克的人生也体现了华裔族群们在经历了自己身份的迷失并徘徊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时通过协商的态度去接受文化的差异,以主动的心态接纳新的文化价值信念,去接受自己身份的复杂性。在美国生活多年的杰克,正是在潜意识里接受自己身份的转变,怀着血脉里安土重迁传统思想,在新的土壤上扎根、开花和结果。
四、结语
无论以杰克的身份或有信的身份生活,主人公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自己,以博爱的心和淳朴的善意融入到异域的文化环境之中。虽然经历了身份的迷失和忧郁,但杰克在寻找和失去、爱与被爱的过程中疗愈过往的伤痛并重新塑造自己和定义自己的价值。他带着超越国界的爱和信念飞向美国,扎根于美国,在文化差异和冲突中找了平衡和安稳之地,在爱与希望中逐渐摆脱忧郁心理,种族忧郁症因而也成为杰克追求自己真实身份和爱情的力量之源,在真与假、对与错之间找回自己的身份和做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