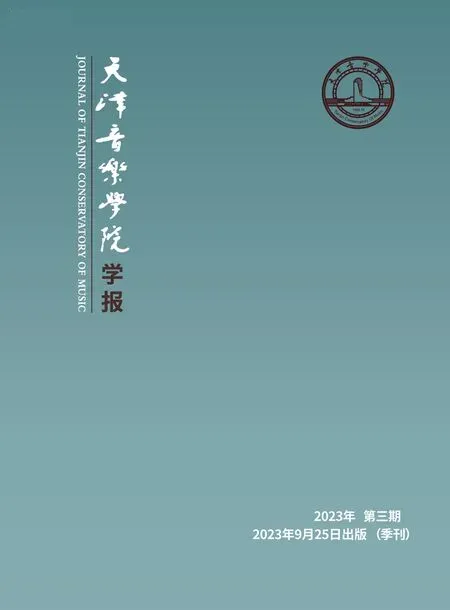“驾后乐”东西班在宋代乐署的地位与词史意义
曹 茜
北宋以唐和五代的战乱为鉴,大力恢复礼乐制度,而乐署担负着建设与传播国家礼乐思想的重任。北宋先后设立了多个乐署,除了太常寺、教坊、云韶部、大晟府外,还有从禁军中选拔善乐者而成立的钧容直和东西班乐,相当于皇家军乐队。东西班乐隶属于殿前司内的诸班直,在以皇帝为中心的各类重要场合进行音乐表演活动,把国家形象和音乐审美带入阖闾。钧容直和东西班乐经常在一起演出,所以有时候放在一起讨论。
词,本就依音律填写而成,文人们在音乐表演场合得以与乐工接触,形成最直观的创作灵感。本文主要是针对东西班乐的渊源、机构设置、职能以及对宋词创作演唱的意义进行论述。
一、文武参修:东西班与东西班乐的由来
东西班作为朝廷官制的组成部分,其命名即指向皇帝这个中心,其职能也是以皇帝本人为指归。从指称文、武官制,到成为皇帝禁军组成部分,再到军乐署之一,东西班名称不改,内涵则发生了相应变化。
(一)东西班:从文武官员的分类到禁军单位
唐代始有“东西班”的称谓,用来指代文、武官员的分类。从《旧唐书》《资治通鉴》可知,唐哀帝天祐二年(905)的敕令就将东西两班归为“文武二柄”(1)(唐哀帝)敕曰:“文武二柄,国家大纲,东西两班,官职同体。”(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91页。;五代后唐也有将文、武官员分为东西两班的记录(2)(后唐)文纪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与两班旅见,暂获对扬。两班者,文武官分为东西两班。”(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132页。。
五代诸帝对文、武的重视程度不同,但总体确立了“五代为国,兴亡以兵”(3)(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7页。的指导方针,大力发展禁军体系,东西班在后晋已经成为皇室的近卫军。后晋宫室因契丹入侵而举族北迁,随行者就有东西班卫队(4)“太后与冯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宝等举族从帝而北,以宫女五十、宦者三十、东西班五十、医官一、控鹤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仪鸾司三、六军士二十人从,卫以骑兵三百。”同注,第178页。。李太后去世,东西班也在扶棺下葬的队伍之中:“(太后)遂卒。帝与皇后、宫人、宦者、东西班,皆被发徒跣,扶舁其柩至赐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5)同注,第179页。可见其与皇室的亲近。
后周君主郭威与柴荣在位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为北宋的统一和集权奠定了基础。后周世宗柴荣正是“西班”出身(6)“汉乾祐中,世宗在西班,后始封彭城县君。”(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03页。,他对禁军的改革与建设亲力亲为、严加把关。显德初年(954—955),柴荣本着“精兵不在众”的原则,亲自面试,挑选骁勇精锐者,无论距离远近都纳入殿前诸班,正式确立了东西班承旨这一禁军单位:
显德元年,……(柴荣)召募天下豪杰,不以草泽为阻,在于阙下,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手者,分署为殿前诸班。
二年十二月。改东西小校为东西班承旨。(7)(宋)王溥:《五代会要》,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7页。
东西班的人员各方面具备过人的素质,宋太祖赵匡胤就曾在东西班中任职:
宋太祖赵匡胤,世为涿郡人,生洛阳夹马营中。后汉乾祐元年,应募为郭威部属。仕后周,补东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挥使,拜定国军节度使。后周显德六年,升殿前都点检。(8)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一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赵匡胤当时的职位变动大致为:东西班行首、殿前都指挥使、殿前都点检,这是一条在殿前司系统逐级升迁的路线。其中,殿前都点检是殿前司的最高指挥官,此身份受到了众军拥戴,赵匡胤也由此而即位。北宋建立后,赵匡胤深知殿前都点检的军权过重,遂罢此职。可见,东西班深受皇帝的信任,其人员有机会锻炼掌管军政能力,前途不可限量。
(二)东西班乐:特色军乐团
东西班禁军选拔善乐人员进行表演的传统,在五代就已开始。后晋皇帝石重贵在被契丹俘虏北去的路上,随行的东西班禁军中就有善乐士兵组成的乐队:“又有东西班数辈善于歌唱”(9)同注,第1128页。。北宋一方面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另一方面大力扩充禁军队伍,太平兴国(976—984)间,宋太宗从东西班中挑选出善乐者,成立东西班乐,并明确了乐队所奏乐器和基本职能。根据《宋史》《乐书》的记载:
东西班乐,亦太平兴国中选东西班习乐者,乐器独用银字觱栗、小笛、小笙。每骑从车驾而奏乐,或巡方则夜奏于行宫殿庭。(10)(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61页。
又诸营军皆有乐工,率五百人得乐工五十员,每乘舆奉祠还宫,则诸工杂被绛绿衣,自帷宫幔城至皇城门,分列驰道左右,作乐迎奉,丝竹鼙鼓之声相属数十里。或军中宴亦得奏之,有棹刀枪盾蕃歌等戏。大中祥符中,建玉清、昭应等宫,亦选乐工教于钧容,诏中人掌之。(11)(宋)陈旸:《乐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49页。
东西班乐确立之后,规模有所扩充,真宗朝“增置东西班殿侍院一于彰化桥北”(12)同注,第4610页。,仁宗朝又将招箭班并入东西班内。自神宗朝元丰改制以来,文献中不再有东西班音乐活动的记载,这或许是由于朝廷在简化乐署的音乐制度时,重新规划了乐人的所属机构。中兴之后,东西班的规模缩减至八班,仍在随驾的禁军队伍之中。
东西班乐伴随着乐署而衰落,却以民间表演的形式出现在戏剧、游戏中。南宋时,城外的勾栏瓦舍也归在殿前司之下,《武林旧事》载:“瓦子勾栏,城内隶修内司,城外隶殿前司。”(13)(宋)周密著、杨瑞点校:《武林旧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页。城外瓦舍为殿前都指挥使杨和王创建,演员和观众也都是军人。这些军人除了擅长音乐之外,还在民间戏剧方面有专长,“驾后乐东西班”的重新出现,就是在杂剧表演中:
大礼后,择日行恭谢礼。……驾后东西班则于和宁门外排立,后从作乐。……御筵毕,百官侍卫吏卒等并赐簪花从驾,缕翠滴金,各竞华丽,望之如锦绣。衙前乐都管已下三百人,自新桩桥西中道排立迎驾,念致语、口号如前。乐动《满路花》,至殿门起《寿同天》曲破,舞毕退。(14)同注,第18—19页。
这段材料是对帝王行恭谢礼的记载,由演员表演东西班乐从驾作乐的场面。姜夔还为此次祭祀典礼作诗:“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头冠样样新。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15)贾文昭编:《姜夔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8页。
东西班从文、武官制的分类,到禁军机构再到仪仗军乐团,其职能不断丰富。直到东西班乐随着乐署衰落,其人员仍有不错的发展空间,或并入其他乐署,或在民间从事表演活动。
二、壮大声威:东西班乐的结构与音乐职能
东西班乐与钧容直都是隶属于殿前诸班直的军乐团,但在从驾队伍里的位置和功能有所不同。东西班的人员构成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动,在皇帝出入、宴饮、巡幸等多个场合演奏不同的音乐,行使其壮大声势、促进外交、安保警示等职责。
(一)军制与地位
北宋沿用五代的禁军制度,但从禁军中选拔音乐人才却是宋代独有的现象。军乐人员兼有士兵和乐工的双重身份:他们是在乐工不足的情况下,从军中选拔的补充人员。《文献通考》载:“先是,角工不足,常取于州县及营兵以充。祥符中,命籍兵二百余工,使长隶太常以阅习焉。”(1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429页。发展军乐队也是宋代“重文”的体现,在殿前司掌管的诸多军事机构中,东西班列于诸班直内。
诸班直是殿前司骑军“诸班”与步军“诸直”的合称,也是殿前司的主体。诸班直是皇帝最亲近的卫兵队伍,据《宋史》:“禁兵者,天子之卫兵也,殿前、侍卫二司总之。其最亲近底从者,号诸班直。”(17)同注,第4570页。东西班与钧容直都属于骑军“诸班”,都有军乐队的职能,若按资次排序,东西班比钧容直还要高一些(18)“诸班直资次相压:……东西班、御龙弓箭直、御龙弩直、招箭班、散直、钧容直。”同注,第4578页。。殿前诸班直的内部结构在不同时期有所调整,东西班的结构也随之融合变动。宋初,东西班已是集弩手、龙旗直、招箭班等十二班为一体的多元化组织。
东西班内有“内殿承制”一职,如苏轼有诗《送钱承制赴广西路分都监》:
当年我作《表忠碑》,坐觉江山气未衰。舞凤尚从天目下,收驹时有渥洼姿。踞床到处堪吹笛,横槊何人解赋诗。知是丹霞破佛手,先声应已慑群夷。(广西僧寺顷有佛动之异,钱君碎而投之江中)(19)(宋)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293页。
钱承制即钱晖,其所任“承制”是内殿承制官,正是东西班内武职(20)(宋)苏轼撰、(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87页。。苏轼诗盛赞钱晖碎佛之举,并用典故来表明自己与其心意相通。另,苏辙也有写给钱晖的《送钱承制赴广东都监》(21)苏辙《送钱承制赴广东都监》:“家声远继河西守,游宦多便岭外官。南海无波闲斗舸,北堂多暇得羞兰。忽闻棠棣歌离索,应寄寒梅报好安。他日扁舟定归计,仍将犀玉付江湍。”见(清)查慎行:《苏诗补注》,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824页。,用“棠棣”来表达二人深厚的情谊。钱晖虽是八品的武职,却与苏氏兄弟二人关系密切、心灵契合,可以看出供职于东西班的家族,有禁军之威武,也不乏琴书之雅好。另如司马光诗《题杨中正供奉洗心堂》云:“阀阅盛山西,朱门扬戟衣。雅知名教乐,深笑宴游非。”(22)(宋)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452—453页。诗中杨中正祖上分别在朝任殿前指挥使、东西班承旨,都是北方名将(23)同注,第9713页。。诗歌写出了杨氏禁军家族的显贵英姿,也道出了其“知名教乐”的文艺内涵。钱晖父子、杨氏门第均为东西班系统的禁军,且分属不同级别,但他们兼资文武,又能和苏轼兄弟、司马光等为友,于此可以想见东西班人员的社会地位。
既然如此,那么东西班官职阶如何?我们可以从乐工的服色来看(24)此部分参考了徐斯嘉《“东西班”钩沉》,《中华文化画报》2018年第11期。:
“东西班小底……,紫夹绫绵旋襕。……东西班权管指挥者……,紫罗杉。”(25)(宋)徐松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标点校勘:《宋会要辑稿》,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第14816段。
“每乘舆奉祠还宫,则诸工杂被绛绿衣。”(26)同注,第849页。
“东西班乐三十六人,紫帽带。”(27)同注,第3641页。
可知东西班的服饰以紫色为主,参考“已上文武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绯,九品已上服绿”(28)同注,第4051页。可知其整体的官职地位较高。东西班乐工在夹道迎驾演奏时着红色、绿色服装、紫色帽带,这些分属于不同级别的颜色耀人眼目,在乐队演奏气势雄壮的仪仗军乐时,辅以锦绣鲜艳的服装,使得仪式表演声色大开。在此意义上,东西班乐代表宫廷军容威仪,又接近皇帝,其实际地位其实超过其品级。
(二)职能与奏乐场合
东西班乐的职能比较丰富,其在以皇帝为中心的各类活动场合都有演出的机会。宋章如愚将其职能总结为:“又有东西班,夜奏乐于行宫,祠祀、驾回及园苑赐宴、馆遇使人,分用诸军乐。”(29)“横行东西班内,有内殿承制官,秩正八品,乃武职也。”(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别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54—355页。总的来说,东西班的奏乐场合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皇行出行途中、住宿行宫、祭祀典礼与宴请使节等。
1.皇帝出行时,东西班主要充当仪仗鼓吹乐队
皇帝出行时,从驾的仪仗队伍十分庞大。东西班与钧容直都是从驾的禁军,只是位置和功能不同。东西班乐属于“驾后乐”,整体规模小于钧容直,据《宋史》:
驾前诸班直。……东西班六人,……钧容直二百七十人,驾回则作乐。驾后部。……驾后乐:东西班三十六人,钧容直三十一人,并骑。(30)同注,第3443—3444页。
可见,负责开路的钧容直制造锣鼓喧天的宏大气势,而随从护驾的东西班乐则偏重留下悠长的芳音,同时有安保警示的功能。
从驾的禁军队伍专门配有御马(31)“凡御马之等三,入殿祗候十五匹,引驾十四匹,从驾二十匹。给用之等十有五,……曰诸班,曰御龙直。”同注,第4927—4928页。,并在出入御路时可以免除行马的限制(32)“熙宁二年,御史台、太常礼院详定臣僚御路上马之制:……正任观察使以上与合出节臣僚,并许自宣德门外至天汉桥北御路上行马,如从驾出入及宗室内庭诸宫院车骑,并不在此限。”同注,第2824页。,此外,东西班还配有仪仗专用的器械——银骨朵:
哲宗绍圣二年,诏:车驾行幸仪卫,驾后东西班殿侍马两队,拨充驾前编拦,分两壁行于前引行门之前,随身器械,各别给银骨朵一。(33)同注,第3390页。
从驾队伍的军乐和鸣、仪容整饬、良马相配,共同传递着国家的威严与亲民之感。
2.皇帝驾回、赐宴时,东西班负责夹道奏乐
皇帝回宫时,东西班也要在御道左右奏乐迎接,从青城门一直列队到朱雀门,军乐响彻数十里,场面热烈,据《宋史》:
诸军皆有善乐者,每车驾亲祀回,则衣绯绿衣,自青城至朱雀门,列于御道之左右,奏乐迎奉,其声相属,闻十数里。(34)同注,第3361页。
青城门和朱雀门是南向的城门和宫门(35)“《三辅黄图》云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本曰‘霸城门’,民见门色青,名曰‘青城门’,或曰‘青门’。”曹金华:《后汉书稽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155页。“齐主引诸贵臣入朱雀门,朱雀门,邺宫城正南门也。”同注,第5367页。,连接两道门的道路也称为御道,是皇帝出行、参加祭祀和大型活动的必经之路,因此规格甚高。御道两侧除了仪仗队之外,还有各种植物花卉的点缀,一直延伸到城门外的御街。黄庭坚有诗云:“晚风池莲香度,晓日宫槐影西。白下长干梦到,青门紫曲尘迷。”(36)(宋)黄庭坚撰、任渊等注:《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46页。提到在“宫槐”“青门紫曲”之处怀念金陵,似乎就是诗人行走于御街时的心绪。御街正对皇宫,皇帝回宫时经过御街,东西班等军乐人也要列队街旁演奏。如太宗皇帝大设宴饮,军乐人在御街之上演奏各类乐器,前来观看的民众、商贩挤满了街道:
太宗雍熙元年十二月,……御丹凤楼观酺,召侍臣赐饮。自楼前至朱雀门张乐,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又集开封府诸县及诸军乐人列于御街,音乐杂发,观者溢道,纵士庶游观,迁市肆百货于道之左右。(37)同注,第2699—2700页。
真宗皇帝巡幸时的场面亦如此:“所过州、府,结彩为楼,陈音乐百戏。道、释以威仪奉迎者,悉有赐”(38)同注,第2704页。。军乐交响、人声鼎沸、商户云集、建筑绝妙,这一切都彰显着市井繁华、皇恩浩荡、礼乐和谐的氛围。
3.东西班于巡幸或大礼时夜奏、为外使演奏胡乐
东西班乐另一个功能是在皇帝巡狩或外宿时,充当警笛,以防闲杂人等靠近。如宋太祖曾于青城门斋戒,每更三奏,名为“警场”,动用鼓吹乐队上千人。封禅、宿斋等仪式将所有乐工统称为“鼓吹”,而东西班乐夜奏行宫的职能,使其也可随时充入鼓吹当中,以满足大型仪式的规模。(39)“太祖乾德元年。将有事于南郊。为坛于城南南薰门外。径五丈……备大驾卤簿。宿斋于青城。上御青城门。观奏严。夜设警场。用鼓吹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奏严用金钲。大角。大鼓。乐用大小横吹。觱篥。笳笛。角手。歌六州。十二时。每更三奏之。”(宋)李攸:《宋朝事实》,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81页。
此外,东西班乐还在外使来访时奏乐。如真宗朝契丹使来访时,就有东西班在场:“俟奏班齐,舍人喝拜,东西班殿侍两拜,奏圣躬万福,喝各祗候。”(40)同注,第2807页。一般情况下,东西班会为契丹使演奏蕃歌胡乐:“蕃歌胡乐,以之待契丹使。”(41)同注,第849页。契丹族是草原游牧民族,能在京城听到东西班乐奏出亲切的家乡音乐,交流的气氛自然和谐。东西班乐勾连雅俗、表达友好,也增强了外族内服之心。
三、沟通君民:东西班音乐活动影响宋词的创作及演唱
北宋乐署乐人的数量庞大,教坊、云韶部、钧容直、东西班乐加起来近千人。隆重的仪式、仪仗队伍、各类乐团等组成了一个礼乐共同体,它能够同时达到宣扬威望、宴饮娱乐等多种目的。上文已述,皇帝出行举办大型仪式、赐宴等活动,都有军乐人在御道、御街两侧表演,他们与民间接触的机会较多。军乐人在闲暇之时也会到市井之中表演音乐(42)“或军营放停乐人,鼓动乐于空闲,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73页。,演奏人们喜闻乐见的俗乐,有着沟通雅俗的重要意义。文人与乐工群体接触,是他们把握音乐形式与内容最直接的方式,通音律的人才能使曲子更鲜活。这样的交流与学习,为宋词的创作与演唱提供了灵感,具体表现在丰富了词作的风格、内容,拓展了词人的想象空间。
(一)东西班乐华丽雄壮、悲慨激扬的特征,影响宋词的风格
东西班乐与钧容直都是军乐,以鼓吹仪仗为基本功能,但二者演奏的乐器不同。钧容直规模较大,演奏的乐器有管乐、弦乐、鼓类等;东西班乐规模较小,演奏的乐器只有三种管乐:小笙、小笛、筚篥(这三种乐器钧容直同样使用),故东西班乐的演奏应有两种风格:一是与钧容直合奏营造出华丽雄壮的气势,一是发挥管乐独有的悲慨激扬的情调。以下分别论之:
东西班乐与钧容直合奏,相当于一个大型交响乐团:御街之上,仪仗队伍鼓乐喧天、华冠丽服,簇拥着皇帝的车马浩浩汤汤而来。笙、笛、筚篥、琵琶、方响、拍板、杖鼓、羯鼓、大鼓、杂剧等声与人声一起沸腾。柳永作曲子词《御街行》(43)(宋)柳永著、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03页。词风华丽、气度非凡,概是在御街观礼时被声色震撼。根据笺注,本词写天子祭天之后的大赦,根据《东京梦华录》对于“下赦”的记录,皇帝赦免罪犯时,的确也有诸班直作乐之情形:
开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楼前,罪人皆绯缝黄布衫,狱吏皆簪花鲜洁,闻鼓声,踈枷放去,各山呼谢恩讫,楼下钧容直乐作,杂剧舞旋,御龙直装神鬼,斫真刀倬刀,楼上百官赐茶酒,诸班直呈拽马队,六军归营,至日晡时,礼毕。(44)同注,第936页。
南宋无名氏以《御街行》为曲调作词,其词沿用柳永的曲牌,其中“禁卫”“锦仗”“战袍”等使得词作风格再现了禁军乐队华丽雄壮的气势:
时康三载升平世。恭谢三朝礼。群臣禁卫带花回,龊巷儿郞精锐。战袍新样团雕拥,重隘围子队。绣衣花帽挨排砌。锦仗天街里。有如仙队玉京来,妙乐钧天盈耳。都民观望时,果是消灾灭罪。(45)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81页。
东西班乐单独演奏时,筚篥音色悲凉,小笙音色嘹亮,小笛声细腻悠长,他们的共通特点是音域较高,可协奏出悲慨激扬的风格。如宋代词人蔡挺《喜迁莺·霜天秋晓》“剑歌骑曲悲壮,尽道君恩须报”(46)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40页。,这是军乐的另一面,进一步说,这是禁军东西班的沙场本色。
北宋时期,宋词演唱的伴奏乐器以琵琶为主,到了南宋,宋词演唱的伴奏以箫、笛等管乐为主流,乐器的转变也促进了词风的转变,东西班乐所用独特的管乐器也暗合了词风转变的方向。如南宋辛弃疾慷慨悲凉之作《贺新郎·梦绕神州路》: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贺新郎》)(47)同注,第1073页。
总之,当东西班乐不再,它作为管乐队所形成的华丽雄壮、悲慨激扬的独特曲风,仍留存于宋词的创作、表演之中,成为宋词风格的一部分。
(二)东西班音乐活动行为本身及其意蕴,丰富宋词的内容
禁军乐队的活动也为词人提供了创作内容,如真宗封禅时夜设“警场”,有真宗封禅四首中《六州》:“良夜永,玉漏正迟迟。丹禁肃,周庐列,羽卫生绕皇闱。严鼓动,画角声齐。金管飘雅韵,远逐轻飔。”(48)同注,第3307页。可知仪式军乐除了整饬规范之外,还有错落情致。另如,仁宗朝祭祀中丝管和鸣“管丝金石含天韵,笾豆荐芬芳。肃然音响灵来下”等,都反映了鼓吹乐曲吹奏雅乐、沟通神灵的肃穆场面。
东西班等军乐团从驾、迎驾的场面前文已详述,以此为内容的歌词令人心潮澎湃。能够参加皇帝的活动,与皇帝的车马同行,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充满荣耀的回忆,如晁冲之“帽落宫花,衣惹御香”(49)同注,第655页。。词人陈济翁追忆曾经扈从圣驾,并与皇帝宴饮的往事,而作《蓦山溪》:
去年今日,从驾游西苑。彩仗压金波,看水戏、鱼龙曼衍。宝津南殿。宴坐近天顔,金杯酒,君王劝。头上宫花颤。六军锦绣,万骑穿杨箭。日暮翠华归,拥《钧天》、笙歌一片。如今关外,千里未归人,前山雨,西楼晚。望断思君眼。(50)同注,第276页。
词人身处关外,内心黯淡,特别是回想起与皇帝近同行、宴饮的往事,简直是华彩万千。词人与君王推杯换盏,头上艳丽的宫花摇动,耳边随驾的军乐“拥《钧天》、笙歌一片”,热闹的场面中一定穿插着东西班乐的演奏。直到南宋时期,这首词还广泛传唱,酒宴上歌妓表演,引起张孝祥的共鸣:
舍人张孝祥知潭州,因宴客,妓有韵此,至“金杯酒,君王劝。头上宫花颤”,其首自为之摇动者数四。坐客忍笑,指目者甚众,而张竟不觉也。(51)(宋)厉鹗撰:《绝妙好词笺》,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另有熙宁间词人作《降仙台》,以皇帝驾回时的仪仗队为内容:“清都未晓,万乘并驾,煌煌拥天行。……四列兵卫,爟火映金支翠旌。众乐警作充宫廷,皦绎成。”(52)同注,第3720页。卫兵警乐的声色仿佛近在眼前。
关于御街节庆活动时,东西班等军乐人于街道两边演奏的场面,也有生动的词作产生,如徽宗朝李持正的《明月逐人来》也表现了禁街上的管弦表演及祥和景象:
星河明淡。春来深浅。红莲正、满城开遍。禁街行乐,暗尘香拂面。皓月随人近远。 天半鳌山,光动凤楼两观。东风静、珠帘不卷。玉辇待归,云外闻弦管。认得宫花影转。(53)同注,第983页。
另有王诜《人月圆·元夜》,营造出另一种清透的夜色:“小桃枝上春来早,初试薄罗衣。年年此夜,华灯盛照,人月圆时。禁街箫鼓,寒轻夜永,纤手同携。更阑人静。千门笑语,声在帘帏。”(54)同注,第274页。元宵节的夜晚,御街上的音乐声已变得微弱,家家都在门内团圆,表现出军乐队与民同乐,与民同安的特质。
(三)东西班音乐活动的声色,拓展词人的想象空间
东西班在以皇帝为中心的各类场合参与奏乐,并与其他乐署机构共同营造出盛世景象,是时代所需礼乐制度建设的一部分,参与其中的文人自然会担负起记录者与传播者的责任。文人们往往具有强烈的艺术感受力与联想能力,精彩如“人间少有”的卤簿音乐活动激发词人的创作热情、拓展了词人想象的空间。如宋徽宗《声声慢·春》,使神话传说中的仙境有了具体的参照:
春宫梅粉淡,岸柳金匀,皇州乍庆春回。凤阙端门,棚山彩建蓬莱。沈沈洞天向晚,宝舆还、花满钧台。轻烟里,算谁将金莲,陆地齐开。 触处笙歌鼎沸,香鞯趁,雕轮隐隐轻雷。万家帘幕,千步锦绣相挨。银蟾皓月如昼,共乘欢、争忍归来。疏钟断,听行歌、犹在禁街。(55)同注,第896页。
在作品中,宋徽宗将春节期间京都宫苑内外喜庆的场面描绘得如仙境一般:乘圣驾穿行在春夜的轻烟里,一路上次第感受“蓬莱仙山”“宝舆”“金莲”“雕轮”“笙歌”。按理说,皇帝本人对盛大场面应习以为常,而难得的是,宋徽宗专为此作词并触发对仙界的遐想,以第一视角,将北宋都城的歌舞升平表现到了极致。
皇帝仪式音乐活动声色大开的气象感染了文人士大夫,他们在兴致盎然时,也向往乘坐宝舆、聆听笙笛,沉醉其中,在想象中体验“帝王待遇”。如黄庭坚《瑶台第一层》,词人置身于阆苑仙境,醉酒登瑶台:
阆苑归来,因醉上、瑶台第一层。洞天深处,年年不夜,日日长春。万花妆烂锦,散异香,馥郁留人。便乘兴,命玉龙吟笛,彩凤吹笙。 身轻。先逢瑞景,众中先识董双成。珮环声丽,舞腰袅袅,浓艳腾腾。翠屏金缕枕,绣被软,梦冷槐清。乐蓬瀛。愿南山同寿,北斗齐龄。(56)孔凡礼辑:《全宋词补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
词人在一场游仙美梦中,飘飘然命“玉龙吟笛”“彩凤吹笙”,竟与西王母的侍女董双成相遇,比起宋徽宗描绘的场面更添情趣。
总之,东西班乐自建立以来,一直承担着为皇家仪仗、仪式、宴请等奏乐的职责,是沟通君民的一道桥梁。东西班乐与宋朝的其他乐署一起,为礼乐建设作出了贡献,同时是影响宋词创作与演唱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