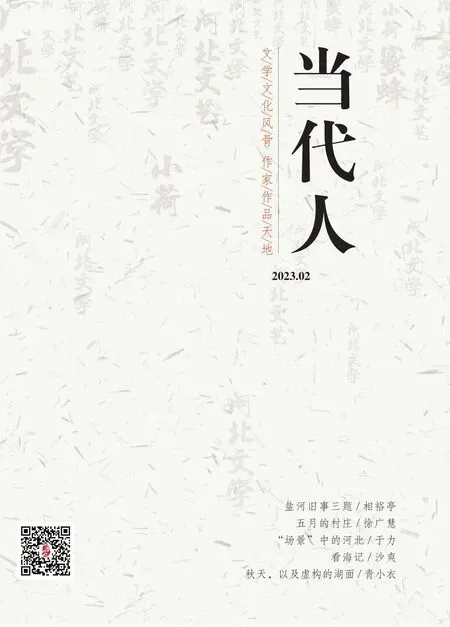宁静与喧嚣:我在一场夏雨中的意识流
◇晚乌
一
我喜欢来这里,这是家生意清淡的咖啡厅。
此时,我在二楼。室内装修带着皖南民居的风格,楼梯上来是一间长方形的厅,几根木头柱子杵在中间,将厅分成两半。朝南有木头的窗户,上面糊着乳白色的牛皮纸,手触上去会有清脆的摩擦声。
桌子临窗。我坐下,服务员端来一杯咖啡。除日常的温开水,我并不偏爱任何一种饮品。每次来这里点一杯咖啡,是因为如果不消费什么,会感觉不好意思。而我每次都要相同的无糖无奶的美式,它包含某种本源的味道,那种温暖的苦,有时显得很醇厚,让人觉得踏实。第三次把杯子举起来送往嘴边时,我才真正意识到雨开始大了。透过窗,我看见雨顺着黑色的瓦往下滴落。
天有些阴沉,刚才我背着双肩包,拎着电脑,朝这里走来。
我对母亲说:“这么多天,只有今天下午稍微有点儿自己的时间。”
她反问我:“放学时,你接亨亨吗?”
亨亨,是我儿子,四岁半,正在读幼儿园。
一个月来,我一直想着这里,来这个清淡的角落写几段文字。我上一篇文章也是在这里完成的,但那是三个月前的事情。当时写着写着,仿佛在文字中遇见了童年的自己,顺势陷进低迷情绪里。今天,我并未想好到底要写出什么,只是此时有种特别真实特别饱满的东西在身体里浮游,它在夏初的雨水中变得轻盈,洁净。
皖南的春天极为短暂,春花匆匆开完,夏天就来了。夏日的雨水没完没了,从天气看,今天跟前天、昨天甚至明天并无差别,总之,这是极为寻常的一天。寻常是日常的底色,我已经习惯并熟悉身边的每个角落。早晨,我曾来过此街,整条街还睡着,而我的身份是晨跑者。这些年,我渐渐习得健康意识,努力学习保重身体的秘诀,戒掉香烟,不喝酒,早睡早起,因为我不想过早离开人世,否则,我的父母会痛,孩子会孤单。想到这里,我觉得我真是俗气透顶,是沉溺在生活泥淖里无法自拔的人。晨间我沿江跑,看到有人在河边垂钓,有人在岸边空旷处耍剑,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在时光的逼仄里,通过某些活动来缓释自己肉身的疼痛,忘却一些忧愁。除了年龄,我和他们没有差异,我们都害怕病痛与死亡,害怕孤单,试图以动态的图式开启新的一天。
有天,我偷听了练剑者的部分谈话,他们说着超越年龄的黄段子。
我有点吃惊。人生暮年里,我原本以为一切都是风平浪静。他们的话,虽是调侃,但对我而言,是有颠覆性的。看来不管人到多少岁,它本身的温度是炙热的,蓬勃张扬的生命力无处不在。我似乎有些大惊小怪,我承认,我自己有一定程度的洁癖,包括精神。这让我活得不那么自在,不那么痛快。在我的认知里,那些上了年岁的人,就不该口吐污言,而应活成江边树的模样,在风清云淡中什么也不想。
晨间跑步,我常路过此间咖啡厅所在的古楼。这是栋庭院深深的旧屋,集民宿、书店、咖啡饮品店于一体。书店有先锋味,所售书籍不俗气,书店老板是个热爱写作的人,我曾在书架上看到过他的小说集,语言有特点,思想前卫。书店有个儿童阅览区,我经常带孩子去那里看书,慢慢,我们跟女店员就熟悉了,孩子会喊她姐姐,让她帮忙寻找某本曾看过的书。
二
我抵达这里时,是下午的1∶30,现在已经3:30了。过去两小时,我写出上面的文字。
雨还没停,天倒暗了不少。
咖啡厅播放着音乐,那是一首日语歌,曲调舒缓,但我并不明白歌词的具体内容。有那么一小会儿,我大脑处于短路状态,不知接下来该写点儿什么。不过,写什么并不重要,我只是想寻个情感的出口,把那些负面的、零散的、不堪的碎片倾泻出去。此刻,我感到自己俨然是台刚跑完磨合的车,需要一次全面保养。
咖啡已剩不多,午间残留的倦意也消失了。雨一直下,这间屋子下午属于我一个人。
我在柔软的椅背上靠了一会儿,后背有隐隐的痛感,母亲说,可能是肩周炎。这疼痛不致命,我并不太在意,能拖则拖,到目前并无大碍。一丝隐痛掠过,我本能地把头朝左转,余光瞟到左前方的墙壁,上面印着两行字:
How much better is silence;
The coffee-cup,the table.
下面印着说这句话的人的名字:Virginia Woolf。
我瞬间被这个句子击中,在我有点儿失措与迷茫的间隙里,它的出现给我惊喜,其实也不是惊喜,应该是某种契合。要知道,在这个午后,我多么渴望在短暂的三个半小时里,能够完成一篇六千字的书写,我并不清楚自己为何要规定字数,只依稀感觉,这个篇幅具有治愈的效果,它可以将藏于身里的那些毒逼出来。
此刻,这里是寂静的,室内有昏黄的光,窗外下着雨,这是淋漓的夏之初的雨。这些天来,我渴望寂静,希望拥有那种独处的寂静。就像我在晨间看到的那只乌鸫,它在草地上发呆,四周静悄悄的。它沉迷的样子,让人觉得它把一切都忘记了。是的,我也想像那只乌鸫,短暂忘掉一切。
出门时,我没带伞。等下回去,我要奔跑,穿过几条巷子才能到家。如果走回去,会显得从容淡定些,但我必须跑,不然雨水会淋湿我的电脑和书包。四年前,我买了这台电脑,我工作上的各种资料全部保存在里面。我必须保证它们的完整,穿过雨水回家后,我再次回到那些资料和数据里,被计算和总结包围着,学会在理性与理智中生活。
这几年来,我总爱在晨间处理工作上的事情。那时,孩子还在酣睡,无人打扰我。天大亮时,我再出门锻炼。孩子虽渐大,他依然像个黏虫,总是跟着我。我晚间不睡觉,他就等着,或者一直在床上催;分离焦虑仍然没完全消失,偶尔他还是会在门口抱着我的腿,不让我走,哭得悲伤。这些俗世生活如此甜蜜,我被其紧紧地裹着。如果我说这背后的害处也格外明显,那算不算一种矫情。这些年来,我放弃男人该有的理想,放弃深造,放弃学术追求,放弃文字书写,把更多的精力赠给孩子。记得我曾给《野草》的编辑投过一篇稿子。我从他真诚的回复里读出“你离生活太近”的意蕴。
这时,有位女孩走上楼。她有一头长发,穿着米黄色长裙。她站在伍尔夫的那句话前面仔细端详,拍一张照片。她下楼领来一个女伴,一起又站在那两行字前评点一番,大意是说,那个 “table”少了一个字母“b”。片刻后,她们踩着木质楼板下去,雨依旧没有停。
手机突然震动,那是个陌生的来自北京的电话,我不接,对方挂断。近两年,陌生电话越来越多,对方总是用很熟络的口吻询问是否需要发表学术论文抑或申请专利,只要付钱,他们能搞定一切。起初,我会耐心解释不需要,但对方多半会坚持索要微信号码,渴望保持联系。后来,我直接说已经改行,偶尔我也会说已评上正教授。听到这些,他们顿感再无继续交流的必要,挂断前甚至还会说声抱歉。我在皖南某二本高校当老师,也暗自渴望在学术上能有一点建树,但这只是渴望而已。繁重的课程教学,没完没了的杂务工作,耗费我太多精力。最后,我终究变成现在不学无术的样子。我从书包掏手机时,顺带拿出一叠五页纸的名单。那里有来自五个班级的190多个名字,全是我授课的大一新生。每个人名后写着的数字是该同学单词听写、读书笔记、单词比赛等各项的得分,这些数据最终会一起构成期末成绩。上午课间,我仔细浏览授课班级的心愿墙,总体来说,他们有三个心愿:暴富、变瘦、不挂科。他们也许不想把真切的人生理想写在墙上供人观瞻品读,于是就直白地写出这些粗浅的心底欲望。还有几个人的署名是某某明星的老婆,我为此感到强烈不满,但并未爆发。时代正发生着巨大变化,虚妄可当理想,心底欲望也可随心所欲地被表达,文化与知识赠与人的斯文与矜持已变得一文不值。写出这些,似有危言耸听之嫌,但我在这颇为极端的表达里获得安宁。
三
把名单放回书包,我触到钱包。除了几张卡片,那里一分钱也没有。今天早晨,我把身上仅有的现金给了母亲。她用一个蓝色的小布袋装着日常用的零花钱,用完了,并不跟我说,直等我自己发现。
孩子出生后,母亲跟我来到皖南。这几年的生活,对她来说是种煎熬。她心里一边记挂在老家的父亲,一边替我们照顾孩子。在她居住的小屋,我们原先没安装网络电视,只买了一个小小的卫星接收设备,今年3月被人上门没收。我又重新找人把电视弄妥当。我们不在家时,这台电子设备像个会说话的伙伴,陪着她。我也会在闲暇里带她和孩子在周边逛逛。有天,去城东的花鸟市场,我给孩子买下一个鱼缸,在挑鱼时,母亲指着红色的金鱼说很好看,想买一只。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听见母亲表达她内心的诉求,她语气柔软,听起来并不坚决。那鱼后来成了母亲的好朋友,它行动缓慢,总是躲在石块下不出来,而母亲总爱静坐在鱼缸前等它露面。后来,它感染白斑病,身体不能平衡,最终死去。
我捞出那瘦小的身体说:“可怜唉!”
母亲看着我说:“就一条鱼哟,可怜啥?”
她隐藏自己对鱼的恻隐之情,言不由衷的话只为安慰我。后来,我在鱼缸里养上野鱼,鳑鲏、青鳉、虾虎混住在一起,它们打打闹闹,在容器里转圈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母亲得出结论:青鳉鱼有攻击性,会撕咬鳑鲏的尾鳍。母亲有极强的叙述能力,她说青鳉鱼会突然冲上去,叨咬后立即跑开。鳑鲏被咬的尾巴,会慢慢腐烂,一条鱼由此瘫痪而亡。母亲不识字,但这更能衬托出她某些令人惊讶的能力,她独自去买菜,能快速算账;她会根据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第二天的事务。在城市囚禁般的生活里,母亲打开身体里那些微小敏锐的感知通道,学着去欣赏一条鱼,栽种一株花,尝试新的烹饪方法,这些是她排遣孤独的技巧。当然这城里依然有许多新鲜的人与事,比如穿花裙子的老太太。
我曾问母亲:“你穿过裙子吗?”
她说:“没有!”
我想带她去楼下的服装店买裙子,她找各种理由拒绝,我无法分辨她真实的内心。面对母亲和孩子,我认为,一个男人应该是雌雄同体的。如果我的细致能带给母亲一点欢愉,我会很开心。
母亲的生活是禁锢的,狭窄的。我不知道聪明的她会不会拿小鱼自比。有天下班,我看见母亲又坐在鱼缸前,后背在明亮的窗户下简约成一副剪影。第二天,我写下一首短诗《鱼》:
从乡下住到城里/母亲离玉米与土豆远了/ 离鱼缸近了/ 每天干完活,她喜欢坐在鱼缸前看/ 几条小野鱼在水里转圈圈
录完上面的分行句,已是下午的4∶30,孩子5∶10放学,我得去接他。雨很大,我没有伞。
四
在写作上,我很愚钝。
三个小时,我并未完成理想中的六千字。此时,仅有三四千字。
当我再次接着上面的继续写时,已是几天后的某个下午。上午上完课,在食堂用餐,再去办公室整理学生的毕业论文材料,到家时,已是三点。
困意阵阵袭来,我在键盘上敲着。只是,我可以坚持,虽然思维比较迟缓。
还是从咖啡厅出来的那个下午说起吧。我淋雨,一路往回跑,灰色裤子很快被雨点洇潮。我夹着电脑包,跑得飞快。穿过巷子和马路,我决定在一家牛奶店的屋檐下避雨。雨水顺着屋顶滑下来,落地砸得粉碎。我往里看,那个女店员是我熟悉的,她原先在对面的母婴店给宝宝们洗浴,后来跟女老板不和,就索性在对面的店里谋了新工作,一直做到现在。她曾托我给她儿子找家教,加我的微信,又觉得两小时一百元的费用她承担不起,也就不了了之。她经常发朋友圈,大多数都是自拍。她并不漂亮,但过得还算有主见,自信。
店里竟然装着自鸣钟,我听见它在雨声里响五次,还有十分钟,我的孩子就要放学。我先把书包和电脑放家里,再出门骑车去接孩子。匆匆忙忙,到幼儿园时,老师们领着孩子刚下楼。我听见:老师,我爸爸来了。那是亨亨的声音,他猛地冲出,踏着地面的积水朝我跑来。我一把拎起他。
时间有些紧,晚饭后,亨亨看会儿动画片,我再带他去上轮滑课。他最近对轮滑开始反感,以前他自己提出要学这个,上着上着,就想放弃。在轮滑教室,我看到他漫不经心的样子,有时会来气,认为那是专注力不够的表现。他滑过我身边,我提醒他要看着自己前面,专心点。上课回来,亨妈妈已经睡着,我抽空温习准备第二天的课。亨亨又看了会儿电视,到洗澡时,他表示反对,哭哭啼啼,还把遥控器故意放在地上。我没理他,他不断挑衅我,站在门外大声说:爸爸,你晚上不要跟我一起睡。嘭一声,他关了门。
我高声说:你说跟爸爸是好朋友,是吗?好朋友要和平相处,不能在家随便发脾气。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母亲后来向我描述他独自在客厅的行为。愤愤不平,用脚推倒垃圾桶,又俯身扶起来,然后坐在沙发上翻会儿书。等一切安静下来,我带他去洗澡,躺下,已是晚上十点钟。想着等孩子睡着,我再起身工作会儿或者写点东西,谁知倦意上头,躺下便再也不想起床。
夜晚,有时思绪翻飞,暗里的宁静是写作的最好时光,哪怕最后的篇章是零散的,它也能给我诸多慰藉。以上这琐碎的文字,是我在几天内完成的。一边是生活的琐碎,一边是内心渴望的纯粹。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孩子给了我无边的欢乐,但我依旧渴望属于我自己的孤绝的精神领地。那天,我在咖啡厅体会到的那短暂的寂静与安详,让我久久不能忘。那场下得十分突然的雨,也有着隐喻的味道。它仿如生活的嘈杂,我穿梭其中,但不能深陷其中。
写作与记录是我对抗琐碎与嘈杂的方式之一。我并不是特别关心此刻的书写是否有文学价值,只是有强烈的愿望去写下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平庸是生活的底色,我在这样的深夜顿然感受到平凡的价值。如果说,这样的内心独白是自我的,它一定也是普遍的。万千平庸男人与我过着相同的生活,晨起去买菜,下班后躺沙发上玩手机,这一切活色生香,况味十足。只是,在这之外,我渴望某种宁静与清醒。那么,不管是在白天抑或黑夜,我可以借着它听风听雨,把生活的琐碎好好整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