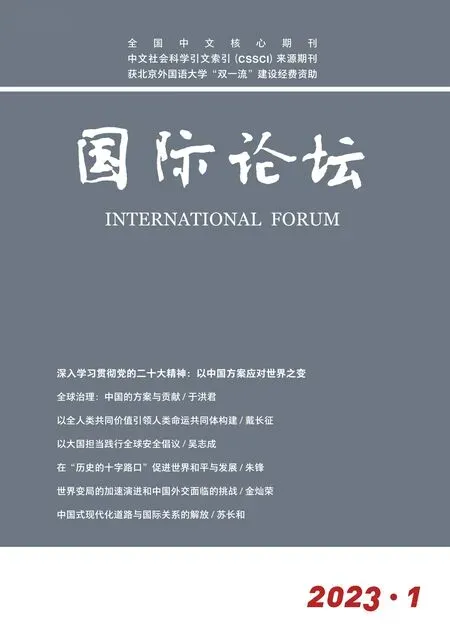核扩散研究的范式、特点与问题*
王 勇 许海云
【内容提要】 核扩散是安全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地区与国际安全,更体现了核扩散视阈下的国际核秩序与国际防扩散体系,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检视学界研究可发现,学者对核扩散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动因、逻辑、论辩和应对四种范式:动因范式说明了影响国家拥核意图的多重因素;逻辑范式解释了核扩散的市场路径和战略路径,解释了供需双方围绕核市场进行核合作的同时追求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原因;论辩范式使学者在争论中深入思考了核扩散产生的乐观与悲观、和平与冲突以及核身份差别等多重影响;应对范式提出了解决核扩散的办法。尽管学界对核扩散的研究拓展和深化了核扩散与安全研究的领域和深度,有助于深刻理解与认识核扩散的复杂影响,却难以解决核扩散的去政治化、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扩散之间的矛盾、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中的双重认识以及研究资料局限的问题。因而,核扩散的研究与现实仍存在差距,就目前核扩散局势来看,核扩散研究未能解决的难题仍然存在于防扩散治理之中,核扩散问题还会持续存在。
2021年9月16日,美英澳提出核潜艇合作,这一行为严重冲击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加剧了核扩散的紧张局势。事实上,自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核扩散一直是国际安全的热点,如何应对核扩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没有因冷战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应对核扩散问题上发挥着独特作用。长期以来,核扩散成为很受关注的探讨对象和主题,引起了国内外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学者的兴趣和持续不断的研究。①Scott Sagan, Kenneth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An Enduring Debate, New York: W.W.Norton, 2013; Jeffrey W.Knopf, Security Assurances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Daniel Joyn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Jeffrey R.Fields, State Behavior and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4; Harold A.Feiveson, Alexander Glaser, Zia Mian, Frank Von Hippel, Unmaking the Bomb: A Fissile Material Approach to Nuclear Disarmament and Nonproliferation,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14; Etel Solingen, Sanctions, Statecraft,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William C.Potter, Gaukhar Mukhatzhanova, Forecasting Nuclear Prolif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崔建树:《从小布什到奥巴马政府的美国核战略和核不扩散政策演变》,《和平与发展》2009年第5 期,第33—39 页;梁长平:《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遵约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刘子奎:《冷战后美国防扩散政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詹欣:《冷战与美国核战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王震:《一个超级大国的核外交:冷战转型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1969—1976)》,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刘宏松:《国际防扩散体系中的非正式机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韩长青:《从中苏防止核扩散论战看中国核政策缘起》,《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 期,第63—80 页。
核扩散是本文讨论的核心概念,它包括横向扩散和纵向扩散。横向扩散(Horizontal Proliferation)是指“核武器国家”扩散到“无核武器国家”的过程;纵向扩散(Vertical Proliferation)是指把更尖端的核武器技术扩散给已经拥有核武器技术的国家,使接受国的核武器技术有质的提高,也指有核国家不断提高核武器技术,谋求核优势。②滕建群:《美国防扩散与反扩散政策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11年,第1 页。这两类扩散存在实质性区别,但通常来说,在没有特指的前提下,核扩散意指横向扩散,提及纵向核扩散时会加以强调说明,本文亦是如此。本文以核扩散研究的理论范式为出发点,梳理学术界关于核扩散起因、逻辑、影响与应对策略的研究,考察核扩散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核扩散的动因范式
从曼哈顿工程来看,核武器及其相关设施、材料和技术很难由一国独立获取,美国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一国难以垄断核武器技术,核武器从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扩散”的烙印。通过相关学术史的梳理不难发现,诸多研究归纳了国家选择发展核武器的复杂动因,主要体现在安全需求、国内政治、技术动力和国际规范四个方面。
第一,核武器是满足国家安全需求的工具。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各国共存于无政府状态下,“自助”(self-help)是无政府秩序下的行为准则,国家保护自身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为自身提供安全。①[美]斯科特·萨根、[美]肯尼思·华尔兹:《核武器的扩散:一场是非之辩》,赵品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 页。核武器无疑成为国家追求安全的工具之一。布莱德利·泰勒(Bradley A.Thayer)据此研究认为,安全是核扩散最重要的原因。②Bradley A.Thayer, “The Cause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the Utility of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Security Studies, Vol.4, Iss.3, 1995, p.482.具体而言,英国和美国之所以大力研制原子弹,是因为它们担心德国率先研制出核武器会产生不可接受的安全影响。美国拥有核武器造成了苏联的恐惧,刺激了斯大林加速研制核武器。同样,中国发展核武器也是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③[英]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黄钟青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第26 页;Davi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56,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7;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 期,第78 页。斯科特·萨根(Scott D.Sagan)认为,一个国家通过发展核武器平衡该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时,会被视为对该地区的另一个国家造成核威胁,后者不得不启动核武器计划,以维护其国家安全。④Scott D.Sagan, “Why Do States Build Nuclear Weapons? Three Models in Search of a Bomb,”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No.3, Winter, 1996-1997,pp.57-58.甚至有学者认为,外部威胁对于一国发展核武器具有决定性作用。⑤高望来:《核时代的战略博弈——核门槛国家与美国防扩散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6 页。
第二,国内政治是一国核选择的重要因素。首先,以领导人为核心的决策者群体根据安全、资金、技术和核能需求等因素衡量拥核利弊,选择是否发展核武器。⑥Jacques Hymans, Achieving Nuclear Ambitions: Scientists, Politicians, and Proliferation,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62-277.换言之,当拥核成本大于拥核收益时,一国决策者决定暂时或者长期不拥核。反之,当拥核收益大于成本时,一国会选择发展核武器。其次,科学家群体在国家发展核武器问题上态度复杂。一方面,科学家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劝服领导者选择研制核武器,为其提供核武器技术支持。⑦Matthew Fuhrmann, “Spreading Temptation:Proliferation and Peaceful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 No.1, 2009, p.13.二战期间,流亡科学家意识到纳粹集权的奴役性质和核武器对人类文明的毁灭性,游说英、美政府投入核武器的研发。①史宏飞:《欧洲流亡科学家、科学国际主义与英美核武器研发合作的肇始》,《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15年第2 辑,第258 页。在印度发展核武器过程中,科学家的作用最为突出,以霍米·巴巴(Homi Bhabha)为代表的印度核科学家在实施计划时拥有充分的自主性。②代兵:《论尼赫鲁政府的双重核政策》,《南亚研究》2014年第4 期,第97 页。另一方面,鉴于核武器的杀伤性和核扩散后果,科学家转而又成为核军备控制的支持者。③Kai-Henrik Barth, “Catalysts of Change: Scientists as Transnational Arms Control Advocates in the 1980s, ”Osiris, Vol.21, No.1, 2006, pp.182-206.最后,除高层决策者与核科学家的直接努力外,底层逻辑在核武器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④尹晓亮:《战时日本开发原子弹的底层逻辑、推进体制与路径方法》,《世界历史》2021年第6 期,第59 页。
第三,技术动力是国家核选择的驱动力。持“技术决定论”观点的学者认为,技术作为发展核武器的推动力,一旦一国掌握了潜在核技术,该国发展核武器只是时间问题。⑤Sonali Singh, Christopher R.Way, “The Correlate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A Quantitative Tes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8, No.6, 2004, p.862.和平利用核能无疑加深了核能、核武器与核扩散之间的复杂联系。马修·克洛宁(Matthew Kroenig)考察了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核合作、民用核合作、核援助与核扩散的关系,无疑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⑥Matthew Kroenig, “lmporting the Bomb: Sensitive Nuclear Assistance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3, No.2, 2009, pp.161-180; Dong-Joon Jo and Erik Gartzke,“Determinants of Nuclear Weapons Prolifer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1, No.1, 2007,pp.167-194.不仅如此,即便是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实施的技术合作项目同样增加了核扩散的可能性。⑦Robert L.Brown, Jeffrey M.Kaplow, “Talking Peace, Making Weapons: IAEA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8, No.3, 2014, pp.182-206.但值得注意的是,拥有核技术的核门槛国家不一定发展核武器,技术因素是国家研制核武器的必要条件而非决定性因素。⑧Sonali Singh, Christopher R.Way, “The Correlate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A Quantitative Test,”p.863.一国掌握核技术无疑增加了核扩散的可能性,但核技术能力是否同发展核武器的意图相结合取决于该国的核选择。
第四,国际规范影响国家的核选择。国际规范把核武器视为国家身份和国家地位的象征。雅克·海曼(Jacques Hymans)认为,领导者准确的国家身份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是否发展核武器。①Jacques E.C.Hymans, The Psychology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Identity, Emo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8.换言之,一国需要发展核武器彰显其身份,国家会重视营造核武器国家身份特性的气氛。如戴高乐及其支持者认为,拥有原子弹是法国通往大国之路的标志。法国核试验后,戴高乐为此发表“法国万岁!从今晨开始,法国变得更加强大而自豪”的公开信。②[美]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637—647 页;朱明权:《核扩散:危险与防治》,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 页。中国发展核武器既是安全需要,也是中国未来国际地位的需要。③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第78 页。现在置身于核扩散问题中的国家也往往把核武器、核技术看做是国家地位的重要象征,例如朝鲜和伊朗。④李彬、肖铁峰:《重审核武器的作用》,《外交评论》2010年第3 期,第8 页。由此可见,核武器不仅是超杀武器,还是一国核科学技术、核工业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体现。
动因范式清晰地钩沉出国家发展核武器的考量因素,是认识核武器缘何扩散的基本思路。除上述因素外,学者还从国家体制、核抑制和威慑理论等角度分析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动因。事实上,核武器只是国家安全、国家身份、国际地位和核科学技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内政治只是影响国家核选择的一个方面,国家核选择应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核扩散合作双方的市场与战略逻辑范式
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动因是复杂多变的,但核扩散的逻辑是有迹可循的。冷战初期,苏联核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仅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还冲击了美英核工业,更证明了苏联和平利用核能技术的能力。美英两国意识到,苏联能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核技术获益,而美英分别受制于《魁北克协定》和《原子能法案》,无法同苏联进行核竞争。1953年艾森豪威尔“和平利用原子能”演讲不仅打破了这一限制,也标志着核技术扩散的彻底转变。⑤Bertrand Goldschmidt, “A Historical Survey of Nonproliferation Polic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 No.1, 1977, p.71.这一转变加快了核技术的合作进程,形成了以和平利用核能为主体的核市场,合作双方在战略利益考量下进行核合作。
(一)核扩散的市场逻辑
核扩散的市场逻辑是描述核扩散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的互动关系。①核扩散的需求理论旨在探究一国为何要研发、制造并部署核武器,以及为何要发展核能产业(包括核反应堆的设计、工程与建造,以及核燃料循环产业);供给理论旨在探究核能供应国向其他国家转移核能产业相关的设施、材料与技术的内在规律。[美]斯科特·萨根、[美]肯尼思·华尔兹:《核武器的扩散:一场是非之辩》,第x 页。据马修·福尔曼(Matthew Fuhrmann)统计,“原子为了和平”之后,全世界达成了2000 多个双边民用核能合作协议(NCAs),承诺所有关涉核技术、材料和信息的交换仅用于和平目的。②Matthew Fuhrmann, “Taking a Walk on the Supply Side: The Determinants of Civilian Nuclear Cooper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3, No.2, 2009, pp.181-208.在这一合作过程中,提供核援助的私营公司往往同政府官僚机构中支持出口的机构和国家核能委员会结成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③Jayita Sarkar, “U.S.Policy to Curb West European Nuclear Exports, 1974-1978,”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21, No.2, 2019, pp.111-112.供应方通过核市场获得经济收益,带动本国的核工业发展,而需求方则获取了先进核技术,满足了本国核技术应用需求。
供应方在核扩散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主要由部分先进核技术国家组成,各个供应方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影响核供应市场的走向,在核扩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和平利用核能的发展,美国在国际核贸易市场中处于绝对优势。④刘姝:《美国核出口管制政策的法律维度——以美国对法国核政策为视角》,《史学集刊》2016年第6 期,第65 页。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欧先进核技术国家在核供应市场上迅速崛起,削弱了美国的核供应优势地位。仅1975年联邦德国和巴西的和平利用核能合作项目总价值就超过120 亿联邦德国马克(50 亿美元),这是第一次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完整的、自给自足的核燃料循环“打包销售”。⑤William W.Lowrance,“Nuclear Futures for Sale: To Brazil from West Germany, 1975,”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 No.2, 1976, p.148.为了进行商业竞争,美国联合盟国向德国施压,试图使德国放弃核敏感物项出口。⑥William Gray, “Commercial Liberties and Nuclear Anxieties: The US-German Feud over Brazil,1975-77,”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34, No.3, 2012, p.449.一时间,核供应方之间出现无序竞争之势,美国便采取了遏制西欧核出口的政策。⑦Jayita Sarkar, “U.S.Policy to Curb West European Nuclear Exports, 1974-1978,”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21, No.2, 2019, pp.110-149.
供应方在竞争中也有合作。1971年成立的桑戈委员会(Zangger Committee)补充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非条约成员国之间的核合作程序。1975年成立的核供应国集团(Nuclear Suppliers Group)是具有核供应能力的国家组成的“供应商俱乐部”。①William Epstein, “The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Scientific American, Vol.232, No.4, 1975, p.32.这些组织的建立旨在协调主要核供应国的出口控制,体现了供应国之间的市场合作。
对于核扩散的需求方而言,接受核供应利大弊小。一方面,需求方总是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存在能力不足问题,但供应方提供的敏感核援助可以帮助一国克服这些技术困难。需求方可以获取供应方提供的经过验证的核技术设计,减少核设施成功运行所需的试错代价,节省需求方的核武器发展成本,帮助需求方避开国际监督。②Matthew Kroenig, “Importing the Bomb: Sensitive Nuclear Assistance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3, No.2, 2009, pp.164-165.另一方面,需求方通过核合作不仅获取了核技术,而且提高了核武器研制能力,成为“潜在核武器国家”,为发展核武器节省了时间。不难看出,供应方与需求方的核合作无疑都难以避免核扩散的风险。
(二)核扩散的战略逻辑
市场逻辑解释了核扩散双方的供需合作,但未能充分说明双方因何忽视核扩散风险,而核扩散的战略逻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逻辑解释的不足。首先,核合作是国家军事战略的选择。二战期间,美英加核合作是曼哈顿工程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战后美国通过的《原子能法案》短暂关闭了美苏合作的大门。艾森豪威尔提出和平利用原子能之后,各国利用核援助加强同受援国的双边关系,并以符合其政治战略利益的方式促进受援国的发展。③Matthew Fuhrmann, Atomic Assistance: How ‘Atoms for Peace’ Programs Cause Nuclear Insecurit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3.马修·富尔曼认为,核援助的战略价值在于它能加强同敌人的敌人之间的关系,巩固民主国家联盟,加强民主国家的双边关系。④Matthew Fuhrmann, “Taking a Walk on the Supply Side: The Determinants of Civilian Nuclear Cooperation,” p.182.马修·克洛宁则认为,国家更可能向有着共同敌人的国家提供敏感性核援助。通过提供敏感性核援助,核供应国能增加敌对国家的战略成本。⑤Matthew Kroenig, “Exporting the Bomb: Why States Provide Sensitive Nuclear Assista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3, No.1, 2009, p.127.20世纪50年代美国向联邦德国出口核反应堆就是东西方政治的考量。⑥Mara Drogan, “The Nuclear Nation and the German Question: An American Reactor in West Berlin,” Cold War History, Vol.15, No.3, 2015, pp.301-319.
其次,核合作是国家经济战略的选择。20世纪50年代,各国普遍认为核反应堆会成为国际贸易的焦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和平利用核能”被英国官员称之为“原子马歇尔计划”(Atomic Marshall Plan),在没有任何外部因素约束的情况下,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巩固美国在民用核能领域的主导地位。①Stephen Twigge, “The Atomic Marshall Plan: Atoms for Peace, British Diplomacy and Civil Nuclear Power,” Cold War History, Vol.16, No.2, 2016, p.229.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欧核出口的迅速崛起才打破这一局面。此时,美国打击西欧核出口过程中,经济战略逻辑起重要作用。②Jayita Sarkar, “U.S.Policy to Curb West European Nuclear Exports, 1974-1978,” p.112.经济利益是衡量美国选择核援助与防扩散的重要考量因素,美国会选择符合美国利益的援助,反之则采取防核扩散政策。③丁思齐:《美国应对核扩散的行为逻辑》,《国际观察》2019年第5 期,第81 页。
最后,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为核合作提供了依据。国际原子能机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都提到了成员国内部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各国便在此框架内进行核合作。同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可以通过核供应国集团或桑戈委员会进行核合作。但是,供应国集团制定了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更严格的出口控制规范,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核供应国集团向外界通报其出口管制安排提供了主要的正式渠道,核供应国集团则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措施作为核出口的条件。④Tadeusz Strulak, “The Nuclear Suppliers Group,”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1, No.1, 1993, p.7.而桑戈委员会一直根据核技术领域的发展不断更新触发清单并进行修改,然后由委员会内部协商一致并做出决定,随后同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交流。⑤Ian Anthony, Christer Ahlström, Vitaly Fedchenko, Reforming Nuclear Export Controls the Future of the Nuclear Suppliers Group, SIPRI Research Report No.2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5.
市场逻辑与战略逻辑都是核扩散的路径,供需双方围绕核市场进行合作,以和平核合作换取共同利益,难以避免地产生了核扩散的风险,而战略逻辑解释了合作双方忽视风险的原因。无论是市场逻辑还是战略逻辑,核合作引发的核扩散风险都是显而易见的。历史表明,足够数量训练有素的操作民用核设施的人员完全具有开发核武器的能力。⑥刘子奎:《核扩散问题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世界历史》2016 第5 期,第93 页。最近研究发现,接受铀浓缩、后处理设备、炸弹设计或大量武器级裂变材料的国家更可能获得核武器。⑦Matthew Kroenig, “lmporting the Bomb: Sensitive Nuclear Assistance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3, No.2, 2009, pp.161-180.由于核技术的两用性,和平核合作与核扩散之间存在因果联系。⑧Matthew Fuhrmann,“Exporting Mass Destruction: The Determinants of Dual-Use Trade,” Journal of Peace Reseach, Vol.45, No.5, 2008, pp.633-652.
三、核扩散的是非论辩范式
核武器诞生之初,核扩散成为科学界、政治界和学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战后初期,部分科学家倾向于把核武器的秘密告诉苏联,认为核扩散不可避免,但美国政府不但拒绝核分享,甚至通过立法关闭了向盟友核分享的大门。事实上,美国的核垄断无法奏效,核武器不可避免地从一国拥有到多国拥有,从超级大国扩散至第三世界国家。于是,如何看待核扩散的影响成为学界争论的话题。
(一)乐观派与悲观派论辩
核扩散乐观派学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认为,核武器因素的介入使得要误算战争的后果也难,因为即使少量弹头所能造成的损失也是显而易见的。新生核国家会同样感受到现有核国家已感受到的强制性约束。①[美]斯科特·萨根、[美]肯尼思·华尔兹:《核武器的扩散:一场是非之辩》,第33—34 页。换言之,由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核战争成本高收益低。由于新生核国家的自我克制,核扩散导致战争难以爆发,核扩散“越多越好”。从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来看,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W.Graham)认为,获取核武器比战略家预想的要难,国际防扩散体系相当成功,声称赢得了防扩散战争。②Thomas W.Graham, “Winning the Nonproliferation Battle, ”Arms Control Today, Vol.21, No.7,1991, p.8; Zachary S.Davis, “The Realist Nuclear Regime,” Security Studies, Vol.2, No.3/4, 1993, pp.79-99.
斯科特·萨根以核扩散的悲观态度回应了乐观派的观点。萨根基于组织理论与威慑理论认为,由于职业军事组织内存在的共同偏见、僵硬成规与狭隘利益,它所呈现出的组织行为可能会导致威慑失灵,并引发蓄意或事故性战争。除非通过由文官牢固掌控的监督制衡体系对其进行专业化管理,否则军事组织就达不到实现稳定威慑的实施要件,他担心未来的核国家将会缺乏有效的文官统治机制。③[美]斯科特·萨根、[美]肯尼思·华尔兹:《核武器的扩散:一场是非之辩》,第39 页。不仅如此,比起冷战时期核技术基本被大国垄断的态势,现今民用核技术的发展与核门槛降低均使得防止核扩散的国际压力增加。④胡高辰:《从国际核态势视角看国际核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1 期,第57 页。因此,核扩散“越多越糟”。
乐观派与悲观派都试图解释核扩散的影响,但难以充分剖析核扩散的实质。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论述把威慑的“不确定性”绝对化了,他忽略了核威慑稳定本身有赖于“试错学习”过程中日益强化的核禁忌,同时也有赖于各国科技发展的动态平衡。同华尔兹相反的是,萨根的悲观论则把核事故导致的核战争可能性绝对化了,片面夸大了核战争的风险,以至于认为由核威慑失灵所引发的核战争最终不可避免。①[美]斯科特·萨根、[美]肯尼思·华尔兹:《核武器的扩散:一场是非之辩》,第viii 页。
(二)和平与冲突论辩
长期以来,核武器被认为是“长和平”的因素之一,是一种谈判工具。②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0, No.4, 1986, p.120.这种核武器和平论认为,如果对抗双方都拥有了核武器,双方会变得更谨慎,从而实现和平。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认为,荒谬而实则有理的结果是核武器破坏力越大,其合理使用的可能性便越小这样一种相反的关系。③[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4 页。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如果德国拥有核武器,欧洲将更加稳定,核武器在战后欧洲免于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④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No.1, 1990, pp.8-27.正是核武器的破坏性与不可用性之间的矛盾关系,造成了“核和平”的假象。中国学者杜彬伟认为,“核和平”观念不禁止核武器的扩散,反而鼓励核武器有步骤地扩散,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为某些核大国实施针对横向核扩散的“双重标准”奠定了理论基础,同防扩散机制的宗旨背道而驰。⑤杜彬伟:《防止核扩散机制的评析及其出路》,《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2 期,第133 页。核武器和平论只是说明了拥核双方产生了核抑制而不敢轻易发动战争,突出了核身份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无形中刺激了核扩散。
稳定—不稳定悖论(stability-instability paradox)虽然认可了拥核双方出现的核和平,但强调了双方的常规军事冲突。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两个国家都拥有核武器、构建了相互威慑的关系,那么谁都不敢轻易地使用核武器,以免遭到对手的报复性打击,导致不可接受的损失;但是,既然战略层面没人敢轻举妄动,那么常规军事层面的摩擦可能会增加。⑥胡高辰、李彬:《稳定—不稳定悖论的批判与美国的安全研究范式分析》,《国际论坛》2018年第4 期,第52 页。照此推断,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威廉姆·赖克(William Riker)认为,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冲突可能演变成核冲突。但两个核国家发生冲突时,考虑到核报复能力,冲突不会演变为核冲突。当所有国家都拥有核武器时,双方冲突演变成核冲突的可能性降至为零。①Bruce Bueno de Mesquita, William Riker, “An Assessment of the Merits of Selective Nuclear Prolifer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6, No.2, 1982, p.283.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身份与常规军事冲突成为稳定—不稳定悖论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典型案例。②Christopher J.Watterson, “Compet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tability-instability Paradox: The Case of the Kargil War,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24, Iss.1-2, 2017, pp.83-99;Michael D.Cohen, “How Nuclear South Asia is Like Cold War Europe,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20, Iss.3, 2013, pp.433-451.虽然印度与巴基斯坦没有发生核战争,但常规军事冲突不断,造成了南亚地区长期的不稳定。
核扩散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核技术,虽然核国家之间没有爆发核战争,但不意味着核武器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核和平假说”不断遭到质疑的原因在于当两国之间存在核不对称时,发生军事化争端和战争的可能性更大。相比之下,如果两国之间存在对称性,并且都拥有核武器,那么战争的概率就会急剧下降。尽管核武器促进战略稳定,但低烈度争端也存在更多风险。③Robert Rauchhaus, “Evaluating the Nuclear Peace Hypothesis: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3, No.2, 2009, p.258.同时,稳定—不稳定悖论也存在逻辑漏洞:常规层面可能在构建战略稳定前更不稳定;常规层面不稳定的判断标准随意。④胡高辰、李彬:《稳定—不稳定悖论的批判与美国的安全研究范式分析》,第53—54 页。无论是核武器和平论还是稳定—不稳定悖论,都突出了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其结果是促使更多的国家发展核武器,造成核扩散的紧张局势。
(三)身份差别论辩
很多西方人的笔端流露出对第三世界国家拥有核武器前景的恐惧,好像仍以过去帝国主义者的眼神来审视这些国家的民众,认为他们“缺乏教养、无法无天”。还有这种种族主义观点在作祟,臆测取代了实证。⑤[美]斯科特·萨根、[美]肯尼思·华尔兹:《核武器的扩散:一场是非之辩》,第10 页。核扩散初期,在第四个核国家问题上,当时的有核国家美国、苏联和英国担心“第四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会造成严重后果,强调阻止核扩散。⑥刘子奎:《美国早期防扩散政策与美英苏禁止核试验谈判》,《历史研究》2015年第4 期,第125—126 页。20世纪60年代初,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不能允许联邦德国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德国成为核不扩散问题的关键。然而,美国在处理德国与中国核问题的过程中,却以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国家身份进行考量,认为中国发展核武器影响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对中国发展核武器存在偏见。①Melvyn P.Leffler, Odd Arne Westa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 II Crises and Déten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401-402.
民主和平论助长了这种核扩散身份差别观念。与冷战时期主要担心西方联盟分裂而实施选择性防扩散不同,冷战后美国实施选择性防扩散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的“民主和平论”。美国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把扩散分为好的和坏的扩散,主张阻止坏的扩散,允许好的扩散。②刘子奎:《论冷战后的美国防扩散政策》,《美国研究》2013年第1 期,第33 页。一些学者认为,民主国家有能力解决安全困境,扩大和平区域能减少核扩散威胁,民主国家不太可能发展核武器。③Christopher Way, Jessica L.P.Weeks, “Making It Personal: Regime Type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8, No.3, 2014, pp.705-719.事实上,上述核扩散动因研究表明,发展核武器是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身份差别观念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不具有说服力。
核扩散的身份差别观念集中体现在核不扩散机制的遵约问题上。尼克松政府容忍了以色列核扩散,美以达成了“以色列保守拥有核武器秘密”的交易。④Or Rabinowitz, Nicholas L.Miller, “Keeping the Bombs in the Basement: U.S.Nonproliferation Policy toward Israel, South Africa, and Pakist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0, No.1, 2015, p.60.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发起国和主导国,美国默认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做法违反了条约规定,成为核扩散双重标准的典型案例。继1974年核试验之后,1998年印度公开核试验成为核国家。印度违反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行为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但美国和印度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签署了《美印民用核技术协定》(CNCI)和美印《123 协定》,这两份文件是美国严重违反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标志。⑤吴彤、张利华:《美国与印度进行核合作的动因》,《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4 期,第1 页。同以色列不同的是,朝鲜、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核项目却被认为挑战了核不扩散机制。⑥Chaim Braun, Christopher F.Chyba, “Proliferation Rings: New Challenges to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9, No.2, 2004, p.5.显然,这种身份差别观念产生的双重标准、选择性核扩散违反了核不扩散机制。
论辩范式是核扩散研究的特色。核扩散受“悲观与乐观”、“和平与冲突”和“身份差别”等不同视角的论辩研究,反映了核扩散议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论辩研究表明,看待核扩散态度的不同,对战争影响的不同,以及国家身份的不同,核扩散的影响就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核扩散论辩范式的研究虽然深化了对核扩散影响的认识,但也常出现争议性问题。首先,核扩散悲观派与乐观派都提出了核扩散“越多越糟”和“越多越好”的依据,但双方都提供了不可靠的预测,因为它们过度依赖那些促使国家发展核武器或者抑制的概念。①Peter R.Lavoy, “Nuclear Myths and the Cause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2,Iss.3-4, 1993, p.192.其次,虽然冷战后超级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从本质上说已经消失,但由于核技术的扩散和一些地区冲突迟迟未能解决等因素的影响,核战争的风险在增加而不是降低。②刘子奎:《奥巴马政府防核扩散政策评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 期,第103 页。最后,身份差别使核扩散研究这一安全问题政治化,产生了选择性核扩散与双重标准这样的核扩散政治化问题,同国际防扩散机制的原则相矛盾。
四、核扩散的应对范式
如何应对核扩散成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和全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1953年原子能和平利用之后,各国进行了密切的核合作,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了核技术,核扩散的局面越来越严峻。在应对核扩散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同国际社会一道制定了多重措施防止核扩散。
(一)原子能国际控制与核垄断
原子能国际控制思想早于核武器产生。1944年夏末,曼哈顿计划工程师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和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开始认识到核能的发展会是人类文明史的转折点,二人认为是时候考虑核能的国内与国际控制了。③Richard G.Hewlett, Oscar E.Anderson,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The New World, 1939-1946,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322.美国政府官员也同样认识到核武器会成为国际问题,亨利·史汀生(Henry L.Stimson)、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Patterson)和迪安·艾奇逊(Dean G.Acheson)认为,应当同苏联进行谈判,不应保守秘密。苏联人肯定是要开发原子弹的,也许在四年或五年之内就可以成功,如果不立即做出努力来交换科技情报,建立某种形式的国际控制,就会引发一场不祥的核军备竞赛。④[美]梅尔文·P.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孙建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27—128 页。
杜鲁门政府展开了原子能国际控制的政策辩论,从史汀生备忘录和杜鲁门关于原子能问题的特别咨文不难看出,美国把苏联作为原子能国际控制机制中的重要合作和反对对象。①刘京:《科学家、史汀生备忘录与美国原子能国际管制政策的出台》,《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20年第1 辑,第44 页。1946年,美苏推动成立的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UNAEC)成为原子能国际控制的舞台。在成立大会上,美国的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与苏联的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提出了各自的国际原子能管制方案,没有达成一致性意见。美国提出的巴鲁克计划被视为冷战开始时形成美国整体政策若干态度和设想的产物,是美国原子能垄断思想的表现。②Larry G.Gerber, “The Baruch Pl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6,No.1, 1982, p.93.
原子能国际控制的失败和冷战的发展致使美国坚持核垄断政策,防止更多国家获得发展核武器的技术信息。首先,1946年杜鲁门签署《原子能法》,关上核合作的大门。其次,成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完全由政府控制垄断核技术。苏联与英国先后于1949年和1950年进行了核爆炸,打破了美国核垄断的防核扩散政策。结果表明,这一时期的原子能国际控制与美国核垄断未能阻止核扩散。
(二)打击、制裁与反扩散
打击核设施在核武器诞生之前便已经存在了。1943年2月27日,盟军袭击了挪威里尤坎地区几个为德国生产重水的工厂。为防止这些工厂的修复,1943年11月盟军对里尤坎地区了大规模的空袭。美国占领日本后,占领军破坏了日本回旋极速器。③[美]莱斯利·R·格罗夫斯:《现在可以说了: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的故事》,钟毅等译,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1年,第152—153 页、第307—311 页。打击核设施无疑阻碍了德日的核进程,德日在战时没有研制出核武器。冷战以后,打击核设施成为阻止他国发展核武器的一种手段。在中国发展核武器时期,美国计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以此来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1981年6月7日,以色列袭击了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奥斯拉克核反应堆。2007年9月6日,以色列袭击叙利亚阿尔奇巴尔核设施。在伊核问题上,以色列更是试图给伊朗核能力设定“红线”,威胁伊朗的和平利用核能计划。
军事打击一国核设施虽然暂时达到了阻止该国发展核武器的目的,但这一方式存在复杂影响。首先,核设施的安全与安保是一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相关国际法尚不能对这种行为进行切实、有效的裁决。①赵学林、赵畅、袁永龙、刘家铭:《关于对攻击他国核设施行为进行裁决时国际法依据及相关判例的研究》,《国外核新闻》2020年第12 期,第17 页。其次,军事打击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技术可行性存在不确定性。历史上,正是担心国际社会的谴责、情报的准确性和政治风险,约翰逊政府放弃了打击中国核设施的选择。②詹欣:《美国对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对策再考察》,《国际论坛》2015年第5 期,第44 页。最后,从长期看,这种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该国的核选择。奥斯拉克袭击事件的结果事与愿违,袭击延缓了伊拉克获取核武器,但伊拉克继续实施了隐蔽的核项目,这一袭击给核扩散风险带来了长期的复杂影响。③Målfrid Braut-Hegghammer, “Revisiting Osirak: Preventive Attacks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Risk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6, No.1, 2011, pp.131-132.
制裁是应对核扩散的“大棒”政策。在原子能领域,制裁核扩散在1946年巴鲁克计划就已经提出了,巴鲁克认为,有必要明确规定对任何违反原子能条款的国家进行制裁,必要时使用武力。④Larry G.Gerber, “The Baruch Pl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6,No.1, 1982, p.72.埃泰勒·索林根(Etel Solingen)认为,制裁是惩罚或否认那些领导人、统治联盟和更大范围支持者获得收益的工具。⑤Etel Solingen, Sanctions,Statecraft,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57.1968年达成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界定了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的区别,安德鲁·格罗托(Andrew Grotto)则认为,制裁是针对那些新扩散者。⑥Jeffrey W.Knopf, “Nuclear Disarmament and Nonproliferation: Examining the Linkage Argu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7, No.3, Winter, 2012/13, p.99.通常情况下,经济制裁核扩散是联合国和部分国家的主要防核扩散手段。
反扩散是冷战后美国提出的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手段。反扩散突出“先发制人”的思维逻辑和预防性打击的行为模式,即把具有防扩散能力的国家列为主要打击目标,只要美国认为该国有核武装的能力,不论是能力上,还是意图上,美国除了动用外交资源外,还可以动用武力把核扩散的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⑦滕建群:《美国防扩散与反扩散政策研究》,第1—2 页。但是,美国的反扩散政策却存在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2004年4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540 号防扩散决议虽然为美国的反扩散提供了更大和更自由的空间,但仍满足不了反扩散所需的法律要求。由于无法论证先发制人的合法性,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美国诸多反扩散行为缺乏国际法基础。①刘子奎:《冷战后美国防扩散政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8 页。
(三)延伸威慑
延伸威慑是指拥有核武器的一方(或超级核大国),依赖于其核威慑力,给予其友邻或盟国以核保护。②张曙光:《威慑理论:美国国际战略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美国研究》1990年第4 期,第41 页。换言之,延伸威慑就是核国家的安全保证,这种安全保证在国际政治中最突出的作用就是同防核扩散相联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那些放弃发展核武器的国家设法确保这样做不会危及它们对有核国家的安全,同时,这些无核国家既要求消极安全保证(Negative Security Assurance),即核武器国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也要求积极安全保证(Positive Safety Assurance),即承诺向正在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攻击无核武器国家时核武器国家应提供援助。③Jeffrey W.Knopf, Security Assurances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延伸威慑最常见的就是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美国最常用的防核扩散手段。
美国利用延伸威慑防核扩散具有多重目的。一方面,美国通过提供核保护伞巩固了美国与这些盟国的主从关系和领导地位。④李彬、肖铁峰:《重审核武器的作用》,《外交评论》2010年第3 期,第9 页。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延伸威慑在盟国布置核武器。⑤陈波:《艾森豪威尔政府与美国在意大利的核部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 期,第73 页。弗里德曼指出,延伸威慑所存在的问题是,美国怎么可能为保卫欧洲而甘冒核战争的危险。⑥[英]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第337 页。江天骄则认为,获得美国延伸威慑保护的国家或约束自己的核扩散行为,或走上研发核武器的道路,抑或推行两面下注的“核避险”战略。只有当延伸威慑的可信度高时,美国的安全承诺才能替代盟友发展核武器,起到防扩散作用。⑦江天骄:《同盟安全与防扩散——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及其确保机制》,《外交评论》2020年第1 期,第125—153 页。
(四)合作构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苏联和英国成为核国家之后,如何应对核扩散逐渐成为美英苏之间的共同利益。首先,艾森豪威尔建议向各国提供和平核技术,以换取他们放弃开发核武器。⑧刘子奎:《冷战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史林》2018年第6 期,第175 页。其次,美国通过的《1954年原子能法案》增加原子能商业化和其他私人机构的参与机会来缓和政府核垄断,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严格的保密限制。①Herbert S.Marks,George F.Trowbridge, “Control of Information under the Atomic Energy Act of 1954,”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11, Iss.4, 1955, p.128.最后,美苏进行禁止核试验谈判,关闭其他国家通过核试验开发核武器的大门。②刘子奎:《卡特政府防核扩散政策的考察》,《历史研究》2021年第5 期,第147—148。美苏继续进行防核扩散谈判,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合作构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指的是国际社会为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和核军控而制定的所有国家的和国际的、双边与多边的法律、条约、协定和所成立的机构的总和。现行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核心,在内容上包括有关核裁军、建立无核区以及限制核武器发展和部署的国际条约、有关无核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的联合国决议和政府声明、有关国际安全的其他协定、有关核裁军和核军控的组织以及有关国际出口控制与核查的机构。③卢静、王文辉:《当前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构成及特点》,朱立群、[美]盖瑞·博驰、卢静主编:《国际防扩散体系:中国与美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26—27 页。同时,也应看到,防扩散机制是个“君子协定”,不足以阻止和抑制“决心求核”的国家。④杜彬伟:《防止核扩散机制的评析及其出路》,《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2 期,第134 页。
五、核扩散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梳理核扩散研究的动因、逻辑、论辩与应对范式,不难看出,这些范式采取了多学科交叉研究,显示了较强的主动性、理论性和现实性。这些研究虽然拓展了认识核扩散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核扩散“去政治化”问题研究不足。虽然现有研究系统地揭示了核扩散的动因、逻辑、影响与应对措施,但防核扩散仍然是国际安全的难题,原因在于核扩散仍是安全问题之外的政治问题,难以使核扩散研究“去政治化”。滕建群认为,“去政治化”不是不讲政治,相反要求有关各方真正达成政治上的一致性,然后把核问题留给技术专家。⑤滕建群:《核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世界知识》2007年第21 期,第63 页。由于核武器兼具军事与政治双重作用,核武器被视为国家地位的象征,给防核扩散带来了难题。防止核扩散的一个方法就是将核武器与国家地位脱钩。⑥李彬、肖铁峰:《重审核武器的作用》,《外交评论》2010年第3 期,第8 页。核扩散的政治化还表现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不完善性和防核扩散的双重标准问题上。作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基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具有明显的缺陷:一是对于退约的国家缺少办法;二是双重标准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大;三是对于游离于条约之外的事实核武器国家只能听之任之。①郭晓兵:《〈不扩散核武器条约〉50年回顾:得失、挑战与出路》,《世界知识》2020年第11 期,第73 页。此外,受核大国核政策与研究材料的影响,现有的核扩散研究主要集中于横向核扩散,学界应加强有核国家纵向核扩散方面的研究。
第二,当前,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扩散之间矛盾突出,应引起核扩散研究者持续深刻的关注。和平利用核能与防扩散对立的焦点是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拥护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②滕建群:《和平利用核能与防扩散的困境与出路》,《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6 期,第67 页。由于和平利用核技术同样依赖发展核武器的材料、设施和知识,和平利用原子能承诺给核扩散造成了长期影响。③Robert L.Brown, Jeffrey M.Kaplow, “Talking Peace, Making Weapons: IAEA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8, No.3, 2014, p.403.现有的国际防扩散体系无法有效对这种通过民用核能项目逐渐积累军民两用核技术的现象进行管控。日本就是以这种合法的形式获得了“核门槛”能力。④赵通:《中国与国际核秩序的演化》,《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 期,第141 页。冷战以来的国际防扩散机制虽然明确了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但在监督保障与和平利用核能环节容易受到核合作双方的限制,难以完全核查。
第三,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之间存在双重认识,难以达成共识,给核扩散研究增添了阻力。核扩散的动因范式认为,核武器是国家安全的一种手段,但核武器给国际安全带来了复杂影响。诚如戈尔巴乔夫所言,“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核武器不再是实现安全的手段。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核武器使我们的安全越来越不确定。”⑤George P.Shultz, William J.Perry, Henry A.Kissinger, Sam Nunn, “Toward a Nuclear-Free World,”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15, 2008.不仅如此,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扩散给国际安全增添了不确定性。虽然恐怖势力目前尚难以直接用核武器进行核攻击,但其在全球的核扩散活动与其破坏核设施、利用脏弹等进行攻击的可能已经构成现实威胁。⑥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主编:《应对核恐怖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 页。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核扩散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国家、地区与国际安全,形成了核扩散破坏安全的共识。但在防核扩散过程中,双重标准和选择性扩散的做法反而增加了国际安全的不确定性。
最后,核扩散研究的文献资料有待进一步丰富。早期核扩散研究主要利用美国的解密档案,但相关档案的解密状况并不理想。⑦陈波:《研究核问题的资料宝库——美国国家安全档案“核历史”电子资源评介》,《军事历史研究》2018年第1 期,第116—124 页;侯锐:《导弹时代的核武器与政治1955—1968——互联网上研究美国核历史的重要档案集》,《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5 期,第310—312 页。由于核历史的敏感性与解密文件的有限性,这就意味着核扩散研究难免受到资料限制存在可靠性与客观性问题。近年来,核扩散研究得益于核安全研究的复兴,随着新档案的解密,学者们开始研究诸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演变,以及中小国家决定是否发展核武器的历史决策等重要课题。①Scott D.Sagan, “Two Renaissances in Nuclear Security Studies,” H-Diplo/ISSF Forum, No.2, 2014,p.2.尽管如此,核扩散研究仍缺乏多边或多国史料的研究成果,史料的挖掘与解读同核军控理论的发展存在差距。
六、总结
核扩散是当代国际政治与安全的核心议题之一。自冷战以来,虽然建立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达成了防核扩散共识,但由于非法核合作、双重标准、超级大国核武器现代化和核扩散问题政治化等现象的存在,核扩散仍难以有效解决。因此,核扩散问题成为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通过分析核扩散研究的理论范式,梳理核扩散的动因、逻辑、论辩与应对措施,有助于认识核扩散问题的缘起、核扩散的市场与战略逻辑演变、学界争论和应对措施。这些研究范式表现了核扩散问题的受关注度和跨学科性,然而却难以解决核扩散研究的去政治化,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扩散复杂矛盾,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中核武器的双重认识,以及研究资料局限性的问题。
就目前的核扩散局势来看,各国的防核扩散政策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仍难以解决核扩散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核扩散问题在未来还会持续存在。事实证明,要克服核扩散研究中存在的安全问题政治化倾向,解决核能需求与核扩散的矛盾,需要构建良好的国家发展与国际合作环境,不断探索符合时代发展的核扩散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