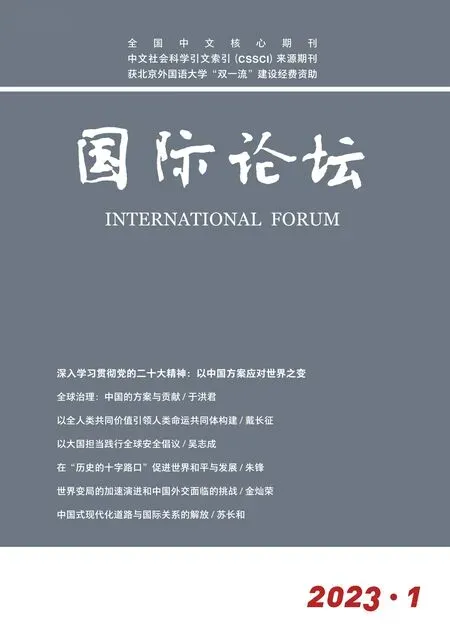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中国方案应对世界之变
于洪君 戴长征 吴志成 朱 锋 金灿荣 苏长和
全球治理:中国的方案与贡献
于洪君
当今世界正处于变乱交织的动荡期。力量对比持续改变和战略格局深刻重组,引发的矛盾与冲突此起彼伏;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重构和全球安全格局重塑,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相互叠加;人类社会生存环境恶化与科技革命在某些国家无序发展,使国际社会愈加困惑茫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2 页。中国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适时提出中国建议和方案,为人类的和平发展贡献了极为宝贵的智慧和力量。
一、中国全球治理观和政策主张极具现实性和建设性
国际社会需要全球治理,必须进行全球治理,首先是因为当今世界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拥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选择不同发展道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面对不同治理方式的各国人民,都是“地球村”村民,都处于历史与现实彼此交汇的同一时空。“各国互相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 页。这是全球治理需要共同参与、需要持续推进的历史前提和客观基础。
全球治理涉及政治、经济、贸易、金融、社会、人文、科技、环境、卫生、安全等人类生活所有领域,涉及主权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在各个领域的行为规则和规范、处理相互关系的原则与准则、约束失范行为并纠偏止损的各种体制与机制。由于各国的利益和立场不同,判断事务的是非标准不同,参与全球治理的出发点不同,国际上有关全球治理的政策主张往往大相径庭。其结果是,人类生活各领域的治理要么显著缺失,要么严重滞后,要么失之偏颇,要么扭曲异化。全球治理赤字长期存在,世界和平与发展深受其累。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常谈论全球治理,目的是要维护他们主导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世界安全框架,维护旧的世界格局遗留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前几年,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顾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悍然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一系列全球治理机构,并将贸易战强加给国际社会,首先针对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极大地破坏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
目前的拜登政府联手西方各国,将经济制裁、“长臂管辖”推向极端,并以经贸、科技、人文、金融等领域“脱钩”方式,切割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就干扰全球治理、阻遏全球化进程而言,拜登政府比其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中国作为特别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始终以建设性立场和态度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大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调整重塑,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为消除全球治理赤字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宝贵贡献。
二、全球治理目的是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
全球治理千头万绪,各种方案蔚为大观,但核心问题只有一个,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合作还是要对立,要开放还是要封闭,要互利共赢还是要以邻为壑”。①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7月26日,第2 版。全球治理的方向和目标,就是“更完善、更符合世界生产力发展要求、更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②《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人民日报》2013年3月28日,第1 版。具体到经济治理,他明确指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至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如何对待全球治理,他郑重表示:“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③习近平:《携手合作 共同发展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28日,第2 版。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参与全球治理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争取建立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紧密相关。因此,他对二十国集团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明显作用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采取的“改革”措施给予充分肯定,指出“这是朝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步伐”。①《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人民日报》2013年3月28日,第1 版。同时,他进一步提出:适应国际力量对比新变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要“体现各方关切和诉求,更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②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第2 版。“国际经济规则需要不断革故鼎新,以适应全球增长格局新变化,让责任和能力相匹配。”“要共同致力于提高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顺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的历史趋势。”③习近平:《共建伙伴关系 共创美好未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7月10日,第3 版。
基于上述理念和构想,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东南亚,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这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联动发展、融合发展、互利发展、共赢发展的意志体现,也是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华民族为国际社会提供的一件公共产品,是中国为全球治理健康发展做出的最宝贵的实际贡献。
三、国际组织应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2016年7月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在中国杭州召开时,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际社会遭遇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二十国集团国家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④习近平:《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人民日报》2016年9月5日,第3 版。
这是中方首次对二十国集团提出具有很强操作性的政策建议,目的是要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建议二十国集团与时俱进,发挥引领作用;知行合一,采取务实行动;共建共享,打造合作平台;同舟共济,发扬伙伴精神。他主张二十国集团根据世界经济需要,从危机应对转向长效治理,将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提高能效、反腐败等诸多领域的行动计划落到实处。他主张二十国集团由清谈馆变成行动队,充分倾听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使二十国集团工作更具包容性,更好回应各国人民诉求。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73—474 页。
四、推动全球治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联
中国领导人利用多边机制向国际社会提出中国理念、中国思路、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贡献,范例甚多。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就是一个经典例证。
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精辟地指出,全球经济领域动能不足、治理滞后、发展失衡“三大难题”,各国当以“四个坚持”、“四个打造”回应人们的困惑和迷茫,这就是: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他强调:“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紧迫性越来越突出,国际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全球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才能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保障。”②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第3 版。
中国积极参与并全力引领全球治理,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和外交实践紧密相关。2018年3月,习近平连任中国国家主席,他再一次向全世界庄严承诺:“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③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第2 版。这时,他已准确地预见到,“未来10年,将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全球治理“关乎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关乎全世界繁荣稳定”。④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7月26日,第2 版。
开展全球治理并进行治理体系改革,必须有广泛认可和普遍遵循的共同原则。为此,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但国际上某些势力,特别是西方的政客和媒体,对该主张肆意否定和歪曲。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没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这样做。”“全球治理结构如何完善,应该由各国共同来决定。”①《习近平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人民日报》2015年9月23日,第1 版。他后来还指出:“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 版。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就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③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6月11日,第3 版。
五、开展和完善全球治理应首先从中国周边地区做起
开展全球治理及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要有选择有重点地逐步展开。中国是世界上周边环境最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多年来,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从周边先行起步。”④习近平:《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1月8日,第2 版。
在2022年4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述了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始于亚洲的重要思想,明确地提出了“坚定维护亚洲和平”、“积极推动亚洲合作”、“共同促进亚洲团结”三大主张。他表示:“地区和平稳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个国家的施舍,而是地区国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他建议亚太国家“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奉行睦邻友好政策,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的泛亚铁路中老段已经通车,中国与地区国家融合发展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生效,习近平总书记主张以此为契机,“推动亚洲形成更加开放的大市场,促进亚洲共赢合作迈出新步伐”,“用对话合作取代零和博弈,用开放包容取代封闭排他,用交流互鉴取代唯我独尊”,“共走和平发展大道,共谋合作共赢大计,共创团结进步的亚洲大家庭”。⑤《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强调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各国要坚定信心 同心合力 和衷共济 合作开创未来》,《人民日报》2022年4月22日,第2 版。
六、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是全球治理的新动力
中国主张全球治理应始于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但绝对不是仅限于此。在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全球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安全格局日益复杂的新情况,向全球提出了新的安全倡议,内含许多新的思想和主张,令世界耳目一新。
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安全倡议是,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提出:“我们必须复苏经济,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并就此提出了新的全球发展倡议,“一是坚持发展优先。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三是坚持普惠包容。四是坚持创新驱动。五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是坚持行动导向。”①《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第1 版。他主张以全球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为切入点,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全球发展倡议与新全球安全倡议密切联系,相互统一,将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持续推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愈发严峻。在不久前闭幕的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2 页。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做出的不懈努力,中华民族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的巨大贡献,必将得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关注、认可和支持。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本文系中宣部“四个一批”暨文化名家人才资助项目“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以及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中国之治’及其国际传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戴长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世界各国应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共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有的全球视野和世界主义胸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和平,为人类谋大同的崇高价值追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产生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不仅表达了中国同世界的相处之道,也提供了对于各类全球性矛盾与问题乃至全球性危机的破解之道。上述思想不仅仅是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中国处理同他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也应当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共享的发展与交往理念,成为各国之间交流合作的“通用规则”。
“全人类共同价值”于2015年首次提出。在当年九月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并同时强调“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需努力”,为此,就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①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53—254 页。因此,这一理念自从提出伊始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诉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其方向引领。从学理角度来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构筑均势、联盟或国家集团,不是构造集体安全体系,不是建立正式的国际组织或制度,也不是创建所谓的“世界政府”或超国家权威,而是在对国家主权原则给予充分尊重的基础上,由各国自愿维系、以各国间的共识为基础的一种稳定状态。因此,无论是以意图不确定和安全困境为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认为唯有权力平衡方能维系国家间和平的现实主义,还是以个体的有限理性为假定,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国际制度克服和规避各类集体行动障碍,从而实现合作并因此共同获利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乃至强调国际关系可以从国际社会发展到世界社会,并最终将国家主权转移到全球层次上,从而使国家边界逐渐消融并最终形成“世界国家”的建构主义理论,都无法触及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内涵。
同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主流概念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命题同中国传统思想精华相结合的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类思维”特点。这种“类思维”是对于传统的将物看作是“现成存在者”,并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和无矛盾性等特性的“物种思维”的超越。它强调人能够超越物种的区别和界限,从而与其他人和其他物建立起本质的一体性关系,并且这种一体性关系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实践活动中通过人们的自由和自觉的创造性活动而人为建立起来的。①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邓纯东主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17—18 页。这样,“类思维”就把人的个性和社会性统一起来,强调在一种一体性关系中尊重个人的独立性并使其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强调在一体性关系中包含着个性、差异性与多样性。从中国传统思想角度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和合共生”、“天下为公”、“海纳百川”、“天人合一”等思想精髓。②张静、马超:《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超越》,《学术论坛》2017年第4 期,第152 页。中华文化自古崇尚和谐,并将建立“大同世界”作为最高的目标。按照儒家思想,“天下大同”是同“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思想建立在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认识基础上,建立在对人类应当如何生存发展的人文主义关怀基础上,也建立在对人的生存价值充分尊重和全面保护基础上。③孙聚友:《儒家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邓纯东主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第9 页。按照儒家的设想,“大同”追求的是整个天下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在一个大同社会当中,政治上要求选贤任能,经济上要求共同发展,人与人之间形成和睦相处的关系。这种对于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形态的追求,显然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致的。④孙聚友:《儒家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邓纯东主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第10页。因此,就可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作是由国家组成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不存在“共同的主人”,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这个共同体的成员面临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义务、共同的责任,因此需要共同努力以到达理想的彼岸——进入全人类自然而又必然的历史进程。①张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9年,第113 页。
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关注各国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挑战与共同命运,因而同全人类共同价值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人类的普遍追求与共同目标,也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处在命运共同体当中的各个国家乃至个人之间相处和交往的基本行为准则。在当前的世界政治中,各类风险和挑战层出不穷,新问题同旧问题相互交织,经济发展失衡、气候变化、信息安全、恐怖主义、传染病乃至地区冲突与战争等,都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各国都迫切需要找到对于这些风险和挑战的应对之道。正是在各种风险与挑战叠加的背景之下,党中央提出了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论断。这一“大变局”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最新表现形式,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和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结果。②李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辩证法审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 期,第33 页。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表现是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对比出现了“东升西降”的趋势,即西方世界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崛起。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各种矛盾——如所有权高度集中、贫富差距加大、民粹主义盛行、社会冲突不断等——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西方国家民众对于自身政治制度的不满和质疑日益强烈,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正在减退。与此同时,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出现了严重裂变,主要表现则包括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正在被逐渐浮现的两极或多级格局所取代,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愈加突出,全球治理赤字空前扩大,二战后建立的各类国际规则与国际制度亟需改革等。③贾文山、江灏锋:《千年视野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路径》,《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7 期,第24—25 页。
当代国际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维系国家间良好关系的各类规范出现了问题,或者说是支撑当代国际秩序的核心价值出现了问题。当代国际关系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片面地将自身所奉行的价值观包装为“普世主义”价值,并极力在全世界推广。事实上,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依据的,立足于唯心主义世界观,信奉个人主义价值论。这种“普世价值”忽视了阶级、民族、国家和时空等客观因素,单纯强调抽象的“人性”,从而使文化、民族、种族、信仰和阶级的差异消弭难见。①李永胜、张玉荣:《论全人类共同价值对“普世价值”的超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 期,第2 页。西方国家将自身所理解的民主、人权、公平等作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刻意忽视不同国家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并以此作为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侵犯其他国家利益的工具。在虚假的所谓“普世价值”基础上,西方国家致力于构筑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这一秩序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方世界对于国际政治的主导地位上,以支持自由贸易、促进国际资本流动、传播民主、保护人权等为核心。它促使西方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所谓的“多元型安全共同体”,并且声称解决了妨碍各国在面对共同威胁时采取一致行动的集体行动问题。②David A.Lake, Lisa L.Martin and Thomas Risse,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Order: Reflection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5, No.2, 2021, p.226.但是,随着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这一秩序的权威和合法性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争议。这些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中,国际权威将决策权集中于少数强大国家官员手中,而这些官员则可以利用各类国际制度来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第二,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强调将普遍性自由观念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从而可以颠覆主权国家的决策。③Tanja A.Borzel and Michael Zurn, “Contestation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Liberal Multilateralism to Postnational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5, No.2, 2021, p.287.
因此,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情景就是西方国家借保护人权、促进民主等名义,遂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实。一些西方学者也指出,自由主义霸权国家号称要在世界上保护各国公民的人权和传播民主,但其代价则是无休止的战争。自由主义霸权国发动的战争增加了国际体系中冲突的数量,导致了体系的不稳定。这些武装冲突通常会失败,有时候甚至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其代价则是牺牲了自由主义霸权国声称要保护的那些国家。④John J.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necticut: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54.可见,自由主义霸权国尽管声称要在国际上促进民主和保护人权,然而他们以“民主”、“人权”为名义所进行的干涉,反而侵犯了那些他们声称要保护的国家的公民的人权,使那些国家陷入长期动荡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讲,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挫败型”的秩序,其内在运行逻辑就包含了导致这一秩序必然瓦解的因素。这是因为自由主义霸权国的对外干涉行动会导致国际体系的不稳定,削弱这一秩序的合法性与道义基础,进而,也同时会导致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对于自由主义霸权国的抵制与反对,最终导致这一秩序的瓦解。①赵洋:《自由国际秩序的转型与混合型秩序的兴起》,《国际论坛》2021年第5 期,第8—12 页。
同西方国家致力于构筑以所谓“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进而以此作为谋求自身私利的工具不同,中国所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普遍性与包容性,是人类自身的价值共识发展的结果。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的理想愿望与共同的命运,因而超越了国家民族、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于一些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的认同。②吴志成:《深刻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丰富内涵》,《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5 期,第12 页。客观而言,当今世界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地区冲突、贫富差距、专制暴政等问题都是长期存在并困扰世界各国发展与进步的重大问题。因而,全人类共同价值代表了各国人民对于更加美好的生活、更加和谐国际关系的普遍愿望与诉求。事实上,早在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中,就确立了七项全人类的“共同基本价值”,包括自由、平等、团结、包容、尊重所有人权、尊重自然和分担责任。③李东燕:《全球治理——行为体、机制与议题》,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第37—38 页。这些价值的提出,表明联合国会员国已经在多年以来的互动中形成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同联合国所倡导的“共同基本价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反映了生活在一个“不完美”世界中的各国人民对于更加美好未来的向往与追求,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与愿望,也指明了各国政府未来的努力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剧”,④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0 页。但同时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也是不可阻挡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正反映了在面对诸多风险与挑战的当下,世界形势将会向着人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的大趋势。当然,要实现各国人民所期望的未来愿景,还需要各国共同付出努力,共同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做到平等协商、开放包容、同舟共济、坚守正义,就要顺应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求,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⑤《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338—340 页。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将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放在首位,并以此作为参照,用以指导本国的对外政策和行为。
以大国担当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重大课题“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8VZL017)的阶段性成果。
吴志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0 页。“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2 页。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精辟分析了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国际安全形势,明确了新时代中国促进全球安全治理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为世界各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一、安全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
安全问题是事关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对于人类来说,安全是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诉求和愿望,对生命财产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的安全需求是人类的本能欲望。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安全和稳定是国家发展的首要前提,关乎各国核心利益。“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2 页。如果将安全需要置于自然界和人的生存、社会发展中系统考察,安全无疑是人类在生存奋斗中积累和凝聚的普遍性观念,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在一定意义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人类努力实现和满足安全需求、推动社会在相对安稳中前行发展的历史。现代安全的意义还体现着人类的进步精神和文明程度,人类已经越来越把安全看作文明进步的基础。正是这种安全感和安全观念促使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向前发展,不断追求安宁、稳定与和平,努力消除社会演进中的各种冲突、混乱与痛苦。所以,安全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它不仅源于人类自身的基本需求,也成为社会的终极需要和根本利益。从“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的中国古训和近代中国外敌入侵、军阀混战不断导致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到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深陷战火和内乱的悲惨景象,再到近年来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和种族冲突带来的巨大危害和当下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给各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无不深刻地启示我们,安全和稳定是人类生存和国家发展的首要前提。没有和平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保障,任何个人、群体和国家都将一事无成,人类的任何美好蓝图也都将成为空中楼阁。①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维护国家安全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学习时报》2020年6月1日,第1 版。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和国际相互依赖的增强,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时空领域范围更加宽广,各种因素的交织影响更加错综复杂。因此,现代安全指涉对象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更加凸显,我们分析和思考现代安全问题,谋划和促进安全治理,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家行为体层面,而应该站在全人类共同安全和全球普遍安全的高度,将安全放在所有人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延伸到个体、群体、民族和整个人类,坚持个人安全与集体安全、本国安全与他国安全、国家安全与全人类共同安全的有机统一,不让任何个人脱离,不让任何国家掉队,致力于实现各人群、各民族、各国家的共同安全。实质上,真正的安全只有通过人民和集体才能获得,国家安全最终也只有在服务和惠及到具体的个人时才显得更有价值和实际意义。在现代安全体系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就必须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人民安全是国家最基本最核心的安全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以民为安危”,“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本身也说明了这个道理。一方面,人民是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全球安全的根本力量源泉。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根基都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底气也在人民。失去了人民的依靠,没有了人民的支持,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另一方面,让民众享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生存生活环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全球安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维护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让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保障,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保护,各种尊严和价值受到尊重,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通衢大道。实现人类普遍安全也必须通过维护各国人民的安全来体现,通过实现各个国家和群体的安全稳定来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前提。①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4月22日,第2 版。
二、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与共、安危紧连的安全共同体,不仅契合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天下一家、和合共生的理念,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安全的普遍愿望。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当今世界,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各国人民安危与共、唇齿相依,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可以说,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复杂精巧、有机一体的机器,拆掉一个零部件就会使整个机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被拆的人会受损,拆的人也会受损。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人类历史前进大势不可逆转的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6 页。面对现实世界中暴力与冲突的蔓延,面对一些国家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的猖獗,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持续肆虐,面对日益复杂化、综合化的安全威胁,没有哪个国家和个人能够独善其身。历史和现实反复昭示我们,世界上既不存在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也不存在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一国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之上,别国面临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人类冲出迷雾走向光明的最强大力量就是团结起来、同心合力,最有效方法就是和衷共济、合作应对。然而,令人忧虑的是,一些国家罔顾人类共同安全利益,固守陈旧的冷战思维和过时的零和博弈观念,谋求本国的所谓“绝对安全”,让他国承担地缘对抗的代价和伤害,甚至热衷于拉帮结派,胁迫别国选边站队,搞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蓄意煽动分裂对抗,制造集团对峙,加剧全球安全赤字。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威胁着全球安全与和平,动摇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基,也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人类实现普遍安全、人人享有和平安宁的美好愿望依然任重道远的严重警示。
处于这样一个风险挑战叠加、动荡变革交织的世界,面对全球安全治理的复杂严峻态势,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安全的期盼更加殷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诸多国际场合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全球安全治理的新理念新倡议。在2014年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①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33 页。在2017年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强调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②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0 页。在2017年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各国共同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号召国际社会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③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9月27日,第2 版。在2020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维护安全和稳定,构建安全共同体。④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80 页。特别是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为了促进世界安危与共,“我们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①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4月22日,第2 版。这一重大倡议顺应当今时代发展潮流,符合各国人民对加强全球安全合作的普遍期待,明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和博大天下情怀,为应对全球安全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实现世界长治久安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担当大国责任
全球安全倡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国际安全领域的重要应用成果,是对西方地缘政治安全理论的扬弃与超越。②王毅:《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守护世界和平安宁》,《人民日报》2022年4月24日,第6 版。这一倡议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指引,以相互尊重为根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指明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因此,推进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要求国际社会以合作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以行动加强全球安全治理,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特别是世界大国更需要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展现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中国既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者,也是践行这一重大倡议、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行动派。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坚守负责任大国的立场和态度,努力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遏制和化解冲突与暴力,成为当今世界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坚强支柱。
坚定不移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和平基因,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深知和平安宁的珍贵,尤其希望同世界各国一道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载入宪法的国家,也是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 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和平发展壮大了世界和平力量,不仅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更加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承诺坚定不移,而且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稳定基础和战略保障。
坚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这一安全观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致力实现持久安全,捍卫全球普遍安全;弘扬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的安全挑战,以团结精神适应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共同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
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地位和核心作用。中国始终忠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以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未经联合国授权、与联合国宪章精神相违背的家法帮规,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根本遵循。中国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出兵国,已经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力量,为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担负着重要责任。积极参与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加强全球集体安全机制建设,使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维护机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在全球范围内破坏他国社会稳定,散播暴力与冲突的种子,助长民族矛盾和极端主义,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对此,中国坚决反对霸权强权、摒弃冷战思维的立场旗帜鲜明,不仅宣示自己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对外扩张,而且坚定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边,不断壮大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干涉的力量;反对在处理复杂安全问题时采取非敌即友、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做法,强调大国竞争不是时代主题,零和博弈不是正确选择,挑起冷战、阵营对抗的老路行不通,为本国地缘战略目的分裂世界的做法更不可取;坚决摒弃独享安全、绝对安全的想法,为缓解国际冲突争端劝和促谈,为防止热点局势升级降温止战,努力让和平安全的阳光普照天下,让人类远离战火硝烟的噩梦。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朱 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0 页。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无疑是二战结束77年以来最严峻和最为动荡的。疫情、气候灾变、地缘政治冲突、大国战略竞争等不安全因素使得世界动荡不安;放眼当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虽未变,但问题和路径却在变化;回溯历史,国际权力结构的“东升西降”虽不可逆转,但其时间和节奏却在改变。
世界经济有可能走向新的萧条时期。推动萧条回归的背后因素,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或者金融危机,而是经济与非经济、金融与非金融、地缘政治与非地缘政治、地缘战略与非地缘战略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受俄乌冲突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2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6%,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战争拖累全球复苏》,2022年4月,第1 页;IMF: “IMF Managing Director Kristalina Georgieva’s Remarks-Tackling Food Insecurity: The Challenges and Call to Action,” April 19, 2022,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2/04/19/imf-md-kristalina-georgievaremarks-tackling-food-insecurity-the-challenges-and-call-to-action.。较2021年下降2.5 个百分点,较1月预测下调0.8 个百分点,其中143 个经济体增长预期出现下调。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战争拖累全球复苏》,2022年4月,第6—8 页。同样,世界银行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也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4.1%下调至2.9%。④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e 2022, p.xv.在军事层面,自2022年初俄乌冲突以来,欧洲大国竞相提升军费预算。德国政府表态未来该国军费开支将提升到GDP 占比2%以上,并紧急追加1000 亿欧元的军费,⑤“Germany Must Meet NATO’s 2% Spending Target over Long Term, Defence Minister Says, ” the Reuters, September 12,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germany-must-meet-natos-2-spendingtarget-over-long-term-defence-minister-2022-09-12/.而整个2021年德国军费开支只不过560 亿美元;⑥SIPRI,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Passes $2 Trillion for First Time,” April 22, 2022, https://www.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2022/world-military-expenditure-passes-2-trillion-first-time.法国将2023 财年国防预算增加到439 亿欧元,与2022年相比增加7.4%,并计划未来每年增加30 亿欧元军费,直至年度军费达到500 亿欧元;①Elise Vincent, “War in Ukraine: France Adds €3 Billion to 2023 Defense Budget,” Le monde, October 11, 2022, https://www.lemonde.fr/en/economy/article/2022/10/11/war-in-ukraine-france-adds-3-billion-to-its-2023-defense-budget_5999938_19.html.英国宣布到2030年,英国的军费支出将比目前水平增加一倍,达到1000 亿英镑。②“UK Defence Spending to Double to £100bn by 2030, Says Minister,” The Guardian, September 25,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22/sep/25/uk-defence-spending-to-double-to-100m-by-2030-says-minister.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变局、动乱结合的效应,确实是二战结束至今我们从未见过的。
目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效应正在不断深化,大国关系在新的百年变局中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下四个方面:
第一,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往往被认为既有冲突又有竞争,然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冲突更重要,还是合作更重要?随着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的合作性不断成长,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的本质已经开始远离所谓的大国对抗。但如今,过去经常定义大国关系的最本质特征又在重新回归。那么,今天的大国对抗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国对抗是否意味着“冷战”也再度回归?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所谓美国标准下对中国的战略应对等,其实质就是美国试图把“新冷战”带到地区和全球产业链之中,另外,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战、贸易战、市场战,包括数字战、媒体舆论战都在不断深化。大国关系重回战略对抗,大国关系中地缘政治因素在增强,国际局势的发展令人担忧。
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变化是大国关系是否会形成新的阵营对抗。二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变化就是围绕着两个超级大国形成的地缘政治分裂以及意识形态的全面冲突而展开。美国试图挑起“新冷战”,东西方之间是否会再次出现地缘战略的对立和两分?今天世界政治又走到了会由大国对抗引发新的阵营对抗的焦虑时刻。
第三,相互依存时代下大国竞争的变化。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相互依存可以弱化国家间的安全竞争,促进社会政治的沟通和交往,有效缓解大国关系间传统的无休止的权力、利益和财富冲突。在后冷战时代的31年中,中美之间的经济社会相互依存度是空前的,中美两国不仅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更是互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伙伴。尽管中美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如此广泛和深入,但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华打压政策不断延续。美国定义下的所谓“战略对抗”,就是重新把安全置于相互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合作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相互依存时代的大国竞争正在展示新面孔、新特征、新走势,从理论以及实证研究的角度看,高度相互依存时代下的大国对抗会出现什么变化?历史在回归,今天美国对华战略打压说明了世界政治正在重回现实主义时代,而传统的新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假设则正在崩溃。
第四,意识形态的分裂和对立正在重新成为大国对抗的“加速器”。意识形态是各国国内政治的价值选择,代表着政治精英和民众对政治社会发展制度的优先选项。全球化时代下,国际化、信息化、社会化使各国民众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这种进程推动了各国人民之间的观念沟通,形成了价值依赖,也使彼此之间对生产生活方式的相互认识和理解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拜登政府从上台之初,就强调今天的国际竞争主要是美西方为代表的民主阵营与中俄为代表的所谓“专制国家”之间的竞争,属于国家阵营之间的对抗。这说明,竞争性、冲突性的国内政治运行架构和机制依然是大国关系最具有决定性的变量,意识形态冲突正在重现。
乌克兰危机成为了美西方“设局、布局、谋局”的外交、政治和军事抓手。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让世界的权力再分配结构进入了单极时代,这就使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仅维持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在亚太地区庞大的双边同盟体系,而且依仗美元霸权和美国全球军事霸权,输出美国式的意识形态,在全球推行外交、政治和军事干涉主义。美西方不顾及俄罗斯基本地缘战略安全忧虑,在乌克兰危机升级过程中更是企图迫使欧洲彻底倒向美国,让美国的地缘政治体系更加坚实,这一战略意图是乌克兰危机持续升级背后的最直接原因。在美国单极霸权的主导下,欧洲已经难以重回19世纪的“大国协调”,反而难以遏制地陷入地缘战略上的大国对抗,乌克兰充其量不过是欧洲地缘战略对抗棋局上的一枚“棋子”。中国坚决反对国家间以兵戎相见,但如果缺乏有效权力制衡的单极体系再延续下去,世界将会难以避免地出现更多的大国冲突和大国对抗。多极化进程不可避免,但世界政治究竟需要为结束单极体系付出多大代价?俄乌冲突使得这个问题前所未有地突显起来。
如今,乌克兰危机在冷战结束31年之后再度引发大国对抗,继续“拱火”俄乌冲突不仅伤及欧洲的经济和民生,更是成为世界能源危机、粮食危机、通胀危机背后重要的刺激性因素。尤为重要的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机制正面临脆裂的风险。对于如何协调应对全球疫情、就俄乌冲突尽快形成妥协性和一致的解决方案,以及如何协调应对俄乌冲突后国际能源危机等严峻挑战,联合国几乎束手无策。自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美西方不仅没有反思乌克兰危机为何持续升级以及他们所应承担的责任,反而借机发难,试图破坏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机制,从而强化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运作需要大国合作,然而在今天,联合国却成为大国冲突和较量的新战场。美西方国家显然在利用欧洲和东亚局势试图扩大核武装的国家范围,以进一步提升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的战略力量。
当前新形势的特点是大国战略竞争和大国战略对抗又重新回归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现实主义回归”时刻重新降临。如今乌克兰冲突不仅使冷战的铁幕可能在欧洲再度降临,最重要的是,美国对中国长期的战略打压甚至遏制,今后可能更甚。美西方国家从霸权地位和单极霸权利益出发,在科技、市场开放和产业链自由竞争等领域对中国设置障碍,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挑衅行径也给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带来了打击。
中美关系的质变将是未来中国大国崛起长期面临的最为沉重的国际压力和挑战。中美在舆论战线和外交战线展开了唇枪舌剑,一个基本事实是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至少还要持续十到二十年。如何应对中美关系的变化和美国对华对抗政策的长期化,是中国需要面对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了强大的对手,其对华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新的调整期。虽然90年代上半期美国也曾有人提出要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但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选择让美国重新意识到美中合作的战略价值。然而,随着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朝野的对华心态、对华认知和对华政策都在变化。从全力维护美国自身霸权地位和“美国例外论”主导的政策心态出发,奥巴马政府末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就开始进入实质性调整阶段。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政府更是把中国定义成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威胁”,拜登政府上台后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当前,美国试图全面发动对华2.0 版的“冷战”。如果说1.0版的冷战是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完全的对抗和阵营化,那么2.0 版“冷战”的核心问题是地缘经济,包括地缘科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美国要进一步推进“去中国化”。不管“冷战”1.0 版和2.0 版有什么不同,美国试图成为赢家的基本战略规划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冷战”的2.0 版意味着美国试图在中长期的时间内解决他们心目中所谓的“中国问题”。
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22年国防战略报告》称,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全面且严峻的挑战,强调与盟友密切合作是美国家安全的基础,需要与盟友集体应对挑战。①U.S.Department of Defens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ctober 27,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ational-Defense-Strategy/.近期美西方的表现说明,在大变局中美西方的“中心主义”依然是结构性现实。美西方在世界政治中的权力优势不仅不能被忽视,而且是中美今后长期战略较量必须冷静面对的客观现实。以未来趋势而言,中美的战略较量在时间上具有长期化的特点,中美战略较量关系着世界政治未来发展进程。
面对当前国际形势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动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及时、敏锐地提醒全党同志,“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0 页。当前国际局势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效应正在不断深化。“世界之变”,是当前新冠疫情、气候灾变、地缘政治对抗、大国冲突四大因素叠加,未来3 至5年的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正处于二战结束77年来前所未有的动荡期和转型期;“时代之变”,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稳定、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和希望没有变,但和平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保障可持续和平的路径正在变;“历史之变”,是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权力、财富和利益结构的“东升西降”不会变,但面临的挑战、问题和国际权力结构合理化的时间表正在变。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党的二十大报告科学、准确地向世界展示了坚定有力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二十大报告不仅在对外关系领域揭示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人民中心”治国基础,更重要的是,报告强调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将坚持“发展优先”中心原则,全面推动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以发展为主、壮大中国的实力和进步历程、走稳走实走好中国自己道路的意志和决心,正是面对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动荡局面应该执着坚持的道路选择。作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和合作、包容、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的稳定、强大和可持续增长,不仅将增强世界和平与发展对中国的依赖,更将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变革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引领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呼吁世界各国人民要加强合作和团结,超越不同意识形态的狭隘与保守,真正站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为世界进步谋出路,为人类利益促发展,为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增合作。这不仅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宗旨和原则,更是一个崛起的中国为世界带来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报告中再度强调,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进程,并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例如,在“一带一路”建设上,报告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我国成为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9 页。这是世界各国都无法忽视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真实魅力。
中国历来反对某些国家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干涉和插手别国内部事务,把自身小圈子的利益和诉求强加给世界各国。为此,近20年来,中国外交始终强调支持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机制,通过开放、平等与公正的多边主义的行动原则,在各种国际共同议题上实现各国共同参与、集体行动的共商共建共享机制。我国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提倡综合、均衡、合作与可持续的发展和安全理念与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2 页。就是要反对在意识形态小圈子中“拉帮结伙”、在国际事务中制造阵营分裂的做法,这种做法与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背道而驰。这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维护中国利益和世界进步,中国必须坚定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原因所在。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指引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在未来迈上一个崭新台阶。实现民族复兴、促进世界进步不仅是中国对外工作的宗旨,更将是引领世界更好地推动和平与发展历史进程不可或缺的“中国声音”和“中国力量”。
世界变局的加速演进和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
金灿荣
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总特点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对过去五年,特别是新时代十年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工作做了很好的总结,对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对未来的展望有很强的延续性,尤其是外交部分,报告中提出,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些过去十年陆续提出来的目标要在未来落实到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0 页。大变局在加速演进,体现在很多方面:第一个证据是西方国家内部矛盾上升。尽管当今世界总体格局依旧是“西强东弱”,西方还是目前的主导性力量,但是这个“主导性力量”的内部问题很大——无论是美国、西欧,还是日本,都“乱象丛生”。政治上,美国的两党纷争愈演愈烈;欧洲部分国家,例如英国,政府换届重组频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等等。经济上,美西方发达国家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通胀压力,经济增长乏力,尤其是西欧国家和日本。总的来说,西方的内部问题表现得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突出。另一个证据是从2022年2月份开始爆发的俄乌冲突,严重冲击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的情况,我想用一个中国人更容易理解的角度提一个新说法,即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到了“大争之世”,类比于中国历史,就是周天子的时代结束,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时代到来了。而大争之世,也就意味着挑战要比之前多。从国际层面上看,未来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以下几点:
第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抵制会进一步强化。首先,在2022年10月12日,美国拜登政府发布了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尽管这份报告中大篇幅地叙述了有关俄乌冲突的问题,并把俄罗斯视为“最紧迫”的挑战对象,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该报告中依然把中国定义为美国最主要的挑战对手——认为“中国是唯一既有改变国际秩序意愿,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①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1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2020年10月27日,美国国防部也发布了三份重要的报告:《国防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核态势评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和《导弹防御评估》(Missile Defense Review)。这三份报告更明确地把中国定义为美国军事上的第一对手,而将俄罗斯降为和伊朗一个等级的挑战者。此外,这些报告中还显示了美国降低核门槛并大力发展战术性核武器的战略,其目的是加强对中国的核威慑。其次,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中国的负面态度也在加强,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另一个现实。再次,美国与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的盟友国家之间的战略也会更加针对中国。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把针对中国的“亚太战略”升级为“印太战略”,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的东和南两个方向的围堵更加严密了。我的理解是,“亚太战略”在地理上对于中国是呈“I 型”,功能是阻止中国向东进入太平洋,但是对于中国的南部通过邻国进入印度洋是开放的;而升级成印太战略后,地理上是针对中国的“L 型”,封堵更加严密,而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战略。因此,未来美西方国家和我国的关系会更紧张,我国面临的压力会更大。
第二,中国面临产业链转移的压力。中国现在处在产业升级的爬坡期,往上走每进一步都会遇到美西方更严重的抵制。以芯片产业为例,美国政府如今试图拉拢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半导体制造伙伴组建 “芯片四方联盟”(Chip4),可以说是对华的芯片产业进行了毫不遮掩地全方位围堵,这是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打压的一个缩影。②戚凯、李燕:《拜登对华半导体政策:竞争认知、遏制路径与效果制约》,《国际论坛》2022年第6 期,第76—79 页。另一方面,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因此,美国想在世界产业链中排除中国。前些年,美国尝试把完整的产业链迁移至美国,后来发现不现实;进而尝试把产业链回流到美国的“近邻”,例如墨西哥和其他中南美国家,做“近岸外包”(Near-Shoring),但是发现依旧不现实;拜登政府只能进一步退而求次做“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纳入产业链的国家囊括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盟友,如韩国等。尽管范围在一步步放宽,但目标一直很明确,是要把产业链移出中国。此外,产业方面中国还有一个威胁是处于“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态势,印度、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都想挑战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希望产业能从中国转移过去。总的来说,在二十大报告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就是中国要进行产业升级,不能只在低端产业徘徊。但是从国际态势上来看,要达成这一目标,我们面临的挑战很艰巨。
第三,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接受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最先实现了现代化,而非西方国家中大都没有实现现代化,为数不多的例外是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均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内。因此,现代化的真实情况是,只有占全世界比例很少的人口和地区做到了。而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通常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原则上是不希望更多其他地区实现现代化的。例如2010年奥巴马在澳大利亚电视台的专访中所说的,“如果超十亿的中国居民都过上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的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实现现代化本身很难,人口规模庞大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并不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想看到的,而“中国式现代化”更是遭到抵触。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无不例外的是采取了西方模式,中国采取非西方模式进行现代化会被视为“离经叛道”。因此,未来几年中国推进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部分周边国家会被美国强制要求在支持中国式现代化与否的问题上“选边站队”,而其中部分国家,可能会跟着美国“起舞”,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制造阻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也是上述挑战最激烈的时段。
面对当下及未来的严峻国际形势,我认为中国的应对之道的关键有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要深刻理解“两个确立”,要坚决践行“两个维护”,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保持团结一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大争之世,内部团结的国家胜算比较大。
第二点,内部发展一定要搞好,尤其是经济发展。没有良好的经济发展作为基础,对外博弈就会缺乏底气。
第三点,针对美西方对我国压制增强,我们要做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 页。回避矛盾是找不到出路的,只有敢于且善于斗争才能解决问题。而特别要注意的是对“善于斗争”的理解——我认为做到善于斗争,意味着我们不要一味地“示强”,要刚柔并济,一张一弛,善于把握好平衡。
第四点,在过去中国成功的外交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未来的外交工作。例如,用中国的发展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一步做好“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来做好区域合作,加速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的扩容工作,等等;在外交理念上,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
第五点,在全球治理上,中国未来也要多做工作,多做贡献。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恶化,导致全球治理难度加剧,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进一步凸显,中国在解决这些赤字方面可以多做贡献。例如,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上,中国可以进一步发挥作用。如今气候变化在加速,而美西方国家的立场在后退,中国近些年在这个问题上做得非常好,未来可以多发挥作用。近些年,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一个基础,即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很好。发展新能源产业在经济哲学意义上是一次变革,即人类用工业制造出的能源再反哺工业,创造了新的工业体系,而不是像传统工业化过程那样依靠化石能源。中国的风能、水电能和太阳能等方面的技术进一步提高,既可以为解决全球气候问题做贡献,又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
第六点,我们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高举公平正义的大旗,高举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法大旗。美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的31年里,强调西方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英文“Universal Value”中的“uni”在希腊语中是“单一”的意思,所谓“普世价值”的含义其实是“单一价值”,用一个尺度衡量一切,这在哲学意义上是错误的。中国强调的“共同价值”即“Common Value”,强调各国的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最大公约数,这比“普世价值”要好。
总之,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中国未来规划了很好的前景和蓝图,值得追求。不过走在通向美好前景的路上是很艰辛的,中国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下一个阶段,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进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未来或许会有惊涛骇浪,但我们不能回避矛盾,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认为在外交方面,我们认清楚上述的挑战并做好预期,做好上述提及的几点“应对之道”,中国未来会有更多的外交成果,在处理国际事务上会有更多的成就。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国际关系的解放
苏长和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变革,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选择。世界怎么了?中国怎么办?这都是世人关注的问题。报告第十四部分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题,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中国的回答。再联系二十大报告其他十四个部分,二十大报告给国际关系学者提出很多重要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学术命题,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我想把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结合起来,谈谈二十大报告对我国国际关系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意义。
一个大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总是在回答世界应该是什么、本国乃至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能为这样的世界做什么的过程中形成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主标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二十大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关键内容之一。中国希望的世界是什么?二十大报告指出,是“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2—63 页。那么,怎么实现这样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国的答案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来推动建设五个美好世界。
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重要的特色,也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一般认为这五个特色中最后一个特色,也就是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知识有关。其实这样理解还不是完整的,其他几个特色也都有国际关系理论意义。再仔细思索,这五个特色确实是中国特色,但是放到人类现代化历程和方向上,这五个特色难道不就是好的现代化道路的一般标准吗?也就是说,中国特色和世界一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为什么这么说?过去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现代化道路经验基础上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巧妙地将西方特色现代化道路转化为一般现代化模式,也就是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这样的叙事,这种理论对世界上一些地区现代化道路产生了较大影响,有时有很多误导。从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进步一般规律的学术标准来审视,西方现代化道路有很多弊端。换句话说,按照这条道路,到达不了中国以及全体人类所期待的“五个世界”。在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理论中,这条现代化道路本质属性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只能容纳并固化少数国家少数民族的现代化,维持一个两极分化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条道路对外扩张、侵略、掠夺、殖民,给其他国家和民族生存状态造成系统性的危害,几乎每一个复制这个现代化模式的国家,特别是大国,最终都走向对外侵略扩张道路;这条道路及其生活方式对人类自然环境造成莫大的损害,有人测算,全世界如果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需要消耗四个地球的资源才能维持人类的需求;这条道路个人主义至上、西方中心主义至上,而真正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是人民至上、社会至上、全人类均衡发展至上。今年世界人口达到八十亿,实现五六十亿人口的现代化,再走西方现代化道路模式,显然走不通。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够看清楚建立在西方现代化道路经验基础上的西方主流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无非在用各种概念和理由来掩饰其弊端,对其缺陷采取回避的态度。以国际关系理论为例子,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用霸权稳定论来为西方统治世界辩护,所谓“自由世界秩序观”为其任性、自由地干涉世界其他国家独立提供说辞,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理论本质上是巩固和维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平衡、不平等状态的理论依据,现实主义理论将国际关系庸俗化为追求权力的工具,等等。这套理论一度在世界上影响很大,但是随着各个地区广泛的世界政治自觉运动,人们愈来愈看清了其本质。当人们不再相信所谓“软实力”背后的西方政治理论时,软实力就不再是软实力了。
概而言之,当旧的现代化道路及其塑造的世界体系不能容纳新生生产力和进步力量,尤其是当更多国家探索适合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在平等的规则框架下竞争的时候,这个旧的体系呈现竞争弱势和劣势,甚至采取极端手段封锁、排挤、打压遏制新兴力量,成为世界发展和进步的阻碍力量。这就是当今时代国际关系出现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之所在。
站在这个理论坐标上,就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其世界意义,其特色包含人类现代化的共同特点,具有世界一般意义。由此,中国人民才有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去创造自己的理论体系,去思考世界的前途命运,给世界以新的启蒙。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种好的现代化模式,本质上还是因为这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人类发展只要还停留在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侵略扩张、世界性不平等的体系之内,社会主义作为纠正力量,永远会为历史进步提供动力。这也是社会主义在21世纪必将产生新的更大历史作用之处。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体系下,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全新的思考空间。
如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关怀,就落在追求全人类发展和解放上,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元气和精神气质所在。我个人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印象最深的是其历史和逻辑是从生产开始,到解放结束。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种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通过自身勤奋和智慧解决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实现现代化指标的累积和迭代进步,在此过程中没有向外殖民掠夺,努力与外部世界实现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模式。这个伟大进程的巨大力量及其蕴含的价值之一是“解放”二字。它对全人类的普遍意义在于,一个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奴役体系获得整个民族独立的自由和解放,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结构性、制度性重压下获得发展的自由和解放,世界更多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人类更大群体的自由和解放。在知识创造上从以往西方现代化叙事下挣脱和解放出来,创造新的现代化道路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推动国际关系的解放,正是国际关系理论守正创新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