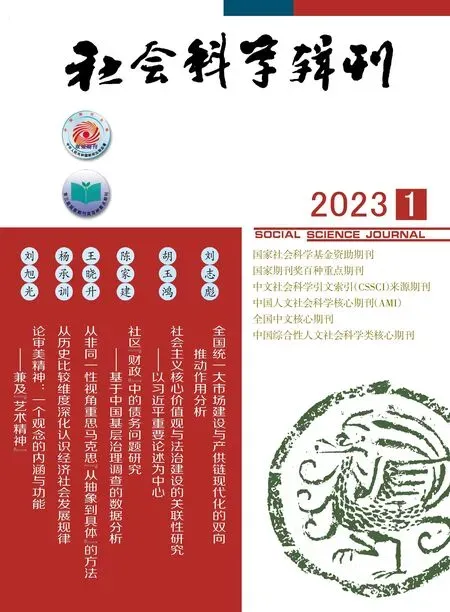李泽厚美学思想的世界贡献
——以“积淀”说为例
黄 一
李泽厚的哲学与美学思想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引起了海外研究者的注意,并且更多的是以一位世界哲学家、美学家而非新儒家或中国美学研究者的身份受到瞩目,这在中国现代哲学美学史上实属罕见。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之下,跨文化交往日益频繁,中国经验作为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异质文化代表,在西方话语中受到广泛的关注。但是在西方理论家的视域中,中国往往是西方的“镜像”,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讨论的出发点与归结点皆指向西方文化自身。简言之,在西方理论中,中国经验更多地以对象或参照系的形式发挥作用,很难真正参与理论话语建构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泽厚在世界美学中的地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笔者查阅的近40年的李泽厚国外研究资料中,“原创性”和“世界性”成为国外研究者对李泽厚思想评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描绘性词语。当今最权威的世界文论选集《诺顿理论与批评选》(NortonAnthologyofTheoryandCriticism)在2008年第二版编辑过程中,将李泽厚作为首位华人理论家编选入集,他也成为文集中四位非西方理论家之一。《诺顿理论与批评选》的编委之一,也是李泽厚的推荐者顾明栋称赞:“李先生的原创性足以使他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世界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之列。”〔1〕在李泽厚众多的著述中,《美学四讲》最受海外研究者的重视,原因在于它是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哲学在美学领域的集中呈现,从美的本质、美的发生到美感、审美经验的呈现,《美学四讲》以体系性的面貌予以呈现,体现了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高度和独特的理论视野。《美学四讲》涉及的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化的经验性材料,令海外研究者耳目一新,同时李泽厚采用的基本思维框架和理论话语又是研究者所熟悉的。李泽厚以西方传统哲学最为常见的本体论思维,统摄了自然美、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及艺术等诸多美学命题,创造了源于本体论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如感性与理性、情本体与工具本体,等等。另一方面,此书备受青睐还缘于它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那个时代是中国现代启蒙的关键时间节点,也是海外研究者认为中国美学真正能与世界美学产生联结甚至对话的时期。正因为如此,《美学四讲》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的代表作备受世界美学的瞩目。《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选录了其代表作《美学四讲》第四章第二节“形式层与原始积淀”,李泽厚从哲学层面回答了艺术起源的问题:“究竟艺术在先还是美感在先?”这个问题的解决路径又与美和美感的来源是一致的。李泽厚创造了“积淀”一词,以此回应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等一系列美学的基本问题,“积淀”说也因此在李泽厚美学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诺顿理论与批评选》对李泽厚美学思想的述评集中于两个方面,充分肯定了他沟通中西方不同文化传统的努力以及对美的本质问题研究的推进:“李泽厚所构建的哲学美学体系以东西方学术传统的汇通为根基”〔2〕,“对美学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实践引入了关于美的本质研究中”〔3〕。这两方面也充分体现在李泽厚的“积淀”理论中。
本文尝试以李泽厚的“积淀”说为例,讨论其美学思想的创新性和世界意义,并提出其原创性的美学思想恰恰是最具中国性的理论话语,彰显了中国作为一种“方法”参与世界美学理论生产的实绩。
一、“作为世界性文论家,而非新儒家”〔4〕
1991年,李泽厚离开中国,在海外多家学术机构任职。1988年,李泽厚“当选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成为20世纪中国继冯友兰之后唯一入选的中国思想家、哲学家”〔5〕。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泽厚的一些代表作被翻译成英语、德语、日语、韩语等在全世界范围传播。最早译成英文的是《美的历程》,1988年出版,英文版的副标题是“关于中国美学的研究”〔6〕。2006年,由李泽厚和简·科威尔(Jane Cauvel)合译的《美学四讲》出版,英文版的副标题为“一个世界视角”〔7〕。2010年,《华夏美学》由夏威夷出版社出版。〔8〕《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的英文版名称是《康德的新研究:一个儒学马克思视角》,于2018年由新加坡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版〔9〕,于2019年由纽约的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10〕2020年,《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在纽约出版。〔11〕
李泽厚的英文研究成果涵盖了专著、博士论文以及期刊论文,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以“李泽厚哲学/美学思想”为主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李泽厚的著述和思想作了整体性的介绍,充分肯定了其原创性美学思想对世界美学的重大贡献。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庄爱莲(Woei Lien Chong)的《历史作为美的实现:李泽厚的审美马克思主义》,作者用“审美马克思主义”〔12〕概括李泽厚的哲学美学思想,并敏锐意识到“历史本体论”是其美学的重要特征:从人类的生存、历史的生成到美与艺术的创造,这些领域的根本目的都是美的创造,不只是经验层面的,还具有本体论的性质。顾昕的《主体性、现代性和中国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比较视野下的李泽厚哲学思想研究》揭示了李泽厚哲学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精神,从1980年代开始,李泽厚关心人类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维度,特别是知识分子道德的、美学的培养。他认为每个个体都是作为整体的世界文明的一份子,中国人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吸纳所有文明中的最强之处。〔13〕二是讨论李泽厚与儒学的现代化。研究不仅将李泽厚所构建的哲学美学思想视为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新发现,而且揭示出他对许多命题的思考,在世界范围内加深了关于人文主义和文化秩序等人类价值的探索。代表性的研究有罗亚娜(Jana S.Rosker)的《李泽厚与现代儒学:一种新全球化的哲学》〔14〕,以及卜松山(Karl-Heinz Pohl)的《“西体中用”:李泽厚关于传统和现代性的思想》。〔15〕这些研究都注意到李泽厚在综合中西传统话语资源的过程中对世界重要哲学美学命题的探索与贡献,以及由此呈现出的理论的原创性。三是着眼于李泽厚学说中的西学资源,将其与李泽厚的某一观点对照研究。比如林琪(Catherine Lynch)的《李泽厚与实用主义》,在与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对比研究中凸显李泽厚“实用理性”说的价值。〔16〕四是将其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代表,出现在汉学家对中国美学重要命题的讨论中,或是将李泽厚所构建的哲学视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重要话语,出现在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讨论中,比如王斑的专著《历史的神圣人物:20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将李泽厚视为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17〕此外,《诺顿理论与批评选》分为26个主题,编者认为李泽厚的思想涉及美学、情感研究、身体研究、文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六个主题〔18〕,这六个主题亦可看作国外研究者讨论李泽厚美学思想的视角。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李泽厚的思想应用范畴之广、影响之大是受到世界思想界广泛认可的。
二、从世界美学眼光看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原创性
要讨论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原创性,需要弄清楚在其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年代里,世界哲学与美学的大体发展状况。20世纪到21世纪初,世界哲学主流形态是盎格鲁—欧洲哲学,它来自17—18世纪西方的两股认识论哲学思潮:英国经验主义和欧陆理性主义。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传统所形成的历史框架中审视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原创性,讨论他在哪些重要的美学问题上进行了新的拓展与丰富。
以霍布斯、洛克、休谟等为代表的经验论作为一种认识论,坚信知识来自感觉经验,通过归纳法获得普遍的知识。与经验论相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相信真理在于理性,知识来源于先天的观念,靠理性的演绎法获得普遍的知识。康德1781年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反思性地“批判”以上两种认识论,讨论认识之所以可能的一切条件与形式,并试图为人的认识划一个界限。在这个框架下,继而提出人具有一种先天的认识形式,它综合了人类经验,使得科学真理具有普遍必然性。1979年,李泽厚出版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在2007年第六版的附录中,他感慨时至今日,“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一传统所提出的有关人类(从而个体)命运问题”〔19〕依然富有价值。李泽厚对康德的述评之后成为其美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西学资源,他将康德关于人的先天认识范畴的表述,改造成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并将其作为自身哲学体系中心“主体性”的两个维度之一。“主体性”在李泽厚看来包含两个维度:其一是外在的工业社会结构,其二是人类认识的结构——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这里的“结构”既具有结构主义所言的共时性,又有历时的意义,即强调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一个历史的、不断变化的过程。由此出发,主体性的形成与发展实则是动态的人类实践的历史过程。李泽厚并没有理所应当地全盘接受康德的先验认识结构概念,它包括人类直观的时间感和空间感,而是对认识结构的先验性予以重新检视,将它改造成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认识结构。人类认识活动的可能、知识得以形成的条件,并非源自人类具有一种先于经验的认识形式,与之相反,李泽厚认为它来自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深刻的历史性与社会性。文化心理结构的提出肯定了人类具有某种共同的心理形态,它源于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实践活动,随着这一活动的历史展开,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改造了外在自然,与此同时被改造的自然不断更新着人类的认识结构。内在的认识结构时刻处于与外在的社会结构互相作用的过程,李泽厚将这一过程称之为“积淀”,“社会的、理性的、历史的东西累积沉淀成了一种个体的、感性的、直观的东西,它是通过‘自然的人化’过程来实现的”〔20〕。用“积淀”理解主体心理结构的形成机制,将之视为历史的实践的产物,与康德的先验主体概念区分开,这亦是李泽厚的独创。另一方面,对文化心理结构内在构成的划分上,他继承了康德关于心意机能的三分法,即“人的认识(符号)、人的意志(伦理)、人的享受(审美)”〔21〕。对于李泽厚而言,“积淀”的历史过程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它表现于审美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美学是李泽厚的第一哲学。
文化积淀说以及李泽厚关于人类认识心理结构的表述,备受国外研究者的重视。国外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其一,与荣格的“原型”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做比较,从横向的比较中凸显积淀说的特性与价值。斯洛文尼亚学者罗亚娜(Jana S.Rosker)提出,“积淀”是人类经验发展史上的一个特定阶段,与荣格的原型理论强调集体无意识相比,积淀概念既包含了集体心理结构,又包含了个人意识,且作为动态的“实体”更具有历史性。与此同时,积淀说更为强调集体意识,又显然受到了荣格的影响。千孟思(Marthe Chamdler)以现代科学的成果肯定积淀说的价值,列举了人类学、儿童心理学、灵长类动物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证据印证积淀说的合理性,并指出李泽厚“采用了一种符合达尔文观点的方式来阐释康德的哲学观点”〔22〕,也就是以进化的发展变化的视角修订了康德主体性的观点。其二,认为积淀说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原创性。李泽厚将艺术作品的层面分为形式层、形象层和意味层,分别对应“积淀”的三种形式:原始积淀、艺术积淀和生活积淀。〔23〕2008年版《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选录的就是《美学四讲》中关于原始积淀与艺术形式的篇章,向读者,尤其是对中国美学不熟悉的西方读者,如此描述李泽厚美学思想中“最著名、最具原创性的”〔24〕积淀理论:“这一理论反映了李泽厚给康德的先验主体性奠定一个马克思式的唯物主义的基础的努力,而他的努力也受到了‘天道即人道’这一中国传统信念影响。”〔25〕选集的编者显然注意到以康德、马克思为代表的西方思想资源以及中国传统儒家观念对李泽厚的影响,那么,积淀说的原创性表现在哪里呢?换句话说,积淀说在综合了中西思想资源的基础之上,又在哪个问题的思考上实现了真正的推进呢?刘再复从李泽厚与康德在“人”的问题上的异同,以及前者如何通过“修正与再建构”康德的表述,讨论了积淀说在其中的意义与创新。在他看来,两个人哲学的中心命题都是“人”,且都认为人是社会性、理性与个体性、感性兼而有之的。区别在于“如何实现理性落脚到个体独特性之中”〔26〕。康德认为理性到感性的中介是一种心理能力“判断力”,李泽厚则提出“积淀”的过程,即人类的历史实践才是统一理性与感性的方式:“最终落脚在个体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以获得人的自由。”〔27〕艺术作为积淀过程的最终目的,“审美则是‘理性对感性的渗透融合’”〔28〕,而人类的主体实践使得这种融合得以实现。因此,“美的本质和审美意识是文化积淀的产物”〔29〕。毫无疑问,积淀说的提出解决了社会历史的结构如何进入意识层面以及美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从美的发生学角度推进了关于美的起源、美的本质、审美意识等命题的思考。在李泽厚建构的美学体系中,美和美感皆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产物,也就是人在劳动实践中“积淀”的结果。
文化积淀说之所以能实现理论的创新,源自李泽厚对人类生存境遇以及个体存在价值的关切,他提出的“人类如何可能”的问题,以存在论和本体论解决认识论问题的努力,并以此与康德形成对话。基于此,李泽厚将自己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称为“人类学本体论”。以人类的生存境遇为思考的起点与根基,在“人类如何可能”的基础上,讨论美如何可能、审美意识如何可能;另一方面,将美学视为第一哲学,认为美实现了人的自由,从美的问题复归人的问题。从人类本体视角讨论美的命题,将美学构建在人类学本体论的根基上,这是李泽厚美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其原创性的重要原因。依据自己的问题——人类如何可能——批判、改造、综合中西方美学资源,这就避免了简单地将西方话语或中国传统作为参照系,或对经典话语不作讨论地作为理论前提去使用。不论是新概念的提出,还是对美学基本命题的进一步思考,乃至理论体系的整体生成,“人类如何可能”之问题贯穿其中。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以文化积淀说为主干的李泽厚美学,是顺接西方哲学传统而作出的理论探索,它所要试图解决的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在感性与理性、人与自然、社会与个体、认识与伦理等富有张力的问题域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推进。因此,即使从世界美学的眼光来衡量,李泽厚的文化积淀说仍然具有原创色彩。
三、中国作为经验与中国作为方法
上文讨论了李泽厚的积淀说具有的原创性和世界性。然而,任何思想的提出都具有自身的历史和现实语境,积淀说有着明确的与现实语境相联系的问题意识。李泽厚何以能提出“人类如何可能”的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对于现代性、人的主体性之探索密不可分。积淀说的思想雏形源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界的美学大讨论,李泽厚在与学人讨论自然美命题的时候,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后来成为积淀学说的思想基石。〔30〕积淀说的正式提出是李泽厚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积淀论论纲》〔31〕,之后在80年代出版的《美的历程》《美学四讲》中不断深化成熟。的确,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从思想界到文学界,到处弥漫着关于现代性与人的问题的思考。因此要想深入理解积淀说,还原其产生的历史语境是必要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还原语境意味着积淀说本身携带的中国问题与中国视角的凸显,它构建了一种可能性,即对于世界美学而言,以中国视角看待美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中国作为一种经验乃至作为一种方法,赋予了美学全新的理论视域。
20世纪末,审美论回到了世界美学讨论的前沿〔32〕,审美的重要性重新成为理论家关注的重心。文洁华注意到,对审美经验的讨论成为中西当代美学共同的理论兴趣,但二者的思想基础并不相同。相较于经过后现代理论洗礼的西方美学,中国当代美学的“思想基础不是植根于后现代理论,以及去中心的主体,意义或符号问题,而是关于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主客关系的现代讨论”〔33〕。这里的“现代讨论”指的就是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以朱光潜、李泽厚、高尔泰为代表的中国学界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大讨论。文洁华(Eva Kit Wah Man)的论文《对社会主义中国回归审美经验的批判性反思》尝试以中国现代美学的经验讨论“何为真正的审美经验”。论文从1988年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审美感兴”谈起,认为它呼应了当今世界美学最关心的命题,即通过回归审美经验完成美学对当代艺术的救赎。“审美感兴”描述了审美心理的过程,它涉及审美发生过程中主客的互相作用,且已经成为美学体系的中心命题。他们认为审美感兴的提出,可以避免美的起源问题上主客二分造成的种种问题,即或认为美在主观,或认为美在客观。论文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美学对于这一问题讨论的基础是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充分肯定了李泽厚认为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不可分有合理之处,意味着美感经验以社会的政治性、物质存在为基础。Eva Kit Wah Man作为一位西方世界的美学研究者,深感审美命题经过后现代理论的洗礼之后的矛盾性,一方面要抵抗意识形态的过度解读,另一方面审美论已无法回归传统的唯美论,审美经验的合理路径是在审美与社会政治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李泽厚的美学思想以人类实践为根基,“美的本质、根源来于实践”〔34〕。美、美感是“自然的人化”积淀的结果,这种将美与人类的历史实践相结合的思路,契合了当下审美论试图在审美和历史政治之间找寻平衡的想法,无疑为当代美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积淀说是在综合马克思、康德、中国传统儒学等不同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产生的,学界对于李泽厚美学理论思想来源的研究甚多,讨论也深刻。①国外研究的代表成果:Cauvel Jane,“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Art:Li Zehou’s Aesthetic Theory,”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49,no.2(April 1999),pp.150-173;Woei Lien Chong,“Combining Marx with Kant:The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Li Zehou,”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49,no.2(April 1999),pp.120-149;Chan,Sylvia,“Li Zehou’s Theory of Ethics:A Synthesis of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New Zealand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no.1(Jan.1994),pp.50-65;Liu Kang,“Subjectivity,Marxism,and Culture Theory in China Social Text,”Third World and Post-Colonial Issues,no.31/32(Feb.1992),pp.114-140。积淀说丰富的中西思想资源使得理论本身呈现了李泽厚关于中国传统和现代性、中学和西学的思索,他将之概括为“西体中用”。“西体中用”既是对中国传统与现代性关系、中国化的积极探索,又是一种全新的中西文化研究方法。
何为“西体中用”?李泽厚首先对“体”“用”的范畴重新规定。“体”是社会存在和生产方式,科技作为社会存在的根本动力,也属于“体”的范畴。正因为工业大生产和科技发展源自西方,由西方传播给中国,故“西体”指的是经济基础,尤其是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基础性地位〔35〕,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对“西体”的解释。“中用”即“如何适应、运用在中国的各种实际情况和实践活动中”〔36〕。“西体中用”的关键处在于“体用”的关系,李泽厚完全采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不二”思维:“实体(Substance)与功能即‘用’(Function)本不可分,……没有离用的‘体’,‘体’即在‘用’中。因此,如何把‘西体’‘用’到中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创造性的历史过程。”〔37〕“体用”之截然不可分,意味着“西体”和“中学”在“用”的过程中实现了双向互动:“西体”既可以应用于中国,“中学”又可以作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38〕,“在这个‘用’中”,即创造性转换的过程里,中国传统的心理文化结构被改变,“‘西体’才真正正确地‘中国化’”〔39〕。李泽厚的“西体中用”曾遭到国内学者激烈的批评,认为这个提法意味着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处于从属的地位。“西体中用”是否如批评者认为的那般“反传统”?国外研究者从中西辩证法不同的角度为“西体中用”正名,认为李泽厚的批评者“并未把‘体’与‘用’这对两极对立理解为一对对立范畴,而是在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二元论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的”〔40〕。的确,不同于二元论的非此即彼,“体用不二”赋予了“西体中用”中国古代辩证法的底色,所谓“不二”说明“体”与“用”是一对对立统一而非矛盾的范畴:西体的实现,在“用”的过程里通过“中体”显现,现代化也就是中国化;“用”之过程的动力在于“体”,所谓中国化实则是被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塑造的文化形态,“体用”构成对立统一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的“西体中用”体现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核心,它非但不是“反传统”,恰恰是在与马克思实践论结合的基础上完成了对传统的延续与深入。
李泽厚对于“西体中用”的新解释创造了一种新的“体用”模式,它非常典型地体现在积淀理论中。积淀理论的核心概念“文化心理结构”也回答了“西体中用”内蕴的新问题。“体用不二”意味着,在李泽厚的话语语境里,现代化和中国化是一体两面,西体和中学在双向互动中得以转换和改变。如此一来,传统的中学受西学影响的命题就不存在了:一是因为这种影响是单向的,二是中学是相对静态的中国传统观念形态,而在“用”的过程中,被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塑造的中国文化形式实则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李泽厚提出“文化心理结构”概念,用它来代表“体用不二”模式中的中学与西学。“文化心理结构”概念一开始就被置于人类学的本体维度,受康德的人学理论影响,李泽厚强调自己讨论的人是“超生物族类的社会存在”,“主体性心理结构也主要不是个体主观的意识、情感、欲望等等,而恰恰首先是指作为人类集体的历史成果的精神文化、智力结构、伦理意识、审美享受”〔41〕。因此,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是人类实践,在由社会存在塑造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人类共同的心理形态,具有超阶级、超民族的特点。
文化心理结构的提出,赋予了李泽厚讨论中西问题一个更大的视野,提出真正的中国化是文化心理结构的更新。他梳理了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在处理西方与传统问题时的立场,发现“传统小生产的经济基础和其上的意识形态”〔42〕如果不改变,中国化的过程往往演变成“‘中学’吃掉‘西学’,使中体巍然不动”〔43〕。强大的中学思想体系与观念形态“善于化外物自用”〔44〕,难以实现真正的中国化。因此,必须找到一种超越中西思想体系的认识结构,它由人类漫长的实践活动积淀而成,传统与现代性双向互动的过程皆由文化心理结构呈现。如何面对传统的命题,转换为由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的心理结构去选择和转化“传统”,继而产生新的心理结构,这亦是真正的中国化。在李泽厚看来,内生于传统儒学的实用理性,不同于西方的先验理性,在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地积淀—重构—再积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占主导的中国当代社会,实用理性所具有的“理知和求实精神”“道德主义”〔45〕,对于中国如何积极处理现代性带来的弊病、重塑民族精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西体中用”的革新意义:以“体用不二”的思维和“文化心理结构”概念拆解了“中西”的表层含义;将“中学西学”的二元性概念转变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把中学受西学影响的单向关系,转变为以社会存在的本体为出发点的双向互动过程。因此,“真正的‘西体中用’将给中国建立一个新的工艺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将给中国民族的生存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46〕。
文化心理结构作为人类共同的经验体,有超民族的一面,同时也是一种民族的身份认同,关乎如何去创造一种现代生产方式所塑造的中国主体性。李泽厚提出回归传统开掘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实则是一种经由历史积淀而成的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没有基督教等宗教传统,是否能从自己传统文化中以审美来作为自己人生境界的最高追求和心理本体的最高建树?”〔47〕从传统出发构建“审美的形而上学”,李泽厚充分发展了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情感维度,将它视为心理结构的中心,情感甚至具有了本体的意义。因为只有在这个领域里,“人成为掌握控制自然的主人。自然与人、真与善、感性与理性、规律与目的、必然与自由,在这里才具有真正的矛盾统一。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在这里才有了真正的渗透、交融与一致。理性才能积淀在感性中,内容才能积淀在形式中,自然的形式才能成为自由的形式,这也就是美”〔48〕。由此可以看出,在以情感为主导的心理结构中,理性积淀于感性中,内容积淀于形式中,美由此产生。沿着这一思考路径,李泽厚将“情感”视为“最后的实在”,提出“情本体”的概念:“无目的性自身便似乎即是目的,即它只在丰富这人类心理的情感本体,也就是说,心理情感本体即是目的。它就是那最后的实在。”〔49〕
以“情本体”为出发点,李泽厚找到了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情理结构。”〔50〕首先,在李泽厚看来,中国的“情”以“动物本能”为基础,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理性主义区别于西方理性主义,“中国理性的特点从动物本能上升为理性,……因此孔子讲‘爱有等差’”〔51〕。因此,“情本体”既代表了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又具有人类共通性。其次,李泽厚将中国的巫史传统视为“情本体”的起源,对情的重视构成了儒家的心理结构。儒学重视“情”“性”“心”的塑造培养,历史上可以追溯至“上古巫术仪典”,巫术仪典在理性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情理交融、合信仰、情感、直观、理知于一身的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信念形态”〔52〕。由此可以看出,李泽厚从中国的巫史和儒家传统出发,找到了以“情本体”为要义、“情理结构”为内容的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他分析屈原作品呈现出以情为始、以情为本、融理入情特征的“情理结构”,以屈原对待死亡的态度为切入点,生死是“大情”,在对生死反复衡量与思索中,“把人性的全部美好的思想情感,……统统凝聚和积淀在这感性情感中了”〔53〕,同时产生的对“是非、美丑、善恶”的判断,即便是理知,也是“沉浸、融化在情感之中的”〔54〕理知。在李泽厚看来,屈原是“第一个以古典的中国方式在二千年前”提出“我值得活着么”〔55〕的勇士,对于死亡问题深刻的情感反思与感受,以死亡淬炼心灵,影响了之后中国士人的心理结构。此外,李泽厚强调屈原赴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认定自己“从情感上便觉得活不下去”〔56〕,这是一种以情感为本,又是极其“具体而个性化”的情感。对个体感性生命的强调,也是李泽厚“情本体”的重要内容。
李泽厚道明了“情本体”的双重意义,“这是一种世界的视角,人类的视角,不是一个民族的视角,不只是中国视角。但又是以中国的传统来看世界的。所以我说过,是‘人类视角,中国眼光’”〔57〕。它是李泽厚以人类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巫史传统和屈骚文化,对中国人心理深层积淀的概括,可以看作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表达;另一方面,“情本体”以动物本能为基础,最后复归到个体感性生命,彰显一种不同于西方世界以理性为核心的本体之路,呈现出李泽厚美学思想的世界意义。
李泽厚贡献给世界美学的原创性思想,恰恰是最具中国性的理论话语。理论话语具有一种普遍性,它可以超越中西、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以形而上的思索讨论人类共同关心的命题。正是为了回答“人类何以可能”的重要问题,李泽厚提出文化心理结构和“情本体”,它们既依据于中国文化与思想传统,具有独特的中国化特征,又具有人类本体论的哲学视角,充分体现了“西体中用”的方法论。“情本体”和“西体中用”,向我们呈现了中国作为一种“方法”参与世界美学构建的可能性。
李泽厚以积淀说为核心的美学思想,其理论本身的构成以及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与影响,充分说明了西方美学与李泽厚之间,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影响与接受的关系,而是一个双向的阐释和交汇的过程。在这种双向的阐释中,李泽厚用马克思的实践论批判改造了康德的先验哲学,使得自身的美学体系建筑在实践而非先验的根基上。更具独创的是,他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出发,从本体论层面提出“人类何以可能”的命题,以此替代了康德认识论的“人类认识如何可能”。作为一位理论的生产者,李泽厚真正地参与了理论的知识生产。李泽厚的重要理论著作产生于20世纪中后期,其理论虽然具有世界视野,但仍有其时代的局限。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对于主体性和理性的高扬以及“自然的人化”反映出人类实践之于自然的绝对主宰,契合了彼时中国的思想现实。然而21世纪的今天,经历了全球变暖、疫情对人类生活的改变以及后现代思想对于现代性的反思等,人类已经深刻意识到主体的有限性以及主体应对自然心生敬畏,生态美学等的兴起充分印证了这一思想趋势。以今天的现实反观李泽厚的理论,其中的时代局限不言而喻。另外,近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革命的来临,也充分说明了李泽厚的“实践”概念内涵之偏狭,人类社会除了物质生产劳动,还有信息的生产以及相应地对于人类物质生产的改变。时至今日,美学已从庙堂之上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与感知事物的方式。美学的理论话语也须相应地随着时代的变化予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