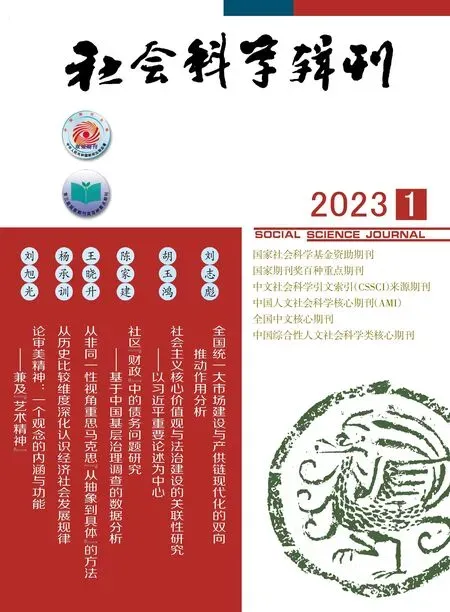论审美精神:一个观念的内涵与功能
——兼及“艺术精神”
刘旭光
在具体的审美活动中,我们通常会有这种审美经验:某个雕塑一眼看去就知道是唐朝的,观赏一张画立即能意识到它是宋代的,某段舞蹈一看就知是阿拉伯的,一段音乐一听就知是西班牙的,等等。有经验的审美者在直观审美对象时,经常能够立即凭感官“感觉到”它属于某种类型,这类型可以是民族的、时代的、地域的,成熟的审美者似乎会有一种关于某种对象所包含的“一般性”的感觉,并凭这个感觉判断对象的表征性——对民族、时代、地域等因素的表征。这种对于“一般性”的感觉确实存在,但又难以言传,大约可以称之为“精神感觉”(这词的内涵稍后再述),而这种审美中的精神感觉,作为某一类审美对象或艺术作品的特征,具有区分、标识与规定的作用。这种“精神感觉”在美学研究中被视为对象所具有的某种“精神”,从而产生了“审美精神”以及与它有亲缘关系的“艺术精神”“美学精神”等话语。这些话语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理论思考与理论表述的工具,并且被广泛利用,比如“华夏传统审美精神”“墓葬艺术与汉代审美精神”“从宫体画看宋代审美精神”“日本审美精神中的侘寂”“维多利亚时代的审美精神”等等。这种表述在美学史、审美文化史和艺术美学研究中随处可见。这个词还有意味更暧昧一些的相近表述——“审美意识”,也还有更情感化一些的“审美意趣”。这些术语总体上有这样一个特性:它指称一种可以感觉到的一般性,这个一般性又可以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性理念。但这些术语本身是有待被检讨的:这些词是什么意思?从何而来?能做什么?
需要对审美精神给出一个预先的定义:审美精神是审美对象所呈现出的某种精神感觉,当这种精神感觉具有肯定性和一般性且可以上升为具有统摄意义与规定意义的原则性理念时,它就被称为“审美精神”①审美精神在中国美学界被广泛讨论过,但主要是对某种审美精神进行内涵罗列,或者把某些文艺作品在审美上体现出的一般性提炼为审美精神,缺乏对“审美精神”的定义。本文关于审美精神之定义的提出,受到了陈伯海先生在《华夏传统审美精神探略》(载《学术月刊》2018年第8期)一文中一句话的启发:“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性理念。”在文中这句话并非作为“审美精神”的定义而提出,但从理念角度追问“审美精神”,笔者认为这对定义审美精神极具启发性。。同样,可以给艺术精神预先下个定义:艺术精神是艺术作品的整体构成、艺术语言与技艺所呈现出的某种精神感觉,当这种精神感觉具有一般性且可以上升为具有统摄意义与规定意义的原则性理念时,它就被称为“艺术精神”。在这个定义中:精神、精神感觉、统摄与规定、理念、原则性这几个术语是基石,它们的内涵与关系需要阐释。
一、可感觉到的“精神”与审美精神
在具体的审美对象特别是文艺作品中,有一些特殊的现象:对象能够给我们一种特殊的感受,这种感受具备一种有条件的普遍性,审美者可以通过它对对象进行分类,比如清代的工艺品精巧繁复,精巧繁复这种感受就可以用来断定某件工艺品的时代;汉代的雕塑古朴雄强,这种感受也可以用来进行具体雕塑作品的断代或它的风格源流的划定;类似的情形还有日本艺术显得“清寂”、中国山水画“空灵生动”、荷兰静物画“精致肃穆”,等等。这些现象说明,我们的审美经验,特别是审美感受,有一种微妙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受到美学家们的重视,康德本人也同意有这样一种源自经验的感受的普遍性,他认为:“感觉(愉快或不愉快)的普遍可传达性,亦即这样一种无概念而发生的可传达性,一切时代和民族在某些对象的表象中对于这种情感尽可能的一致性:这就是那个经验性的、尽管是微弱的、几乎不足以猜度出来的标准,即一个由这些实例所证实了的鉴赏从那个深深隐藏着的一致性根据中发源的标准,这个一致性根据在评判诸对象由以被给予一切人的那些形式时,对一切人都是共同的。”〔1〕这段话中关于感觉的无概念的可传达性之说,为我们理解上文提到的感觉的普遍性提供了启示,而且康德把这种普遍性视为“深深隐藏着的一致性根据”,这种感觉尽管是经验性的、微弱的,但它仍然可以作为标准帮助我们进行判断。
康德的这个观念为理解审美精神提供了启示:一种普遍可传达的感觉,它可以作为标准供我们进行相关的评判,虽然康德认为这是由对象的形式引起的,但或许作品的材质、构成、样式、艺术语言、技艺、情感、理念等因素,都会促成这种普遍感觉。但“感觉”还不是“精神”,康德还提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一首诗可能是相当可人和漂亮的,但它是没有精神的。一个故事是详细的和有条理的,但没有精神。一篇祝辞是周密的同时又是精巧的,但是没有精神。”〔2〕这个被他称为“精神”的东西,可以产生一种独特的效果:它可以使欣赏者的内心获得鼓舞,从而产生生动之感,审美似乎是在感知和领会这种“精神”。这种“精神”是直观感受到的,但又超越于对象的具体构成而成为对象整体所呈现出的风貌。这个现象确实是审美经验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我们通常会说一个小伙子看起来“很精神”,这个“精神”是对生命状态的整体统摄,虽然这个“精神”无法进行具体分析,但在感官上却是鲜明的。康德所揭示的这个“精神”,如果具有某种类的普遍性,或者具有他在上文所说的“深深隐藏着的一致性”,比如某个时代或某个民族的文艺在精神上的一致性,某个地域的文化产品作为审美对象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就可以被称为对象的“审美精神”或“艺术精神”。
在这个观念中,首先确认了“精神”这个现象的存在。审美对象所具有的能够鼓动审美者之内心的那种力量,虽然无法明确地分析出是什么,但它确实会让审美者做出精神反应,因而那种力量就被称为对象的“精神”,虽然我们无法断定它是不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但它在具体的审美经验中确实存在。其次,这个观念肯定了这种精神具有一致性,而且这个一致性是可以被感觉到的。当某一类审美对象或艺术作品具有相一致的“精神”时,这个“精神”就成了此类作品的“审美精神”。这是“审美精神”这个词最外在的含义,它是审美对象的可感觉到的非概念的一致性,且具有一种鼓动心灵的力量。元青花瓷给我们的素雅沉静感,宋工笔花鸟画给我们的工静典雅感,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所具有的雄强壮大感,凡·高作品带给我们的忧郁深邃与浓烈感,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审美精神”。
二、肯定性的精神感觉与审美精神
一个审美对象中所包含的“审美精神”是感觉到的还是反思出来的?18世纪初的意大利思想家维柯认为:“人们起初只感触而不接触,接着用一种迷惑而激动的精神感觉,最后才以一颗清醒的心灵去反思。”〔3〕这就把认识分为感官感知、精神感觉和反思三个环节。对于艺术欣赏和审美来说,认知过程就是一个由三阶段构成的统一体;上文中得出的非概念、可感觉到的一般性,就是这样一种统一体。感知其中的一般性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肯定。寻求审美精神的目的,是为了探求其中包含着的值得肯定的某种一般性,感知本身是为了肯定对象而展开的,这是审美与艺术欣赏中感知对象的特殊性,它们在寻求对象中可感觉到的肯定性因素。在审美中,感性与它的对象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也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4〕。这是马克思的名言,其中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让感性对象成为自己的现实与自己的确证,可以间接说明审美活动的特性。
在这一特性中,人的感觉是以人自身的“社会的器官”来感知世界的。“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5〕
“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精神感觉”与“实践感觉”,这些词汇想要强调的是:感觉不是器官的应激反应,而是人肯定自己、肯定世界之存在的方式,感觉可以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作为人对于现实实践的感觉,作为人对精神理想的感觉,从而成为一种“丰富、全面而深刻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对康德提出的那个“精神”的深化。在这种感觉中,那种鼓动人心的力量一方面是人的本质力量,也就是人的劳动与实践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人的创新性、想象力、技艺、意志力、行动能力、协作能力等与劳动实践相关的力量的确证;另一方面,也是人的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现实的问题,包含对规律的认识,现实的情感、理想、愿望、矛盾等带给人的感受。这意味着,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中的“精神”具有人文主义和社会历史内涵,这种内涵可以凭“精神感觉”感知到,这种被感知到的内涵,在美学中被称为“意蕴”,黑格尔对这个概念有过一个阐释:
遇到一件艺术作品,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蕴或内容。前一个因素——即外在的因素——对于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并非由于它所直接呈现的;我们假定它里面还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即一种意蕴,一种灌注生气于外在形状的意蕴。那外在形状的用处就在指引到这意蕴。因为一种可以指引到某一意蕴的现象并不只是代表它自己,不只是代表那外在形状,而是代表另一种东西,就像符号那样,其中所含的教训就是意蕴。文字也是如此,每个都指引到一种意蕴,并不因它自身而有价值。同理,人的眼睛、面孔、皮肉乃至于整个形状都显现出灵魂和心胸,这里意蕴总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艺术作品应该具有意蕴,也是如此,它不只是用了某种线条,曲线,面,齿纹,石头浮雕,颜色,音调,文字乃至于其它媒介,就算尽了它的能事,而是要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作品的意蕴。〔6〕
这段引文中提到的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精神等,是文艺批评的主要话语,意蕴相比于上一节提到的“精神”,后者只是泛泛提到的可感觉到的一般性,是一种朦胧的感觉,但意蕴却是通过精神感觉获得的,与对象所包含的人文性的、社会历史性的内涵有关。
精神感觉与意蕴,呈现着“审美精神”这个词的另一重内涵,审美精神是对象中包含着的可以被感觉到的人文性与社会历史性内涵,相比于第一个层次的审美精神——非概念的普遍可传达的感觉——要更具体一些,是对象作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而呈现出的内涵。这些内涵的审美性质在于,它们必须是可感的。我们在杜甫的诗歌中所感受到的大爱情怀与沉郁顿挫,在黄宾虹的山水画中感受到的浓厚华滋,在米勒的作品中感受到的对劳动者的敬重与深情,在列宾的作品中感受到的深沉与苍凉,在赵树理作品中感受到的乡土与明晰,都可以纳入这个层次的审美精神中。相比于第一个层次的审美精神,这个层次的审美精神会多一些价值内涵与社会历史内涵,这些层次的审美精神,不能只通过直观获得,还需要意义与价值的反思,是感知与反思相结合所产生的,它表面上看是精神感觉直观到的,但更多的还是对具体的意义与价值的反思与精神感觉的结合,或者说,是被精神感觉引领着的反思的结果。同时,这个层次的审美精神,还体现为对对象中包含着的价值内涵的肯定:在浑厚华滋中,观者肯定了黄宾虹对墨法的传承与冲破;在沉郁顿挫中,欣赏者肯定了杜甫的人文情怀;在敬重与深情中,则肯定了米勒对劳作和平凡的劳动者的态度。这种肯定和马克思主义者所寻求的确证感是相通的,通过精神感觉而完成的对对象之存在或对象之特征的肯定与确证,对可感觉到的价值内涵的肯定,是审美精神的第二重内涵。
三、审美统摄:审美精神的统摄性
当我们说某个人“精神很好”时,这个“精神”是对象整体生命状态的整体统摄,这种统摄先把对象视为一个整体,然后认为这个整体的生命状态有其可直观到的风貌,这个被统摄出的整体风貌,就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而一个审美对象与一件艺术作品也有其精神状态,这个状态是审美统摄的结果。
中国古代绘画鉴赏理论中有这样一个步骤性的描述:“先观气象,后定其去就,次根其意,终求其理。此乃定画之钤键也。”〔7〕“先观气象”是第一步,这说明审美并不是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的整合过程,也不是分析到综合的逻辑演进,审美始于对对象的整体统摄。对对象的审美统摄,是对其精神风貌所做的一种整体性的领会,并由此获得一种整体性的精神感觉。这种统摄,康德用拉丁词Zusammenfassung来表示,随后他注了拉丁文(comprehensio aesthetica)①〔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0页。Zusammenfassung邓译为“统握”,英文译为comprehension“理解”,由于用这个词时康德强调的是把对象的“量”直观地纳入想象力,因此中文译为“统摄”比“理解”要好,但“统摄”一词无论在康德那里还是在现象学里,都更偏重于“统觉”这重含义,因此本文根据“直观”这层意思,译为“统观”,而这个译法也符合本文所说的对对象的精神风貌进行整体直观把握的意思。,这个词可译为“审美统摄”,也就是中国古代鉴赏传统中所说的“观气象”。对对象之气象的“观”,首先是一种整体感受上的统摄,它把对象视为一个整体,是对这个整体所进行的统摄,这就意味着,观看一幅绘画时,着眼点并不在于线条、构图、色彩、形象等具体因素,而在于对象所给予的整体性的精神风貌。
统摄是怎么做到的?按康德的说法,人类理性可以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视为整体”就是理性的本质性功能,但统摄的实现需要工具,而对经验进行统摄的概念叫理性概念,只有理性概念可以达到对经验认识的统摄,但在审美中,进行统摄的是“审美理念”。审美理念本质上是一种理念化了的表象,它是想象力所创造的表象,但起着理念的作用,因而也是一种特殊的理念,它有以下层次的内涵:
首先它是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一类表象;其次,这类表象具有对于经验的统摄性,又具有对于经验的超越性,接近于理性理念;第三,它可以引起很多思考,但不可被完全理解,意义具有不确定性;第四,它的内涵可以甚至只能以感性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比如天国或者善良、幸福这样的理念,内涵不明确的,但在具体的经验中,或者说感性对象中,我们却可以体悟到。最后,审美理念不具有直接的经验形态,它不是形象,也不能称之为意象,它在自然界中找不到实例。〔8〕
这种“审美理念”非常接近我们在描述审美经验时所使用的“雄强”“雅逸”之类的概念,这些概念是上文所说的肯定性的精神感觉,它们可以被直观所把握,我们在此将通过直观把握对象中的精神风貌或审美理念的行为,叫“审美统摄”。审美统摄本质上是主观合目的性的反思判断,审美统摄的目的是肯定性的心灵愉悦。对对象的审美统摄,更像是通过对对象的整体性的直观而激活我们心灵的某种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审美统摄是主观合目的性的,是一种特殊的反思判断,即用某种心灵状态对对象进行统摄的反思判断。审美统摄也是感性的,是通过感性直观而获得对象的整体表象,而这个整体表象具有整体性的精神风貌,这风貌可以被心灵直观感受到,进而成为一种心灵的状态,而后我们把这种心灵状态宣告为对象的“精神”,由于这种精神是审美判断的主要对象,因此也可以称为“审美精神”。
这种审美精神是这样获得的:审美统摄是主体对对象进行了主动的整体关照,领会对象总体呈现出的精神风貌。它不是判断,因为它不把对象归给某个明确的一般(概念),但它类似于判断,因为它把对象归给某个不明确的但具有一般性的心灵状态(审美理念),比如柔媚、朴拙、雄浑、明晰等,这些词汇所表达的不是概念的一般性,也不是如自由、和谐、真诚一样的实践理性的理念,而仅是对象的整体所呈现出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有时候是对象的神态与情态,有时候是对象的材质、技艺、色彩、形象等等因素呈现出的某种感觉上的统一性,这些都是统摄的结果,它们既是对象的风貌,又是主体心灵的状态,但都是在审美统摄中被激活的。当代美学家们对这种统摄有一种新的阐释:“积极的概括性感觉本身,就是将一些复杂事物统一起来的生机勃勃的活动。”①这是英国美学家R.W.Hepbum的观点,见〔美〕M.李普曼编:《当代美学》,邓鹏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317页。“积极的概括性感觉”这个说明颇能解释审美统摄的发生,“积极”意味着肯定性,“概括”意味着统摄与归纳,而“感觉”则意味着有一种感觉上的“一般性”可以被概括出来。
上述审美精神的获得,是对单个对象与作品进行统摄而实现的,在实际的理论应用中,审美精神更多地应用于对某一类作品或对象的统摄,从而成为“类特征”,或者说是可感觉到的类特征。比如,所有的唐三彩都会给我们一种相通的感觉:浑朴、饱满、意趣横生、典雅,再加上“三彩”所造成的共同的视觉感受,就会形成一种整体的感觉,使得我们一看某件作品就能“感觉到”它是唐三彩,由于这种感觉可复制,因而唐三彩较好的仿制品同样能传达这种感觉。再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派和威尼斯画派,前者基于线描的明晰典雅与沉静和后者基于图绘的明丽生动与现实感,会有细微的差异,这种感觉上的差异会让我们对某些作品进行大致的风格分类,并且成为赏析一件作品时参照性的感觉与尺度,也会成为创作中的审美理想。这种作为类特征的普遍感觉,当其被视为此类对象的审美精神时,会成为鉴赏与创作的引导,甚至成为鉴定的尺度,但作为统摄性的感觉,它不具有概念所具有的明晰性与确定性,这种审美精神不能靠概念与理论话语来传达,只能通过审美者在其具体的经验感觉中经由统摄、比较和反思而得出。
审美精神的统摄性质,使得它成为在审美与艺术领域中营造一般与个别、局部与整体的二元场域的有效手段:每一件作品,每一个局部,都作为个别而与作为一般性的“审美精神”形成对话关系,在对话中,“个别”所具有的特性和审美精神所要求的一般性相互制约,此类对象的审美精神要求每一个被归入此类的作品都可被涵盖其中,而每一件被归入其中的作品,还想表现自己的特性与个性,这就为审美与艺术批评提供了言说与评价的方式。由此,“审美精神”是理性的统摄式思维在“审美”这个感性领域中独特应用的结果,是理性与感性直接对话与协作的结果。
四、理念:审美精神的观念性与原则性
审美精神作为理性所进行的统摄的结果,是以“审美理念”为工具完成的统摄,但在对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进行统摄时,还有其他理念,如纯粹理性理念和道德理念,甚至宗教与意识形态的理念,都会介入到对审美对象的统摄中来,这意味着审美精神不仅仅是用审美理念对对象进行统摄的结果,审美精神还有更观念化的一面。这个时候,诸种理念的统摄会使得审美精神在其经验应用中获得远超出“审美”这一目的内涵,同时理念的超越性由此会传递给审美精神,使其成为一种超越现实对象的有限性的一种手段。
理念产生于人类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们总是相信,我们所处的这个经验世界总是包含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我们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有其特性,而这个整体的其他部分作为条件影响着我们。由于这种思维方式,人类理性自身会有一种更高的要求:它不满足于仅仅按照综合的统一性来解释诸现象,它还想超越经验所能提供的对象,超越经验现象的时间性变化与现实条件,成为经验对象的真实本原,这个本原既能完成对经验现象的统摄,又是经验永远达不到的,康德称这个真实本原为“理念”。理念是一种概念——“概念要么是经验性的概念,要么是纯粹的概念,而纯粹概念就其仅在知性中(而不是在感性的纯粹形象中)有其来源而言,就叫作Notio(这个概念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思想”“概念”,是“知性范畴”的意思——笔者注),而一个出自诸Notio的超出经验可能性的概念,就是理念或理性的概念。”〔9〕对知性范畴进行统握的这种概念,叫做理性概念,它不是经验世界的原型,而是对知性认识的再统摄或者说综合统一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其先天根源,这种根源康德称之为纯粹理性概念,或者叫先验理念。先验理念的任务就是对知识认识的统摄,由于理念涉及一切经验都隶属于其下而其本身却不是经验的对象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说,“一切现象的这个绝对整体只是一个理念”〔10〕,这样一来理念就可以完成对对象的统摄。这个理念有这样一种性质:
对这个理念而言,一切可能的经验对象虽然都用作实例(即用作对理性概念所要求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之可行性的证据),但不是用作蓝本。从来不会有人合乎纯粹的德行理念所包含的那个内容而行动,这一点根本不证明这个观念就是某种妄念。因为一切有关道德上的价值或无价值的判断仍然只有借助于这一理念才是可能的;因而每一次向道德完善的接近都必然以这理念为基础,不论在人的本性中那些按其程度来说是不可确定的障碍会使我们对此保持多么遥远的距离。〔11〕
表述是为解释道德行为与道德理念的关系而提出的,道德理念在经验中永远不能得到完全的表达,因而不能从经验性的原则达到“道德理念”这种综合的统一性,但只有通过具有综合的统一性的“道德理念”,经验性的道德判断才得以实现。道德理念的这种性质可以移用到审美精神中,每个具体的审美对象与此类作品的审美精神之间,正是借助审美精神才能完成对对象的审美统摄与分类判断,但这个审美精神又不能作为蓝本,具体的审美对象可以例证它,但不能“就是它”。
由于审美精神是用审美理念对审美对象所完成的统摄,那么审美对象是不是还可以用道德理念或形而上学的理念进行统摄?当然可以,而且,由于道德理念、形而上学理念和审美理念之间具有交叠的部分,也具有亲缘关系,因此,道德理念和形而上学理念,甚至宗教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关理念,都可以成为统摄审美对象的方式,审美精神由此可以从审美理念被拓展到整个理念的领域。
理念有哪些?康德认为纯粹理性理念是由灵魂、自然和上帝三者构成的,这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基本领地,也奠定了诸如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灵魂不朽、自然无限等信念。但各个民族的形而上学是不相同的,各有倾向,比如在华夏文明的形而上学中,三者统一为“道”,在印度文化中为“梵”,在日本文化中是“粹”,这些形而上学的最高理念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中都能起到对知性知识进行统摄的作用,从而建构出一套形而上学。
在道德领域也就是实践理性的领域中,存在着许多道德理念,当我们对一个经验对象进行道德评判时,一定先有一个关于诸道德现象的统一性的认识,比如德性、善良、忠诚、仁爱等,这种认识在经验中不能得到完全的表达,但却是对经验现象进行道德判断的前提。例如“人的最大自由”这个理念在经验中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经验现象达不到的,但在社会实践中,康德认为一部国家宪法,甚至所有法律,都必须以这个理念为基础。在实践理性的领域,自由是最高的理念,再有诸如善、恶、福、祸以及仁、义、礼、智、信等关于人类实践行为的理念,以及这些理念的一些更经验化的样态,组成了道德理念的星丛。而在宗教领域,关于救赎、神恩、信、圣爱、普度众生、解脱、慈悲、般若、仁爱等观念,可以构成另一套理念论。而政治和意识形态还有自己的一套理念话语,如民主、平等、公正、自由等等。
所有这些理念所构成的世界是一个观念化的、在经验世界中无法找到蓝图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又可以对经验世界进行统摄与反思,进而将现实世界理解为一个“合理念的”世界。理性主义者和理念论者相信这些理念是实存的,经验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只承认它们是对现实进行理性统摄的结果,而不是工具与原因。无论哲学的各个派别如何判定它们的性质,它们在审美领域中的实际应用通过“审美精神”与“艺术精神”之类词语得到了肯定。这是因为诸多理念构成一个“精神世界”,进入这个世界并以这个世界为现实生活的目的与原则,这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而审美作为一种精神生活,具有“理念”意义上的精神性,是进入这个“精神世界”的一个方便法门。
把“审美精神”理念化,让理念所构成的精神世界成为审美对象与艺术作品想要传达的内涵,这实际上把审美哲学化了,或者说,把哲学对人生与世界之“一般性”的思考,引入对审美对象的理解,试图寻求某个哲学问题对艺术创作与对对象之审美的引导作用,从而把艺术史和审美活动视为精神史的一部分。这使得审美和另一个意义上的“精神”结合在了一起,产生了具有哲学内涵的“审美精神”。这种审美精神必须在具体的审美对象与作品中显现出来,即它必须贯彻在对象整体中,引领并统率对象的各个部分,成为对象内在的原则,成为对象之构成部分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某个“审美精神”对于艺术家而言是一次创作的原则,对于某个审美者而言,是一次审美的调节性原则。作为原则,审美精神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创作目的与创作方法,也不是具有确定性的审美目的,而是对审美行为进行引领的范导,这个范导并不直接影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和审美者的自由选择,但其范导作用又可以被反思出来。
五、审美精神与时代精神、民族精神
在上文提及的审美精神中,它的主要内涵是指一种由审美对象所引发的肯定性的精神感觉及其理念化,但由于理念的哲学性,纯粹理性理念和实践理性理念也介入到对审美精神的统摄中,这就产生另一个层面的审美精神: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宗教精神与意识形态精神,只要它们在审美对象中被发现或在艺术作品中有所体现,那么它们也被称为“审美精神”。这种审美精神观可以追溯到赫尔德—黑格尔的艺术哲学。
18世纪末的德国思想家赫尔德指出,“若要彻底理解一个民族的哪怕一个思想或行为,必得先进入它的精神”,这个精神可以被一个词所概括,“你必须找到一个入其骨髓的词,通过它深入理解一切”,而那个词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得到理解——“为了领会灵魂的那个本性——它统摄一切,人的所有倾向和能力都依着它安排,即便最细微的作为也摆脱不了它的影响——不要把你的答案基于那单独一个词上;毋宁说,你要进入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它全部的历史——你要领会它的每一个细节。只有如此,你才是走在理解那个词的正道上。”〔12〕他所说的“那个词”,应当是指一个理念,一种形而上学式的思维使得他相信任何一段历史或一段历史中的文化产品都可以统摄为一个理念,这种思维方式使他相信每个民族都有其可以进行统摄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和“时代精神”(Zeitgeist),而这两种精神可以进行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摄。赫尔德的这个思想非常适合于把一个哲学理念与具体的历史现象相结合,用理念统摄历史现象。在审美领域中是用理念统摄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并宣称其为审美对象的“审美精神”。这种研究方式的经典案例是欧文·潘诺夫斯基所著的《哥特建筑与经院哲学——关于中世纪艺术哲学宗教之间对应关系的探讨》及《理念》,这两本书展示了时代的哲学观念和该时代的艺术之间互为表征的关系。再如德沃夏克的《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一书对时代精神与美术的关系的探究,特别是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都示范了这样一种研究审美活动与艺术的方式:把哲学理念与审美、艺术联系起来,探求哲学理念如何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审美方式和艺术创作,以及它如何引导对艺术作品内涵的解读。这构成了“审美精神”一词较为日常化的内涵。
一种更深刻的关于审美精神的观念来自黑格尔。黑格尔追随了赫尔德的关于精神的思想,历史不仅是要探知事实,而且还要理解这些事实产生的原因,以及这些事实所构成的那种合力与这股力量前进的方向,这些东西他统称为“真实”。黑格尔所说的“真实”,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是事物的对立统一状态:“抽象地去了解,这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普遍性要保持独立存在,不依存于特殊性,特殊性也要独立存在,不依存于普遍性;更具体地说,这种对立在自然界中就是各有特性的抽象规律与杂多个别现象之间的对立,在心灵界中就是人的心灵性与感性的对立,灵与肉的冲突,为职责而职责的要求,即冷静的道德意志的命令,与个人的利害打算、情欲、感官倾向和冲动,以及一般个人癖性之间的对立;内心的自由与外在自然界的必然性之间的尖锐矛盾;也就是本身空洞的死的概念和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即认识和主观思维与客观存在和客观经验之间的矛盾。”〔13〕
这实际上是要求把任何一个对象视为一种包含着矛盾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状态,这种状态是现实性与普遍性的:普遍性指矛盾本身在任何时代的任何领域都存在,社会历史性指矛盾的具体内容是历史性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身特定的矛盾和矛盾通过对立统一的和解,这个和解状态,就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在任何一个具体的领域中,比如一个宗教观念、一种意识形态立场、一种流派的艺术、一种关于自然美的观念、一种关于审美的观念,都可以看作是矛盾对立统一的结果,而这种对立中的统一作为对象的理想,就成为了对象中的“精神”。这种对立统一在艺术中体现为黑格尔的名言——理念的感性显现,对这句话的更深入的阐释是这样的:“一切艺术的目的都在于把永恒的神性和绝对真理显现于现实世界的现象和形状,把它展现于我们的观照,展现于我们的情感和思想。”〔14〕其中“永恒的神性”和“绝对真理”是抽象的,但现实世界的现象与形状又是具体的,怎么把二者统一在一起?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艺术观:
我们要肯定的是: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现真实,去表现上文所说的那种和解了的矛盾,因此艺术有它自己的目的,这目的就是这里所说的显现和表现。〔15〕
“真实”与“和解了的矛盾”是同义的,也就是说和解了的矛盾就是真实。这实际是对艺术提出了比哲学更高的要求,艺术的使命不再仅仅是美与创造,而是对时代的“一般世界情况”进行统摄,发现其中的矛盾,为这个矛盾寻求和解的可能,并且将这种矛盾冲突及其和解以感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意味着,艺术的真正精神就是这种社会历史与心灵中的矛盾及其和解。
以矛盾及其和解为中心的“精神”观可以被拓展出去,它的纯思辨的逻辑学意义上的状态是“绝对精神”,具体到民族性是民族精神,放置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就是时代精神等。其中与审美理念相关的是“时代精神”(The Zeitgeist)这个词,这个词把“个体的心灵状态”,与同时代的“所有个体的心灵状态”的共通处结合在一起,而所有个体的心灵状态又是由时代的“一般世界情况”决定的,通过把个体精神上升为时代精神,就使得艺术作品之中的精神不单单是指作品本身所引起的内心状态,而且是由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所决定的“时代精神”。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结语中强调了这个概念:“我希望这部哲学史对于你们意味着一个号召,号召你们去把握那自然地存在于我们之中的时代精神,并且把时代精神从它的自然状态,亦即从它的闭塞境况和缺乏生命力中带到光天化日之下,并且每个人从自己的地位出发,把它提到意识的光天化日之下。”〔16〕这意味着有一种内在于每个人的时代性的个体心灵状态的普遍性,而艺术的任务就是把这种普遍状态带到光天化日之下。
黑格尔的号召至少给美学家们提供了两种启示:其一,有一种超越性的“时代精神”统摄着一个时代的艺术与审美文化,比如我们把李白的诗歌、张旭的草书、韩幹的画、颜真卿的楷书等艺术作品统摄在一起,称其有“盛唐气象”。这个气象不是内容性的,也不是由形式因素造成的,它是风格上的一般性,而这种一般性可以被直观地感受到,这种中国人用“气象”所称谓的,类同于黑格尔所说的“时代精神”。其二,艺术应当揭示时代的主要矛盾,揭示心灵内在的矛盾,并为这个矛盾的和解寻求一个出路,这个和解在黑格尔的体系中的另一个称谓是“解放”,这个解放能够带来真正的自由,因此真正的美和伟大的艺术,总是这种心灵的解放与自由的结果。
六、艺术精神与审美精神的同异
审美精神和艺术精神在黑格尔的理论中是可以替换的概念,审美精神是在审美对象中寻求普遍性的精神感觉,并且理念统摄对象,在这个定义中把审美对象收缩为艺术作品就可以称之为“艺术精神”,但在现实的理论应用中,艺术精神与审美精神有两个层面的差异。
第一个层面的差异在于,除了上文所述的审美精神四个方面的内涵之外,艺术精神通常有一个对审美精神的发展之处:艺术精神往往还指某种艺术对于人的精神价值。也就是此一类艺术,对于它的受众而言,能够给欣赏者的精神产生什么样的积极影响。这一点与审美精神的肯定性有关,即艺术肯定并表现着一种什么样的人的精神状态?它对于人的精神有什么积极意义?这两个问题关涉艺术创作的精神动力以及艺术作品的精神价值,这是艺术精神对于审美精神的发展。以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为例,该书的主题是中国“艺术精神”,但书中并没有定义什么是艺术精神,徐复观提出此著的目的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并由此而在绘画方面,产生了许多伟大地画家和作品,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也不仅有历史地意义,并且也有现代地、将来地意义。”〔17〕徐氏想把中国艺术对于人的精神自由解放的意义视为中国艺术之精神,他在讨论中国艺术精神时,一方面强调精神的自由解放如何推动着中国艺术的创作,另一方面强调中国艺术如何能够推动它的欣赏者的精神之自由解放。在这个总观念的引导下,他从儒家和道家两个思想体系的角度讨论了这两种思想所给出的人的精神理想如何呈现为“艺术精神”。
就儒家而言,他从儒家的乐教观入手,把儒家的艺术精神概括为“为人生的艺术”,即艺术是人生之“志”的表现,是“仁”这种人格理想的实现,由于儒家把“乐”所代表的艺术与“仁”所代表的精神理想统一在一起,徐复观由此认为“孔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位最明显而又最伟大地艺术精神的发现者”〔18〕。这种艺术精神是孔颜之乐与舞雩之乐①关于舞雩之乐与审美的关系,见刘旭光:《赫连勃勃:在儒家美学中植入审美自律性的可能与路径》,《孔学堂》2021年第3期。的统一,他称之为“乐(音洛)”,乐的精神就成为儒家艺术精神的主旨,这一精神的本质在于:“乐与仁的会通统一,即是艺术与道德,在其最深的根底中,同时,也即是在其最高的境界中,会得到自然而然的融合统一;因而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艺术助长、安定了道德的力量。”〔19〕乐与仁的会通,更直接的表达是美与善的统一,徐复观认为由孔子所传承、发展的“为人生而艺术”的音乐,决不曾否定作为艺术本性的美,而是要求美与善的统一;并且在其最高境界中,得到自然地统一;而在此自然地统一中,仁与乐是相得益彰的。〔20〕善与美的统一由此成为儒家艺术的创作动因,也是儒家艺术的审美效果,从而也是对儒家艺术精神的一次概括性的表述。
就道家而言,徐氏认为道的本质就是艺术精神,进而阐释道:“说道的本质是艺术精神,乃就艺术精神最高的意境上说。人人皆有艺术精神;但艺术精神的自觉,既有各种层次之不同,也可以只成为人生中的享受,而不必一定落实为艺术品的创造;因为‘表出’与‘表现’,本是两个阶段的事。所以老、庄的道,只是他们现实地、完整地人生,并不一定要落实而成为艺术品的创造。但此最高的艺术精神,实是艺术得以成立的最后根据。并且就庄子来说,他对于道的体认,也非仅靠名言的思辨,甚至也非仅靠对现实人生的体认,而实际也通过了对当时的具体艺术活动,乃至有艺术意味的活动,而得到深的启发。”〔21〕这段话所说的“人人都有艺术精神”是个不恰当的表达,应当说人人都有精神追求,当这种精神追求自觉地落到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中时,这种精神追求就成了艺术精神,对于道家而言,当艺术成为体认“道”的一种方式时,“道”就成了艺术之精神。这种艺术精神有其鲜明的人生维度——“至乐”“天乐”;而“至乐”与“天乐”的真实内容,乃是在使人的精神得到自由解放,成为至人、真人、神人。为了至乐与天乐而进行艺术创作,通过艺术欣赏而获得至乐与天乐——这就是徐复观提炼出的庄子的艺术精神。〔22〕
对儒家与道家之艺术精神的提炼,实际路径是把哲学所追寻的人的精神理想、人生理想与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结合起来,当精神理想成为艺术创作的动因与艺术欣赏的效果时,这种精神理想就是艺术精神。这实际上是把审美精神的理念属性在艺术中进行了落实,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精神与审美精神是可以互换的两个概念。但还有一个不可互换的部分。
艺术创作是一种行为,在行为过程中,它需要以艺术家特定的身心状态为出发点;艺术创作作为一种行为,它是建立在一定的技艺的基础上的,技艺本身有其理想状态。艺术家的身心状态和技艺的理想状态,在艺术作品中是可以被感知到的,通过对艺术作品的鉴赏,可以感知到艺术家的身心与技艺所达到的状态,这与“审美精神”有关但有不同之处。比如说,“虚一而静”的内心状态在道家看来是艺术家的创作心灵状态,这一点也可以成为艺术欣赏者感知到的艺术效果;庖丁解牛式的自由与踌躇满志的状态,是艺术家的技艺自由的状态,这个状态也可以在其作品中被感知到,“虚静”和“技艺的自由”可以被纳入艺术精神,但很难归入审美精神:虚静的心灵状态既是艺术家的修养的工夫,也是作品在读者处引发的体验,还可以上升为一种人生理想,即在面对万事万物时保持心灵的虚静状态,这种基于艺术家之工夫修养的理念,与审美精神中的理念是相通的,但审美精神通常只是对审美对象的反思与统摄的结果,对于艺术家创作中修养的工夫关切不够,这是艺术精神有别于审美精神的地方之一;技艺的自由会达到从心所欲的境界,在“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状态下,进行自由创造,无法而法,不期而然,这种状态是艺术的自由状态,它可以理念化为一种“艺术精神”,但它属于艺术创作行为而不是审美行为,因而不能说是审美精神,这是艺术精神与审美精神的第二个差异之处。
七、尾论:审美精神的意义
感受到并反思出审美对象中所包含的审美精神,这对于“审美”意味着什么?——这是反审美的,一旦审美者有一个关于对象中的审美精神的在先的认识,而在对象中寻求这种精神,那么这不是审美,而是一次规定判断,这是不自由的符合性认知。比如说在一幅山水画中感受到元人气息,在一件雕塑中感受到古典精神,如果审美者像一个夸夸其谈的鉴赏家一样只是说这件作品体现了盛唐气象,那件作品有宋代雅韵,这不是审美,这只是一次认知。这种认知会被诸种教科书中的成见所引导,而不是一次主体的自由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对某个时代或某类作品之审美精神的认知,无益于审美,反而会干扰审美——认知判断会取代他的直观感受。当一种审美精神引导着艺术家的创作时,它会形成艺术上的保守主义,艺术家如果固守一种精神感觉,不断重复它,他就不是在进行自由创造,而是在进行合目的性的生产。只有一种情况:当审美者脑海中充满了诸种审美精神,而需要反思出一件具体作品包含着哪种审美精神时,这是审美的,因为这是一次主动的反思判断。审美精神因此处在一种悖论中:统摄出一种审美精神是为了肯定,但如果头脑中只有一种或几种“审美精神”,那就会陷入“意、必、固、我”的状态而丧失反思判断的能力;只有脑海中接受了尽可能多的精神,才可能直观与反思出一个对象中可能的审美精神。对审美精神的错误使用,在于把它作为标识与符号,以肯定或标榜某一种或一类审美对象;对审美精神的正确使用,是在诸种审美精神间进行比较与对话,尽可能开放地接纳新的审美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偏执的意识形态论者和民族主义者那里,对某种“审美精神”的执念会使他们丧失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因为他们的头脑只能被动地接受规定,而无法进行主动的反思与自由创造。
总体看来,被我们称为审美精神的东西,它最直观的意思是对象呈现给我们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精神感觉,而这种精神感觉具有价值内涵,是对可感觉到的价值内涵的肯定;审美精神也是我们用审美理念、道德理念和诸种理念对对象进行审美统摄的结果,由于理念的介入,使得审美精神成为把对人生、自然与社会之“一般性”的思考引入对审美对象的理解中的主要方式,从而使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成为“精神”的一部分。最后,审美精神也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在审美对象与艺术作品中的显现,同时揭示着时代与心灵的矛盾及其和解,是对时代之真与心灵的解放的显现。这三个层次的内涵都是号召:号召人们去探寻普遍的肯定性的精神感觉,从而坚守精神活动的审美性;号召在审美中使用理念的统摄性,把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而不是分裂开;号召在审美中,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这个层次上,对审美对象进行意义与价值的反思。
由于“审美精神”过于依赖理念的统握与理性的反思,因此它无益于纯粹的鉴赏判断,对对象中审美精神的把握,更像是一次理性认知而不是审美,但“审美精神”把审美这种寻求愉悦的活动精神化了,试图赋予感觉以精神性的内涵与超越性的价值。在审美精神这个概念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审美观:审美是对对象中所包含的一般性的理念的感知与反思,它期待审美有内涵方面的真理性。这个概念还包含着这样一个信念: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隶属于一个更高层次的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是属于整个民族、属于某个时代、属于人类心灵的。这种审美观和信念会把审美哲学化,最终导致审美的终结(就像我们在当代所看到的哲学对于艺术的入侵所造成的后果),但这个信念又使得审美可以形而上学化,可以价值化,从而使得审美活动具有更重大的精神价值。这就是“审美精神”这个概念的内在矛盾:用精神来提升审美,用审美来抵抗精神——这个词可以用来反对把审美过于感性化与浅表化,也可以用来反对把审美过于精神化,强调它仍然是审美的。这个概念因此是柄双刃剑,任何一次对审美精神的操弄,都会有反面效果。
对“审美精神”这一术语的基本内涵的明确,将有助于我们探究什么是“艺术精神”:这两个词有交集,但“审美精神”一词还可以涵盖大自然的伟大作品以及人类文化的诸多方面;而“艺术精神”这个词还可以探索艺术创作的技艺与艺术语言的精神感觉与理念内涵。审美精神的内涵探析对于探索“中华美学精神”这样的概念也有意义——要在中国人的审美与艺术创造活动中提炼与概括出中华美学精神,至少应当从本文五节所给出的角度来概括,或许能让这个术语的内涵具体化与明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