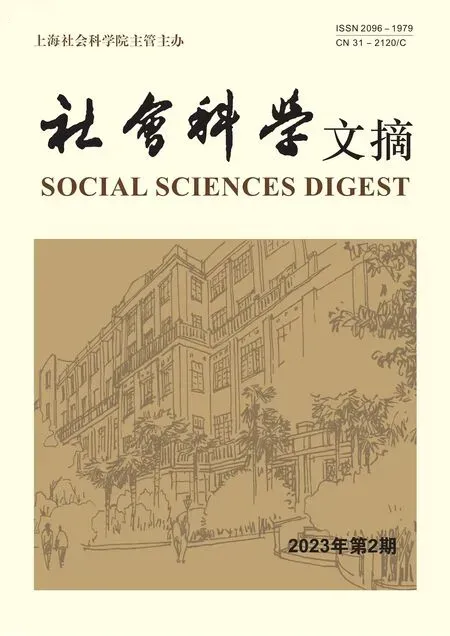再谈回归生活世界的价值诉求
——从儒学变迁史补叙
文/冯达文
学界许多人知道,我对宋明儒学的派系,不取通行的“气学”“理学”“心学”三分说,而是将之分为五派:把“气学”,区分了周敦颐、张载与清初王夫之、戴震的不同进路;把“心学”,别离为陆九渊、王阳明与阳明后学—泰州学的不同取向。这种区分在于呼唤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以为回归生活世界的价值诉求作理论上的铺叙。
我于1997年撰写的《宋明儒学略论》已认定泰州学为“主情论”;2001年发表的《“事”的本体论意义》又揭明泰州学可称“事本论”。这些文字通过凸显“情”与“事”的形上品格,以为回归生活世界张目。摆脱繁杂的文献释义与空洞的形式建构,让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为日常生活方式提供正当性说明,或许已成为哲学新的生长点?
要不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李泽厚在注释《论语》时,就称孔子主“情”本体。在2014年出版的《李泽厚对话集·中国哲学登场》中,他更称,讲“情本体”就够了,其他的“气本体”“理本体”都可以不要。稍后,王庆节撰《道德感动与儒家示范伦理学》亦称,儒家伦理的生命力,“起于和源自原初生命与生活世界中的人心感受、感动与感通”。李泽厚、王庆节高扬情感,杨国荣则用心于“事”,撰写《人与世界:以“事”观之》一书,称:以“物”观之、以“心”观之、以“言”观之,都不是本源性的,而“事”才是首先与人心现实活动相联系的。人去做“事”,带有具身性与感性,故凸显“事”的本源地位,其实也在倡导回归生活世界。
为什么凸显“情”与“事”,可以被认为构成儒学乃至中国哲学当代转向的重要视域呢?要弄清楚这一点,还需要回到儒学的变迁史。我曾于2019年发表过《回归生活世界的价值诉求》一文,从儒学变迁史予以略说。在此基础上,我围绕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一点补充。
一
追踪儒学发生发展与变迁的历史,首提孔子。我认为孔子开创的儒学,是从“原人”出发的。所谓“原人”是指:一方面淡化了神或“天命”的支配力,回到了“人自己”;另一方面是,这个“人自己”没有被理性分解与改变过,也没有被信仰异化为偶像的原来样态。它是如王庆节所说的“原初生命”。而确保人得以保持原来样态、原初生命状况的,便是孔子“随时随处随情随事”指点“为仁之道”。依孟子所说,“仁者人也”,“为仁之道”即是“为人之道”。“随时随处”,为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随情”,即情感的当下呈现与流出,未被理性分梳过;“随事”,指任何各别行事,未作“类”的归纳与抽取。语录体的文字记述正体现了“随时随处随情随事”的指点方式。唯“随时随处随情随事”指点“为人之道”,才能确保未被理性分解与改变、未被作为信仰偶像升华,而得以保持其“原人”状态。
孔子“随时随处随情随事”指点“为仁(人)之道”,在《论语》中比比皆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孔子这些不同的提法,都是针对不同个人不同情景说出来的。孔子没有区分事物的类层关系,“有教无类”。学界也有一种说法,孔子连“类”的概念都没有,《论语》所记的都是一些散殊的经验材料,怎么可以称得上哲学家?他们认为,哲学的构造,必须满足先验性、普遍性品格。但恰恰是保持了“原情”“原事”“原人”,未被知识理性分解过的本然状态,最能满足先验性品格。孔子生活于春秋时期,还未被抛落于“百家争鸣”的混乱局面,未开始作知识的理性建构,正是他的幸运。通过抽取共同性的知识建构,无法摆脱经验性;而一旦抽空所有内容,从“无”给出的先验性又只会远离世间生活。
然而,“原人”是生活在世间中的,不可能不与世间现实相遇。既然会与现实相遇,“原情”“原事”及其体现的“原人”又岂能不被改变?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庄子甚至太息“道术将为天下裂”,后世的人们,再也无法见到“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这是“战国时代”,在理论建构上也被称为“百家争鸣”的时代。
用概念的递变来描述这个时代诱发的思想变迁,也可以说:“原人”失去了“原”义而坠落为各别个人—功利个体;“原情”失去“原”样而演化为追逐功利的心智与术数;“原事”失去“原”状而退变为心智与术数捕捉的认知对象,被指为“物”。
尔后,道家开启了形上学建构,通过抽离充满矛盾的现实世间,把现实世间的利益纷争“无”化,而求取安身立命之道。孔子的后继者不然。他们坚持不离世间,把孔子原在世间中引申而出的信念往两个向度予以展开:孟子把孔子价值理想的一面推高,将孔子塑造为圣人,以便从道德示范的意义上引领世间;荀子则把孔子不离现实的一面启动,建构起理性认知体系,企求从道德规范的角度驾驭世界。
然而,在战国的“大争之世”,人与人间的关系为利欲争夺撕裂了。孔子的理想追求,孟子的性善论和大丈夫的人格示范,只被作为不切实际的东西弃去了。荀子直面“大争之世”的客观现实,暴露人性的阴暗面而拒斥孟子的“性善论”,主“性恶论”,更能为世间接纳。荀子的“性恶论”传给了韩非子,韩非子便张扬为严刑峻法的治国理论。
秦王朝统一中国,是韩非子集大成的法家思想的胜利;秦帝国立国15年即大厦倾覆,亦是韩非子完整建构的法家路线的失败。而新建的汉朝皇帝刘邦没有想到自己一个布衣出身的人竟然坐拥天下。于是,“天”“天命”的观念又重新为人们所认信。其体现的正是社会的正义诉求。这种正义诉求,在人的范围内,特别是人性被认为“恶”的状况下,无法给出。正义诉求超越人与人的现实利益纷争与理性谋划,价值信仰再次走进哲学的视域。但是与孟子有别:孟子高扬的价值信仰是人—主体的自我认定。入汉以后,孔子所提倡的价值信仰有了宇宙论作为存在论支撑。
二
孔子倡设的价值信仰,被引入宇宙论作为存在论的支撑,有一个过程。在孔子那里,人道与天命是分立的。来到孟子,“天”是从“本心”之“逆觉体证”给出的,是价值实体,而非存在世界。及《中庸》,从“天命”下贯论“性”,才开始涉及存在世界的问题,但也并未真正开出气化宇宙论。真正开出气化宇宙论的为《易传》,只是《易传》未及五行,缺失五行作为空间的维度。引入“五行”与“四时”,以“气”作为原初生命力,分阴分阳而在时间空间交变的节律中化生万物的,为黄老思潮。把黄老思潮的天地宇宙观引入儒家,使儒家脉络的宇宙论有了更系统的建构是董仲舒。
董仲舒称:“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这就把宇宙化生元气、阴阳、四时、五行的变迁作了系统化的描画。董仲舒再把仁义礼智信与宇宙时空变迁节律勾连起来,立意在说明,价值信念不仅是人—主体的一种认定,而且是有客观宇宙论支撑的。
但是,这样一来,客观宇宙—存在世界因为具有价值取向,而被灵性化了。这无疑是把孟子作为精神性的价值信仰,借宇宙论导向宗教性信仰。及孔子的形象,在孟子那里,是作为人的典范树立起来的;至汉儒,则被树立为“神”(黑帝)。
正因为董仲舒通过宇宙论把儒家的价值追求导向宗教信仰,近世儒家学者对宇宙论和董仲舒思想多不认同。如牟宗三即称,董仲舒不属儒家;徐复观认定,董仲舒及两汉思想家所说的天人关系,都是通过想象所建立起来的,没有知识的意义;劳思光更说,“两汉期间,支配儒生思想者,非孔孟心性之义,而为混合各种玄虚荒诞因素之宇宙论”。
西方汉学家们则常常取宗教人类学视野。如普鸣所撰《成神——早期中国的宇宙论、祭祀与自我神化》一书,几乎把中国古典文献中“天”“一”“太一”“元气”等概念,都解读为具有灵性的“神”,古典宇宙论讲求人与天地宇宙的关联是为了使人获得神力而成神。从普鸣的论说也可以看到西方学界对中国古典宇宙论研究存在误区。
在中国历史上,宇宙论对中国人的认知方式、思想信仰影响巨大,如果未能作出确切的分析与评价,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的独特传统。我的看法是:其一,汉唐宇宙论是基于对天地万物及其变迁节律的了解建构起来的,它有认知的价值,不可以简单地指认为神学信仰;其二,宇宙论对社会管治与社会历史的影响,就其强调的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观念而言,守护着自然世界的生命—生态本色,具有独特的价值,不应当贬斥为落后的;其三,由宇宙论导向神灵信仰,源自人对天地宇宙—自然世界的变迁节律的敬畏与感恩,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人格神崇拜。
三
诚然,汉唐盛行的宇宙论致力于生命的守护与探索,虽有认识论的基础,但也不能说没有缺失。从宋儒的视角看:首先,宇宙论终究不免导向神学信仰,此为理性所无法接纳;其次,宇宙论以“气”为生命本源,“气”化既兼及精神,也兼及身体,身体的欲望诉求亦必影响精神价值的提升,而且气禀之不齐又得认允个性差异。有鉴于此,宋儒重新回到以形式建构为特征的理性路向。形式建构通过贬斥各别个体事物,给出不同于以生化过程及其节律为捕捉对象的宇宙论,这种借区分普遍与特殊、共相与殊相的分析方法建构起来的理论,用冯友兰先生的划分标准,称之为本体论。
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必须说明的是,宋朝前期,作为宋明儒学开创者的周敦颐、张载,还持守着气化宇宙论,用以拒斥佛、道二家的“空”“无”观。程颐、朱熹二子直接认定,“气”是“生物之具”,为形而下者;“理”才是“生物之本”,为形而上者。“理”之所以得以成为“形而上之道”,乃因为对于各别之物事而言,它具公共性;对于有生有灭的物事而言,它有稳定不变性。追求公共划一性、稳定不变性,构成为程朱“理”本论的论说宗旨。
原先,孔子、孟子是以“圣人”的示范作用引领人们向上的;汉唐儒生以董仲舒为代表,引入宇宙论为价值追求,给出了存在论依据,更把价值意识上的圣人装点为神人。但是,圣人、神人的影响力都有取于信仰,不一定为人人所认同,唯诉诸公共划一、稳定不变的“道”或“理”,才具规范的意义。可以说,由先秦—汉唐儒学,向程朱为代表的宋元儒学的变迁,是从示范伦理(圣人与神人)向规范伦理(天理)的转变。
就在朱熹把“理”本论推向顶峰之时,陆九渊已与其抗辩,公然宣称“心即理”,把“理”收归于“心”的认信。来到明中期的王阳明,不仅主“心即理”,而且明确指认仁义礼智作为价值之理,是心“自然”生发的:“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这里的“自然”“不假外求”即指孝弟仁爱等价值之理的先验性。何以见得价值之理具有先验性?因为它源自情感。阳明这里显然回到了孔子、孟子,通过重新激活情感心使价值信念获得先验性,并借先验性凸显其绝对性。阳明“知行合一”说揭明,认知给出的“实然”世界无法开出价值的“应然”追求。阳明特别强调“行”必须见之于“事”上,这也有似于孔子、孟子,在随时随处的“行事”上指点与见证“为仁(人)之道”。
如果说,朱熹立足于认知理性上对一般与个别、共相与殊相的区分,通过把一般、共相确认为“道”或“理”,并把价值信念置入“道”或“理”中,去求取价值的普遍有效性,或可以被认同;但朱子并不满足,还力图让作为共相的这些价值成为“天理”而使之获得先验绝对意义,这就成为问题,因为先验绝对性属于信仰范畴。阳明认“心即理”,通过废去认知理性而回到情感,从情感的自然—本然性,确认价值信念的先验绝对性而得以守护价值的信仰性。然而,由本心认取的信仰,其实是具个人性的。阳明很有担当,又一定要赋予它普遍意义。他晚年提出的“致良知”说显示了这种担当精神,可惜其目标并未实现。
四
儒学发展至程朱的“理”本论与陆王的“心”本论,在经验与先验、普遍性与绝对性、理性与信仰之间,经常纠缠在一起。哲学下来的努力是把它们分开,使各自得以相对独立地言说,由是有泰州学派和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构建。
泰州学的开创者为王艮,阳明晚年一个特立独行的学生。阳明去世后,自立门户,弟子多为平民,但他和弟子们的思想,在明末很有影响。王艮提出的最受人们关注的命题是:即事是道。这是直接指“事”本身即“道”。
何为“事”?王艮称:“百姓日用是道。”这是特别指世间日常生活种种需求为“道”为“理”。朱子、阳明论“道”说“理”,只为强化价值理想。王艮却用于认肯与提升平庸的生活世界。再,谁去做“事”?是一个个的人。一个个的人是带着身体去做“事”,去谋划的,故王艮又有“尊身”之论,他直认“身”是“天地万物之本”。朱子、阳明都以为“身”是使人追求利欲、诱人堕落的根源。王艮却以“身”为“道”,有“身体”才有“个体自我”,故泰州王艮在儒家脉络中最是凸显个体自我。
王艮开创的泰州学借指“事”为“道”回落生活世界,借认“身”为“道”回归个体自我,在明末深深影响了文艺界。徐渭、汤显祖、冯梦龙、公安三袁,纷纷应和。泰州学派指“事”为“道”,实际建立了“事”的本体论。“事”本论全幅认肯世间日常生活。世间日常生活的活泼性源于情感的流动性,所以“事”本论又即“情”本论。
当今,我们看到,人们借认知能力的拓展,往形式化、符号化的方向越走越远,人类抛离真实的感性生活,越来越漂游于虚拟世界中。泰州学回归“事”本论、“情”本论的价值诉求,面对当今世界,也许有特别的提示意义!
泰州学的“情”本论、“事”本论,把日常具体各别的情感生活与凡俗追求指之为“道”,即赋予一种先验绝对意义,属信仰范畴。但具体各别的情感生活与凡俗追求,其行进其实现,毕竟离不开不同个体之间的交往和交往所需的规则。只是,这些交往规则不可以再视之为绝对至上的,它应该从经验中给出。应和哲学视域转变的这一需要,于是有清初中时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代表人物为王夫之、方以智、黄宗羲、颜元、李塨、戴震等学人。
所谓“经世致用”,“世”指经验世界,“用”为经验操作。这一思潮是以回落经验世间、建构经验知识,以支配经验世界为的矢。王夫之首先就明确认定,经验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可以从经验操作的效用性确认世界的真实性。那么,真实的世界是怎样存在的?王夫之恢复了“气”的本源地位,明确宣称“理”是“气”之“理”。王夫之进而从共殊关系否弃朱子的“理”本论。朱子讲共殊二分,以共相具普遍性、稳定性而指认“共相”之“道”或“理”为本体。王夫之却以作为殊相的“器”具有先在性,还原自然世界的客观性。尔后论“性”与“欲”。首先,王夫之不认同“性善论”与“天命之性”说。他指出,“道”是涵盖万有的,“性”只涉及部分内容,而“善”指涉人类的部分行为,三个概念外延与内涵均有大小之别,以为“善”即是“道”、“性”即是“善”,在认知上是不成立的。其次,王夫之又不认同“性”的一次性圆成。他称,自然生理有一成长过程,绝无一次性赋予人在品格上的圆成与自足。而且王夫之以为人所受的自然禀赋并不是“德性”而是情欲。王夫之把圣人也从神坛上拽下来,圣人和普通人,一气化生,便自有身体有欲求。“一气化生”,为“天理”,具正当性;由一气化生而有欲求,自亦为“天理”,具足正当性。朱子、阳明同主“存天理,灭人欲”,王夫之则将之翻转过来了。
戴震之学,无疑是王夫之等学人所营造的“经世致用”思潮的拓展。戴子指出,程朱陆王的形上形下之分,指“理”或“心”为形上本体,并以复性之初为精神追求,以“敬”“静”为功夫路径,其实都从老释中来,他们是援儒入于老释,把儒家老释化了。戴子借批评从老释到宋明诸儒的形上形下二分,而回落到现实经验世界中来。
“理”作为经验之操作,如何实施?黄宗羲作出了探索。黄宗羲不仅认为人的情欲诉求具有正当性,而且直接揭明:“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人各自利也。”正因为从有人类以来,人在本性上是自私自利的。后来之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宗羲把君权统治神圣性的面纱撩开了。当然,面对凡俗世间人心的险恶,亦不可以没有公共行政安排。他认为,君主世袭,无法选择;丞相却可以选择,有贤明的丞相治国可使治国设施不至于太偏失。不过,宗羲称,“必使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这是赋予学校以议政、立法、监督等多种权力。分权的政治架构出自凡俗世间利益切割的需要,但宗羲却把议政、立法与监督等职能留给了学校,为的是让沉溺于权力争夺的社会,还保留有一点“诗书宽大之气”,持守若干人文关怀。
结语
来到现代,“诗书宽大之气”,还能够保住吗?我们看当今社会,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地区与地区、国与国之间的争夺如此激烈,便不难感觉到,人往功利化,理智往工具化、权术化的方向越走越远了。
如果人类还需要救赎,那么,我们仍然不得不回到儒家,回到孔子。我们说回到孔子,并不以为孔子完全看不到人世间丑恶的一面,而是说,孔子面对现实,绝不以为现实的恶变无可拯救。孔子与孔子开启的儒学取向,在面对现实的恶变时,总是致力于守护美好的东西,用美好的东西来培育每个个人的心灵,建构美好的世界。
那么,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亲亲之情、恻隐之心。这是每个个人自然—本然具足的,即所谓“原情”。至于“随时随处指点”,就是把个人自然—本然具足的这种“原情”唤醒起来,激发出来。我们每个个人依自己的这份“原情”去行“事”,便是“原事”;去做“人”,便是“原人”。孔子期望每个个人做回人自己,有“亲亲之情”“关爱之心”;只要每个个人做回人自己,每个个人便成为仁人,世界便成为美好的世界。孔子致力于建构的价值信仰只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