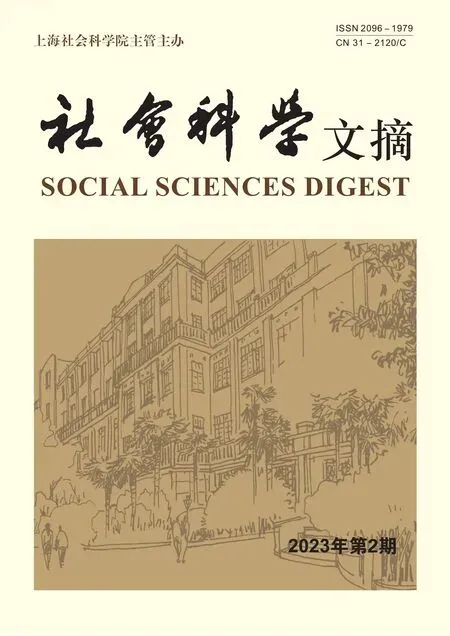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哲学观
——作为批判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政治哲学
文/鲁克俭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消灭哲学。在此之前,从撰写博士论文的这一时期到撰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这一阶段,马克思对哲学都持肯定的态度,甚至把哲学的地位抬得很高(高于实证科学)。马克思早期哲学观在《莱茵报》时期(特别是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一文中)得到集中阐发。通过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哲学观的考察,笔者将马克思早期哲学观界定为政治哲学。
马克思早期思想从观念论哲学观到人本哲学观的演进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对哲学比较集中的论述有三处。第一处是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的笔记五中。第二处是在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第四章(佚失)的“附注(2)”中。这两处论述强调哲学的批判功能,这种批判哲学更多是与政治哲学(或伦理学)而非认识论或形而上学相关。第三处对哲学的集中论述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的笔记七中。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哲学体系之间的联系、语境,还特别强调哲学体系与其历史存在的联系。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关于哲学有一处著名的论述,马克思强调“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此外,马克思又强调哲学是“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那么,何为“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否直接来自黑格尔?马克思确实多次使用过类似黑格尔的“时代精神”的说法,但这里马克思用的是“时代的精华(精神上的)”的说法。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强调哲学是“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与“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说法的含义是接近的,都在强调“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非常强调观念和观念化的作用。尽管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也有对“观念”的负面看法,但总体来看,说马克思此时的哲学观是“观念论”的,应该是没有错的。当然,马克思的观念论不同于黑格尔的观念论。马克思所谓的观念,来自现实世界,是基于对现实的研究和对事物本质的把握。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定位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但马克思所谓的观念,也并不是像鲍威尔那样的纯粹的主体性自我意识。如果说鲍威尔倡导的批判哲学是外在批判(将理想即应然与现实对立起来),马克思的批判哲学则属于内在批判。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还赞扬“国家观念”,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转而严厉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念”,也一并放弃了观念论哲学观(马克思将其称为“逻辑神秘主义”)。马克思像费尔巴哈那样,强调哲学是关于“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的理论(“实证的批判”),而非对“事物现状的超验的、抽象的表现”。马克思也追随费尔巴哈,将“抽象”(观念)与“思辨”画等号。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甚至将“抽象”妖魔化。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马上放弃对哲学的巨大作用和功能的强调。我们可以将马克思此后的哲学观定位为人本哲学观。所谓人本,一是类似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二是强调人的本质,三是与人的解放密切相关。
把哲学与观念画等号,是欧陆哲学自笛卡尔以降的传统,在莱布尼茨那里达到顶峰。不过在海峡对岸,经验主义是英国的哲学传统。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经指出,自霍布斯的机械唯物主义开始,“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唯物主义自我意识哲学”,本质上是霍布斯社会契约论传统下的原子论政治哲学。个人作为现代社会的“原子”,恰如孤岛上的“鲁滨逊”,他是具有高度主体性和自主性的独立个人,同时也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单向度的人”的异化现象,倡导“丰富的人(即总体的人)”。《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正处于从自由主义到哲学共产主义的转变之中,即处于共和主义时期。共和主义就意味着人本主义因素的增加,以及自由主义冰冷因素的“褪色”。而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自由主义,是具有浓厚德国观念论色彩的自由主义。因此,马克思从博士论文时期的自由主义到《莱茵报》时期的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转变,伴随着马克思从观念论哲学观到人本哲学观的转变。这种人本哲学观在《莱茵报》时期就具体体现为马克思基于内在批判的批判哲学和国家哲学,而基于人本哲学观的马克思人本主义(或译为“人道主义”)哲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达到顶峰。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并没有放弃哲学,不过他反对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倡导旨在“改造世界”的哲学。不能从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意义上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哲学称作实践哲学。《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哲学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即作为心脏之“大脑”的哲学,也就是共产主义政治哲学。不过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已经把共产主义理论和学说看作实证科学,而不再是哲学(政治哲学)。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批判哲学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哲学观是观念论的内在批判。所谓内在批判,就是有别于外在批判的批判。从采什科夫斯基的《历史哲学导论》开始,青年黑格尔派就采取了“批判”的哲学姿态和对现实进行无情批判的政治立场,鲍威尔甚至明确退回到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哲学。与“唯物主义自我意识”哲学相对应,马克思持一种“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立场,而鲍威尔的批判哲学是“批判的唯心主义”。“批判的唯心主义”是外在批判,“批判的实证主义”是内在批判。
马克思内在批判的核心是所谓的“本质主义”。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被看作本质主义者。但马克思的本质主义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而非黑格尔。在黑格尔那里,本质先于现象,先于实存,这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与现实的关系。因此黑格尔与柏拉图都属于实在论者。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既然是本质主义者,当然不属于唯名论者。但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属于温和的实在论者(介于唯名论和极端实在论之间)。亚里士多德强调个体实体,而马克思强调事物本身是出发点,本质属于第二实体或事物的本质规定性。
马克思主张“遵循事物的本质并且决不满足于该本质的纯粹抽象的规定”,反对用“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马克思承认事物的存在(实存)不一定与本质(概念)相符合。与此相应,马克思把本质与假象(现象)对立起来。透过假象(现象)把握到的本质,就是理性概念。于是就有自由报刊的本质、人的本质、法的本质(概念)、国家的本质(概念)、婚姻的本质(概念)。马克思依据这些本质(概念),来审视和批判现实事物(实存)的不合理性。这种批判是内在批判,即基于事物内在理性的批判,是对偏离本质(概念)的实存的批判。
需要指出的是,从内在理路上讲,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有意识地进一步强化了博士论文中已经形成的自己的“逻辑学”,并据此对现实问题进行内在批判。从内容来看,马克思关于法的本质、国家的本质的界定,确实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有一定的继承。因此,从表面上看,马克思这一时期仍然是遵循黑格尔的逻辑学,处于黑格尔国家观的影响之下。这也是长期以来国内外马克思研究学界的普遍看法。不过,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虽然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国家哲学总体来看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但也开始偏离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
《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马克思放弃了内在批判,也淡化了自己的本质主义立场,但他并没有放弃本质主义。特别是随着1857—1858年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马克思重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和“人体解剖方法”(与此相关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加以完善的典型化方法),马克思唯物主义实在论的本质主义再次登场。在马克思那里,“价值”不仅仅是“价格”背后的“本质”,“价值”也不仅仅是作为认识抽象产物的概念(即唯名论的概念),而且是一种客观实在(实体),是“现实抽象”。这是唯物主义实在论的本质主义,有别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以“果实”为例,对“思辨建构的秘密”的批判所体现的唯物主义唯名论立场。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国家哲学
表面上看,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强调国家代表自由、理性、普遍、必然性,这与黑格尔是一致的。马克思还指出,契约论理论家和现代哲学家“构想(建构)国家(概念)”具有不同的进路:前者基于个人理论,后者基于社会理性。这与黑格尔也是一致的。但马克思的国家思想中也有不少黑格尔国家哲学所不具备的新内容。
第一,马克思关于国家概念的具体内容有别于黑格尔。同样是代表自由、理性、普遍、必然性,黑格尔的国家是立宪君主制国家,《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国家已经转向作为法国大革命结果的共和国。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给卢格的书信中曾提到要写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其批判的并不是代表自由、理性、普遍、必然性的国家概念,而是黑格尔的立宪君主制。马克思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则转向对代表自由、理性、普遍、必然性的国家观的批判。因此,《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设想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有本质区别,代表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即从国家崇拜到批判国家本身)。
第二,马克思明确区分现实的国家与国家概念。马克思有时用“国家本身”“真正的国家”来指代国家概念。与此相应的是国家与政府的区分。现实的国家对应于政府。而黑格尔的“现实的国家”是国家概念的实现。马克思的“现实的国家”相当于黑格尔的“不真的国家”,即与国家概念不符的实存的国家。马克思以国家概念为标准来对现实国家(政府,特别是官僚系统)进行批判。
第三,马克思提出“国家生活”的概念,并将其与“非国家的生活领域”相对立。国家生活指的是国家的“精神领地”,马克思强调国家是“自然的精神王国”。而“非国家的生活领域”指的是市民社会领域。
第四,马克思提出“国家权利”概念,并将其与“私人权利”相对立。在黑格尔那里,利益、需要都与市民社会有关,处于人的自由发展的特殊性阶段。国家是自由的实现,而自由正在于摆脱了利益的纠缠。马克思则直接把利益、需要从特殊性推广到普遍性,将其赋予国家概念。这显然是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引申,同时也是对黑格尔的偏离。将普遍利益、普遍需要赋予国家,就为马克思最终走向否定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一旦马克思意识到国家从来不可能真正代表普遍利益和普遍需要的时候,对国家本身的质疑就顺理成章了。而黑格尔的抽空了具体内容的国家普遍性,就不存在这样的风险。
第五,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属于对抗性关系。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是个人自由发展的一个阶段,即特殊性阶段。国家并不是对市民社会的完全否定,而是将市民社会包含在自身之内。因此国家普遍性不是抽象普遍性,而是包含特殊性的具体普遍性。国家会抑制市民社会的负面效应,具有纠偏效应,但国家与市民社会不是对抗性关系,国家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和理性的结果。而马克思强调,特殊利益企图窃取(垄断)国家。显然,将国家与市民社会定位为对抗性关系,使马克思更接近契约论理论家(特别是洛克)的国家理论。只不过洛克的国家理论将个体的特殊利益看作目的,将国家看作手段,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将国家看作目的,因为国家代表普遍的善。
第六,马克思强调人民报刊(而非官僚)是联结特殊与普遍的中介,黑格尔则完全反对出版自由。马克思对人民报刊作用的强调,应该是受到费希特的影响。更一般地说,在黑格尔那里只有思想自由、市民社会的财产自由,以及最终人在国家中的自由。而政治自由却是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大力强调的,是马克思国家哲学的重要内容。
第七,马克思强调人民概念。《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口中的“人民”不是无产阶级,但也不是黑格尔所说的“贱民”。人民概念在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哲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民代表着社会的弱势群体,马克思同时又赋予其“普遍性”化身的角色。人民与市民、公民的关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理论难题(包括弱势群体何以自动成为普遍性的化身),显然尚未引起马克思的足够关注。我们只能以马克思同情弱势群体的价值立场,以及马克思此一时期的共和主义政治立场(其要旨是对利己主义的否定和批判),来解释这种明显的理论跳跃和不严谨。这一问题也预示着马克思必然要走向理论的彻底性:要么退回到博士论文时期的自由主义,要么前进到共产主义,共和主义只能是短暂的思想过渡。
结语
总体来看,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哲学观的主基调是政治哲学。除了批判哲学和国家哲学,马克思还强调“哲学是阐明人权的”。这种哲学观显然接近自霍布斯以降的现代政治哲学传统。如果说马克思早期有关于建构“逻辑学”的设想,就此进一步断言马克思早期有政治哲学之外的哲学抱负,则是缺乏文本依据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否是“哲学”,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但对马克思来说,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哲学就不存在了。科学共产主义仍然具有伦理维度,但它已经不再是哲学(包括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