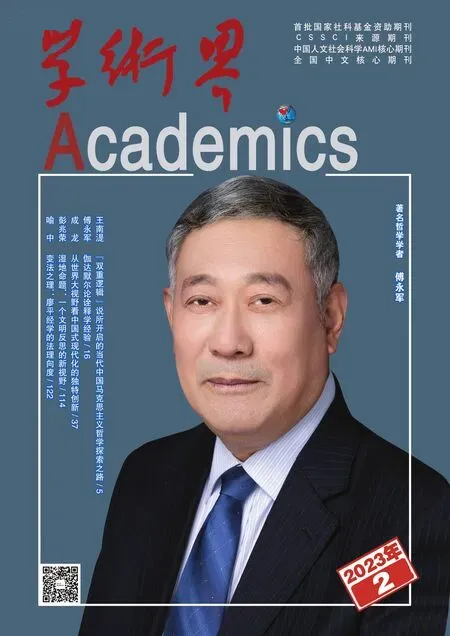新时代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国际化建构
沈正赋
(安徽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因长期集聚、栖居地生活和工作在一起,自然会在一定的领域内逐渐形成各自的话语及彼此能够认同和接受的话语表达方式与叙事体系,这样在全球的不同地区、群落或组织的“圈层”里,可能就会衍生出不同的话语及其叙事体系。从社会交往、信息交流的逻辑出发,如果要打破这种内部固有的“圈层化”结构,走向和融入到更加开放的社会新形态和新格局,那么重构话语及其叙事体系就变成对外传播的“必选项”。在世界舞台上,中国作为拥有十四亿多人口和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与发展,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其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在长期的社会交往实践中,中国话语及其中国叙事体系早已形成并逐渐定为一尊,成为中国人在国内话语场域进行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与遵循的基本规则。然而,在面向新时代国际传播的风口时,中国话语及其中国叙事体系就难免会存在一些不适应国际化发展进程的阻碍和困难,甚至在国际传播中可能会陷入到一种困境或窘境之中。因此,顺应全球化和时代化的发展节奏,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及其中国叙事体系,就成为中国“走出去”“走进去”、加强和推进国际传播工作必须要科学回答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在迈向国际化和推进史无前例的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征程中,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加强与世界各国交往与交流的重要砝码与筹码。况且,在大国之间的竞争中,不仅有“硬实力”的博弈还有“软实力”的比拼,面对作为文化软实力的西方强势话语的咄咄逼人和步步逼近,中国话语及其中国叙事体系亟待从这种“他塑”的格局中实现突围,凭借“自塑”的中国话语立场出现在国际社会的话语场域。因此,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构建中国话语及其中国叙事体系,就理应成为新时代我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发展目标和核心竞争力。
一、“话语”与“叙事体系”的理论溯源
话语是叙事的基础和前提,话语需要通过叙事的方式才能实现其表达的功能。话语不仅是对事实或信息的一种简约化、符号化表述,而且还能够传达和表达行为主体对事物的认知态度、观点与意见,实现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密切勾连和有机契合,因而具有一定的建构空间和现实意义。叙事体系又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言语系统,相关联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因素也多元化,建构的层次和框架则呈现出较为缜密的逻辑性和规制性。从理论的源头上来梳理,话语和叙事体系是源于西方学界的概念和术语。
(一)作为理念的“话语”。西方从语言学的角度最早提出“话语”概念的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他认为,人们在日常表达中运用“语言”这种符号所发生的“话语”应称为“言语”,“语言”和“言语”是话语的两种表现形态。语言不是简单化映现对象世界和自然实在的一面镜子,而是构建人们所认知的自然实在的材料和规则系统,语言的功能是构建而不是映现。这实际上是对“话语”的功能和价值所作的一种分析。此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叙事学等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学者们,相继对“话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理性阐发。
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语言与言语的结合可以生成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话语是指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纠缠的具体言语方式,它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诸要素。福柯对话语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将话语理论进一步运用到社会学领域,用它去说明语言使用的社会规则和社会情境,去发现言语之外的一切生活中的规范形式。他认为,话语既是它已经说出的东西,也“是它没有说出的东西的逼迫出场,而这个没有说出的东西又是从全部销蚀所有已说出的东西的空洞”。〔2〕
受福柯的影响,一批话语理论研究者开始研究语言对社会现实、社会身份以及社会过程的建构作用。其中,美国语言学家帕克(Kenneth L.Pike)认为,“话语是社会文化语境下互动过程的产物。”〔3〕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首席教授詹姆斯·鲍尔·吉(James Paul Gee)认为,语言带有政治性,在使用中处处能够透露出人们的社会身份、政治态度等,“语言细节反映社会行为、身份和政治”,〔4〕“创造和建构了我们周围的行为和世界”。〔5〕
美国著名哲学家艾莉森·利·布朗(Alison Leigh Brown)认为,话语是“一种调控权力统治的规则系统”,〔6〕话语的功能是“产生真理”。〔7〕美国布朗大学教授迈克尔·夏皮罗(Michael Shapiro)认为,话语是“隐藏于人们意识中的深层逻辑,它在黑暗中控制语言表达、思维以及所有不同群体的行为标准,它是某种认知领域和认知活动的一种语言表达”,是“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话语深处的意义根植于人类劳动、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8〕
在叙事学领域中,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叙事学理论奠基者之一的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首先提出“话语”的概念。他认为,话语是超出句子的统一体,是“叙事内容外在表现的综合”,〔9〕其研究对象是“在内容和结构上构成一个整体的言谈或文字”,包括整篇文章或整篇作品。叙事学学者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仅仅研究文本语言是不够的,还要关注句子的上下文或语境,因为语境中的话语既包括叙事主体说出的所有话语,还包括以潜在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话语。在叙事话语研究者看来,叙事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言语交际活动,这是他们对话语及其功能认知与论述的共识。
概而言之,西方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流派研究的“话语”,重在对话语的社会性建构功能进行探索,意在挖掘潜藏在话语背后的行为主体的态度、观点及其意识形态,勾连话语与社会现实、社会制度之间的契合关系,阐述话语的语境性发展趋向,呼唤回到语境的知性与理性层面进行学术对话和思考。
(二)“叙事体系”的逻辑结构与功能。在西方语境中,“叙事”是指用话语讲述社会生活事件过程的一种表述方式。叙事不仅仅使用作为文本符号的语言,而且还要使用一套话语体系,特定的话语体系便构成了叙事文本。荷兰当代著名叙述学家米克·巴尔(Mieke Bal)在《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提出的“叙事文本的理论”〔10〕就是所谓的“叙事学”(narratology)。他认为,叙事实践主要包含“谁讲故事”(叙事者)、“什么故事”(文本)、“谁听故事”(接受者)三个基本核心环节。叙事者是叙事实践的主体,文本是叙事实践所依托的客体即内容、框架和材料,接受者是叙事实践的对象,这“三位一体”便构成了叙事学的基本逻辑框架。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西方叙事理论的鼻祖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柏拉图对叙事所提出的“模仿”(mimesis)和“叙事”(diegesis)的“二分说”被公认为“叙事”概念的源起。他认为,“模仿”就是行为主体把自己装扮成另一个行为主体的身份并用其声音讲述故事,而“叙事”则是行为主体用自己的声音直接讲述故事,前者是真正的行为主体处于“缺席”状态,而后者是行为主体即叙事者“在场”,这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讲故事方法。在二者中,柏拉图对“叙事”的价值属性和功能作用予以高度重视和十分认同。他之所以褒扬“叙事”而贬抑“模仿”,是因为在他看来叙事者在叙事实践活动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就是说,作为叙事者的行为主体“在场”与“缺席”是判断叙事实践成功与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参考指标和考量条件。柏拉图对上述两种叙事或称讲故事方法的区分到20世纪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展示”(showing)和“讲述”(telling),“展示”是作为行为主体的叙事者通过自己的思想意识反映外部客观世界,让接受者直接观察所呈现的事物及其物质形态,从而作出接受者自己的主观认知和价值判断;“讲述”则是叙事者用语言把自己的主观感受直接传达给接受者,希冀得到接受者的普遍认同并形成共识。前者是从客观到主观,是事实到观点的逻辑演变;后者是从主观到主观,是从观点到观点的简单传递与思想交换。
亚里士多德主要是从文学叙事的视角来分析和阐述叙事的显性价值与潜在功能。他的著作《诗学》被视为系统阐述西方古典叙事理论的发轫之作,其在《诗学》中首创了“情节”等重要的叙事学概念,并且在《诗学》中一再强调叙事的目的、叙事的艺术观和叙事的接受等三个重要变量。在叙事的选择和舍取上,他提倡以“可能”与“可信”的原则来进行叙事批评,不但要认识到叙事来源于生活,更要考虑它的艺术目的和创作追求。他多次在《诗学》中强调:“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可取。”〔11〕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对于叙事本质的论断显然已包含了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哲学命题。他的理论主张因此被学者理解和解读为:“不但要关注生活的真实,更要提炼叙事作为艺术形式所表现的真实;不但要有叙事艺术的精英意识,也要落实于叙事艺术的大众接受。”〔12〕亚里士多德把现实世界中发生的真实事件与故事中的叙事情节进行适当的“分野”和“割席”处理,并认为叙事永远是一种建构,叙事者可以根据审美的考虑,呈现出经过主观化选择和授意安排的事件的一部分。〔13〕
由此可见,西方语境中的“叙事”虽然关注叙事方式,但更看重叙事者在叙事中的“存在”,文学叙事并不在意文本内容与事实之间的吻合度与匹配度,甚至为实现和达到叙事的张力与致效,不惜将“现实世界”与“文本世界”相剥离,进而让叙事文本游离于现实生活事件之外。
综上所述,无论是作为理念的“话语”还是具有内在逻辑结构与潜在功能的“叙事体系”,它们显然既具有工具的属性,又具有价值的属性。如果仔细揣摩一下,那么我们甚至不难发现,话语的主观性介入以及文学叙事的这种“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辩证处置方式,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方法论上值得新闻传播叙事借鉴与参考。在建构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实践中,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功能与作用,从而为新时代的国际传播工作赋能。
二、新时代中国话语国际化建构的社会语境与行动策略
话语理论虽然源自于西方,但是话语作为一种语言的实践活动一直与人类相伴相随。中国话语在中国历史和社会语境下经过五千多年的涵化、发展和演变早已定型,并且在中国的语言文化环境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方式和叙事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语言交流和传播的形式,荷载着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符号,也是中国从事国际传播与交往的言语工具和国家名片。
(一)新时代中国话语国际化建构的逻辑起点。中国话语理论是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社会语境下由中国学者对话语实践进行高度概括、总结和阐述的结果,是历代中国人话语智慧的结晶。作为人类文化的精神财富和宝贵遗产,西方的话语理论对于建构中国话语的确具有不可否认的观照价值和借鉴意义。然而,我们需要坚持理性思维和辩证认知、思考与价值判断的是,西方学者往往是以西方的话语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和立论基础,进而总结和推演出关于话语和叙事体系的一系列理论学说。这些理论探索虽然有其一定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大多基于西方实践的地方性记述、局部性概括、阶段性总结,是基于人类文明局部实践的理论总结。问题在于,这些理论总结却成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被奉为圭臬的“元话语”和“元叙事”,从而成了无须论证、只需服膺的“真理”。〔14〕这是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在理论上的挑战之所在。因此,如果要对中国话语进行国际化建构,那么就不能简简单单地、盲目地照搬照抄西方的话语理论,片面地向西方话语靠拢,或走完全“西化”的极端化道路,而是要把立足中国语境,主动寻求并建立与国际语境之间接驳、接洽和对话的生成机制,让中国话语在国际传播环境下“重新语境化”作为建构新时代中国话语国际化的逻辑起点。所谓“语境化”,一般是指当一种理论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移置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时,它的研究方法、理论范型、价值取向尤其是批判对象,必须根据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出相应的调整。〔15〕也就是说,在跨国际、跨文化、跨语际的实践进程中,要实现在新的文化空间中的“再语境化”,而不是所谓的“去语境化”。“去语境化”的结果就是迷失或失去本国文化和话语的独特内涵和魅力,及其对外的扩散性价值和功能,不仅无法实现异域文化和话语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共生发展,而且会造成一种文化和话语被另外一种文化和话语无端地、武断地取而代之,这便导致一种文化和话语在国际传播视域中的逐渐消遁与消逝,而这绝不符合任何国别话语国际化与多元化的初衷和目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历来虽被学界称为哲学上的“二律悖反”,但它们又不是“水火不容”“水土不服”类的“死结”和“无解”,全球化理论与实践表明,“球土化”是破解和有效化解这一现实矛盾的重要理论成果和实践路径之一。新时代中国话语国际化建构,既要彰显中国话语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元素和本土化特色,又要将中国话语融入到国际话语的社会语境中,通过适配化、共通性的演绎路径,把普适性和个性化有机结合起来,为解决中国话语国际化建构的现实困难,制定中国话语国际化建构的行动策略与方案,为在世界范围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奠定实践基础,提供理论保障。
(二)中国话语国际化建构的现实困境。在中国的国际传播历史与现实中,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实践上,中国话语国际化建构都存在一定的症结与短板,这是新时代中国话语国际化建构不可回避、也无法绕开的现实困境与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国际传播终端缺失:“有理说不出”。信息生产与传播终端既可以指作为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物质形态主体即媒体本身,也可以指作为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人的主体即新闻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国际传播场域中,中国一直缺乏对外传播的旗舰媒介和新型主流平台等信息载体。国际传播工作长期处于有米无锅、有船无海的尴尬状态和落寞局面,这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大国形象不相适应。中国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实给予的回答是,我们既缺少像美联社、路透社、CNN、BBC以及Facebook、Twitter等这样有全球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国际头部主流媒体或新媒体平台,也缺少像报业大王普利策、政治采访之母法拉奇、驻华战地记者斯诺等国际一流新闻记者与国际舆论领袖。正是由于在国际传播领域长期没有打造和培养出这样“顶流”级的代言媒体和代言人,既做不到“造船出海”,也做不到“借船出海”,填补国际传播终端缺失的空白,使得中国国际化传播一直处于“有理说不出”的被动局面。
其二,国际传播渠道不畅:“说了传不开”。即使有了媒介,如果没有与之相匹配和持续性的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和点击量作保障与配合,那么信息在传播环节也会受到干扰和负面影响并出现不应有的问题,这个问题便表现为媒介的传播渠道受阻,新闻或信息虽然能够及时生产,但是由于传播渠道不畅使得传播乏力,这种传播大多体现为或被诊断为无效传播,信息表征为飘忽不定或漂浮在空中,根本不能及时落地和有效落地,无法根据预期抵达目标受众,相当于有花无果、有名无实、徒有虚名而已。究其原因,大多是因为媒体的传播力、辐射力较小或较弱,信息输出管道狭窄,幅宽度不够,导致信息传播的覆盖面较为局促,从而让整个新闻传播陷入逼仄和窘境之中。此时,疏通传播渠道,打通信息传播的“任督二脉”和排除“最后一公里”障碍,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发生的“肠梗阻”和迟滞现象,可以有效避免或尽量减少传播中的“信息折扣”和“信息耗散”,走出“说了传不开”的歧途与困境。
其三,国际传播效果甚微:“传开叫不响”。传播效果是新闻或信息传播的落脚点和价值体现。逻辑学理论认为,传播媒体和传播渠道是传播效果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其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既具备传播媒体也具备传播渠道,未必就一定能取得令新闻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满意的和预期的传播效果。如果受到种种外在因素的干扰或羁绊,或者某种先天不足因素的局限,那么也会导致媒介的“声量”总体偏小或偏弱的现象发生。国际社会虽然看也看到了、听也听到了,但是缺少必要的感觉和反应,缺乏被关注的力度和社会反响,给人留下类似于“雷声大、雨点小”“广种薄收”“花落无声”“雪落无垠、雁过无痕”的表面与实质之间的传受落差和“亚媒介”与“亚传播”印象。造成这种“传开叫不响”结局的原因,一般是与新闻媒体的权威性、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整体上较小较弱相勾连,中国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力度虽不小,但收效甚微,使得国际传播未能发挥应有的致效作用。
(三)中国话语国际化建构的正当性与行动策略。针对中国话语国际化建构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新时代的中国需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和措施,最大限度地摆脱现实困境和传播迷局,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话语国际化传播与建构的特色路径。
其一,争夺国际传播话语权。话语权是话语得以构建并且为其提供正当性和合法性保护的重要保障与制度屏障。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话语理论,为媒介话语建构提供理论基础。话语权又称文化领导权,媒介话语权或传播话语权是指媒介通过新闻传播对受众所构成的潜在和显在的影响力。国外学者大多将国际传播话语权界定为一种国家权力,强调国家舆论影响他国意志和行动的能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认为,“作为信息载体的话语能够在特定情境下发挥物质权力所不具备的功能,以非威慑方式改变行为主体的决策方向。”〔16〕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维维恩·施密特(Vivien A.Schmidt)将行使国际传播话语权归纳为观念表达、身份塑造和规则建构三个方面。〔17〕国内学者则大多将国际传播话语权定义为通过话语主导国际局势的能力和权力。王江雨认为,国际话语权是一国在国际社会中掌控舆论和影响国际局势发展的能力和权力;〔18〕张新平等将国际传播话语权理解为言说者以语言、文字或其他文化形式为载体,表达利益诉求、引导国际舆论、确立国际标准的能力;〔19〕李朝祥等认为,国际话语权的实质是“权力话语”,是政治操控层面的“显性话语”和文化价值等“隐性话语”的结合体;〔20〕龙钰认为,国际传播话语权是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以争取国家权益和国际地位为目的的话语表达资格和效果体现,是一国话语在国际话语场中的优势显现,是一国话语对国际话语体系的影响力、主导力、支配力。〔21〕一般而言,权力既是行为主体行动的护身符,又是来自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上帝之杖”之授权,拥有传播话语权便意味着行为主体从事国际新闻传播的正当性有了重要依托与合法性外衣。然而,在国际舆论争夺战中,话语权一直掌握在西方人手中,寰球舆论场上“西强东弱”的局面一时难以得到彻底扭转和根本改变,传播话语权是国际舆论斗争制胜的砝码,在这场看不见刀光剑影和硝烟弥漫的舆论战场上,中西方围绕传播话语权的博弈和争夺将长期存在下去。
其二,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中国声音是中国话语的“物质化身”与“精神标识”。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古国和东方泱泱大国,中国人向来以勤劳、勇敢、聪颖、智慧著称于世,并赢得世界的普遍赞誉。无论是我国汉代杰出的外交家、被誉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张骞开拓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还是15世纪初我国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三次东渡扶桑,他们都在国际行程中将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密切与世界的交往与交流,他们走到哪里就把中国的声音传播到哪里,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在走向国际化的征程中从来都不缺乏中国人的身影和声音。只是后来始于明朝、结束于清朝末年的闭关锁国政策的长期推行,严格限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使得曾经一度辉煌、傲然于世的东方大国顿然失去了与世界的正常交往与联系,整体国力及发展步伐慢慢地落后于世界并逐渐沦为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洼地”。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进入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再次打开了通往繁华世界的大门,拥抱世界,融入世界。社会现实表明,世界发展需要中国,中国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在国际化的赛道上,中国声音再度被激发和次第响起。然而,由于经济上的贫穷和文化上的落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实力较为低下,在国际舞台上“大音希声”。随着新世纪、新时代的翩然而至,中国已大踏步迈入到经济和文化大国的第一方阵,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衔作用和主导地位日益凸显,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不仅成为国人之所愿,而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之所盼。因此,建构中国话语、传播中国声音就不仅是现实诉求,而且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其三,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话语需要通过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等中国化名片彰显出来,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就成为中国话语的具象化表征。在国际传播中,向世界提供中国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代表中国、正名中国和责任中国是中国话语建构的出发点和价值取向。在中国话语的国际化建构中,具有鲜明中国元素和浓郁中国特色的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是中国话语的主要建设指标和精神内涵。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22〕由此可见,用中国话语主动向世界说明和阐述中国道理是新时代中国话语国际化建构面临的重要任务,中国道理蕴含在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之中,是中国解决自身问题和公正公平处理国际问题的基本方法与根本遵循。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我们要依托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生动实践及其取得的丰富经验和成就,全方位地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进而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贡献中国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三、新时代中国叙事体系国际化建构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在人类社会交往和交流的历史与实践中,叙事是人类社会共建、共通、共享信息的一种行为方式之一,叙事究其本质来说是叙述言说,世界范围内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人们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叙事,在讲述发生在自己生活或视野中的故事,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符合自己认知、理解和评价的叙事体系。叙事体系一般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即叙事逻辑、叙事文本、叙事技巧。新时代中国叙事体系国际化建构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体现在叙事逻辑、叙事文本、叙事技巧的建构等三个方面。
(一)新时代中国叙事体系国际化建构的叙事逻辑。叙事逻辑构建的是“道”,属于叙事体系的内核,它主要探索和解决的是“为什么”(Why)的问题。逻辑泛指规律,一般包括思维规律和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是不随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而思维规律则是客观规律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属于主观范畴的对象物,是思维对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势的主观化理解、阐释与再现。客观规律和思维规律的一致性可以在认识与实践中实现并逐步达成。就叙事而言,遵循叙事逻辑是增强话语叙事说服力和可接受性的重要前提条件。逻辑的两个要件中,一是事实最具有说服力,二是观点和结论要力求以理服人,遵循叙事逻辑最起码能够做到自圆其说,让受众认可并接受假设与结论的统一性和合规律性。那种纯粹的自我炫耀、观点先行、强词夺理之类的简单化、粗暴式叙事自然难以令人信服和服众,其结果只能变成自说自话式的拙劣化表演和自我娱乐式的虚妄化满足。国内有专家认为,“构建中国叙事体系,我们不缺精彩的叙事文本,也在逐步学习和借鉴优秀的叙事技巧,但最需要下大气力构建的就是叙事逻辑,我们的任务是努力构建具有共同价值基础、能被广泛接受的叙事逻辑。”〔23〕其中,“共同价值基础”和“广泛接受”是建构叙事体系的基本逻辑参数和自变量,“共同价值基础”既包括客观的新闻事实本身,也包括主观的彼此认同的价值观。柏拉图后期的叙事体系框架理论,就是将叙事分为“展示”和“讲述”两个层面或阶段,主张在客观“展示”的基础上进行主观“讲述”;亚里士多德的叙事体系框架理论,则是以“可能”与“可信”的原则来强化并彰显叙事艺术问题,为了获得大众接受的终极效果,可以适当以“情节”原生态和真实性的部分被遮蔽和被虚化为代价。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叙事体系在国际化过程中,其叙事逻辑要考虑到两个因素:一是坚持事实胜于雄辩的人类社会基本认知逻辑和行事法则,及时、准确、全面地向国际社会客观披露和展示事件的事实真相,尤其是那些令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所谓民主问题和人权问题,在不可辩驳的事实面前,让那些持有意识形态偏见、戴着有色眼镜、不怀善意、恶意污蔑中国的少数国际敌对势力和反华分子,对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突发事件或事端进行大肆渲染和造谣惑众的不实之词、欲加之罪现出原形,失去在国际传播场域生存和发酵的土壤与条件,而此时的中国对外传播媒体如果仍然处于缺席、沉默和失声的状态,则会丧失主动向国际社会进行叙事的契机;二是把“陈情”与“说理”有机结合起来,既要摆事实,又要讲道理。在国际外交场域,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中国,坚信“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解决国际上的事情,不能任凭少数大国从自己所谓“实力地位”出发,推行霸权、霸道、霸凌,而是始终站在公平、公正和道义一边,主持和伸张着社会公道与正义。循此规制,在国际传播和话语体系建构中,我们仅仅停留在“陈情”的地步往往是不够,还要善于“说理”,在世界大国交往的丛林法则中,要敢于和善于同强大的对手进行面对面的交锋与较量,针锋相对,据理力争,该表态时要旗帜鲜明地亮明中国态度,该批评时要毫不客气地宣示中国立场,进而不断建构中国叙事体系国际化的叙事逻辑。
(二)新时代中国叙事体系国际化建构的叙事文本。叙事文本呈现的是“事”,属于叙事体系的骨架,它主要探索和解决的是“讲什么”(What)的问题。叙事文本实际上就是指叙事内容和叙事对应物,新时代中国叙事体系国际化建构的叙事文本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以及中国故事背后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24〕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是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核心内容,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中国叙事体系构建的标识性符号。叙事形塑了人们感知世界、认知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要求,就是为了满足国际社会对新时代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的理解诉求,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建构国际化叙事体系的思路。叙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讲故事”,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的叙事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世界不同文明的历史渊源、现实根基和发展脉络。中国国家叙事与叙事体系构建和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有着紧密的联系。叙事体系构建和讲好中国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抽象和具象、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叙事体系强调概念、范畴、表述等表达方式的构建,讲好中国故事强调具体事件的叙事和论理创新。叙事体系构建属于上层建筑的顶层设计,强调以何种逻辑思维展开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是具体执行环节,强调以何种逻辑思路做好内容的国际传播。中国叙事体系构建离不开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也必须以中国叙事体系构建为指引。〔25〕
“就国际传播而言,文化要素既是存量故事的润滑剂,也是增量故事的内容源。”〔26〕中华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凝聚的中国哲学思想是中国构建国际化叙事体系的主要文本和蓝本。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27〕当然,不同历史时期由于面临的任务不同,我们往往会有阶段性不同的叙事文本。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叙事文本就经历了诸如中国梦、一带一路、脱贫攻坚、小康社会、乡村振兴、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八项规定、反腐倡廉、刀刃向内、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人民为中心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理念及其相对应的不同内涵的文本,到如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自我革命等一系列新概念新表述新思想,是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中国大地进行艰苦奋斗与不懈探索的理论成果和行动指南,闪烁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光辉,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深刻的精神实质与特质禀赋,不仅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与成就,也是世界文明进步的经验与成就,值得国际社会一起进行参考与借鉴、共享与分享,这些无疑都是我们对外阐述中国理念、中国精神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文本。比如讲到“自我革命”自然就要讲述建党初期关于“民主”的故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局和民主人士的疑问,提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8〕这两个答案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叙事文本,其中都有值得讲述的中国现代和当代故事。讲到“中国式现代化”,就要善于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国情故事”这些关键故事,进而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成长、内涵式成长、实践性成长和理论性成长,为我们对外讲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提供了维度清晰的话语叙事框架。
(三)新时代中国叙事体系国际化建构的叙事技巧。叙事技巧追求的是“术”,属于叙事体系的表层,它主要探索和解决的是“怎么讲”(How)的问题。国内有专家认为,“叙事‘文本’是否有效,是否能与文本的接受者形成心理上的契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叙述者采取何种叙事策略。”〔29〕
其一,遵循客观和理性的主流叙事方法。虽然中国叙事是一种典型的大文化叙事模式,西方则是以形式和结构的“数学化”分析为特征的西方现代叙事模式,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叙事模式,秉持客观、理性的叙事都是东西方世界普遍能够接受的叙事方法,而且这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认知共识和共同的价值取向。西方社会虽然早就形成了自己头脑中所谓的“中国叙事”,但是他们眼中这种“中国叙事”的意识形态色彩很浓,不能客观理性地叙述中国和看待中国。现在我们需要确立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叙事,并影响外部世界的中国叙事。特别是当“西方话语”已形成一整套污名化中国的主流叙事时,我们需要解构这种话语和叙事体系,根据“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话语”的中国化现实语境,建构起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善于和勇于对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进行的“虚假叙事”予以揭露,尤其在新媒体时代,要适应数字化、全媒体发展的趋势,借助于各级各类新媒体平台,让真相在全世界传得更广,让谎言无处遁形。
其二,倡导基于人类道德与良知的共情叙事。在全球传播中,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能够获得国际认同才是建构的关键。跨文化传播的本质并不是单纯的文化输出,而是基于“共情”的传播互动,在多元文化主体的多维互动中,达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情感效应,构建起全球共有价值观为参照的体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30〕道德与良知是人类社会共有的基本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是构建叙事体系的最基本要素与内涵,无疑是全球叙事的共情点。心理学认为,道德是指由社会舆论力量和内心驱使支持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的实行主要依靠舆论、传播、说服、教育、示范、内化和自我调节。〔31〕良知是人类道德自觉。我国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著名的“王门四句教”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认为,良知是至善之心体性体,是人类永恒存在之普遍人性,是人类行为之准则明师,为人类历史文化确立终极之价值源头与超越之意义本体。有鉴于此,我们应在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平等性的基础上,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倡导基于人类道德与良知的共情叙事,并把它的养成与提升变成全人类的共享价值财富和共赢精神成果。
其三,发挥社会化媒体平台的辅助性和建设性叙事功能。进入Web2.0时代,围绕大众媒体的枝节传播模式被技术赋权下的关系网络重构为“去中心化”的链式传播结构,信息环境由区域传播转向全球流动。社会化媒体的参与性、开放性、复向传播性、对话性及圈层性等介质特性将有助于提升国际传播中的认同感、影响范围和粘合度,〔32〕成为对外传播的新赛道,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在国际传播中的发展迎来弯道超车的新契机。尤其是在互联网“下半场”,传播和价值“变现”观念将从把个人看作“流量”演化为把个人看作“具象”的场景,处于社会化媒体场域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国际传播互动机制的设计,需要更多地强调高场景度交互情境的搭建,以定制化互动方式满足海外用户个性化多层次的互动需求。〔33〕不仅如此,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建构还要积极利用社会化媒体平台的“适航性”,可援引现有国际传播媒介矩阵中其他媒介的观点予以辅助式证明,特别是一些在海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外主流媒体和强势媒体,可借助它们对于国际社会已有的权威性,让海外用户感知到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正当性,实现中国形象国际认知的“祛魅”。社会化媒体平台的界面也可以同步通过嵌入来自其他传播主体或者第三方媒介关于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议题信息衍生的链接,从而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匹配适航性语境。
其四,坚持“中国叙事”的基本原则与态度立场。既然是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那就必须将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符号、中国元素纳入到话语和叙事之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在叙事体系建构中立足中国方案,彰显中国智慧,擦亮中国底色。我国历史学家吕思勉指出:“中国人的对物,允宜效法西洋,西洋人的对人,亦宜效法中国。这两种文化,互相提携,互相矫正,就能使世界更臻于上理,而给人类以更大的幸福。采取他人所长,以补自己所短;同时发挥自己的所长,以补他人之所短。这就是中国对世界的使命。”〔34〕我们要坚持“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全球价值观与共享观,而且我们一再强调坚持这样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在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国际化建构中,中国只是输出一种文化模式,而绝不输出国家制度模式。作为世界叙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叙事体系在参与全球叙事体系建构与互动过程中,既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要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特色,以及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底线思维,加大和提升建构的力度与效度,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35〕的建设性目标。
四、结 语
新时代,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国际化建构是一项涉及全球性、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的综合工程,它需要国际社会的精诚协作、通力合作,而绝不是中国单方面的力量和愿望就可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尤其是西方一些敌对势力总是带着意识形态偏见,千方百计地干涉、阻扰,难免会使得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在国际化建构的征程中遇到一些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障碍。即便如此,中国需要走向世界和世界需要了解并解读中国都是不可否认的时代诉求与世界共识,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国际化建构虽然任重道远,但是既然“鞍马已备好”“铠甲已上身”、议程已经设置并启动,那它就已变成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和时代潮流,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建构图谱,势必将被打造成为新时代“球土化”世界话语和世界叙事体系中一张精致的中国名片和向国际社会呈现的一道靓丽的中国风景线。
注释:
〔1〕〔2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
〔2〕〔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9页。
〔3〕Bolinger D.,Aspects of Language,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5,p.135.
〔4〕〔5〕Paul G.J.,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Theory and Method,Beij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Routledge,2000,pp.2,11.
〔6〕〔7〕〔美〕艾莉森·利·布朗:《福柯》,聂保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8、40页。
〔8〕Michael Shapiro,Language Politics,Oxford:Basil Blackwill,1984,p.206.
〔9〕欧阳明:《新闻叙事学学术建设视野中的话语、新闻叙事话语》,《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0〕Mieke Bal,Narratology: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9,p.1.
〔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70页。
〔12〕李志雄:《论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古典叙事理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3〕章晓英:《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一个叙事学视角》,《国际传播》2019年第1期。
〔14〕〔23〕赵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中国叙事体系》,《理论导报》2022年第6期。
〔15〕童庆炳:《20世纪中国文论经典》,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94页。
〔16〕Robert O K.,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245.
〔17〕Vivien A S.,“Does Discourse Matter in the Politics of Welfare State Adjustment?”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2,35(2),pp.168-180.
〔18〕王江雨:《地缘政治、国际话语权与国际法上的规则制定权》,《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
〔19〕张新平、庄宏韬:《中国国际话语权:历程、挑战及提升策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20〕李朝祥、韩璞庚:《国际话语权的三重维度和基本构成》,《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5期。
〔21〕龙钰:《叙事·制度·学术——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理路》,《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22〕〔24〕〔3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17、317、318页。
〔25〕崔士鑫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论述的发展脉络和深刻内涵》,《中国出版》2021年第13期。
〔26〕姬德强:《立足元叙事、识别舆论场:中国国际传播内容体系建设的系统化思维》,《现代视听》2021年第8期。
〔27〕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29〕谭旭虎:《镜像与自我:史景迁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6页。
〔30〕曹进、赵宝巾:《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月21日。
〔31〕黄希庭、毕重增主编:《心理学》第2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228页。
〔32〕栾轶玫:《社交媒体:国际传播新战场》,《中国传媒科技》2012年第11期。
〔33〕周敏、王希贤:《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社会化媒体信息可信度提升路径探析——基于MAIN模型的思考》,《新闻大学》2022年第10期。
〔34〕吕思勉:《你一定爱读的极简中国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