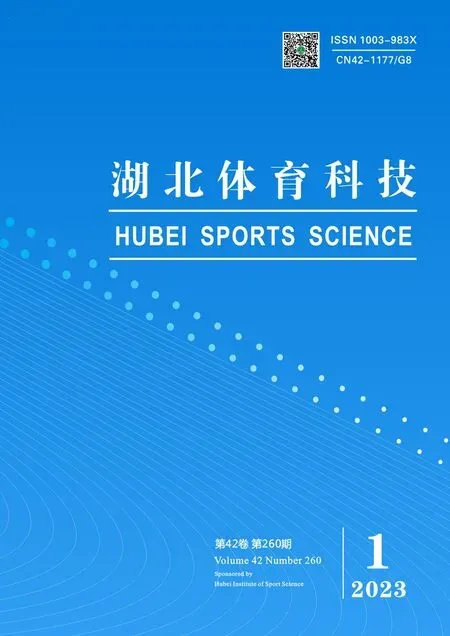探源与启示:先秦武术教育
王伟业,张 鑫
(1.江南大学 体育部,江苏 无锡 214122;2.江阴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无锡 214405)
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时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1]。中华武术是中华文明的产物,深入理解中华武术,是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需要,从历史中深挖武术价值,可更好的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近年来,审视中国武术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1)自2017年以来,由于“徐雷事件”的持续发酵,中国武术受到极度的社会关注,武术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尤其是2020年“马保国事件”[2]的发生,将武术推向了风口浪尖,以致引发了人民日报对“马保国事件”的关注与批评,直至最后的封杀,这直接造成了中国武术的信任、形象、文化等危机;2)我国“青少年这个年龄段中教育和体育是处于分离状态”[3],一方面 “当前学校武术教育也存在现代教育与体育教育 ‘去身’‘去人’化问题”[4],另一方面“从事竞技体育专门训练的学生运动员依然被排斥和隔离在教育之外”[5]的“去心”化问题,为此,体育界、教育界不得不采取“体教结合”“教体结合”“体教融合”的接连措施来解决“体教分离”的教育问题。面对武术认知、信任、形象等危机与武术教育的“去身”“去心”等问题,有学者认为,应“回头探源,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洞察中国武术的本真性特征,发现其文化精深价值之真意,实现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再发现’”[6],“回到原典,能够让武术不再‘失语’和‘他者化’,为武术教育教学和文化传播提供元训练理念和元术语”[7],“从根源入手,‘重新扣好第一粒扣子’是新时代武术在发展战略上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问题”[8]。
综合上述,其一,中国武术不得不回向雅思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先秦元典中,从先秦元典中重新梳理、解读、认知武术,合理把握第一粒扣子的内涵;其二,先秦武术教育是文武结合的教育,既有个人技能,又有个人品德,较好地统一了身与心、文与武的“成人”教育,为当代“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有机结合”[9]提出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供理论镜鉴与启迪作用。
1 先秦武术教育的文化记忆
商周时期,据《左转》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当时看来,祭祀与军事是最为重要的两件事,这两件事均与武术有关。因此,早在夏代我国已有学校武术教育,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其中“‘痒、序’的教育中,武艺是最重要的内容”[10]23-24。 其实“校”也和武术具有莫大关系,邱志诚[11]认为,“校”本是养马、训马之所,后变为习武、比武之地,故校之名“校”,起初必为“军体性质的教育机构”。进入周代,“六艺”成为周代的重要教育内容,“其中的礼、乐、射、御都与古代武术关联”[12]。 对“礼、乐、射、御”的微观透视,照见先秦武术教育的“成人”“完人”(文、武、德)内涵,这种内涵使得武术脱离原始时期的生存技术,走向人与天、人与心的内向升华,完成生物人向社会人的过渡,成为武术最为精华的血液,对武术后来的发展与走向奠定了基础与指明了方向。
1.1 以礼见天:等级规范教育
先秦时期,人们的生活世界无不被“礼”文化裹挟着,这种“礼”文化一直影响中国两千多年,流风余韵至今未绝,因此中国素有“礼仪之邦”著称。在《礼记》中,无论人们的行、走、坐、卧,抑或婚、丧、嫁、娶、穿着等方面无不体现着“礼”,就连人与禽兽的区别,也将“礼”作为分判依据,如:“鹦鹉能言,不离鸟飞;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13]371-372。春秋时人之所以崇尚、恪守礼文化,绝不仅仅因为外在的仪表修饰,在于“礼”贯通“天道”,如,“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左转》),“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转》)。这均是天道之“礼”的规范,因此孔子复礼亦被看作是复天道。中国文化在强大的“礼”文化笼罩下,自然带有“礼”的印迹,其中具有代表性之一的便是中国武术。在先秦武术教育中,最为表征的便是“射礼”教育。
射礼是社会等级规范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射礼可分为“大射礼”与“乡射礼”,而各自的内容与要求又各有差异,在“大射礼”中,又分为“大射、燕射、宾射”三种,每一种所参与的人之等级不尽相同,所使用器材也不尽相同。《周礼》记载:“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诸侯,合七而成规;大夫,合五而成规;士,合三而成规。”在所射靶子的质地上形成了“凡侯:天子,熊侯,白质;诸侯,麋侯,赤质;大夫,布侯,画以虎豹;士,布侯,画以鹿豕。凡画者,丹质”(《仪礼·乡射礼》)。可以看出,“人们可以从不同质地的候、画有不同动物的候中判断使用者的社会地位”[14]25,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所遵守与行使的礼也不同,不同的礼代表着不同等级,故“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状,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重”(《礼记·曲礼上》),借用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根内普的话说,“在任何社会中,个体生活都是从一个年龄到另一个年龄、从一种职业到另一种职业之过渡”[15],这种阈限之后的聚合,个体重新获得了新的身份、新的道德、新的责任、新的礼仪行为与规范。射礼不仅教化上层贵族人士,同样也在规训着下层市民。在平民所举行的“射礼”则称为“乡射礼”。“乡射礼共有两种,其一即每年春秋两季各地方为了教化万民知礼,厚风俗而举行的射礼,参加者为卿大夫、士、州长、国人,地点为乡之州序。 其二为乡大夫在三年一次的大比之年献贤能书之于王行乡射礼”[16]。同样,“乡射礼”也存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对所射靶子的质地进行了严格区分,这显然与“大射礼”所要表达与强调的“明君臣之义”“长幼之序”的“礼化”意义相同。但“乡射礼”较之“大射礼”而言,则更加突出竞技性的竟攀精神与规则的细化,如在规则上以 “不贯不释”为原则,要求箭矢必须射穿靶心上的皮革,以此作为评判标准,若箭矢没有射穿靶心,则不予计分,以保证“乡射礼”的公平、公正。
射礼之所以在先秦时期深受喜爱,是因为射礼带有一定的竞技性、娱乐性、身体性、教育性、礼仪性,故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射礼应是大家都去参与的一项运动,在比赛前双方互相作揖、谦让,赛后双方还要共饮以示友好,在整个过程中可以很好的培养君子人格。综上来看,孔子所提倡的射礼已完全超越了身体技术,是一种“寓武于礼,以武扬礼”的“成人”教育,而射礼之乐,也脱离了射术之乐、完胜之乐,升华为一种“见其大”之乐,这种“见其大”之乐便是王艮《乐学歌》中的“见良知”与“见天”之乐。因此,对射礼的修习实质是“以礼见天”“等级规范”“明礼成人”的求道过程,追求的是以“见道之乐”为终极之乐的武术教育。
1.2 乐舞之和:制敌时的武德教育
据白川静研究,“舞”“会意,‘無’与‘舛’组合之形。 ‘無’形示舞蹈者。衣袖上佩戴饰物,舒展衣袖翩翩起舞。‘無’后加表示双脚的‘舛’(双脚张开之形)构成了舞,用来表示跳舞、舞蹈。 ‘無’本指所谓‘無雩’的求雨仪式”[17]384-385。 “舞”,在先秦的实质本是祈雨仪式上的一种舞蹈,而能在祈雨仪式上进行舞蹈之人,恐怕只有“巫”。之所以是“巫”,是因为只有“巫”才有资格与上天进行沟通,来协调神界与人界的关系,继而给出上天的指示。因此《说文解字》在解释“巫”字时指出:“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不仅如此,“巫”在先秦时期其实还有另一种身份,这种身份是直接导致“巫”与神界对话的可能,即“巫君合一”“王为首巫”的政治身份。换言之,“巫”不仅掌握着精神统治,同时也掌握着政治统治,是“政教合一”的统一体。原始歌舞既然是“王为首巫”所垄断的身体技术,周公在“制礼作乐”中必然有所偏倚,将“非日常活动的‘巫’已变为社会生活的‘礼’。少数巫师、巫君所垄断的巫术歌舞已变而为上层社会并不断扩及整个社会的礼仪制度”[18]。因此,“舞”在先秦时期便成了促进身体、陶冶情操、培育审美等修养身心的教育内容。
可以看出,“舞”是“身体礼教”的教育内容,这一教育内容贯穿周人“成人”教育的全过程。据《礼记·内则》记载:“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 ”《诗经·维清》郑笺注曰:“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在习“舞”的教育中,西周之人“十五、十六岁时,学练象舞,也就是学习武术的一种方式”[10]23。 因此,《释名·释言语》云:“武,舞也,征伐动行如物鼓舞也。”其实早在先秦时期,作为“乐舞”种类的“武舞”不止“象舞”一种,其中还包括“干戚舞”“万舞”“大武舞”等。据《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 ’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这种执干戚以‘舞’而降服三苗的文明斗争,其中昭示着猛虎下山般的威武‘气势’,以震慑与威服三苗”[19]。可以看出,“武舞”的出现是对暴力的消解,从中可以体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武德文化。这种文明化的斗争方式,还促进了武术套路的形成。在武术人看来,武舞的练习为武术套路的诞生提供了灵感,表征为“‘舞’的形式来复述‘武’的动作、记录‘武’的精华”[20],将战争的身体动作隐藏于“舞”中,促使武术套路的形成。此外,除消解暴力的武德文化与武术套路形成的历史贡献外,武舞的练习还在于对人的陶冶性情与修身养性方面,故,《荀子·乐论》言道:“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体言而知,荀子所主张的修身方法是对乐舞的习练,以此促进人的身体、思想、审美、道德等的培育。因此,乐舞成为先秦时人喜爱的一种修身教育技术。
时下武术工作者,在汲取古人乐与舞合组而成的乐舞经验后,对现代化的武术也提出了要求,如在现代竞技武术套路比赛中,对武术套路的评分改为“分块评分”,其中B组版块评分即是对音乐与套路编排的合理性进行的评价,在“B组中由裁判员按照套路动作劲力、节奏及音乐的要求整体评判后确定的等级平均分数减去对套路编排错误的扣分,即为运动员的演练水平分”[21]。这种对节奏与音乐的要求,也算是对古代擂台比武中或进或退、或交手或分开时附之以大鼓为乐的继承。可见,乐舞与武术套路在演练形式上几乎无所差异,只是在动作内容的选取上各有不同,换言之,武术与乐舞(舞蹈、武舞)存有太多的“家族相似性”,无怪乎“巫、武、舞,在原始人那里,是合而为一的”[22]论说。可以说武、舞在内容与风格上有所不同,但在演练形式上是一致的,所要完成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即强健体魄、陶冶情操、培育审美等,其共同目标就是以身体教育为手段的再造“新民”。
1.3 射以观德:内外不伪教育
射,“会意,古字金文为‘弓’‘矢’‘又’(手)三者组合之形,箭矢搭于弓,意味着发射”[16]。“射”其实质就是射箭的技能,是古代最为重要的军事武艺技术,在十八般武艺中位列第一。在先秦时期关于射箭的技术主要有五种,故称为“五射”,分别为:1)“白矢”。主要强调拉弓时,要将镞(箭头)碰到持弓的手,以保证拉弓的张力;2)“剡注”。要求镞(箭头)直前对准靶子,是对瞄准的要求;3)“襄尺”。是指拉弓的姿态,要求拉弓的手臂要保持水平,以至臂上可以放置水杯;4)“井仪”。指对力量的要求,将弓拉至圆形状态,达到井口之圆样态;5)“参连”。是指一种连射的技法,先发一矢,其余三矢夹于三指间,随后相继拾发。综上所述,射箭即是“弓、矢、手”三者相合的身体技术,但对于教育而言,射箭不能简单的归为身体技术,而必须与“何以成人”的育人关涉。
在先秦时人看来,射箭不仅是一项身体技术运动,还是一项“内外合一”的身心运动,这里的“内”指的是人的德性,因此《礼记·射义》指出:“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认为射箭者无论前进、后退、左移、右移,其外形动作必须合乎规范,内心要沉着冷静,以致“打时不可呼吸,呼气恒低,吸气恒高,故需心气平静”[23],方可一箭命中。因此,通过射箭者的动作就可看出射箭者的内在德性(心理),德性反映在外便是德行(动作),认为德性好的人必有好的德行,所谓德、艺不分即是如此。故,“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愿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礼记·射义》)。射箭之道,正在于身正则心正,心正则身正的身心一体、内外互感,即所谓“诚于中,形于外”(《大学》)。同时,射箭之道也在于不断的自我反省,不断发现自我的不足,通过不断的自我检查完成“内向超越”的精神升华,因此“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中庸》),射不中者也会被象征为“不正”之人,而需要“治心”与“正身”。可以看出,射箭看似是一项关乎身体之运动,其实质是身体为表,仁德为里的一项身心运动,所射之箭是否命中,已不在是技术好坏的评判,而是“完人”“成人”与否的评判,将“命中”与“身心”相联系。故射箭比赛既考验技艺,又考验德性,但其重点在于后者,即对温良恭敬、进退有仪的德性之考验。因此,射箭在先秦武术的教育为“以射修礼”“以礼养德”“射以观德”的实质教育内涵。
射箭之术的求仁之道不仅在于自我的身心超越,还将这种超越的水平、高低外化于人格的评定,体现于先秦晋升官职的制度文化与社会治理当中。如“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不得与于祭者有让,削以地;得与于祭者有庆,益以地。进爵绌地是也”(《礼记·射义》)。当天子祭祀之前,要在泽宫的地方通过射箭的方式来选择诸侯,被选中的诸侯再参加射宫中射,命中的可以参加天子祭祀仪式,没有命中则不准参加,未参加祭祀的诸侯将要面临削减封地的处罚,参加祭祀的诸侯将受到增加封地的奖励。这种以射箭为求仁之道的内向超越显然已外化为官职晋升与奖罚的制度,以命中与不命中的结果来检验人格的是否完备,以此成为一种晋升制度。这种品评人物的德性作为入仕依据的举措,影响了汉朝选取官吏的“征辟”“察举”制度,“汉朝人鉴识人物往往由外貌的差别,而推知其体内的才性之不同,故有所谓‘骨相’之法”[24]。因此凡不命中者被认为在伦理道德方面存在缺失,伦理道德缺失之人不仅不能参与神圣的祭祀仪式,还面临不在具有管理四方的能力而被罢官黜爵的可能。相反命中之人不仅获得与天子祭祀的“门票”,同样也被视作道德完备之人,以获得官职的晋升。除皇家外,射以观德的教育在当时社会亦普遍存在。当孔子在矍相的泽宫演习射箭,围观人数较多时,便命子路手持弓矢曰:“‘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其余皆入。’盖去者半,入者半。”到了旅酬的时候孔子又遣公罔之裘对在场的人讲:“‘幼壮孝弟,耆耋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盖去者半,处者半。”接着序点又言:“‘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旄期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也。’盖仅有存者。”这样看来,凡参与泽宫射礼的人员,也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否则就难以参与射箭活动。故君之参与的射箭(大射礼)比赛表达了国家意志的治理形态,君之不与的射箭(乡射礼)比赛贯彻了国家意志的政策规范,张君贤将之概括为“君与君不与”[25],君与为里,君不与为表,表达了先秦“表里一贯”的社会治理文化。
1.4 御以载道:天下治理教育
御车上达御民的天下治理之道。御在商周时期是及其重要的一项身体技术,其因在于“殷商时期,主要以车战为主”[10]27。据《尚书·周书·牧誓》言:“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商战于牧野。”可见这种“牧野洋洋 ,檀车煌煌 ,驷騵彭彭”(《诗经·大雅·大明》)的场面是多么浩大。车子的使用不仅体现在军事战争,还涉及到经济、生活、交通、狩猎、教育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轮子是商贸经济的产物,商业活动必然追求效率,而轮子本身就是效率的标致”[26]。因此,早在5 000年前中国就有了轮子,对轮子的发明也归功于4 700年前的轩辕皇帝,故“横木为轩,直木为辕”(《路史·轩辕氏》),号曰轩辕。不过这种“托古”正名的附会,刘安在《淮南子》中就已揭露,“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因此,关于车子的产生年代与实际发明人难以考证。虽难以考证,但许进雄指出,“车子的拉拽改进过程是由人而后牛而后马”[27]373的发展过程。就马车而言,迟至4 000年的夏朝已有,认为是初夏的奚仲所发明。对车子的使用,在马取缔人、牛为拉拽动力的车子后,其用途也发生了重大改变。“马奔跑快速,宜于快速传递消息或追逐猎物,后来又直接参与战斗任务,是贵族游乐及打仗所依赖的工具”[27]373。对于马车的使用基本被皇家、贵族、权势所垄断,成为军事、畋猎用途的重要工具。囿于马的性格狂躁难以控制,加之要想在马车上进行作战,对驾驭技术也就更加严格,因此需要专人经过长期的训练方能胜任,“御”在商周时期便成为一项军事用途的身体技术。
降至春秋时期,随着社会“下学上达”的道学兴起,以及车战历史性的让位于骑兵,御车不再是一项仅局限于军事、身体的技术,而成为一种教育技术。故“春秋中叶之后,由于机动灵活的骑兵作战方式逐渐取代了笨重的车战方式,御的技术渐渐失去了军事上的实用价值,御在贵族教育中,也就变成为一种礼仪训练项目了”[28]。 据《周礼·地官·保氏》记载,在所教授的御中主要有“五御”,即:“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午交衢、逐禽左。”“鸣和鸾”指在行车时与挂在车前撗木上的“和”,或与挂在轭首或车架上的“鸾”之声相应;“逐水曲”是指沿着河边曲岸奔驰而不至落水;“过君表”是指驾车经过天子表位时要有礼仪、行礼致敬;“午交衢”是指可以快速自如的通过各种通道;“逐禽左”是指在田猎时,使车子驾驭到猎物的左方,以便于猎杀。可以看出,春秋以降御车已不在简单的指向驾驭,还要与乐舞的节拍相结合,使其在行使过程中与挂在车上的金玲节奏相契合,同时驾车经过国君所在地时要行礼致敬,成为一项教育技术。除此之外,大教育家孔子还对御车技术提出了具体要求,孔子指出:“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论语·乡党》)。当然,御车之礼不仅是对驾驭之人的礼仪修养,同样对乘驭之人亦有要求,如《礼记·曲礼上》记载:“故君子式黄髪,下卿位,入国不驰,入里必式。”“国君下齐牛,式宗庙。大夫士下公门,式路马。乘路马,必朝服载鞭策,不敢授绥,左必式。”都是对乘驭之礼的要求。可以看出,此时的御和乘已经成为个体“下学上达”的修身文化。
御车的教育不仅指向个体“下学上达”的修身方面,其重点在于通过御车之道指向御民之道的帝王治理方面。在《韩诗外传》中记载了孔子用车御之道阐述御民之道,曰:“故有道以御之,身虽无能也,必使能者为己用也;无道以御之,彼虽多能,犹将无益于存亡矣。诗曰:‘执辔如组,两骖如舞。’贵能御也。”因此,“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韩诗外传·卷二》)。作为法家代表的韩非子,也曾借御车之道教导帝王以专心致志,曰:“赵襄主学御于王子于期,俄而与于期逐,三易马而三后。襄主曰:‘子之教我御,术未尽也?’对曰:‘术已尽,用之则过也。凡御之所贵:马体安于车,人心调于马,而后可以进速致远。今君后则欲逮臣,先则恐逮于臣。夫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此君之所以后也’”(《韩非子·喻老》)。其实,在春秋时期,这种“下学上达”的教人文化已普遍存在,如庄子曾以“说剑”为寓,教导赵文王如何治理天下。是故,“上学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29]的猛攻只谈中国文化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形上学家。
2 先秦武术教育的启示
在栗胜夫教授看来,现代竞技武术是“经过科学训练、反复磨炼的精英们,在赛场由开始到结束,礼仪、心理 、体力 、状态、形体、技术、战术以及精神、风格的展示等,都是中华武术前所未有的规范性表现”[30]。但观照先秦武术教育发现,上述种种现代竞技武术的优点,在先秦武术教育中无不蕴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换言之,今天竞技武术套路的演练形式在先秦时期的武舞中就已具备,只是当时人们并未发明现代竞技武术套路里的“难度动作”。如若再作细微观察会发现,今天武术的竞技性、健身性、技击性、娱乐性、艺术性、教育性、礼仪性等多元性价值,在先秦武术教育中就已显现,只是今天的武术发展倾向于竞技性,以致竞技武术成为“一花独秀”,占据武术半壁江山,这同时也为武术带来了现代性问题。1)由于现代武术的发展倾向竞技性,造成了当下时人对武术的偏颇认知,以西方竞技理念的竞争、KO、成败之视角来否定武术,出现了民间“约架”现象。2)现代竞技武术依照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更团结是第32届奥运会新加入的奥林匹克格言,武术更多受更快、更高、更强的格言影响)的发展理念,在教育上造成了体与教的分离,使“体”成为一项专业人员从事的技术工作,“教”亦从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项专业人员从事的教育工作,因此当前的教育出现了“离身”“去身”的现象。在面临现代武术文化认知的错乱与体教分离的去身问题,先秦武术对现代武术与武术教育的良性发展主要存在的启示:武术的礼仪之教育;武术的体教融合之教育;武术的乐学之教育。兹分论列于后。
2.1 武术“以礼始终”的礼之教育
武术教育贵在礼学的知行合一、仁礼合一。儒家典籍《礼记》记载与规定了中国人行、走、坐、卧、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的种种礼仪规范,以致塑造了若“无礼,则手足无措”“无礼无以立”的中国礼仪世界。其实,儒家不仅为人们建立了一个带有“礼”烙印的世界,也为武术之“礼”的形成给予了诸多启蒙。譬如,“先生书策琴瑟在前,坐而迁之,戒勿越”(《礼记·曲礼上》)就是对书具教材的尊重。这形成了武术文化中对武术器械的尊重,“在尚门中学剑是隆重的事情,每天早晨起来要向剑磕头,名为‘拜剑’”[31]。在武术教育中,虽不至做到李仲轩那样对器械过于虔诚的跪拜,但起码做到对器械的应有尊重,毕竟器械是与我们同甘共苦的历史证物,它早已与我们打成一片。故武术教育中应着重对“爱物”的礼仪教育,譬如武术中的递械礼、接械礼和持械礼,并以此辐射学生对课前书包、衣服、鞋子、生活用具的规整摆放,杜绝随意摆放、踩跃物品的失礼行为。在世界软实力争夺战中,武术礼仪教育的重视绝不是一件小事,因为时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的钟秉枢,已经在实际中看到武术与跆拳道关于礼仪方面的差异,对武术礼仪教育方面极度不满,以致学界大有“跆拳道教练已经把礼仪规范融入到了平时的课堂教育之中,而中华武术却忽视了本应具有的礼仪规范”[32]之呼声。基此,时下武术教育应借鉴先秦武术教育,因为先秦武术教育实质就是一种礼仪教育,时下的武术教育不应再将技术教育放在首位,应着重强调礼仪的成人教育,这种礼仪成人教育不仅体现在抱拳礼、持械礼等方面,更应体现在“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的从容、得体、端庄之体态,继而外化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的生活化礼仪之教育。
武术礼仪教育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身体行为上,最终指向的是对“礼仪”背后“礼义”的情感唤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王阳明所谓的“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里的“知”可视为“礼义”,“礼义”即是人之本心的“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礼义)本是人们天生就具有的,只是人们在后天的引敝习染中被蒙蔽了,因此王阳明以致良知(礼义)为其工夫论。换言之,礼义即是良知,即是心之昭明灵觉处。这种心之昭明灵觉处在武术礼义中可体现为,见到武术器械被践踏、损毁、遗弃而发放的悲悯情感与对错之心,继而付之行动的去爱护、珍惜、归置武术器械,实现“知行合一”。因此,王阳明再三强调“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33],其根本之意是将心中的良知(礼义)必须在行为(礼仪)中实现,这样从根本上规避了理论与实践、表面与内里的分离,使学生不仅在表面上实行“拜师学艺之礼,祭奠祖师之礼,同道见面之礼,较技打斗之礼,献艺表演之礼”[34]的礼仪行为,在内心里也唤起敬畏与敬重的本心,使外在的行为(礼仪)从属自我的本心(礼义),自我本心(礼义)落实到外在的行为(礼仪)上,以此达到“真知”。作为“礼学”专家的孔子也认识到这一点,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 ”(《论语·八佾》)、“射者,所以观盛德也”“内志正,外体直”(《礼记·射义》)的要求。在历史事件中,宋襄公就以“知行合一、仁礼不二”的“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来恪守军礼,虽沦为历史笑柄,但不可否认的是,宋襄公“临大事不忘大礼”的将内在礼义(不可见)与外在礼仪(可见的)合二为一的付之于实践,这种实践在孔子看来即是“仁礼合一”,在王阳明看来即是“知行合一”,同时也侧面反映古之尊礼、尚礼的历史时事。
总之,时下尽管我们很难接受武术的“去技击化”或“技击的弱化”,但武术的“去技击化”已在历史中表明,时下我们不能再抱有武术的唯技击论、唯竞争论来看待武术的整体,应从先秦武术再审视武术的价值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消解以所谓“打假”的名义来否定武术的事件发生。是知武术在先秦时期就已脱离唯技击论,而成为一种“身心合一”“心技一如”的教育手段,这种教育手段即是“习武明礼、释礼归德”的武术——礼仪——礼义三位一体的武术教育。
2.2 武术“寓教于体”的身心教育
破除“唯体独尊”“唯心独尊”,实现“以身载道”“文武兼济”的武术教育。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合格的君子必须是文武兼备,否则就难以成为真正的君子,至少在孔子看来是一个不完备的君子。孔子不仅设想出君子的形象,在其自身实践与传道中也付之于行动,“世人只知孔孟二圣教书育人的道德文化思想超越古今,却少有人知道二人的武艺之高超也鲜有人匹敌”[35]。其实孔子对君子形象的设想并非是自我的偶发之见,而是参照西周贵族士人的君子形象,正如雷海宗所言,“士族阶级已被推翻,文武兼备的人格理想也随着消灭”[36],文武兼备的贵族士人走向文武分途,“擅文者”为儒士,“擅武者”为侠士。这样古之文武兼并之士,走向了分歧为二,文者过柔,武者过刚。作为春秋时人的孔子等人,面对文武分途的境况与对西周贵族士人的怀念,不得不将儒士的气节与侠士的武功进行重组,企图复兴西周贵族之士的君子形象。戴国斌教授认为:“按照‘气节和武功’创作的‘武侠’形象,可谓周之士的回归,也是人们对春秋以来士之人格分裂的医治”[13]151。实际上,尽管孔子在“新六艺”中取缔“老六艺”中的“射”“御”之内容,但也仍然保留“老六艺”中“礼”“乐”的身教内容。此外,随着贵族阶层的下降与庶民阶层的上升,“创教师之专业的孔子”[37]在大批招收学生的教育下移中,也不乏对“射”“御”的教育,这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俯拾皆是,如“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子罕》)。“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故,“在那个时代,为了出仕,贵族成年人除了学习《易》《诗》《书》《礼》《乐》《春秋》,也要学习射艺、御车、角觝、蹴鞠等各项技艺,亦战亦娱,这才算完整的贵族教育”[38]。因此,孔子自始至终都未排斥身体教育,而心中最为理想的便是文武兼备之人才。但为使皇权稳定,本集于一体的文武之士,不断发生文治与武功的分离,使文、武互相牵制,以便皇权统治的将文、武分离,彻底形成文臣武将。
从上述可知,商周时期的人们所提倡与实践的教育是“体教融合”的教育,在身体技艺的修习中实现“成人”的培育。因此,我们在考察先秦武术教育时发现,先秦时人在武术教育中带有浓厚的技艺性、礼仪性和道德性,先秦武术教育与其说是对技艺的传授,不如说是对礼仪行为的规范,与其说是对技艺的竞赛,不如说是对礼仪行为的展示。可以明显看出,先秦武术教育是“技道一体”的教育,这与当下武术教育所出现的“体教分离”“技道相分”的现象相佐。“体教分离”来自上世纪中叶,在西方奥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强的理念与“举国体制”的“奥运争光”影响下形成。体教分离虽有时代性贡献,但已不适合当下体育、教育的发展,严重影响与偏离了以“全人”为教育的目标。
总之,在“体教分离”的今天,武术教育不能偏执一端的以“技术至上”“锦标至上”“完胜至上”的理念作为武术教育的发展目标,否则中国武术教育仅仅只是技术层面,很难实现中国武术家引以为豪的道术层面;反之,偏执于“理论至上”“头脑至上”“学术至上”的理论教育,则易造成无下学载体的上学而显得过于虚渺,极易造成缺少载体与实践的空谈,以致走向唯心主义的“去身化”教育。因此,以“体教融合”“体教互补”“以体寓道”的先秦武术教育之道路,才能真正实现武术“由技至道”的完人教育。可以说,时下“体教融合”的提倡亦是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使命。除此之外,关心青少年成人教育的同时,在武术教育中更应以家、国、天下的“教”之事为重,使之放眼于全球的大视野观与社会责任感,促进武术与社会的发展,毕竟中国古代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就已形成“身国一体”(《孟子·离娄上》)的身体观,将家事、国事、天下事皆看作身内之事。
2.3 促进武术兴趣的“技术之乐”教育
技术之乐的兴趣,促进人生化的武术教育。“乐学”不仅体现在主体方面的“乐之者”(《论语·阳货》),还体现于教育内容的趣味方面,以教育内容的趣味性来诱导学生的积极性,促进当下的武术教育改革。对于当下“学生喜欢武术,不喜欢武术课”的问题,刘文武[39]在武术教育改革中提出套路之练与竞赛之用的结合,以竞赛之用的乐趣来改变 “死板单一”“枯燥乏味”的套路练习。刘文武所谓的竞赛之用的乐趣,与“六艺”中的“礼”“射”之“必也争乎”不谋而合,这种“必也争乎”的趣味教育受到广大学生的喜爱也并非纸上空谈。据调查,“当今的大学生喜欢具有竞争性、对抗性、激烈性的体育项目”[40],在高校中,“有篮球、足球等多种运动项目可供选择的校园内,除非是强制必修课,否则学生往往选择忽略武术课程”[41]的现象已愈加频繁。这种忽略武术专项课而抢选具有对抗之乐、必也争乎的篮球、足球、网球并不少见,皆因武术套路的死板单一和枯燥乏味,缺少篮球、足球运动的对抗之乐。因此,武术套路要想在学生群体中获得支持,必须加强、丰富对抗之乐的内容元素。其次,学生除喜爱具有“对抗之乐”的专项课外,在健美操、啦啦操、体育舞蹈等专项课中也颇受学生喜爱,这些专项课虽不具有篮球、足球的对抗之乐,但却有极强的陶冶情操、丰富审美之功效,一方面以“舞”来实现、塑造理想中的身体美,另一方面以音乐宣导内心中的情感。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就强调音乐对士大夫的影响,认为“音乐既为士大夫日常生活之一节目,而其事又无关乎利禄,则必因与士之内心情感起感应”[42]。由此可知,音乐融入武术至少有两大益处,一是以音乐的节奏、律动带动身体的舞动与协调,二是“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传习录》)的心理变化,这亦是《武术套路竞赛规则》要求音乐融入的意义所在。综上所述,从高校学生选课的视角来看,侧面反映武术教育内容“套路化”的“死板单一”“枯燥乏味”,与其它专项课相比而缺乏“对抗之乐”“音乐之乐”的“技术之乐”。
基此,欲改变“学生喜欢武术,不喜欢武术课”的“厌学”现象,应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在总结、汲取先秦武术教育中提出:一是学习“礼”“射”文化中的“对抗之乐”;二是学习“乐”“御”(鸣和鸾)文化中的“音乐之乐”。借鉴先秦武术教育中的“技术之乐”,促进当代学生“其趣”或“意趣”的产生,使之“学至于乐则成矣”(《二程集·遗书》)的不停业而持久之学的生活化与人生化。只有如此方能落实《意见》中提出的“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的指向要求。
3 结语
通过对先秦武术教育研究发现,1)先秦武术教育是“以身为载体、贯通天道”的“身心”教育之学,表征为“礼”重在礼仪(身)、礼义(心)合一的“成人”之学;“乐舞”是身心和美与消解暴力的身心艺术之学;“射”在治心与正身的至诚教育,教人“诚于中,形于外”“有诸内,必形诸外”的不伪之学;“御”上达帝王之道,教人御民之术的天下治理之学。2)先秦武术教育是集竞技性、娱乐性、技击性、健身性、艺术性、礼仪性、教育性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考察发现,作为先秦武术标致性的技击文化,在先秦武术教育中并不突出,甚至处在边缘位置,而贯通天道的“成人”之学则处于先秦武术教育的核心位置,对先秦武术教育文化综合体的认知,有利于消解现代武术出现的认知、信任、形象等危机。3)针对现代武术教育出现的“去身”“去心”等问题,提出:首先,武术教育应重视武术的礼仪教育,将先秦武术教育中的礼仪观,贯穿武术教育的全过程。其次,破除“体教分离”的对立教育,回归“体以载道”“寓教于体”“全身教育”的先秦武术教育,从根本上实现“体教融合”的对立统一之教育。再次,欲改变学生对武术课的“厌学”现象,整合武术教学内容,借助现代科技,创新、开发出具有先秦武术教育趣味性的武术教学技术,使学生“乐中学、学中乐”“学至于乐则成矣”的人生化武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