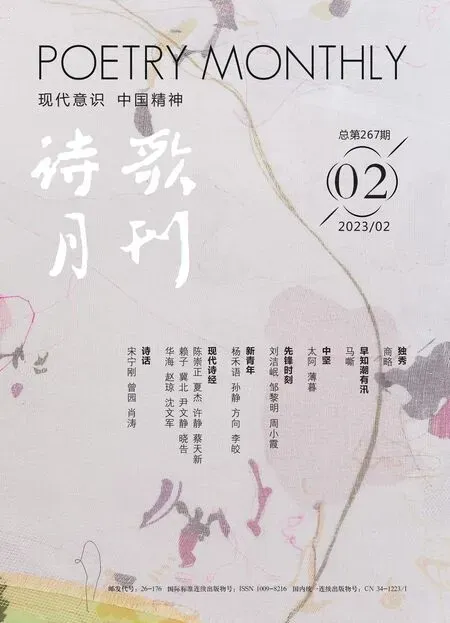初冬的鸟巢(组章)
周庆荣
初冬的鸟巢
初冬的下午,阳光照耀着一只鸟巢。
还没有冷冽的风,此刻温柔。它在鸟巢的左右,飞远如游子的鸟儿,会记住故土的呼吸?
我曾经目睹过这只鸟巢的搭建。
应该是两只鸟的共同努力,高高的树杈间才出现一个巢。
让家高高在上。
而不是别的。
初冬的下午,阳光延续着秋天的灿烂。
万顷温暖,这个鸟巢只取一瓢?
一对鸟儿,携儿女飞向南方。
等人间换了天气,它们将再次回来?
我眼前的鸟巢,就是家的等待。
如果鸟儿永远在南方栖息,这只鸟巢便是新增加的一间老屋。
往日的怀想也是未来的时光。
一冬一夏,一春一秋。
身体的变异
有一天,一对铜号从我的耳朵里长出。
和谐美妙的声音如乐曲,我的耳朵听过,真理和谎言,也都曾在耳畔响起过。
当我的左右耳变成铜号,耳朵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包括我的心跳,对人与事的赞美或者愤懑,铜号不再被动地聆听,它们将自己嘹亮。
有一天,我的眼睛突然拒绝睁开。
双目里的图谱自由地组合,黑白的、绚丽的,一切的景象都保留在我瞳孔的胶卷里。
或被曝光,或被冲洗。
谁想知道我目光里的秘密,她要具有足够的魅力,我再次睁大眼睛,是我自己,我想看天看地,看人间的风云。
身体的变异有时属于错觉。
比如我的嘴,它忘记呐喊,只缄默。
比如我的鼻孔,渐渐地学会藕孔那样地呼吸,污泥状的物质即使将我掩埋,我依然没有窒息。
自从我在苦寒的边陲看见过一株白杨,我开始担心我的脊梁。
气候严酷,但白杨挺拔。
我的脊梁,它不能弯曲,屈身佝偻。
司田者
我想向一块土地上所有的可能性学习。
稻谷成熟后,谦卑地低下头颅。小得不能再小的蚂蚁,土壤里必有它们的家。
给我一亩。
土地对于我,就不再是一种概念。
我是劳动者,也是主人。
因为春天的扶犁,我要尊重一头黄牛。
我要善待种子,需要了解它们的脾性和土地的态度。
长出来的苗,将准备雨露去滋润。
要有正确的办法去对付害虫。我自己一定要勤奋,浇水、拔草、施肥。
让我做司田,我是快乐的。
茁壮成长的禾苗,我会善待它们。劳动者是庄稼的慈父。
庄稼和植物,种类繁多。
我会尽我的所能,让这一亩田长出的事物丰富多彩。
只是不去栽寒梅,凌霜傲雪的事有我就足够。
也不会栽下竹子,形式上的气节,怎能与我体内的骨骼相比?
另一种角度
老叶子只有落下,才能给新芽腾出地方?
初冬说来就来,我把厚厚的落叶踩出季节的声音,干燥、脆裂。
同行的人,一边为落叶抒情,一边担心枝头离开的小鸟究竟会飞向哪里?
已经过去的夏天,枝叶茂盛时,待在树下的人享受着阴凉。他如果抬头,只是树冠在上。
有必要换一种方式去看待落叶。
此时抬头,天空随时高远。
蓝蓝的高处环境,如果有白云几朵,那是心的写意?
当为落叶抒情的人做好了过冬的准备,我决定尊重树枝的简约。
相信叶子会重回枝头。
新一代的叶子定会更加葱茏。
时间是点名簿。
春天将从树枝的体内露出脸庞。它说一声:“到。”
因此,我拒绝把落叶看成是一种结果。
我从落叶这里,看到新的春天。
隧道
这复杂的地理,请给我一次直线的抵达。
与从容的散步不同,我可能要实现真正的曲径通幽。
曲,表达有误。
幽,是必须的。
隧道,属于技术。暗度陈仓的技术。
上面,或许是洪水猛兽,或许是泰山压顶。
直线的穿越,仅仅是体内的呼唤吗?
时代的地理也对我提出同样的要求。
从甲地到乙地,从现在到未来,从苦难到幸福,从蹉跎到希望。
隧道,能够战胜这复杂的地理。
是的,我听到深壑那边的山峰上传来了她的歌声。
我确实想为爱唱和。
我想说明的是,正是爱,让我的抵达需要一次直线。
迅雷不及掩耳?隧道,是地面上的道阻且长。
暗暗地,鼓足干劲地穿越。
这地下之旅。
这斩钉截铁的抵达。
侠影
此生乐于为奴,因为不知侠为何物。
合上一部史书之后,又到了凌晨时分。披衣走在湖畔,听到水击岸的声音。
冬天了。它只需再多咳嗽几声,剩下的鸟将尽飞南方。一层冰会缄默水浪,待冰层继续厚实,会有人在柔软之上滑行,快乐而忘情。
史书虽然合上,书里的古人却没有离去。
几个月前读过友人的一本《十侠》*,突然想要在经历过的人生景象中,搜寻侠影。
不显萍踪的那种,更不是简单的仗义。
它首先是一根骨头。
不软的骨头。
侠影应该就在骨子里面,它是骨髓一样的暗物质。
既能被遗忘那般地潜伏,又能核力量那样地震慑。
精彩纷呈的人间,幸福与安宁正一个接着一个走进规划。
侠影,不是幼稚的日常实践。
它暗藏体内,法术无边。
它蔑视一切的旁门左道,至于沧桑,它中气十足。
它是丹田里的那股劲,是沧海中的一声笑。
*《十侠》,邱华栋著。
未竟之渡*
此刻,只是路途中间的一个停顿。
你停顿在一片落叶上,说明你正处于深秋时节。你停顿在饥饿中,说明还需要更加努力地劳动才能温饱。也会停顿在一个竹笋前,未来将会生长。
你正在远方旅行,你告诉我自己停顿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雕像前,我就知道因盗火而失去了自由。
未竟之渡,许多人把汗水留给了谬误。
蛾卵在等待它们的父母,飞蛾却在扑火。
我经常把未竟之渡假设为一次励志,还在途中,一定不能玩物丧志。
事实上,我看到已经在彼岸的人,围着篝火狂欢。
红红的篝火,只需一渡,我也是狂欢的一员?
你在停顿,我也不渡。
未竟之美,出发地是无法感知的。目的地如果偏误,不妨让自己的生命之渡永远未竟。
未竟,可以是命运的荒诞,也可以是精彩的哲学。
*未竟之渡,好友柴小刚早年的一幅同名油画。
召唤
我边上的河流,正泥沙俱下。
我站立的地方,郁金香绽放得美艳,仿佛土地刚打印出来的文献。
可以就此乐享其中,而且,许许多多的人们都在流连忘返。
“从温柔乡离开!”
夏天的雷突然炸响。
好,我离开。可是,新的远方在哪里呢?
又一声雷。
一条河流的结果或者现状,已经是大众的常识。
要溯源而上,看看这条河流来时的路。
“历史中为什么要有革命?”
我边上的河流,是水革命的结果。
我在地图上,呆呆地看着河流一个又一个的上游。
无数船只驶过,水面也被称为航道。
群山之间的穿越,揭示着我们已知的排除万难。
地形的起伏,落差之大,需要义无反顾的粉身碎骨。
河流的根部,也就是历史的深处,海拔之高,让我意识到低处的水,曾经会当凌绝顶。
一尘不染的雪,在太阳的劝说下,一点点放弃自己。
它和光同尘,由冰的坚硬变为水的柔软。
并且,接纳更多的泥土,携带广泛的世俗,把水的故事以河流的名义进行到底。
召唤我的是这条河流的高度?
召唤我的是这条河流曾经的一片冰心?
我把地图卷起,重新召唤我的是一条河的流水,河边的郁金香绽放,在绽放的郁金香的旁边,大片的麦子正在抽穗。
我是现实主义中的一个人物,一条河流仿佛生活的来龙去脉,最初的声音一定会把我招之即来,河流中途的湍急和粉身碎骨,它们也无法将我挥之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