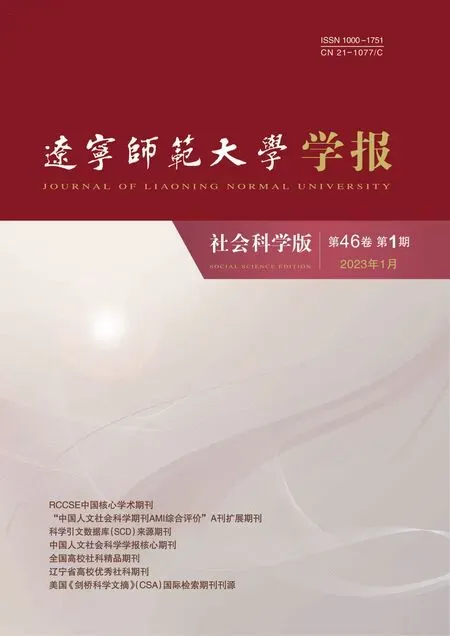一幅诠释生态美学思想的文学画卷
——论迟子建《候鸟的勇敢》
楚 金 波
(佳木斯大学 人文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20世纪90年代,当对工业文明反思和超越的“生态文明时代”到来时,中国研究者借鉴西方环境美学和生态学思想,在中国传统生命意识的基础上,把生态学和美学联姻,研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审美生存状态,构建了新的研究空间——生态美学。生态美学以人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作为审美观照对象,突破和超越了传统美学思想领域,同时将自然的生态维度放入审美观照领域,带来了全新的美学理念和生态认知方式。正当生态美学思想从哲学到生态学再到美学层层推进研究的时候,当代作家迟子建已用生花妙笔,悉心创作长篇小说《候鸟的勇敢》,描绘了一幅诠释生态美学思想的文学画卷。
一
传统的实践美学面向自然对象,强调人的主体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认为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李泽厚就曾说:“自然美的崇高,则是由于人类社会实践将它们历史地征服之后,对观赏(静观)来说,成为唤起激情的对象。所以实质上,不是自然对象本身,也不是人的主观心灵,而是社会实践的力量和成果展现出崇高。”[1]生态美学思想改变了人对自然的观照方式,力求展现人与自然之间真正“平等共生”。而在文学创作领域,迟子建即是这样一位满怀生态思想的文学书写者。迟子建在东北的小城长大,小城美丽的自然风光带给她深厚的滋养,她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家乡的地域美景融汇为她文学创作的血脉和灵魂,也成为她文学作品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在迟子建的眼中,自然从来不是人的对立物,她从不以人为中心和标准去感受自然,恰恰相反,自然总是以审美主体的姿态映照她的内心,每个季节每种变化的风景都深深打动她,被她温柔地感知,在她内心刻下深深烙印。对大自然的细腻观察、感知和体悟已融到她创作的血液。写作之笔一旦进入指间,自然美景便会在文字间铺展开来,《候鸟的勇敢》就是最为典型的一部。
在《候鸟的勇敢》中,迟子建以景仰的姿态书写了金瓮河的自然生态美景。作品以候鸟为中心,以一年四季时节变化为线索,倾注全部的温情书写金瓮河上候鸟生活的自然生态:春天,春风为候鸟归来亲吻开冰冻的金瓮河,阳光给大地调上钟情的“绿”色调,“吹开野花的心扉”[2]。夏日,山林在向晚阳光普照下绚丽多彩,霞光四溢,丰饶的山林,良好的生态使金瓮河流域成为鸟儿天然的粮仓。当秋天来临时,树叶和草叶由最初微黄变为通体金黄,由微红成为带有火焰似的光芒。而狂风卷集白雪的冬日,是为又一次召唤春天候鸟的归来蓄积能量……迟子建笔下,自然生态的四季流转充满了诗情画意,有其内在的灵动和魂魄,而联结和展现这灵魂的生灵——候鸟,种类繁多,丰富的鸟类与白山黑水构成一幅勃勃生机的自然生态美景图。
作品在候鸟自然生态美的全景观照中,以各种特写镜头拼接呈现了自然的神圣性和潜在的审美价值。《候鸟的勇敢》中的自然是纤尘不染的,没有任何“人化”的痕迹。自然不再是人眼中被“静观”的对象,而是带着主体的审美眼光来装扮自己,呈现出美的姿态。自然美景在迟子建的笔下总是浑然天成,具有天籁之美,即便是把自然当作“谋生”和享受对象的周铁牙,也要时时享受自然的润泽。自然生物雌雄之间的耳鬓厮磨、无尽相思和不离不弃给滥情的瓦镇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小说在展现自然审美价值的同时也解读了自然生物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不仅表现在大鸟救了被老虎吓晕的张黑脸,从此以后让他拥有了神秘的对自然现象预测的能力,还彰显在自然生物细微之处蕴含的生命本真中,以及这种生命本真对人世的启迪。当德秀师父与张黑脸结合之后,一直心存罪孽之感,坠入心底深渊,但当她看到花间蝴蝶后,从蝴蝶的生命短暂却尽情欢娱领悟到珍惜生命自由的真谛。因为懂得露珠形成的神圣过程,所以她渴望用马莲草托着的甘露来拯救自己,洗掉尘世法则束缚下思想和肉体的“污浊”。在这里,自然不再是“人化的自然”,而是人精神世界的引领者和启迪者,迟子建由此呈现出自然的神圣性。
小说中对自然生态的审美书写,推进了从“自然袪魅”到“自然复魅”的转变进程。传统的实践美学对自然美的阐释完全是以社会实践中人对自然的“人化”为中心的,这与工业革命所倡导的“自然的袪魅”一致,完全抹杀了自然的魅力和审美价值。而当生态美学用自然的视角、用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进行观照时,自然就开始走向“复魅”的历程,开始显示自己生态维度的审美价值。金瓮河的自然生态美景给人们带来了舒适的生活空间,所以当地的候鸟人会在春季转暖时飞回消暑,享受自然生态美食,外地的候鸟人也会适时蜂拥而来享受金瓮河完美的自然生态环境。金瓮河不再是实践美学眼中被人征服的“自然”,而是以独立的审美姿态彰显自己的存在价值。作为自然的“我”,提供美好的生存环境,作为人类的“你”因为“我”的美好而享受美好的生活空间,人与自然在“自然的复魅”中拉近关系,彼此和谐。自然的魅力不但体现在美丽的自然生态上,也体现在自然生物的生存智慧中。自然生灵看似没有人的主体思考判断意识,但在生态系统运行法则中,其生存智慧绝对不比人类低,也许因为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而低估了自然生灵的价值。迟子建用文学神笔,倾心描写具有神奇魅力的自然生灵,而自然的本真也会给复杂的人类生活以本质的启迪,绿头鸭的本能择偶交配让人类重温两情相悦圣洁纯粹情感的美好,蝴蝶在短暂的生命时空中绽放最灿烂绚丽的生命本色让承载负罪感的德秀师傅有了宽慰和对生命的感悟,甘露形成过程的艰辛给人带来拯救灵魂的希冀……作者以自然生态表象比照人类生活的现实图景,以自然生态表征人的生活百态,以自然独有的魅力启迪人类去更好地认知人自身和人生,重新从生态自然角度思考生活的真谛。
二
《候鸟的勇敢》中,作家的生态美学思想不仅表现在对自然维度生态美景的书写,更是通过巧妙的人物形象塑造来重新思考人的自我建构,尤其是“生态本性”建构,以达到人类对“自我”的全面认知。
小说中,以候鸟为中心来辐射、塑造人物,消解了传统美学思想中“人是主体性”的认知。在欧洲,随着17世纪理性主义的兴起,人类中心主义开始盛行,其中培根就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主人,主张“人类中心”,鼓吹“工具理性”,声称自己“已经获得了让自然和她的所有儿女成为你的奴隶、为你服务的真理”[3]。这种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受到20世纪以来各种哲学理论的挑战,以美国环境主义哲学家J.B科利考特为代表提出的新生态观,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整体生态观念,主张“生态平等”。在生态平等观念下,人与地球的关系超越以往的物质利益关系,开始着眼于人类与地球持续美好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在《候鸟的勇敢》创作中,迟子建秉持“生态平等”的创作理念,人物都是围绕“候鸟”进行设置和塑造的,所有的人物都可被称为“候鸟人”,且“候鸟人”的属性两两相对。“候鸟人”中,第一种是照顾候鸟的“候鸟人”,包括真心照顾候鸟的张黑脸和以候鸟作为谋生手段的周铁牙,两者对待候鸟的态度形成对照;第二种是和候鸟习性相同的“候鸟人”,包括暑归寒去的本地人和前来避暑的南方人,他们的“迁徙”是有硬件条件的,能迁徙的本地人必须有钱有闲,能避暑的南方人生活要相对富足,这样的“候鸟人”和没钱没地位的“本地人”形成鲜明对比;第三种就是和“候鸟”有关系的人,他们或是吃候鸟的人,或是谈论候鸟的人,或是研究候鸟的人,他们和候鸟形成对照。可以说瓦镇的芸芸众生都是“候鸟”生物辐射到的人物。迟子建以候鸟为中心的人物设置,消解了传统美学对“人是主体性”的界定,表达了生态文明时代对人的本性的重新思考,即探索人本质中的生态性——生态自我。生态美学思想观念中,“生态自我”的前提是人要退去以往自诩为“自然界主人”身份的光环,自然美也不再是人的主体性的最终成果[4],主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中心地位被解构,回到与生物共生的平等状态,同隶属于生物圈,人的特征也要通过生物属性才能得以彰显。
以候鸟为中心的人物形象设定,实现了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美学思想的超越。“人是自然的主体”“人对自然的驾驭”“自然是人化的自然”,这种思想一直存在于实践美学思想中,可见人的中心地位是不可撼动的,自然以其被动的方式进入人类视野,成为人类观照的对象。《候鸟的勇敢》则改变了这种认知方式,人物设定皆源于候鸟归来。因为候鸟的来临,引出工作人员与候鸟之间的感情纽带关系、工作人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候鸟是周铁牙利益关系的纽带,他躲避爱鸟的张黑脸,去套取候鸟并把候鸟作为礼物送给领导以谋取更大的利益,由此各级领导、饭店老板和候鸟之间,因为吃与被吃,也和候鸟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于是演绎了一场乌龙似的“禽流感”事件。禽流感事件中,先前被猎捕的野鸭这个看似被人征服的对象,变成了制造事件的“主体”。事件的发展态势都要依赖于候鸟主体的自身健康状况,此时候鸟的悠然和人的恐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动和主动形成了讽刺性的反转。禽流感风波过后,又形成新一层的主体间性关系,就是瓦镇的民众和候鸟之间的关系。由于候鸟迁徙的习性,瓦镇人觉得它们有离弃之嫌,所以并不喜欢它们。但一场禽流感过后,针对发病和死去的人的身份,人们突然把候鸟看作神兽,对它们开始顶礼膜拜,这是主体人对“人化”候鸟关系的又一次反转。迟子建用一次次反转的关系来消解人的主体地位,对人与人,尤其是人与自然两主体,进行主体间性的观照与对话,以此表征自然与人的“平等共生”的“间性”关系。
小说尝试以候鸟为中心的人物设定,进行人的“生态本性”的深度构建。迟子建以候鸟为中心,塑造了石秉德、德秀师父、张黑脸三个人物形象推进人的“生态本性”建构历程。石秉德是来筹建金瓮河候鸟研究站的二十六岁的小伙子,他以人的“主体性”姿态关注以候鸟为代表的自然生态,用人类发明的孵蛋器救助候鸟没有成功孵化的蛋,为受伤的候鸟做手术,科学地喂养候鸟,采取措施保护候鸟的安全,在河边设置钓鱼竿,研究候鸟的智慧。在石秉德这个人物身上,有对自然掠夺、占有和征服的突破,但“自然的主人”的痕迹仍很明显,对自然生物的观照仍是人类高大、生物弱小的姿态。可以说,石秉德是人类“生态本性”建构的初阶。
德秀师父是松雪庵的尼姑,成为尼姑是她悲苦的身世经历不得已的选择,所以在她身上既有人类俗世的“主体性”气息,也有身处自然加修行之后的“生态性”体现。她对张黑脸有很深很纯粹的情感,愿意为他穿衣打扮,生活上对他倍加关心,她对俗世的依恋就是对张黑脸的男女温情,唯有情感而没有任何物质利益的索取。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塑造体现了对“生态本性”建构中的“生态本源性”思考。“生态本源性”注重生命的诞生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人类如此,生物也是如此,生命的流动才是生态存在的本源。德秀师父的这种近乎本能的思考使她眼里观照的自然也都是本真和纯粹的,她会望着出双入对的野鸭叹气,对自然界中的“一朵花、一团雪、一棵树、一片云,甚至叶脉上的一颗晨露”的生命都有无限感怀。但她的“主体性”和“生态性”两面又决定了她思想和行动的矛盾性,她和张黑脸之间既有彰显生命力的冲动和疯狂,但也有怕因果报复的担心和恐惧,她时而能从自然生灵的生命痕迹中体悟人生的真谛,时而又陷入违反戒律痛苦的煎熬中。这个人物是人类“生态本性”建构的提升。
精心照顾候鸟的张黑脸有着和大自然生灵一样未被社会规则侵染的单纯思想,尤其是遇到危险被一只神鸟救了以后,他就呈现出人的属性的退化、自然属性的加强,记忆力和交往力的下降,但却获得了对自然的感知力和预知力。他可以准确地预知半个月后的天气,知道每种鸟的生活习性。他满怀生态平等观念,精心喂养失去父母的小雨燕,很客观地看待东方白鹳的生存行为,用最自然的方式喂养被石秉德解救的白鹳,鼓励它飞翔,理解它和伴侣的所有情感。他对候鸟、对自然满怀景仰,对自然的神圣性有最清楚的认知。每天早早起床穿戴整齐的投喂都充满了仪式感,对有翅膀的鸟类充满了无尽的崇拜,甚至期望自己可以长出翅膀飞翔。他用美好纯洁的情感去看待自然生物的求偶和繁衍,并践行着自己对德秀师父的情感诺言,不自卑、不畏人言。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倾尽了人的生态本性建构的深入思考。张黑脸与自然的交往方式不是周铁牙式的掠夺和占有,而是与自然平等共生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不张扬人对自然征服和驾驭的主体性,而是呈现人类主体和自然主体的主体间性关系,在他与自然平等亲和的关系中,自然完成从“袪魅”到“复魅”的过渡,呈现出自身的审美维度,彰显出潜在的审美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人也进行着自我“生态本性”的深入建构。
迟子建通过石秉德、德秀师父和张黑脸三个人物探讨人的“生态本性”形成的三个阶段。除此之外,小说中其他人物的设置也都体现着人从“工具理性”向“生态本性”回归的思想:和候鸟的春来冬去的轨迹相同的候鸟人已渐渐失去人的主体对自然的征服和占有欲望,让自己的生活习性回归自然生态本性;随着候鸟迁徙而经营生意的瓦镇商贩们,虽没有正确认知自然生态影响下的日常生活活动,但因为“禽流感”事件的发生,他们开始顶礼膜拜候鸟的“神圣性”;即便是那些完全依靠主体意识、不顾自然生态的周铁牙等人,也开始从发生在候鸟身上的诸多事件开始反思,进行控制人作为主体的征服欲。小说全面地呈现了候鸟与人的平等关系,以及在候鸟的勇敢抗争下人的主体意识的削弱,迟子建以此召唤人的生态本性的回归。
三
生态美学不同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美学观,人类中心主义美学观立足于抽象的美的本质的探讨,是一种注重思辨的抽象美学。思辨美学严重脱离人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观念。但生态美学观“是一种人生的美学,而人都是立足于大地之上,生活于世界之中,与空间紧密相连,所以生态美学也是一种空间美学”[5]。海德格尔曾就荷尔德林的诗详细地阐释过生态美学的“空间性”,他说:“在这里,‘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有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与。”[6]人居于这样的家园,从而“诗意地栖居”,获得审美生存。《候鸟的勇敢》中,作者在生态审美观的统摄下,独具匠心地构建了小说的生态空间,并赋予生态空间以不同的表征,同时也更好地诠释了海德格尔的在“家园”中“诗意地栖居”的审美状态。
首先,在小说叙事进程中,金瓮河流域是表征瓦镇人和候鸟存在状态的总体生态空间。在迟子建笔下,金瓮河不是单纯的瓦镇人和候鸟的生活环境,而是良好的生态空间——既是候鸟也是瓦镇人的“家园”。在这个家园中,候鸟可以在适宜的温度中获得丰美的食物,可以寻求配偶、繁衍后代,维护着生态环链的平衡;同样,这个家园也是瓦镇人居住、依寓和逗留所在,瓦镇人和金瓮河生态空间血肉相连,不可分割,金瓮河的生态空间时刻表征着瓦镇人和候鸟的存在状态。金瓮河的生态空间良好,不但引来更多候鸟的回归,还让稀有的东方白鹳也飞来生存繁衍,因为它们也感受到“家”的安定和舒适。瓦镇那些出走有钱又有闲的“候鸟人”无论走向哪里,都会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回到瓦镇,一方面是因为金瓮河舒适的生态空间,更重要的是这里是生养他们的“家园”。在这个安定的家园中,它们能快速恢复身份,知道自己“曾经是谁”,理所应当地享受着认为应该享受的待遇,也有与留守的瓦镇当地人比较后的优越感。在整个金瓮河大的生态空间中,候鸟、留守鸟类与瓦镇候鸟人和留守人为了寻找“家园”的共同目的而走到了一起。小说叙事中人与鸟的各种爱恨纠葛,表征着人对自然家园的皈依,人与自然家园融为一体的亲密存在。
其次,在更具体的小说叙事中,构建了瓦镇平安大街和金瓮河管护站两个具体空间。平安大街是瓦镇人的活动中心,是瓦镇人气最旺的街道,这里商铺林立,应有尽有,展现着瓦镇人的具体生活状态。金瓮河管护站远离“闹市”的瓦镇,被设在金瓮河中游,一幢平层木刻楞房子,简单朴素。一个是烟火气浓郁的具体生活空间,一个处在世外桃源中的具体自然空间,这两个空间理论上应该是分离或者说是对立的,但实际上,小说叙事中匠心安排的这两个空间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第一,管护站是为保护候鸟设置的,丰富食物的及时投喂保护候鸟的生存繁衍,也是保护生态链条的完整和健康。而良好的生态正是瓦镇兴盛的最根本保证,可以引来各种“候鸟人”消暑度假,支撑瓦镇经济发展,保障瓦镇人的生活质量,所以看似两个远离的空间实际表征着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第二,联系管护站和平安大街的主要纽带就是看护管护站的周铁牙和张黑脸,通过他们的休假、工作、各种生活活动把两个空间紧密联系起来。正是周铁牙把野鸭作为尝鲜的野味带给瓦镇的重要人物而引起的“禽流感”事件,才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自然与人的关系,认识到自然的神圣性,也正是通过周铁牙以候鸟为媒介的谋取钱财,或猎杀之后的送礼揭示了人作为主体对自然征服欲望的丑陋和愚蠢,并通过张黑脸这个人物——无论从本性上,还是从思想、认知上都以和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物来诠释“诗意地栖居”的人应该具有的存在状态。
再次,小说还设置了既现实又乌托邦的理想空间,也是真正“诗意地栖居”的空间所在——松雪庵。松雪庵依托于金瓮河流域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庵内的建筑材料取于自然,庵内的美景也是原生态,加之泥塑彩绘,形象生动朴拙的各种菩萨塑像,更让凡尘中的人心有了安全和依托之感。海德格尔所谈的“诗意地栖居”意指“天地神人四方游戏”,从而建造自己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获得更多的审美存在。迟子建在她的小说创作中一直心怀皈依之感,皈依宗教,皈依自然,以天地自然为境,心怀宗教神圣,在“天地神人共处下”使现实的日常生活充满诗意,这一切都应和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迟子建笔力深厚,她巧妙设置尼姑庵内三个女性形象来言说“诗意地栖居”的可能和境界。云果师父是贪恋尘世、修行不深的尼姑,从她来尼姑庵的各种猜测可以看出,从她佩戴的各类佛珠、星月菩提念珠、红玛瑙手串、明黄色蜜蜡手串可以看出,尤其是从她爱上挑的眉毛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身处自然纯净之地,有佛家经典陶冶,云果身上的世俗和超越在不断地斗争、融合,慢慢化解了尘世间的“不安分”,让她在庵内寻找到安定和自我。“松雪庵”对于她而言是一个“关系场域”,在这里她逐渐完成面对世界、面对自我的认知,这也是“诗意地栖居”的第一个境界。德秀师父是被现实逼迫而来,现实的遭遇让她的身心遭受巨大打击,成为无“家”可归的人。来到松雪庵,在这远离尘世的自然清净之地,她找到了“家”的依托、安定的感觉,这时的她可以感受到身边大自然的生命和美好,并能从中获得对于自身生命和人生的诸多感悟,这是“诗意地栖居”的第二境界。松雪庵中不但有各种神灵雕塑,还有一个“神”一样的人物就是师太慧雪。她是在五台山削发为尼,被请来护法的,小说没有对慧雪做过多的具象描绘,但通过这个人物给瓦镇人做讲座的言语中可以看出,她对现实生活有清晰透彻的洞察,对自然有“顺其自然,尊重生态,尊重生命”的理念,让自己化入自然,不纠结人世,成为一个神圣又自然的存在,这是小说想要表达“诗意地栖居”的最高境界。
迟子建以独具匠心之笔,在小说中设置了广阔的自然生态空间、具体的现实空间,来观照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并把“松雪庵”设置成理想的精神空间。松雪庵看似是一个佛家神仙之地,但迟子建在构建中通过这里生活和朝拜的人,将神和人紧密相连,同时又交融于自然天地空间之中,用具象人物的活动诠释了海德格尔生态美学思想中“诗意地栖居”的深刻内涵和多种境界。
四
生态美学思想中独有的“生命性”内涵,是区别于人类中心主义美学的思想之一。认识论美学倡导外在的形式之美,如“比例、对称、和谐、黄金分割”等,但过分强调外在形式就会导致一种无机性和纯形式性:生态美学则抛弃了认识论美学的做法,把“生命力”引入美学范畴,并把它作为生态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著名的“盖娅定则”就是生态人文主义的重要内涵,它将地球比喻为能进行新陈代谢充满生命活力的地母盖娅,以是否充满生命力和健康状态作为衡量自然生态的重要标准。生态美学的“生命力”强调展现自然生态的健康状态——“生生不息”与“气韵生动”。
《候鸟的勇敢》中,作者用一支妙笔勾画出具有蓬勃生命力的自然生态画卷:金瓮河河边,漂亮的绿头雄鸭和雌鸭的缠绵悱恻,奏响了他们孕育生命的序曲;三圣殿烟囱后的一对东方白鹳,雄鸟受伤之后雌鸟不离不弃的情感历程,表征了自然生物对生命价值的认知和践行:燕子带领雏燕无数次地练习飞翔,都是为了延续美好的生命;茂草中静悄悄开放的野花,自由恣意;自然界中蝴蝶也能很好地洞知生命的过程和意义,在生的时刻珍惜生命的可贵,焕发出生命最美丽的色彩。
在迟子建笔下,不但铺设了自然生物五彩斑斓的生命色彩,而且也密切关注人的精神价值和灵魂归宿,体现了人文主义特征。小说中设置的人物,从“生命力”的角度观照,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能感知和彰显生命力的人,一种是与真正“生命力”相对的人。前者如张黑脸、德秀师父、慧雪师太以及石秉德等人,石秉德对候鸟及候鸟蛋的救助、孵化和培育,是对自然生物生命的尊重;德秀师父对自然花草虫蝶的生与死的感悟,是由物及人、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更高理解;张黑脸眼中万物皆生灵、万物皆生命的观照方式已进入“生生不息”的哲学范畴;而慧雪师太对生命“顺其自然”的无为态度正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这种生命力包括人和自然生物在内,爆发出人与生物紧密联系的内在能量,是整个宇宙生生不息的动力。除此之外,小说还展现了另外一种“生命力”,即以瓦镇为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看似和自然生态无关,却处处体现和自然生命力的紧密联系与对比。瓦镇经济兴盛、人丁兴旺时节正是候鸟归来之时;食用野鸭的邱老和庄如来都是注重养生和生命力旺盛的人,但和候鸟相比,生命如此不堪一击;瓦镇的人喜欢达子香野性的美和旺盛的生命力,用它来装扮自己的家,让家充满鲜活的生气;瓦镇的男女关系混杂、肮脏的肉体交易全然没有金瓮河生物结伴求偶的美感,原因就在于后者是繁衍生命的圣举,而前者只是满足人的肉体欲望的龌龊行为。迟子建将两种生命力加以对比,诠释出“生命力”的真正内涵。真正的生命力是:它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生态的健康状态,既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延续,又有保持健康生态平衡的环链性。
生态美学在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并没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而是延伸出一种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结合的新的精神——生态人文主义精神,这是一种既包括人的维度又包括自然维度的新时代精神,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迟子建一直怀有对自然皈依之感,她不是把自然作为人的生活环境看待,而是将其视作与人类共生的家园。她用自然生态的健康隐喻人性的本真、纯美和蓬勃的生命力,希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她的小说既包括自然主义精神,又时刻关注人的价值和灵魂,饱含生态人文主义精神。
迟子建的故乡情结深厚,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深深烙刻在她的心中,她对自然的热爱融化为她创作的血液,转化为对自然生灵的尊重和对自然精神的皈依。对于人和人性,迟子建有着深刻的洞察和解剖,而且一直保持人类的本真、纯洁以及对生命力的发现和赞美,因此她的叙事总是能巧妙地把人与自然的维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展现人的存在状态,呼吁真正的“诗意地栖居”。正是这样的创作理念和表现手法,无不暗合“生态文明时代”美学领域的新思想——生态美学。可以说,迟子建以《候鸟的勇敢》为典范,用生花妙笔,用具象的人物刻画和自然描写,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和应和时代的主题,在文学范畴内展现、深刻阐释生态美学思想,带给读者一场穿行于文学画卷和美学思想之间的阅读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