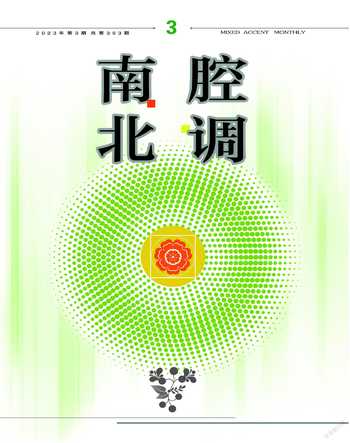文学虚构介入现实关怀
王玥枭

摘要:阿乙的小說《骗子来到南方》通过三个彼此关联的故事——唐南生的集资骗局、监控盲点处发生的谋杀案以及各部门彼此推诿形成的民生难题,呈现出当下社会“系统”的封闭困境:单向度的价值观支配着生命的意义,抽象化的资本逻辑将人简化为原子化的个体。受“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影响,两厢情愿的骗与被骗很难终结。叙述者凭借从在场抽离的“第三者书写”,构建叙事的权威。但阿乙没有满足于纯粹客观的冷静记录,他将温情深埋于文本细节,为文学虚构介入现实关怀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
关键词:阿乙;《骗子来到南方》;系统;共同富裕;“第三者书写”
小说《骗子来到南方》由三个彼此交织的故事构成:随着高铁线路开通,“骗子”唐南生来到偏僻的小城红乌,通过捏造的空头公司“更江南集团”进行集资,骗取了民众的众多钱财却依然在当地逍遥法外,直到一个夜晚突然失踪;以王池深为首的几位被骗股东寻找到街头监控的盲点,贿赂路边临时民工,用暴力宣判了唐南生的死刑;警方借助摄像头调查案情,在一筹莫展之际接到潘洹夫的举报电话,最终在柏油马路下发现了唐的尸体,此案告破。此外,小说中还有一个可被视作引子的情节:“我”成为著名作家后,回到离开17年的家乡,凭借自己的人脉资源整修了母亲家的自来水管道,在这期间,人们不断向“我”诉说着骗子唐南生的传奇,“我”最终也见证了针对他的离奇凶案。文本中的三个故事不仅在时空上紧密交织,还通过“我”的叙述视点统摄于一体。然而,这种融合并非出自“我”置身事外的整体思考,而是借用信息/数据的“扫描”与整合。这些碎片化的情节被作者紧密编织进整个文本:从自来水公司彼此推诿的“循环风”到欺骗与受骗的无限繁衍,从被“虹吸效应”卷入资本市场的偏远小城,到笼罩万物的电子监控媒介……真正的主人公不是骗子,甚至已不再是“人”,而是一个又一个独立运行又彼此相关的封闭“系统”,这些“系统”包括唐南生构建起的诈骗体系、大街小巷无所不在的监控网络、犯罪团伙处心积虑设计的死亡谜团,总体的社会运作结构。错综复杂的“系统”,让这场看似拙劣的骗局变得旷日持久,也让众人在悲剧终结后仍然表现出麻木不仁。
在访谈中,阿乙认为这部作品比以往作品更贴近生活:“整个故事写的就是这样一个荒谬的现实,我的小说背景一贯和现实有关系,但不是这么贴近,这部小说如此贴近,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渗入我们的生活中,像空气和水一样。” [1]那么,对这篇小说的理解也应该突破文本自身或“纯文学”的思考范式,将小说的人物与情节放置在“现实”的深层结构下追问,让历史、当下的真实空气与小说的虚构世界彼此映射。
一、“困在系统里的人”
2020年9月8日,《人物》杂志在其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发表了一篇专题报道,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该文通过详实的数据指出:骑手在外卖系统算法和数据驱动下,不得不与死神赛跑,让“送外卖”也变成新的高危职业。这篇报道之所以备受关注,不仅因为文章对外卖骑手这一群体的人文关怀,更在于将“系统”的概念引入对当下现实的思考。我们的世界似乎日益被笼罩在庞大的“系统”之下,个体的价值、生命的意义越来越被抽象的“资本”所支配。当人与系统的单向沟通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切联结,“物化”的噩梦随之到来。职场人士和学生群体口中频频出现的概念——内卷,同样以一种尖锐的方式呈现出当下的“系统”困境——在封闭体系的规训下,生命的意义被不断窄化,竞争随之加剧,个体寻求发展出路时频频陷入死循环,于是“骗子”来到“南方”,这里也成为时代症候的表征。
故事依托的空间小城红乌,即是一片被“系统”遗忘的飞地。两年前,红乌高铁站开通:这“是对他们(红乌人)的一次重新命名和授予……人民都感觉自己置身于世界与历史的中心,或者至少是被纳入某张网或某个体系中”[2]。然而,这种美梦很快就濒临破碎。轨道交通并未给此地带来神话般的招商引资,反而因“虹吸效应”卷携走了本地的资源和人才。红乌虽已被纳入系统之中,但却被“进步”的未来抛弃,没有成为得利者,反而成为“被剥削者”。当骗子唐南生操持着崭新的宏大话语,发售股权,向人们兜售集资致富的神话时,红乌市出现了历史罕见的群体骚乱。对于那些未能第一时间拥有所谓的《协议书》的人来说,“痛苦是双重的。一是错过近在眼前的致富机会,二是再次在街坊面前暴露出软弱与无能。过去他们和学区房无缘,现在又没办法弄到一份由银象江南投资有限公司盖章的《协议书》。他们在社会中的估价再次被无情地压低。”[3] 在一个被“系统”所笼罩的时代,人的价值很难靠自我认定和完成,不可避免听凭体系给定的标准。“被社会低估”正是“系统”的宣判,它令个体的存在变得虚无,产生被抛到历史之外的深刻失落。
在这种社会背景中,红乌民众深陷诈骗难以自拔的行为就不难被理解,有骗子在接受采访时就这样自我辩解:“不是我要骗他们,而是他们要我骗。”[4]人们对欺骗的渴求,恰恰不是因为被虚假蒙蔽,而源自对真实、实在的渴望:在一个“全民向钱看”的时代,“被抛弃”的恐惧驱使人们用财富证明自己。在封闭的红乌,这种欲望只会无限增殖,甚至,试图证明自己未被欺骗的人只能选择继续受骗。即使受骗者之间也没有真正的联合,因为这些所谓的股东从未休戚与共,仅仅盯着自己的利益,甚至各怀鬼胎。唐南生只需抓住寡妇新姐一人略施恩惠,股东间的结盟便土崩瓦解,甚至这种恩惠,还是变相让其再度投钱。在最后,随着一次次斗争的失利,红乌的股东甚至内化了骗子的逻辑:“就像是极富耐心的溺死者,在一步步等待别人下水,好替代自己成为新的水鬼。”[5]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然变成了金钱的债权交易,亲人之间也未曾流露出温情。“骗子”播撒在红乌城南的金雀花宛若这些人的心灵隐喻: “为了存活,为了内心最黑暗的欲望,它们几乎是毫无死角地搂住对方,相互倾轧、杀害,相互切割。它们吃对方的肉,喝对方的血……”“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6]最初,人们渴望用金钱实现自我价值、紧跟时代潮流甚至参与历史进程,而后,人们对赎回金钱的绝望挣扎,又通过“系统”的无限扩张酿造新的灾难。
相较而下,唐南生似乎是这部小说中最具自我意识的主体形象,他构建起了这个吞噬红乌众人的“体系”并“稳坐钓鱼台”。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利用小说前后的几个片段拼凑出他的生平:
唐南生,自称台湾人,实为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赖店镇留仙村十一组人。妻子患结核病早逝,未有子女。其家常年无人居住。老屋在几年前被台风摧毁。
2013年,唐南生的更江南集团在红乌发售股权,开展系列活动,被民众抢购一空。混迹于各种场合的唐南生常常失态,在赌场中冲动急躁、损失颇多,甚至在一次招待会上醉酒后失态大喊“想发财,做梦吧!”即使如此,也未阻止人们对他的轻信。
2017年,股东找唐南生要求退钱。但在法律保护下,唐选择了分期撤资。此后,唐南生不再费心向红乌股东编造新项目,而是“有钱还钱,无钱筹钱”。其间他多次离开,又都“诚信”归来。
2019年的一天夜里,摄像头捕捉到唐南生在哭泣。一旁跳广场舞的市民对此并无关注。随后,在一处监控盲点下,唐南生被私刑审判并杀害。
正如这些情节所示的,比起骗子常见的理性、冷酷,唐南生的举止简直难与他巨大的成功匹配。相较于行骗者通常的筹划算计,唐南生的骗术特点更在于概念的密集和喷薄其中的激情:从“若不能克服自己的弱点,就把它变成优点”[7]等被杜撰的西方经济学话语到面对新姐时“你必须这样”“这是你最佳选择”的父权式语气,从 “二幺〇四工程”等匿名计划到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商业热词,甚至还有对项目弱点的主动展示……凡此种种都表现了唐南生高超的话术技巧,他灵活地将种种宏大叙述,通过自我编织转化为掌控民众的“主人话语”。所以,与其说唐南生是“财富系统”的缔造者,不如说他是系统中承担“转换器”的组件,把人们虚幻的狂想转换为看似周密的骗局。甚至可以说:不是“个体”唐南生在说话,而是“语言”在说话,是种种关于财富的“时代话语”,向这个充满呆滞感、似乎被“进步”所抛弃的小城呼唤。这些关于“个人奋斗”“政府规划”的话语体系无一不带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唤寻”红乌民众去填充“系统”的空缺。细究起来,读者可以发现:出生于莆田重要的侨乡赖店镇,唐南生却仍是一穷二白的农民。他同样历经人祸与天灾,也是“时代进步”中被抛却的一员。事实上,唐南生的骗术本身就反映出他心理的“病态”,在骗术引起众人怀疑时,他不是携巨款逃走,而是直面债主,“享受那种冲浪才有的快感”[8],在对群众的撩拨和玩弄中感受某种满足。也许,只有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让他获得生存必要的掌控感与安全感。
同样迥异于亿万富翁应有的多彩人生,唐南生的日常活动异常死板,“除开应酬,唐南生一天三餐都在肯德基快餐店解决。……每天往返六次,合计十一点四公里,对应手机里统计的步数是两万步。唐南生将它理解为一种旨意,每天虔诚且甜蜜地去执行它,甚少违反”[9],他只能用机械化的行为把自己填入骨架,才能拥有活着的感觉。这位狡诈多端的骗子信仰一个电子设备统计出的数字,坐拥无数钱财却热衷于美国快餐。如此吊诡的反差绝非闲笔,它们分别标识出两个主宰当今时代的深刻“系统”:物化人类的电子媒介及其深处的数字逻辑与被奉为世界想象却也是文化入侵手段的跨国资本。虚拟的机械给予人们所谓的确定性和安全感,“肯德基”则令人啼笑皆非地成为小城红乌唯一所谓的“世界性”因素。种种细节,其实是唐南生挤进一个更大“系统”的内在渴望的投射。最终,他没有被所谓的“系统”接纳,没有摆脱被抛弃的宿命,在自己构造的红乌骗局里,他甚至都“求死不能”。在生命最后的一个夜晚,不知出于对不安命运的预感,还是自我良心的突然羞愧,唐南生忍不住地在路边哭泣,虽被人目击却没有获得帮助。最终,他只能在社会的冷漠中重新封闭自己,再次变成“系统”“非人”的化身。
二、盲区内的谋杀案
阿乙在小说中建构了错综复杂的种种“系统”,虽然,个体随时随地被系统所覆盖吞噬,但却很难得到系统的保护,甚至在很多时候,“非法主义”的行为正是借“系统”之名实施,或者被“系统”纵容才得以实现。
在谋杀案发生后,两名青年警官根据上级指令用原始的方式走访调查,但除了唐南生的身份外一无所获。队长高晓强还试图辩解:“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有了监控,就丢掉其他侦查技能。你们得有一技之长,否则就容易被替代。看监控是小学生都会的事情。”[10]但“科技比我们的想象要快”[11],无所不在的监控镜头使很多传统的侦查技能失去价值。在密集的摄像头和电子技术的帮助下,警官很快拼凑出唐南生消失前的轨迹,并据此开展对永修路的搜查。两位警官利用当地居民法律意识淡薄,用过期的搜查证敲开这些“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法律程序了解更少”[12]的居民的家门,展开了“领导不会批准”“也不会阻止”的入室搜查,甚至还听信一则建构在道德偏见上的传闻,给一名独身的文艺女青年带来莫大的羞辱。
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入室搜查行为和唐南生的集资敛财一样,都是 “非法主义”的具体表现。前者虽然是为了法律意义上的正义,但也隐藏着以刑侦之名展开的“暴力”。集资敛财欺骗了大量民众,以非法方式攫取巨额财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为都被本应维护正义的“系统”所覆盖,或者以“系统”之名实施,或者被“系统”纵容才得以实现。青年警官侵犯人权的调查方式,可以被视作意图尽快破案的“权变”。唐南生大摇大摆地横行红乌,拥有法律与监控的保护,源自政府官员为求经济发展给予民间集资的默许。所以,无论是来自平民层面的财产非法主义,还是特权行使中出现的权力非法主义,它们都不在社会总体运行的“系统”之外,反而内在于隐形的规范之内[13]。这些“规范”怀疑甚至歧视如“文艺女青年”那样的“不正常的人”,让她成为执法过程中的无辜牺牲品。所谓的“系统”,也让王池深等被骗股东求告无门、难寻正义,他们最终妄图替天行道,铤而走险,策划了这场残酷的凶案。
从人道的角度来说,倘若监控设备更完善,唐南生的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作者也曾感叹道:“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盲区会被消灭。制造和铺设摄像头的成本越来越低,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去扩张繁衍。它们繁衍起来就像城南荒地上的灌木一样迅猛。”[14]但是,如果不再存在盲区,现代的凶案似乎也无法书写。所以,“罪恶”是否能依靠摄像头来杜绝?答案可能并不乐观。一方面,监控社会在制造出一条条被监视的大道时,也创造着一处处被命名为盲点的阴沟。探头一视同仁地直面视野所及万物,但正是在这些可见的图像下,被忽视掉的是隐形结构中存在的等级秩序及其不公正。“在生活中,谁会花心思去記忆一名加油工、一名送水员、一名清洁工的样子呢?”[15]两位警官的眼睛同样内化了摄像头的逻辑,也未对被当今社会轻易忽视的农民工“曝光”,导致案情毫无进展。另一方面,纤悉无遗的摄像头画面,并没有给人带来源自形象的情感共鸣,反而加剧着冷漠。“被置于监控设备之下的人产生了去人格化、去主体化、去自主化的效应”[16],个体经验被程序化,压缩为钟表式的平庸自动性,生命被贬低到输入与输出的“演算”层级,同化为机械地重复。人不仅被“原子化”,还沦为失却共情的“非人”。假如在唐南生高调宣称“你们自己数数有多少摄像头吧,你们想要坐牢的话,就动手”[17]时,处理监控数据的计算机能给出正义的结果,灾难(既是投资者的倾家荡产也是唐南生的逍遥法外)就能被阻止;如果在唐南生独自哭泣时,俯视这一切的镜头能呼唤他人的关爱,至少不会有最后的凶案。
在此意义上,凶案与其说是发生于监控之外,不如说发生在监控盲点之内。这场精心策划的谋杀,又何尝不能被看作一个凭借监控漏洞建立起的严密“系统”呢?从事前的勘测到执行凶杀,从行刑宣判到化名签字,对外界来说,计划完全天衣无缝。案情最终的告破是因为内部的叛变。潘洹夫,这位曾经谋杀行动最热情的支持者,突然在怀疑和思考后倒戈一击,将凶手全盘托出。对于这位叛变者,凶案主谋王池深早就对他心怀惮惧——“因为他热爱真理”[18]。生活中,潘洹夫宛如一位当代的“堂吉诃德”——不满于公务员的庸碌日常、主动清点超市上有违健康标准的食品、拒绝发售消费卡、以时代的“匕首投枪”自居……在其公布于社交媒体上的种种言论里,充斥着对诸如“善”“恶”的质问和“容不得任何沙粒”般对纯洁性的偏执。然而,与其说这些行为源自正义,不如说这些是一种无法被规约的混沌。因为早在凶案尚未发生时,潘洹夫就已觉察到犯罪动向,这与始终冷漠拍摄下一切的监控探头何其相似!检举凶手对他来说,不过是将自己从自我诘难的道德困境中解脱的手段。
阿乙设计这样一位疯子般的人物作为破案的核心,最终的正义就被质疑与拷问。因为封闭的“系统”无法给人以出路,所以王池深等人的暴力行为便似乎带上了些许神圣的光环。尽管九位“义士”自称的代号充满着滑稽性,但他们对唐南生宣读的长达六页的判决书,又无疑使这场私刑变得无比庄重。暴力,是他们试图挣脱“系统”禁锢的极端尝试,也是这些走投无路的股东们最后的挣扎。
唐南生死后,红乌的民众依旧麻木愚钝——他们拒绝承认自己的“受骗”,惋惜骗子的早逝,甚至假想唐南生的英明以自慰。无论如何,随着唐南生的死亡,这场旷日持久的诈骗落幕了。但这与其说是一次令人快慰的解放,不如说是更露骨的伤害,它在实质上暴露出红乌“被抛弃”的宿命,这里是一片无法被发展之光照耀的时代盲区。因为对“致富历史”的参与再度变得遥不可及,无人行骗,红乌民众只得自欺,延续“系统”播撒给他们的罪孽。就像福柯在论及监狱“替代方案”时给出的结论:“如果不探索一个新的社会,就不可能有监狱改革!”[19]倘若没有“共同富裕”的实现,没有一种克服全球市场化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匮乏感,重建人与他人和社会的深度关联的“共同富裕”,两厢情愿的骗与被骗或许将了无终止。
三、冷静叙述后的温情
关于小说中三个故事的关联,有论者从结构的层面上理解,小说前6节与后6节相接续,讲述“我”回到老家见证修理自来水管的经历以及针对骗子的谋杀案,中间则宕开一笔,“整篇小说呈现出类似座机电话听筒的几何形状” [20]。这一说法很有启发性,它提示我们注意小说中“我”的重要性——来到“南方”的不仅有骗子,还有业已成为著名作家的“我”本人。于是,取自作家真实经历的修水管情节,就不能被简单视作一个引子或插曲,而是与小说主题之间存在深刻的关联。
水管难题可以被追溯到很多年前,在“我”幼时,原本理性的父親按捺不住“让一大家子住进商品房的欲望”[21],错误搬进一处无法接通自来水的房屋。多少年过去,生活用水仍只能靠细线般的积水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自来水公司的几个部门推诿塞责,打电话的居民也未实现有效地联合,原文有这样的描述:“母亲说:‘打了啊,光一家打没有用,要十家一起打。可是在家的都是老人家,没法打。青年人都在外头,即使在屋,也不见得齐心。”[22]母亲的窘境说明:孤立的原子化个体在现代社会势单力薄,经常放弃解决问题的努力,甚至以“增压泵”这样的方式损人以利己。直到著名作家“我”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偶然相遇,把此事告知对方,水管才被最终疏通。
这段情节貌不惊人,甚至可谓稀松平常。然而,当我们将这段情节与小说中另外两个故事并置,其间的共通性颇值得关注:它们都呈现出相似的“系统”式难题。在修水管过程中各个部门层层推诿,呈现出“循环风”般的结构困境,个人在其中难以寻到解决民生问题的可能;资本市场的发展将无数红乌民众虹吸其中,个体并没有因此实现发财梦,反而被唐南生一手创办的集资模式套牢,难以自拔;借助监控技术开展的刑侦对案情一筹莫展,摄像探头的严密网络给不出正义的答案,更助长了残酷和冷漠,忽略了那些我们本应给予关怀的弱者。在这些故事中,笼罩众人的“系统”夺去具体个人的力量,它无限滋生并繁衍着新的罪孽。
如果说三个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故事共同呈现出“系统”的难题,那么,小说对这三个故事的叙述方式则深刻体现出作家阿乙对这一现实困境的思考。对于现代小说而言,“怎么写”似乎是比“写什么”更为吃劲的一件事,所以,笔者着重分析小说的叙述方式就是一件必要的事。小说把叙述严格限制在第一人称限制视角“我”的身上,这个“我”不断地重复着自己相较红乌众人拥有的某种超越性地位:著名作家的身份、与种种能把握时局者的交往(人大代表、警察同学等),还有今昔之间、物是人非的对比……全知视角的权威性、信息的密集度,都是在表现其优势地位。因为,不同于福柯笔下的通过禁锢运作的惩戒社会,一个社会的控制行为“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23]。任何重要的决策都依赖着信息达成。小说不止一处暗示出“我”与社会“高层”的交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小说中描述的“我”和一位已调至外县任职的刘姓处级干部的对话:“我就更江南的事请教于他。他沉吟良久,说:‘你说是骗子可以,说不是也行。最重要的还是看实绩。事情如果成了,我们就要承认它是一种创新。要看你怎么看。我没有将他的话转述给亲人们。”[24]其实,正是这一“信息”,让“我”成为唯一没有陷入唐南生骗局的人。所以,确切地说,并不是“我”的作家身份或由此带来的人脉关系,而是更为权威的信息将“我”与众人区隔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在信息占有上具有他人不可比拟的优势,身为作家的“我”更不缺乏评述的能力,但故事的讲述却始终在一种冷静克制的语调下展开。小说中的“我”不仅不对周围的事件给予评述,甚至避免表达自我心灵的感受。以唐南生为例,作者对他形象的描写都是通过他者目光的拼凑,从激动迎接的市民到激愤难抑的债权人的目光,从“无所不在”的监控探头再到被手机镜头捕捉的尸体。种种来自道听途说的叙述,始终保持着“反高潮”的静止节奏,甚至,无论是对唐南生的骗局,还是对王池深等人的暴行,叙述者都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态度,更没有义愤填膺。小说中还有一个阿乙式的残忍片段:在警察开掘现场,一名小女孩莫名其妙地飞奔入机动车道,血淋淋地撞击向一辆汽车。面对这样的场景,叙述者也并未改变他的腔调,描绘始终冰冷而无情,只负责记录,不提供分析。这种视角与“我”竭力逃离红乌的渴望是一致的。对拥有著名作家的身份的“我”来说,故乡小镇简直是生命中的某种污点。但这种书写在让叙述者隔绝情感、保持客观冷静的同时,也停止了“我”对社会现实进一步地思辨。
文本中的“我”,了知一切却又缄默不语,以抽离主观感情的方式来描述客观显示,笔者将这一写作视觉称为“第三者书写”。可以肯定的是,“第三者书写”是隐形作者自觉的叙事策略。文本中有一处夫子自道:“我相信有读者在把这篇小说看到一半时,就知道谜底是什么了。我自豪于自己有不少这样感觉敏锐的读者。不过今天所写的这篇小说,更多的意图是让读者看见生活的某一块或者某一面。生活滚滚向前,我们在其中浮沉,我扫描出其中一段,大意就是这样。”[25]“扫描”这个词非常精辟,它在有意无意中将“第三者书写”与小说的核心意象摄像头关联在一起。“我”的身份是作家,又是种种事件的记录者,身处红乌,但却时刻想当一位“局外人”。文本中冷静甚至冷漠地叙述语调,和无处不在的“数据”“信息”一样,是对个体情感的抽离,隐含着“我”保持自己理性时的不安:只要“我”身陷迷狂参与投资,便也有成为“乌合之众”的危险,无法维持自身的优势地位。
在小说中,本为维护安全而生的监控探头却可能沦为罪恶的帮凶,许多最先表现出了新的自由的事物,“同时也就加入堪与最严酷的禁锢相提并论的控制机制”[26]。身处这样的“控制社会”之中,“我”的焦虑正反映出“相信世界”能力的匮乏,既没有改变世界的勇气,也没有拯救、帮助他人的意愿。在德勒兹看来:“我们完全失掉了世界,有人剥夺了我们的世界。相信世界,也就是激起一些哪怕是很小的避开控制的事件,或者是使一些哪怕在平面上或立体上都很小的新的时空产生。”[27]一个无法“相信世界”的人,必然选择以漠然的姿态描述事件,这种客观角度虽然使洞彻“系统”具有了可能性,但也使人同时失去了与他人共鸣的情感体验。看似居高临下、拥有理性的“我”,也并非能真正战胜骗局之人。
在惯常的认知中,骗子的成功源于他对人性的洞察。这一论断固然有合理之处,但其立论的根基在于对人性的贬义认知。事实上,骗术之所以产生,与其说是它抓住了人们的贪欲、愚昧等弱点,不如说它真切击中了受害者的愿望,甚至是那些毫不恶俗、真挚纯洁的心愿。在这点上,“我”的父亲就是一个例子:“让一大家子人住进商品房的欲望战胜了他的理智,他原本应该是故乡少有的几个理性的人。”[28] “(我父亲自)2009年中风不良于行后,多半时间用于公园锻炼,期待能再次拥有如飞的步履,或者像骗子承诺的,‘可以重新下地劳动。” [29]甚至众人对财富变态的渴望,也无法被笼统概括为贪念,它源自对美好生活的认知与希冀。这种幻觉是远比理性更为深挚的执念。
因为真正优秀的作家,他的温情总是看透真相后的同情和悲悯,所以,阿乙对骗术的另类解读,其实是作者的人文关怀的特殊表达,而除此之外,阿乙还将自己的人文关怀散布于文本的细微处,与“第三者书写”的冷漠构成潜隐的对话。在“我”的讲述中,曾有两处奇妙的动情瞬间闪过,一处是对自己初恋的回忆,留恋而感伤;一处是和警官秦彤的对视,亲密甚至温柔。更明显的是叙述者在文本中曾发出这样的声音,带着同情抑或义愤:
“他们看着续章将《协议书》垫在膝头,甩动钢笔,龙飞凤舞地签名,无不面露狞笑。签过百份之后,续章因为想到什么(我估计是罪孽),舌挢色变,签字的手麻痹起来。”[30]
“有人开始到红乌站、红乌西站以及汽车站坐着等。几乎是下来一批乘客,就逐个地瞅去。又是怕唐老板是易装出现,还抓住某人的双肩细加辨认。写到这里时,我庄严而忧伤,想起那些不知儿子已被大海吞没仍竖耳听风、苦苦等待的母亲。”[31]
最富深意的是小说结尾,此处氛围一反前文冷涩,写到母亲为“辟邪”摆在窗口的花。这平添的亮色不禁让人再次想起鲁迅在《药》的结尾处补写的花环。在这段与全文语调截然不同的断裂背后,是文本中两种花朵的潜在对比。窗台种花的行为并未在红乌成为绵延百年的“美好习俗”,它很快被城管出面阻止,只留存在“我”的想象之中。而真正从未消散的是城南“像一卷又一卷铁蒺藜”[32]的金雀花,它向我们暗示着:骗子在南方死去,却可能从未离开。
结 语
如何以文学这一历史悠久的艺术形式书写现代生
活,尤其是被数字技术等科技高度架构的当下社会,对任何今天的写作者来说都是难题。《骗子来到南方》呈现了阿乙独特的思考。作家没有选择对个体心灵进行刻画,而是借由“我”的观察呈现出一个被“系统”笼罩、控制的世界。其中,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与无从挣脱的资本控制形成一体两面的关系,都是功利、冷漠、意义缺失等现代社会顽疾的帮凶。在以抽离式的“第三者书写”让这一切残酷纤毫毕现的同时,阿乙又在细节下埋藏了他的温情和关怀,为当下小说的情感表达提供了新的可能。或许,就小说中的骗局和谋杀而言,谁是凶手无关宏旨,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这些像金雀花那样无限生长的罪愆,如何可能在某刻终结?
参考文献:
[1]郭洪雷.重返故乡的写作——关于阿乙《骗子来到南方》的对话[J].西湖,2021(10).
[2][3][4][5][6][7][8][9][10][11][12][14][15][17][18][21][22][24][25][28][29][30][31][32] 阿乙.騙子来到南方[M].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81,104,106,141,117,107,130,155,154,160,167,159,191,135,177,83,86,126,191,83,88,105,146,118.
[13] [法]安东尼·阿密赛尔.什么是非法主义[M]//[法]米歇尔·福柯.监狱的“替代方案”.柏颖婷,吴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86.
[16] [英]托尼·费里.监控下的住宅[M]//[法]米歇尔·福柯.监狱的“替代方案”.柏颖婷,吴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64.
[19][法]米歇尔·福柯.监狱的“替代方案”[M].柏颖婷,吴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35.
[20] 胡少卿.阿乙《骗子来到南方》:继承故事传统,回应迷宫般的社会热点[Z].《文学报》公众号,2021-6-6.
[23][26][27][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M].刘汉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91,196,193.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