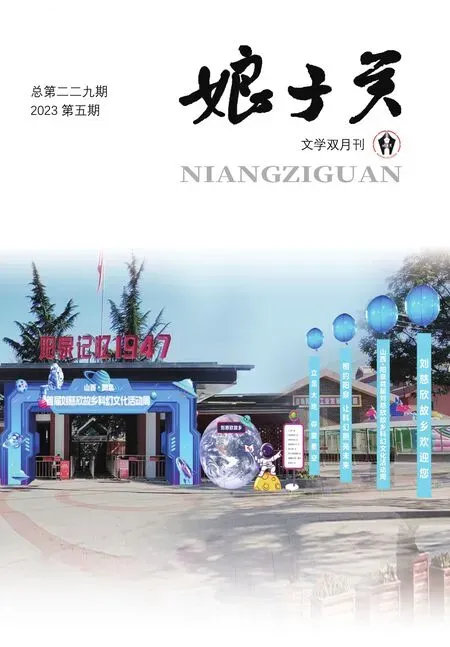幻享未来 共筑盛会
◇吴琦 王玥珂
编者按
8 月16 日,在山西·阳泉首届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活动周期间,《刘慈欣创作年谱1999-2022》首发式暨“从现实主义传统到科幻文学高地”主题对话会,在“阳泉记忆·1947”文化园城市会客厅举办,这是阳泉市的一场科幻文化盛会。刘慈欣、蒋树强、窦文章、肖克凡、石一枫、姚海军、超侠等嘉宾结合自身经历,围绕“从现实主义传统到科幻文学高地”主题展开交流对话。本刊转发《阳泉日报》8 月24 日刊发的对话会嘉宾发言,以飨读者。
刘慈欣:科幻文学的最终目的是超越现实、拓展现实
刘慈欣是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主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阳泉市文联名誉主席,刘慈欣文学院终身名誉院长。代表作有《超新星纪元》《三体》《球状闪电》《中国太阳》等。《三体》三部曲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荣获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是亚洲作家首次获此奖项。目前,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流浪地球》《三体》等作品的影视化改编收获广泛好评。
科幻和现实主义关系很微妙,科幻文学本身不是现实主义文学,它的最终目的是超越现实、拓展现实。科幻作为文学的一个体裁,和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所没有的视角、角度来观察现实、隐喻现实、批判现实。作为科幻文学作者,我把现实作为想象力起飞的平台。
创新能力不论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这个能力的培养其实不像我们想得那么简单。我之所以很热爱科幻文学,是因为我感觉科幻文学是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文学体裁。它每一个文学作品都在努力做到从0 到1,虽然只是在文字上、在想象上,但也许能够对开拓想象力、提升创新能力起一点微小的作用。
科幻作为一种文学,不可能离开现实,但是有现实内容的文学不等于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现实主义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有它要表现的内容。比如欧洲的小说,巴尔扎克的作品就是现实主义的,描写的是现实;而《基督山伯爵》同样描写的也是现实的内容,但不是现实主义,因为它要表现的是超越现实的。我在科幻作品中写现实,目的是能够通过现实的平台把读者带入到一个想象世界里。我认为科幻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构造出现实中没有的世界。
建议青少年要尽可能地多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尽可能地多了解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未来,还有大自然、宇宙的知识。当你知道了很多、了解了很多,你可能在未来就拥有更多的前进方向,也拥有更多的选择。
蒋树强:科幻文学有“科”也有“幻”
蒋树强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图像、视频等多媒体内容分析信息的分析与多模态智能技术。曾获得中国计算机学会科学技术奖、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国际合作奖、吴文俊人工智能自然科学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从古至今,人们将想象力通过科技的逻辑和合理性来推动创新。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一定程度是想象力在推动发展。科幻文学有“科”也有“幻”,我认为科幻作家需要站在现实主义的起点上,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推动科幻文学的发展以及科技的发展。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就目前的进展来看,人工智能距离自我意识尚有时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未来值得期待。ChatGPT 是通过大规模的预训练和深度学习技术,使得它可以理解、生成人类语言,在对话、文案产出方面有不错效果,但是它不具备独立的情感和思想,推理和创新能力与人类比相差甚远。文学创作还是要依靠作者个性化的思想和不断创新的想象力,才能让读者产生共鸣。
肖克凡:科幻作品所展示的是我们尚未置身其间的现实世界
肖克凡是天津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鼠年》《原址》等八部,小说集《你为谁守身如玉》《蟋蟀本纪》等十六部,散文随笔集《一个人的野史》《有时候想念自己》等四部。作品曾获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小说选刊》年度奖等多种奖项。
我引用自己创作的“铁句”:现代主义是我们尚未置身其间的现实主义,进而提出我们今天的科幻作品所展示的是我们尚未置身其间的现实世界。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还是当今的科幻文学作品,文学的本质都未改变。作家的成长与现实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以及对生命、对世界、对未来的看法,都出自现实土壤。故而一位作家的作品无论是写未来几百年几千年的那个遥远世界,都脱不掉与自身成长的现实主义的关联,这两者是很难剥离的。
科幻文学对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作的作家意义很大,增强了他们突破自身边界、疆域的渴望。刘慈欣给予了现实传统写作者勇气和激励,就像是一面镜子,鼓励现实主义作家应当更大胆地突破多年写作所形成的固有疆域。
石一枫:科幻提供一种对于现实的审视
石一枫是中国作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入魂枪》《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作品入选中国好书年度好书、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榜单等。
我一直很爱看科幻小说,小时候是《科幻世界》《科学神话》的忠实读者,因为机缘巧合,我没有走进科幻小说的写作领域,而是向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迈进。对于科幻文学,我觉得可以把它放在一个相对宏观、整体的文学角度。现实主义文学和科幻文学我都看,我认为它们各有各的好,文学的好贵在创新、贵在“你看见了前人未见之事,说出了前人未说之问”,这个是文学核心的“好”。
“好”与“不好”,关键在于眼界,能不能提出一个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什么是现实主义?我们把它拆开来看,“现实”和“主义”,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主义”。“主义”是人对现实的看法,如果你的这种看法是新的、是能够对人有触动的,那么它就是好的,不管它是科幻还是传统文学。科幻作品伟大与否的标准,就是能不能真正提供对现实的新看法。
超侠:科幻现实主义可以给予读者不一样的体验
超侠是北京元宇科幻未来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作家,编剧,主要作品有《少年冒险侠系列》《超侠小特工系列》等近百部,参与创作《快乐星球》《蓝猫淘气》等,编剧作品有《三体》立体书、《决战暗魂》《高手》《皇城相府》《常夜灯》等。荣获2020 年小说排行榜前十名、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16 次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多个门类奖项、4 次少儿科幻星云奖等。参与创作的科普书、漫画书曾获第十六届国际动漫金猴奖、“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高中时期,我就是《科幻世界》的书迷,看了很多《科幻世界》杂志的内容,后来上了大学,试着把科幻和童话、少儿文学结合。看了刘慈欣老师的《乡村教师》,觉得没有哪部讲老师的作品能像这部作品一样,让我们看到老师的伟大。还有《球状闪电》,我认为这部作品能给科学家一些启示,它的想象、思考在以前的一些科幻作品里难以见到。到了《三体》,刘慈欣老师把科幻的想象通过文字扎实地表现出来,让人感觉“科幻不是科幻,它是一部纪实的作品”,非常震撼。
到了研究生时期,我写的论文也是关于《三体》的。再之后,开始编写《三体》立体书,把《三体》三部曲的内容展现出来,让小孩子能触摸、能看、能玩。尤其是《三体》电视剧创作出来之后,很多小孩子特别爱看《三体》,喜欢研究宇宙。
刘慈欣老师把《三体》写得很真实,他把这种真实架构在一个三体游戏里,让人更容易理解其内部的“核”。这些年讲科幻现实主义,其实就是在现实中,一个问题可能没有那么尖锐,矛盾没有那么突出,但是科幻现实主义可以给予读者不一样的体验,把现实中的问题用凸透镜放大,这可能就是科幻作家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同的地方,科幻作家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反映现实中存在的某样东西。
窦文章:努力把科幻作者创作出来的东西变为现实
窦文章是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金融信息与工程管理系教授、西北大学资环学院客座教授。文化和旅游部“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参与或主持多项国家基金项目、科研项目、咨询项目,先后承担国家“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发展规划重大专项研究工作。参与并主持多个企业管理咨询项目,编制上百个区域(景区)旅游规划、特色小镇规划等全域旅游规划,县(市)级旅游总体规划以及近百个景区详细规划等。
我第一次听说刘慈欣老师,是我女儿问我有没有看过《流浪地球》,她告诉我这部作品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非常轰动的影响,我觉得很惊讶。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优秀的科幻作品,还有这么厉害的科幻小说家。我记忆当中,我是读《西游记》这类作品长大的,后来看了《十万个为什么》,到了大学时期,看过《第三次浪潮》。更多的业余时间是看网络小说。通过我女儿的推荐,我打开了《流浪地球》,一晚上没睡觉,把这本科幻小说读完了,我觉得刘慈欣老师真的是科幻大师。
中国科幻研究中心发布的《2023 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2022 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877.5 亿元,比上一年增长47.9 亿元。在科幻文旅板块,2022 年,产业总营收150.3亿元。其中,主题公园科幻游乐项目占据主要份额,以国产科幻IP 为核心打造的科幻主题公园有望成为新的增长极。
我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有几个着力点,第一个着力点就是把科幻故事情节与现有的主题乐园、主题公园结合;第二个就是在国际上把科幻的故事打造成一个系列;第三个是旅游,现在是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时代,我们要把各个要素与科幻结合;最后一个就是把科幻产业做大。我觉得我们要把科幻作者创作出来的东西变为现实。
姚海军:科幻和科技的关系非常紧密
姚海军是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科幻世界》主编,现兼任《科幻世界译文版》主编、《四川科技报》总编,成都科幻协会理事长,四川省科幻学会副会长,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联合创始人。2010 年被评为“建国60 年百名有突出贡献的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并荣获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科幻编辑奖”;2019 年荣获中国科幻银河奖“特别贡献”奖;2023 年荣获钓鱼城百万科幻大奖“科幻出版家”奖。
文学整体上来讲是现实主义,但是现实正在发生变化,有些人可能很敏感地关注到这些细微变化,这可能是科幻的一个机会。这种细微的变化,就是生活发生的变化,无处不在的科技,对我们生活的渗透,对我们的思想观念、对我们的行为都会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影响在科幻作品当中就有体现,它是一种科技跟现实发生深刻互动之后的一种文学样式。世界科幻文学的诞生,其实也是科技触动了一些作家的敏感神经。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1818 年玛丽·雪莱创作的《弗兰肯斯坦》使这种关系不断得到深化。现在有一个共识,当年玛丽·雪莱创作这部小说时,非常敏锐地感受到即将到来的工业时代的气息和脉搏。
我做过比较,美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中融入了一些科技元素,我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对科技的关注相对较少,这就给了科幻文学一个巨大的空间。科幻文学之所以能获得这么大的热度,我认为与它与我们跟科技的复杂关系的融入、表达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科技无处不在的环境中,需要一些人有一些思考。
作家很难脱离现实创作出一种新的文学,但是科幻作品产生的新的派别与现实主义文学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创作的样式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探讨。科幻文学分为两类,一种是延续科技的变革,另一种则是科技的创新。能遵从现实主义去创作出一种新的样式,在我看来,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正如过去我国在科幻文学领域的影响非常有限,但是刘慈欣老师的《三体》出版之后,改变巨大,我们能看到不同国家对于这部作品的关注,以及作品的畅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