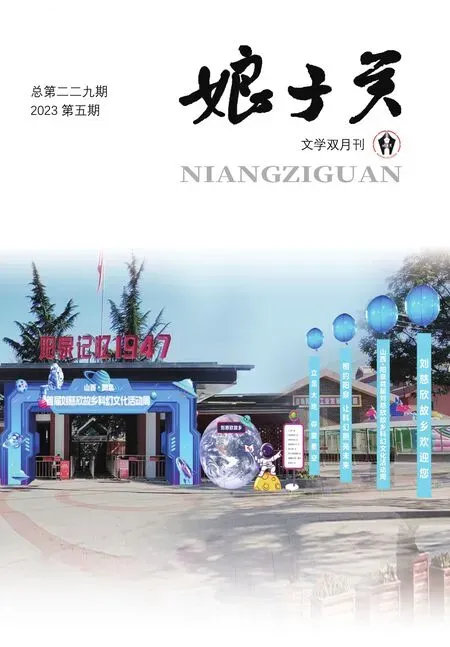走姥姥家
◇魏军
一
山村的旧礼,大年初二要走姥姥家。
姥姥家住在姜家沟,我家住在魏家沟,中间隔了三座山。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如一条长长的绳子,一头系着我,一头系着姥姥。
相传我的祖上是梁丘人士,因犯了事,携一家老小逃命。数月奔波,花费殆尽,行至此处,已是隆冬季节,大雪飘飞,漫山遍野,白茫茫的不见尽头。在不远处,有一陡立的石壁,石壁下方是一处平坦的山坡。一行人前去躲避风雪。那坡台大约有十丈见方,积雪却并不深厚,尤其是中间锅盖大小的一处,竟一片雪花也没有。大家甚是惊讶,断定这是一块聚福之地。他们便决定在此安营扎寨,用树枝搭建窝棚,避风挡雨。
从我记事起,三间茅屋便是我家的全部家当。据说这房子还是爷爷的爷爷建造的,只是后来增添了两间羊屋。奶奶一生中生育了几个子女。却一个接一个夭折了,到了父亲这里终于活了下来。然而奶奶也只是将父亲养到半岁便撒手人寰。村里的二神仙说她死于月子病,又或许是中风。二神仙是村里唯一去县里读过书的人,会给人看病扎针,又会给牲口治病。他的话自然是可信的。
父亲从小很乖,不哭不闹。奶奶去世后,家人就用羊乳去喂他,他也不挑不拣,一天天长大,身体还算壮实。两岁以后,大家慢慢发现父亲和别的小孩儿不一样,眼睛呆滞无光,对外界事物反应迟钝。到读小学时,便印证了大家的猜测。父亲应该属于先天性大脑迟钝,说精不精,说傻不傻。父亲读了三个一年级,两个二年级,直到十五六岁才勉强读完小学。父亲虽然读书不行,跟爷爷学农活儿倒是上手快,一身力气,干得一手的好农活儿。刨耕耘耙,播种打场,一丝不苟。不仅如此,父亲还跟村里的老人学会了条编。山沟沟里虽然穷乏,但漫山遍野总有数不尽的藤藤蔓蔓,这些藤条儿割下山来,编成篮子、筐子等物品,放到集市上也可以卖一些钱,换取油盐酱醋。
三十岁之前,父亲没有走出过永兴镇。那些日升月落的时光里,父亲除了去田间做爷爷的帮手,其他时间都在割藤条编筐子。父亲胆小木讷,他很少和别人说话,也不善于说话。因为父亲是爷爷的第五个孩子,小孩子们都会偷偷地叫他五哑巴。父亲开始很是气恼,后来也就默认了这个名字,就没有人再记得他真正的名字。
穷困的家,两个光棍男人,日子的拮据程度可想而知。然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在野蛮落后的山村更是如此。从父亲十八岁起,爷爷就开始央求三乡五村的媒婆。讨媳妇是爷爷心间的头等大事。父亲并不着急,他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干活,编筐子。很显然,以父亲的条件,是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他的。
那年槐花飘香的时候,李石河沟的王婆子领来一个女人,相貌还说得过去,可是智商如不足五岁的孩子。憨实的父亲自然说不上喜欢还是不喜欢。因为自家儿子有毛病,很难讨到正常的媳妇。山里的行情,越是残废的女人彩礼越高。爷爷寻思了许久。爷爷终于还是狠心同意了。卖了五只羊,爷爷着实心疼了一阵子,却也了却了他的一桩心头大事。担心夜长梦多,定亲,收拾房子,迎娶仅仅用了半个月。当然,又花了不少钱。
槐花落尽的时候,山上的田里就忙起来了。爷爷要去集上卖父亲编织的筐子,因为心情高兴,也为了让父亲多一些见识,决定让父亲和女人一同去。集市上人流如潮,待售的山货让人流连忘返。筐子卖得差不多了,集市上人也明显少了,爷爷给了父亲一些零钱,让他带着媳妇去逛逛,买些好吃的。为安全起见,爷爷还用一根绳子把两人的胳膊绑在一起。
一个时辰过去,父亲回来了,心神失落。爷爷本就着急,一看这情形,赶忙质问。父亲说他们见有人在表演耍猴的,就看了起来,等人散了,才发现那女人也不见了。爷爷急火攻心,连忙奔去寻找,来来回回几趟也没见个人。一旁的人说,一定是让人给拐走了。就这样,父亲又成了光棍儿。这件事也让爷爷伤心了好几年。
二
在姜家沟,男人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手头上有十几亩田,最让人羡慕的是他有六个闺女,田里的活儿总是干得风风火火。家中有五间正房,三间配房,还有一个高大的门楼,两扇厚厚的木门足以显现出主人的实力。
那年麦子是一个大丰收,十几亩的麦粒堆在院子里,被炙热的太阳晒干后就能入囤存放。中午时分,一家人正在吃饭,不知什么时候,一团乌云从山后涌了上来,几分钟时间就化作倾盆大雨。男人和女人扔下碗,拼命堆积麦粒,又用塑料布遮盖。即便用尽全力,还是被大雨冲走了一部分麦粒。更糟糕的是,一场大雨把女人淋病了,她高烧三天三夜,黄家梁子的先生都没有好办法,熬了三天才平静下来。期间,先生也主张去县城诊所瞧瞧。可是到县城人抬马扛的要好几天,各种费用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男人思索了一番,还是作罢了。
北风吹了三次,满山的树叶就陨落殆尽了。天气寒冷,一座山一座山都被冰雪包裹着,村子里的人们也如蛰伏的动物一般深居简出。汪家沟的王婆子一大早就在女人的床前忙碌了起来。王婆子是接生婆,一个脸盆儿、一把剪刀、一瓶高度烧酒便是她工作的全部家当。不仅姜家沟,附近几个梁都来喊王家婆子接生。
女婴哭第一声的时候,王婆子就大声告诉了早已在外面等候多时的男人。男人没有进屋,他转身去了后院,喂他那两头骡马,他这是失望了。女婴前面已经有六个姐姐了,男人金盼银盼,盼她是个男娃儿,却事与愿违。不仅如此,女婴从哭出第一声后,便不再动了。她奄奄一息,四肢柔弱,王婆子担忧地说,怕是活不成了。
一直到傍晚,这婴儿都没有好过来的迹象。她不哭不闹,不吃东西,眼睛紧闭,只有胸膛微微地颤动,表明还有一口气在。男人始终没有细看孩子一眼。他抽完一袋烟,毫无表情地说,扔了吧。是啊,他家里那么多女娃了,也不差这一个,况且这女娃奄奄一息,或许熬不过天亮呢。女人就呜呜地哭,或者她不敢阻拦男人,又或者与其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掉,还不如快刀斩乱麻。男人用一个小被子把女婴卷了,塞进了箕子。女人小声哀求,裹严实点啊。男人把女婴扛到下山沟里,随手倒在边边上,回来时女人还在哭。他不耐烦地说,你的肚子没本事,怪谁?
女人不再哭,可她心里如刀绞一般呀。等男人去了后院,女人顾不得身体的疼痛,她穿好衣服,顶个头巾,把腰间的带子扎得紧紧的。即便这样,她依然气力不足。女人又寻到一根木棍,蹒跚着向山下移去。或许是母女心有感应,她远远就看到一个包裹,静静地躺在一片白茫茫的雪上。女人回来时,泪水洒了一路。她迅速脱去衣物,钻进被窝,紧紧搂着女婴,如抱一块冰。女人一夜没有合眼。
太阳爬上第二道岗时,她被一阵蠕动惊醒了,怀中的孩子全身热乎乎的,半睁着眼睛,小嘴儿在寻找着什么,女人的泪水又下来了。她把奶头塞进小嘴里,双手抱得更紧了。可是这怀中的婴儿又哪知人心的险恶呢?因为女人怀孕时发了三天高烧,孩子出生又被扔在雪地里受冻,女婴的身体状况非常差,经常生病。女人想尽办法一次次把她从死神手里拉回来。黄家梁子的先生总叹息女人的犟劲儿,他说,换作别人,十个孩子也没了。
第三年,她的弟弟就出生了。一家人都把心放在这个男娃的身上,她便更孤单了。直到三岁,她才开口说话。五岁还不能独立行走。她的身体一直虚弱,不用说去上学,更不用说去田里干活儿,只能待在院子里赶麻雀,防止它们偷吃晾晒的粮食,简直就是一个废人。嗯,是的,等吃等喝,还花很多钱买药,这愈发让大家讨厌。好在有母亲的袒护,他们也只能暗自生气发狠。
这中间,她的姐姐们陆续出嫁了。男人对求亲的人家要求挺高,家里没有高头大马不嫁,谁让他的女儿个个那么漂亮呢?可是,她一直是一家人的心病。父亲为她什么时候嫁出去发愁,母亲也为她什么时候嫁出去发愁。父亲觉得嫁出去就省心了,母亲担忧她嫁出去怎么生活。天地之间,人的命运竟是这般渺小。她深深地埋在大山深处,自然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但她明白自己很多时候都是多余的。她不想这样,她努力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帮母亲做饭,喂猪羊,洗衣服。这些也是母亲要求她学会的本领。如果有一天她不在这个世界了,她的孩子能养活自己才行啊。
她二十岁时,父亲给她寻了一个婆家,尽管母亲还想多养她几年。她的父亲不同意,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其实两年前她的父亲就想把她嫁出去,她的弟弟也快要娶媳妇了,家里有这样一个姐姐,名声不太好。
三
她寻得的丈夫便是我的父亲,自然,她是我的母亲。
此时母亲的身体好了许多,却依然不能长时间走路,也不能去坡上干活,但她是一个坚强的人。父亲虽然憨厚憨实,却是她的依靠,他当然是她的天。母亲接连生下我们兄妹三人,这在外人看来,她得攒了多少勇气呀。
母亲依然经常吃药。等我长大一些,便常常帮母亲在院子里用砖块架一个陶罐儿熬药。黑乎乎的药水又苦又涩,母亲却能一口气喝下去。或许她觉得,这药水比生活还是甜多了。山里人讨生活本就不容易,母亲还要常年吃药,家中境况愈发困难。三个孩子一天天地长身体,吃的多着呢。
我记不得曾经什么时候穿过新衣服,弟弟妹妹更不用说,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是我穿小过的。尽管如此,母亲还是会用各种布片儿把所有破洞的地方补上。其实在那些年月里,不露肉便让人很知足了。生活的苦,母亲从不向别人诉说。和父亲在一起,和她的孩子们在一起,她已经感受到了幸福。这世间的人各有各的命,有的人鸡鸭鱼肉,会嫌盐多盐少,有人烧米汤时会为多放一把米而心疼。生活是什么,在每个人眼里绝不一样。欲望不同,心境不一。
母亲枯乏惨淡的生活,姥爷是不会放在心上的。他觉得,嫁出去的闺女就是人家的人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肯定要由男人负责。他甚至不希望母亲回娘家。说到底,他是嫌弃母亲没有本事,给他丢人,所以除了大年初二,母亲是很少回娘家的。
或许天底下女人的心都是相通的,更何况母女一场。姥姥一辈子都在挂记着母亲,或许正是因为她多病的身体,愈是没有本事越让姥姥放心不下。姥姥就趁着赶集的当口去我家稍带点吃的。比如用头巾包一些高粱或玉米,或者刚做的窝窝头。有一次大约是三月三庙会,姥姥来住我家。她从赶庙会的篮子里拿出一包蜜三刀,这是过年的时候才能收到的礼物,姥姥竟然藏到了现在。这蜜三刀是我们小时候见过的绝上的美食。母亲规定每天只能吃一块儿,而且是我们兄妹三人分着吃。小孩儿总是贪吃的,在温饱问题都困难的岁月里,吃零食总归是奢侈的。我们兄妹总盼着姥姥来,可是一年到头姥姥又能来几趟呢?最让人期盼的是大年初二去姥姥家,因为只有那一天,我们兄妹才能吃到一年中最丰盛的美味佳肴。那饭桌上的味道紧紧地拽着我们的神经,在梦里经常出现,即便过去了许多年,依然挥之不去。
大年初二去姥姥家,是我们这里流传已久的风俗。春节走亲戚,要按亲疏远近的顺序。大年初二是头一天,自然要去媳妇的娘家,也就是孩子的姥姥家。以后的日子里还要去姨家、姑家……家中亲戚多的,往往到正月十五前才能走完。媳妇回娘家是有讲究的,外人看女人一家人的穿戴行头,便知夫家的门庭高低,也能知道女人在夫家的地位。所以女人携夫带子回娘家,总会尽量装点门面,摆摆阔气,一来显摆自己,二来为娘家长脸。
我有六个姨,她们自然知道这个道理。每个大年初二,不用通知,便自会不约而同去姥姥家。当然,我们也去。山路弯弯,长路漫漫。为了在中午前到达姥姥家,大家往往吃过早饭就要出发。她们动身前总会把一匹马精心打扮。她们去姥姥家总会骑上白色或红色的大马,用棕刷子把毛梳理得油光发亮,又用精饲料把马儿喂得膘肥体壮。马脖子上定要围上一圈儿铜质的铃铛,马头的鬃毛上也要绑上几条红色的布条儿。人端坐在马背上,双手抓紧缰绳,马头高昂,一路上叮叮当当,红带飘飘,自然是一副耀武扬威的阵势,着实让人羡慕一阵。走亲戚,礼物是硬头货,她们总是阔绰得很。一个木排横在马的后背上,两边挂上两个或多个用柳条编成的斗子,装上满满的礼物,一路上颠来颠去。实力不济的也会骑一头黑色的毛驴,好歹也能替人行脚。
我们家自然是没有这阔气,没有高头大马,毛驴也没有,只有两只羊和几只鸡。我曾经天真地对母亲说,鸡要是能变成马那么大就好了,我们就可以骑着它飞过去。母亲就苦笑一下,我们都吃不饱饭,鸡要是长那么大,拿什么喂它?幻想终究是不顶用。我们去姥姥家,只能靠两条腿步履蹒跚走在山路上,翻过一座又一座山。有时拄一根拐棍儿也算是三条腿了,也能比两条腿快一些。灰秃秃的山坡上,父亲挎着装着礼物的小篮子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母亲身体虚弱,总是落在最后面。父亲只好一次次放下篮子走回去,背她走一段儿,一路上还要歇几次脚。
四
行路迟缓。早晨蒙蒙亮出发,挨到中午才勉强赶到姥姥家。此时他们早已到达多时,或围坐在一堆火旁吹嘘,或围着高头大马夸赞。我们的到来并不会给他们带来惊喜。姨和小舅他们只是象征性地打个招呼,有人甚至都没有多看一眼。姥爷在火堆旁抽旱烟,他冷冷地说,路都走不了,还来凑什么热闹?这句话自然是说给母亲听的,当然也包括我们。这明显是嫌弃。倒是姥姥,她踮着三寸金莲的小脚从厨房里跑出来,把双手的水在胸前的布巾上擦了几下,一手拉着母亲,一手拉着我,引进偏房里。姥姥又用一个残破的泥盆儿从灶膛里扒拉出一些灰烬,给我和弟弟妹妹烤冻得通红的手。外面的大火堆是他们的,我们没有围坐的资格。
他们依然在高谈阔论,话题无非是去年的收成收入,扯了几匹布,做了多少新衣服。从偏房的门缝看过去,他们还真是衣着光鲜。瞅了一下自己,我身上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与他们真是格格不入。自然,他们的头发也收拾得精致有型,不像我乱蓬蓬的盖在头皮上。可能是烤火热了的缘故,他们扒开胸前的衣服,露出长长的脖子。或是将袖子袖口撸了起来,露出手腕儿,让人一眼就能看到脖子上和手腕上的不知是金是银还是铜的首饰。他们恨不得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穿戴在身,显示出与众不同。
说到底,我们家与他们就不在一个层次,人穷志短呀。不过我们也识趣,离他们远一点儿,尽量不打扰他们的兴致。其实原本走亲戚就是各走各的亲,各拿各的礼,有多拿多,有少拿少。礼多礼少,都是一番情意呀。但是他们骑着高头大马,还带着高档礼物,得意洋洋地拥进姥爷的村子,这给姥爷赚足了面子,很是讨姥爷的欢心。我们一家的出现则明显略带寒酸,应该是扫了姥爷的兴吧,让他们没有颜面。与他们的高头大马相比,我们的出现就是一股晦气,让人生厌。理所当然的,不管饭前饭后,我们都是他们谈笑的内容。
看,七妮儿一家人连个囫囵衣裳都没有。
小孩儿一个比一个懒。
拿那仨核桃俩枣,还好意思回娘家。
就是一家人来混吃饭,不知又要赔给他们多少。
小小年纪我就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把锋利的刀,杀人于无形。父亲多多少少也能明白大家话中的意思。他很少说话,一个人躲在偏房的角落里。母亲一次次满脸愧疚地望着父亲,父亲拉了母亲的手,指着旁边的小凳子,让她不要总站着,又把妹妹揽入怀里,给她扎小辫子。
酒饱饭足,说的是他们。我们一家人和一些孩子坐在一张桌子上,饭菜本来就少,姥爷说小孩子吃不多。孩子们一阵抢夺,轮到我们伸手时,差不多就没有了,姥姥从厨房里赶过来,守在旁边,时不时小声呵斥他们,趁机加一些饭菜放到我们兄妹面前。父亲母亲把馍掰成一小块儿,蘸盘子底上的汤,自己吃也给我们吃。饭后,他们继续拉呱儿。孩子们则跑出院子放鞭炮、找鸟窝。小孩子想不了太多,我和弟弟妹妹也会随他们去玩儿。有时他们会从兜里掏出零食塞进嘴里,馋得我和弟弟妹妹不知咽了多少口水。弟弟就捡起他们扔在地上的糖纸,伸直了舌头去舔上面残留的甜味,还要给妹妹舔一下。我不会去舔,我知道那样很丢人。那些小孩儿会经常编一些顺口溜来嘲笑我们。
烂衣裳,打补丁,撅起屁股露着腚。
这时候我就会不自觉地摸摸后面,担心衣服真的破了,腚露在外面。
姥姥把桌子上的残羹冷炙收拾起来,热菜倒在一起,凉菜倒在一起,端到厨房,又把喝完酒的包装盒捡回来,将剩菜装进去,悄悄地塞进我家装礼物的篮子里。这一幕有时逃不过妗子的眼睛,她总撇着嘴,盯着母亲说,真没有出息,又吃又拿。母亲确实没有出息,她紧闭着嘴唇。姥姥也装作没听见,她一直在忙不停。
这些混合在一起的剩菜,有咸有甜,有辣有酸,各种味道碰撞着,经过一系列物理化学的反应,又生发出多少不知名的味道。这混合的美味儿,自然能让我们兄妹开心地品尝好几天。母亲挖出一坨剩菜,再配上一些萝卜或白菜,舀上一瓢水,点火烧透。这一盆儿回锅菜,散发着独特的味,香味儿充溢在厨房里,充斥着每个人的鼻孔。即便过去了几十年,这混合的香味儿依然不经意飘进我的梦里,让我欲罢不能。
冬季日短,太阳红红的,偏过山头,大家都要各自回家了。贵客先行。于是他们带着醉酒后的各种满足和快感,跨上高头大马,排成一队,浩浩荡荡地上路了。姥爷和妗子把他们送到路口的大石头旁才作罢。
生活就像山上的树叶,生了再落,落了再生,一年年重复着。本是苦命的人,哪有多少幸福来临?如草间的虫子,风来了,雨来了,横竖忍着就行。
山里人干活儿是不分季节的,天天有忙不完的事,刨地、平地、打垄、播种、施肥,浇水、除草、打药、捉虫、收割。一年到头,每天能看见走路就要起床上坡,看不见路了才回到家里。即便冬闲季节,父亲也会早早起床,去山路上捡拾动物的粪便作为农家肥。父亲老实本分,庄稼种得精细。母亲常为自己不能亲自帮父亲一把而内疚,她在家里也闲不住,洗衣做饭,喂羊,喂鸡,每件事都做得很仔细。
有一年秋天,我家的苞米成熟了,父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个去梁上掰苞米。我们负责掰,父亲负责装进袋子里,再扛到梁下的山路上,用平板车拉回家。山高坡陡,父亲每扛一次回来都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甚至顾不上喝口凉水。中午时分,本该吃饭的时间,母亲却不在家。父亲四下打听,也没有信息。我们都急坏了,便邀人一起四处寻找,却也找不到。一直到后半晌,才听到村头一个婆婆说,看见母亲端着饭篮子上山了,我们又急急顺着山路找。在一个拐角处,有人发现了坡下的灌木上飘着一个头巾,那正是母亲经常带在头上的。一行人急忙顺着山坡往山下的灌木丛里找。在沟底,母亲趴在那里,竹篮子还在她的胳膊上,身体和沟底的小溪的水一样凉。我能猜到,母亲一定是担心我们又累又饿,才冒险去梁上送饭。她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经不起一块石头的磕碰,更没有想到会跌落谷底,她的孩子再也没有娘。
那一年,我十二岁,弟弟十岁,妹妹八岁。母亲去世后,父亲像个孩子一样哭了一场又一场,从不喝酒的他也学会了喝酒。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去过姥姥家。可是我想我的姥姥呀,况且姥姥也想我呢。
五
我想一个人去给姥姥拜年。
我去给姥姥拜年,一般是大年初二的午饭后出发。我骑上我的两条腿,有时半路上捡一段树枝当拐杖,算是三条腿了,但依然赶不上四条腿的马跑得快。这些我不在意,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我胳膊上的篮子里是我夏天在后山捡的蘑菇,还有一些木耳,却只有一点。我只好弄一团草垫在下面,把蘑菇和木耳在上面铺一层,又用一块蓝色棉布盖了,鼓鼓的,还可以。
翻过几座山,远远地就看见山坡上姥姥家的院子。有时还能看到他们在院子里烤火,飘到院子上方的一缕缕青色的烟。我不急于走进姥姥家,他们的大马还拴在院子门口,隐隐还能听见脖子间铃铛的响声。我放下篮子,在附近捡拾枯树枝,时不时观察那些大马和毛驴。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蓝黑色的天幕下,一些星星逐渐钻了出来。
我捆好树枝放在背上,又掂起篮子,摸索着向姥姥家走去。我在门板上轻轻拍了两下,很快就听见一阵细碎的脚步声移了过来。门开了,姥姥里外看了下,一把把我拉进去,径直进了厨房,又把房门关了。
姥姥一辈子都是一个内心柔软的人,除了对富足的后代赞赏之外,对我这个穷外孙,也是惦记倍至。姥姥很疼我,从小到大都是。有时候太黑了,姥姥等了很久不见我的身影,她就佝偻着身子去门外观望,有时又端着油灯迎我很远的距离。
灶膛里,中午烧饭的灰烬还没有完全熄灭。姥姥添了柴,大火又熊熊烧了起来。姥姥让我坐在灶门口,解了上衣的扣子烤火。她洗了手,把锅里的碗端到案板上给我吃。这个时候我早就饥肠辘辘了,心里想,随便吃点他们中午剩下的饭,喝点他们剩下的汤,也是天下最好的美味。然而,这些热气腾腾的菜并不是中午他们吃剩下的,是姥姥特意为我留下的。
昏暗的油灯下,我默默趴在桌子上吃起来。姥姥见我吃得太急,她轻轻拍拍我的背说,慢慢吃,锅里还多着呢。那些年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姥姥给我留的饭菜那么苦,那么咸。现在才知道,一些液体从脸上流进碗里,也就分不清是谁的味道了。
吃饱了饭,我就把藏在山坡上的柴抱进来,放在姥姥的厨房里。姥姥就会惊奇地问,你是不是偷别人家的柴火啦?我说,哪能呢,我会变啊,我变出来的。姥姥终究还是知道我捡了半天树枝,她把我拉到怀里,拍拍我的头。其实那个时候,我比姥姥还高一点。昏暗的油灯映照下,姥姥的表情难受,嘴角抽搐。我担心是惹姥姥生气了,不敢看着她。
我又拿了扁担去给姥姥挑水。山里人吃水是很困难的,那时候吃水都吃泉水。水在很远的地方,需要爬过一道梁子,那里有一口泉眼。靠近泉眼的一段路比较窄,因为常有人去打水,又湿又滑,晚上更是难走。我往往一手扶着石壁,一手扶着扁担。我还是太年轻了,不如大人懂得控制节奏。等两桶水担到姥姥家,路上会洒了一半。姥姥并不赞成我去打水,但是她拦不住,只好站在大门外,听见我回来了,就远远地迎过去,让我停下来,给我擦汗。姥姥家有三口大水缸,等我把水缸都灌满了,基本上已是半夜时分。
这时候我会说,姥姥,我该回去了。
姥姥把我的篮子小心翼翼放在姥爷面前,掀开盖布让姥爷看一眼。姥爷一直都没有正眼看我,他知道我的篮子里也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姥姥说把我的蘑菇木耳留下,给我换成几个窝头。姥爷就回过头来呵斥她,咱救急不救穷,你这是干什么?你能帮他一辈子吗?姥姥低下头,默默地又把窝头拿出来,把我的蘑菇、木耳放回去,对姥爷说,那我送送外甥吧,说完就拉着我的手急急往外走。
深色的夜幕吞噬了一切。这个时刻,世间才是最平等的,没有高低上下之分。
走出几十米,姥姥在我耳边轻声说,前面拐弯那个大石头的后面有一个包,里面是你姨她们拿的礼物。我给你包好了,你拿回家分给弟弟妹妹吃。记住,不要让别人知道了。
黑暗中,我使劲点点头,勇敢地向前走去。
六
有一年,大雪从除夕一直下到大年初二的早晨,整座整座的山都被茫茫的白雪覆盖,只有一些落尽了叶子的树干,光秃秃地待在山坡上。大雪封了门,早晨推开房门的时候,颇费一些力气。见我一直呆呆地望着远处的山,父亲说,雪这么深,你出不了门,就甭想着去姥姥家了。弟弟妹妹尽管盼着姥姥家的零食,盼了一年了,他俩还是小声说,哥,你还是不要去了。我没有理他们,中午比平时多吃了一个窝头。我是铁了心的,姥姥家必须去。
我还是跨上篮子,装上礼物——蘑菇和木耳,自然下面还是蓬松的枯草,枯草里面还有一条小鱼。
刚放寒假的时候,听别人说后山的溪水里有鱼,我带着弟弟妹妹去捉。那时溪水上面结了冰,我们就沿着溪边观察。在一个小水坑里,还真有小鱼,太冷了,它们都懒得动。我用一把铲子砸冰,好半天才挖了一个洞。那鱼也真傻,它竟然钻到洞口,伸出头来。可能只是想透口气,水下太闷了。弟弟用一把笊篱一下子网了上来,扣在妹妹的筐子里。半天的功夫也就捉了几条,最大的一个也才像一个萝卜大小。然而,这足以做一顿鱼汤喝了。
鱼汤是父亲做的,他只是尝了下味道,剩下的被我们仨分了。我把鱼背上的肉分给他们俩,然后严肃地说,鱼头和鱼尾是我的,你们谁都不能和我抢。后来捉的鱼越来越少,我想到了姥姥,就把一条最大的鱼,藏在了屋后的一个石坑里,又用石块盖好。
出门只是走了几百米,我就后悔了。雪太深了,快没到了膝盖。每迈一步都要用力从雪中拔出一条腿,再一次插进前面的雪中。我把篮子放在雪上,每前进一步就把篮子向前推一把。太阳比平时亮得很,一簇簇光线射进雪粒上,又四下反射出去,望过去晃得眼睛疼。漫山遍野的雪地上,我如一个小黑点,慢慢地移动。
反正到处都是雪,我不再走原先的山路,况且也找不到那山路了。我选择最近的距离爬上山坡,又从山坡上爬下去。其实从山坡上下去最爽了,我不再走路,直接趴在雪上往下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滑雪这个运动,不然弄一个木板或许会更快一些。
我站在姥姥家后面的山坡上,天色已经快黑了,路上用的时间太久了。白茫茫的雪中看不清姥姥家的情况,但我估摸着他们已经打道回府了。我凭着感觉一步步向姥姥家走去。
走上那个拐弯的大石头的旁边时,我看到姥姥家门前的这条路被扫出了一段。我拍打身上的雪,放心地向门口走去。远远的一个声音传来,是娃儿吗?那声音着急又惊喜。我应了一声,心里顿时明亮了起来,脚下忽然有劲了。
姥姥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娃儿,你咋来了?这么大的雪,不能晚几天吗?我故作轻松地说,没事的,姥姥,我就想今天来给你拜年。姥姥说,你的姨她们都没有来,你姥爷也病了,在床上躺着,家里今天也没做好吃的。说着,姥姥把我拉进了厨屋。她把灶门的一块石头挪开,从灶灰里扒出一块红薯,放到我的手里,还烫着。姥姥说,娃,快趁热吃了,又从锅里端出一碗丸子汤。我早已饥肠辘辘,这些食物很快就下了肚。
我对姥姥说,雪太厚了,我没有捡柴火,也不能去梁子那里打水了。姥姥说,傻娃娃,哪里用得着你捡柴火,水就更不用操心,这大雪化的水,吃上半个月也不愁。
我提上装着礼物的篮子去看姥爷。他的脸在灰暗的油灯下没有了往日的神色,估摸着是生病的缘故。老爷看见我来了,没起身,他只是恨恨地骂,儿大不中用,让他去喊个先生来都不肯,造孽啊。
黄家梁子的先生我知道,母亲吃的药大多都是从他那里买的。我走出堂屋,拿上姥姥的手电筒去请先生。姥姥死死地抓住我不松手,我还是挣脱了。姥姥只是在后面小声抽泣。
先生的家不算太远,转过两个坡就到了。我敲门进院,他并不认得我,不由得惊讶起来。我说明来由,他想了一下说,外甥,也只能是你,也只能是看在你娘的份上,我蹚雪走一趟。先生在收拾药箱的时候又自言自语,这都什么世道?
先生坐在姥爷床前,让他着实吃惊不小。瞧了病吃了药,临走时,先生说,可惜,我一个闺女也没有,也没得一个外甥。姥爷把头扭向床内侧,没有回他。
我要走了。姥姥让我住下,我坚持回去。姥爷说,把娃的礼物留下吧,再给他回点吃的,手电筒也拿上。
拐弯的大石头旁,我接过篮子,沉甸甸的。姥姥说,可不要弄丢了。
七
魏家祠堂的门窗重新上了漆,朱红色映衬着坡上的薄雪。山间小路也铺了黑色的柏油,如巨人在山坡上写的草书。我关上车门,背上背包,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
此时,山坡上的风依旧寒冷,吹动着我鬓间花白的头发。远处一些鞭炮声零星地响着,一束烟花在天空中闪烁了一下,映照着姥姥家东倒西歪的土房子。天空如黑色的冰块,繁星点点,那颗最亮的星一定是姥姥在迎我。
我走上前去,在倒在一旁的门板上轻轻拍了两下:“姥姥……姥姥……我来给您拜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