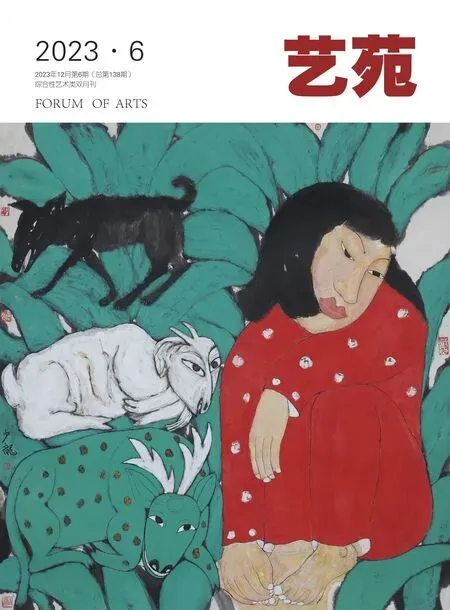形式创意、系统思维与文化表达
——论博物馆展览设计评论的三个维度
陈纯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博物馆事业方兴未艾,展览日渐增多。(1)展览设计的专业化、艺术化、个性化程度越来越高,正在迈向更加多元的创造之境。如何更好地发挥博物馆展览的独特教育与文化传播功能,使博物馆展览设计成为更能增益公众观展体验且更具公共审美价值的现代视觉文化创造方式,已然成了当代博物馆的光荣文化使命。这里显然需要评论的参与,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深层互动。可喜的是,近年来,有关博物馆展览的评论多有跟进且渐趋活跃,如微信公众号“源流运动”就专门开设了“展评”栏目。当然,展评本身也有待检视与提高,方能更见效益地与发展中的设计实践交流互动,助力展览设计的创作与发展。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当前展评多是围绕主题与内容策划展开,鲜有专门针对或围绕形式设计的论评与解析;而且,展评自身的理论反思与建设也尚未开启。这些都局限了展评对设计实践的学术助力与创作启导。有鉴于此,本文不揣浅陋,拟从评论的两个核心环节——理解与评价问题入手,通过考察博物馆展览设计工作的特殊性、目的性及创造性所在,尝试对博物馆展览设计的评论目标及其学理基础做初步探讨与建构,以期助推博物馆展览设计评论的专业化发展。
一、形式创意:博物馆展览设计评论的艺术维度
必须说明,本文的博物馆展览设计就是指展览的形式设计。(2)很显然,博物馆展览设计不同于自由艺术创作,其特殊性就是要在主题内容充分烘托传达与展览条件充分优化利用中实现形式美感创造,因此,它的工作思维乃是一种综合着科学遵循与艺术创造的系统思维;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特定的文化表达,不仅要实现展品文化内涵的表达,还要致力于展览形式自身的视觉文化表达;其艺术创造性主要体现在合目的性、合条件性的形式创意上。
作为博物馆展览设计的主要艺术性工作,形式创意是一种服务于展览主题内容表达的二度创作。因此,我们不能脱离开展览的内容策划来单独评论形式创意。而且,不同展览主题与内容给形式设计留出的创意空间大不相同。比如,同属精品展览,基本陈列的形式创意空间往往小于临时展陈,因为基本陈列内容相对固定、内涵边界也相对清晰,形式创意的发挥余地往往有限;而临时展览多为发掘性、交流性选题,展品选择相对自由、也相对不固定,主题内容多求新颖或讲时效,常常呼唤形式创意的填充表达、扩充表达,因此,出新出奇的形式创意相对多见。当然,对于临时展陈来说,主题内涵丰富与否以及展品种类、样式、来源的丰富与否等也都会直接影响形式创意的发挥。从近些年的设计个案来看,形式创意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寻常内容的新奇传达。比如,首都博物馆2017年的“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3),在由起伏墙板传达出的富有流动感的序厅中,来自全国21个省的49 家单位名牌从天花板垂挂下来,不仅呈示了展品来源的地域(“中华”)广布性,而且将空间性地域信息给予了“空间化”展示,新颖而适切;将与展览四部分内容“道法自然、天地之道、保合太和、和合能谐”相对应的四个历史时期“史前时期、夏商周、汉唐、宋元明清”用灯光打在地面上,不仅突破了墙面呈示主副标题的常规方式,更是实现了空间的时间性转化,把漫长的历史流程缩略成观展的行程,让观者感觉自己的脚步迈进的不是展厅的一个空间,而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直观而富有代入感。第三部分展厅上方以骆驼、沙漠、寺院、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等主要物象组成的“大唐西域”剪影造型,以及第四部分在一面空墙上设计的“月洞门”造型,都拟真地创设了相应展品(如汉唐时期雕饰繁复的漆器与佛像、宋元时期的素雅瓷器等)得以产生的历史情境,既烘托了展品又颇具形式美感。此外,将陶器碎片摆放在红色弧形阶梯上(喻示陶器来源)、雕文刻镂的青铜圆柱造型悬灯(喻示青铜时代)等等许多细节设计都可谓是设计师时空思维格局下的出彩创意,均贴切、新颖、可感地实现了“美·好·中华”这一展览主题的形式传达。
二是主题内涵的开拓表达。由中国民族博物馆策划,自2018年起陆续在北京、银川、南宁、杭州、南通等地举办的主题展“传统@现代——民族服饰之旧裳新尚”(4),设计师就以装置与陈列并行的方式对“服饰”背后的丰富文化内涵进行了多维开掘与表达。如,呈现在展览序厅的“缝制·时间”装置,将24 条在二十四节气当天浸入蓝靛而染成的深浅不一(因为受气候、温度差异的影响)的布条垂挂至地面,二十四节气以圆周的形式标识在织布下方,分别与其上方悬挂的染布对应。设计师更将三匹织布垂浸于蓝靛水池之中,让观众目睹染料慢慢向上渗染的过程。装置中央悬挂着一套有着365 根垂条、由彝族女性每天缝制一条而成的裙摆的云南寻甸的彝族女服,女服完整地经历了四季轮回,直观显效地传达出了服饰制作与四时节令的关联,突出表现了该单元的“时间”题旨。再如,第四单元“交错”中,一个由白色纱网围成的三面可穿行的三角形立体装置上,一边展示三套风格各异的民族服饰与流行服饰的搭配效果,一边又在三个通道中垂挂着的白色帘幔上循环播放混搭着自己的服饰与民族服饰造型的“素人模特”的访谈投影,当观众穿过通道时就产生了物、人、场景的交错,贴切而显效地实现了“传统@现代”这一主题立意的表达。还有像第三单元“工艺”中通过展示拆解了的制成一件华美衣裳所需的全部工具、原材料还原服饰成型过程,呈现前工业的服饰制作,引人回顾服饰从传统“手工制作”到现代“机器生产”的历史变迁;通过采用“实验室器皿”和“植物花房”展示服饰色料来源,让人省思服饰中所蕴含着的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等等,整个展览处处可见这种开拓主题内涵表达的形式创意。其间的创造性价值主要在于成功地开掘并展示了作为“静物”的服饰背后所蕴含的诸多“活态”内容——历史记忆、生活现场、服饰制作、季节轮替等等,让观众不仅观赏到了民族服饰多样性的美,还领略到了服饰中的鲜活生命气息与丰富文化内涵。
除了要从主题内容的表达出发努力实现最佳形式创意,博物馆展览设计很多时候还要针对展厅空间的大小、结构、采光以及展具供给等现实条件进行巧用性、化用性设计,这里当然也是凝聚着创造性思维的形式创意。不过,对于这类形式创意应该一分为二来看,当它不仅规避了不利因素,而且还为展览效果增色添彩时,就应该从艺术与科学的双重维度来理解与评价;当它只是最大限度地规避了不利因素、最大限度地不损及展览效果,则主要应该从科学-合理的维度进行理解与评价。
二、系统思维:博物馆展览设计评论的科学维度
博物馆展览设计不仅受主题内容与展览条件制约,还受展品安全性(5)与人体工程学规约。面对一个设计项目,设计师必须对展览条件、展品安全、艺术效果、观展体验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由此应该说,展览设计中的艺术创意思维,只能是科学系统思维指导下的一个“子思维”。不仅空间布局、展线设计、材料选用等需要在安全性、功能性前提下考虑审美性,像采光与展具选择等方面,也都要在展品安全性、观赏的清晰度与舒适度的前提下来考虑光、色搭配的审美效果与展具的形式美感等。因此,系统思维是我们理解与评价一项博物馆展览设计的更为基础的维度,即科学的维度。按“一般系统论”[1]16-17的观点,“系统”是诸要素依数目、种类与关系三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一个包含不同层级的复合体概念。对于博物馆展览设计来说,统领级的系统思维就是安全性、功能性要求与审美性追求的统筹兼顾思维。该系统思维要运用到展览设计的方方面面。比如,从大的方面来说,既要考虑空间的充分利用、安全利用;又要考虑展线的宏观控制,把握平叙和高潮的节奏,使观者兴致收放有致;还要考虑展柜的形式、材料、肌理与色彩等,与展厅的结构、采光、墙面材质、肌理、色彩等方面的整体的审美协调与呼应。小的方面比如文字说明牌的设计,既要从信息传递效果的角度考虑字体大小、位置安排;又要从形式美感的角度考虑牌子形态、字形颜色、放置方式等方面的搭配效果;还要从人体工程学的角度考虑位置高低、字数多寡、横竖排版等方面的问题,如人的双眼综合视野约为横向较宽的椭圆形,这种构造使人眼左右移动比上下移动方便,而且,看上面费力易疲劳,看平线以下则较为便利,同样对于人的颈部,左右移动也比上下活动省力,仰头就比低头活动量大等等,因此,一般高于视平线的文字材料只适合标题等短文字,说明牌的位置则应与视平线一致或低于视平线。与材料、光线、温湿度等安全性指标一样,人体机能特点等也都是展览设计所要顾及的科学性因素。像西藏博物馆2022年6月开展的“离太阳最近的人——西藏民俗文化展”中的文字材料位置明显偏高,就说明设计师缺乏人体工程学角度的考虑。
博物馆展览设计的次级系统思维是从展览主题内容的表达出发对形式设计作整体性安排的结构思维。它要求一项展览设计要有一种既能准确圆满地呈现内容结构、又具有自身艺术逻辑的形式结构。前者主要服务于观展理解,后者主要服务于观展体验。其科学性主要体现为一种学术合理性。由此,从该结构思维的角度评论某项展览设计,就应首先从学术合理性角度来审视其对大纲内容结构的空间形式化、形象化呈现的状况。展览的内容结构主要有线性、板块两种基本形态。线性结构最常见的就是以时间为序安排的内容结构。板块结构则是指基本处于并列关系的各部分依学术逻辑、文化范畴、习惯等方式来安排顺序的内容结构。比如,“离太阳最近的人——西藏民俗文化展”就是板块(主题板块与地域板块)中综合着线性(四季顺序)的内容结构,而且在这种综合结构中还做了前“静”(实物)后“动”(场景)分割。从学术合理性来看,这里就存在部分“无意义重复”问题,即一部分前面独立展示的实物又在后面场景展示中出现,说明该展览设计系统性考虑欠周全。形式结构的合理性除了体现为有助于观展理解的展览内容呈现的学术逻辑化,还体现为能提升观展体验的空间形式呈现的艺术逻辑化。比如,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协调,空间的合理分割与安排,展线设计的单向呈现、通道通畅,动线节奏的松弛有度,灯光明暗与色彩冷暖变化的合度调节、合逻辑安排等等。
博物馆展览设计再低一级的系统思维还有诸如展品系统性组合以及展览有关信息的系统化整理呈现等。如上海博物馆2017年8-10月展出的“遗我黄鲤鱼——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吴门书画家书札精品展”中就设计了49封信札中的人物关系图,不仅有助于人物关系的简便了解,还让人们对当时吴门书画家艺术风貌形成背后的封建宗法社会组织形态有所了解。
在《理解视觉文化的方法》一书中,马尔科姆·巴纳德梳理了视觉文化理解的阐释学与结构主义两个传统,前者认为理解视觉文化主要应着眼于创作者个人的行为和意图,后者则认为个人的行为和意图其实受制于某个先在的“结构-模式-无意识的价值体系或表征体系”[2]49,理解视觉文化应首先着眼于个体意图背后的那个先在的“结构-模式”。本文以为,就博物馆展览设计而言,既有先在结构(如展厅空间结构,功能性、安全性、审美性的牵连结构等),也有主观创造(如形式创意、结构布局等),而且主观创造中也包含着结构思维、系统思维的先行运用,展厅空间结构等先在结构也正是主观系统思维的处理对象。由此,我们还是赞同保罗·里尔克的“双向理解”观点:“没有结构上的理解就没有阐释学上的理解,反之亦然。”[2]40这也正是本文所强调的系统思维的理解维度。
三、文化表达:博物馆展览设计评论的效益维度
在博物馆展览设计中,形式创意与系统思考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在有限空间里实现特定的文化表达。因此,评论一项展览设计,最终还得从这一根本目的出发,去理解它的形式立意,审视其文化表达效益。
首先,应站在展品内涵视觉化诠释的角度来理解与审视。展品内涵主要靠研究人员探索发现,陈列设计的中心工作则是对大纲所提供的展品内涵说明进行视觉化、通俗化的 “翻译”与表达。这里就有个连环理解的问题,即大纲撰写者对展品研究成果要有很好的理解与选择,设计者对大纲也要有很好的理解。因此,评论一项展览设计的展品内涵表达效益,就必须通过对大纲内容的理解与检视,在区别不同内容类别(如艺术类、历史类、人物类、科技类、自然类等)与不同传播目的(如审美或叙事等),了解阐释方式(如解析、呈示、体验交流等)、媒介运用(如图文版面、辅助艺术品、新媒体和科技装置等)及所有形式立意的基础上,结合对现实效果的体察,方能给出公允评价。比如,面对“卢浮宫珍藏展——古典希腊艺术”(6),就应当站在以审美为主要传播目的、以实物配以氛围呈示为主要阐释方式、以标志性实物与符号为主要媒介手段的艺术类展览的角度来进行理解与评价。其序厅设计,除了必要的主标题,没有一个多余的字,而是在一个圆形的平台上布置了帕特农神庙遗址的石柱,并在顶端悬挂了蓝色灯光效果的希腊地理位置图,简洁而大气地营造出了希腊文化所特有的氛围。从“古典希腊艺术”这一主题的氛围烘托与内涵呈示效果来看,该序厅设计显然取得了预期的文化表达效益。再如,在“破碎与聚合:青州龙兴寺古代佛教造像”展(7)中,设计师将部分佛像碎片直接平放在地上,然后在墙上挂着1997年整理这批造像时郑岩先生绘制的第一张测绘图,以及记录田野发掘现场、室内整理工作的照片的展板,展厅中间则是寺院氛围拟仿中的完整佛像展示。这里其实叠合着三重历史场景叙述:完整佛像中的古代造像场景、佛像碎片中的后代毁像场景、测绘图与照片中的佛像出土及整理场景。通过现代装置艺术方式与传统文物展览方式的两相结合,直观且对比强烈地展现了佛像在不同历史情境下所遭遇的“破碎与聚合”的命运,极具冲击力地表达了设计师的文化立场与情感态度。
其次,应站在观众接受的角度来理解与审视。按接受美学观点,博物馆展览设计作品的教育、传播功能都要在观众观展中实现,而实现过程即是作品获得生命力和最后完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观众并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设计师的作品,而是积极、主动地进行着三度(一度是策展人与大纲撰写者、二度是形式设计师)的创造活动。在设计师、作品和观众三者的动态交往关系中,观众位于意义发生与实现的中心地位。[3]3当然,观众中心论未必完全正确,因为观众的观展理解既有前见,又是动态变易、被引导的,发生怎样的意义、发生多少意义都是在设计师与观众的动态交流中出现的,且总是因人而异。但是,展览设计终究是为观众观展而存在的,其价值意义与文化表达效益终究取决于观众的接受情况。因此,如何在多元化视觉文化环境中,设计出既易于为大众理解与接受,又能拓展大众视觉审美体验、提升大众视觉审美能力的作品,是当代设计师体现自身创造价值的根本目标,也是人们评价形式设计自身文化表达效益的主要着眼点。比如,当观众走进“古典希腊艺术”展序厅的瞬间就能感受到浓厚的希腊色彩、领会到蓝色地毯对希腊文明的喻示,内心会被引向安宁、引向“古典希腊”的特有审美情境。再如,在“传统@现代——民族服饰之旧裳新尚”巡展中,本地元素的地缘性、现代装置的时尚性、过程呈示的真切性、交错场景的体验性、内涵呈现的丰富性等等,无不给观众既熟悉又新鲜、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时尚、既获新知又获启迪的美妙观展体验,审美效益可见一斑。当然,形式设计总是为内容表达服务的,不能喧宾夺主。“传统@现代”的所有形式创意都是服饰内在的“ 活态内容”,不但不存在喧宾夺主,反而拓展了内容表达,所以值得高度评价。
四、结语
博物馆展览设计评论的三个维度实际上也就是设计实践需要综合考虑的三重工作目标。当前三个方向都能做好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要么科学性、学术性考虑欠周全,要么形式创意乏善可陈,要么文化表达欠自觉或不充分。本文的探讨只是想尝试厘清实践与评论的三个根本目标,希望目标的明确有助于实践与评论的互动,有助于展览设计艺术的发展,并不是要建立固定范式去框定博物馆展览设计评论。评论当然更应该是个性化、多视角、多触点、创造性的。但根本目标的探讨总是必要而有益的。尤其在当前展评还欠发达、形式设计评论明显落后的专业情势中,指出评论与实践互动的重要性,厘清评论的目标指向,才能在唤起业界重视形式设计评论的同时,把个性化评论的根本出发点往展览设计艺术发展的根本路向牵引与集中,才能聚力推进展览设计事业的突破发展。
注释:
(1)2023年5月18日,在福建博物院举行的“5·18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正式发布了如下中国博物馆发展数据:2022年,我国新增备案博物馆382 家,全国博物馆总数达6565 家,排名全球前列。全年举办线下展览3.4 万场、教育活动近23 万场,接待观众5.78 亿人次,推出线上展览近万场、教育活动4 万余场,网络浏览量近10 亿人次,新媒体浏览量超过百亿人次。通过持续完善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我国90%以上的博物馆实现免费开放。
(2)有的博物馆学论著(如耿超等编著《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18年8月版)把博物馆“展览”表述为“陈列”,并把“陈列”的创造性工作内容分为“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两部分。本文还是沿用陈红京主编的《博物馆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1月版)中“博物馆展览”的表述,主要探讨该著关于博物馆展览的“内容策划”“形式设计”与“施工管理”等三个工作环节划分中的第二个环节“形式设计”的理解与评价问题。
(3)该展览国家文物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和首都博物馆承办,策展人为俞嘉馨,展览时间为2017年5月18日—8月27日,展览地点为首都博物馆一层B 展厅。
(4)该展览为巡回展,由中国民族博物馆出品,迄今已在北京、银川、南宁、杭州、南通等地成功举办,策展人为吴洁、罗潘等,北京场展出时间为2018年2月7日-3月4日,展出地点为中华世纪坛一层专题陈列厅。
(5)博物馆展览不仅必须符合一般公共场所的所有安全要求,还有着特殊的对于展品的安全性要求,比如,对展柜就有诸多技术要求:防尘、防火、防盗、防潮、防水、防霉、防蛀、防有害光(防红外线、紫外线)、防眩光、防环境因子(温、湿度控制,防有害气体如氧气、挥发性气体的入侵)等等。
(6)该展览由首都博物馆将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联合主办,展览时间为2007年8月12日至11月9日,展览地点为首都博物馆地上一层临时展厅(B 厅)。
(7)该展览由中央美术学院和青州市博物馆联合主办,策展人为郑岩,展览时间为2016年9月3日至9月20日,展览地点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一层大厅、二层A 区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