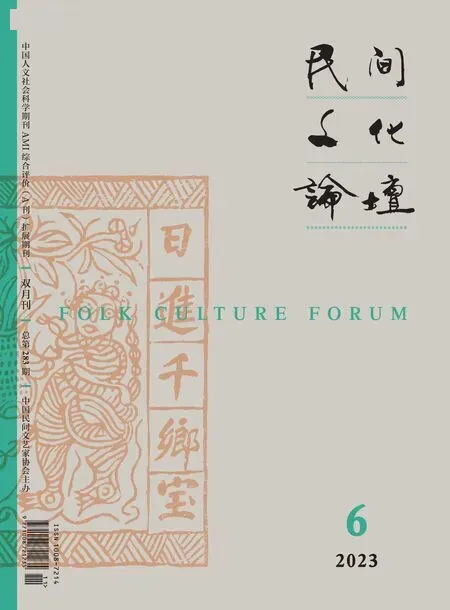时代变迁与文化症候:晚清民国上海地区的冬至节日生活与消费转型
王敏琪
清末民初,国门洞开,中国卷入了世界近代化的浪潮之中,面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变革转型。其中岁时节日的变迁,作为一个反映社会大众生活方式的缩影,呈现了中国社会由传统乡土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嬗变的历程中传统文化的转变及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冬至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节日。
目前学界对于传统冬至的研究已较为完备,无论是对节俗源流的钩稽梳理①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张勃、荣新《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中对冬至的发展脉络、节日饮食、社交活动、信仰禁忌等作出详细而深入的归纳与总结。(参见张勃、荣新:《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356—370 页。)周星《“冬至饭”的世界:民众体味的神圣时间节点》,通过对涉及冬至的谚语、歌谣以及各地冬至饮食习俗的梳理和分析,生动具体地呈现出冬至这一新旧交替、阴阳消长的时间节点如何根植于中国的民俗文化之中。(参见周星:《“冬至饭”的世界:民众体味的神圣时间节点》,王加华主编《节日研究》第15 辑,2020 年第1 期,第3—15 页。)李向振《冬至节俗源流及其文化内涵》就冬至日形成的官方与民间两套过节系统予以详尽的整理和总结,认为冬至是“礼俗互动的重要机制和各种社会关系调适的文化场域”。(参见李向振:《冬至节俗源流及其文化内涵》,《节日研究》第19 辑,2022 年1 期,第55—85 页。),还是对文化内涵的阐释分析②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萧放在《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以“冬至大如年——冬至节俗的传统意义”专章剖析了冬至在传统阴阳观念中“顺阳助长”的文化意义。参见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220—230 页。又如袁瑾《天正与人时:冬至时间意象的滋生》探讨作为节气交接点的冬至,其时间意象的建构过程。参见袁瑾:《天正与人时:冬至时间意象的滋生》,《节日研究》第16 辑,2020 年2 期,第55—65 页。,均有丰硕成果,却较少注目于晚清民国上海地区传统冬至与作为“外国冬至”的圣诞节之间的文化互动。对于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相关研究多以圣诞节为主题而兼及对“外国冬至”的探讨,如邵志择在《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近代以来圣诞节在中国的节日化》③邵志择:《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近代以来圣诞节在中国的节日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29—34 页。第二章中详细梳理了圣诞节被称作“外国冬至”的来龙去脉,刘芳也进一步阐发了“外国冬至”这一“嫁接式称呼”所存在的偏颇之处。④刘芳:《制造圣诞——论民国时期耶稣圣诞节在上海的流行》,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第20—22 页。以上两种研究均着重强调了传统冬至与圣诞节之间呈现出的差异性和对立关系,而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与互动关系则有待更深入的探讨。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启发下,以传统冬至为起点,注意到特定的时空背景中“冬至”这一概念脱离原有文化属性而呈现出的症候性特征①“症候”,本为医学术语,指疾病显现出来的情状。本文以其概括在近代社会转型期伴随着外来文化与传统产生碰撞、民众生活方式急剧转变而出现的具有阶段性特征的时代问题。。这一特殊现象为我们认识与理解近代社会转型期节日的符号化及变异提供了新的思考面向。
一、传统冬至节俗与江南社会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前缘,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八府一州”的组成部分之一②目前学界较为公认的“江南”核心地区,其大致范围应是苏南的苏、松、太、常、镇、宁及浙北的杭、嘉、湖等八府一州。参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1 期。。而随着晚清上海开埠以来经济地位的不断抬升,移民人口急剧增加。在各地迁居上海的移民中,江浙移民亦是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的移民团体③近代上海人口的籍贯构成,“一般说来,距离上海地区的远近与其有关省份籍贯人口的多少是成正比例的。例如,1934 年上海‘华界’人口中,除了本籍人口占总数的25%以外,江苏省籍贯人口占39%,浙江省籍贯人口占19%等等。旧上海公共租界有类似的情况。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上海人口籍贯的构成也有类似的情况。”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42 页。。因此,在地理空间和人口构成双重因素的作用下,近代上海本土文化呈现出以江南文化为底色的显著特征。
在天文历法意义上,冬至作为“二分二至”之一,从殷商时期便得到记录,并不断被塑造为具有神圣性的时间节点。与冬至相关的仪式活动较早记录在宫廷祭祀之中,《周礼·春官宗伯》之中即有周天子“以冬日至,礼天神、人鬼”④杨天宇译注:《周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397 页。的记载,此后历代君王均将冬至日视作敬天祭祖的朝仪活动日。
而民间对于冬至的重视亦源远流长,并构成了延绵不绝的庆贺传统,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冬至祝节活动,多见于南宋以来乃至于明清的史料记载。在祭祖飨神之外,民众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休憩宴饮、赠礼往来,丰富的节日活动呈现出鲜明的世俗享乐特征。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六即载临安城中为了庆祝冬至,士人百姓设宴庆祝、互赠礼物、祭祀祖先的种种场景:“最是冬至岁节,士庶所重,如馈送节仪,及举杯相庆,祭享宗禋,加于常节。……此日宰臣以下,行朝贺礼。士夫庶人,互相为庆。”⑤吴自牧:《梦粱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48—49 页。《武林旧事》卷三更为生动具体地描绘了冬至之时城中热闹非凡的“做节”盛况:“而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遝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炫,往来如云。岳祠城隍诸庙,炷香者尤盛。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帘饮博,谓之‘做节’。”⑥四水潜夫辑:《武林旧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45—46 页。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妇女小孩纷纷打扮一新,上街游玩,行香祈福。而三日之内,店铺商肆也都关门歇业尽情宴饮娱乐,可见冬至节是临安一地全民庆贺并沉浸其中的重要节日,场景之盛大、气氛之欢腾溢于言表。
而明清时期,冬至节在江南地区也得到了一以贯之的关注与重视,“冬至,邑人最重”“诸凡仪文,加于常节”之说常见诸文献记载,民间甚至称其为“亚岁”⑦“冬至,谓之‘亚岁’。官府、民间各相庆贺,一如元日之仪。”参见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321 页。,又有“冬至大如年”的俗语,其重要性可与新年相媲美。从这一时期的地方志与文人记录中看,江南民间对于冬至的庆贺,从冬至前一日的晚上便已开始,即所谓“冬至夜”。正如《清嘉录》载:“节前一夕,俗呼‘冬至夜’。是夜,人家更速燕饮,谓之节酒。女嫁而归宁在室者,至是必归婿家。家无大小,必市食物以享先,间有悬挂祖先遗容者。”①顾禄:《清嘉录》,来新夏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155 页。冬至夜,也称“节夜”“除夜”“冬住”,是江南地区的民众在祭祀祖先后设宴待宾、家宴贺节的欢乐时间,凝聚着家人团聚的喜悦与幸福。第二天,官府、民间交相驰贺:“士大夫家,拜贺尊长,又交相出谒。细民男女,亦必更鲜衣以相揖,谓之‘拜冬’。”②同上。
因此,有关冬至的节日消费亦较多,须备办各种美酒佳肴以祭祀祖先,采购各类礼品以往来馈赠,有时宁可过年时节俭一些也不肯虚度冬至,故有“肥冬瘦年”之称。如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记载吴中民间“舂粢糕以祀先祖,妇女献鞋袜于尊长”③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321 页。。同样是苏州地区,清代时又有做“冬至团”的习俗:“比户磨粉为团,以糖、肉、菜、果、豇豆沙、芦菔丝等为馅”④顾禄著,来新夏点校:《清嘉录》,第156 页。,既为祭祀祖先与灶神的供品,也能够当作互相馈赠的礼品。冬至前后人们出门在外,常手提盘盒拜贺亲友,而盘盒内装的都是供人享用的冬至美食以及冬酿美酒等,俗称“冬至盘”。在杭州,当地民众每逢冬至夜,还购买几条包头鱼做菜,并留下头尾,意为“吃剩有余”,一如除夕。故有诗云:“学做西湖宋嫂羹,包头鱼担遍杭城。明朝冬至如年大,早办辛盘话甲庚。”⑤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册,长沙:岳麓书社,2013 年,第523—524 页。而在冬至日这一天,市场上亦有年糕出售,“颜色或青或白,有成元宝式者,有成如意式者,无论贫富人家,咸购食之,成为牢不可破之习。”⑥同上。
与江南地区庆祝冬至的隆重热闹相比,在江南地区以外的部分地区,民间已渐渐不再重视冬至。据《日下旧闻考》引明代李默《孤树裒谈》道:“京师最重冬节,不问贵贱,贺者奔走往来,家置一簿,题名满幅。自正统己巳之变,此礼顿废。”⑦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8 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2365 页。可见在时局的影响下,明代正统以后,北京地区的冬至民间朝贺之礼逐渐废止。而到了清末,根据《燕京岁时记》的记载,“冬至郊天令节,百官呈递贺表”,在朝堂之上还保留着形式上的庆贺,但在民间过节的气氛已所剩无几,只余吃馄饨之俗尚存:“民间不为节,惟食馄饨而已。”⑧王碧滢、张勃标点:《燕京岁时记 外六种》,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 年,第111 页。
由此可见,无论是将冬至作为重要岁时节令的一致认同,还是冬至节俗在地域内部所呈现出的高度相似,都鲜明地昭示着江南地区如何在冬至节日文化上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具有辨识性的文化共同体。起居饮食的同频共振,风俗传统的守护相望,是文化共同体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肯定性体认。在晚清时人秦荣光的《上海县竹枝词》中,对于上海冬至节俗的叙写,显然亦基于江南生活的共同经验而加以阐述:“冬至花糕更粉团,冬分酒吃闹闹年。衣冠拜贺亲朋后,肉块堆盘夜祀先。”⑨欧粤编:《松江风俗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242 页。竹枝词中所述种种节庆事项,如制作花糕粉团、吃酒宴饮、拜贺亲朋、祭祀祖先,均表明上海对于冬至的庆祝,正是植根于江南共同的文化传统,保有并承续着丰富多彩的节日生活。
二、“外国冬至”的名实之间
清末开埠之后,随着经济地位的迅速上升,上海一跃成为整个江南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中心,同时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也在中西往来交流中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空间。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外国租界的扩大与外侨人口的增多,以西人家庭和西人社区为主体的过节方式在租界中形成规模,由此,以“外国冬至”为名的新鲜节日圣诞节感染并影响着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所谓“外国冬至”,是耶稣圣诞在刚刚传入中国时的民间俗称,另有“西历冬至”“西国冬至”与“西人冬至”等代名。笔者所见最早记录这一别名的是《上海新报》1868 年12 月29 日的报道:“昨西人过冬至节,即耶稣诞日也。”①《中外新闻》,《上海新报》,1868 年12 月29 日,第2 版。而其他报刊的报道中如出现“耶稣诞日”等名称,其后也总加上“阳历冬至”“称作外国冬至”“外国冬至节”等字样,以消解读者面对异域文化时所产生的困惑与隔膜。
之所以能将标志来源的“外国”一词与传统节日名称“冬至”一词嫁接在一起代称圣诞节,固然如陈东林在《外国冬至 外国清明》一书中所言,是二者日期接近将错就错发展出的称呼②“中国冬至节每年总是在圣诞节的前二天或者三天,而一般中国人又对圣诞节的意义不大明了,所以将错就错把它称作外国冬至了。”陈东林:《外国冬至·外国清明》,上海:中华书局,1948 年,第1 页。。除了这一偶然因素之外,事实上也能够从中发掘出更具深意的文化缘由。
当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为基础形成的中国传统节日体系与外国思想资源相碰撞时,一方面,作为一个外来的异质性洋节,圣诞节需要借助中国的本土资源获得认同,依靠传统节日“冬至”的合法性力量进入文化主体的场域,从而安身立命。另一方面,“外国冬至”之名正体现着民族文化本位思想,是中国民众以自身传统中的“中国冬至”为参照,推己及人形成的对于他者的认识与定位。也正如此言:“第一个把耶诞叫作‘外国冬至’的人,必然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这名词洋溢着异国情调,而又充分地迎合着国人的口味。”③上官大夫:《冬至当然外国好 葡萄美酒玻璃杯》,《申报》,1946 年12 月25 日,第12 版。与此命名逻辑相似的,还有被称为“西历除夕”的公历新年和别名“外国清明”的复活节。
而我们如今用以指代耶稣圣诞的“圣诞节”之名,其推广流布则要归功于《申报》。据邵志择考证,自光绪中叶起《申报》中即有“耶稣圣诞”之称,1918 年刊发了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撰写的《耶稣圣诞节》,此文正式将“圣诞节”解释为“耶稣基督诞生之日也”④邵志择:《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近代以来圣诞节在中国的节日化》,第38 页。。从此“圣诞节”渐成定名,并在社会范围内广泛流传。
与“外国冬至”相比,“圣诞节”一词得到了教会机构的正式认可,并有意亲近中国本土的信仰资源,在与“孔子圣诞”“观音圣诞”等宗教节日相提并论的同时,亦借此强调了基督教自身的宗教地位与教义思想。而圣诞节在上海扎根的历程,始于租界内的外侨社区中在华外国基督教徒对庆祝耶稣诞辰的需求,尽管负载着深层次的宗教文化意义,然而就其表面上所体现出的庆贺方式,如放假休憩、团聚宴饮等热闹场景,则与冬至十分类似。出身老派上海家庭的作家程乃珊便认为:“西方人圣诞节,其程度比元旦更隆重。外出的亲人怎么都要赶在平安夜前回家团聚,与我们的‘冬至大过年’可谓异曲同工。难怪老上海称圣诞节为洋冬至。”⑤程乃珊:《土冬至和洋冬至》,程乃珊、谢春彦编著:《上海TASTE》,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年,第227 页。“外国冬至”这一过渡性的称呼,体现出在节日文化产生碰撞的初期,民众事实上是以世俗眼光来审视这个西方宗教节日的,并不断发现和对比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1897 年《新闻报》有《西节志盛》一文,专门记载了在沪居住的西人是如何享受与欢度圣诞节的:
先期,各西人家俱用冬青、柏叶系作垂花门,室中陈设辉煌,争相炫耀。届时邀宾燕饮,尽日言欢,燃木炭以围炉,飞螺觞而醉月,暂抛俗务,藉洗旅愁。各店铺更踵事增华,铺张场面而尤以“福利”为耳目一新,入其中,觉十色五光,陆离璀璨。凡用物、食物,绫罗、绢帛、锦绣、金银,以及珊瑚木难之瑰奇,锦贝文犀之美丽,如入波斯之域,令人耳眩神摇。平时送货至买主家,悉用高大马车载运,兹以五色颜料就车上写吉利语,以表祝忱,更令出店马夫穿五色衣,戴假面具,高坐车上,若演戏然。①《西节志盛》,《新闻报》,1897 年4 月17 日,第2 版。
此篇报道详细备至地描述了种种盛大美丽的场面,从头至尾流露出的都是被节日气氛所感染后“耳眩神摇”、心生艳羡的情绪。新鲜有趣的物质享受、欢腾浪漫的异域风俗,是非基督教徒的视角观察圣诞节的主要着眼点,也构成了早期圣诞报道中的主要内容。这不仅说明圣诞节的庆贺方式与庆祝冬至的相似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海市民的情感共鸣,“真不肯辜负良辰佳节”②东吴:《通俗谈》,《申报》,1909 年12 月26 日,第20 版。,亦体现出上海市民心理中一种开放与接纳的姿态——在消弭了其原有的宗教意味之余也欣然吸收了其中所包含的物质文明。
在“外国冬至”越来越引发社会关注之时,传统冬至却遭受了重大的打击。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从此,在公共生活中,来自西方的格里高利历以公历的名义取代夏历,而后者只在百姓日常生活中使用,并被称呼为“废历”“旧历”。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历并未完全取代旧历,二者分庭抗礼的同时也造成中西历法上的混淆。
尽管政府的意愿在于通过废除旧有夏历,使用公历与世界节奏接轨,但这种思路却也强调了“进步”与“落后”的简单二元对立。与旧历相关的一系列传统年节不再受到官方重视,如1912 年和1913年的传统冬至,在上海本地的报刊中均无相关的报道,反而《时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庆祝外国冬至”③《庆祝外国冬至》,《时报》,1913 年12 月26 日,第14 版。的文章,记当地官员在圣诞节当天预备酒席宴请海关一事。1914 年,袁世凯政府将四个旧历节日(正月初一、端午、中秋和冬至)分别称为春节、夏节、秋节和冬节,其中冬至被北洋政府正式命名为“中华民国冬至节”④《冬节停止办公》,《申报》,1919 年12 月22 日,第11 版。这则新闻中说:“明日(二十三号星期二,阴历十一月初一)系冬至节,经中央定为中华民国冬至节,本埠各机关均循例停办公务。”冬至节也简称“冬节”。,准予放假以示庆贺。然而冬至却因其祖先祭祀和岁时仪礼的成分不断受到质疑,不仅祭祀活动被当作繁文缛节和旧俗糟粕⑤《冬至节日之南通》,《时报》,1917 年12 月24 日,第6 版。加以贬斥,而节俗庆祝也以助长铺张浪费的奢靡风气为由被批判⑥《冬至节之大老官》,《小时报》,1917 年12 月23 日,第4 版。。国民政府掌权之后很快便革除一切旧节俗,使得冬至节俗缺少官方带头认可的正当性,受到自上而下的抑制;而另一个“外国冬至”却日益成为上海城内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相较之下,传统冬至的节庆气氛也就似乎日渐淡化了。时人不禁感叹,如今“过完一个冬至又是一个冬至”,看似好事成双,实则“本国冬至不时髦,西国冬至看热闹”。本国冬至的风头逐渐被圣诞节所取代,甚至出现了“冬至之名,幸托耶稣以存”①黃浚:《冬至与圣诞节》,黃浚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27 页。的说法。由此“昔之风俗,冬至日献袜履于舅姑,今日但知有圣诞节,不知有冬至,但知有圣诞老人赠儿童玩具之袜,乃至新妇多不愿有舅姑,遑知有献袜乎?”②黄浚:《《马夷初记武林新年风俗》,黃浚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393 页。
三、新式消费周期的生成
尽管出现了传统冬至走向没落、“外国冬至”在上海站稳脚跟并为新派市民所接受的新旧交替之变,但人们对于节庆娱乐的需求是一以贯之的,而不断涌入上海的西方物质与精神文明亦正契合新兴市民阶层的享乐需求。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借由冬至之名,爆发出空前的世俗享受狂潮,不仅出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新变化、新发展,还与圣诞节、新年等节日连接为更长的消费周期“冬至汛”,形成了以娱乐消费为目的的新狂欢。
在多种多样的新式消费中,物质消费最为突出。以饮食为例,在传统的食俗基础上,西方饮食逐渐进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沪上人士常以吃西餐为时髦。在冬至这一天,许多酒楼挖空心思从海内外“搜集珍馔佳酿”,特备阖家团聚的“冬节宴”③《广告》,《申报》,1944 年12 月24 日,第2 版。,如邓脱摩饭店的冬至大菜,菜品包括龙虾、火鸡、鹌鹑等④《邓脱摩饭店添冬至大菜》,《申报》,1929 年12 月25 号,第16 版。,一经推出就被预订一空,有的甚至邀请外籍演员进行歌舞表演,以为招徕顾客的噱头。这不仅丰富了上海民众的食谱,也使得传统的菜肴点心得到了革新,如笔名为天台山农的某文人曾写《冬至节之新食品》⑤天台山农:《冬至节之新食品》,《大世界》,1920 年12 月22 日,第2 版。一文,博古证今分析今日冬至之新鲜吃食,如《四民月令·冬至》曾记载之荐黍糕,现在有各种文明糕饼,口味大为丰富,有枣泥、玫瑰、鸡绒、肉松等等,古人冬至要吃赤豆粥,如今大世界天香斋有桂花赤豆汤可供品尝。至于天台山蜜橘和梅花茶则是最近为时人所喜爱之冬季特产,能够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宠儿也有赖商业的繁荣与交通运输的发展。
而在精神消费方面,也涌现出新变化、新现象。以戏剧为例,在西方戏剧传入以前,观戏是民众最重要的娱乐活动,每逢节日,城乡盛演地方戏曲,听戏就成为民众主要的娱乐活动。在传统生活方式之中,冬至所观看的戏曲演出虽然有一定的娱乐作用,但通常是为酬神谢祖、迎福纳祥而举行的具有祭祀意义的仪式性活动,而自开埠以来则逐渐走向完全意义上的世俗娱乐,戏曲演出的功能由娱神变为娱人。民众在冬至之时除了可以观赏男女合演的梨园戏之外,还可以携情人观赏“歌白爱情喜剧《璇宫艳史》”⑥《广告》,《申报》,1931 年12 月27 日,第20 版。等西式戏剧,学校与进步学生团体亦举行游艺会,届时更有教员与学生共同搬演新剧,并辅以舞蹈、双簧、国技等文艺表演⑦《志成公学冬至节将开会演剧》,《申报》,1925 年11 月26 日,第15 版。,场面极为热闹。
从冬至到圣诞节,乃至于元旦,构成了一个漫长的年末消费时段,在当时的报刊上被称作“冬至汛”。正如严独鹤所言,“上海人对于‘冬至汛’,似乎很感觉兴趣……于是到了这个期间,又不免有许多社交馈赠。这几天,尽管风云激荡,局势紧张,圣诞老人依然出现在各大商店的橱窗中。‘冬至礼品’的广告,也依然占着各报很大的篇幅了。”①桐乡市政协文教卫体与文史委员会编:《严独鹤杂感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 年,第434 页。越来越多的商人发现了这块“诱人的蛋糕”,打着“冬至汛大减价”的字样促销冬至商品,传统的冬至节便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被重新接纳进资本经济的消费体系之中。事实上,在“冬至汛”的命名之下,传统冬至与“外国冬至”已然不分彼此,两者一前一后被统合进更大的“冬至”概念中,背后所负载的神圣或世俗的时间意涵也趋于模糊,只是作为符号化的节日标志而在物欲的海洋中流动。现代物质文明在都市商业思维中作为主体的欲望对象而得到肯定,各式各样现代娱乐消费包蕴着鲜明的时代特性和全球视野的眼光。
各个报刊所刊载的广告无疑作为重要的媒介载体,宣传中大力介绍多样的节庆商品,为新式洋货附加“冬至”的符号价值,从而实现了契合消费者心理的“本土化”融合。从刊登广告的时间跨度来看,自20 世纪初便零星见诸报刊,20 年代以来数量激增、层出不穷,至1949 才告一段落。而从刊登广告的周期性来看,一般从公历12 月初就开始陆续有减价促销、新品上市的广告见报,一直到月末方收场。如1925 年12 月5 日《工商新闻报》所刊《新年与冬至日之送礼品》,从此文中可以看出庞大的年末礼品市场的冰山一角:“美记华珍公司之电刻银器、银盾、风景画片等,张裕酿酒公司之高月白兰地及红白葡萄酒,冠生园之各种中西点心,与新出之罐头牛肉汁”②《新年与冬至日之送礼品》,《工商新闻报》,1925 年12 月5 日,第7 版。等等时兴商品不一而足,从价格高昂的银器到价格亲民的牛肉罐头等,品种丰富,中西兼有。为迎合顾客喜爱洋货的心理,凡是非本国生产的商品都要特意提到从欧美进货,如“商务印书馆之上等美国信封信笺”。即使同一种礼物,也有不同的生产厂家为此大打擂台。别出心裁的销售商家采用了礼券这种新型消费形式,面额从一元到千元,鼓动消费者购买代金券当作冬至礼物送给亲朋好友,持有礼券的人可以凭券随时去指定部门支取商品,极大地煽动了民众的购买欲望。除了报刊广告之外,街头还有百货公司的橱窗和霓虹灯,以及广播、电影等视听媒介,不遗余力地营造烘托出上海社会整体消费氛围,进而对市民的年末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产生影响,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风气。
由此,西方的消费主义文化与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冬至享乐观念在这片土地上相互交融,产生了独具特色的上海市民年末消费文化。“冬至”作为一个促进消费的节日要素,与圣诞节乃至于元旦一道,被消费文化引导包装成一个购物娱乐、消费狂欢的摩登节庆,是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重要表现之一,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尤其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摩登男女尤为热衷。而他们正是庆祝“冬至”的新兴主体,既不受繁琐的基督教宗教礼节拘束,也摆脱了传统冬至中迎福践长的浓厚道德规约,以消费娱乐为主要节日活动,实践着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中西融合的、极尽世俗享受的“冬至”文化。
四、时代变迁下的文化症候
中国几千年来传统农业社会性质决定了小农经济下的日常生活与天文、物候循环往复的变化直接相关,并以此为依托形成了具有农业社会色彩的传统的岁时、节气以及一系列的相关的民俗文化。中国自古便十分注重节日对于世俗生活的重要意义。在传统冬至中,我们能够看到江南民众在特定时段脱离平日的生产生活,投身到节日的狂欢当中来,进行节日消费的场景。尽管这直接促成了上海民众对于外来享乐文化的容受路径,但在清末民初的现代化过程中,“冬至”这一词汇虽然不断地出现在近代上海地区的消费场景之中,但在许多情形中已脱离了与传统冬至的关系,更大程度上可视作由商业利益的驱使而包装成的一个异象。
结合“外国冬至”的传入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文化适应和文化碰撞的过程被人为加速,节庆消费也产生了量的激增和质的变化。市民阶层由此通过确立新型生活方式,消费新鲜生活用品,包括年末冬至的礼品等,来定义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商品塑造自我的社会角色。尽管有一定的提高市民生活水平的积极作用,但节日消费本身逐渐从“物质的消费”转向“象征符号的消费”,也就意味着“冬至”在被拜物化的同时也被抽象化为一种符号,在不同的消费名目下被附加了各异的价值和意义,因而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的文化症候而存在,能够作为一个切片展示出现代性在上海的生长和异变。
人们寄托于“冬至汛”的消费诉求,已从追求商品的使用功能转变为追求商品的附加价值。通过广告宣传和新闻报道的种种宣传手段,节庆商品被赋予超过“冬至”本身的更多的符号意义,如“摩登”“高级”“名贵”等。可见消费者在打着节日旗号的消费活动中,消费行为通常并不是为了满足节庆需求本身,而是与商品所蕴含的符号属性联系起来,进而寻求某种对于身份的认同。消费者通过消费活动接收这些商品中所包含的象征质素,除了满足自身对于新鲜事物的追羡与对新式生活的效仿外,亦能够通过消费行为本身进行自我价值的肯定和社会认同的获得。
因此,作为符号的“冬至”,从本质上说,与当下由电商打造的消费节“618”或“双11”并无二致,是一种传统节日消费心理和新型媒介功能的融合驱动下产生的文化消费方式。但在特定历史时期背景下,其后隐喻着更为复杂的外资洋商对华商业竞争与市场渗透。当近代商埠大开,进口商品大量涌入国内,国内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传统的消费观念已经无法消化过量商品的时候,于是便需要人为建构一些能够引导并刺激人们进行消费的符号。其中,“冬至”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巧妙地模糊了人与物之间的单纯的“生产-消费”关系,将其转化为节日背景下的人际交往关系,利用上海民众较强的冬至消费意愿为其设下了不易察觉的陷阱,促进了冬至消费的扩张和新式娱乐的普及。
作为消费符号的“冬至”,其认知构建过程是由报刊媒体主导,新兴市民阶层参与而共同完成的。其隐患也正在于商业资本筑起的消费之墙致使文化价值的消弭和弱化已经超越了媒体宣传应有的边界与限度。它通过新兴媒体渲染和夸大消费导向,将这场盛大的消费庆典塑造为近代上海民众的对于“冬至”的文化记忆。憧憬和享受着西方生活方式的人们,在被眼花缭乱的物质形式迷惑之际,有时也难以坚守传统的文化身份,随波逐浪地盲从热闹、投身于过度的消费生活之中,甚至以此成为西方经济侵略不自觉的支持者。而当我们剥开层层纷繁迷人的物质外壳,想要探寻内里的节日文化和精神内涵时,却也发现“冬至”原本所指意义里的传统节日意义和价值已暂时被人淡忘。
节日文化固然需要商业资本的加持而历久弥新、发扬光大,经济活动也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点缀为其增光添彩,但终究需要把握文化融合的底线、提振文化传承的自觉。事实证明,对节日文化过度挪用只能带来短期的经济利益,却使得传统冬至的内涵沦为娱乐消费的附庸。这样一种过度消费的浪潮终究是不合时宜的,并且招致了上海以外全国各界的批评之声。这些批评纷纷剑指上海在战争时期所呈现的奇异社会景象:在战火纷飞、时局动荡的情况下,处于相对安定状态中的上海“孤岛”在经历了短暂的萧条阶段后,便又重新恢复了往昔繁荣的消费景象。大部分上海市民为逃避战乱之苦,纷纷流入租界,使“孤岛”人口急剧膨胀到300 万人左右,愈发刺激和扩张了上海本地的商业消费,形成了租界内歌舞升平、欣欣向荣的假象①刘红主编:《上海商业百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81—82 页。。从当时的报纸上刊登的年末广告的种类与覆盖度便可以看出,尽管外界在饱受乱世之苦,但是上海的商业文化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市民的消费活动依然处于过度享乐主义和颓废主义的洪流之中。但除了这些有钱有闲能够参与到年末狂欢中来的人群之外,还有大量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穷人与难民,这些居于社会底层又无经济条件的人群愈发无法参与其中,成为这场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冬至狂欢沉默的缺位者。
结 语
要之,通过梳理文献材料中江南地区冬至节俗的源流发展,可见江南民间素重冬至,至今仍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在冬至前后,民众不仅进行多种热闹非凡的庆祝活动,同时也保留着冬至节日消费的一贯传统。从而,当清末民初圣诞节作为“外国冬至”在上海地区流行开来时,民众欣然接纳了其中部分能与本土传统冬至的团聚、宴饮等产生共鸣的要素。一方面,随着历法改革的实行,传统冬至失落,出现了年末节日文化的混乱和空白;另一方面,民众对于西方现代生活方式和“外国冬至”持有向往和欢迎的态度,由此在商业消费的推动下便出现了一种作为抽象消费符号的“冬至”,各种新鲜的物质和精神消费藉由“冬至”之名大行其道,传统冬至与圣诞节、元旦一同整合成大型年末狂欢,成为一例时代变迁下的文化症候,使得原本传统冬至的民俗价值日益消弭,取而代之的则是报刊媒体助推下新型购物节庆的经济性意义。
从晚清民国上海地区的冬至节日生活与消费转型中,我们不难看出,传统节日的生命史往往经受着政府与民间、本土与外来多种力量的复合形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于节日的传承与变异。政治运动中的改历风潮造成了传统冬至的传承断裂,而西方现代消费的引入则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并丰富了当时的节庆娱乐。然而一时的热闹与繁荣无法掩盖节日内涵的空洞与丧失,“冬至”的消费符号化明白无误地昭示着现代文化对传统的持续冲击与蚕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冬至”得以作为观察传统节日传承与变异机制的一个案例,成为我们思考当下传统节日所面临的诸种问题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