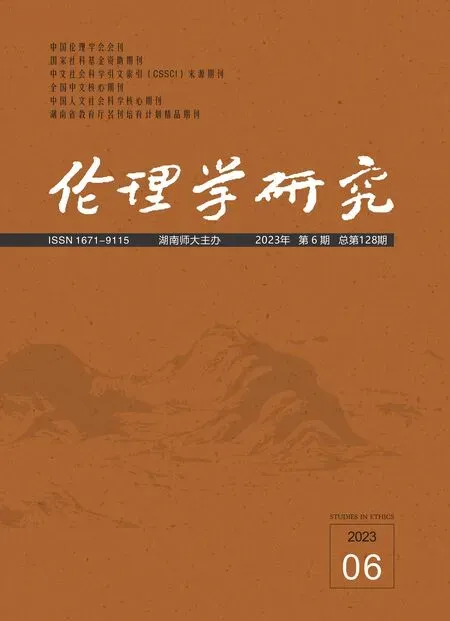论杜威的美德伦理学进路
肖根牛
当代美德伦理学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对传统规则伦理学的系统批判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它为说明正确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辩护方式,把对行为的评价转向了对行动者的评价。但当代美德伦理学面临的问题也是棘手的,因为它把道德评价的中心转移至行为者之后,面临着如何从“出于正确动机的行为”到“正确行为”转变的问题,如何衡量不同情境之中的行为的问题,以及不同行为者出于美德如何形成同一情境之中的行动方案等,这些问题都是当代美德伦理学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从其他思想传统中寻找资源。无独有偶,古典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早在当代美德伦理学复兴之前就已展开对传统规则伦理学的系统批判,他不赞同传统规则伦理学把行为的道德属性立足于普遍主义规则之上的做法,而是主张把行为的道德基础置于行为者的品格之上,只有稳定的道德品格才能在不同道德情境中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杜威在未接触当代美德伦理学的情况下,发展出了一条实用主义进路的美德伦理学。杜威基于实用主义立场,从一种发生学视角把实际情境中行为发生的真实过程揭示了出来。通过对美德在道德行为中作用的论述,我们会发现杜威对美德伦理的思考不仅不同于当代美德伦理学,而且可以为当代美德伦理学面临的困境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美德作为一种习惯
当代美德伦理学兴起的重要背景就是人们对以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规则伦理学的不满,认为规则伦理学并不能促使道德行为的真正发生。规则伦理学所追求的是一种普遍主义理想,它把所有行动者都预设为理性存在者,每个行动者只要诉诸理性就能接受道德的要求并且遵守它,在当代美德伦理学看来这是有违实际情况的。当代美德伦理学批评规则伦理学所追求的普遍主义实际上把人抽象化了,认为规则伦理学关注的是一个排除品质特性、文化背景、传统习惯等因素的“一个人”(one),而不是生存于具体情境之中、有各种偏好和个人品行的“这个人”(this one)。正如威廉姆斯所说,“如果说康德主义者在道德思想中是从个人的同一性中进行抽象,那么功利主义者就是显著地从个人的分离性中进行抽象”[1](157)。所以当代美德伦理学主张把道德行为评价中心扭转过来,从以行为为评价中心转为以行为者为评价中心,相信有美德者必然会作出美德行为,但这一主张也必然会招来质疑,因为“有好心”不一定会“做成好事”。
虽然当代美德伦理学在解释如何依靠美德动机来辩护正确行为的问题上有多种方案,但依然面临诸多的批评。斯洛特认为决定正确行为的因素不是具体动机而是总体动机,如果总体动机是正确的,即使具体动机有些瑕疵,也不影响行为的正确性,如果总体动机有问题,即使具体动机是正确的,也不能辩护行为的正确性[2](34)。斯洛特实际上把正确的行为与具有正确动机的行为混为一谈了,依然没有解决如何由正确的主观动机产生正确的客观行为。赫斯特豪斯看到了仅仅把美德当作主观的动机不足以说明行为正确,她把美德理解为规则,她说每一种美德本身就包含着一条规则,如要诚实、要正直等,每一种恶习也产生一条戒律,如不要不诚实、不要不正直[3](9)。赫斯特豪斯把美德视为规则的主张也存在问题,这种观点一方面并未说明美德如何成为行为的有效指导,另一方面又面临被指控为规则伦理学的嫌疑。总之,当代美德伦理学在批评传统规则伦理学方面是有建树的,但在回答如何从美德动机来说明正确行为的问题上并未获得足够多的认同。
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对传统规则伦理学也持批判的立场,不过他是把对传统哲学批判的立场延伸至伦理学领域。杜威认为伦理学领域所出现的问题是理智主义路线在伦理领域的展现,基于理智主义基础之上的规则伦理学,其结果表现为形式伦理学,康德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便是典型代表。在杜威看来,规则伦理学的问题在于未能真正地从具体发生的行为出发,而是立足于抽象的、普遍的道德原则,这会导致难以解决的问题,即抽象的道德原则如何运用于具体的道德情境之中,或者如何让道德原则变成行动者的道德动机。杜威在批评康德义务论时就指出,康德的义务是一种抽象的“应该”,这种“应该”不是来自行动者自身的需求,而是来自排除一切感性因素的理性法则,这导致义务要么成为一种空洞的义务,要么成为单纯的顺从。杜威说:“试图遵守一种把满足和义务分离开来的理论并将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落实,意味着通过怀疑欲望的道德意义而使其残缺不全,进而通过取消行动的动力而把生活化约为单纯的顺从。”[4](285)康德强调行为道德属性的来源不是任何经验的东西,而只能是出于对实践理性所发布的命令的无条件服从,是为义务而义务。杜威认为康德的做法是把义务原则和现实情况分离开来,最后的结果就是无法产生具体的义务内容。杜威对功利主义所主张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也持批判立场,因为“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道德问题就是对总体幸福和他人的幸福的关心而非对自己的关心,如何可能在自己的行为中成为一个支配性的意图”[5](309)。在杜威看来,每个人的自然倾向是偏向自己的利益,而功利主义强调的最大多数原则很多时候是与自己的自然倾向相冲突的,即使最后的结果是促进了多数人的幸福,也无法说明个人的动机就是为了促进这种多数人的幸福。功利主义的这种幸福原则具有社会性,而行为动机具有私人性,两者存在直接的冲突。
杜威批判规则伦理学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们未能真正地从实际发生的具体行为出发。行为的发生从来就不是受单一因素影响,个人的情感、欲望、意志、观念、习俗、传统、心理状况等因素都会对行为的决策产生影响,每个行为都是在具体情境中发生的,不存在脱离实践环境的行为,每个行为都是丰富的、完整的过程,不存在哪一个单一因素决定行为的道德属性,行为动机和行为结果都是一个完整行为不可或缺的部分,传统规则伦理学的问题在于,“它们把一个统一的行为分裂成为两个毫无相关的部分:内在的部分被称为动机,而外在的部分被称为行为”[6](29)。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的做法是把一个统一的行为中的某些要素抽离了出来,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误解或扭曲了真实发生的行为,所谈论的行为的道德属性也就跟现实的行为无关了。在杜威看来,所有的行为都是发生在具体情境之中的,这些情境又出现在行动者与世界的交互过程之中,所以行为产生于个人与环境的交互过程之中,行为的目的也是交互活动。换言之,个人与环境的交互活动不断出现需要解决的障碍,行为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障碍。行为在促进交互活动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不同的资源,包括道德原则、目的、知识、观念等,但这些资源只是促成行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道德原则来决定行为的方向,解决情境中的问题并且恢复行动者与环境的顺利互动才是行为的方向。不同情境中问题不一样,导致行动者所施展的行为不一样,但是行动者在处理同一类型问题的时候会形成稳定的处理方式,这便是习惯。习惯是行动者处理问题情境的稳定方式,个人与环境中所产生的需求也主要是通过习惯性活动来满足,所以“习惯性活动主导着生活的全过程,从简单的到复杂的,包括人类的行为。基于这些理由,习惯是杜威行动概念和道德哲学的基础因素”[7](30)。处理每一种类型的问题都会形成习惯,而习惯之间又会相互渗透影响,由此整合成为稳定的、更强的习惯,这就是行动者的品格。品格让行动者在面对道德实践情境时表现得更为理智、稳定和有力,使行动者能够作出合理的选择。所以,在杜威看来,行动者在作出道德选择的时候不是根据已有的道德原则,而是根据行为者自身的品格,确定行为道德属性根源的也是行为者的品格。
杜威把品格理解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倾向或习惯,但品格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习惯存在于个体与环境的交互过程中,经验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习惯的变化,所以品格也在不断更新之中,美德概念由此引申出来。在杜威看来,“某些习惯能够被视为美德,意味着那些拥有的倾向能够在变化着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有效地满足需求,并且能够提升在未来增长和扩展经验的能力”[7](34)。在此,杜威把美德当作一种习惯。杜威从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来看待美德问题,他并不像当代美德伦理学家们那样把美德视为一种固定的心理状况,比如麦金太尔把美德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心理倾向和个人自然情感的表达[8](290),赫斯特豪斯强调美德作为人的一种善的存在方式,能够让行动者内在地变善,进而让他作出正确的行动[9](15)。当代美德伦理学实质上是从一种“内在—外在”二分的角度来理解美德,仅仅把美德视为内在的固定品质,而不去思考美德所包含的生活内容和情境维度,这必然无法解释美德如何产生美德行为的问题[11](187)。杜威把美德放置在经验发生的过程之中,不存在对行为全过程进行“内在—外在”式的人为割裂,他认为只有那些能够处理好情境中的问题并能增长经验的习惯才能被称为美德,相反的则被称为恶德。美德并不是固定的心理品质,而是随着交互活动的变化和实践经验的增长而发生变化;如果处理问题情境的习惯越来越有效,对未来的成长越来越有帮助,则美德的水平就越来越高;美德处于一种弹性的状态,不能根据之前的美德状况来决定当下行为的价值和善的水平,而必须从整个美德的发生过程来看待。
二、自我和行为的统一
杜威从发生学的视角揭示了行动的复杂性和全程性,任何行动都是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之中,不存在固定的一致的行动,而且行动的发生受各种因素影响,不可能只根据理性所理解的道德原则来行动,对行动影响最大的力量是行动者形成的心理倾向,即品格。换言之,真正影响行动动力和方向的就是行动者自己,自我具有什么样的品格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决策和行为表现,在这一意义上,杜威的伦理学无疑属于美德伦理学范畴。不过,虽然当代美德伦理学和杜威一样都把道德评价的中心从行动转向了行动者,认为行动者的美德是行动道德属性的来源,但二者关于行动者或自我的理解差异极大。当代美德伦理学实际上是基于一种道德心理学视角来理解自我的特质。斯洛特就把美德界定为不假外求的独立的内在力量,认为只要掌握行动者的德性状况而不需要借助对外在实践环境或条件的了解,就能判断一个行动者作出的行为是不是道德的。如果一个具有诚实美德之人在任何时候都做诚实之事,那么会面临“好心办坏事”的问题,即在不该诚实相待的情境中是否依然诚实以对,比如纳粹统治时期一个从不撒谎的德国人家里躲藏着一个犹太人,当纳粹士兵来搜查时要不要诚实交代。很多人质疑斯洛特的观点缺乏事实根据,不能有效地说明现实中的道德实情。斯洛特也意识到只依赖美德状况来决定行为属性是不充分的,他承认美德作为动机之外还需要探究把握外在事实经验,通过外在认知行动来弥补认知上的缺陷,从而不改变行为在道德上的正确性[2](34)。很明显,斯洛特单纯依赖作为心理内在力量的美德无法解释行为的正确性,它还是离开不外在行动的参与。这也揭示了当代美德伦理学试图把行动与行动者完全切分开来的做法难以一以贯之。
杜威虽然重视行动者美德状况在决定行为道德属性问题上的关键作用,但是他并没有把美德视为一个封闭的、固定的、静止的东西。在他看来,行动者并不是一个事先完全成型固定的主体,而是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的。行动者和行动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两者互相依赖和相互塑造,在这一点上他和当代美德伦理学是完全不同的。杜威说:“自我和行动的统一构成了在性质上突出于属于道德的一切判断的基础。”[5](368)杜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自我和行动是互相构成的,自我从来就不只是单方面对行动施加影响的一方,自我同时接受着行动后果对自我的影响,当然这些影响并不是自我被动接受的,而是自我在行动之前就会对将要产生的影响实施某种向导或控制,品格就是自我控制行动后果的作用方式。一个信守承诺的人希望自己所作之事都是诚信行为,他必然会依据自己诚信的品格来行动,诚信品格是他能够达成目标的保障,所以“个性或品格不是实现某些目的的纯粹手段或外在工具。它是一种达成后果的力量”[5](367)。同时,这些行动的后果反过来也会影响自我的品格。杜威说过,行动者的品格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处理问题情境而形成的习惯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杜威还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一个正常的孩子因为饥饿而抢夺他人食物,在他自己看来也许并不具道德意义,但是如果不注意行为后果与自己品格之间的关系,这种倾向就会很容易被加强而把自我往这个方向塑造,所以行动的后果对自我具有塑造作用。一个诚信的人并不仅仅在于他自身具有的诚信心理特征,而是他不断地去做诚信之事才使他成为一个诚信之人,正如杜威所说:“事实上,只有热烈地欲求和追求善的后果(也就是说,那些促进受这一行动影响的那些人的福利的后果)的那个自我才是善的。”[5](368)
杜威把自我和行动绑在一起,自我是行动的动力,行动是自我的表达[10](847)。既然行动是变化的,那说明自我也不是固定的,自我一直在被塑造。正如杜威所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一个固定的,已成的和已经完成的自我。每一个活着的自我都是行动的原因并且进而自身又被自己所做的事情影响。所有的自愿行动都是自我的一次再造,因为它形成了新的欲望,激起新的努力模式,发现规定着新目的的新条件。”[5](391)从此处杜威的论述可以得到再进一步的推论,即自我完全处于行动之中,行动规定和塑造了自我的内容,选择什么样的行动最后就会造就什么样的自己。杜威反对自我的先天本质论,在他看来,自我完全是由后天的行动决定的,处于一个塑造的过程之中,自我的品格也就处于变化之中。但是,既然行动是自愿的,在不同情境之中可以有不同的行动选择,甚至选择跟自己品格相反的行动,那品格作为一个稳定的习惯倾向是如何可能的呢?杜威认为品格或美德的重要特征是整全,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之中可以采取某种与自己品格要求相反的行为,但并不一定立马就会对品格形成损毁。例如上述关于儿童抢夺食物的例子,如果此儿童认识到自己因为饥饿而不得不抢夺食物,同时也认识到这一抢夺行为与自己的品格之间的紧密关系,并由此决定下不为例而不让这一行为成为自己的倾向或行为模式,它就不会对品格造成直接的伤害。当然从第三人称视角来评论此事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杜威认为某些情况下允许相反的行为选择并不影响品格的整全性,比如对不该讲实话的人撒谎,对不该仁慈的对象不仁慈等。
美德之所以能够维持它的整全性,关键的原因在于它和目的论式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即:我是谁?我相信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之所以称其为目的论式的观念,是因为其构成了自我发展的方向。但是这一方向并不是固定的、明确的,而是流动的、弹性的,每个行动者并不确切知道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但是却能发现“在每一点上,都存在着一个存在于旧的、已经完成的自我和新的、正在运动中的自我之间的区别,也就是存在于静止的自我与变动的自我之间的区别”[5](391)。正是这样一种运动着的自我在不断影响品格,同时“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道德形象(moral image)又引导着自我的运动,“美德就存在于变化的品格之中”。在此,“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道德形象虽然不能给出具体的规定性内容,但是它为自我的变化提示了方向,由此也就影响了品格的发展方向。虽然已经完成的自我为品格的形成提供了平台,但是品格的意义在于它能为未发生的道德情境提供决策根据,换言之,它能够回应道德情境中的道德需求,而这些都不是已完成的自我所能提供的,而是由“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道德形象所规定。所以,在杜威看来,美德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但同时也不是偶然任意的,而是在一种自我的运动中保持统一,即整全性,这种整全性把自我和行动紧密地统一在一起。
三、对正确行为的说明
当代美德伦理学在批判传统规则伦理学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但是在如何让自身成为一种能指导行为的规范性道德理论方面却并没有那么顺利,依然面临着各种质疑和诘难。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为正确行为提供辩护。当一种道德理论无法说明行为在何种情况下是正确的、何种情况下是错误的话,那就无法为行为提供向导。传统的规则伦理学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在对何种行为是正确的回答上却是清晰的。比如义务论会把正确行为奠基于理性的道德原则之上,而功利主义则把正确行为奠定在“最大化”的后果之上。当代美德伦理学正是要反对传统规则伦理学把正确行为奠基于单一的规则之上,而试图通过行动者的品格状况来说明正确行为,认为动机源自美德的行为才是正确行为。但是,当代美德伦理学家如斯洛特[12](110)、赫斯特豪斯[9](28)把正确行为奠定在作为动机的美德之上,这一做法面临不可避免的困难。首先,如何判断行为的动机是出自美德?美德伦理学家只能把作出正确行为的人认定为具有美德,这将面临循环论证的问题,即依靠美德来说明正确行为,又依靠正确行为来证明美德;其次,是否出于美德的行为就是正确行为?这明显又面临“好心办坏事”的诘难。另一位当代美德伦理学家斯顿旺看到了“出于美德动机”来论证正确行为的困难,他把辩护基础转为“击中美德目标”[13](19),认为只要行为最后击中了美德目的,行为结果是关于美德的就可以证明该行为是正确行为。很明显,他把正确行为的论证从动机论转为了后果论,但是又面临后果主义式的质疑。杜威的美德伦理学跳出了当代美德伦理学的论证路径,他从一种实用主义角度来论证美德何以决定行为是正确的。
杜威认为所有的行动都是和自我联结在一起的,两者是互相塑造的,自我是行动的发动者,行动塑造着自我及其品格,甚至可以说自我就处于行动之中。如果要追问行动的动机是怎么产生的,它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1)与自我相联结的行动动机来自哪里?(2)某一具体行动发生的动机来自哪里?前一个问题中的动力来自自我的品格,而不是来自外在的东西;后一个问题所指的动机实际上是对一种外在刺激的回应而不得不产生的行为改变。真正的道德行为指符合前一种情况,自我和行动统一,自我虽然通过品格的作用而促发行动,但是这一品格并不是与行动对象无关的。在杜威看来,行动中的自我并不仅仅与行动相联结,同时也与行动的对象和目的相联结,杜威把这样的情形称为兴趣,“兴趣就是对一个对象的关心、思考和帮助;如果它不被表现在行动之中,它就不是真实的”[5](371)。兴趣是品格发生作用的状态,或者是品格的客观化表达,它不再单指行动者内在的心理品质,而是和外部的行动、行动目的与对象相关联,所以它包含了行动的整个过程,从主观动机的品格到客观行动的对象。很明显,杜威的美德论比当代美德伦理学更具综合性,而不是单指行动过程的某个环节或某个元素。根据杜威的观点,医生具有仁爱的品格,这种品格只会存在于医生的医治行为中,而不是医生身上的某个特质。医生的仁爱品格表现于医生不断地投身于救死扶伤的行为之中,同时和医生所追求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即通过自己的医治行为让病人恢复健康,所以医生的仁爱品格会使治愈病人成为他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在指挥着医生的整个医治过程。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何兴趣会成为行动者展开美德行为的表现。“因为兴趣或动力是自我的某种需求和欲望在行动中与某种被选择的对象在行动中的统一,而这对象本身在第二种和派生的意义上可以被说成行动的动力。”[5](372)在此,杜威的意思很明确,兴趣之所以会成为美德行为的表现,是因为在兴趣之中我们的某种需求和行动对象得到了统一。那是何种需求呢?此种需求就是保持自我在不同实践情境之中的整全性。这种整全性也是美德的基本特征。自我的行动面临着不断变化的行动环境,而不同环境中的行动又塑造着自我的品格,但是自我并不是毫无统一性地进行选择和行动,而是让不同环境中的行动朝着某个方向,即“我是谁,我相信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道德形象,这一道德形象也不是固定的,更不是抽象的,而是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之中的,自我的整全性就是行动与道德形象的统一。不过这种整全性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而是一个变动发展的过程,它表现在变化着的环境之中。整全性朝着程度更高的方向发展就是成长。“成长作为一个道德词汇,表示不断增强个体的功能而成为一个圆满的人。”[10](849)“功能”一词是杜威用来表达个人的能力、性情和天赋在与之相关的环境中实现出来的过程和结果,它包含内在方面的品格和外在方面的道德环境,两者协调一致促成功能的实现。比如一个医生的功能不仅具有仁爱的品格,同时也能在救死扶伤的工作中满足各种要求和承担各种责任,达到让患者痊愈的目的。正如杜威说:“一个履行其功能的公民不仅是在内心培养爱国主义情操,而且也必须满足他所生活于其中的城市和国家的需求……一个学生、一个公民、一个艺术家的功能不是在单纯遵守某种外在需求中得以履行。没有内在的性情或自然倾向,我们就称行为举止是僵死的、草率的、虚伪的。”[4](255)在个人履行其自己的功能的问题上,内在的品格和外在的行为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一个人越好地履行自己的功能就越表示自己在不断成长。
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杜威强调道德环境或行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行动者的品格需要不断地去适应这些变化着的环境,让道德形象能够适应更多的新情况,在这种意义上才能判断行为的正确与否。当代杜威伦理学的研究者约翰·蒂恩(John Teehan)举过一个例子来展示杜威的美德理论是如何解释正确行为的。设想一个公司职员某一天出门去上班并准备参加一个为自己举办的升职会议,领导准备提拔他当部门经理,当他走到半路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领带褶皱不堪,让人看了非常不舒服,他这个时候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回去用熨斗把领带熨平?如果选择回去熨平领带那肯定会迟到很久,一想起让会场的领导同事等这么久会让他倍感自责;如果选择不回去熨平领带而是直接去参会,邋遢的形象会让自己非常难堪。这名职员面临选择何种行为才是正确的难题。根据杜威的伦理学立场,这个问题的解决既不是根据某个先天的原则,也不是计算何种选择获益更大,而是先回答“我希望自己成为何种人?我希望拥有何种世界?”这种自我期许的道德形象。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重要?因为自我生活在与他人交互的共同体之中,任何人都不能脱离他人而存在,进行道德思考的重要动机就是考虑行为结果对他人的影响,所以任何个人主义或自我主义式的道德选择都是行不通的。正因为如此,个人与他人交往的前提是确认自己应当成为何种人,或者期许他人如何来评价自己,他人对自己评价的基础是自己的行为,包括行为选择和行为结果,因而只要准确定位自己的道德形象,行动者即使在不断变化着的道德环境中也依然可以做到让行动与道德形象统一起来。回到上述例子,此职员若是回去整理自己的着装,虽然会让自己的形象看起来更为得体,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但是会浪费他人很多时间,实质是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人利益之上,而这并不是职员对自己一直以来期许的道德形象,所以该职员选择准时参会才是正确选择,它让自己的道德形象与这种特殊环境中的道德行为统一起来,而不是走向对立。
结语
相较于当代美德伦理学,杜威的美德伦理学特色是实用主义进路。这一路线的特点就是从发生学的视角把道德实践还原为具体情境之中的行动。决定行动的因素是多样的,而不是某种事先准备好的单一道德原则,真正具有稳定因素的是行动者的品格,正是在这一点上,杜威伦理学才被归类至美德伦理学的范围。不过,杜威并没有像其他美德伦理学那样面临相对主义的困境,因为杜威的美德论并不是要建立一种为行动提供指导的普遍道德理论,他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情境、消除自我和环境的互动障碍,情境论和后果论才是杜威美德伦理学的底色。同时,杜威的美德伦理学致力于对经验和情境保持开放的态度,这不仅仅是为了能够应对来自外在环境的挑战,同时也是为了自我的成长。自我存在于行动之中,如何实现自我和行动的统一是美德的重要使命。杜威和当代美德伦理学家一样,认为行动者基于美德的力量来施展道德行为,并且追求美德的行为都有其目的。不过,他们虽然都把幸福作为美德行为的目的,但是对幸福内涵的理解却是不一样的。当代美德伦理学把幸福理解为一种生命品质得到充分实现的状态,而杜威则把它理解为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只有不断适应新的经验和环境才是较好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