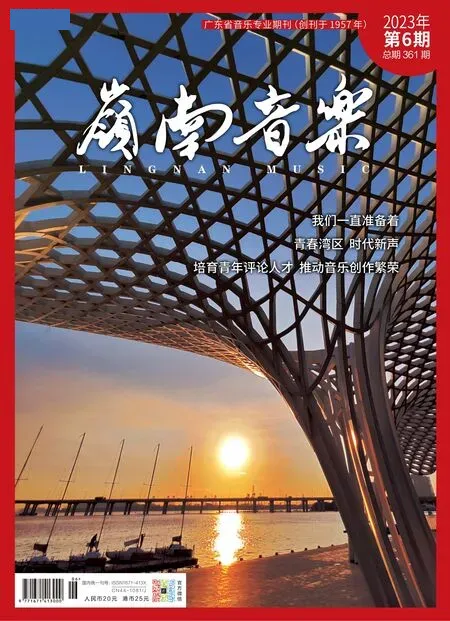从《钢琴大师论钢琴演奏》看黄金时代的钢琴演奏美学观念
文|林浩 韶关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人们通常把19 世纪末20世纪初视为西方钢琴演奏的黄金时代,当时正处于浪漫主义音乐美学思潮式微和现代主义音乐美学思潮兴起的阶段,一大批极富艺术个性的钢琴家活跃于音乐会舞台。可以说,这些钢琴家的精彩演奏为钢琴艺术发展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演奏所折射出的美学观念的影响更是一直延续至今。因此,探究这些黄金时代钢琴大师的美学观念,对今日的钢琴学习者将是颇有助益的。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大多数职业钢琴家要奔波于忙碌的巡回演出,因而他们当中极少有人留下文字著作来论述其音乐观念,致使钢琴家在作古后令后世者唏嘘不已。
《钢琴大师论钢琴演奏》是一本以访谈形式记载多位钢琴家关于其钢琴演奏理念的书籍,1917年初版,作者是美国人詹姆斯·库克,2011年此书中译本由刘弋珩翻译、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一名钢琴教育者,作者库克在本书的代前言中有以下说明:“作者20年的教琴经验使得他能够掌握、领会一些钢琴家词句中难于表达的细腻寓意。虽然他们在言词表达方面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但却庆幸地看到他们的意思被作者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了。这些采访的首要宗旨是坦白和真诚……这本书囊括了关于钢琴演奏的方方面面,内容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学生、教师及音乐爱好者都可以通过这本书接触到不同键盘大师的见解,从而达到对技术、诠释风格及表现力方面的一个总览。”①虽然语言之间不无自夸,然而此书所载内容,确实无愧其超凡价值。作者所采访的28位钢琴大师,都是当时音乐会舞台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其中一些钢琴家,得益于扎实的艺术功力以及录音技术的帮助,时至今日仍为大家所熟知,如霍夫曼、列文、戈多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巴克豪斯等。作者库克通常就某一个中心议题与采访对象展开论述。于是,28个各不相同而又相互联系的议题就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28个议题可谓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钢琴演奏的各个方面。对于学琴者而言,很难说出哪些议题更重要,读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对各议题给予相应的关注。而笔者所感兴趣的是,从28位钢琴大师的论述中总结出黄金时代钢琴演奏的美学观念,做这种尝试自然是不容易的,因为所有受访者的论述均为经验之谈,而每个钢琴家的学琴经历又各不相同,因此有时两位不同的钢琴家对同一问题持截然不同的看法。经过一番梳理后,笔者总结出以下黄金时代钢琴演奏的四个普遍美学理念。
1.技术为音乐服务
自钢琴诞生之日起,关于技术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钢琴发展的早期,技巧大师总是能得到大众的青睐。著名的美国乐评人哈罗德·C.勋伯格曾这样论述塔尔贝格等早期炫技大师:“塔尔贝格、德赖萧克、戈特沙尔克、赫尔茨等技巧大师都是演艺人,是大炮,是沙龙音乐家,是早场音乐会的偶像,丁零当啷各有其道。”②李斯特和安东·鲁宾斯坦更是把炫技看作音乐会成功的秘诀。可以想见,长期以来,大众对技巧大师顶礼膜拜,促使了钢琴家们把技术看得非常重要。成功扭转“技术至上”的关键人物则是门德尔松、克拉拉·舒曼等一批献身艺术的音乐家。他们抨击李斯特杂耍式的演奏方式,使钢琴音乐会演变为今日我们所见的高贵严肃的模式。在《钢琴大师论钢琴演奏》中,以技术见称的拉赫玛尼诺夫、列文和巴克豪斯等人强调了技术在音乐中的重要性。拉赫玛尼诺夫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技术,不管怎么说,被视为最重要的事情。所有的学生必须在技术上达到胜任的程度,无人能逃。”③作为拉赫玛尼诺夫同学的列文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这样论述俄国的钢琴教育:“俄国钢琴家一直以技巧著称,甚至连很平庸的艺术家也具备胜任的技巧。伟大的艺术家意识到钢琴弹奏的机械的一面只是基本,但是他们必须承认没有技术的基础,就无法建造美丽雄壮的艺术殿堂。俄国钢琴家以技术控制著称是因为他们确实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每一件事都以最扎实和最坚固的方式做到。”④而巴克豪斯则表示:“我本人技术装备的根基就是音阶、音阶、音阶。日日不间断地练习音阶不仅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需的。至今,我还是保持每天尽量练习音阶半小时以上的习惯。”⑤由此可见,许多钢琴大师都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在诠释音乐中的重要性。然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随着人们对钢琴演奏技巧研究的逐渐深入,早期手指学派把技术与音乐割裂的观念越来越受到质疑,之前的“技术至上”逐渐被“艺术至上”所取代。在28位受访者当中,哈罗德·鲍尔(Harold Bauer)的论述尤其值得关注。作为从学小提琴转到学钢琴的钢琴家,鲍尔缺乏许多钢琴家同行从小练就的扎实技术,这样的出身让他对技术有了独特的看法。鲍尔的技术观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技术就是艺术,因而也必须如法炮制地学习,音乐中的技术同音乐本身并无二致。”⑥在鲍尔的观念中,钢琴演奏的终极目标便是音乐本身,因此不能对音乐表现有所助益的技术练习都是不值得提倡的。事实上,“技术为艺术服务”“音乐至上”的观念并非鲍尔独创,而是公众在经历了炫技钢琴家们的洗礼后对技术的重新认识,以及对音乐美回归的重新呼唤的体现。即便是前述提及强调音阶练习的巴克豪斯也谈到了他对炫技表演的看法:“那些仅仅依靠炫技就可以成名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可能与发明出的机械装置有关,公众不再推崇任何可以用机器替代的事物,而是向往一种可以显示艺术家灵魂的精巧微妙的东西……事实上,公众对于纯音乐和纯艺术的呼声从未间断。”⑦由此可见,当19世纪强调音乐效果而高度关注演奏技术的美学思潮达到顶峰后,行家和公众都认识到表现音乐才是钢琴演奏的本质所在。而把技术并入艺术的范畴乃至把二者视作同一事物在今日也不乏其人。笔者认为,大师们对技术议题的经验之谈给予了后人一个重要的启示:在钢琴演奏中符合自身需要的技术训练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技术训练。联系当下,琴童在教师的引导下孜孜不倦地弹奏车尔尼的练习曲以获取技术,自然也是有效的方法之一。然而学生切不可忘记在训练技术的同时对耳朵的训练。大师们通过自身实践告诉大家在技术训练上应该有所侧重,把专注力放在音乐上,这是浪漫主义时期强调个性、强调内容的应有之义。
2.用音乐思维激活乐谱
在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音乐家们对待乐谱往往采取随心所欲的态度。尤其是到了李斯特主宰音乐会舞台的时代,随意改编、拼接作曲家的作品成了演奏家习以为常的事情。勋伯格这样描述浪漫主义鼎盛时期钢琴家们的做法:“李斯特毫不在乎地用贝多芬《降A大调钢琴奏鸣曲》(Op.26)的主题和变奏作为第一乐章,用‘月光’的末乐章来结束,拼凑成一首钢琴奏鸣曲。彪罗演奏韦伯的《音乐会曲》时‘加上了一些效果’;在音乐会上,他常常把李斯特的《第十二号匈牙利狂想曲》同《第二号匈牙利狂想曲》的后半部分合在一起弹奏……李斯特从来不肯照搬别人的音乐,也从来不在乎别人改动他的音乐”⑧。由此可见,在浪漫主义美学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乐谱并不被演奏者重视。《钢琴大师论钢琴演奏》一书中采访的钢琴家几乎都生于19世后半叶,所接受的都是浪漫主义的演奏理念。然而,武断地认为他们对待乐谱的态度就如同李斯特等前辈一样将大错特错。诚然,如果用今天人们通常所奉行的“乐谱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来做比较,那么书中钢琴家们的态度无疑要自由得多。事实上,他们对待乐谱的态度可以看作是李斯特等前辈作曲家观念和20世纪后的现代钢琴学派观念的折中。如前所述,音乐表现是钢琴演奏的一切出发点,那么对待乐谱自然也立足于音乐表现。而在许多有见识的演奏家看来,乐谱并非音乐音响忠实反映或终极文本,它仅仅是音乐作品的一份蓝图,而重要的是演奏者对乐谱字面意义的挖掘。这一过程被许多人认为是演奏者与作曲家沟通的过程,这种沟通是否顺利,直接决定着对作品诠释的成败。拉赫玛尼诺夫在采访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要对一首作品建立正确的概念:“在学习一首新的作品时,首先需要获取对作品总体的概念,作曲家的主要规划必须被深入了解……每一首作品的背后都蕴藏着作曲家对此作品的建筑蓝图,学生应该首先力争发现这个蓝图,然后完全依照作曲家的设计来建造这座音乐建筑物。”⑨显然,拉赫玛尼诺夫认可乐谱是演奏中的依据,但是他更为强调的则是从乐谱背后折射出来的作曲家意图。无独有偶,斯托霍夫斯基在谈论诠释这一议题时指出:“诠释者是音乐思绪和恰当表现的‘继任者’。音乐,在所有的艺术之中,是一种未完成的艺术……当巴赫、贝多芬、肖邦或勃拉姆斯把思绪记在纸上,他们只是留下了墨水的痕迹,这些痕迹必须在每一次演奏中重新在人们心中被复活。这种复活是诠释技术的核心。”⑩他最后得出结论:“表演者的义务就是依照自己最佳的理解能力,一次次尝试透过不合体的外衣,看到作曲家那来自神灵的乐思。”⑪在论及读谱这一议题时,萨马罗弗所指出的“他(演奏者)还必须钻研那些没有用记号标出来的乐句的含义”⑫以及麦克斯·鲍尔所指出的“哪怕已经学习过很多年了,如果仔细搜寻,每首杰作的谱页上还是包含着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⑬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综合几位大师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9、20世纪之交的钢琴家们承认乐谱对重现作曲家意图的重要性,但他们也都清醒地意识到演奏者在诠释中的重要地位。不止一位钢琴家谈到音乐学习中的悟性,而悟性的重要使命之一便是发掘乐谱背后的深刻内涵。可以认为,黄金时代的钢琴家们普遍致力于通过乐谱寻找开启作曲家创意的钥匙,进而激活隐藏在乐谱背后的音乐构思。这也是大师们对今日许多信奉乐谱“直译主义”的音乐工作者们最有价值的启示之一。
3.综合文化修养对音乐学习起到重要作用
20世纪以来,随着学科划分的日益细致,加上在此之前汉斯立克倡导的,着眼于音乐形式的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出现,许多专业学者以一种“纯粹”的倾向从事音乐研究,这种倾向的一个突出表现在于认为音乐作品即是音乐本身。对作品唯一正确有效的诠释或解读仅通过技术层面的分析便足矣,换句话说,他们认为音乐的学习与音乐乃至与乐谱以外的一切无关。这种观念至今不乏拥护者,对于其对错与否笔者不予置评。而通过《钢琴大师论钢琴演奏》一书,我们可以知道,黄金时代的大多数钢琴家非常看重文化修养,并且认为综合的文化修养对音乐学习起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做了一番统计,在全书中对综合文化修养做出专门论述的有阿里奥拉、哈罗德·鲍尔、布鲁菲尔德-蔡勒斯、卡莱罗、埃米尔·绍尔、帕德雷夫斯基。作为神童的阿里奥拉提及自己沉迷于拉丁语、法语、电力学,天文学,同时热衷旅游和地理学。哈罗德·鲍尔指出“音乐学习中需要广博的知识……一个人知道得越多,经历得越多,关于各种人类信息的视野越广,他也就越有话要说。”⑭蔡勒斯在给读者的10条建议中的第4条中指出:“饱读文学佳作,学习绘画,旅行,开阔你的视野,对文化有所了解。”⑮卡莱罗告诫读者:“艺术家的心智必须具备素养,事实上,他需要具备与创造作品的作曲家同等层次的素养。素养来自对许多事物的观察:自然、建筑、科学、机械、雕塑、历史、男人、女人以及诗歌。”⑯而埃米尔·绍尔和帕德雷夫斯基则论述得最为详尽,绍尔认为“想要成为钢琴家的孩子必须拥有最广泛的文化修养,他必须生活于艺术和文学之中,成为他们的一位合法公民”⑰,帕德雷夫斯基则告诉读者:“艺术家只有把自己沉浸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才有可能接近伟大。”⑱从这些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取得非凡成就的钢琴家都非常重视对自身综合文化修养的培养。放眼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许多音乐学习者因为种种原因沾染了急功近利的观念,漠视综合文化修养对音乐学习的作用,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正如书中许多钢琴家指出的,要成为杰出的钢琴家变得越来越难,因此学习者要具备定力,在成名前做好全方位的知识储备。其实,即便是业已成名的钢琴家也会出于加强自身文化修养的需要而暂别舞台。莫里兹·罗森塔尔在18岁时中断了一段成功的演奏生涯,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和美学长达五年之久即是此理。他以及其他一些清醒的同行都明白,如果没有全面的知识背景,他们只能是普通的钢琴演奏者,而不是音乐艺术家。因此,黄金时代的钢琴家们重视对全面文化修养的培养应是一种普遍的风尚。
4.钢琴家承担提升公众音乐品味的义务
自李斯特1839年发明钢琴独奏音乐会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钢琴家就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音乐才华。然而,受历史因素和大众观念的影响,早期的钢琴音乐会的场景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音乐会场景相去甚远。勋伯格写道:“一切都是很随意的,李斯特在伦敦的打破惯例的‘独奏音乐会’上弹了一两首曲子后,‘从台上走到台下——台下的凳子排得让人可以自由走动。李斯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和朋友寒暄,像亲王那样降尊纡贵,直到他自己想起要回台上去继续演奏’。在演奏过程中,听众们谈天、大笑、抽烟、吃东西、走来走去。只有少数几个脾气乖张的大艺术家才要求听众安静。”⑲由此可见,早期音乐会观众的态度是极其随便的。经过门德尔松和克拉拉·舒曼等人的努力,严肃音乐会才逐渐成为主流。克拉拉在音乐会上只弹高雅的作品,也就是今天我们在音乐会上听到的常规曲目,包括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曼等作曲家的作品,她所鄙视的则是以李斯特、塔尔贝格为代表的一众以炫技来吸引听众的作曲家。克拉拉认为演奏家有引导公众、提高公众品位的义务。这一观念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更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拉赫玛尼诺夫说:“演奏大师必须抱着比名利更伟大的动机而弹。他有一个使命,那个使命就是教育大众。”⑳冈茨的观点与拉氏几乎相同,他说:“艺术家们要做的工作是引领公众认识到那些伟大作曲家作品中的高尚和人性,这些可贵的精神在哗众取宠的作曲家的作品中是找不到的。”㉑马克·汉伯格则认为艺术家在选择音乐会曲目时最重要的是真诚。他主张充分尊重公众的要求,但不能做出亵渎艺术的行为。“出卖艺术而换取掌声的艺术家在有思想深度的人脑中无疑最终会一文不名。”㉒看来,黄金时代的钢琴大师们在演奏的动机上都是克拉拉·舒曼的信徒。联系今日,我们在钢琴音乐会上听到的均是钢琴文献中的经典曲目,这不得不归功于克拉拉以及世纪之交的钢琴家的努力推广和普及,今日钢琴家已被视作一种神圣的职业,这既是音乐家本人之福,亦是公众之福。
以上是笔者通过《钢琴大师论钢琴演奏》一书总结出的黄金时代钢琴家普遍秉持的美学观念。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四点仅仅是概况,因为钢琴家的经验之谈就犹如钢琴演奏本身一样,极富个性,尚有许多其他的流行观念没有体现在书中。笔者希望的是,通过了解这些美学观念,今人在从事钢琴演奏和教学中能多一分思考,多一分感悟,毕竟,这些都是大师们对自身职业思考总结而得来的经验,无论如何,它们对启发后人而言弥足珍贵。
注释
①詹姆斯·库克:《钢琴大师论钢琴演奏》,刘弋珩译,暨南出版社,2011,第20页。
②哈罗德·C.勋伯格.《不朽的钢琴家》,顾连理、吴佩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203页。
③同注1,第117页。
④同注1,第93页。
⑤同注1,第11页。
⑥同注1,第23页。
⑦同注1,第12页。
⑧同注2,第114页。
⑨同注1,第116页。
⑩同注1,第163页。
⑪同注1,第165页。
⑫同注1,第204页。
⑬同注1,第114页。
⑭同注1,第25页。
⑮同注1,第37页。
⑯同注1,第53页。
⑰同注1,第138页。
⑱同注1,第168页。
⑲同注2,第105页。
⑳同注1,第121页。
㉑同注1,第185页。
㉒同注1,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