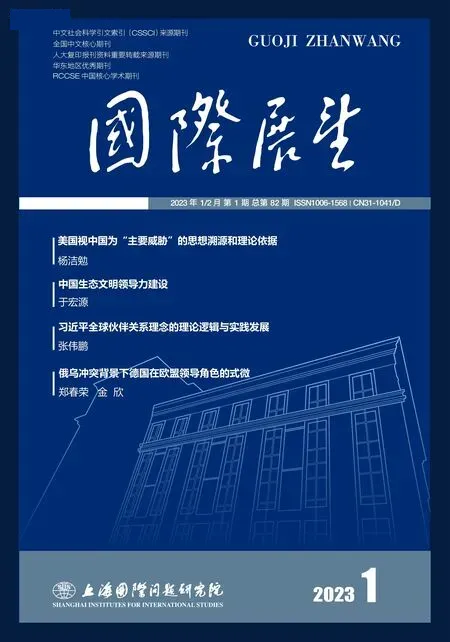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理念探析*
张 帅
粮食安全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与区域安全、国家安全、人的安全密切相关,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通力合作积极应对的主要议题。自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气候极端化加剧、全球经济疲软、局部战争和冲突不断等因素叠加,削弱了全球粮食体系韧性,导致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日益恶化。①张帅:《全球发展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4期,第117 页。联合国向世界发出全球面临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的预警。②“World Faces Worst Food Crisis for at Least 50 Years,Warns UN,” The News,June 12,2020.《2022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重度粮食不安全人数已增至9.23 亿,较2020年增加约7 360 万人。③FAO et al.eds.,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Repurposing Food and Agricultural Policies To Make Healthy Diets More Affordable,Rome: FAO,2022,p.26.该数值或将因俄乌冲突的爆发而继续攀升,加重了到2030年实现“零饥饿”目标的压力。④张帅:《乌克兰危机下的全球粮食安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4 期,第156 页。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正处于紧要时刻,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2022年11月先后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二十九次非正式会议上,粮食安全是重要议题之一。会议发布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宣言》和《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均表示,要构建更具韧性的粮农系统,强化全球粮食供应链。
当前,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制,主要涉及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发基金等三大粮农机构。其中联合国粮农组织是综合性的治理机制,既协调和加强与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合作,也在地区组织、基金会、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中扩展合作伙伴,还积极推动与联合国内部其他机构的对话协调,服务于全球粮食体系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二是以地区组织为中心的区域机制。旨在确保区域内粮食供应链的完整,如欧盟实施的《农场到餐桌战略》、东盟制定的《东盟一体化粮食安全框架》和《东盟地区粮食安全战略行动计划》、非盟制定的《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等。⑤张帅:《探寻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有效模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9月16日,第3 版。三是国家之间基于保障粮食安全的共同需求而建立的双边机制。主要是双方农业部在节粮减损、绿色产粮、粮仓建设等具体领域开展合作治理。在上述机制中,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最早建立的粮食安全治理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地区面临严重饥荒,减少饥饿人口、保障粮食安全成为国际社会最迫切的需要,这使联合国在成立之初便将粮食安全作为优先治理事项之一。此外,在联合国参与的全球事务中,只有粮农领域建立了三个联合国机构,反映了联合国对粮农问题的高度重视。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或地区粮食危机的频发,联合国也积极制定并实施应对策略,彰显了其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的重要角色。
粮食安全不仅是农业问题,还与人权、主权、发展等理念密切相关,这种相互依存性决定了联合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需以人权、主权、发展为指导,并在这三个维度统筹施策,提升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综合绩效。事实上,联合国长期践行的粮食权、粮食主权和可持续发展就是以人权、主权和发展为蓝本,是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理念的充分体现,也是联合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根本遵循。因此,本文以粮食权、粮食主权和发展观为中心,论述三项理念对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影响,并根据观念落实所面临的问题,对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发展方向进行前瞻性分析。
一、粮食权: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国际法依据
充足的粮食供应是保障人权最基本的要求。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生理需求是人最优先的需求,其中粮食是重要的构成要素。一个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很可能对食物的渴望比对别的东西更强烈,此时,“饥饿”反映了人类机体的特征,人的意识会完全被“饥饿”所支配。①[美] A.H.马斯洛:《人的动机理论(上)》,陈炳权、高文浩译,《经济管理》1981年第12 期,第67 页。可见,使人时刻处于果腹状态是确保人体正常运转和人类追求物质、精神等其他一切需求的前提。
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处于普遍饥荒的危急时刻,发展中国家民众甚至因饥饿而死亡,以粮食为核心的人权受到威胁。因此在联合国成立初期,保障粮食供应便成为其人权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1948年12月,作为联合国基本法之一的《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获大会通过,《宣言》第25 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①《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网站,1984年12月10日,https://www.un.org/zh/about-us/universal-decla ration-of-human-rights。这是联合国首次以国际公约形式赋予粮食权以合法性,并确立了其作为首要人权的国际地位。1966年,联合国通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这是联合国从国际人权宪章②《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共同构成国际人权宪章。参见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our-work/protect-human-rights。层面对粮食权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公约》第11 条规定,“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有免受饥饿之基本权利,”并明确了国家实现此目标的特定方案。③《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网站,1976年1月3日,https://www.un.org/zh/documents/ treaty/files/A-RES- 2200-XXI.shtml。《宣言》和《公约》的发布表明,粮食权是具有法律规范的人权,任何国家和组织都不能剥夺人民获取粮食的权利,这为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奠定了国际法基础,也反映了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目标,即通过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捍卫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权利。
上述两个国际公约虽然强调了粮食的人权属性,但并未对粮食权做出准确的界定。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多极化趋势愈发明显,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在为国家发展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不平等,其表现之一就在于南北粮食获取力存在巨大差距。这促使联合国对粮食权产生新的认知,即保障粮食安全不仅要确保市场上有充足的粮食,还要确保人民有获取粮食的能力。因此,1999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通过的第12 号一般性意见提出了充足粮食权(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的概念,并规定,“充足粮食权是指每个男人、女人、儿童,独自或与他人一起,在任何时候都能拥有获取充足粮食的物质和经济能力或获取充足粮食的手段的权利。”①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CESCR General Comment No.12: 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 UN,https://undocs.org/E/C.12/1999/5.该定义明确了粮食权的三个核心要素:可获得、买得起、满足需要,也指明了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施策方向。②“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 FAO,http://www.fao.org/3/b358e/b358e.pdf.为更好地落实粮食权,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2000年4月设立了粮食权特别报告专员,负责检查各地的粮食权现状,配合国家、地区和全球粮食事务的开展,促进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粮食安全合作,进而服务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③“About the Mandate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Food,” UN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https://www.ohchr.org/EN/Issues/Food/ Pages/Mandate.aspx.联合国粮农组织还专门制定了《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粮食权的自愿准则》,将与人权相关的平等、非歧视、善治、法治等原则作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遵循,以凸显联合国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高度重视。④FAO,Voluntary Guidelines to Support the Progressive Realization of 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Rome: FAO,2005,pp.2-9.
粮食权的提出反映了联合国以保障人权为根本的治理理念,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的宗旨。⑤《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about-us/un-charter/full-text。在粮食权的框架下,联合国将“尊重、保护、履行”作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基本义务,⑥“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 FAO,http://www.fao.org/3/b358e/b358e.pdf.以期更好地践行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人权观。这从新冠疫情期间联合国对粮食权的保护便可管窥一斑。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阻断了全球粮食供应链,恶化了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为减缓卫生危机对粮食体系的冲击,保障粮食供给安全,联合国在2020年4月发布了《联合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即时社会经济框架》,提出了联合国在社会经济领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框架。其中“维持粮食和营养需求,重点保障婴儿、儿童、妇女的粮食安全和膳食营养”,是联合国在社会保护和基本服务领域的六大核心议题之一。⑦“A UN Framework for the Immediate Socio-Economic Response to COVID-19,” UN,https://www.un.org/ sites/un2.un.org/files/un_framework_report_on_covid-19.pdf.这表明,保障粮食人权是联合国在疫情期间的优先关切。5 家联合国机构还在2021年11月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向60 多个国家组成的“全球学校营养餐联盟”提供支持,确保在校儿童的营养供给免受疫情侵扰。①《5 家联合国机构承诺为校餐联盟提供支持》,新华网,2021年11月17日,http://www.news.cn/2021-11/17/c_1128072509.htm。同时,联合国粮农组织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发起“新冠疫情应对和恢复计划”,并将全球人道主义应急、提升小农恢复能力、开启粮食体系转型等列为优先领域;②“FAO COVID-19 Response and Recovery Programme,” FAO,https://www.fao.org/partnerships/resource -partners/covid-19/en/.启动由意大利政府发起的“粮食联盟”,以保障贫穷国家和弱势群体的粮食获取,推动以可持续的方式增强粮农体系的抵御力等。作为全球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机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北非、东非、西亚、拉美等多个地区实施学校供餐替代机制,以解决因疫情导致学校关闭期间学龄儿童的食物获取问题。③WFP: State of School Feeding Worldwide 2020,Rome: WFP,2020,pp.1-17.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因长期致力于保障弱势群体的粮食权,于2020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同样也是对联合国维护粮食人权的高度肯定。粮食援助是联合国保障全球粮食安全义务的体现,也是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的重要构成。它的基本目标是通过“输血”保障人在突发状态下的粮食权,维持其基本生存;价值根基是使人免于粮食不安全感的恐惧;实现路径是一种应急式的管控,④程子龙:《中国与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体系:受益者、参与者与建设者》,《人权》2021年第3 期,第106 页。凸显了危机时期的国际道义。此外,面对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体系的冲击,联合国和土耳其、俄罗斯、乌克兰在2022年7月达成黑海谷物出口协议。四方均同意从当年11月19日起,将该协议延长120 天,以推动粮食供应链持续运作。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1年举办的全球粮食系统峰会上表示,“粮食不只是被交换的商品,也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权利”⑤“Food’s A Human Right,Not just ‘A Commodity to be Traded’: Guterres,” UN,September 23,2021,https://news.un.org/en/story/2021/09/1100942.,再次凸显了粮食的基本人权属性。粮食权作为联合国基于保障人权而提出的粮食安全治理理念,强调全球治理要明确“为谁而治”。人类不仅是治理实践的主体,更是治理议题所应惠及的对象。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与演进,形塑着人类的“现代性”与“现代化”,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互存、互助、互享的“类生存”时代。①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 页。“类生存”方式形塑人类的“类安全”认知,即关心和维护作为“类存在体”的人的安全,把维护人的安全建立在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统一为整体的“类”安全。②林国治:《“类安全”观与“安全困境”的超越》,载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32 页。粮食是“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也是“类安全”最重要的构成,它存在于“类生存”和“类安全”的复合场域。维护粮食权的实质,就是稳定“类生存”和保障“类安全”。联合国将粮食权作为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理念,其目的也是为了在保护“类安全”不受威胁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类生存”。综合来看,主要包括三方面目标。一是基于短期目标,体现联合国对个体的尊重,保护他们既有的粮食权不受损害。二是基于中期目标,表明治理是实现粮食安全的有效手段,通过这种手段赋权民众,促使其拥有更多改善粮食安全现状的权利。三是基于长远目标,期望个体能够在粮食安全领域实现自我治理和自我满足。
二、粮食主权: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去政治化”
粮食是维持国家生存的基本资源,也是国家安全与稳定的主要保障,起到稳定国家根基的作用。由于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刚性必需品,具有不可替代性,故常被作为服务于国家外交的工具,甚至是霸权国干预别国内政、攫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武器。在全球粮食体系中,发达国家凭借着充足的资金保障、先进的农业科技、精干的农业人才和实力雄厚的跨国粮商,长期处于粮食体系的核心地带,对粮食产量和粮食定价享有较高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虽在粮食体系中占据数量优势,但由于农业整体发展缓慢、粮食自给率较低,导致体量优势薄弱,一直处于粮食体系的边缘地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粮食体系中的地位差异,使得二者之间形成了非对称相互依赖,前者所制定的粮食政策能够直接影响后者的粮食安全。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粮食政治化”现象才普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产粮过剩和亚非拉粮食短缺的现实境遇促使华盛顿将粮食作为实现其外交战略的重要抓手。其中,美国对日粮食外交挤压了日本粮食的生产空间,影响了日本粮食安全乃至政治、经济主权与自主发展进程;①徐振伟:《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粮食战略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20年第1 期,第88—107 页。美国对印度的粮食援助迫使后者接受了种种附加条件;②参见冯立冰:《基金会、冷战与现代化——福特基金会对印度农业发展援助之研究(1951—197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6—140 页。美国在阿根廷广泛推销转基因作物,致使阿逐渐丧失粮食自给能力,整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完全受控于外国权势集团。③[美]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164 页。可见,粮食安全并非单纯的社会问题,解决粮食供需矛盾、改善粮食生产结构和调节粮食价格等一系列行为,仅仅是粮食安全议题的外在表象,其背后隐藏的是权力的争夺和利益的冲突。因此,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认知不能仅停留在确保有饭吃这个层面,还需从保障国家主权的宏观视角来审视该问题。
“粮食主权”(food sovereignty)最初由非政府组织“国际农民运动”(La Via Campesina)在1996年的墨西哥特斯卡拉会议上提出。该组织认为,粮食主权是指每个国家在尊重文化和生产多样性的基础上维持和发展自身粮食生产能力的权利。人们有权在自己的领土上生产自己的粮食,粮食主权是真正实现粮食安全的先决条件。④“Food Sovereignty: A Future without Hunger,” http://safsc.org.za/wp-content/uploads/2015/09/1996-Declaration-of-Food-Sovereignty.pdf.同时强调,保障粮食主权应以粮食权、土地改革、保护自然资源、粮食贸易重组、消除饥饿的全球化、社会和平、民主管控等七项原则为根本遵循。⑤Ibid.但“国际农民运动”对粮食主权的界定过于宽泛,且主张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因而未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也没有被写入联合国的相关决议中。相比之下,联合国所主张的“粮食主权”更加聚焦,其核心要义是“去政治化”。这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粮食被用作武器干预别国内政的现象日益严重,急需改变这一局面。
1974年,联合国世界粮食大会通过的《世界消灭饥饿和营养不良宣言》指出,“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还无法实现在任何时刻满足其粮食需求的目标,因此,必须采取紧急有效的国际行动,向他们提供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压力......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和受影响最严重国家的粮食生产,必须由发达国家以及有能力相助的国家采取有效的国际措施,在双多边机制下,向他们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财政援助,条件要优厚,数量要能够满足需求。这种援助不得附有与受援国主权不符的条件。”①“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the Eradication of Hunger and Malnutrition,” UN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https://www.ohchr.org/EN/Professio nalInterest/Pages/EradicationOfHungerAndMalnutrition.aspx.这是联合国首次在同一份决议中两次强调帮助发展中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摆脱政治权力的束缚。1996年,世界粮食峰会达成的共识性文件《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指出,“粮食不应作为一种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手段。我们重申国际合作和援助的重要性,必须制止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并危害粮食安全的单方面措施。”②“Rome Declaration on World Food Security,” FAO,http://www.fao.org/3/w3613e/w3613e00.htm.2018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2417 号决议,重申禁止将饥饿作为战争的武器。③“Resolution 2417: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in Armed Conflict,” UN,http://unscr.com/en/resolutions/2417.此外,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在第42 届会议(2015年)和第47 届会议(2021年)审议通过的《长期危机中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行动框架》④“Framework for Action for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Protracted Crises,” FAO,https://www.fao.org /3/mo194e/mo194e.pdf.和《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⑤“The CFS Voluntary Guidelines on Food Systems and Nutrition,” FAO,https://www.fao.org/3 /ne982en/n e982en.pdf.也都强调,粮食不能被用作施加政治或经济手段的工具。可见,联合国粮食主权观的“去政治化”原则已贯穿于联合国的治理体系之中,旨在防止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主权遭受来自发达国家的能力性侵蚀(国家维护主权能力的侵蚀)、意志性侵蚀(捍卫主权意志的侵蚀)、结构性侵蚀(政治经济结构的侵蚀)和进程性侵蚀(国际制度的体系进程的侵蚀)。⑥周立:《粮食主权、粮食政治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世界环境》2008年第4 期,第38—39 页。
为防止粮食沦为政治对抗的武器,联合国也为战乱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创造条件,努力确保当地的粮食供给。2014年,联合国安理会2165 号决议通过了“跨边界人道主义援助”提案,允许粮食等人道主义物资通过土叙边界运到叙利亚。⑦“Resolution 2165 (2014),” UN,http://unscr.com/en/resolutions/2165.2021年,联合国安理会2585 号决议又通过了延长该援助实施期限的提议,①“Resolution 2585(2021),” UN,https://undocs.org/S/RES/2585(2021).以维持叙利亚人民的基本生存。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叙利亚战争爆发后,也一直致力于保障当地人民的粮食需求。
粮食主权观是联合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价值体现。这表明在全球粮食体系处于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现状下,联合国并未沦为发达国家推行“粮食霸权”的权力工具,而是将维护发展中国家粮食体系的独立性作为其治理方向。作为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非国家行为体,联合国的治理实践重在突显粮食作为生存必需品的社会属性而非作为战略品的社会属性。这主要是因为,生存必需品是粮食的第一社会属性,战略品是粮食的第二社会属性,二者次序不能倒置,且后者永远从属于前者。②周立、潘素梅、董小瑜:《从“谁来养活中国”到“怎样养活中国”——粮食属性、AB 模式与发展主义时代的食物主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21—22 页。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常将二者颠倒,尤其是在对外战略中,粮食的战略品属性常被置于生存必需品属性之前,使得粮食成为迫使发展中国家让渡政治利益的武器,这从上文美国对亚非拉国家的粮食外交中便可看出。事实上,联合国粮食主权观所倡导的“去政治化”原则,就是为了防止西方通过干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市场侵犯其国家主权。该理念重在强调,发达国家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但无权干涉。更不能以粮食援助为名,推行新殖民主义霸权。③Raj Patel,“Food Sovereignty,”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Vol.36,No.3,2009,p.675.
联合国的粮食主权观是站在国家角度去看待粮食安全问题,反映了粮食安全和国家主权之间的关联。在国家权力的构成要素中,粮食自给自足或匮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因素,一个在粮食上自给自足或基本自给自足的国家,相对于一个不能自给自足而必须进口粮食,否则就会出现饿殍的国家而言,具有很大的优势。④[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0 页。因为前者在外交开展的过程中,不会受制于粮食这一基本生存品,但对于后者,粮食匮乏将影响其外交自主性。从这一层面看,联合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不仅是规范自身对维护发展中国家主权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对发展中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警惕。联合国的粮食主权观也是对粮食回归生存必需品这一本源的呼吁,希望粮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生存资源,而不是通过让渡主权所获取的暂时性物资。
三、发展观: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可持续导向
发展一直是联合国参与全球事务的核心关切。《联合国宪章》明确指出,“决心……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为达此目的……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并将“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作为联合国宗旨之一。①《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about-us/un-charter。粮食安全也是发展议题,欠发展是导致饥荒的重要因素。因为在一个经济体中,粮食不是由慈善机构或某种自动分享的系统来分配的,取得粮食的能力要靠挣得的权益(entitlement),当一个人可以建立其所有权加以支配的商品,但在无法对足够的粮食建立起其权益时,就会挨饿。②[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版,第163 页。如美国学者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在研究1845—1850年的爱尔兰饥荒时所指出,此次饥荒就是由爱尔兰前几十年经济总体不发达造成的。③详见[美]乔尔·莫克尔:《饥饿的爱尔兰1800—1850年历史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这也说明,若要有效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发展是关键。
“发展权”最初是由阿尔及利亚在1969年提出的,旨在捍卫发展中国家的权利。197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34/46 号决议指出,平等的发展机会是各国的权利,④朱炎生:《发展权概念探析》,《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3 期,第35 页。此后发展权逐渐成为联合国参与全球事务的理念指导。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提出“可持续发展观”,并得到与会国家的支持,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可持续理念开始成为联合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遵循。⑤“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UN,https:// 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topics/nationalsustainabledevelopmentstrategies.联合国以发展观为指导,将粮食安全问题嵌入发展议程之中,其实质是为了调和发达国家粮食过剩和发展中国家供给不足的问题,以期实现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均衡。1986—2015年,在联合国发布的以发展为中心的多份重要文件中,粮食安全都是主要议题。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发展观导向,具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从领域层面反映了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依存性。粮食安全是非传统安全和农业经济的复合体。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是建立完整的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确保农业市场良性运转,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而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农村收入不平等、加速小农生产的进步。同时,粮食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助于农民留在农村,提升农业发展水平。农业经济和粮食安全所形成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是联合国将二者置于同一发展目标之下的原因所在,这从《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和《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发展目标设置便可清楚看出。
二是从行为体层面突显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个人的粮食安全的统一性。根据粮食安全的衡量标准,判断国家维度的粮食安全主要以供给为主,判断个人维度的粮食安全主要以获取和有效利用为主,①Tony Castleman and Gilles Bergeron,“Food Security and Program Integration: An Overview,” in Louise C.Ivers ed., Food Insecurity and Public Health,New York: CRC Press,2015,p.2.二者的实现都以国家经济发展为保障。尤其是个人粮食安全的维护,更需要国家提供发展福利并创造发展机会。个人的粮食安全处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体系之中,如果个人因粮食不安全而陷入了发展困境,将会威胁国家稳定。2008—2009年阿拉伯人民粮食安全境遇的恶化是2010年底西亚北非大动荡的重要诱因。②张帅:《民生为先:当代中东粮食安全问题及其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年第5 期,第150 页。因此,国家应首先实现经济发展,以便在国内粮食供不应求时,通过购粮确保国内供给。同时,应使经济福利惠及普通民众,助力个体发展,以增强其粮食获取能力和自由选择能力。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也是基于这种发展逻辑,正如《发展权利宣言》所强调的,国家应实现发展,并保障个人获取粮食的机会均等。
三是从议题层面体现了粮食安全可持续和其他议题可持续的关联性。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将“到2015年饥饿人数减少一半”列为8 项发展目标之首。①《联合国千年宣言》,联合国网站,2000年9月13日,https://undocs.org/zh/A/RES/55/2。2015年,《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到2030年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列为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二位。②《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网站,2015年10月21日,https://undocs.org/zh/A/RES/70/1。在“千年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两个重要的发展节点,联合国都将粮食安全置于发展目标中的重要位置,突显了粮食安全在多议题综合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在2009年的世界粮食安全峰会上表示,“粮食是一项基本权利,粮食和营养安全是过上体面生活、获得良好教育甚至是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的基础。”③“Opening Remarks at Food Security Summit,” UN,https://www.un.org/en/issues/food/taskforce/pdf/rome%20food%20security_FINAL.pdf.
四是从时空层面强调了粮食安全的阶段性发展和地区性发展。在时间维度,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重在突出目标实现的渐进性。粮食安全按严重程度可分为无饥饿/低度期(none/minimal)、紧张期(stressed)、危机期(crisis)、紧急期(emergency)、灾难/饥荒(catastrophe/famine)等五个等级,④Food Security Information Network,2021 Global Report on Food Crises,Online Publishing,2021,p.11.需根据不同时期的粮食安全境遇提供发展资源和发展动力,逐渐降级粮食安全的威胁程度,最终实现整体粮食安全。如到2030年实现“零饥饿”,就是联合国在“饥饿人数减半”这一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基础上提出的远景目标,强调以可持续发展为动力,消除全球粮食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粮食需求又不威胁后代人粮食安全的发展目标。在空间维度,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重在强调目标实现的地区性。发展中地区是全球粮食体系的短板。2014—2021年,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重度粮食不安全人数分别增加了1.29 亿、1.79 亿、4 700 万。⑤FAO et al.eds.,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Repurposing Food and Agricultural Policies To Make Healthy Diets More Affordable,Rome: FAO,2022,p.26.发展中地区粮食安全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粮农领域的实现。因此,发展中地区的粮食安全形势受到联合国更多的关注,支持发展中国家制定合理的粮农战略规划,以发展赋能粮食,是联合国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保障粮食安全的首要议程。
为实现粮食安全可持续,联合国采取了多项举措,其中助力增强粮食体系的气候韧性最具代表性。201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发基金、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5 家联合国机构联合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将“增强气候抵御力,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作为核心议题,就如何制定和实施气候抵御能力政策以及如何借力《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营养问题罗马宣言》《人道主义议程》等全球政策平台,减缓气候对粮食安全的冲击提供指导。①FAO et al.eds.,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Building Climate Resilience for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Rome: FAO,2018.202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盐渍土壤分布图,为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和灌溉项目提供参考。202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达成合作共识,双方将打破政策壁垒,共建气候友好型农业体系。在具体项目方面,自2016年以来,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亚非拉等气候灾害高发国家实施预先行动项目,保护农业生产免受极端天气的破坏。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非洲农业适应倡议》,已帮助34 个非洲国家获得了10 多亿美元的适应气候变化资金,有效提高了15.6 万多公顷耕地的抗灾能力。②吕强:《加大投资力度,强化国际合作:非洲多国全力保障农业生产》,《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2日,第17 版。此外,为解决气候变化所造成的蝗灾等衍生危机,联合国还建立了沙漠蝗虫灾情监测平台,并与多国开展防蝗合作,以期做到早发现、早预防,减缓蝗群对粮食的侵蚀。气候环境是影响粮食安全可持续的最大变量,联合国机构通过发挥各自的功能优势,在政策、资金、技术等多方面提供支持,以绿色发展赋能粮食生产。
以发展促安全是联合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可持续路径,它强调发展是粮食安全的基础保障,发展能够创造红利,可以惠及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进而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将发展带来的经济红利转化为粮食体系的安全红利。因此,在复杂系统下,应以发展为动能,推动粮食体系转型,实现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但粮食体系转型不仅是粮农系统的结构性变革,更是一场社会、生态、经济、技术、政治、卫生系统的共同演进。换言之,粮食体系转型不仅涵盖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更替,也包括各场域政策、粮食市场、粮食生产者、加工者和消费者行为、饮食文化内涵与知识体系的建构和调整。当前,全球粮食体系正面临气候变化、卫生危机蔓延、生物多样性锐减、交通运输受阻、经济衰退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需打通粮食安全关联场域的治理堵点,推动各场域朝向共同目标并释放出发展动能,进而实现粮食体系从脆弱性系统转向可持续发展系统。事实上,联合国将粮食安全作为一项发展议程,就是为了吸收政治(发展政策)、经济(发展资金)、生态(发展资源)、科技(发展技术)等各场域的发展红利,并将其作为粮食安全治理资源,以期构建一个涵盖丰产富足(粮食供给)、公平包容(粮食分配)、尊重赋权(粮食选择)、韧性(粮食抵御)、健康营养(粮食利用)等高质量元素在内的可持续粮食体系。①High Level Panel of Experts on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of the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Building a Global Narrative Towards 2030,Rome:HLPE Steering Committee,2020,p.13.
四、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理念面临的问题及因应之策
从某种意义上讲,联合国是最早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机构,其在发展和安全治理过程中,培育了一整套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②张贵洪:《联合国与联合国学》,《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4 期,第20 页。粮食安全是联合国最早参与全球治理的领域,所倡导的粮食权、粮食主权和发展观,构成了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理念遵循。
(一)面临的问题
理念的生成和落实之间仍存在尚未逾越的鸿沟,需予以重视。
第一,保障理念落实的治理机制不健全。全球治理机制是在全球治理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规制和治理效能等要素的整体治理结构。③石晨霞:《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与中国的参与》,《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 期,第19 页。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与气候、卫生、水等领域的治理不同,它属于复杂系统治理。环境体系、生物体系、卫生体系、交通体系、金融体系等都存在于这一系统之中,且任一体系出现不稳定迹象,都会影响粮食安全治理效能。这表明粮食安全治理在主体、对象、规制等方面都具有多元化的特征。粮食安全所具有的这种系统效应,决定了粮食安全治理机制的构建要从单一转向综合安全维度。①于宏源、李坤海:《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参与》,《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6 期,第86 页。联合国在落实粮食安全治理观的过程中,虽在气候、卫生等领域给予协助,减缓突发因素对粮食权、粮食主权和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冲击,但治理实践多发生于单一机构内部,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治理观,缺少综合治理机制的保障。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系统性粮食安全治理机制的缺失,导致联合国无法从全球层面构建粮食危机预防体系,加重了卫生危机对粮食体系的威胁,阻碍了全球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便是在疫情持续蔓延时期,联合国内部也只是建立了二维安全合作模式(农业+卫生),并没有将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粮食安全保障上的相关机构纳入其中,小农、难民、土著居民等弱势群体的粮食人权未得到有效维护。
第二,缺乏确保理念落实的治理资源。全球治理既需要精神层面的理念指导,也需要器物层面的物质支持。前者明确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治理方向和治理目标,规范了治理行为,后者决定了治理能力及所产生的综合绩效。粮食权、粮食主权和发展观明确了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所要惠及的主体(人),体现了粮食安全治理的价值遵循(去政治化),确立了粮食安全治理的路径导向(可持续发展)。治理理念的践行离不开治理资源的支撑。但随着气候极端化的加剧和新冠疫情的传播,全球饥饿人数与日俱增,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资金困境也逐渐显现。2021年3月,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出了2.66 亿美元的募捐呼吁,以解决非洲东部300 多万难民的口粮配给被削减问题。同时,世界粮食计划署也被迫削减卢旺达、乌干达、肯尼亚等多国的口粮配给,削减幅度16%至60%不等。②《联合国机构寻求2.66 亿美元以援助东部非洲难民》,联合国网站,2021年3月2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1/03/1079312。资金的匮乏,将联合国置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之中,只能采取消极的应对策略,无法满足受援国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和日常营养补给,使得粮食权、发展观等治理理念,在上述国家仍未得到真正落实。
第三,缺乏理念落实的“强制力”。全球治理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相互合作,共同完成的重大课题。任何一个行为体出现抵触和懈怠的消极情绪,都可能使全球治理沦为“伪治理”。粮食权、粮食主权和发展观虽是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理念构成,但具体落实仍需国家行为体的配合。在全球粮食体系中,由于联合国和国家所处的立场不同,其所代表的利益也存在差异。这增加了联合国落实粮食安全治理理念的难度。其中联合国粮食主权观所倡导的“去政治化”原则最难落实,时刻面临挑战。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借粮食危机向俄罗斯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并通过经济制裁阻碍俄粮食出口。同时,污名化中国,认为中国并未参与解决全球粮食危机。①Lara Jakes,“U.S.Aid Chief Criticizes China’s ‘Absence’ in A Food Crisis Stoked by Russia’s Invasion,” The New York Times,July 18,2022,https://www.nytimes.com/2022/07/18/us/politics/samantha-power-china-food-crisis.html.在粮食权落实方面,联合国虽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呼吁各国避免实施出口限制政策,但这一呼吁不具有约束力,各国仍继续根据国内粮食供需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出口管控政策,使得疫情时期战乱贫困地区的粮食人权因域外粮食出口限制而受到削弱,其粮食安全在供给、获取、利用和稳定四个层面的恶化均呈螺旋式上升。同时,联合国发展观的落实也面临国家博弈的挑战。如前所述,联合国机构致力于帮助国家和地区提高粮食体系的气候韧性,但由于大国在气候领域仍面临领导力之争、能力建设和方案供给的博弈等问题,无助于实现绿色产粮和绿色兴农。
(二)应对策略
为解决理念落实所面临的困境,联合国宜在三个方面统筹施策,提升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综合绩效。
第一,在联合国全球治理框架下,构建综合治理机制,开展系统治理。粮食安全是一个复杂系统问题,需要跨领域合作和跨部门协调。当前,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发基金、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每年在编纂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时开展合作,联合国还在2022年3月宣布成立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应对小组,这构成了联合国内部跨领域合作治理的积极尝试。未来,若要真正提升粮食安全治理能力,还需重视机制构建和策略实施。首先,联合国应以粮食安全为经,以经济、环境、生物、交通、卫生等粮食安全关联议题为纬,形成网状治理结构,将与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密切相关的联合国机构纳入其中,构建一个多维度的粮食安全综合治理机制。可考虑将粮农组织总干事作为机制的协调人,并以会议的形式使机制常态化,以便及时应对由突发因素所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其次,为提高全球粮食危机的管控能力,联合国内部各机构宜在粮食安全综合治理机制下,打破政策壁垒,借助互联网技术,搭建“云平台”,推动“云合作”,及时共享领域信息,以减缓农业关联领域的危机爆发对粮食体系的冲击。此外,联合国机构还应在综合治理机制下就赋权弱势群体开展合作。妇女、小农等弱势群体承担着粮食生产者的角色,但却长期处于粮食体系的边缘。对于保障这一群体的粮食安全,不仅要“输血”,还要“造血”。联合国机构可考虑在农业技术培训和农业生产资料供给等方面加强合作,以提高弱势群体的粮食获取力和自主生产力。
第二,加强对粮农事务的资金支持并提高融资能力。资金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联合国的发展合作项目、发展援助项目和人道主义救援项目能否顺利实施。如前文所述,资金匮乏已造成西亚、非洲多国的口粮配给被削减,当地民众的粮食权和发展权受到重创。为突破资金困境,在机构内部,联合国宜从会费中划拨粮农资金,用于危机时期的粮食安全保障。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农发基金宜考虑共同设立粮农基金,明确基金的受众群体、使用情境、使用额度等相关规则。在机构外部,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应建立多元化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与企业和基金会的合作,拓宽资金获取渠道。同时,还可通过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切实参与农业项目经营,以获取经济利益,加强物质保障。此外,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宜加强与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经合组织的合作,并推动南北粮食对话和南南粮食安全合作,促使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帮助后发国家,进而减轻其资金压力。
第三,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国际法规则的制定能够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起到一定约束力。联合国应考虑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具体而言,一方面,联合国宜考虑召开粮食安全保障法会议,组建专家委员会,针对粮食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存在的问题以及在危机时期粮食供给面临的挑战和阻力等进行探讨和研究,制定相应的法规,并明确国家、国际组织、地区组织、跨国企业等各利益攸关方的职责和干预别国粮食自主权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对粮食生态安全、粮食金融安全、粮食运输安全、粮食质量安全等概念做出界定并制定保障条例。另一方面,要发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设立的粮食权特别报告专员的监督职能,并赋予粮食权、粮食主权和发展权受侵犯的国家或社会群体“上告”权,以期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形成硬约束。
结束语
联合国是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习近平在2022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上明确强调了各国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协调下共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①习近平:《共迎时代挑战 共建美好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6日,第2 版。粮食权、粮食主权和发展观构成了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理念集合,其中粮食权强调,人类是治理所要惠及的对象,要在保障“类安全”的基础上维护“类生存”。粮食主权强调,国家是治理的主体,需保持治理的自主性。粮食安全可持续强调,可持续发展是治理的最终目标,宜盘活发展资源,推动粮食体系良性运转。三个理念虽有所侧重,但也相互依存。
第一,保障粮食主权是实现粮食权的基础。个人能否吃得饱、吃得好和吃得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治理能力。一个具备独立自主的农业发展权和土地耕种权的国家,能够确保人民更有尊严、更加体面地获取粮食。相反,如果生活在一个连粮食这一最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的国家,无论个体如何拓展获得粮食的交换权利,都无法真正实现粮食安全。
第二,发展是确保粮食主权的前提。“粮食政治化”产生的重要条件,是发展中国家不具备改善本国粮食安全境遇的硬实力。这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感”由自我给予转向他者给予。粮食若要去政治化,除了提升发达国家的道义感和正义感之外,还需要发展中国家培养自身的造血功能,学习和借鉴域外国家的粮食安全治理经验,创新农业科技,以“发展赤字”的解决带动“安全赤字”的解决,从而构建以粮食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模式。
第三,粮食权的维护需以发展为保障。发展既可以是目的性权利,也可以是手段性权利。作为手段性权利的发展,注重保障个人平等参与发展的机会,享有促进发展的权利,并享受发展成果,最终实现人本身的发展。①常健:《发展主义人权理论及其基本建构》,《学术界》2021年第12 期,第101 页。粮食人权是发展作为手段性权利所要维护的最基本的人权,这主要是因为粮食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义。保障粮食人权,需重视发展资源和发展红利的公平分配,以确保社会群体的利益共享,从而提高其粮食获取力,最终实现粮食自由和膳食营养。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现了粮食权、粮食主权和发展观的核心价值,并在三大理念的框架下,规范治理行为,明确治理目标,以期实现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和更好生活的粮食安全治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