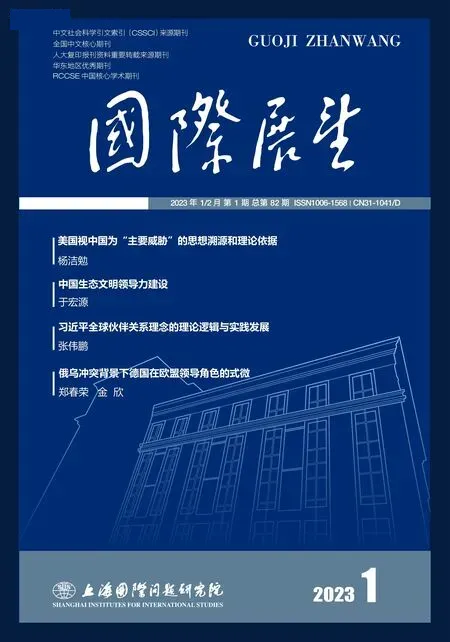代表性断裂与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危机*
刘传明 林奇富
所谓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危机,并非指通常意义上“民治、民有”式的民主理想或理想的民主政治制度出现危机,而是指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代议制民主或民主代表体制的危机。①Philippe C.Schmitter,“Real-Existing 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Sources,Conditions,Causes,Symptoms,and Prospect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4,No.2,2019,pp.149-163; and Gianfranco Pasquino,“The Ideal of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 and Real Democracie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4,No.2,2019,pp.238-254.作为当今世界较为普遍的民主形式,代议制民主面临着民粹主义的严重挑战。在频繁出现的民粹运动中,民众往往会绕开既有的代表体制,转而采取政治精英所控制不了的手段来影响政策制定,比如以全民(地方)公投、街头活动等直接方式来表达诉求,或者选择民粹主义的政党、个人来代表自己。这一现象是民粹主义的直接反映,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在心理上对体制内政治代表的不信任或不满意。政治代表原本是代议制民主的核心主体,而现在却面临着代表性危机和公共治理困境。这与政治代表(精英)与民众之间产生的代表性断裂有直接关系:普通民众的诉求长期无法被纳入政策议题,决策体现的往往是精英集团等受益群体的利益。这种情况的存在产生了亨廷顿所说的“非代表性民主”②所谓“非代表性民主”是指政府政策与民众的意愿相脱离,两者越来越呈现出不一致的状态。民主变成了精英人士的民主,政策法律主要偏向他们,对民众的代表性出现问题。[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278 页。,同时也意味着欧美国家民主政治出现危机。本文主要聚焦于西方政治体制来分析欧美国家的系统性政治危机,虽然这并不能完整解释欧美国家的全部困境,但却可以通过剖析政治体制的代表性断裂实现对政治代表体制更集中的讨论,并加深对欧美国家民主政治危机的理解。
在既有研究中,学界对欧美国家民主政治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从政治极化③庞金友:《国家极化与当代欧美民主政治危机》,《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 期,第44—56 页。、民主赤字④魏南枝、黄平:《西方“民主赤字”背后的制度性缺陷》,《光明日报》2018年4月17日,第11 版。以及民粹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从代表性断裂角度来分析和解释欧美国家代议制民主困境的研究尚少且不成系统。本文主要从政治代表体制的代表性断裂而非政党的代表性危机角度对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危机进行剖析。一方面,通过厘清代表性断裂的本质特征、形成原因以及政治影响来理解由这种断裂所造成的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危机;另一方面,基于代表性断裂与欧美国家民主政治危机关系的分析,进一步思考代表性断裂与民粹主义、民主政治与民意政治的关系。
一、代表性断裂的本质特征
在既有研究中,代表性断裂多指政党政治所面临的代表性困境。具体而言,就是作为组织和行动主体的西方国家政党在其自身发展中日益服从国家的逻辑,不但将其职能而且将其组织形态逐渐与国家机器同构,从而模糊甚至丧失了政党本身的代表性特征,出现政党国家化的现象。①汪晖:《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开放时代》2014年第2 期,第71 页。在欧美国家,这种代表性断裂主要体现为政党的左右区分模糊化。欧美国家内部的两大政党原本主要是通过提出针锋相对的主张来表明立场,以吸引和代表各自的民众。但当前无论是两大主流政党还是一党内部的左右两翼,为了争取中间选民都呈现往中间靠拢的趋势。这使得政党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以至于给人一种“选择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一样”的感觉。②刘瑜:《民主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7 页。而这种政策取向上的模糊或趋同所造成的结果恰恰是西方政党政治代表性的丧失。
当然,政党的代表性断裂只是当今世界多重政治危机中的一种典型样态。代表性断裂是一个普遍的政治现象,而不单纯指政党政治的危机;它也可以直接指政治体制或代议系统与民众(社会)之间出现的政治裂隙或信任危机。这两者虽然看似相差不大,但实际上却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些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发生“断裂”的主体存在不同。尽管两种代表性断裂都有着相同的代表对象——民众,但在民众另一端的主体却明显不同,一个是政党,另一个则是包含了更多行动者的政治体制。③政治体制一般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和法律,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情况下会有所不同。本文中的政治体制具体是指政治代表体制、政治精英体制或代议系统。在这个体制中,不仅包括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政治代表(如议员),而且还包括以间接方式产生的政治代表,比如由所选代表选举任命的政府机构的官员等,其包含范围明显大于单一的政党。其次是代表性所关注的重点不同。就政党而言,其代表性主要强调的是阶级或左右区分,更加注重身份的代表。所谓代表性断裂往往意味着政党的阶级或左右区分变得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党提出关于对应群体的保护性政策,如果两者没有以前那样的有机关联,可能仍然被认为是代表性出现了断裂。①在汪晖看来,政党的代表性断裂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我们可以找到对于工人和农民的保护性政策,却难以发现在人民战争中形成的那种工农政治和政党政治之间的有机联系。汪晖:《“后政党政治”与中国的未来选择》,《文化纵横》2013年第1 期,第17 页。因为民众对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已经淡化。在民众看来,那些优惠政策只不过是政党作为整个国家的执政党对全体民众施政的一种措施。与此不同的是,政治体制的代表性则主要强调代表的实际行动,其更加注重的是政策与民意的一致程度。因为在现实政治中,即使议会与整个社会在形式上实现了精确吻合,可能也难以避免事实上的代表性断裂。如果政治代表更多偏向精英集团的利益而使得民众诉求长期无法在政策议题中得到体现,那么往往就意味着政治体制的代表性出现了断裂。本文所讨论的代表性断裂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政党通常内嵌于政治体制之中,所以两种代表性断裂在外在特征上又有着很多重叠和相似之处。就政党的代表性断裂而言,其具体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党逐渐跳出先前的阶级或左右之分,宣称自身的普遍代表性;二是政党与处于底层的普通民众关系日渐疏远。②汪晖:《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第71 页。政治体制的代表性断裂也具有这两方面的特征,只是由于行动主体的不同而略有差异。政治体制代表性断裂的主体主要是通过制度授权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政治精英,其中不仅包括议员群体,也包括很多政府官员。所以,在这种代表性断裂中,一方面,体制内政治代表虽然也在强调自身的普遍代表性,但并未跳出阶级或左右之分,而是建立在超越地域性选民利益的基础之上,主要通过自己的理性和独立判断来维护整个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政治体制的代表性断裂也表现为体制内政治代表与普通民众的关系疏远。只不过这种关系疏远主要体现在政策议题的选择上,即普通民众的诉求很难进入决策议程,政策结果更多体现的是精英集团的利益。这也是当前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之所以在选举投票时态度越来越消极,甚至会发动更为直接的街头行动来影响政策结果的原因所在。除上述两个特征之外,政治体制的代表性断裂还体现出“去政治化”的特点,①“代表性断裂”这一概念是在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它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的革命主体性的消逝、国家及其主权形态的转变和政党政治的衰落。所以不管是政党还是政治体制的代表性断裂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去政治化的特征。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 页。这主要表现为技术官僚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上升,“专家治国”的色彩浓厚等。具体而言,就是在“去政治化”的民主体制中,代议制民主的运作已经发展为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回应民意为中心,民众逐渐被排斥在正常的决策过程之外。以上三个方面是政治体制的代表性断裂的基本特征,它所勾勒出的代表性断裂的大体轮廓,可以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政治体制的代表性危机提供基本的参照。下文将对欧美政治体制代表性断裂的生成原因进行剖析,以便更好地理解代议制民主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因为对代表性断裂的深挖是理解民粹主义为何产生以及如何挑战代议制民主的理想途径。换言之,当代民粹主义对代议制民主挑战的本质依然是传统社会中民主政治的衰落,这种衰落主要体现为原有制度的代表性赤字。②Kenneth M.Roberts,“Crises of Representation and Populist Challenges to Liberal Democracy,”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4,No.2,2019,pp.188-199.
二、代表性断裂的生成原因
就本质而言,代表性断裂可视为政治代表关系的嬗变。因为在传统的政治代表理论中,完整的政治代表关系通常是从授权和责任两个层面来建立和完成的。③Hanna F.Pitkin,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58.如果政治代表只是得到了民众的授权却并未及时回应民意,那么代表关系就会出现问题。代表性断裂就是这样一种单向的代表关系,它是导致欧美国家民主政治危机的关键所在。所以为了更准确地理解欧美国家代议制民主出现危机的内在逻辑,我们有必要对产生代表性断裂的原因进行深入探究,以便揭示其内在的发生机理。另外,由于代表过程是一个包含选民与代表者的复杂过程,所以为了更准确地探析代表性断裂的成因,就必须对代表的主体、客体、代表过程和外在环境等进行全面考察。
第一,从代表的对象即民众的角度来看,社会或民众内部的个体化和差异性加剧了民意整合的困难程度,使得民众变得很难甚至不可被代表。这是代表性出现危机的客观原因。即使不出现民粹主义,这也是政治代表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在传统的代表理论中,代表性通常是建立在同一性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代表观看来,民众内部是同质的且存在一个可被客观认识的共同意志。正是基于这种共有的同质性才使得多元异质的选民有了能被代表的可能。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本“建基于同一性之上的代表性”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①聂智琪:《代表性危机与民主的未来》,《读书》2016年第8 期,第129—130 页。一方面,这是因为无论是在以地域划分的地理选区中,还是在更具同质性的特定群体内部,民众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以美国的地理选区为例,由于频繁的人员流动,部分选民的利益逐渐与其所属的地域发生分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由数十万人组成的内部更加分裂、多元的地理选区可能会变得很难被代表。而即便将代表的对象转向更具同质性的特定群体,其内部多元的身份认同也会引发同样的问题。可见,民众的进一步分化是导致代表性危机的深层原因。因为正是它破坏了代表能够实现的同质性基础,使得民众由于缺少一个“可供代表或参考的关于意见或利益的实体或本质”而变得无法被代表。②Iris Marion Young,“Deferring Group Representation,” in Will Kymlicka and Ian Shapiro,eds.,Nomos: Ethnicity and Group Right,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6,pp.349-376.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今欧美社会的日益个体化加剧了民众的不可代表。③Simon Tormey,The End of Representative Politics,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5,pp.59-82.通常,民众可以基于对所属群体或组织的认同凝聚成一个整体而被集中地代表,但是随着欧美社会的日益原子化,民众开始不断地从原有的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而变得更加原子化。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代表往往会变得无所适从,因为民众的差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代表能够整合和回应的有效范围。如果说民众的进一步分化只是增加了其内部的差异性进而加大了代表的困难程度,那么社会的高度个人化则直接使民众变得不可被代表。从更深层次讲,代表性问题并非简单地代表双方关系的疏离和断裂,而是身份政治带来的社会民众本身的分化以及网络社会带来的生活方式的革新。①郭湛、曾东辰:《代表性断裂问题与群众路线之解》,《学术交流》2019年第5 期,第51 页。
第二,从代表的主体来看,政治代表的自主性增强和更强调自身的普遍代表性也是造成代表性断裂的重要原因。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由于政治代表(尤其是体制内政治代表)自主性的增强,可能会弱化由选举所建立起来的与选民之间的联系。这可以从政治代表本身的行动逻辑进行考察。通常,政治代表的行动主要分为遵命和独立两种模式。②[美]汉娜·费尼切尔·皮特金:《代表的概念》,唐海华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第176—205 页。其中,遵命模式主要是指政治代表作为选民的代理人存在,代表一旦当选,其一切行动必须严格遵从选民的指令;而独立模式则认为政治代表是选民的受托人,当选后的代表,其行动应该根据自己的良知与智慧进行自主判断。③聂智琪、谈火生编:《代表理论:问题与挑战》,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在现实政治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政治代表在行动时往往更加偏重受托人的角色,即更依赖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很少直接按照选民的指令行事。究其原因,这与议题的复杂程度、代表与选民的时空距离以及两者的相对能力有着很大关系。作为在现代国家实现民主的重要发明,政治代表原本应该作为代理人来行动,即时刻与民众保持密切联系以保证自身的合法性。但是政治代表所处的时空优势及其本身的精英特性和专业知识都使其行动更偏向于受托人模式。这使得政治代表在行动时往往会更加依赖自己的判断,而很少顾及选民的意愿。当政治代表变成纯粹的受托人时,其与选民间的关系就会断裂。④Iris Marion Young,“Deferring Group Representation,” pp.349-376.另一方面,政治代表日益脱离地方而服从国家治理的逻辑,会使代表的重心和范围都发生较大变化。在欧美发达国家,政治代表原本是选区选民选出的地方代理人,但其当选后却被经常要求应对整个国家具有普遍的关怀和同情。这一情况以柏克(Hanna F.Pitkin)的实质代表制最为典型。⑤Hanna F.Pitkin,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pp.168-189.概言之,当代表的逻辑逐渐被国家治理的逻辑所压制,政治代表的功能将不再局限于部分或小范围群体,而是宣称其具有普遍代表性。这使得政治代表与原选区选民之间的联系减弱,两者之间的代表性因此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
第三,从代表的过程来看,代议民主运行机制的异化也是代表性断裂的重要原因,它会使得代表性民主变成非代表性民主。具体而言,虽然在欧美国家中选举仍然在周期性进行,但社会成员尤其是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却并未被纳入政策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作为代议民主运行的重要环节,原本保障民意传达的选举问责机制现在却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导致代表性危机的直接原因。因为在正常情况下,选举不仅是实现制度授权的必要手段,还承担着问责政治代表的重要功能。也就是说,当政治代表被选出之后,如果其行动违背选民的意愿或偏离人们的公共利益,选民是完全可以在下次选举时通过更换代表来实现惩罚的。但现今,随着社会成员对政治越来越冷漠甚至直接退出选举,选举本身所具有的问责功能逐渐失去效力。这使得周期性的选举只能发挥向精英赋权的功能,而无法实现有效的政治问责。①高春芽:《民粹化民主的制度逻辑:包容与对抗》,《学海》2018年第4 期,第32页。在这种情况下,代议民主的运行机制发生了异化。政治代表不再是对授权阶段的选民负责,而是为了成功连任转而迎合那些在未来选举阶段的选民和资助竞选的各类金主的偏好。当人们的公共利益被遗弃或逐渐被小集团的特殊利益所稀释时,政治体制本身的代表性也随之出现断裂。其次,与民众的周期性选举相比,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施压等方式能够更加直接、有效地影响政策过程。在代议民主中,尽管周期性选举是民众问责政治代表的常规手段,但是它在平时即选举之外的其他时间却很难发挥作用。也就是说,选举的问责功能只有在选举期间才是最有效的,一旦选举结束选民就很难约束政治代表了。②原文为:“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1 页。而利益集团通过目的性更强的游说施压,不仅可以随时影响政治代表,而且其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也更加直接、有效。随着利益集团的游说施压逐渐成为政治常态,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很容易形成稳固的利益联盟,从而使得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更加边缘化。显然,代议民主运行机制的异化是导致政治体制出现代表性断裂的直接原因,同时也是民粹主义兴起的制度根源。
第四,从代表过程的外部环境来看,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集团利益关系逐渐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公共政策开始更多偏向国际层面,进而偏离了国内民众的总体利益。在当今世界,作为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跨国流动和优化配置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不仅把人们的活动重心从国内层面扩展到更广范围,而且随着其持续深入,几乎在“每个国家内部都产生了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挫败者”①刘擎:《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及其对自由民主制的挑战》,《知识分子论丛》2018年第1 期,第10 页。。这些人通常基于自身的基本立场和利益得失而对全球化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例如,拥有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精英集团往往是全球化的受益人群。他们在政治上更关注有助于推动全球化的相关议题,如本国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及其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等。相对而言,普通民众则大多很少获利甚至是利益受损方。他们更关心的是自身在本土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如全球化所带来的工作机会的减少、生活成本的增加、公共基础设施的匮乏以及教育、医疗等条件急需改善等。但是,由于精英集团在议会政治中的话语权较强,面向民众的、本土的政策议题长期以来并不具有政策优先性。公共政策更多体现在精英集团所关注的全球性议题。这种情况的存在也是导致反全球化、排外等民粹主义运动兴盛的主要原因。因为如果普通民众不采取极端方式绕开体制内精英,那么他们将很难对决策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也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超越民族与国家的“超级阶层”②Samuel P.Huntington,“Dead Souls: 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The National Interest,No.75,2004,pp.17-18.。他们对国家有着较弱的责任意识,却有足够的力量影响国家的政策制定。这很容易导致政策议题偏向国际性事务而脱离国内民众的基本诉求。由上述分析可见,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环境催生了跨国精英和对利益的垄断,也是导致代表性断裂的重要原因。因为正是他们的存在才使得政策议题更多地偏向了国际层面,从而脱离了国内民众的基本诉求。
三、代表性断裂的政治后果
代表性危机是当前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无论是基于经济诉求引起的左翼民粹主义还是基于文化诉求激发的右翼民粹主义,其产生的直接原因都在于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诉求长期得不到足够关注和有效回应。民众本来是政治体制获得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也是政治代表行动和决策的基本参照。但是欧美国家现行体制所推行的诸多政策却严重偏离了民众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对体制失望的选民往往退出选举或采取更为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和影响决策,这显然破坏了国家正常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具体而言,代表性断裂主要导致三方面的政治后果。
第一,就政治体制而言,代表性断裂所引发的民粹主义会冲击和瓦解传统的政治代表体制,削弱政权的合法性。在现代国家,政治代表是实现民主和有效社会治理的首要方式,其政策取向和实际作为往往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换言之,如果政治代表能够及时有效地回应民众诉求,即通过将他们的偏好转化为公共政策,使政策与偏好相一致,那么他们就可以赢得民众的支持;反之,则很容易丧失民意基础。所以,当公共政策长期严重偏离民众诉求而出现代表性断裂时,欧美国家民众会因此而失去对其政治体制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将不再寻求通过政治代表来间接表达诉求,而是努力绕开他们,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来影响政策的制定。这将对传统的政治代表体制造成强烈冲击,从而威胁政权的合法性。
以英国的脱欧公投为例,它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首先,作为一种直接的民主形式,全民公投绕开政治代表由民众直接决定英国在欧盟的去留这一事件本身,就是对传统政治代表体制的瓦解。在英国,议会原本应享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但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欧盟制定的法律却逐渐建立起了对欧盟各国法律的优先地位,这使得英国议会在讨论政策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欧盟的影响。当公共政策愈发偏向欧盟而偏离国内民众的总体诉求时,英国民众将不得不诉诸更能体现公民意志的全民公投来决定国家的关键议题。这一做法势必对传统代表体制的核心地位造成强烈冲击。其次,公投作为公众意见的直接表达,其产生的意外结果也会导致民众与议会的对立。在对欧盟的去留问题上,英国议会的多数议员所持的立场实际上是继续留在欧盟之中。①英国下院有650 席,其中工党作为下院最大的反对党在脱欧的问题上持中立的立场,自由民主党则反对脱欧。英国的第一大党保守党在下院中拥有330 席,在脱欧的问题上,保守党的分歧比较大,这一分歧在脱欧公投后被彻底激化,其中43.6%保守党议员支持脱欧,52.1%支持留欧。参见Heppell Timothy,Andrew Crines,and David Jeffery,“The United Kingdom Referendum on European Union Membership: The Voting of Conservative Parliamentarian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55,No.4,2017,pp.1-17。但是公投的结果却使他们不得不接受相反的决定。这种代表与民意的巨大反差实际上削弱了英国议会本身的合法性。因为从法理上讲,虽然公投的结果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却具有民主程序上的最高合法性。②周淑真、孙润楠:《悬浮议会、全民公投和政党政治结构性问题——英国脱欧背后的政治逻辑》,《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4 期,第8 页。这使得英国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将不得不严格遵循公投结果,否则将可能由于人民主权与议会主权的对抗而产生宪政危机。
第二,代表性断裂会降低民众对政治的参与热情从而退出选举,或者转而寻求由民粹主义的政党或个人代表自己,导致政治代表体制的民主性大打折扣。在国家的重要议题上,当公共政策长期偏离民众诉求时,民众往往会由于对政治失望而退出政治参与,或者转而通过更为激进的体制外代表人物来表达诉求。这对政治代表体制的民主性实际上有很大伤害。民主的核心要素就是政治参与,③段德敏:《民主的核心要素是政治参与——兼与唐亚林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2 期,第46—49 页。如果民众及其代表在参与上缺席则必然会影响既有体制的民主性。首先,代表性的断裂会使民众参与选举活动的人数不断下降,这会削弱民主代表体制本身的合法性。以美国的选举为例,从1960年起,民众几乎对所有选举活动的参与都减少了。从竞选活动的志愿者人数,到收看电视实况转播候选人辩论的观众人数,莫不如此。④Thomas E.Patterson,The Vanishing Voter: Public Involvement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New York: Knopf,2002,pp.4-5.甚至在大选和中期选举中,民众的投票率也不容乐观。由于民众的退出,选举活动已逐渐变成少数人参与的游戏。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充分和不平等,使理论上的多数决定原则很多时候变成了实际上的少数决定,①魏南枝、黄平:《西方“民主赤字”背后的制度性缺陷》,2018年4月17日。政治代表体制本身的民主合法性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底层民众只有打破政治规则,通过体制外的代表人物才能影响政策决定。其次,民众的退出和政治冷漠也弱化了周期性选举的问责功能。在西方代表体制中,选举通常被视为代议民主的重要标志。因为通过选举,民众不仅可以完成对政治代表的制度授权,还可以实现对政治代表履职情况的问责。但是,随着政府政策日益脱离公众诉求,对政治失望的民众逐渐退出选举。这使得选举原本具有的政治问责功能受到了极大削弱。民主政治本来是一种责任政治,可是选民的退出却使对政治代表的有效约束陷入失灵,进而使代表为了寻求连任往往会舍弃本该负责的授权阶段的选民转而迎合下次选举阶段选民群体的偏好,这为民粹主义政党或个人的当选孕育了有利的竞选环境。再次,就民主本身而言,由于民主和参与存在紧密关系,民众退出参与也会降低代议民主的民主程度。在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看来,民众的参与和政府的参与不同。前者的参与在于选出政府(政治代表),而后者的参与则是治理和决策,②[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95—396 页。两者共同构成了代议制民主的参与过程。但由于当前政治体制代表性的断裂,对政治失望的民众却不断地退出选举过程或者选择体制外的政党和个人来代表自己。这种情况严重削弱了代议民主本身的民主性,甚至存在着使民主政治彻底蜕变为精英政治、寡头政治和民粹政治的可能性。
第三,代表性断裂使得群体性运动频发,容易导致政治失序和社会混乱。当政府政策严重脱离公众诉求而使得民众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时,他们往往倾向于通过更为激进的街头行动来释放自己的不满。这给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埋下了极大的隐患。激进的街头行动本来只是一种制度外的补充手段,大多发生于欧美国家民众遭受歧视或其正常诉求无法满足等极端情况下。但是由于代表性的断裂,街头行动却成为人们表达诉求的常用手段。值得注意的是,新近发生的这种制度外的政治行为与以往的社会运动的本质不同主要体现在二者对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上。通常情况下,社会运动主要是通过非暴力手段来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即抗争通常会表现为政治体制能够接受和容忍的形式。①Carles Boix and Susan C.Stoke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449.但在代表性断裂的情况下,利益受损的民众会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这导致民众为宣泄自己的不满和表达自身诉求,往往会诉诸更具破坏性的政治暴力来引起欧美国家政府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街头行动将升级为更具暴力性的行为,从而严重破坏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就是这一情况的典型体现。这一席卷法国的社会运动虽然以抗议法国政府提高燃油税这一具体政策为开端,但从本质上讲,却是法国政府政策长期偏离底层民众诉求的结果。因为早在马克龙政府对燃油加征碳税之前,随着国际油价的上涨,法国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当年已经分别上涨了15%和23%。②许振洲:《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民粹主义的泛起还是精英政治的危机》,《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5 期,第10 页。所以当马克龙不顾国内中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而试图通过加税来促进节能减排、履行《巴黎气候协定》时,民众的愤怒情绪就被彻底点燃,进而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法国发生的社会事态实际上是代表性断裂的结果。
结束语
民粹主义是当今世界重要的政治现象。从代议民主的运行机制出发,民粹主义的兴起实际上是代表性危机的结果,即首先并不是民粹主义诱发了代议民主的政治危机,而是民主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催生了民粹主义。③高春芽:《政党代表性危机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 期,第111 页。其次,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谈的代表性断裂主要是指政治体制的代表性断裂,而非政党的代表性断裂。换言之,代表性断裂其实是在政府政策与民众偏好的一致程度这一实质层面上展开的,而不是指阶级或左右之分的身份代表。因为在现实政治中,形式上的身份代表可能并不能避免事实上的代表性断裂。再次,从代表性断裂产生的原因来看,它不仅存在民众分化、代表自主性增强等客观因素,而且还包括体制失灵、金钱政治等内生性因素。其中,民众日益个体化的趋势和代表日益服从国家的治理逻辑是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即使欧美国家不出现民粹主义,民众分化和代表自主性增强等因素也会由于自身的特性而引发不同程度的代表性危机。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体制异化等内生因素才是真正导致代表性断裂和当前欧美国家民粹主义盛行的主要原因,其他两个要素则是在不同程度上加重了代表性的断裂或为其产生创造了条件。此外,面对代表性断裂所导致的严重的政治后果,政府需要做的不仅是要重视和回应民意,而且还要避免盲目追随和顺从民意。因为在欧美国家政治中,虽然抽象的人民在话语上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具体的公民却在实践中陷入无助的困境。①高春芽:《民粹化民主的制度逻辑:包容与对抗》,第35 页。这种情况使得民众的诉求表达往往只能通过选择“民粹主义代表”等作为替代模式。②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61.典型的如通过追随民粹主义政党等方式来响应排外和反全球化的政策等。这些情况对传统的政治代表体制和正常的社会秩序都造成了严峻的挑战。而另一方面,在重视民意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民意本身所具有的短视和非理性的一面。因此,对于民意,欧美国家政府必须慎重行事,以审慎的态度尽量保持自主性和代表性的平衡。换言之,人们原本所追求的其实是民主政治而非民意政治。这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通过对代表性断裂与民粹主义、民主政治与民意政治关系的反思,可以发现,代表性断裂与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危机紧密相关。代表性断裂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因此对于欧美国家来说,探索弥合代表性断裂的可行性方案以推动其社会民主健康发展十分必要。这或许可以从代表性断裂的产生过程,即代表与选民的内外部关系中寻找破解之道。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欧美一些国家也认识到了有关问题并采取了相应对策,但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本质和制度特征使得它们可能无法克服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勉冲·罗布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