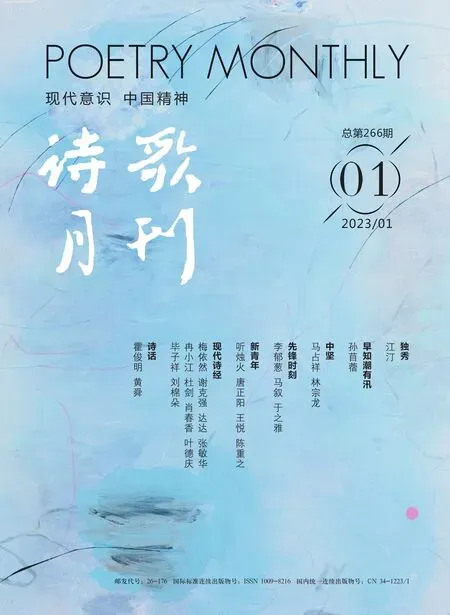朝向未来的音乐:评王敖《十二束绝句》
黄舜
在正式进入王敖那布满精妙字词的绝句丛林之前,请先来听听其中一首小诗的音乐:
很遗憾,我正在失去
记忆,我梳头,失去记忆,我闭上眼睛
这朵花正在衰老,我深呼吸,仍记不住,这笑声
我侧身躺下,帽子忘了摘,我想到一个新名字,比玫瑰都要美
很显然,这是一种说话的声音,这声音平静、悠扬,略带一丝感伤,但又如音乐般动听。“很遗憾,我正在失去”,简短的八个字,以语言的魔力立刻引来一种忧郁但沉稳的调子,似一个心有所悸却已然宽慰的智者发出的叹息。
如果说,一首诗周围的空白是恒久的沉默,那么一首诗的出现就是用一种声音来刺破这种沉默:该挑选怎样的音色?携带怎样的词语,对于诗人来说都是艰难的挑战。但当那个捕捉已久的声音准确出现时,好的诗歌就能循着这声音的调子生长下去——让我们再次跟着这首诗的第一句,追随每一个音节来感受词语心脏般微妙的跳动:“很遗憾,我正在失去”,随后是短暂的沉默,这句话并没有结束,而仅仅是被分行刻意制造的寂静暂时打断,紧接着,那个重要的词出现了——“记忆”。
这种设计源于诗人对语调精准的把握,它以瞬间下沉的休止符来构造断裂,又因这份断裂刻意强调了“记忆”一词。然而这句话还没有结束:“我梳头,失去记忆,我闭上眼睛,这朵花正在衰老……”诗歌沿着这个声音继续下去,越来越快,并时而在周围环伺的沉默间发出回响。
从失去记忆到梳头的日常,从人衰老的征兆到对花朵衰老的体察,日常的种种动作伴随着“我”之思绪对细微之物的触碰,这首诗在“想到一个新名字,比玫瑰都要美”中翩然结束。语言停止了,但声音仍在读者心中回荡——这是一个怎样的新名字呢?又是对谁的命名?诗人没有说,也不必说,因为一旦说出来,就不是诗了。
这首诗媲美一个轻盈的叹息,我们知道有很多诗歌的声音是尖锐、高亢的;有很多又是晦暗、沉郁的,但这首短诗只是一声叹息——极为重要的是,它轻盈、干净,既不忧愁亦不沉重,而是一个悄然鼓起又轻声破碎的气泡。
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足以在遥远的得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这个微小但晶莹的气泡发出的轻响,也极有可能在汉语诗歌的世界掀起一场风暴。至少我们看到,《十二束绝句》(以下简称《绝句》)系列无论是在王敖个人的诗歌写作还是当代汉语新诗的写作中,都已然形成了一道不可忽视的语言风景。
熟悉王敖的读者可能都知道,他既是一个资深的摇滚迷,也是一个业余的摇滚乐手,房间里摆放着林林总总珍贵的吉他,朋友圈里“回响”他风格迥异的吉他演奏。一个在琴弦上滑动并拨弄乐音的歌手,回到诗人身份中时,也总以一颗颗质地温润的词语制造着动人的珠玉之声——王敖的这些《绝句》,也是一首首“音乐之诗”。
在2007 年11 月版的“汉花园青年诗丛”里,王敖的集子《绝句与传奇诗》中就已经出现了几首脍炙人口的《绝句》。臧棣则在这本诗集的序言《无焦虑写作:当代诗歌感受力的变化——以王敖的诗为例》中准确提炼出了王敖诗歌的一个特点,即“无焦虑”。
在那些被古典—传统,西方—东方的阴影所覆盖的诗歌书写间,王敖的诗歌的确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气质,其色泽明媚而语调轻盈且轻快,凭借超级的想象力配合着动人的乐音从那团阴影里一跃而起。这不禁令人想起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提到的,从墓园栅栏边轻轻一跃的形象。王敖诗歌中展现出的轻盈气质,也无意间回应了卡尔维诺对未来文学之轻的预言。
作为朦胧诗重要代表的顾城,早在八十年代已经以其《布林》组诗完成了一种和王敖诗歌极其类似的“无焦虑写作”,遗憾的是,他比王敖出发得更早,却没有后者走得长远。当然这是后话,从第一次读到王敖的《绝句》到现在翻开这本新出版的《绝句》,我仍然坚信王敖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并继续尝试着去实现汉语诗歌对纯粹的美学的追求。
当我们提到“绝句”,首先就会想到古典诗词里那些短小精妙但排列整饬、对仗严格的五七言诗。这容易造成一些读者的疑惑甚至是质疑,即《绝句》里那些诗作,是否仅仅是对古典资源的当代效仿?它们除了形式不同,语言不同(白话—文言)之外,究竟有什么区别?
“新—旧”二元对立的思维总是埋藏在我们的认知深处,如影随形却毫不察觉,这导致我们习惯于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寻找所谓的不同,却忘记了对传统资源的继承和延续。可以说,王敖的《绝句》并无意于在新诗旧诗之间继续划出一道至少在今天的时代已然毫无意义的鸿沟,而是追求在古典与当代幽暗的峡谷间打出一条可能的通道。循此,我们在这些《绝句》的文本里听到一种诗人与中国古典传统对话的声音,注意,对话而非对立——这对话跨越时空,与传统资源勾连,回响于过往,又穿透当下,响彻未来。这些《绝句》的书写向我们佐证了艾略特所谓“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关系,也显示出一个诗人更新并延续其写作的可能路径:即与传统对话,与过去的诗人、过去的形式对话并个人化为自己的风格特征。从这个层面看,王敖的《绝句》并非对古典资源的简单“改造”,而是携带着一种“历史意识”的古今之对话。简单来讲,王敖解决了这样一个难题:古人是那样写“绝句”的,我们当代的写作者可以怎样写“绝句”?
王敖曾自己坦言:“现代汉语诗歌的名字就叫‘新诗’,这种新与旧的对立和区隔,已经演化成了一种症结,即使是杰出的诗人和批评家,遇上也会忙于拆解……新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建立在与旧的区别上的,而是一种有未来感的动能,它铸造出的区别可以跟过去的任何光彩和声响相安无事。我们并不需要让一首唐诗显得更旧了,而是在古今之间,找一种能一起守恒的感觉。”
这段话一方面透露了王敖作为一个汉语诗人的抱负,一方面也很好地显示出一个诗人对其自身作品的理解、自信与自觉。怎么去理解这里所说的“一种有未来感的动能”呢?私以为,王敖的《绝句》系列开创了一种新的诗体,它既面向古典传统,又具备当代特质,最重要的是,它还朝向未来——它们,这些《绝句》仅仅是一个起点,它们不凭借与古典资源寻求差异而获得“新”的标签,而是发明新的语言形式、新的表达方式,从而在当代新诗自身的可能性上不断激发新的动能。
不得不提的是,翻开这本薄薄的诗集,《绝句》犹如一把把锋利的匕首,为我们划破经验的屏障,又以其惊人的想象丰富着我们平庸的日常。那些新奇而精妙的句子在这本诗集里比比皆是,它们不断撩拨着我们的神经,欣喜、惊讶甚至带一点冒险的恐慌,如同在想象的海面引我们冲浪。可当我们合上书试图平静的时候,竟如禅宗顿悟般,仿佛真感受到了那“万千砂轮下的动与静”。正如史蒂文斯对黑鸟的观看或者在一杯水中发明了水,王敖《绝句》里的想象丰富了观察这个世界的向度——既丰富了世界,更丰富了语言。
不了解这些的读者如果急于从《绝句》里搜寻那些有关人生、现实的意义,难免失望而归。但正如开头所说,诗歌的音乐往往先于主题,神秘先于意义——诗人事实上并不具有教导我们认识现实的天职,他只有创造艺术以愉悦心性、磨砺思维的能力。当我们阅读一首诗的时候,优秀的读者并不执着于从其中获取什么说教或意义,而是寄希望于阅读的行为能带来精神的享受。在这个意义上,诗歌是对人类智慧的精心浪费,但无用之用有时候却又比一切所谓的真理更有价值,至少,它教会了我们如何更为愉悦地消磨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