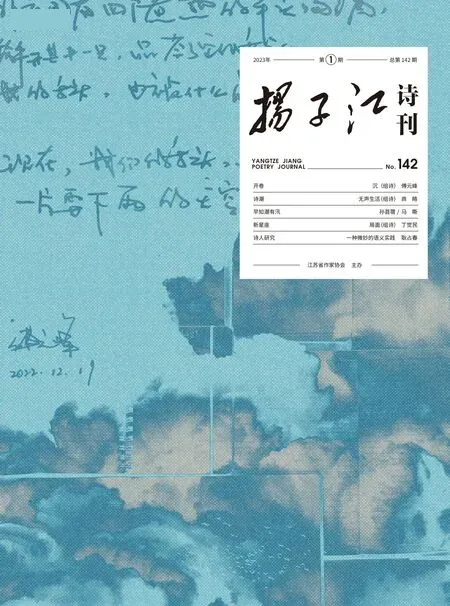凉风(组诗)
张进步
巨鲸散章·夜色之美
现在夜色朝上,朝下的则是
其他所有起起伏伏的事物
我不善于描写黑色覆盖下细碎的一切
但我想尝试描摹这种黑
像一尾大鱼的背部,那么苍健有力
像一棵古老的柳树,在它不愿发芽的冬日
但这都不是我想说的,我想说
——精巧的构思是不必要的
不信就看夜色下的一切,仿佛有序
但谁又看到了秩序到底在哪里?
只有夜色一直朝上,缓缓升起
为我们谋划着美学的一切原则
巨鲸散章·秋夜七弦
在入秋的灯下,我打开一扇窗
如同打开一本放置许久而未细读的书
闪烁其词的灯火:美妙的象形文字
藏在书页深处的几粒寒星,仿佛细鳞闪动
又仿佛是标注书籍页码的数字序号
每当我开始读它,幽深的形象
就会赶来,以一种庞然大物的身姿
巨鲸散章·风的回应
蟋蟀在回应,撞开静的领域
岸上时代,风成了呜咽者
再也不是那个有形的,能够一次次
号令波涛站立起来的创作者
灯火也在回应,以并非沉默的无声参与:
每盏灯都在捅破夜色,每捅破一次
夜晚的草稿纸上就多出一个0
现在你这个孤独的1,正站在岸边
或许这个岸边也叫窗前
此时你转过身来,在你身后排列着
无穷多的灯火,与你组成一个无穷大的数字
这巨大的数字即将成为遥远距离的隐喻
烙印
我庆幸在我十三岁那年看到了满天繁星
此后我的一生都在描摹。
我庆幸那年的蝉声曾点亮一个个夏夜的窗口
同时点亮的,有一双是我的眼睛。
让我抬头就看到
燃烧的石头,从此我开始在夜空低飞
我的航班总是准时到达,反复寄送的却是同一封信
并无地址,亦无署名
唯一的信息:火焰封缄纸张的烙印
这个春天
与春天一起到来的是各种各样的事物
当然不可能只有草木发出了嫩芽
我在念诵《心经》中入睡。三月底的空气
抽出了万物的鞭子,从我身体里抽出的
那一根,仿佛同时抽出了一条火辣辣的小路
三月底的空气,抽响了万物的鞭子
我的心同样发出了声音,比那鞭声更响
我看到一棵桃树在风中任性地晃动自己
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以为我们都被
大风摇动着,只是我想努力站稳身体
我不是那棵树。在风里,我无法像一棵树
那样肆意地抛撒花朵。在生命的丛林里
我紧张地想要抓住必将飘零的一切,当然
焦虑轰响着到来,像一场又急又乱的骤雨
我无法入眠,我念诵《心经》,但又不寻求意义
我身体里被抽出的那条小路长满了荒草
我用观自在的方式去梳理它们,菩萨
是一阵细雨:有无数根梳齿,令枝叶清晰
这个春天各种各样的事物都发出了新芽
生活的谜底止于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在大运河上乘船
天空昨夜刚给这条河送来过一场暴雨
在这崭新的一天,又给它带来了混血的蓝
即便如此,天空还是天空,河水仍是河水
两者界限分明,被一条窄窄的人间隔开
也许是担心人间正变得越来越狭隘
远处的青山用上了所有的力气:把天撑高一点儿
再高一点儿。但它们终究是大山
无论如何都不好意思削尖自己的脑袋:
一笔笔柔和的曲线勾勒出浓淡相间的墨色
当天色逐渐暗了下来,所有人类的大师便都失效了
野鸭大师在水上刻画的细节明显更为精妙
夕阳大师所运用的颜色也显然更加完美
连刚放暑假的微风都拿起了笔,在水面画鳞
嚯,整条河都开始摇头摆尾
一艘刷着红漆的大铁鱼也在这细波浪中穿行
经过几千年的虚构:把越来越沉重的巨大内心
挖空,令其漂浮,从而一步步涉足于未知的空间
——此时我正坐在整个人类的想象上……
凉风
只有这样的夜晚
凉风才会吹拂:
灯火零落,但永远有灯亮着。
与我相同或不同的生命
和我同在这个世上运用着加减法。
仿佛一不小心
我们就能听到
按动计算器的声音:
灯火是屏幕上明灭的数字。
那些大楼的轮廓
多像一个个生活的公式
在夜色里潜藏。
但这一切都不是凉风
应该关心的事情了。
和天上那轮混沌的月亮一样,也和此夜
蟋蟀们微弱的琴声一样
在这个中元节的晚上,秋天影影绰绰。
我静静地坐在南楼的窗前
感觉自己正在用跳动的心脏
一槌一槌地慢慢敲打着
这个略显沉默的宇宙。
秋日登两髻山
人一旦与山相遇
人就想比山更高:
至少要高出一个人的高度。
好在我还没养成这样的臭毛病
我怕累:我慵懒、多汗,爱坐在树荫下发呆。
在两髻山,我边走边歇
路过山泉,摘了山枣,在腐草上
还遇到过两只用口水写作的
粉红色蛞蝓。
它们先后向我传递过如下消息:
“此山野性、神秘。”
字迹未消,一只青虫
就从我手中的山枣里爬了出来:
冲出了果壳,但没能冲出宇宙
能冲出宇宙的,或许只有山顶发电的风车
一轮一轮地,在虚空中画着光圈
众山众树众鸟众虫
都匍匐着
压低了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