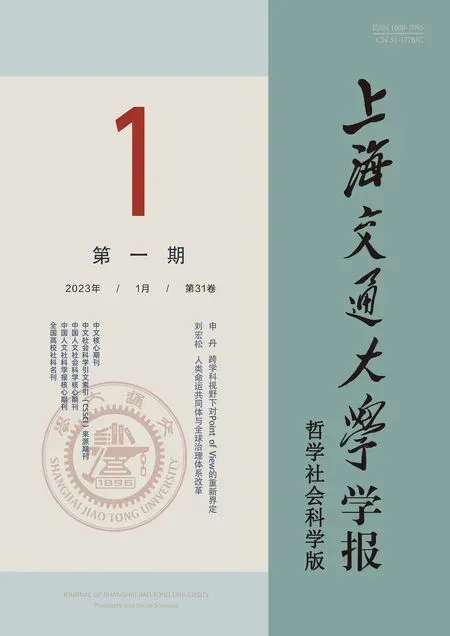论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的构建
刘 洋 王守仁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93)
作为文艺批评的专门术语,“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席勒的《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1795),席勒在该书中将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进行比较,指出“现实主义者受自然的必然性支配……他的知识和活动……会被外在原因和外在目的所规定”。(1)席勒:《席勒文集VI:理论卷》,张佳珏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5—156页。在法国,“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最早被用于具体文学是在1826年。(2)“现实主义”这个词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运用最早出现在Le Mercure du dix-neuvième siècle 1826年第13期第6页。如果把现实主义理解为一种基本创作方法,追求真实反映现实,则不难在19世纪之前的中外文学中发现许多相关手法具体运用的案例。1830—1890年间,现实主义发展成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潮流,一方面,它挑战了古典主义的艺术成规,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的主观性自我表现,抵制一切不现实的事物。由此观之,作为“时期概念”(period-concept)(3)R.Wellek,“The Concept of Realism in Literary Scholarship,”Neophilologus,vol.45,no.1 (1961),p.2.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在反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文学艺术思潮。
19世纪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时期。后世批评家凭借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创作实践,概括出现实主义客观性、典型性和历史性等具有辨识度的特征。20世纪,文学版图发生巨变,现实主义文学不再一统天下,在现代主义文学的冲击下,“现实主义已经过时”“现实主义枯竭”的论调一度颇为盛行。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解构中心、同一性、总体和绝对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开始流传并产生重大影响,声称要“真实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更是成为其攻击的标靶。与此同时,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建设滞后,未能回应世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种种质疑。进入21世纪,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消退,现实主义文学强势回归,文学批评领域也出现了“新现实主义转向”(4)J.Esty and C.Lye,“Peripheral Realisms Now,”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vol.73,no.3 (2012),p.276.,一批有影响的论著问世,从新的角度对现实主义进行审视和思考。
中文语境中的“现实主义”是从国外引进的术语。19世纪日本学者将西方的“real”和“realism”译为“写实”和“写实主义”。梁启超最早将日语的汉字词汇“写实”引入中国,1932年瞿秋白在高尔基现实主义文学的启发下注意到“写实主义”这个翻译的局限,提出将“写实主义”翻译为“现实主义”。(5)高尔基:《高尔基论文选集》,瞿秋白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第2页。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现实主义文学逐渐成为主流主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和革命文学最鲜明的色泽。但是,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出现了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趋势,公式化、概念化的应景之作削弱了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受此影响,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也出现了偏差,成为口号式的宣传工具,离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越来越远。“文革”之后,那种遵循“三突出”创作的作品无人问津,在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现实主义因其与阶级斗争政治的关联而为人诟病,几乎与“极左”“政治宣传”同名,处于边缘地位。
与此同时,随着国门打开,国外的文学、文化理论蜂拥而至,泥沙俱下,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反现实主义理论得到大量引介,众声喧哗,进一步弱化了现实主义的地位。各种外来理论在拓展了文学研究视野的同时,也严重遮蔽了文学理论脱离现实生活的真相和是非善恶美丑标准的匮乏。部分学者不再关注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复杂关系,而是照搬西方现成的批评理论,将其应用于研究对象,证明各种符码化抽象学说预设的论断。研究者在未进入具体文学文本研究之前,不是独立思考建构,而是首先在形形色色的外国文论中寻找肢解研究对象的工具。而现实主义理论本身未能与时俱进,缺乏应有的深度和活力,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如何直面问题,探赜文学的基本规律,梳理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的重要思想资源,溯源和甄别中西文学理论中现实主义相关术语和概念,考察和阐释其嬗变轨迹,正本清源,确立现实主义的本质内涵和逼近真实的主要路径,从零散的现实主义文学评论中梳理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并构建起相对完整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秉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精神,本文对国外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进行系统检点分析,同时充分汲取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养分,在对古今中外现实主义理论学说进行综合比较的基础上,建立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和话语坐标,考察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认知、审美、情动等多重维度,从世界各国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中找到现实主义的共通之路,关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从而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文学原理,建立起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新范式,为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建设作出贡献。
一、基本问题:现实主义文学是什么
“文学或诗学原理的首要任务是回答文学是什么,以及文学何为、文学何如等诸如此类的问题。”(6)陈众议:《文学原理学批评及其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3页。作为文学原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研究需要回答“现实主义文学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现实主义文学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文学与现实发生关联,对文学与现实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表现出有辨识度的基本态度、立场和倾向。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构建现实主义诗学体系的奠基石。
现实主义文学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文学艺术领域,现实主义首先是存在,然后才是理论,其重要的一个观察点是创作方法。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可追溯至遥远的古代,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也由来已久。广义的“现实主义”,是小写的“realism”,泛指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品。在西方,源自古希腊时期的“摹仿说”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初雏形理论。中国古代文论中“言”“象”“意”的审美意象也涉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陆机《文赋》的“穷形而尽相”、刘勰《文心雕龙》的“模山范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实主义基本创作方法的意识。
创作方法是作家艺术地认识现实、反映生活的方法。人类自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出现起,就开始运用一定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包含创作精神、创作原则和创作手段三个要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精神,指作者对客观现实的态度和观念,即追求作品与表现对象的相似程度,从以往文学作品的产生方式看,方法和手段取决于态度和观念,思想观念的变化促使方法实现转型,手段发生变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是真实反映现实,自觉或不自觉践行这一原则的作品可视为具有现实主义倾向或特色的文学,这一特征可以采取不同形态,但其内涵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作为具体手段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则是包容并蓄,多种多样,服务于作家反映现实的目的。就创作方法而言,现实主义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维度,具有丰富的内涵,构成了一个体系。
现实主义作为基本创作方法,适用于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同时具有历史性,即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解不能割裂其与历史的联系,不同时期、不同的文艺思潮使用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使其内涵不断丰富发展。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从首要的原理开头”,指出所有的艺术形式“实际上是摹仿”,而“惟妙惟肖”的摹仿可以让人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7)亚理斯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页,第11页。莎士比亚借剧中人物声称:演戏的目的是“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白居易则倡导“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要求诗歌面向社会现实。奥尔巴赫在其被誉为“现实主义文学史”的《摹仿论》(1946)中从文体风格入手考察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提出了“现代现实主义”(8)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76页。的概念,奥尔巴赫所说的“现实的再现”实际是指在创作手法层面的日常生活如何突破古典文学的文体分用原则,进入严肃的文学作品。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达到高潮,狭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是大写的“Realism”,专指1830—1890年间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19世纪的作家受当时科学思想观念的影响,尤其注重以细节描写的手法,对客观现实进行精准描摹状写,以期为读者带来视觉性或图像式的现实表征,使文本的虚构世界与现实生活中的生活世界达成同构关系。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后现代现实主义,作家关于现实的认知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创作手法进行实验,使现实主义向着更加多元化、多样化的形态发展。
文学原理研究旨在对重要文学思想进行历时性梳理和共时性观照,总结和揭示文学的基本规律。从基本创作方法的角度研究现实主义文学,为我们理解现实主义文学是什么提供了重要途径,并揭示现实主义绵延不绝、永葆勃勃生机的内在机制和原因所在。
二、核心概念:现实、摹仿、真实、虚构
概念是人类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的构筑单位,界定和阐释现实主义文学核心概念是构建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的基础性工作。一般性的文学理论论著不乏关于现实、摹仿、真实、虚构等术语的讨论,但将其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原理专门概念的系统性研究则相当欠缺,特别是这些概念的内涵外延处在不断变化、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必要从新的角度对其进行梳理、辨析。
(一) 现实
“现实”作为现实主义的理据根基,是其区别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美学原则的客观依据。在传统哲学中,它一方面指向主体基于感官和经验的切身经历,另一方面代表着“自足的,独立于主观意志且不受经验传统和理性认知框架束缚的客观存在”。然而无论从哪个层面看,“现实”所内含的主体经验性和外在超越性都揭示了概念内部不可化约的暧昧与矛盾属性。从中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司各脱,到启蒙哲学家笛卡尔,再到古典哲学家康德,他们不约而同地借助现实概念的不同分类(如本质现实、形态现实;形式现实、客观现实、主观现实;客观现实、经验现实)以弱化其内在的不稳定性。然而,当心灵、精神、无意识等内在性要素自19世纪末陆续被纳入现实的基本内容时,现实的内涵与外延便经历了持续的扩容与挑战,进而演化为拉康、齐泽克理论中最为晦涩与神秘的“实在界”——具有创伤性、令人无法直视且无法被表象的“未被扭曲的原始世界”。西方哲人理解与认知现实的进路也提示了现实主义概念百年来的脉动:由映射外部客观世界主导的现实转向关注内在精神生活的现实,从言说可言说之事到通过“歪像”斜目瞥见现实,现实主义在齐泽克、伊格尔顿笔下已经成为所有文艺作品的底色。因此,对“现实”概念的廓清与梳理,对于理解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嬗变具有意义。
(二) 摹仿
围绕艺术与现实之间精妙复杂关系的讨论在西方美学史上由来已久,从古典时代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的机械模仿论改造扬弃为再现式的动态摹仿论,进而将艺术从其无法效仿的原型中解救出来,到文艺复兴以来被艺术家们反复援引用以说明摹仿本质的“镜子说”,摹仿论的底层逻辑始终依托于艺术与现实这对关系的本体论认知,而这也正是现实主义文学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文学究竟是对现实世界的映照与复制,还是自有其内在逻辑,更接近莫泊桑提出的“幻觉论”或詹姆斯追求的“真实感”?奥尔巴赫、托多罗夫、利科、沃尔什、多勒泽尔等现当代学者将这一美学基本问题式重新演绎为文体论、象征符号学、认识论、可能世界理论的多种命题,在与传统摹仿论的对话中不断发掘新的诠释空间。不言而喻的是,动态、延展的摹仿论在当代理论话语的激荡下也推动了表征危机后现实主义概念的重新认知。
(三) 真实
求真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真切愿望,而真实反映生活更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根本所在。西方哲学视外部世界的客观本质为“真实”或真理的认识论由来已久,其中柏拉图的理式说与亚里士多德的可然律为人们把握形而上真实定下基于唯心和唯物的两个方向,并分别在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为真理之根本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以实践为获得真理唯一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中发展到极致。马克思基于实践的唯物真理观以主体能动性的实践打碎了主客分裂的形而上学真实,为人们理解真实打开了新的维度。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似乎从一开始就与真实牢牢绑定在一起,从《鲁滨逊漂流记》纪实文学般的标题、巴尔扎克《高老头》开篇宣示的书中讲述“一切都是真情实事”,(9)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第五卷,傅雷、何友齐、袁树仁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4页。到当代科幻小说被认为蕴含着“非真实的真实”,或将科幻视为“一种高密度的现实主义”,(10)参见Seo -Young Chu,Do Metaphors Dream of Literal Sleep?A Science -Fictional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1-10。真实的意义已然发生了变化,随之牵动着对现实主义概念及创作的影响。现实主义文学追求真实的根本在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实践性认识,即作家以忠实再现现实生活为其根本原则,不断通过革新写作手法来书写生活表象的本质,向读者呈现超越生活表象的深层真实。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取决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真诚态度,表现为作家对生活的深切感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自己体悟到的生活本质的忠实再现,是经验感知与理性认知的辩证统一。作家通过真实反映或再现具体的人同外部社会间的感性活动,吸引读者对文本描绘的现实发生认同,并通过反思式阅读获得对生活的深刻认识。
(四) 虚构
“虚构”一般被认为是与现实相对立的概念,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起,这一概念在后结构主义、可能世界、新历史主义诗学等理论思潮的冲击下,逐渐转化为与现实、真实相关的重大命题,大大拓展了现实主义概念在当代的语义场,值得深入探究。罗兰·巴特的“真实效应”虽然揭示了现实主义文本自我指涉的幻觉,但在托多罗夫、卡勒、伊瑟尔等学者看来,由于虚构缺少单一直接指涉物的事实,反而有助于理解指代的本质,正是这种缺陷让虚构找到了更丰富深刻的指涉方式——虚构制造了它所指涉的对象本身,在自我指涉的行动中指涉现实。可能世界理论认为事物可以有与它们实际存在不同的存在方式,现实是一个由不同可能世界组成的多元宇宙,不仅包括物理存在事实的总和,也包括想象的事物,因此遵循可然性法则的虚构世界尽管不是真实世界的表征,但是具有真值及本体论地位的实体。虚构不等同于虚假,对虚构概念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构建伟大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标准。
揭示以上概念的形塑过程及相互缠绕,需要从学理渊源入手,同时还要将其放在历史和时代社会的纵横坐标中,“一旦置概念于学术史和现实语境这两个维度之外,接近文学规律或文学真谛的努力也就被悬置了”。(11)陈众议:《文学原理学批评及其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4页。
三、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范式
现实主义的内涵丰富,其边界亦随着时代变迁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为揭示现实主义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文学批评理论需要从多角度、多层面对现实主义进行考察,主要遵循的路径有认知、审美、情动、跨媒介等,由此建构相应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范式。
(一) 认知
当代文学批评界在处理文学和知识的关系问题时常持消极或回避的态度:一方面,从文学中获取知识似乎有损纯文学自给自足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学所能提供的知识难免因带入了作者本人的主观看法而失之偏颇。在后结构主义理论崛起之后,文学与知识的关系遭受了进一步的瓦解——文学的指涉功能被限制在了文本本身。然而,现实主义文学追求真实反映现实,必然与读者身处的周遭现实紧密相关,并提供“真情实事”的信息。马克思充分肯定现实主义文学的认知价值,他把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和盖斯凯尔并列称为“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认为这些作家“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86页。现实主义文学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在讲述对生活的具体感受和体验的过程中描写人的生存境况,展现人性,揭示真理。作家采用的标志性手法是对具体细节的精细刻画,这种细节的铺陈为读者传递视觉性信息,读者通过“看”的方式接受现实,达到认知目的。另外,现实主义在转喻的层面上与社会历史现实发生关联:在转喻模式下,局部通过相邻性原则与整体建立关联,局部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同时代表整体,从而使得文本遵循相邻性原则与世界发生关联,组合为其组成部分,消解了语言与现实的鸿沟。以认识论为基础,我们可以建构认知批评范式。
(二) 审美
审美关乎对再现对象的价值判断和美学选择。17世纪荷兰画派开创现实主义画风,伦勃朗等画家以其精湛的绘画技艺创作日常生活的静物画和凡人肖像画,日常生活成为审美对象,在美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现实主义小说在“兴起”之初将中产阶级日常生活作为创作题材,关注最广泛并且最具典型性的社会人物与现象,扩展了古典主义文学再现的题材范畴。在随后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现实主义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审美对象——哪些现实值得书写,应该采用何种书写方式——是引发批评界争论的话题。卢卡奇在讨论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区别的文章中指出现实主义作品应该揭示出社会变革的重要发展阶段,呼吁现实主义作品叙述人的行动和活动,反对多着笔墨对日常生活和日常物品进行细节描写。(13)参见卢卡奇:《叙述与描写》,《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此后的现实主义审美批评多沿着上述两条路径展开:一方面,奥尔巴赫等批评者提出,严肃地反映日常生活正是当代现实主义发展的基础,从而重拾日常生活现实的重要文学价值;另一方面,在当代物理论和新物质主义批评兴起之后,曾被视为静止、无生命力、居于客体地位的物品重新得到了重视,其阐释的价值也被挖掘出来。审美批评构成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向度。
(三) 情动
现实摹仿冲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与认知世界之必需,在现实主义文本世界对真实世界的再现中,情动天然就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由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引领的当代现实主义批评的情动转向,拓展了情动的概念范畴,赋予了情动以肉身感知、动态势能与力量等特质,以与其他描述情感的术语相区分。詹姆逊提出,情动与叙事构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双生源头,从而将此前被忽略的深嵌于现实主义细节描写之中却无法被语言捕捉和表征的肉身感知纳入批评范畴之内;同时,詹姆逊认为共时性的情动破坏了代表现实主义朝向永恒现在迈进的历时性叙事,从而将现实主义发生机制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揭示出来,为现实主义批评引入了新的维度。对现实主义情动维度的探究须以现实主义在文学史中的发展为脉络,考察文学现实主义捕捉情感生存状态的内涵与方式变迁,从现实主义兴起时的社会情感结构入手,进而勾勒情动通过打破语言进入叙述的路径,讨论新时期情动表征受益于叙事技巧革新,将读者带入情动的“永恒当下”,再现情感主体间的流动与调谐。(14)参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王逢振、高海青、王丽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四) 跨媒介
当下学界兴起了跨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放眼世界,跨学科已经成为一种知识创新的共识”。(15)彭青龙:《知识体系创新、跨学科交叉与跨媒介融合——访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何成洲》,《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5页。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领域是跨媒介研究。自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论(16)参见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以来,媒介与媒介性一直是文化和文学研究关注的重点对象之一。而当下学界兴起的跨媒介研究范式则尤其应该引起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界的重视。从跨媒介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文学属于以印刷为主的媒体形式,文学艺术研究关注文本性是应然之意。面对带给观众/受者强烈的感官刺激和沉浸感的现实体验的虚拟现实等新媒介和新技术,现实主义文学应该保证和巩固自身独特的价值,积极有效地在认知、审美、情动等方面向读者传达现实感。与此同时,跨媒介研究涉及不同媒介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需要以学科交叉融合的思想为指导。伊恩·瓦特在其现实主义小说研究经典著作《小说的兴起》中就注意到理查逊、笛福以及法国现实主义与伦勃朗等荷兰画派追求“艺术细节的逼真和精确”的相似之处。(17)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0—11页。现实主义文学与其他文类和媒介的互动在跨媒介的时代背景和批评语境之下更易显露出来。菲尔斯基指出:“我们以世界为标准来衡量文学文本对真理的论断,但这个世界已经过了故事、形象、神话、玩笑、常识假定、科学知识的残羹、宗教信仰、流行格言等的调节。我们永恒地陷入意义的符号和社会网络之中,它们塑造了我们,并支撑着我们的存在。”(18)丽塔·菲尔斯基:《文学之用》,刘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34页。通往现实可以经由中介性的文学媒介,而跨媒介则通过混合、指涉、转换等方式提供更多渠道帮助读者抵达由意义符号构成的现实网络。学科交叉融合引领的跨媒介批评范式可以拓展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边界,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以认知、审美、情动、跨媒介等为线索,梳理现实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流变,可以发现,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现实主义文学并未固守一途以应无方,也并不存在单一固定的批评模式,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表现出复杂多样的发展态势。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各种范式并不具有排他性,而是相互渗透融通,互为支撑,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正是在这样一个思考、探究和实践过程中,批评范式得以不断丰富内涵、走向成熟、创新发展。
四、复数的现实主义
世界历史进程进入20世纪中期后,以卢卡奇、奥尔巴赫、巴赫金等的学说为轴心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和以巴黎—伦敦为地理坐标的现实主义发生地逐渐发生了变革和偏移,现实主义文学不再拘于一格,而是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复数的现实主义”一词出自克莉斯汀·布鲁克-罗斯的批评著作《不真实的说辞》(1983):“由于语言的表征本性,多种复数的现实主义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19)C.Brooke-Rose,A Rhetoric of the Unreal,Studies in Narrative and Structure,Especially of the Fantast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6.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现实本身变得愈加复杂多样,而现实主义作为以“摹仿”为核心表现手法的文学风格则必须相应地进行调整和重构。布鲁克-罗斯曾慨叹:“我们从未感到过,自己表意传情的手段是如此的匮乏,它不仅仅无法解决我们不断制造出来的问题,甚至无法解释这个世界。”(20)C.Brooke-Rose,A Rhetoric of the Unreal,Studies in Narrative and Structure,Especially of the Fantast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6.在不断变化、丰富的现实面前感到手足无措是20世纪中后期至今的知识界和文艺界的共同感受。2010年,大卫·谢尔兹在《真实的饥饿:一份宣言书》中提到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它的标志性特征是一种“故意而为的非艺术性”:“‘生’的材料,看上去未经加工,未经过滤,未经审查,也不够专业:也即是现实的诱惑和模糊”。(21)D.Shields,Reality Hunger:A Manifesto,London:Penguin,2011,p.5.在此背景之下,现实主义并未固守上述轴心和地理坐标,而是不断革新自己的表征手段,以期紧跟更新迅速的时代潮流。
“复数”体现在现实主义不断跨越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别边界,进入更丰富、多样的世界文学话语体系之中。现实主义批评家在美国当代小说家的作品中发掘出21世纪文学力量对19世纪现实主义的创新——元虚构现实主义、物质现实主义、量子现实主义等。2012年,《当代语言季刊》以《边缘的现实主义》为专刊标题,讨论欧洲中心之外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状况,内容涉及非洲、印度、爱尔兰、中国等。乔·克利里在开篇序言中提出,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史往往从其欧洲古典文学和中世纪文学滥觞写起,以描写中产阶级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为开端,至现代主义的挑战结束,鲜有论著跳出此框架。克利里指出了经典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不足之处:罔顾帝国主义扩张背景下的殖民地社会现实,依存于以巴黎—伦敦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和以英语—法语为中心的文学体系。当这一体系崩塌之时,部分现实主义作家转向了“边缘”,开始向上述体系之外流动:如英国新浪潮小说、印度进步作家运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等。甚至,现实主义在后冷战的历史背景下大有取代现代主义之势。(22)J.Cleary,“Realism after Modernism and the Literary World-System,”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vol.73,no.3 (2012),pp.255-268.2016年,耶德·埃斯特撰文《现实主义战争》,追溯在19世纪末期大英帝国霸权逐渐没落和20世纪中期美国霸权逐渐兴起期间学界对现实主义的两次批判热潮,提出后冷战时期由于世界政治格局转入全球化的发展潮流,现实主义正重新焕发生机,并与现代主义分庭抗礼。(23)J.Esty,“Realism Wars,”Novel:A Forum on Fiction,vol.49,no.2 (2016),pp.316-342.
这一“复数”现实主义的发展潮流推动了现实主义文学写作主体的多样化进程,也使得曾经不被纳入现实主义文学题材的社会现实进入了其表征的范畴之中,从另一个角度将现实推向了无边。诚然,以欧洲为中心的观察视角和写作方式难以把握错综复杂的当地现实,并因此容易造成殖民主义式的误解和误读。从传统文学形式中汲取灵感,以本土方式表征现实,也成为“边缘”现实主义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法国,学界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了重估与开拓,以加洛蒂为代表的学者对现实主义引入了更广阔的讨论范畴,并进一步探究当代现实主义理论对“摹仿”“虚拟与现实”“叙事与描写”等经典概念的再发展。现实主义逐步摆脱传统摹仿论、机械反映论的窠臼,明确了艺术与现实各自的独立性,走向了“适配说”“动态模仿说”“梦境说”等多元复调的理论模式。德语当代现实主义理论则结合后结构主义,形成了“破碎现实主义”概念,进一步消解历史文献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限,催生出自我虚构与文献小说两种新型文学体裁。俄罗斯的“新现实主义”作家在西方后现代主义以及本土各类文化思潮的推动之下,开始了文化内省进程,形成了文化重建思潮,对社会历史、文化进行解构与重建,并在此过程中体现了俄罗斯文学所特有的“内省”“反乌托邦主义”“聚合性”等民族思想内涵。在非洲,阿契贝、索因卡、桑贝内、恩古吉等对现实主义文学与非洲文学的适配性进行讨论,使得现实主义理论与反殖民、文化身份等产生互动,形成了具有非洲社会、文化特征的现实主义批评理论。此外还有以大江健三郎为代表的日本批判现实主义以及发源于朝鲜的主体现实主义等,都是我们应该考察和关注的对象。
就中国而言,虽然现实主义来自对欧洲文学的译介,但其在中国的扎根与发展却不是简单的翻译与文化移植,还离不开历史悠久的古典文论传统滋养。从概念来说,中国古典文论中很早就存在“实”与“虚”、“真”与“假”、“真”与“幻”等多对重要美学范畴。现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家也积极在题材、体裁、风格等方面展开探索与创新,力求忠实记录社会的发展。尽管许多作家的创作风格各有特色,但他们都追求以恰当的形式去再现宏大历史、描摹社会百态、书写日常生活,他们的作品注重的仍然是一种现实主义精神。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写实主义小说”或“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概念被提出,用来指称莫言、王安忆、刘震云、池莉、叶兆言、迟子建等人此一时期的作品,这些被冠以“新写实主义”之名的作品吸收了先锋派文学的创作技法,但本质上仍崇尚文学“直面人生关注现实的勇气和真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发展,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也处于不断变革之中,有研究者针对近三十年的创作提出“微写实主义”的概念,认为贾平凹的《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开启了当代中国“微写实主义”小说的两条路径,前者是一种描述型“微写实主义”,重在精细刻画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象,后者是一种分析型“微写实主义”,重在理性剖析日常生活或人物心理,无论哪一种路径,都是一种“极致性的日常生活叙事”。(24)李遇春:《从“现实主义”到“微写实主义”——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新潮探微》,《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12页。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给出的获奖理由是莫言“通过幻觉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近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界围绕“幻觉现实主义”的诗学特征、其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异同等问题展开探讨,拓展了对现实主义外延与内涵的理解。阎连科则在反思自身创作实践基础上,富有创见性地提出“神实主义”的概念,将其视作对西方传统现实主义的反叛与超越,并在《发现小说》一书中对“神实主义”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阐释。(25)参见阎连科:《发现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发现小说》现已翻译成法语,进入现实主义文论的发源地法国,体现出一种理论的反哺。
结 语
现实主义文学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同时,它的反映现实并不是对现实做机械的翻版,而是能动的创造,体现出认知和审美价值。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的构建,一方面是以中外优秀作家现实主义创作实践为基础,另一方面是批判性继承前人积累的中外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思想,对基本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对核心概念进行爬梳辨析,把中外的知识融会贯通,转变批评范式,从而实现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6)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21年5月18日,第14版。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开展包括现实主义文学原理在内的外国文学原理研究,正逢其时。毋庸赘言,现实主义理论内部存在悖论和争鸣,存在许多新的未知领域,有待我们去探索。立足中国,借鉴国外,从本土实际出发,胸怀天下,树立国际视野,坚定文化自信,我们可以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观点,突破固有的疆界,为构建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学术话语体系添砖加瓦,提供富有建设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