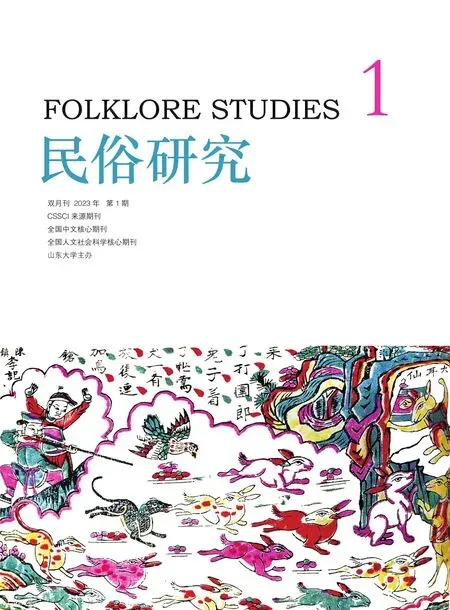文化转场、个人的非遗与民族共同体
岳永逸
非物质遗产既是一所医院,也是一支伴舞乐队:一个关注传统与社区生死存亡的严肃事业,一个服饰绚烂、灯光闪耀、旋律优美的筹款晚宴舞会。
——[冰岛]沃尔迪玛·哈福斯坦(Valdimar Tr.Hafstein)
一、制造出来的非遗
多年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以下称“非遗”),人们基本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公约”)的界定为准。(1)关于非遗保护公约的宏大意义,学界多有阐释,可参阅户晓辉:《文化多样性与现代化的人权文化——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个公约的政治哲学解读》,《遗产》2020年第1辑。然而,隐含了历史、政治、地方、个体复杂性和行动主体生命体验与情感的非遗,并非一个先在的东西,其能指与所指有一个生成的过程,内涵与外延有着人为的规定性。这使其作为一个语词和符号在不同时空、语境、人群的使用交流中,有着转喻和隐喻的可能。因此,暂时脱离抑或超越非遗保护公约的界定,直面那些标识为非遗和力求“非遗化”的文化事象——民俗,结合中国的实际与传统,我们会发现非遗始终有着作为一种技艺的政治属性。换言之,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实乃非遗的一体两面。以此,再审视下述问题就别有洞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何要推行非遗保护?其本身存在哪些悖论?这些悖论又为何是世界性的?中国的非遗保护该何去何从?怎样才能切实服务人民和文化强国的初心,并产生世界性影响?
毋庸置疑,非遗是一种文化。然而,当按照一定标准将之从一个文化整体中辨析出来,单独作为一个门类予以强调时,有了意识形态判断且暗含道德、伦理色彩的非遗,就已经演化为一种政治文化。进而,对非遗的申报、评定与保护也就在事实层面成为大小、层次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之间互动的政治技艺。在这一过程中,因共识或妥协而生的多元性实践在所难免。在所有政体科层制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中,非遗保护容易远离其原本试图呈现和强调的价值理性——人类文化的多元性,而日益呈现出褊狭的民族主义、保守的地方主义甚或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换言之,不同群体、不同名义、不同方式的利用、改造以及“创新”,使得非遗保护容易发生“文化转场”现象,并呈现出非遗“馆舍化”(2)王巨山:《遗产·空间·新制序: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岳永逸:《本真、活态与非遗的馆舍化:以表演艺术类为例》,《民族艺术》2020年第6期。或“馆舍非遗”的形态。
二、政治的博弈与技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非遗保护公约的缔结与推进的历史语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国际秩序重组、苏美争霸和最后美国一家独大的后殖民时代,这也是一个工业文明全面盛行,信息文明、数字文明迅猛来临而日新月异的时代。在此番国际格局的重组中,相较新生超级大国美国以及不可避免处于颓势的英国,曾经在西方世界自我优位的法国明显处于次等地位。自然,文化就成为不甘人后的法国欲重整昔日威风和在国际领域拥有话语权的一种工具。就此而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落户巴黎实非偶然。2003年缔结非遗保护公约时,英、美的同时缺位和至今缺席亦属情理之中。(3)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页:https://ich.unesco.org/en/states-parties-00024?,发表时间:不详;浏览时间:2021年12月12日。换言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的非遗保护,是不同政治集团、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之间斗争和妥协的产物,且与冷战思维下的民族主义、大国文化外交有着松紧不一的关联。在长期被殖民后独立发展的玻利维亚、韩国,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在非遗保护公约的缔结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均有其必然性。(4)Valdimar Tr.Hafstein, Making Intangible Heritage: EI Condor Pasa and Other Stories from UNESCO.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25-68, 73-85.事实上,效仿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非遗保护公约,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前者奉为圭臬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物质主义的一种反动,是对文化领域内既存西方霸权的挑战与冲击。
在中国,伴随经济发展,非遗保护公约借行政力量的嵌入,使“非遗”一词不但快速代替此前盛行的“原生态”,而且具有了与20世纪初的“民间”“民俗”一样的启蒙性以及在日常生活领域的革命性。如果不固守非遗一词在中国落户、安营扎寨的时间节点,而是将时限溯至清末,我们就会发现在100多年前那个被列强侵凌的岁月,已有不少被当今界定为“非遗”的中国技艺性文化在世界博览会上的亮相。1884年,中国音乐是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的主题之一。期间,除在中国展厅展陈了40多种中国乐器之外,有六名八角鼓艺人每天定时在展区的中国茶室、餐厅演奏,并应邀助兴英国权贵的社交。(5)参见宫宏宇:《晚清海关洋员与国际博览会上的中国音乐:以1884年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1915年,茅台酒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银奖。(6)参见黄萍:《从小偏乡到大舞台:茅台酒声望的拓展(1915-1935)》,《中国饮食文化》2020年第2期。1949年以后,周恩来指示成立中华杂技团,主要就是用中华儿女身体的极限美征,向世界展示新中国不屈不挠、奋力前行、睦邻友好的新形象。同期,凝聚着高超技艺、具有重要审美价值、在宫廷与市井乡野回环流转的景泰蓝、漆器、雕器、料器等现今被命名为非遗的手工艺品,不仅是创汇的文化产品,还是国家外交常用的国礼。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由何人选送,这些文化产品在世界舞台的亮相,不仅让参与者自豪,让国人振奋,而且至今都是相关技艺传承者的谈资,是申报非遗名录与宣传非遗时必然大书特书的光荣历史。这些并不久远的史实,意味着文化在传承、传播和交流过程之中,始终与政治保持着高度关联性。在传统意义上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不同国别之间对非遗资源的争抢,借非遗申报对文化主权的宣誓,更强化了文化的政治意涵、疆界与族性。不同国家或地区对某一文化事象的联合申报,同样有着相互妥协而政治结盟的因素。在此意义上,非遗绝非客观化而外在于政治的存在,其本质就是一种政治文化。
那么,又该如何理解非遗的文化政治的一面?在不到20年的时间,非遗保护在中国就成为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一种社会运动,成果斐然。事实上,从20世纪初的“民间”“民俗”,到21世纪初昙花一现的“原生态”,再到活力强劲的“非遗”,这一语汇变迁链表征着中华民族崛起的奋斗历程。这些意在唤起国民意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的语词的盛行,都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一环,其本身就是民族国家政治建设,尤其是国民精神重塑的关键点,有着不言而喻的政治属性。如果说在20世纪初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同到来的民间、民俗,标志着中华民族觉醒,是精英阶层眼光向下、到农村去、到民间去联手工农的誓言,那么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的非遗则是中华民族崛起的一座纪念碑,是21世纪的中国以平等之姿参与世界规则制定的一种象征。内向性与外向性兼具的非遗,全面代替以内向性为基本旨归的民间、民俗等语汇,就有着当下政治上的应然性。当然,非遗也赋予民俗以新意涵,即民俗不再仅仅是文化,还是需要主动继承并向外展示的优秀民族文化遗产。(7)在众多类别的非遗中,近代中国以来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民间信仰尤为敏感。与高丙中一样,李华伟也认为非遗保护运动赋予了民间信仰以新的生机,其文化意涵得以有限还不乏善意地认可。但是,在强调民间信仰被整合进大传统的同时,李华伟更意识到因为非遗化的民间信仰强调的是地方性与特异性,而存在潜在的解构功能。陈进国则注意到为融进非遗序列,民间信仰弱化其宗教性而强化其遗产性的谋略与技艺。参阅高丙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的民间信仰》,《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李华伟:《正祀与民间信仰的“非遗化”:对民间信仰两种文化整合战略的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陈进国:《信俗主义:民间信仰与遗产性记忆的塑造》,《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5期。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政府对非遗保护运动持续地大力度投入。2020年,教育部正式将“非遗保护”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归类在艺术学之下的“艺术学理论”,代码为130103T。(8)参见光明网:https://m.gmw.cn/baijia/2021-03/01/1302141041.html,发表时间:2021年3月1日;浏览时间:2021年12月25日。值得关注的是,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情绪的簇拥下,非遗进一步激活了传统文化意识中的家国情怀与天下意识。如是,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自然而然,乃至兴起文化自觉与自救的书写浪潮。(9)诸如魏小石:《民歌笔记:田野中的音乐档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格桑卓玛编著:《喜马拉雅童话》,西藏人民出版社,2020年;巴晓光:《诸神的游戏:中国福州龙舟的传统与禁忌》,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年;罗易成:《求同存艺:两岸手艺人的匠心对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一苇述:《中国故事》,晨光出版社,2021年;严优:《诸仙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与之同步发生的是,自上而下推进的非遗保护运动也成为社会治理中有效的一环。
因为制度性的强力推进,非遗保护运动产生了海量的就业岗位,广泛涉及行政、传媒、出版、科研、文旅、博物馆以及乡建(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行业。行政方面,从文化和旅游部的非遗司,到其下线的文化馆、群艺馆、非遗保护中心、非遗馆、非遗传习基地等诸多单位,都有着大量的职位。传媒方面,非遗版块已经全面覆盖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影视传媒。出版业方面,与非遗相关的志书、丛书、音像等电子产品连绵不绝。科研方面,许多高校都设有非遗研究机构,研究生、本科生招生正在大举推进,关于非遗的专业期刊和期刊的非遗专栏同样稳步增长。文化和旅游部主管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杂志已经于2020年创刊。在消费层面,不少民俗旅游易名为非遗旅游,旅游目的地也相继建立非遗体验馆、展览馆等。因横贯多个行业的“非遗业”,包括各级非遗名录的传承人在内的“非遗人”已成为一个新生的职业群体和身份标签。
在极大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非遗也起到了振奋国民精神的作用。不过,非遗在强化文化自觉、自豪与自信的同时,也促生了某种画地为牢的文化自恋,以及将非遗对象化、他者化后而生发的浪漫想象。政治、经济与作为文化基因的家国情怀的合力,使得非遗保护运动从原本意义上以非遗传承人或传承主体为核心的日常行为,转型为多个异质性群体广泛参与的全民事件,以致有了能同时实现非遗内、外价值的可能。(10)参见李向振:《作为文化事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外价值实现》,《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因应信息时代的多介质,非遗原本内敛型的社区传承、群内传承、师徒传承、家族传承、性别传承,逐渐向着开放、散点、多元、不拘一格的社会传承迈进(11)这应该是当代社会非遗传承的共性,日本已发生了这样的转型。参阅王晓葵:《现代日本社会的“祭礼”——以都市民俗学为视角》,《文化遗产》2018年第6期。,甚至还出现了虚拟空间的虚拟传承。在此过程中,“婉饰”(euphemism)非遗、“制造”非遗的现象在所难免,产业化发展也理所当然。
随着以活态传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主流话语为托词的非遗产业的兴盛,原本与传承主体的日常生产、生活、生计一体的非遗,便不可避免地会与原境(context)有所脱离。与此同时,非遗传承人也同步被非遗“物化”,而呈现出一种无我无人、惟国与艺的非遗叙事诗学与神学。在事实层面,有形、无形的非遗产品必定成为凸显历史悠久、文明厚重的国家符号。湖北黄石道士洑村的端午节,就是在非遗化过程中与历史文化英雄屈原紧密结合,而升位于民族层面、国家层面以及世界层面。(12)参见宋颖:《端午节:国家、传统与文化表述》,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26页。在表述层面,如同山西洪洞羊獬三月三接姑姑的非遗叙事那样(13)参见周希斌主编:《尧舜之风今犹在》,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往往凸显在艰难岁月甚或生计无着的窘境下,如何大无畏地传承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曾被否定的皇权政治、帝王趣味,也化身为诸多非遗叙事浓墨重彩的要素或亮点。
就总体而言,非遗作为社会治理技艺,是作为文化政治的非遗保护运动的必然结果。它使得非遗保护运动成为一种润物无声的教化工程,成为一种有效统合文化、整合社会、整顿社区以及凝聚人心的工具。与此同时,作为社会治理技术的非遗保护运动,还凸显了另一个悖论:非遗保护公约中所强调的个性、地方性、多样性,与申报过程中凸显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之间的难以通约,而在逐层申报制度中被过滤掉的,可能正是非遗保护公约试图要强调的地方性与多样性。
三、馆舍非遗的镜头美学
众所周知,非遗保护公约的缔结,日本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中国非遗保护运动的迅猛展开,与韩国江陵端午祭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紧密相关。部分国民因“端午”两字对韩国江陵一个地方性庆典的误读,大大激发了各阶层国民的爱国主义。有关政府部门快速介入,将非遗迎请进来,积极顺应国际潮流并致力于中国特色保护方式的探索。
从申报的角度而言,中国非遗保护运动是自下而上推行的。随着行政规章、制度的日渐完善,非遗的相关申报条件日益明晰。有着终决权的评审专家、行政官员,可能早先会有走马观花式的调研,但就总体而言对申报项目本身并不熟悉,因而只能根据申报材料与从非遗保护公约而来的政府文件的匹配度、根据申报材料的完美度和个人主观判断进行裁决。由此导致的非遗申报书的形式化、标准化,使其很快成为一种特征鲜明的文类。其中,申报项目的历史演进、传承谱系、精湛技艺、社会影响与效益等不可或缺。当一拥而上的申报者都想分得非遗政策红利时,申报条件就日趋复杂,诸如挂靠单位、法人、图片、视频等等,各有要求。
非遗多是前工业文明时期的产物。虽然有着官民互动的回环流转,但散乱、碎片式的非体系化,以及因时、因人、因地而异的个性化,是其普遍特征。1931年,定县平民教育运动发现的秧歌艺人刘洛福,被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派送到北平演出,引起轰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当年能在城乡游走的名角,其生卒年也不详。在传说叙事中,人们将定县秧歌的发生与曾在此短暂为官的苏东坡连接起来。按照当下申报文本的要求,需要将这些散乱、口耳相传的知识逻辑化、精细化,由此形成了对非遗的神化趋势。
首先,谈及非遗源起,必坐实传说中的人物。相声行当的祖师爷“穷不怕”朱绍文的生平,就是随着非遗保护运动的展开而更加清晰的。其次,非遗申报时必渲染创始者的伟力。再次,强调申报项目与上层文化,尤其是宫廷文化、皇权政治之间的关联。如北京的太平歌词、双簧等,都会强调与慈禧太后的渊源;中幡、掼跤会等强调其从宫里出来的高贵出身;与妙峰山庙会关联紧密的诸多香会,则会追溯其“皇会”基底。最后,都会对传承谱系的连续性予以强调,并由此强调文化大革命期间非遗活动的困厄。如不少申报文本都强调,在此期间人们如何大无畏地将神圣物饰藏匿起来,并暗地里举行仪式等等。如此,非遗申报文本就标准化地呈现了中华文化的上下一体性和历史演进的连续性。但与此同时,非遗本身与践行者-传承者、体验者-观者/消费者-享用者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生命体验、情感和心性之间的关联反而被淡化了。
非遗保护是被地方政府纳入行政管理系统中的,因而在申报成功之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就成为考评的新杠杆。文化遗产如何转化为文化资产、文化资本,直至最后的文化产品,就极为重要。
从报刊、电影到电视,从商家推出的各类节目到直播带货,从相片到VR,当代社会早已使视觉“癌变”,并“依据事物展示或被展示的能力来衡量其真实性”。(14)[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1页。特别是对于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而言,在固定的空间展陈种种非遗物象,不但反讽式地强化了非遗的物质性——使非遗成为可视抑或可读的,活化了异质时空——“房舍”的非遗,迎合了都市人对乡野桃花源式的浪漫想象,对于慢生活的追求,以及象征性的短暂拥有。美轮美奂的镜头化非遗、百科全书式的“馆舍非遗”大量出现,即以此为背景。
在利奥塔那里,“房舍”是与都市文明相对的乡村文明的代称。(15)参见[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5-221页。然而,在呈现房舍与大都市整体性对峙的同时,利奥塔反而忽略了二者并非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互相投影、呈现的涵盖关系。从空间形态而言,作为房舍对立面的“馆舍”,或者能更好地体现利奥塔“大都市”的隐喻与转喻。落实到非遗层面,馆舍(化)非遗并非是对先在的房舍(态)非遗的置换,而是退化与蜕化兼具的覆盖及更新。
就字面意思而言,房舍是作为生计、行当、人际交流、伦理阶序以及审美情趣的被非遗化前的地方文化的传衍时空,低矮、粗鄙、素朴、“道阻且长”等是其基本的外在形态。馆舍则指的是博物馆、展览馆、民俗馆、非遗馆、会所、礼堂、剧场、图书馆,以及学校、机场、火车站、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有着围墙(有形或无形)、闸机口、智能扫码系统以及人脸识别系统等门禁设置而专门展演非遗的场域。虽然在管理学意义上是全开放的,但处处设防且镜头密布的馆舍,明显标识着进入者的阶层、阶级、身份地位以及品味。诸如在地的传承人、大中小学生、公职人员、外来探寻文化或到此一游消费文化的有闲阶级,等等。
按照都市文明的标准,馆舍的外在物质形态较之房舍更为光彩逼人,其摆布设置颇有讲究。离地、离土、离人,馆舍构拟的是一个带有真实性的镜像空间,在无所不能的电脑时代,通过声、光、色、电、影、模拟态等多种配置,当下的馆舍俨然电影实拍地。在进入其中的瞬间,观者就不由自主地成为大型实景演出的演者。
当然,馆舍也完全可能藏在都市某个远离喧嚣的角落,或如北京天桥印象博物馆一样,在闹市地下蛰伏。(16)参见岳永逸:《“土著”之学:辅仁札记》,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252-265页。因少人问津,即使身处闹市,这些馆舍仿佛都市中的房舍,还叠加了“心远地自偏”的桃花源意象。反之,诸如2009年晋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侗族大歌等,原本就是在乡野的房舍非遗,此时与旅游目的地开发经营配套,除增加导演精心设计、依靠声光色电等电子技术增色而一劳永逸的大型实景演出之外,还有智能扫码系统的闸机口快速跟上。基于“游客凝视”的消费主义美学,运用视觉性生产机制,景观生产者将房舍馆舍化,在当地民众和游客之间塑造出对视——互看与被看,当然也是因陌生而群体性地相互窥视的表演性社会舞台。(17)参见刘晓春:《当代民族景观的“视觉性”生产——以黔东南旅游产业为例》,《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3期。虽然这可能反向地强化了在地的民族特性,但馆舍化的房舍俨然成为嵌入乡野的不夜城、游荡在青山绿水间的“本土异域风情”(18)[德]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9-123页。。
如果说馆舍的房舍化,象征了都市人因疲惫不堪而生的逃逸形态、心态,那么房舍的馆舍化在呈现都市文明规训乡野的强劲的同时,也展现了乡民提升自己的诉求。换言之,作为兼具“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19)[美]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45页。的里程碑和“记忆之场”(20)[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99页。,林立的都市-馆舍与乡野-房舍是相向而行、相互涵盖的,表征着当下技术世界“地点的统一性”(unity of place)(21)[德]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0-93页。,以及在这种统一性地点中的大众生活的同质性。某一项地方文化,在列入非遗名录、得到政府认可之后,它必须进一步呈现其非遗性质。显然,非遗性质的凸显,难以由拥有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单独完成。于是,文化经纪人、文化商人很快就捕捉到商机,加速了非遗项目在不同舞台、镜头、荧屏的呈现。在全媒体时代,一旦进入代表人类一切的眼睛(22)参见[美]巫鸿:《陈规再造》,郑岩编:《巫鸿美术史文集》(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5-170页。之镜头美学领域,服饰、道具、声音、体态、神情、光、色等各个方面均需迎合大小导演、摄影师、照相师以及潜在观者的嗜好。这又使得似有魔力的镜头反向支配了一切,成为能动的行动者。(23)参见富晓星:《作为行动者的摄影机:影视人类学的后现代转向》,《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
就这样,非遗及其传承、表演与经营的主体——人,都被镜头支配。在大小镜头的注视下,所有的非遗在高度整合而同质的空间中,成为时尚的“表演的艺术”和过滤掉粗粝的“萌文化”,(24)刘文嘉:《别无选择》,《读书》2022年第2期。走上了一段肤浅的美学化历程。土家族毛古斯在搬上舞台后,原本与生命节奏、生活韵律一体的文化旨趣被镜头荡涤得干干净净。(25)参见王杰文:《论民俗传统的“遗产化”过程:以土家族“毛古斯”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在此情形下,以观和被观为核心重组的当代节庆,哪怕是有着厚重底蕴和民意基础的春节,也因为丧失了与个体成长的关联而淡乎寡味,“年味越来越淡”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感受。
毫无疑问,当非遗仅仅是在观与被观的关系体、连续统中存在时,就已经脱离原境,脱离与之相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丧失其原本因“匮乏”而生的远乡近邻的交际、维系情感的创造性、审美性、宗教性(至少是神圣性)、娱乐性与游戏性。(26)参见郑长天:《瑶族“坐歌堂”的结构与功能:湘南盘瑶“冈介”活动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41页。转场后被展陈的非遗可能是美的,但因外在于人,与个体生命体验无关,也就只能指向外在的形式美。
值得警醒的是,在被纳入不同级别的非遗名录之后,国家财政会给予非遗项目、传承人一定的经济支持。级别越高的非遗项目,实力雄厚的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就越多,这多少会滋生传承主体的惰性。原本是助力活态传承的“陪护”,反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非遗传承的阻力。
四、呈与发的传统
其实,申报、批复、评估之流程,并非是现代民族国家行政的产物,传统中国就有这样的行政传统。如同当下位列非遗名录之后,地方常常会将之转化为非遗馆、非遗传习所、工作坊以及巨型雕塑等人文地景,甚至将之节庆化一样,在传统中国遍布乡野的乡贤祠、贞节牌坊、神庙以及高耸的石碑,多数都是地方精英申报而得到朝廷敕封之后,将文字、叙事再度转化为具有纪念碑性的人文地景。
清初,像颜元这样“乡里的圣人”,一个在地方有着好口碑的读书人身后要位列乡贤祠,同样需要由地方上报朝廷,得到恩准。可想而知,朝廷的赐封又加速了后世地方精英对相关传说的再生产。(27)参见王东杰:《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86-202页。当然,正如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江西德化县万衣入祀乡贤祠的申报流程(28)参见牛建强:《地方先贤祭祀的展开与明清国家权力的基层渗透》,《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那样,呈报批复的程序严谨而繁琐。到清雍正二年(1724),入祀的乡贤必须上报礼部复核,最终由皇帝拍板。如同光绪年间山西洪洞刘志入祀乡贤祠呈报的各类文献(29)参见常建华:《捐纳、乡贤与宗族的兴起及建设——以清代山西洪洞苏堡刘氏为例》,《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那样,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更是繁杂。
在推进儒学社会化的过程中,明清两朝设置了日渐严密的源自圣贤的五经博士和奉祀生制度。一旦获得这两个头衔,就意味着与之相伴的祠宇、祭田、地位和新身份“乡贤”的获得。这些实际利益,引发了与有子、左丘明、子张、曾子等圣贤有关的后裔承袭、争袭和冒袭案。在争夺过程中,祠庙、志书、庙神碑、家谱、家书等作为证据,纷纷被制造出来。事关地方声誉,地方官员不得不卷入到圣贤后裔申报与朝廷审查定夺的繁琐程序之中。由此可知,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与制度设计是促成家族兴旺的关键因素,所谓乡贤未必根植于“乡”,更可能来自于“国”。(30)参见贺晏然:《圣贤与乡贤》,《读书》2022年第10期。其实,妈祖等神灵也是通过地方士绅对其护佑一方的灵验事迹呈文上报,而得到朝廷赐封,纳入正祀系统,才从一个地方小神成为弥漫全国的大神。(31)参见[美]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6-101、126-159页。这种对地方性神灵的敕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将“淫祀”标准化抑或说正统化的治理术,一直持续到清末。光绪十九年(1893),在经过地方士绅以种种灵验事迹申报并上达朝廷之后,河北井陉苍岩山的三皇姑被敕封为“慈佑菩萨”。
对忠孝节义,尤其是贞节妇女的这种呈文、旌表褒扬的制度在1918年还存在,且是官方《褒扬条例》的核心内容之一。这让胡适倍感愤怒。(32)参见胡适:《贞操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在20世纪末,因为庙首老王的能干,陕北榆林一个小乡村的黑龙大王庙为寻求其存在的宗教合法性,在经过申报后终于成为政府认可的道教活动场所,因而在庙门口悬挂上了市宗教局颁发的龙王沟道教管理委员会的牌子。(33)Adam Yuet Chau, Miraculous Response: Doing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224-225.简言之,尽管皇权不下县,但地方士绅有写申报公文及报表的传统。在进入与工业革命相伴的民族国家时代之后,上传下达下报上批的频率越来越高。但是,由于现代民族国家政权的内卷,行政效能并未有明显改观,以致于成为“公文的处理,档卷的庋藏”(34)李安宅:《论语言的通货膨胀》,《文化先锋》1945年第5卷第15期。。
中国自古就有采风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明显有着采风遗韵。征集令得到各地不同层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响应,并要求所属学校奉此合行、遵照办理。这一自上而下的采录传统——采、报、批、建(刊载)——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1958年,学者就民间文学采录工作,提出了“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的十六字方针,并延续到了30年后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35)参见毛巧晖:《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学苑出版社,2018年,第72-79、127-130页。显然,采风不仅是文明的生成方式,更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生产机制。(36)参见祝鹏程:《采风:一种文明生成方式的古今流变》,《民俗研究》2022年第5期;《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机制的采风》,《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换言之,作为手段的采风,是目的也是形式和内容。在其自上而下的展开过程中,它也成为一种具有支配力的意识形态。
一目了然,申报-批复的公文书写传统并未因社会变迁、政体变化而断裂。受工具理性的支配,学界对非遗保护运动的释读、建言大致是以学术之名发挥其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配合作用。而就非遗保护而言,学界基本是秉持本真性的原境(生态)传承-社区传承与创造性的活态传承-社会传承两种观点,并争论不休。(37)参见吕微:《社区优先还是社会优先?——民俗学的逻辑出发点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修正案”》,《民俗研究》2021年第3期。其实,这两种观点异曲同工。
本真性原生态论大致持保守主义与复古主义的立场,将非遗视为静态与恒定不变的,主张不要用过多的外力去干预。但是,随着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引入、交通的便捷、人口流动的加剧、信息交流的快捷与多元,原境生态保护几乎没有可能。诸如曾经热闹一时很快就门可罗雀的贵州隆里生态博物馆等,就是明证。如前文言,生态博物馆本质上是展演性的,它迎合的是外来他者对自身镜像的投影,以及当地拥有决断权的强势群体(新乡绅)对外在世界的臆想、模仿。活态论则莽撞抑或说乐观地秉持“发展就是好的”之幻象,一厢情愿地认为非遗应有因时应景的变化发展。这种观点不但忽略了非遗的“内价值”(38)刘铁梁:《民俗文化的内价值与外价值》,《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还容易将非遗剥离传承主体而工具化、庸俗化、舞台化、表演化。
于是,与非遗研究有关的海量写作,也大致是以下八个版块的不同配置与排列组合:1.非遗的概念;2.非遗的理论与政策;3.国际经验,尤其是近邻日本与韩国;4.非遗化前的原态;5.非遗化;6.非遗化后的新态;7.现状弊端和建言献策;8.理想愿景。这些“八股”式的写作促使非遗一词成了意味着“先进”的霸权话语。可是,正如说书、八角鼓、京剧、评剧等百戏和玉雕、牙雕、根雕、陶器、云锦等制作技艺一样,(39)参见[美]巫鸿:《陈规再造》,郑岩编:《巫鸿美术史文集》(卷三),郑岩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71-287页。当下被称之为非遗的这些文化事象,始终是在不同时空、群体、阶层之间流转,并不断发生着量变或质变的。
当非遗常态性地为他者在馆舍中展演时,其可持续性、良性传承就难以实现。鉴此,我们必须直面下述问题:1.非遗为何?为何保护?怎样保护?2.谁的非遗?谁在舞台中央?3.谁应该在舞台中央?谁真正在舞台中央?舞台又是谁的中央?
五、复数非遗,涵盖公活的出作
如果将文化视为一种资源,那么从其所有权的角度而言,文化可分为四类:1.私人所有(private property);2.特定成员组成的社群共有(communal property);3.国有(sate property);4.非任何个人或群体所有的开放性资源(open access)。(40)David Feeny, et al.,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wenty-Two Years Later”, Human Ecology, Vol.18, No.1(1990), pp.4-5//1-19.在非遗化过程中,被称之为非遗的文化已经被资源化,(41)参见[日]岩本通弥、山下晋司编:《民俗、文化的资源化:以21世纪日本为例》,郭海红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年。而且是整体性地发生了从前两类向后两类的转换。换言之,非遗保护运动是促使相对的“私有”让渡于相对的“公有”,促使“大我”包裹“小我”,促使与“小我”密切联系的社区传承、群内传承、师徒传承、家族传承向着散点、多元、不拘一格的社会传承转型。(42)当然,也不乏社区传承盘活非遗的例证。参阅杨利慧:《社区驱动的非遗开发与乡村振兴:一个北京近郊城市化乡村的发展之路》,《民俗研究》2020年第1期。当然,这样也易导致对作为(开放性)共有资源的非遗的争抢,引发“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43)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162, No.3859(1968), pp.1243-1248.。
显然,在交通便捷、交际频繁、传播手段多元且日新月异的当下,想固守一方、一群、一地的文化已经几无可能。保持自身特色或者说独特性的变,才是最佳选择。对于非遗的有效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回归生活日常,回归传承主体——文化享有者那里,将其还原为可以支撑人之“生”、与个体生命、感受、体悟紧密相关的“非遗”。换言之,要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使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真正成为可持续的有源之水,就有一个如何促使“大我”内化于“小我”、“小我”反向涵盖“大我”的辩证施策问题。事实上,如果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并直面资源化的文化本身,就会发现这种辩证法原本就一直存在于自上而下的非遗化的过程之中。它使非遗呈现出复数形态,而且正是“非非遗”的形态在支撑着非遗形态。
五四歌谣运动时期,参与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学者大都对民俗的传承主体有所忽视,将“俗”从“民”那里剥离开来。这使得原本意在启蒙的五四歌谣运动,基本止步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作为亲身参与者,钟敬文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意识到:歌谣运动与民众的隔膜、对社会意义的疏于了解,使得歌谣运动的好些工作“差不多白费”。(44)钟敬文:《民间艺术探索的新展开》,《钟敬文全集·14》,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29页。同样,杨堃也曾将周作人领军的“文学的民俗学”和顾颉刚担纲的“史学的民俗学”的失败,归于并未真正与民间、民众日常生活发生关系。(45)参见杨堃:《民俗学与通俗读物》,《大众知识》1936年第1期。大致同期,传教士司礼义也鲜明指出:中国民俗学同行并未对民俗本身“投入全部心力”。(46)Paul Serruys, “Children’s Riddles and Ditties from the South of Tatung(Shansi)”, Folklore Studies, Vol.4(1945), p.214, pp.213-290.
事实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上述不足,在今天的多数非遗调研活动中亦有延续:忽略了要非遗化的文化事象的内价值——对于民众生活世界的意义。服务于非遗申报和保护工作的短平快的调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非遗保护运动中张冠李戴、挪用以及编造、拼贴的不正之风,及至造成财政浪费。事实上,一旦将非遗视为情感对象,基于长期田野调查的非遗,就在调查者眼中呈现出另一种丰盈景象。
为完成学位论文,赵雪萍对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天津汉沽飞镲作了持续年余的调查。她以给合作者孩子义务辅导功课等生活交往方式,“以心换心”地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47)参见赵雪萍:《公活与出作:汉沽飞镲的田野考察》,北京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4、130-132页。2018年7月13日,在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举办的“仰望非遗——京津冀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研讨会现场,当着与会者的面,汉沽飞镲天津市级传承人刘洪生称许赵雪萍说:“这孩子,和记者、专家不一样!没把我们当外人,没有看不起我们。很多人来了,打一头就走!给他个苹果,擦了又擦。小赵不一样,给她苹果,拿着就啃。”因为有这样的情感认同,赵雪萍叙写的汉沽飞镲,也就呈现出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更为繁杂的文化风貌。
历史上,飞镲在被用于渔业生产的同时,还承载着渔民和盐场盐工的精神生活及诉求。汉沽飞镲传承的时空,不仅是当地渔闲时的日常生活,也包括年节、农历四月的迁西景忠山庙会等非常时节,还在改革开放后,快速融入到当地的白事之中,成为丧仪必备的仪式符号。当地新生方言“出作”,就被用来指代白事时的飞镲表演,其中熔铸了人们对生者和死者关系的理解和对死亡的敬畏心理。(48)参见赵雪萍:《公活与出作:汉沽飞镲的田野考察》,北京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8页。此前,汉沽飞镲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丰厚意蕴与多元表达状况,并没有被“八股”式的非遗写作准确认知。汉沽飞镲在非遗化之后,在传承主体那里很快就诞生了“公活”一词,专指以非遗名义进行的展演活动。作为“公活”的汉沽飞镲展演活动,参与者除了传承主体之外,媒体精英、评审专家、文化经纪人等纷纷参与进来。在媒体报道层面,“公活”一词完全替代了此前使用多年的“出作”。其实,在传承主体的生活世界中,汉沽飞镲包括了相互依托又相互影响的“出作”和“公活”两个部分、两种类型,明显大于非遗“公活”的能指和所指。此后,伴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展开,脱离原境的汉沽飞镲表演更加倾向于展示侧重技巧与美观的技术性动作。
与汉沽飞镲当下传承类似的,还有2006年跻身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河北定州秧歌。在非遗化的定州秧歌叙事中,在红白喜事中操演的“挡小事”和在庙会上演出的“唱台口”都被排除在外。然而,正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地方经济发展大潮中,定州秧歌以“挡小事”“唱台口”等方式,有机融入当地人生仪礼之中,为其后来的非遗化奠定了基础。当然,非遗化也使得定州秧歌与汉沽飞镲一样,衍生出了专门作为非遗演出的类型,如配合摄影师拍摄、学者和评审专家调研、政府部门安排的送戏下乡及汇演与竞赛等。这些与非遗相关的定州秧歌复数多元的文化风貌,同样是定县人谷子瑞持续调查两年的收获。(49)参见谷子瑞:《从乡村戏到非遗:定州秧歌百年小史》,北京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18-120页。
充分尊重传承主体,深入体会其关联日常生活的神经末梢,自然就会发现“出作”“挡小事”“唱台口”等在非遗诗学中难以描述到的地气、生气与人气。尽管非遗化确实可以为具有调适能力的某种文化事象提供了衍生新类型的可能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不是非遗化的“公活”而是“出作”“挡小事”“唱台口”等文化形态,将这一文化事象与大众生活形成牢固连接。只有让非遗回归日常生活,关联个体生命价值,非遗语境下的非遗研究才有可能实现突围。
六、支撑人之“生”与筑牢民族共同体
文明是一种进程,而非一成不变的标准。(50)参见[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与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人们讲故事的方式,促生了新闻,繁荣了小说;照相术不但快速影响了人们对宏观宇宙和微观世界的认知,还日渐改变了众生的视觉和对空间的知觉。(51)参见[德]华特·班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班雅明精选集》,庄仲黎译,商周出版,城邦文化出版,2019年,第325-362、167-191页。经历三个多世纪的传播、弥漫,从欧洲到美洲再到亚洲,作为镜和镜头的“捕获物”的世人,对自己呈镜像态的“物化”“异化”状态早已习以为常。(52)参见[美]巫鸿:《物·画·影:穿衣镜全球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无论是鲍辛格对与技术世界水乳交融民间文化的诠释,还是航柯对民俗的再定义(53)参见[芬]劳里·航柯:《民俗过程》,刘先福、唐超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第4期。,都在说明:民俗是一种变动不居的过程;民俗的为“我”所用是民俗传衍的常态;民俗二次生命的获得,常常是从档案等书面材料中再出发的;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的民俗自身,同样具有适应性。在数千年来文明未曾中断的连续统中国,无论是用民俗、民间文化、非遗等哪种称谓,都是如此。
如前文所述,传统中国的民间文化在其演进历程中,总是与精英文化交相互动而回环流转。乡风民俗的形成,更是经历了历朝历代统治者持之以恒的制度性的传衍教化,被民众内化为自觉进而反哺精英意识形态的结果。(54)参见杨开道:《明清两朝的民众教育》,《教育与民众》第2卷第4期,1930年12月。如同说书艺人的墨刻、道活儿之间泾渭分明又交互影响一样(55)岳永逸:《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64-166页。,图像、绘画、书本、档案、碑铭等可视符号(书面)传统,都在口耳相传、言传身教的民间文化传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同地域、族群文化的绵延互动及至最终混融,也很好地体现在边陲之地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张轲风在对滇池之“滇”和彩云南现的“云南”的释义耙梳中,发现在边疆内地化、地方王朝治化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旧有传说和作为祥瑞的彩云南现而新造的“庆云”传说,亦逐渐被地景化、文本化、审美化与意识形态化,从而成为一个外来者和本地精英长期互动的文化建设或文化重建的工程;在育化“望治”的边民的同时,这个工程成功而有效地将国家情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为广大民众的自我意识。(56)参见张轲风:《从此滇池不倒流》,《读书》2022年第4期。
毫无疑问,正是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与融合,铸就了中华文明的一体性,与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恒定性。有了这一长时段视角,我们就会明了:在当代中国,民俗整体性的非遗化、非遗的民族国家化、馆舍化和有新技术强力支撑的数字化,乃是当下民间文化演进的正常态与应然阶段。乐观地看,因应创作者和消费者对文化内涵的追求、数字与技术的完美融合,将会在利于非遗等优秀传统文化展示的同时,促生数字文化精品、造就文化高原与高峰并存的多彩美景。(57)参见江小涓:《数字时代的技术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换言之,在全球化语境和数字文明时代,非遗化赋予了民间文化以新形态、新价值,并使之在向“上”流动中得以发展。(58)参见徐赣丽:《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来自田野的民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40-251页。通过非遗化,主动与世界对话交流的国家意志为民间文化以及边际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完全可以将非遗化视为这些体现民族精神、国家意志的民间文化演进的里程碑,是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继续开拓进取的必有历程。
然而,要想使非遗化在作为“模仿系统”(a system of imitation)的民间文化(59)参见[德]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1-214页。的演进长河中具有永久性价值,就必须直面在经历了以非遗化名义的国家化、馆舍化与美学化的型塑之后,这一文化能否有效回流民间或再民俗化(re-folklorization),尤其是能否形成与民众的情感体验、生命历程的深度互动。换言之,只有在“小我”反向作用于“大我”,被非遗化的文化才能接地气、有人气,因获得新的个性、活力而生生不息。如此,非遗保护运动后的非物质文化,不但是社会演进的动因、社会文明的基石,还是增进人们安全感、幸福感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刚健力量,必将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成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完善。
近年来,因应作为一门学科的民俗学发展的需要,在美国、日本民俗学界,用vernacular一词替换folklore的尝试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并形成了不小声势。(60)Leonard.N.Primiano, “Vernacular Religion and the Search for Method in Religious Folklife”, Western Folklore, Vol.54, No.1(1995), pp.37-56; Richard Bauman, “The Philology of the Vernacular”,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Vol.45, No.1(2008), pp.29-36;[日]小长谷英代:《“Vernacular”:民俗学的超领域视界》,郭立东译,《遗产》2020年第1辑;[日]岛村恭则:《狄俄尼索斯(Dionysos)和民俗(vernacular)——何谓民俗学视角》,《日常と文化》第9卷,2021年,第157-174页;陆薇薇:《日本民俗学的vernacular研究》,《民俗研究》2022年第3期。正是在对vernacular的引入中,日本民俗学家菅丰将民间艺术界定为“支撑人之‘生’的艺术”,即vernacular艺术。他还在对日本、中国非遗保护运动的审视中,提出了“家庭级文化遗产”和“个人级文化遗产”两个概念:
对于尊重民众多样化的文化实践并以之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而言,“突出的普遍价值”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如老人的花墙那样不具突出价值或普遍价值的造物在人类的生活世界中俯拾皆是,但即使没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它们却依然有自己的价值……它们固然无法被列为“世界级”“国家级”的文化遗产,但却可能是某个家庭的“家庭级文化遗产”,或是某个人自己的“个人级文化遗产”,是无可替代的重要存在。(61)[日]菅丰:《民俗学艺术论题的转向:从民间艺术到支撑人之“生”的艺术(vernacular艺术)》,雷婷译,《民俗研究》2020年第3期。
七、个人的非遗及学科归路
在19世纪,与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尤其是反启蒙运动相伴,“民俗”(folklore)被发现并大书特书。到20世纪中叶,有了“民俗学主义”(folklorism)的兴起。(62)参见周星、王霄冰主编:《现代民俗学的视野与方向:民俗主义·本真性·公共民俗学·日常生活》,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9-202页。在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新的世界格局的建立,受到国别间的文化传播、政治角力的激发,“非遗”概念被制造出来,并在近20多年来大行于世。
作为民俗学家的哈福斯坦,注意到玻利维亚、韩国、日本等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公约制订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认为非遗是“弱者”对抗强权——欧洲中心主义和“物质遗产”这一霸权话语的武器,并将之归结为二战之后因地缘政治争斗而兴起的一种意识形态。这一命题具体表现为:非遗即民俗;非遗即治理术;非遗即主权;非遗即领土;非遗即社区;非遗即节日;非遗是指代人际关系、忠诚和社会组织的伦理概念;非遗是一种强化疏离感和危机感的诊断;外力介入的非遗保护是有着副作用的治疗。(63)Valdimar Tr.Hafstein, Making Intangible Heritage: EI Condor Pasa and Other Stories from UNESCO.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8,pp.122-135, 137-141, 152,166, 183-188, 203.虽然都有“人类文化遗产”这顶王冠,但是以国家为界,非遗对外强调的是国家性,对内则更强调地方性、差异性,进而成为有效规训民众、规范社区的治理术。哈福斯坦的《制造非遗》(MakingIntangibleHeritage)一书,正是从制造非遗概念、制造威胁(危机)、制造非遗名录、制造社区和制造节日等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的。
在此基础之上,笔者更想强调的是:在经历了人类化、国家化、非遗化以及社区化之后的非遗,当其回落个体的日常生活,成为看得见摸得着并实实在在有益于个人的非遗的重要性,也即民俗在经历非遗化后“再民俗化”的重要性。这种民俗化不是“民俗主义”所说的对于民俗的片面使用,而是“把民变成民俗学者的现代性反思能力”,(64)Valdimar Tr.Hafstein, Making Intangible Heritage: EI Condor Pasa and Other Stories from UNESCO.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8,pp.171-177.是个体对自己及其文化(遗产)之间关系进行反思和配置的实践,进而服务于个体生命感受、社群和谐、社会文明、国家康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铸造。就此而言,强调行动主体的非遗的“个人化”或“个体化”可谓意义非凡。长时段观之,已经发生的非遗化仅仅是民俗传衍的一个方面或阶段。而个人的非遗——非遗的个人(体)化,才是所有非遗的核心,才是将民俗非遗化后应有的终极旨归。显然,“支撑人之‘生’的艺术”(vernacular)这一命题,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前文已指出,诸如礼俗互动(65)参见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大、小传统之间的交互缠绕与两位一体,是作为人类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而口头传统与符号书写两大系统之间的互动,则是不同类型的人类文明传衍的普遍特征。为此,人类学家古迪还创造出了“文字-口语(lecto-oral)”这一强调书写和口语两者连带性与交互性的新词。(66)参见[英]杰克·古迪:《神话、仪式与口述》,李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8-155页。显而易见,在中国兴起的非遗保护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对民俗文化、口承文化全面摸底并使之整体性进入国家序列的综合性文化治理工程,是大传统对小传统的井然有序的整合工程。有鉴于因统合而日益呈现出的镜像化、馆舍化之不足,本文才从行政治理传统、文化传衍逻辑、个体生命感受等不同层面,强调个人的非遗和社区、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辩证关系。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作为眼光向下的学科,一度亦称为“民学”“民人学”以及“人民学”的民俗学,(67)参见江绍原编译:《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中华书局,1932年,第276-277页;杨堃:《民人学与民族学(上篇)》,《民族学研究集刊》1940年第3期。始终都不应背离其关注常民之生活态、对作为民族国家主体的民众保持敬畏的基本定位。面对现今非遗叙事的空泛,特别是工具理性支配下对非遗内价值的轻忽,民俗学应努力促进非遗向日常生活的返归,这既是非遗化后的民间文化的前行正道,也是民俗学与非遗学发展的学术坦途。
民俗也好,非遗也好,民俗的非遗化与非遗的个人化(民俗化)也好,这些关联上下、纵贯古今又与“小我”一体的日常生活文化——vernacular艺术-个人/家庭级的文化,不但是社会文明的核心与常态,更是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石。作为以非遗化的民俗和个人化的非遗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民俗学如果仅仅回应公约、诠释政策、建言献策,而完全丧失“在野”的批判性立场和深度的学理思考,不关注个体生命本身,无视鲜活的文化本体及其自主调适能力,都将仅仅是“高鸟尽良弓藏”的那张弓。事实上,群起而快速地处于对非遗的“神化”或“同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民俗学置于某种尴尬境地。(68)参见周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和中国民俗学——“公共民俗学”在中国的可能性与危险性》,《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
民俗学也罢,非遗学也好,其真正使命是以影响人们评价、传承和实践自身文化的方式,赋予一种文化以生生不息的活力,使之成为有本之木。只有将承载民族精神的非遗藏之于民,尤其是如何使之与个体“小我”的生命体验形成紧密关联,这样的探索才是民俗学、非遗学以及文化遗产学的安身立命之本。扩而言之,当代中国的学术、学科,只有真正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之中,才有可能在国际学术舞台中形成自己的话语权甚或引领性,中国的经验才是世界的。
八、结 语
世界范围内非遗的申报、裁定、公布与评估,虽然有自信、保护、传承、发扬等诸多名义,但操持者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是在通过“运作文化”与“文化运作”构拟历史。在以非遗的名义将文化标准化之后,在全景监视空间中受镜头美学支配的馆舍非遗批量出现,就是自然而然的现象。
对“非遗”一词的定语从“人类”到“个人”的递进,正是基于对当下中国非遗保护运动的省思,而对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庸俗化、行政化、官僚化与形式化的非遗保护运动的批判。因为每个置身种种关系、配置、网络中的个体,既是个人生活世界中的主体,也是一个“具有决定关系的相互作用间冲突不断(通常是对立)”的场所。(69)[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32页。在对种种教化、规训机制的承受、抗争等不同形式的消费-使用即化用中,个人也反向地作用于其置身的大小生活共同体直至人类命运共同体。
化用,也就意味着创造。在庞大的消费者-使用者群体中,对于社会供给品的使用存在巨大差异,因而这种化用就“表现为一种几乎不可见性,因为它几乎不以自己特有的产品来引人注目,而是借助于一门使用的艺术,并且使用的是被强行赋予的东西”(70)[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2页。。就在个体化为己有、为我所用的这一化用模式中,使得包括非遗在内的诸多文化有了多个声部、变调、间奏与变奏,呈现出叠加、杂合的“复数态”。而所谓“个人的非遗”所涵括的社会实践,其实也是一种化用,是基于复数非遗这一民众日常实践而形成的化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