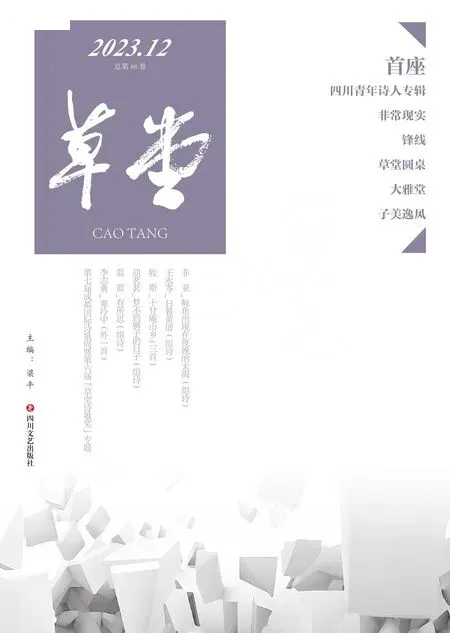络石花开了(组诗)
◎韩少君
[火杞园二题]
一
来到山顶,获得一身的光。
她的身上也有了光
淡绿色外衣,搭在火杞丛上
苍翠与红果,让他们彼此靠近。
高山草地尽是羊粪蛋蛋,一只羊
也没有,但人们对羊的态度还在。
大地冒出的石头还在
处处都有时间的爪痕。
一圈铁蒺藜、谁的保温壶
遗忘在火杞园,被日光照耀。
二
一棵白皮木,朽木,枯,春天一到
慢慢有了香气,恢复了它的俗。
趁着花色正好,雀舌变得
嫩黄,胸腔积有春天的雨滴。
山下一览无余
蜂蜜在贩卖的途中
无法抵达的,就当没有发生。
从前,躲在黑绒布下面
摄影师的声音,从天而降
小个子,衣着朴实
再次跳到板凳上
人与人,间距一拳头
咔嚓,背对落日。
[先农湖畔,络石花开了]
月光下,想的还是月光
先农湖,我也遇见了我
那么多卷须植物,伏于
便道,络石花开了
有一小节沙石路
我走得更慢,荆山之外
现实还在演进,但是
在这里,山涧淌出清流
疏朗的马尾松林,我选择
接近简单而明亮的事物
为“一支大地和水的歌谣”
保留耳朵,丢失的
银子,将在今晚找回
拨开轻轻触碰额头的枝条
手臂上,两只小蚂蚁
在爬,仿佛回到古老的时间
谷神呵,酒神,没人知道
你们,会在什么时候醒来
[荆山秋意]
站在窗口,就不想离开
秋意袭来,幽阴铺满了
城郭,风从黄昏开始
刮起,今天怎么回事
居然有些缠绵,眺望
荆山浩荡,横亘远处
他怀抱小犬,随着它
的眼珠子,向北移动
他们当然不是在看天色
几颗胡柚悬于南枝
月光垂挂而下,只要
伸手,便可抓住它的巨尾
[秦江渡逸事]
码头消失之后,下河
取水的人,会在那里
多坐一会,时常谈论
客轮和远去的汽笛时代。
旧式建筑,石头鱼,几处
铁疙瘩,削成梨状的云雾山
一起移进一本蓝色旅游手册。
“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
古老襄河,悠悠漫漫
交给落日照料。黄雀
划过小江湖,甩出
长长的虚线,千里之外
有人找到了它细小的源头
秦岭南坡,扒开几片
深秋的落叶,掬起
清冽溪水,他洗了一把脸。
[一只棉虫躺在大厅]
棕红色报告厅宽阔而荒凉
一只棉虫悄悄爬了进去
躺在大理石上,睡着了
它肯定已经拥有什么梦想
门缝的青草试图唤醒它——
这并非是一个抽象的话题
几只花喜鹊哪里知道,它们
隔着玻璃幕墙,翘起尾巴
盯着棉虫,在白杨树梢
跳上跳下,叫喳不停
路过的人察觉不到它敏锐的视力
当人间的烟火在平原上空弥散
这一切刚好处在隐秘的深处
[石牌镇长江明月湾句子]
一轮明月落入峡谷,在
大坝涌出的绿波中闪耀
江河因截流而平缓,焦虑的
情侣,不再蜷宿夜航的船仓
巨轮,运送煤灰
运送钻石和灯火
镇上,生意人出售奇石
伸出左臂,接住青白之光
粗重的锚链,哗哗沉入水中
回头看见,江口数顷杏花白
小酒馆里,他们准备喝一通宵
但愿他们的明月还在枝丫间
·创作谈·
开启“下半场写作”
2020 年3 月,那段特殊的日子,我写下了一首短诗《下半场》,“那棵老樟树/枝尖上的小籽粒/满胀着黑色光亮/似乎不用去捏/也会自动爆灭”。这首诗不重要,但却让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诗歌写作也已进入“下半场”。从1983 年,在大学阅读何其芳诗集《预言》和屠格涅夫散文诗集《爱之路》,写下第一首诗《小憩的朦胧》,创办“墙蔓诗社”开始,已过去四十年了。好快呀!
艾略特说过,一个人过了二十五岁还要写诗的话,应该建立起必要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对于我来说来得要晚一些。我认为四十岁之前都是在构建一种属于自己的写作秩序,努力走向自觉。21 世纪初,我写下《麻燕考》《9 月25日,咏蛇》《到北京见一见芸》等诗篇时,我开始消化现实,拓宽自己的精神视域。这又过了二十年,我决意在古老的时间中安身立命。我时常想,“下半场写作”如果给我十年、二十年时间,我会写些什么?
“我想时间是一个根本之谜,其他东西顶多只是难以理解。空间并不重要”(博尔赫斯),那就让我们真诚地体悟时间的力量,启动内心,与万物对话,并重塑自我。
我一直生活在楚国都城“郢”的废墟之上,荆门正处在连通中原和神秘南方的荆襄古道的关键点上,为“荆楚之门”。南北朝时期,诗人江淹旅迁途中,经过此地,写下一首《望荆山》,“奉义至江汉,始知楚塞长”。他深深感受到江汉大地的苍茫和寥阔。我推窗所见的峰峦应该包含在这一脉“荆山”之中。当年“秦风拂楚”,也是首先吹拂此地。
楚文化绚烂而沉郁。“行于郢”,当属于我“下半场写作”的重要内容。诗歌不在远方,在不断加长的时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