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美学的双向混杂:论萨义德的对位阅读与音乐批评
□李 盛
【导 读】 作为萨义德的重要批评方法,对位阅读源于音乐却超出音乐,成为萨义德展示音乐和文学等美学文本与现世权力斗争之间复杂关系的中介。从概念定义看,对位阅读有着双重面向,其一是经由美学文本施行政治批判,其二是在政治批判中反顾音乐的美学属性。从具体实践看,萨义德对威尔第歌剧《阿依达》及其与东方学共谋的历史考古、他对瓦格纳歌剧回归音乐的反说,成了他实践对位阅读的经典案例。
从萨义德1983年在《名利场》(VanityFair)发表第一篇乐评文章《音乐:古尔德的对位法视野》(The Music Itself:Glenn Gould’s Contrapuntal Vision)起,“对位法”(counterpoint)就对他产生了强烈吸引,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对位法”触发了他的音乐批评。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于“对位法”做了如下描述:“对位法的本质在于声音的同时性,对(音乐)素材异乎寻常的控制和仿佛永无止境的创造力。在对位法中,一个旋律总是处于被另一个声部重复的过程里:结果就是水平式,而非垂直式的音乐。因此,任何音列都能做无限变换,因为这个音列(或旋律、主题)先由一个声部实施,接着被另一个声部接续,这些声部持续处在与其他声部的对抗与协作中发声。”[1]5可见,萨义德最先是从音乐本身的角度来认知和解读对位法。然而到了《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andImperialism),他却将对位法发展为一种言说音乐和文学的独特方法,它游走于历史与个体、世界与文本的边界,要求我们把文本中自在、客观的美学主题与关乎权力、现实的主题并置,关注不同声部的交织和斗争,看到宰制性声部之下世界的暗面,从而给予被压制的叙事以一席之地。
在约翰·库奇克(John Kucich)看来,源于音乐的对位法与《文化与帝国主义》的中心主题并不一致,前者意在给予每个声部平等的话语权,后者则强调对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这一宰制性声部的批判。[2]二者之间的转换或曰矛盾给予我们一个契机,得以将萨义德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在萨义德的批评语境中,对位阅读的概念内涵是什么?萨义德怎样实施对位阅读?他最终又如何克服了《音乐:古尔德的对位法视野》与《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关于对位法的不同界定和内在矛盾?带着这些问题,本文从萨义德对位阅读的概念界定和具体实践入手,经由对位阅读重识萨义德的音乐批评,进而为激活萨义德乃至音乐与社会的关系构筑合适的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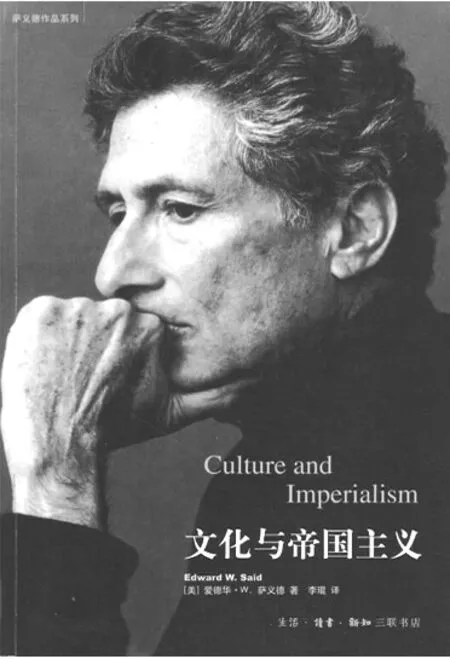
一、萨义德对位阅读的概念界定:美学与政治的交互混杂
萨义德在《音乐:古尔德的对位法视野》与《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关于“对位法”有着不同界定,但多数学者总对后者偏爱有加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前者。诚然,萨义德的对位阅读最初是为了挖掘歌剧、小说等美学文本的不纯性、复杂性和杂糅性,并揭示它们与殖民帝国及其意识形态的内在勾连。典型案例是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关于威尔第歌剧《阿依达》与英、法帝国对埃及的入侵和殖民统治做的对位阅读:威尔第意图呈现“真正埃及”的动机与埃及学在审美中排除埃及(他者)的共谋,以及如下事实:歌剧本身作为威尔第的天赋与诸多社会机构、文化环节“集体努力”的结果,它是一个艺术家的帝国观念与一个非欧洲世界的帝国观念彼此契合的产物。包括对《阿依达》的分析在内,萨义德对许多美学文本做了类似的政治解读。然而,正如萨义德在别处所言:“伟大的文化纪念碑(我就是如此处理《阿依达》的例子的),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不会因为它们和世界相当肮脏龌龊的方面共谋,而失去其纪念碑的地位。或者在一些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下,因为它们参与、介入了社会和历史的过程,就有失地位。”[3]
虽然对位阅读最初意在发掘音乐、文学经典的意识形态,但这些杰作的美学魅力深深吸引着萨义德,以至于使他的政治批判蒙上了浓重的美学底蕴。因此,音乐、文学经典的不纯性实则是文本的美学要素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交互影响和双向混杂,对此阿德尔·伊斯干达(Adel Iskandar)与哈克姆·拉斯托姆(Hakem Rustom)有过精到的评述:“萨义德在其批评中的诠释方法既是辩证的而又是整体性的:美学与政治无法相互分离却又能同时以和谐与对抗(both in unison and in contrast)加以审视。[……]在萨义德看来,一部作品的美学既可以是矛盾的,也可以是互补的,允许将对立的叙事并置。也许萨义德对欧洲古典音乐传统的迷恋,以及复调(polyphony)和对位(counterpoint)在他心目中的核心地位,为他的人文主义理想提供了借鉴。他在讨论政治问题时经常使用这些术语,暗示和谐只有通过多种声音或乐器才能实现,每组乐器的演奏方式不同,却能汇聚成一个综合的、复杂的音乐作品。”[4]由此可见,萨义德的对位阅读有着双重面向:其一是经由美学文本施行政治批判,显然它已经得到足够的关注;其二是在政治批判中反顾音乐文本的美学属性,这一点常被人忽视。在这方面,萨义德对瓦格纳及其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反说”最为典型。当瓦格纳与其作品被全然当成反犹主义的注脚时,他站出来坚定反抗这一化约性的固定解释,从美学的角度为音乐辩护,同时也为瓦格纳及其音乐作品的内在丰富性辩护。
更进一步,萨义德的对位阅读同样形塑了他看视经典(classic)的态度。在萨义德眼中,音乐经典不只是作为一部部典范文本的西方音乐作品,如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贝多芬的歌剧《菲岱里奥》、勋伯格的无调性作品,更在于这些作品在被创作、阅读、接受的过程中与历史和社会的复杂联结。换言之,萨义德要做的不仅是从静态的、既定的、其起源已然被忘却的经典中提取意义,更是以历史的目光重新审视“经典”的发生学,在一系列被纯化的“西方正典”(western canon)中发现权力操作所遗留的痕迹,以及那种绝难像外科手术般被简单切割为某些巨大实体(比如西方和东方)的含混性和不纯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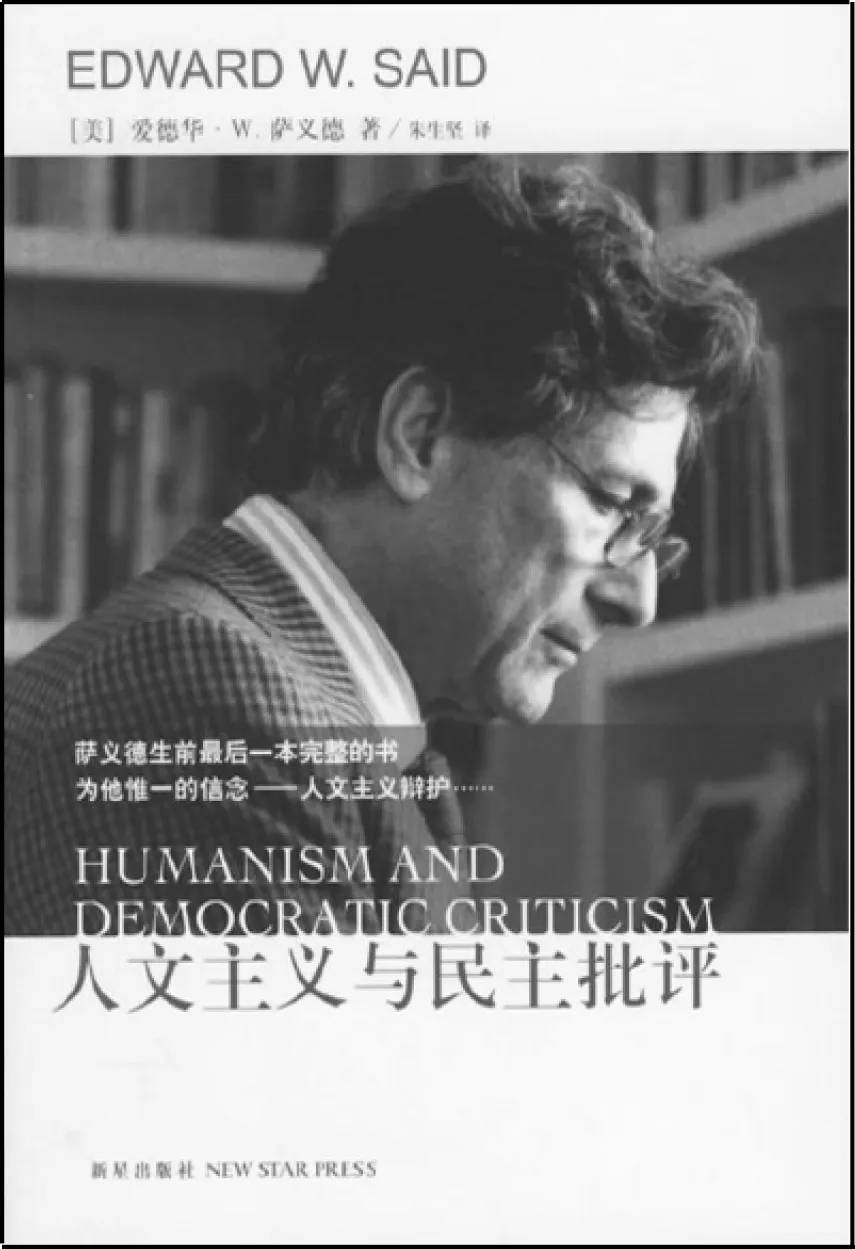
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HumanismandDemocraticCriticism)一书中,萨义德谈及与“classic”有诸多意义联系的“canon”一词的词源:根据词源学家推测,该词与阿拉伯语的“qanun”一词有关,或至少与后者在约束和教条主义意义上的法则有关,但那只是一种极为限制性的含义。他更强调该词的另一个来源,它源于音乐,是指一种对位形式,采用多种声音,通常是彼此之间形成严格的模仿,换言之,这种形式用于表达曲调和旋律的变移、戏谑、发现以及在修辞意义上来说的发明。[5]30与限制性的教条相比,萨义德更愿意揭示“经典”一词与讲求变移、戏谑、发现和发明的音乐对位技巧的关联。在他看来,“经典”远非铁板一块的固定文本和典范,而是一种动态的阅读习惯乃至认知模式,它“始终向变化中的感觉和意义之结合保持开放”,“依然对当前和突然出现的挑战,对反叛者、对有待回报和有待探究的一切敞开着”。[5]31-32因此,他从未试图对“经典”做任何类似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列举“西方正典”那般的静态定义,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排斥标准,使自身受困于“哪些属于经典,哪些不属于,为什么?”这类的问题而疲于应付,相反,他总是通过一次次重读激活经典并使这些文本时刻处于生成之中。
一言以蔽之,萨义德的对位阅读将自身定位于美学与政治之间,进而以兼有美学面向与政治面向的双重目光看视西方传统中的音乐与文学经典。
二、对位阅读的政治面向:萨义德论《阿依达》及其与东方学的共谋
关于对位阅读的政治面向,萨义德音乐言说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有关威尔第歌剧《阿依达》的分析。《阿依达》讲述了一个古老的爱情故事:在古埃及法老王时代,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战事又起,埃及将领拉达梅斯率部出征,迎战埃塞俄比亚国王阿姆纳斯洛。埃及公主阿姆涅丽斯爱恋着拉达梅斯,而拉达梅斯的心上人阿依达是公主的女奴,同时也是埃塞俄比亚的公主。经过激战,拉达梅斯最终获胜并俘虏了伪装成军官的阿姆纳斯洛。阿姆纳斯洛知晓阿依达与拉达梅斯的恋情后,逼迫阿依达从拉达梅斯那里问出埃及军队的进军路线并向拉达梅斯亮明了身份。拉达梅斯震惊之余,因为阿姆涅丽斯和主祭司拉姆菲斯等人的到来,他让阿依达父女赶紧逃走,自己却被已成为法老的阿姆涅丽斯以叛国罪关进地牢。后者许诺,如果拉达梅斯放弃对阿依达的爱情就放了他,可拉达梅斯宁死不从。虽然阿姆涅丽斯企图阻止,但拉达梅斯最终被祭司们判决窒息而死。阿依达不愿苟且偷生,事先来到墓穴,与拉达梅斯相伴赴死。
从故事看,《阿依达》并无特别新鲜之处:设置儿女私情与家国大义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以爱情实现超越。然而,正当爱情被认为是《阿依达》的永恒主题之际,萨义德经由保罗·罗宾逊的论述表达了他视这部歌剧为政治歌剧的反常观点,进而开始了一场现世的音乐考古。罗宾逊指出:“坦率地说,也许威尔第修辞风格中最明显的成分是纯粹的高调,他和贝多芬一样,是所有最重要的作曲家中声音最大的一个……好像一位政治演说家,威尔第不能长时间保持安静。在威尔第的歌剧录音中随意扔下一根针,通常你就会得到相当厉害的吵闹声的回报。”[6]159他继续说道,威尔第的喧闹被用于“游行、集会和演讲之类的场合”[6]160,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喧闹甚至与瓦格纳的音乐取得相近的效果,第二幕第二场的凯旋进行曲和尼罗河大合唱就是绝佳例证,它不仅成为克代夫所作埃及国歌的灵感来源和曲调素材,也成为意大利抒发爱国主义情绪的重要手段。直到今天,其政治影响也未消散,而是成了埃及政府国家形象宣传的重要一环。比如,2015年埃及庆祝新苏伊士运河开通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就再次采用了《阿依达》中的一个场景。[7]
《阿依达》作为美学与政治的对位式存在,它一方面既是威尔第的美学追求,另一方面又在现实中被用作政治宣传,这一对位式关系甚至让约瑟夫·科尔曼感到“《阿依达》有一种令人奇怪的不真实”[6]159。这种“不真实”或“虚伪”的感性直觉被萨义德转化成理性追问:“为什么威尔第习惯性的混合手法会产生如此不寻常的大师级的作品和受人欢迎的中立立场呢?”[6]160在这一追问背后,暗含萨义德对《阿依达》独特性的好奇,其中最能挑动他敏感神经的莫过于这部歌剧浓郁的异国情调,也就是剧中那个被想象、被再现、被埃及学对象化的“古埃及”。在当时的西欧剧坛,表现神秘东方成了某种时尚,除《阿依达》外,梅耶贝尔的《十字军在埃及》(1824)、《非洲女郎》(1864)和德利布的《拉克美》(1883)这类东方色彩浓郁的剧作风行一时。如果仅有一部《阿依达》,我们还能认为再现埃及是威尔第个人美学趣味的偏好,但这样一批东方剧作的涌现甚而成为风尚,从个人美学趣味的角度来解释就显得无法自圆其说。
在此背景下,萨义德从“不只是美学”的角度对“《阿依达》的虚伪特质”给出回应:“《阿依达》和歌剧形式本身一样,是个混血儿,一部属于文化史和海外统治的历史经验的极为不纯的作品。”[6]161“《阿依达》的尴尬归根结底是帝国主义统治本身。”[6]161在他看来,帝国主义的幽灵首先游荡在《阿依达》的创作动机之中。1869年11月,苏伊士运河竣工,同年开罗歌剧院落成,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埃及和苏丹总督伊斯梅尔·帕夏邀请威尔第为歌剧院写一部埃及题材的歌剧,以庆祝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威尔第曾两次拒绝邀请,但在看过法国著名埃及学家奥古斯特·玛里埃蒂撰写的故事梗概后,他最终同意了伊斯梅尔的请求。因为在玛里埃蒂文字虽简单内容却丰富、关乎真正“埃及”的剧本中,威尔第看出“一种单一的意图,一种大师的印记和内行的愿望”[6]163,从而希望自己的乐曲能配上这一愿望,甚至使它变得更真实、更丰富。然而,就像萨义德指出的,“埃及学是埃及学,不是埃及”[6]166,玛里埃蒂和威尔第想象的“埃及”与现代埃及完全脱离,他们心驰神往的是已不复存在甚或从未存在的古埃及,在他们那里,埃及成了被想象和再现的美学客体。悖论的是,看似与埃及息息相关的作品反而距离埃及最远,且它的美学成就越高,两者的鸿沟就越大。关于这一悖论,柄谷行人在《美学的功用:东方主义之后》中做了精准说明:“殖民主义最典型的暴虐是对他者进行审美至上的尊敬和崇尚。……东方主义的特点从来不是对他者的忽视,而是在审美中对他者进行的排除。”[8]
在《阿依达》努力营造的“真正的埃及”中,不论情节还是音乐,威尔第的美学改动暴露了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渗入。例如,他将男祭司换成女祭司,萨义德认为这一做法违背了古埃及的传统,遵循的是欧洲习俗。这些女祭司在职能上与舞女、奴隶、妓女相等,因此,第一幕第二场女祭司为拉达梅斯着圣衣的庄严仪式和第二幕第一场阿姆涅丽斯屋内摩尔女奴的热烈舞蹈,两者恰如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的极端对立,却取得了完全一致的实际效果,这些东方式女性的表现“说明了权力关系并显示了想通过表现的手段巩固优越地位的欲望”[6]171。就音乐而言,《阿依达》第一幕终曲祭司合唱大量运用在吉卜赛风音乐中广泛存在的增二度音程,使全曲弥漫神秘的东方风味。第三幕《阿依达》的浪漫曲,管弦乐队依次奏出主题和具有异域情调的乐句,一面激起阿依达对祖国的怀念,一面提醒观众这部歌剧的东方属性。
专业音乐研究者赵玲[9]和杨晓琴[10]都注意到威尔第歌剧的现世性,但她们讨论的中心是《纳布科》《阿提拉》《弄臣》《茶花女》,对《阿依达》总是一带而过。在她们看来,《阿依达》的异域题材和想象特质,使它既与意大利脱离,又不关注当下现实,浪漫而超脱的《阿依达》成了威尔第“革命性、民族性、现实性”歌剧的另类。然而,萨义德通过步步深入的论述向我们展现了另类的《阿依达》与东方学的隐秘共谋。虽然《阿依达》自身并未背上统治他人的包袱,但它从酝酿到生产的过程无可避免地与帝国对他人的统治绞缠不清。这一杰作不仅增加了欧洲观众关于“东方/异域”的知识(获取知识作为东方学的核心任务乃是帝国统治的开端),其美学外壳也对他们施加了麻醉效果。最终,音乐的生产“用叙事的形式,驱散矛盾的记忆,抹杀暴力。关于异域的叙述,用好奇心代替了权力的印记”[6]186。
三、对位阅读的美学面向:萨义德反说瓦格纳与《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美学复归
“伟大的作品并不必然就意味着是无辜的作品,或者完全不涉及我们所谓的卑劣的任何东西。”[11]这是萨义德通过对《阿依达》的音乐考古努力向我们传达的观念,然而,这不意味着他否定《阿依达》这类杰作长久而持续的美学价值。本雅明的经典之语,每一部文明的文献也是一部野蛮的文献;在萨义德这里,反过来,一部野蛮的文献也可以是一部文明的文献,同样成立。当有人完全置作品(尤其语义模糊的音乐作品)美学价值不顾,纯粹从政治角度加以评判时,萨义德又一次站出来为音乐辩护。
在萨义德唯一的音乐“理论”著作《音乐阐发》(MusicalElabration)第二章“论音乐的越界元素”中,萨义德以保罗·德曼和瓦格纳作品的悖论特质——一方面,它们拥有无可争议的美学价值;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同情甚至暗中与纳粹共谋——切入,讨论了美学杰作与其肮脏社会背景的关系问题。但关于德曼对犹太民族最具冒犯性的一篇文章,萨义德却做出了“反常识”的解读。德曼在文章中说:“由此可见,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旨在建立一个与欧洲隔离的犹太殖民地,这不会给西方的文学生活带来可悲的后果。”[12]38当这段文字被视作德曼反犹主义的有力注脚时,萨义德却敏锐地捕捉到犹太殖民地与1948年后巴勒斯坦人被驱逐的流亡命运之间的历史关联。萨义德的解读当然与他个人的现世关怀密切相关,但稍稍脱离私人情境,他反对的是惯于“强调一些而无视其余”[12]40的一元视角。在他看来,不仅德曼、瓦格纳被认为反犹的作品以及同时作为“受(纳粹)害者”与“加害(巴勒斯坦人)者”的犹太民族甚至这一霸权视角本身,都需要更为多元的审视。到音乐领域则更是如此,因为“音乐不是指示性的(denotative),也不能同语言分享一个共同的话语”[12]40。这是萨义德讨论瓦格纳乃至评论音乐的前提,音乐非直接语义的暧昧本质无时无刻不在抵抗一元的霸权视角,在“只能是这样”的论断之下呼唤“还可能是那样”的另类解读、一种他者的视角。
首先,萨义德分析了瓦格纳代表作《尼伯龙根的指环》(以下简称《指环》)的反犹思想,揭示出这部大型乐剧与纳粹共谋的阴暗面。这一共谋直接体现在俯拾皆是的歌词当中。比如,《指环》第一部《莱茵的黄金》,阿贝伯里希拥有指环后的狂妄之语:
所有的尼伯龙根人,都来向我致意!
我无处不在,将你们监视,
你们再也无法休息,
看不见我时,也要为我做事,
我盯着你们,即使你们也无法将我注意,
你们永远是我的臣子!
咳!咳!听着,我来到这里,
我是尼伯龙根人的主子![13]67
歌词体现的极权恐怖与半个世纪后的纳粹主义何其相像!阿贝伯里希那句“我是暗夜,我是迷雾,
无人可比”(Nacht und Nebel,Niemand
gleich)[13]66被用作纳粹集中营臭名昭著的口号[14],更直白暴露出瓦格纳乐剧与纳粹的共谋是如何败坏了人性。与此同时,瓦格纳把阿贝伯里希的独裁者形象以动机形式化入音乐。比如,指环被盗后,阿贝伯里希的“诅咒动机”(见谱例1),该动机前三个音的减三和弦(见谱例2)使它蒙上了阴森可怖的色彩,且这一动机前四个音又是“指环动机”(见谱例3)#F 音之前的反向进行,即“#f-a-c-e”,这种反向进行的设计显示它来自指环,同时反映出音乐的可变品性:不仅指代指环由莱茵河中圣洁的黄金到被铸成蒙上尘世之肮脏、邪恶和诅咒的指环这一堕落过程,更带有萨义德意义上音乐在现世情境中的适应性(易变性),正如他所说:“瓦格纳意识到音乐非常易于适应现世情境,这是他为标题音乐或叙事音乐奉上的最核心而宝贵的礼物。”[12]42

谱例1:阿贝伯里希诅咒动机

谱例2:指环动机(减三和弦)

谱例3:指环动机(前四个音)
然而就在此处,萨义德表现出与“纯粹视《指环》为纳粹注脚”的观点分道扬镳的倾向。当所有人将《指环》斥为纳粹共犯,萨义德也从音乐自身找出大量证据加以佐证时,他却又以自反的态度对这种“只能是这样”的单一视角做出重新审视。音乐的适应性或易变性使它在不同情境面对不同的阐释话语,往往呈现不同甚至相反面貌。在萨义德看来,所有关于音乐或其他任何一种人类活动回溯性的历史分析,如果试图宣称或规定以下“连等式”,即“一件事物(比如,音乐)= 所有事物,或所有音乐=一个巨大的概约化结果=它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发生”[12]50,那它就是一则完全的“神话”。音乐当然是政治的,但同样是美学的,它一面通向社会政治环境,一面通向私人情感世界。即便是政治性极强的《指环》《纽伦堡的名歌手》,也不能被简化为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因为每部音乐作品都有其自身的性格,它们首先也最终朝着人的内心情感世界而非沉重的政治内容敞开。萨义德引述了法国当代著名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的话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后者认为“音乐以其自身存在,拒绝忍受它被要求传达的意识形态信息[12]61”。
在此背景下,萨义德撰写了多篇乐评文章,如《〈女武神〉〈阿依达〉〈X〉》《瓦格纳和大都会的〈指环〉》《巴伦博伊姆和瓦格纳禁忌》,一再申明并实践了评判瓦格纳及其作品的多元视角,着重从作品和表演自身的美学品质入手,在反犹主义的标签下发现音乐的丰富性和暧昧性。谈到1986年由莱文(James Levine)和咸克(Otto Schenk)合作而在大都会上演的《指环》,萨义德称其“完全无视战后以来瓦格纳作品演出的所有进展。他们的合作里没有丝毫象征荣格、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或结构主义的成分,只有1900年前后那种北欧型的自然主义式呈现,依照那种呈现方式,所谓戏剧性就是以激动的姿态从舞台中央跑到门边,再从门边跑回舞台中央”[1]38-39。音乐方面,“莱文令人生气之处是,他天资过人,却不知为何,总是忽略音乐里最具省思意义、最知性、最浸于思想反省之中的层面”[1]39。
大都会于1989年、1990年连续两个春天上演了三套《指环》,萨义德称赞其为“不太可能的壮举”“纽约音乐生活里一个奇怪而且的确出人意表的变化”[1]105,“在音乐方面的收获,事实上绝非微小”[1]105,却依旧批评它“刻意、有目的、细心地讲求‘传统’……走乏味的忠实路线……结果是一种怪怪的,半生不熟的舞台经验,缺乏真实的脉络或清楚的哲学意涵”[1]106。从剧院的剧目单到排演理念,大都会无处不在的保守性、不变性以及背后仰赖的经典性、霸权性,取消了音乐的个性。这在萨义德看来是对音乐的背叛,是不可接受的,他念兹在兹的是歌剧的创新性和革命性,它们“不只是这样”,完全“还可能是那样”。
当瓦格纳被认定为狂热的反犹分子,《指环》被解释为纯粹反犹作品,被犹太民族视为禁忌,禁止在以色列上演时,如2001年4月7日巴伦博伊姆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一首歌剧的弦乐选粹而倍受批评。萨义德为此撰写了《巴伦博伊姆和瓦格纳禁忌》一文,既为巴伦博伊姆也为音乐辩护。他说道:“甚至对许多非犹太欧洲人,基于同样的理由,瓦格纳也只是勉强可以接受,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占领过的国家。……虽是如此,但在剧场、在音乐上,他毫无疑问是伟大的天才。他为整个格局观念带来革命;他完全转化调性系统;他写出十部伟大的杰作,十部至今名列西方音乐伟大高峰的歌剧。他给我们的挑战,不只对以色列犹太人,也对我们的挑战是,如何佩服并演出他的音乐,同时将音乐从他可厌的文章以及纳粹对他的利用分开来。”[1]290-291通过对瓦格纳作品美学性的强调,萨义德以复归美学的姿态重归政治和历史,最终将歌剧表演置入流动、具体的情境,使其不断朝向现世敞开而非走向简化与封闭。
结语
在一次与巴伦博伊姆的对谈中,关于音乐的社会意义,萨义德说道:“音乐是用来确认——确认现存的情况,因为没有什么值得去挑战的,你不是在批评,就像在某种社会里,比如,你提到的那种社会,贝多芬‘第九’或者《菲岱里奥》成为在没有自由的社会里对自由的支持。在一个自由已经被普遍接受的社会中,比如,我们所处的社会,这些作品还有什么意义?它们只是对现存状况的肯定吗?它们是对于管弦乐团这种机构的魅力的肯定,而这种机构则代表着我们社会的繁荣?作为知识分子,我不想一次又一次有着这样的发现。我感兴趣的是去挑战所给予我的东西。”[15]萨义德认为挑战而非承认现存是音乐之于社会最为重要的价值,也是音乐最具魅力之处。
不论在音乐文本还是其他历史的回溯过程中,当“一件事物(比如,音乐)= 所有事物,或所有音乐=一个巨大的概约化结果=它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发生”这一连等式变得自明且无可争议之际,萨义德要做的恰是借助对位阅读发掘这一自明关联的人为性,在无可争议之处大胆质疑并给出独立见解。这种现世性的态度使萨义德在饱受流亡之苦的同时,坚守知识分子流亡式的批评位置,借助音乐与社会的对位式阐发,为现世之中每个人的幸福与尊严不断尝试。总体而言,萨义德的对位阅读最终指向现世之中活生生的具体之人,也只有“人”才构成了萨义德音乐批评的初衷和旨归。
注释
[1]Edward W.Said.Musicatthe Limit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
[2]John Kucich.Edward W.Said[A].ModernNorthAmericanCriticismandTheory[C].Ed.Julian Wolfrey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6:68.
[3]Edward W.Said &Marranca,Bonnie.Criticism,Culture,and Performance:An Interview with Edward Said[J].Performing ArtsJournal.13.1 January,1991:36.
[4]Adel Iskandar and Hakem Rustom.Introduction:Eman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on[A].EdwardSaid:ALegacyofEmancipationandRepresentation[C].Berkeley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10.
[5][美]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M].朱生坚译.胡桑校.上海:三联书店,2013.
[6][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7]参见环球网:《新苏伊士运河开通埃及形象宣传片》第48 秒镜头,2015年8月10日,http:/ /v.huanqiu.com/observation/2015-08/7234440.html,2020年12月1日。
[8]Kojin Karatani.Uses of Aesthetics:After Orientalism[A].EdwardSaidandtheWorkoftheCritic:SpeakingTruthtoPower[C].Ed.Paul A.Bové.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145.
[9]赵玲.革命性、民族性、现实性——论威尔第歌剧创作的艺术成就[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
[10]杨晓琴.威尔第歌剧中的现实主义特征[J].音乐艺术,2014(4).
[11][美]萨义德.萨义德:在两个文化之间[A].[美]薇思瓦纳珊.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C].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24.
[12]Edward W.Said.MusicalElaboration[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
[13][德]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M].鲁路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14]1960年,法国导演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拍摄了一部展现集中营、反思纳粹历史的同名纪录短片《夜与雾》(NightandFog),由此可见《指环》与纳粹共谋的程度之深、影响之大。
[15][美]阿拉·古兹利米安.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巴伦博依姆、萨义德谈话录[M].杨冀译.侯珅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8.
——《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略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