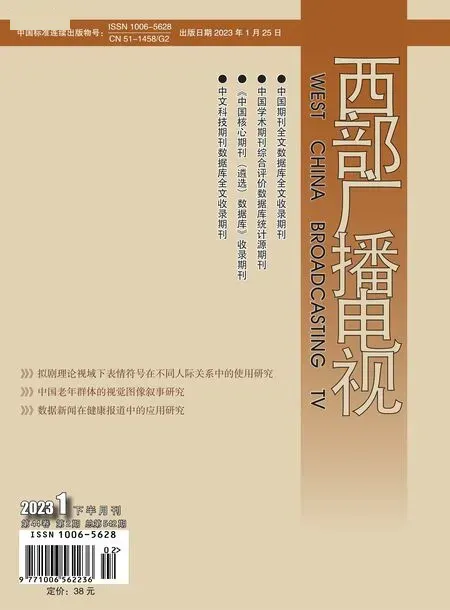突围、嬗变与觉醒:“孤岛”时期历史古装片《木兰从军》的创作之思
王 群 陈刘昱安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1937年淞沪会战,日军武力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从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军由于外交原因并未向英、法、美等国家宣战。因此,日军并未占领上海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却将这一区域包围起来,这一时期被称为上海“孤岛”时期。在这一特殊的社会时期,日寇及其卵翼的反叛政权,不断地从各方面加紧对“孤岛”的思想文化围攻,以期麻痹“孤岛”人民思想[1]。在日寇妄图收买“孤岛”电影产业之时,进步文化工作者也对“孤岛”电影界发出了忠告,并揭露了日寇的阴谋。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影片《木兰从军》与早期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影片形成鲜明的对比。《木兰从军》一经上映,便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创下连续放映85天的纪录,其影片内容与价值观的表达也恰好对应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在产生剧烈反响的同时,该片将历史古装题材影片推向了一个新高潮,为后来此类题材的影片奠定了类型基础。
1 突围——古装题材的大胆尝试
国难当头,“孤岛”电影的发展相较于戏剧显得尤为困难,几家主要的电影制片公司都因战火陷入停滞状态,大部分进步文艺工作者也选择了撤离,当时的上海电影界可谓是一片混乱。然而,地主和商贾的不断涌入,使上海租界繁荣起来,因此,中国电影行业也因为这畸形的繁荣开始复苏,并不断拍摄能够满足某些人低俗趣味的商业影片。一方面是各个影片公司为了获得眼前利益投机赚钱,另一方面是日寇汉奸企图侵占上海电影业,《冷月诗魂》《恐怖之夜》《武松与潘金莲》《地狱探艳记》等一系列封建低俗的影片就此诞生[2]。这些影片虽然质量不高,却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娱乐业的发展,以至于当时只要能够在上海这一市场进行放映的影片,基本都可以收回成本,甚至谋得大量的利益。因此,虽然当时的社会条件恶劣,但是上海这一“孤岛”地区娱乐业的繁荣却为历史古装片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张善琨看到了电影行业中的巨大利润,于1934年组建了新华影业公司,开始拍摄影片。1937年至1938年上半年,上海租界也只有新华影业一家电影公司维持拍摄,张善琨在短期内连续拍摄了十多部影片。巨大的商业利润使得其他竞争者也开始竞相拍摄。但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日本通过《上海租界对策要领》明确表明日本不仅要维持与西方列国的友好关系,更明确指出西方列国不能扶持与日本敌对的势力。同时,租界内的贼寇、汉奸秘密监视着各行各业的一举一动。内忧外患下,中国共产党带领的左翼进步电影工作者进行创作活动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在“孤岛”初期随着各个影视公司相继开始参与拍摄电影,竞相投机取巧追逐利益,影片的质量不免开始下滑,一时间整个上海电影市场被扰乱。这极大地引起了当时广大观众的反感,于是便有五十多位文艺新闻工作者联合发表《告上海电影界书》,痛斥当时的电影创作风潮,严肃批评了商业投机者拍摄的情色、反动的片子,指出这些影片会麻痹国人,电影创作者应当坚持操守,拍摄启迪国人思想的影片[3]。由于高压的社会环境无法拍摄抗战题材影片,就需要另辟蹊径,从侧面反映抗战,激起人民的爱国情感和抗战情绪,最优的选择就是古装历史题材影片。1938年4月28日,由卜万苍自编自导的历史古装片《貂蝉》在上海大光明戏院上映,其创下了当时的放映纪录,也成为“孤岛”电影复兴的重要开端,为而后古装片《木兰从军》开辟了一条道路。
当大多数电影工作者的创作还是摆脱不了低俗化的商业利益追求时,卜万苍已通过观众观影后的反响,意识到此时影片的一些缺陷。历史古装片《貂蝉》的热映,让卜万苍发现了历史题材影片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为了弥补前一阶段所拍摄的影片的一些不足,卜万苍便根据家喻户晓的《木兰辞》,邀欧阳予倩于我国香港编写《木兰从军》的电影剧本,而后影片《木兰从军》于1939年2月上映。影片一经上映便因其制作精良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真正将古装历史题材影片推向了高潮。卜万苍巧妙地选择了用古装题材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借古喻今,传达出民众的抗战决心,隐喻着浓浓的爱国思想,为“孤岛”时期电影创作找到了一个新方向。
2 嬗变——传奇故事的解构重塑
虽说“孤岛”时期的历史古装片带有20世纪20年代古装电影的影子,但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孤岛”之前的古装电影视听符号是以古代元素作为素材去创作,而内容绝大多数则是经过现代式改编,偏向于才子佳人或神魔鬼怪之类的故事,以新奇的故事内容去娱乐大众。如1927年由上海影戏公司出品的影片《盘丝洞》和1928年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影片《火烧红莲寺》,都以浓郁的神怪色彩、新奇的故事内容博得了观众的喜爱,满足了观众的精神需求。“孤岛”电影虽然吸取了之前古装片的创作经验,但在《木兰从军》之后,影片更多的是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将古时的民间文学进行改编,在这一特定社会环境中融入现实主义元素,在娱乐的同时也能够对民众起到教化作用。
2.1 改编与再现
1939年2月,在高压的社会环境下,卜万苍毅然将影片《木兰从军》上映,并得到了空前的反响。影片《木兰从军》以南北朝时期的《木兰辞》为蓝本,并结合当时社会情景进行改编。因此,该片的故事情节虽延续了广为人知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但其精神内核却在创作者的改编之下融入了更多的爱国主义精神,借以启迪民众的爱国之心,激发抗战斗志。影片以花木兰打猎与邻村男子刘元度发生矛盾作为开始,花木兰凭借自身高超的武艺,打猎满载而归。与《木兰辞》中“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这一花木兰织布的形象相比,影片在开端便展示出一种“谁说女子不如男”的英雄气质,为之后花木兰主动请缨,替父从军做铺垫。同时,影片开端中无论是木兰穿军装,还是模仿男性嗓音的故事情节,都给观众带来了观赏的趣味性,也能让观众感受到影片中花木兰的人物形象与印象中截然不同,是更加勇敢、主动、乐观地抗击外敌入侵的人物形象。片中花木兰与刘元度从相识到共同刺探敌军军情上阵杀敌,再到互生情愫,战后归乡喜结良缘的剧情设置,也为影片增添了爱情元素,多了一份对于美好未来的期盼。在当时大多数制片公司选择利益当前的时候,《木兰从军》将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以新颖的视角再现,无疑吸引了大众的关注。
2.2 隐喻与想象
卜万苍在《木兰从军》中,为了隐喻其故事内涵,大量使用了对比、反衬的叙事手段。这种创作手段虽然是电影创作中一种比较常用的技巧,但将当时的社会环境通过影片暗喻出来,再通过对比反衬的手法来警醒观众,在历史题材影片中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影片开始木兰打猎归来与村中孩童共唱的民歌“青天白日满天下,快把功夫练好他,强盗贼来都不怕,一齐送他们回老家”,可见剧情背景设置便与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同,暗指1937年日本开始大举入侵,国人应当自强抗击侵略者。当然,片中人物形象的设置也代表着不同的社会人群,花木兰、刘元度这两个人物代表着抗日爱国人士;韩奎、刘英二人则是思想愚昧、无所作为的人群的代表;元帅身旁的奸人代表国难当头虚伪奸诈的汉奸。这些直白且显而易见的隐喻,是极具讽刺意味的。相较于以往民间花木兰的故事传说,片中的花木兰形象淡化了对于替父从军的忠孝之感,取而代之的是浓烈的卫国之情,圆满的故事结局也在当时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同时赋予民众坚决抗战便能取得胜利的信心。
3 觉醒——意识形态的自我认同
1938年,日寇妄图收买“孤岛”电影,以实现对民众思想的麻痹,而当时的上海租界相比于重庆和香港地区来说更加没有政治自由,以电影和戏剧这两种大众文艺去正面宣传抗日斗争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通过历史故事,抒发爱国之情、展现民族气节就成了当时文艺工作者从侧面反映抗战、唤醒民族意识的重要途径。《木兰从军》叫好又卖座的原因,不仅是传统故事改编后能够满足观众的审美预期,更多是其故事所隐喻的内涵对当时社会大众有着启迪作用。20世纪30年代末,在外敌入侵、国家动荡的危急时刻,位于上海租界的民众也不再满足于那些讲述神魔鬼怪、封建迷信的劣质影片。那些曾在20世纪20年代泛滥成灾的侠怪影片,随着社会环境改变,其意识形态的表达也开始重塑,虽然其特有的“消解现实矛盾、淡化人生痛苦的‘娱悦’功能”和“刀光剑影的‘侠客白日梦’”功能在片中得以保留[4],以在焦灼压抑的时期带给观众慰藉,但片中更值得关注的是故事内涵催发了民众的爱国救亡意识的觉醒。
3.1 个体身份的觉醒
在“孤岛”时期,《木兰从军》上映之前,各影业公司为了利益,不得不选择“吃起老本”,重摄或重映以往的武侠、神鬼、僵尸、恐怖、艳情等类型的影片,使得中国电影业又回到十年前的混乱中[5]。在这样的文艺作品侵染下,致使原本就处在战争阴霾下的上海人民更加丧失“自我身份”。而《木兰从军》对于花木兰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无疑是当时民众找准自我身份定位的一个重要角色。片中花木兰的人物形象在改编后愈发饱满,除去最基本的“替父从军”“家国大义”这些元素,片中木兰对于战争的厌恶、奸邪的痛恨、爱情的向往都有所展现,结合时代背景,这无疑增强了观众个人身份的代入感。当然该片中除了着重刻画花木兰、刘元度这两位主要角色之外,对于韩奎、刘英二人形象的刻画也很鲜明,二人虽在出场时仗势欺人,刁难花木兰,但在最后见到花木兰建功立业恢复女儿身后,二人对花木兰流露出赞美钦佩之情。
3.2 社会意识的觉醒
卜万苍在以往古装题材影片的创作思路上,将《木兰从军》融入现实主义元素,剧中花木兰、刘元度等人物乐观、向上的性格在感染观众的同时,其故事的背景也与当下社会形势呈现出互文关系。片中故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具有相似性,都表现为战火年代、山河破碎、外敌入侵,彼时《木兰从军》的上映很难让人不联想到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花木兰在这乱世中却以女儿身站了出来,这无疑不是对于世人的一次警醒。因此,该片无时无刻不在暗示着群众应当站起来,去与敌人抗争,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最后的胜利。
4 结语
“孤岛”时期的电影界,虽然有着高压的政治环境和混乱的经济状况,但自《木兰从军》上映后,历史古装片领域产生了别样的繁荣景象。从1939年始,历史古装题材影片掀起了一股热潮,《木兰从军》的故事内核更是成为同类题材影片效仿的对象。至1940年,“孤岛”影界近半数影片为历史古装题材。后来由于政治原因,处于半沦陷地区的“孤岛”影业的繁荣现象引起了重庆电影工作者的抵制批评,他们认为电影应当是激发全国人民抗日积极性的宣传工具,甚至左翼电影人沈西苓也认为“孤岛电影的商业性质会消散民众抗战决心”。同时,时任上海伪市党部执委的卜万苍因其身份也受到重庆观众的抵制,因而也就发生了焚烧《木兰从军》的事件[6]。笔者认为,彼时对于《木兰从军》的抵制还过于片面,忽视了其内在的精神内核以及创作者所想要表达的抗日爱国情怀。
在“孤岛”时期,《木兰从军》这部历史古装题材影片的上映,无疑掀起了一股新的影片创作高潮。其内容题材的大胆突围、独特的叙事手法,以及隐喻的故事内涵,都为随后两年此类题材影片的创作指明了方向,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上海人民带来精神慰藉,激起了他们的爱国意识,更坚定了抗战胜利的决心。因而,《木兰从军》的创作在“孤岛”时期有着独特的影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