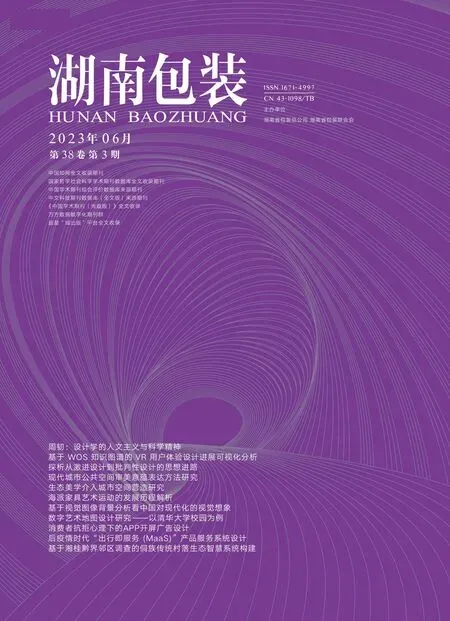基于湘桂黔界邻区调查的侗族传统村落生态智慧系统构建
1 国内外对生态智慧的认知
“生态智慧”概念最早由1973 年哲学家阿恩耐斯提出,生态智慧是研究生态平衡与生态和谐的一种哲学,其他学者认为生态智慧是生态哲学与生态实践的结合[1]、是当地人适应特定自然地理环境而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地方知识[2]等。其中国外关于传统生态知识的传承与保护,主要集中在传播与倡导传统生态知识从而融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国内关于传统生态知识的传承与保护,主要集中在继续发扬传统生态知识的作用、加大对传统生态知识的重视力度、生态知识的活态传承等方面[3-5],由此可知,生态智慧中关于传统村落的研究较少,特别是侗族的村落。
1.1 西方国家认知:从茫然到界定
西方国家民众生命观中认为他们是“上帝之子”,祈佑上帝福音并追求个性张扬与“自由”。在人、地关系认知中以攫取的姿态对待自然,进入工业文明后造成的生态破坏导致集体茫然,之后进入多向度探讨与界定,最终在实践层面切入生态智慧运用。20世纪50—60 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频发的环境问题(如“八大公害事件”)将生态思考带入公众视野并诱发民众环保运动及政府层面思考。1962 年,Racheel Carson《寂静的春天》出版,该书讲述DDT 进入食物链而导致生态系统失衡。尽管这只是一本通俗读物,但它被认为是“智慧生态”开端。伴随西方环境运动崛起及充斥哲学界反省为背景[6],20 世纪70—90 年代,西方国家生态研究从困境走向明晰,包括生态根源、深层生态学两个研究视角。根源研究旨在解释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给生态整体研究提供基础;深层生态学研究用30 年时间呈线性发展特征逐渐构建完整生态智慧理论体系,通过对生态内部知识理解、挖掘、运用展示生态危机时代下生态智慧范例,以整体主义实在论修正人类中心价值观。21世纪以来,“生态中心主义”“自然全美”“人本参与”等理念大量专著问世,生态智慧作为一个命题从过于形而上层面走向具体实践,最终将研究结果落在实践运用层面,探讨了生态智慧理论向实践转换的操作性,这一结果恰好符合生态理论价值指向及内在旨趣。
1.2 国内认知:从传统到提升
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但更呈现出地方特点,发掘地方生态智慧,解决区域性的生态问题,不仅符合逻辑,更具有实践可行性。中国自然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人居形态的丰富性,随着中国步入工业社会,环境问题得到政府重视以及学界的敏感把握,对如何提取中国本土灿烂辉煌的生态智慧成果,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
从目前研究来说,学界以民族文化传统挖掘及对西方成果借鉴为基础理论,并展开民族生态智慧提取、梳理、归纳及运用研究,基本涵盖4 个层面内容:第一,对传统生态智慧“接着讲”;第二,对国外成果借鉴;第三,对理论的实践运用提升;第四,对少数民族特质生态智慧的提取。
20 世纪末期,国内学界将研究目光转向生态智慧传统文化层面,解读传统儒道文化精神及农业生态文明,落脚在对自然、人、社会和谐关系“基本面”的把控,并从美学、哲学、生态伦理学、社会学等多角度进行再总结,如周银凤[7]对老子生态智慧对现代生态危机的启示,认为当前人类正面临着生态失衡的生存困境,审视和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找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源是拯救生态危机的必然选择。
21 世纪以来,学界对西方研究成果梳理探讨并用于实践,以西方学界生态思想为研究对象,试图全面、系统、深入解读,认为每一种生态智慧都可以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提供动力并关注实践向度;实践方向以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研究为前提,提出生态智慧运用尺度,如俞孔坚《桃花源与生存的艺术:我的治愈地球之旅》《复兴古老智慧,建设绿色基础设施》、李博《乡村振兴中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蒋思珩《“生态智慧与城乡生态实践研究前沿”讲堂》等,这些研究试图将宏观性与个案性相结合,并取得一定实践成果。
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空间生态智慧研究在近20 年来成热点,文献以个案、局部研究为主,多重视生态智慧特质形式,或在非遗传承、人类学和美学方面进行学理分析,并将传统村落生态智慧置于每个学科研究边缘或非中心地带,如王子研等[8]对聚落景观多样性的研究,认为人为活动对大型乔木影响较小,但对盆栽类灌木和草本类等小型可灵活栽植的植物影响较为显著。因此,以思想与实践高度统一的理论解析、构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中国传统村落生态智慧系统构架有重要学理意义。
2 侗族传统村落生态智慧构成特征
从视觉表象来看,侗族传统村落空间具有审美奇特度:民居排列鳞次栉比、灰瓦白带、青山绿水间或鼓楼高耸、风雨桥临河飞渡,呈现乡村祥和生态景象。但这一物质表象是如何形成的?物质文化并不存在纯粹的审美状态,而是承载着伦理与思想的目标[9],因此,物质表象与人群思想机制有内在关联。
马世骏等学者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概念[10]。经研究证实,侗族传统生态文化共同体之智慧系统有3 个重要特征,一是族群生命观,二是非物质文化传播,三是生态知识掌握运用。侗族传统村落景观作为一个物质结果,其形成流程包括:族群生命观核心—生态观念指导实践—集体无意识传承—生态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侗族人群对“天、地、人”和谐的生命观导引生态观念产生,通过“人”的实践实现物质化表达,从而形成侗族传统村落的生态智慧体系。
2.1 族群生命观的主导性
生命观是人们对生命本质和意义的看法[11]。对一个民族来说,生命论题始终是一个焦点,对生命探讨结果形成的生命观直接影响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对族群思想、伦理以及文化创造活动起到始终一贯的主导性。侗族生命观中认为“人”立于天地间,现实世界由天、地、人三部分构成,同时,对应现实世界的还有虚幻的“神”像世界,“神”像世界以趋吉精神弥补现实世界的不足。因此,“天、地、人”具有人性与神性二重文化属性,以文化生态的态度将三者有机联系与转化。尽管生命观以非物质文化形式存在,却在主体社会活动起到支配及无声命令的作用。由于侗族生命观中具有和谐统一的朴素意识产生生态观念,形成侗族传统村落生态智慧思想基础,主导着传统村落景观空间物质表达。
首先,主导了对待自然生态性认知,并分化为人性自然尊崇与神性自然附属两部分。侗族是一个迁徙民族,迁徙历程可从民族口头文学与民歌找到明证,如流传于榕江车江三宝千户侗寨祭祖歌《嘎斗莎》唱道:“想当初,真遥远,我们侗族祖先哪里来?老人传,老人摆,我们祖先从梧州、音州来。”“公公戴着斗笠前面引路,奶奶扛伞随后紧跟,爬山涉水沿河上,寻找幸福村。”“古州地方宽,三宝坝子平,我们祖先很高兴,决定在这里建寨落村。”[12]唱词描述先人迁徙、仰天俯地、选址建村过程,认为“地方宽”“坝子平”的地理环境有利于人居,注重环境的自然生态属性。侗族主体位于湘黔桂交界区约5 万km2区域内,该区域地理位置较特殊,是岭南岭北交界线、第二与第三地势交界线、亚热带与温带交界线交叉处,山多岭多地少。从实用意义上讲,平地、平坝较稀缺,但却是物质生产重要自然资源,也是村落选址重要考量因素,稀少与珍贵的自然资源使该人群对自然生态认知有较强尊崇意义始初。该结果也使侗族村落对自然环境充分利用,并形成有利于人居的生态圈层。从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金秀村、贵州榕江县大利侗寨的考察来看,村落、稻田、茶油林、杂木林、原始林的秩序排列感很明显。
其次,从族群核心文化认同来说,一种文化的传承必须有精神内涵的附属且形成约定俗成性,即对自然的生态认知需上升到民俗的约定俗成性才能使“核心文化”有被固定、传承的可能。侗族生命观中“天人合一”生态理念包含了人、自然与虚幻神性世界的和谐对应,在人与地的认知中导入民俗精神的神性思维并通过非物质文化定式思维进行传承,这一点主要反映在村落景观节点中,如鼓楼的功能比为乘凉、存鼓、登高、祭祀等场所,具有父系血缘的神性功能,往往选址于具有村落“地土”概念的中心位置;而位于村落后面的山岭被称为“后龙山”,以 “龙”神护佑村落发展。通过侗族生命观对自然的双重考量,侗族村落在生态认知上展现智慧之光,从而形成侗族传统村落良好的水土保持及绿树参天的外观视觉效果。
第三,侗族生命观主导了人群关系的生态确立,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族群对个体的人文关怀;第二,族群对祖先的神性崇拜,二者合一,展现出侗族人群生态伦理,并通过村落物质景观得以部分展现。群体对个体的关爱表现出人文情怀,如鼓楼里的火塘为聚集聊天的村民取暖、风雨桥为过往行人遮风挡雨、水井边的水瓢可为路人解渴。侗族族群生命观中,活着的人和逝去的人尽管活在不同的世界,但都以“活着”的状态呈现,如侗族为族群先祖萨岁建有萨坛,还派专人看守。通过调研观察,这种崇拜在贵州黎平、榕江及湖南通道、广西三江等侗寨中都有发现。由此说明侗族传统村落景观空间构建中,生命观主导了人群以生态的态度对待人与自然,并尽可能以物化的形式得以体现。
2.2 非物质文化传播的多向维度
侗族族群生命观凝练了对“天、地、人、神”的和谐精神,为族群创造生态智慧奠定思想基础,其目的在于构建完整生态系统以利人居。在文化核心至物质实现的过程中,非物质文化传播是实现该过程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段隐含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不被旁观者所关注,但其作用极其重要。“非物质文化传播分为纵向传播及横向传播两个维度,其中纵向传播主要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延续;而横向传播则主要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的文化信息向周边扩散的过程,侧重于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13]”由于族群对血缘、地缘的文化认同只限于该民族人群之内,所以非物质文化传播以纵向为主,从形式上来说主要指前辈对后辈的集体无意识传承。尽管侗族非物质形式及传播机制多样,但生命观对非物质文化观照有明显层次性,包括族群意义、人群意义、个人意义3 个层次,呈现由总体到个体的秩序性建构,由此非物质文化传播出现多向度。
首先,有族群意义的非物质文化传播多通过传说、民歌、舞蹈等形式实现,以起到对整体人群的教化。有首款词说:“未曾建寨先立楼,砌石为坛祭祖母,鼓楼心脏作枢纽,富贵兴旺有来由。[14]”该款词以非物质的形式传播了敬神敬族、建鼓楼、后代兴旺的生命观,而在村落空间中,萨坛、鼓楼不仅是神性场所,同样也是村民休闲、交流的场所,以人神合一的生态理念构建村落公共空间。当然,如果具有族群意义的生态空间遭到破坏,也会有口头文学等形式的非物质文化对其禁止,如天柱县乌龟寨流传一个故事:以前有个外人不懂村规,偷偷挖了寨子的后龙山,导致寨子里没有了水,后来只能做“招龙”“接龙”等巫术才使村子恢复正常。类似禁忌传说有很多,尽管没有实际关联说明其逻辑的正确性,但通过文化认同及历代传承实现了对生态环境保护功能[15]。
其次,有人群意义的非物质文化传播主要阐释族群内部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关系。对没有自己民族文字的民族来说,劝世歌就是人生的教科书和调解文本,以口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传承手段实现其目的。如关于斗气的劝说:“与人交往莫斗气,说话轻轻不费力。人生在世有时难免要受气,不要为争口气去做蠢事吃苦头”;关于相处的款词:“独木不成林,滴水难成河。一根绵纱容易断,十根绵纱能把枯牛拴。三人同行老虎怕,一人走路猴子欺。我们要像鸭脚板连块块,不要像鸡脚爪分叉叉。”[16]这些歌唱、款约等阐述了集体力量约定下人与人和谐的相处规范。在现实生活中,侗族群体注重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其结果在村落空间中也以生态智慧的方式得到呈现,并产生了许多具有生态观念的人居形态。如避免与邻里在地块上发生纠纷,木构民居往往主动缩小地面面积增大上层的空中面积形成上大下小的“倒三角”形;民居与民居之间没有明确界定,而是以“场意念”划分,从而出现宽松的交往空间。
再次,对于对个人而言,族群生命观起到制约及引导双重作用,在生态智慧宏观导向下,生活中的细节需要以尊崇的态度去解决,从而产生若干生态知识。如“酸耶”、酸菜酸鱼、墨理香杆、竹编技艺等。这些生态知识的产生毫无疑问是在生命观约定下形成,并通过口头交流、师徒传承等手段使得民族非物质文化得以传承发展,并形成具有地方意义的特质生态知识[17]。
2.3 生态知识遍布其中
生态知识是民族认知与相关生态系统制衡互动并积淀下来的结果。传统生态知识可以充分体现文化与生态的制衡互动过程,甚至历史上不可重复的生态事实和社会事实都能在各民族的传统生态知识中得到有效反映[18]。由于侗族是一个稻作民族,传统村落的功能在于生产与生活,而长期栖居此的人们通过生活经验的传承及交流产生众多生态知识,这些生态知识主要包括3 个方面的内容:生态实践、生态技能、生态精神。
第一,生态实践是生存与生态之间调和的实践结果,是人的意图对自然能动地利用。侗族历经漫长历史岁月积淀与磨合,产生丰富的生态实践知识。以水的生态利用方式为例,雨水(天上之水)落入稻田后植稻养鱼——通过挖掘田埂豁口排出(也可能排入另一块稻田)进入河流;通过水车将河水引入稻田(地表之水)——人造水渠实现水的自然流淌——水塘囤水养鱼——汇入河流。对水的生态利用催生众多生态知识,如水车、豁口、水渠生态运用实践等。第二,生态技能作为完整性传承的生态知识不仅具有“点”性特征,也具有“线”性特征。“点”性特征指单纯一项技能,“线”性特征指多个“点”性技能合作共同完成完整生态。如侗族民居构建由 “香杆”技艺、“墨理”技艺、“穿斗”技艺等协作完成,形成具有和谐人居的生态智慧技艺体系。第三,生态精神为规范的伦理道德体系,是人群与自然相处“非理性”过程带给人的经验并上升为一种精神存在。比如杉树被侗族所崇拜,甚至鼓楼的建造也按照杉树的外形,这种崇拜不被理解甚至被认为是迷信的信仰,杉树能带给人们什么呢?实际上杉树是该地区植物群落中的优势树种,说明杉树适应该地区生存且有良好生命力,如果生态遭到破坏,杉树都不能生长了,人生存也就困难了,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族群生活的生态精神具有强烈的科学指示作用。
3 侗族诗意栖居的理想关联生态智慧三要素
侗族有“饭养身、歌养心”的说法,而侗歌是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重要传播方式,其内容涵盖了日常生存、精神生存状态,并以含蓄的教化、有声的诗意反映了族群栖居理想[19]。
要使人类做到诗意栖居,则需要通过“自然”“人文”两个因素来构筑,既要依据生态学理念建立物质家园,又要通过文化需求构建精神家园[20]。从诗意栖居角度来讲,侗族传统村落生态智慧与栖居理想存在3 个关联,包括:“辨物居方”生态环境生成与生命观的始基性关联;“与祖先同在”的文化生态还原与非物质文化流播存在解构性关联;居安思“久”的生态约定与生态知识创造的统领性关联。
3.1 “辨物居方”生态环境生成与生命观的始基性关联
有学者[21]认为:“侗族祖先迁徒的年代,至早在唐代中叶,甚至在五代期间,也就是说,侗族定居于湘黔桂交界地区,也不过一千年左右。”尽管学界对侗族族源、迁移地址、时间等都没达成共识,但从民间传说、民歌等案例都能证明该民族属迁移民族。迁移是以“聚”为主,“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 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22]”这一论述与侗歌中说的“姓吴的住高坡,姓杨的住低岭,低处开成大田坝,高处开成棉花坪”有异曲同工之处,即群聚生活时代是一个人群集聚行为。形成由人地关系的正向理解及和谐处理结果形成生态环境观。在这一点上,侗族生命观指导了环境观形成,而环境也以实践行为充实了生命观,二者在初始时期存在基础性关联。
3.2 “与祖先同在”的文化生态还原与非物质文化流播存在解构性关联
侗族先民在建村立寨之初注重村落选址,体现了人地关系较好的生态性考量,村落选址的先期文化生态认为村落不仅能给他们提供生存条件,同时也能保佑后代人丁兴旺,但如何能实现这一夙愿是很难的。借助于人神共通的生命哲学,先划定一块“人类学常数”意义上的被称为“肚脐之地”的“地土”用以修建鼓楼和然萨,对创造世界范式行为进行神圣化。这种行为成为民族认同后经过集体无意识传承定势为“与祖先同在”的文化生态还原,还原主要表现在对原初事件的重复和模仿。有记载认为:贵州黎平境内遗存的一座酷似一棵大杉树的独脚(独柱)鼓楼可以为此作证。据传,这个地方曾经生长着一棵巨杉,村民在树下议事、唱歌、娱乐。后来巨杉死了。经商议,在巨杉生长的地方修建一座楼,以表缅怀之情。文化还原对族群自我的栖居理念的意义构成产生深远性影响。
3.3 居安思“久”的生态约定与生态知识创造的统领性关联
侗族人地关系生态考量具有居安思“久”集体约定特性,并对生态知识的认知与创造起到统领性作用。首先体现在对居安思“久”的集体思考,子孙后代繁荣发达是民族栖居理想重要反映,这一认知在种类繁多的非物质文化中得以体现,尤其是侗款的集体约定。侗款中蕴含着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环境保护意识,体现为“人与其他自然万物同根共祖、共生共存的生态伦理观念”,尽管款组织的一些执款严格及残酷在今天不宜传承,但从生态保护角度讲,该约定为侗族地区保留自然风貌特色自然环境起到重要作用[23];其次,自然环境与人居生活存在非理性联系,自然界可以为人类提供衣食住行的基本资源,但有些资源不能直接为人所用,必须由人的劳动、智慧参与并对其进行创造与转化才能符合人之所需。因此,在生态环境制约与侗族族群集体约定双重标准之下,侗族对环境的适应及改造催生的生态知识有明显的地方性及生态性两个特点。也可以说,没有这些约定与传承,侗族村落中也不会出现特质木构干栏的精巧技艺、美轮美奂的民族服饰及多姿多彩的民俗礼仪。不仅如此,该约定对侗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也起到重要作用,如“每年一到春天和秋天,全寨民众聚集到村中的鼓楼,寨老等头人出面宣讲生态保护措施,要求全体人员在此期间封闭式管理环境与资源,这样慢慢就形成了一种习惯法。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地传播生态理念的教育模式,值得现代人效仿。[24]”
4 生态智慧视角下侗族传统村落保护及优化策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是重大问题[25]。生态智慧研究是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重要视角。尽管生态智慧对当前国家亟需生态文明建设而言意义重大,学界也以众多文献量表明对这一研究的关注,但对生态智慧的体系构架、保护及转化研究依然没有明确且权威提法。侗族传统村落空间蕴含的生态智慧应对此有启示借鉴意义。
4.1 侗族传统村落生态智慧现实困境
项目组在2013—2020 年对湘桂黔界邻区侗寨调研,在7 年时间内侗族传统村落景观已发生许多变化,蕴含其中的生态智慧已遭到部分破坏,认为有两个重要原因导致村落景观呈一定负向趋势发展,即空心村亟需旅游带来经济发展导致传统村寨过度商品化现象。具体体现在二方面:一方面是生态智慧系统破碎化导致村寨普遍空心化。其缘由:首先,人口大量流失,原有生态系统得不到完整维护,“空心化”的显性体现为农村传统生态智慧表征的凋零而隐性体现为人的思想和文化层面的“空心化”问题[26],这也是侗寨普遍面临的问题;其次,侗寨生态智慧体系没有在村落保护中被提出,其不可视性没有被政府层面及村民所关注,重要的是没有提高到一个被认知的高度;最后,生态智慧作为村落景观中特定文化,生成这一系统的主体性人群并不能主导,而是由地方政府部门主导的规划具有地方性及行政性权利,原住民发声的可能性不大[27]。另一方面,村中空心化现象需发展旅游增加经济收入,但是过度商品化致使生态智慧系统不完整。美国学者科尔曼认为:“土地商品化这一发明创造才是特别具有革命意义的分水岭,而且也是人类亘古未有的事件。当土地被视为商品,人类社群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有机联系不复存在,自然坏境和人类社会双方走向大祸临头的境地。”随着侗族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加速,产生的生态问题层出不穷[28],致使传统村落生态智慧体系遭到破坏。以程阳八寨为例,首先体现在村寨体积不断扩大,在7 年时间里,该村落的建筑体量增加无度,但这并不仅仅是村落人口增多而导致,关键在于“抢地盘就是抢钱”的理念所导致。单体建筑空间变大包括建筑高度及单层人居面积,从高度来讲,侗寨民居一般高度界定在12.5m 左右,为两层半的高度(顶上半层放置杂物)现在的新民居普遍增加到3—5 层,一般下面一层或两层为水泥、砖混,3—5 层为原有干栏式木构,对于这样的改变,村民认为“不管是拆迁还是做宾馆都能赚钱”;还有就是村落外围在无序生长,停车场、新建民居、道路穿插出现使村落生态节点破坏,原有的生态秩序难以维持,这些现象不仅不符合侗寨营建之初的生态智慧考量,在视觉上也出现了不和谐。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还不只体现在人居空间,原有的生产空间如田园生态也在遭受破坏,包括部分土地抛荒、改变种植等都做法都使原有生态链条断裂。这样做的结果并不如人所望,本以为改变结构能吸引游客增强收入,但实际上,旅客在欣赏侗寨视觉景观的同时,更享受浸染在侗文化中的过程,将消费侗寨视觉与体验生态智慧合为一体的整体感受,而不断侵蚀的生态反而使景观失去吸引力。从生态智慧的保护意义上来说,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在短时间内很难逆转。
综上所述,主导部门对生态系统认知致使其在保护规划中难免使生态智慧链条缺失,侗寨在表面上看似存在景观破碎显现,实则隐含了生态智慧系统破碎。
4.2 侗族传统村落生态智慧优化策略
“土地养万物” 是中国人对土地的崇高理解,这一理解不仅体现着人对生命、生活和生计的功能性关注,也嵌入了精神、社会和伦理关怀,也就是说,关于文明“社稷”家园、人生哲理皆寓于土地之中。由此形成的生态智慧在人居环境中生成系统完整性。从这个角度讲,对生态智慧的保护应采用整体性保护原则。从现阶段来说,仅仅从物理空间进行保护还是有缺陷的,尤其对具有生态智慧的传统村落来说,其保护内容还应包括人群的核心文化及具体情境及不能可视的智慧关联。因此,对侗族传统村落生态智慧要施行整体保护策略,其环节应表现为:确认认知—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合理区分保护层次—保持重点区域和重要场所的文化风貌—确定原真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创新性利用。在这个环节中,确认认知是首要的也是重要的,侗族传统村落生态智慧历经几千年积淀而成,其中隐含的文化、技艺需抽丝剥茧认真梳理、挖掘、提炼,以形成保护传承基础。合理构建评价指标是其中重要环节,只有导向正确评价合理才能真正将这一传统文化用来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态乡村问题。合理区分保护层次指的是将侗族传统村落的各区域分区、分层进行保护,对村落最原始且易忽视的地区给予重视,区分出重点保护区域和重要的场所,以确保侗族传统村落的原真性与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实现创新性利用。侗族传统村落生态智慧是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的特质之处在于没有终点,至今,尽管其传承保护、发展都遇到了农耕文明没遇到的问题,但中央文件对乡村振兴的提出也使其迎来了历史性转机,因此,不仅将侗族传统村落智慧“接着讲”,还要将其发扬光大,而合理转化是整体性保护的延展手段。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先人们对于生态问题的认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且在传承中积累了较完整的生态智慧体系。这也是中西方不同之处,站在中国当前发展的转角处,传统生态智慧需要另一个“转化”,即运用传统生态智慧进行研究和开发,转化为符合当前乡村振兴视角下的人居环境,但如何转化是一个重要问题。从目前侗族传统村落生态智慧转化来看主要集中在3 个方向,包括旅游开发、照搬侗寨样式构建特色小镇、乡村振兴。
从旅游角度来讲,结合近些年对传统村落的开发与打造可寻到一些端倪,如侗寨、苗寨等传统村落生态游日趋火爆,这与当今打造的特色小镇呈冷暖不一的现象有所区别。除却经营手段等因素,窥其本质,一方面,传统村落人群生命观的传统文化展现上有无可比拟的完整性,并通过生态性非物质文化叙事结构以物质形式体现,使游客产生远观、近观、品味、教益等多重效果;另一方面,生态文化传播使对非物质文化能够进行编码及解码的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气质。通过具体的非物质文化,特定群体中的个体通过文化的纽带感受到他人的存在,并能够理解同一文化群落中他人对世界的感悟。因此,在侗寨旅游开发的同时要注重对原有生态智慧系统的维护与合理开发。
依据侗寨景观构建特色小镇的例子也较多,如南宁市相思湖小镇、三江柚上小镇、丹寨特色小镇、新晃侗族特色小镇等,这些案例从视觉上还原了侗寨特色,力图以侗寨特色为起点,打造生态游、文化游等多重目的,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也做得很成功,但对侗族传统村落营建的生态智慧都有缺失。“不管农村旅游特色小镇采用何种运行模式,其本质都是需要建立一种能够在多方面实现自我循环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在经济体系层面上,必须要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不断循环往复,为小镇的生存、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只有这样小镇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平正义的环境,进而解决发展不均衡、生态恶化等一系列问题。[29]”从这一点上来说,生态智慧体系构建可以对特色小镇规划设计起到基础理论及实践运用的启示性作用。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必须与时俱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因此,侗族传统村落生态智慧对改善广大农村地区人居环境有启示性,如在人居环境改善、规划设计方法及传统文化要点传承等,从而营造出温暖、熟悉、亲近的空间体验,建成舒适人居的建设目标。
5 结语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也不是包含,而是双向互动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人的“智慧”活动驱使人地关系 “合理化”。从侗族传统村落调研来看,生态智慧有物化及文化隐含双重属性,由该族群所创造并反映其人地关系,凝练了族群文化精华,表达了人群生命观,通过多向度传承,催生众多生态知识点,构成生态智慧系统,而这一系统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其挖掘及运用对当今社会发展有启示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