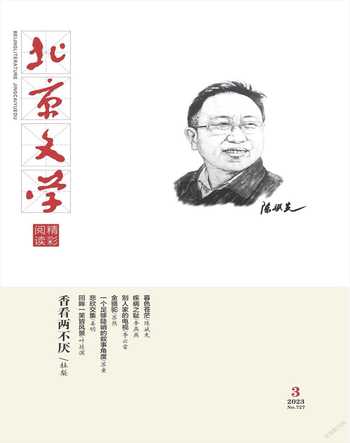妫宴
一切都始于一个叫生子的人。
是夜,生子从被窝里坐起来,忍着浑身酸痛,慢慢把手伸向土炕沿,摸起长柄手电筒。
生子心里有事,睡不踏实,漫漫长夜像母亲手里的面片被揪成了许多细碎,像极了他父亲去世那天,母亲用剪刀剪碎的二姐的新棉布鞋面,很久以前他在二姐藏私人物品的水泥方缸里,找到过那些碎片,他把碎片拿在手里,那些纯棉布做的鞋面已经朽烂了,纤维失去了经纬的约束。在母亲发疯似的在鞋面上用过剪刀之后,大部分碎片后来都找不到了,但它们并没有离开生子,反而在无数个生子无法成眠的暗夜,出现在生子的脑海里。那些暗红色的纯棉布碎片,有菱形的、三角的,也有没剪出形状的,在它们滑落时,生子还能听到它们说话的声音。那是一双要了他父亲命的棉布鞋,也是他大姐人生第一次对一双新鞋有了向往而酿成的大祸。出事不久,也就是父亲七七那天,大姐左胳膊上戴着黑孝箍离家出走了,据说她一辈子都恨自己。可生子知道,父亲的死不能全怪她。
生子提起木门减轻了门与轴摩擦发出的巨大声响,走出沉睡的老屋,朝院子西南角茅房附近的窨井走去。这是2004年的初春,生子四十有二,是妫村的村主任。此前,他来到老县城,在城南寻得一处阔院,成立了一支二三十人的建筑队,专门给大工程打边围,包揽一些建筑方面的零工碎活,别看只是给人擦屁股,可这都得看人脸。一来二去,他有了想法,弃商从政,总算在妫村直起了腰杆。
连日来,村里遍布含糊不清、稀奇古怪的各抒己见,使这一百多户人家就像要面临一个重大时刻。市里的、区里的、镇里的重要人物,越来越多地来到这个闭塞的四面环山的叫妫村的小村子,他们一一看过村里现有的房子,然后聊着与盖房有关的事。村民不时出现,却并不靠前,他们当中耳朵好使的,听得一句半句,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远远地看着重要人物们皱眉头、摇脑袋。有时快速深挖土层,掘进一米多深;有时又把刚铲出的新土晾在那儿,一晾就是好几天。生子默不作声,待那些重要人物一拨一拨走后,他站到挖开的土层附近发呆,直到蹲得两腿发麻,才伸出手去,量一量用白石灰新画出横横竖竖的线,每条线都有巴掌宽,直直的,交叉处又圈了一些符号,那时,生子还不知道整个妫村都被一种神秘笼罩,在充满生石灰味的空气里屏住了呼吸。
皎洁的月光下,生子从窨井里提出一网淡水鱼,那是他踏过河边的菹草、金鱼藻、穗状狐尾,蹲在芦苇和香蒲丛里,用细网从妫水河里网的麦穗鱼、拉氏鱥、棒花鮈,现在它们大大小小地被他倒进白铁皮盆里,在它们身边晃动着生子匆忙而利落的身影。
在生子看来,只要今晚把这锅老醋闷杂鱼往桌上一搁,三位姐姐“嘚嘚”一通说,怎么也能说服母亲大人,同意他把这座老宅给拆掉。他不能光说不练,他得干出个样,让村民瞅瞅,他是第一个带头拆房的,他是全村第一批划片的第一家上铲车的。他径直走到东边棚子下的碗橱前,从最下面的抽屉里取出了只有过年、姑爷上门,或者来了顶尊贵的客人才用的、描着缠枝莲的青花瓷碟碗,往水盆里一浸,水面上立刻浮起黑灰色的一团,轻轻地飘动的煤灰,用水冲洗干净,他又兑盆热水,仔细洗过手和脸,开始刮那些络腮胡的胡茬,然后,特意穿上媳妇新给他买的蓝格子衬衫。他心说,用这么好吃的家宴,引诱姐姐们出马,到底成不成呢?别看生子长得眉眼清秀,他生来嘴笨,母亲说他嘴笨心实。嫂子们则调侃他,嘴笨得跟棉裤裆似的。二姐当着外人从不向着生子,她紧找补,还是放个屁三天绕不出去的臭棉裤裆,都有味了。二姐自从大姐离家出走,便包揽了大姐的义务。她那张嘴能跟母亲势均力敌,三姐和四姐就只会说,谁说不是呢。
他是事先給家宴定了调的,就为在村里开个好头。
太阳当空,树叶有些疲惫,它们的暗影在满是尘土的路边,窄窄地成了靠近山崖的一条。没有一丝微风穿过干燥的正午,却把路上粗糙厚重的尘土沾到裸露的躯体上。生子心里的火终于从他的嘴唇上燃烧起来,很快,烧出了一长串大小不一的水泡。人和,是从家和开始的,可生子知道自己的嘴说不过母亲,更说不过姐姐们的三张嘴,他只能用了心力,花一整天工夫把杂鱼焖香了。
一家人围坐在只有25瓦,拧在黑电木螺丝口里的电灯泡下,这已经是砖搭瓦垒五间正房的小院里,最最正经的、仪式感很强的时刻。可是,生子媳妇把碗筷刚布置到位,饭桌上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二姐说,生子你甭想让我拆房,甭想,我那房刚盖的,是全村最好的房,农家院的执照都起了,这两天就办下来了,我不拆,我也不劝妈拆。二姐这个开头就很有些强势,完全把生子的意思弄拧了。生子还没反应过来,三姐说,生子,我那房是赖,可我不偷不抢不欠债,你贴村委会的建别墅费用公式我都按我家情况算下来了,一处别墅国家按人头补贴,区里镇里村里几下再补贴,去掉了全房款的大半,可剩下的小半咋办?你让我背债,那我可不干,也不是我不干,是你让我拿啥还?是身子还是命?这是序曲,接下来,她们一一历数了生子一直以来在这个家里得到的实惠,作为老来得子的母亲是多么待见生子,生子之所以有今天,正是母亲为他挡了“枪林弹雨”。
生子听出来了,姐姐们不要娘,也不要弟弟,她们都各自说她们自己,由于双方的力量太不对等,反而让强势的一方,因为生子不及时还嘴,吵得带不起节奏,感到很气馁,很难尽兴,很受委屈。无法正常发挥的姐仨,加上母亲,都瞪着生子,生子感到目光灼灼的戳痛,他肚子里的话反而又往下沉了沉,这无疑激怒了人多势众的一方,变成了她们自己阵营里愤怒的争执,起初生子感到很生气,不知是生自己的气,还是生姐姐们的气。二姐又说,你别以为别人不知道,你应名盖别墅,是在嫌弃爹妈给你盖的房,咱爹妈这辈子只给你生子盖了房,你倒最没良心!母亲一开始还坐在生子媳妇旁边,接过生子媳妇给添的饭,她身子没动,心已经站到闺女那边去了,这真是,灯芯不挑不明。母亲说,我现在就烧香,跟你爹说说去,老头子啊……
这就不是吃饭,是吃气了,生子气不打一处来,姐姐们别的作用没有,倒是把母亲的心给彻底伤透了,几个女人雨天的蛤蟆似的,背上湿肚皮湿眼睛也湿。
当村民们得知生子在鼓捣“别墅”,“别墅”就像舌头一样长在了所有人的嘴里。老书记在部队带过兵,见多识广,他说,这俩字,笔画不简单,不会写不丢人,念错了丢人。因为,养兔子、放羊又在村里开着豆腐坊的生子二姐夫,就把这俩字念成“别野”,经老书记一一纠错,总算在全村统一了口径,念对了这个新词儿。大多数村民不明白生子为什么对别墅这么上心,生子也不解释,他打定主意,到时候请大家伙撮顿饭,在他看来,村里的大小事,没有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生子所在的妫村地处燕北,是著名的北关锁钥,隶属军事要冲,大量兵器冶炼生铁的需求,奠定了这里的奇特社火和人文,不仅使成吉思汗的骁勇骑兵败在遍布铁蒺藜的百里山沟,还使这里成为冷兵器圣地“辽代首钢”。由于林木覆盖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妫村四面环山,依在妫水河右岸,并行有大秦铁路,而且,两年前考古工作者就在村西发掘出辽代冶铁遗址,有关部门还专门给立了汉白玉的标志碑,这都是开展旅游业的好由头。
就像人跟人不同,村民的期许跟期许也是不一样的。有人只想亲眼看看生子手里的《别墅规划图》,有人更关心具体的别墅内部结构,干过工程活的叔叔大爷们就不一样了,他们一张嘴问的是砌三七墙还是二八墙。就这样,村民嘴里交替念出的“别墅”就和生子缠绕在一起,生子就像一种令人希冀的野火,和“别墅”一起在他们的世界里燃烧起来,又掺杂着想一探究竟和佯装事不关己。只有生子的母亲,人称妫大娘,站出来说,没有生子,你们几辈子能知道,这世上还有个好住处,叫“别墅”?别看生子是她四十三岁时生的男孩,自从有了生子,她终于可以说硬话拉硬屎了。有生子之前她一共生了四个闺女,直到有了生子,她才活得有里有面,她知道自己的脾气得罪人,生子执意拆家,只不定多少人跟着解恨呢。
坐在村西峭壁边的冶铁炉前,生子立刻分裂成俩,一个是妫水河边的村民生子,一个是立志要让家乡脱胎换骨、脱颖而出的村主任生子。作为村民的生子完全可以像老辈人一样端粗瓷碗,吃时令饭,可当了村主任的生子让村民生子有了梦想。
生子想大姐了,因为大姐跟家里这些女人不一样,生子出生时,大他二十岁的大姐年纪都赶上村子里当娘的女人了,生子清晰地记得大姐离家出走那天,在村西北出村的路口遇到了他,生子正在美美地吃着刚出锅的火勺,在妫家母亲只给生子一人这种优待,生子总是吃独食。生子记得大姐看着他,把他手里的火勺连同他的手一起握住,握了很久,然后放手,走了。生子长大以后,一想到饿着肚子、心里憋屈的大姐,便对自己说,等我混阔了,一定把大姐接回家,全家人一起吃顿好的。
生子突然听到一声叹息,仿佛是大姐在说,我干吗非要穿那雙不跟脚的鞋?现在看来,大姐离家很远,却一直都没有走出父亲出事的那个夜晚。在这个家里,生子跟大姐最好,大姐比娘还疼他,而且跟娘疼的地儿不一样,娘只关心他的饱暖,大姐更关心他的学习,有一次还说,只要生子你考上大学,大姐累死也要挣钱供你。可生子不爱学习,一看书就脑袋发胀,倒是当了村干部以后,才理解大姐,知道大姐有格局,后悔自己书读少了。他坐在那里,做了人生最艰难的抉择,因为他知道人没有信仰只是活,有了信仰才有信心和动力去创造梦里见过的生活。
第二天清早,村民待在家里都感到了大地的震颤,那是围住生子家的几台破拆机和挖掘机,洒水车把柴油机发出的沉沉的味道,扬洒到晨雾之上,飘出很远很远。此刻,妫大娘没有出现在围拢过来的人群里,她是见过世面的人,知道生子昨晚受了三位姐姐的致命打击。所有的村民出于好奇,都围拢来看他们娘儿俩,当看到他们时,个个都显得非常吃惊,那些想看笑话的人都不好意思了。只见生子目不旁视地从他们面前走过,跟工程公司的技术人员说好他的安排,便进屋关掉了电灯,然后,指挥工人们搬运那些母亲视之如命,而在别人眼里只是家常的物件。随后村民们看见生子背着妫大娘,跟在抱着他儿子的媳妇身后,他们像是从模子里浇铸出来的铁锭,神情中有金属般的刚毅。
这时,旁边院里响起一阵野兽才有的粗鄙嗥叫,是生子的四姐,被生子背在背上的妫大娘铁青着脸,尽量让人看不出她一晚没睡的样子。生子听出来了,哭声不只是四姐还有柔弱的三姐发出的嘤嘤声,那是从来没被人欺负过的人才会发出的哭泣。接着,两委都到齐了,现在,妫大娘搂住生子,一声不吭,她不再是全村最矫情、最护犊子、最能讲自己道理的人,真正有手段又令人讨厌的老年妇女,而这样一位母亲,她不是想通了,是心疼自己的儿子。生子听到身后传来推倒房子的声音,先前充满柴油气味的空气里夹杂进土腥味,生子家的方向,腾起了一房多高的烟尘,生子已经把母亲背到了小学校,两人都是满脸泪水,为了不让母亲看到自家老宅轰塌的场景,他用身体挡住了母亲面对的小学校教室的窗户。可楼道里响起局促的脚步声,是施工公司的总工来了,见到生子就说,第一排进展顺利,第二排事主不让拆!你是知道的,我们施工单位的重工机械是租的,按天计付的租金可是真金白银,不能按原计划走进度,就不只是延误工期,租设备的费用得由你们村委会出,因为你没有给我们施工单位提供施工条件,你得负全责。
那个钉子户是谁?生子问。
你二姐。
生子一进二姐家,就听到了隆隆的洗衣机在转动,二姐在院里拴好晒衣绳,正在把第一批甩干过的被单往绳子上抛。生子上去把电闸给拉了,洗衣机一下没了声息,跟二姐一样闷在那里。二姐原本见他从外面进来,就知道他无事不登三宝殿,根本没给他好脸,可没想到他这么绝,于是嘴炮立刻架上了,说,让我把这点衣裳洗完吧。生子说,不行!现在就拆,通知已经下达了,别人都搬,你不搬,影响的是全村的工程进度。那你姐夫不在,我可搬不了。二姐在给自己借口。不用我二姐夫,您在这儿瞅着点,我找人搬!说罢,生子已经走到当院,老支书带着民兵,紧着大件开搬了。
生子觉得挺对不住二姐,因为,就在刚才走出二姐家时,他看到了掉在地上的装修设计图,真不错,这在全村都是顶超前的,生子叫它,顶配。无论是盖房还是装修,二姐两口子都是动了心血的,心是心思,血是全部积蓄。明明人家就要革命成功,你一铲子下去,给挠平了,搁谁不肝疼呢?生子默默地对自己说,生子呀生子,你这辈子要还能活成人,你就得对得起二姐。
当第一批三排别墅从妫村耸起,外墙粉黄相间顶着红顶子,这里就成了远近闻名的临时参观景点,后边的一百多户拆房合同顺利签完。这年冬天,刚搬进新居的村民就享受到地源热泵的动力澎湃,家家都穿得跟要下河摸鱼似的。让那些之前不想拆房的,想在新房里搭火炕的,说出一串串笑话。那些曾经不赞同别墅,签字时打退堂鼓的,都关紧房门,听任媳妇用说过多少遍的话,又把他们恶心一遍,村民们倒是都把独自打吊瓶的生子给忘了。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生子终于长出一口气时,气象台发出了暴雪蓝色预警,突然跳闸、停电,妫村像一下子沉没了。生子举着吊瓶检查线路,结果是因为使用地源热泵,比过去使电热器用电功率大,需要及时增容。可天一亮,生子就傻眼了,雪,一般的地方没过小腿肚,山坳里齐腰深。电力工程公司根本不同意在这种路况出车,还说,唯一的办法,只能给有老人孩子的人家多抱几床被了。生子一听这话,眼睛都红了,为了动员统一使用地热,炉子是他一家家收缴的,母亲和刚生了二孩的媳妇都待在凉屋子里呢。
刚一进村,就见老书记已经手拎撬棍,从雪里挑出一把铁锹,这是全村第一件清雪工具。老书记说,咱村通电力工程公司只有一条唯一的路,就得过瓦庙岭,那里有一个长隧道,地势险要,山环水绕,是事故多发地段,雪是水做的,可有分量呢,铺在这条长达二十多公里的山崖上,随时都有让全村人希望破灭的可能。生子也知道,从妫村西去,坡大弯多,但只能先把路清了。村民一听,二话不说,握铁锹、拿手铲,也有几个推车背筐的,男女老少手里都没空着,实在没工具的攥着扫炕条帚。老书记说,得去找平头锹,铁锹是清除冰块的神器,缺点就是清理面积小,又特别费劲。妫大娘说,我有办法,我在县环卫干过,使过清雪铲。我知道清雪铲可以做成清雪车,等清雪车把道路中间的积雪清除,剩下的积雪只能靠人工了。生子一听,暗自叫好,老妈真给力,咱这就找木方、铁皮做清雪铲和清雪车。
当村民们手脸通红,帽子围巾上罩着一层霜壳,出现在二十多公里外的电力工程公司时,负责人吃惊地看到公路上的雪竟然被村民铲得毛都不剩,疑惑地说,难道你们借了天兵天将?这时老书记说,瓦庙村里有饭馆,招呼生子和村民一起去吃饭,热屋子让大家的眉毛眼睛嘴都活跃起来。热水来了,拎着热水瓶的妫大娘则一眼看出生子不对劲,生子连眼皮都没抬,头和肩膀都耷拉到一块儿去了。
生子,你咋了?她这一喊就岔了音。
村卫生所的女医生来得挺快,是位刚生过孩子的小媳妇,从没见过这么紧急的情况,她紫着一张脸,用听诊器听生子的心肺,看着她的人,都緊张得快背过气去了,只见她摇摇头说,得送县医院,血压都下来了。
其实,别墅盖好,装修完成,生子面临村主任期满,让生子万万没想到的是,历经九九八十一难,非但没得到村民的礼遇,还在操心费力后失去了选票。据说,村里几乎有一半人不打算再投他,而媳妇说,自家姐姐都不敢挺他,怕与村民闹对立。生子名正言顺挺直的腰杆,反而塌得比当村主任之前更厉害了。他找好了出外搞建筑的退路,决心背妫村而去,像极了当年的他大姐。因为有了地源热泵,生子挨家动员处理原有的铁炉子,不让囤煤,甚至还亲自上山拦下了几拨拾柴火的,当时他怎么夸下海口,现在就怎么被啪啪打脸。雪把妫村人冻成了三孙子,生子是耷拉孙,他埋头用铁锹尖去錾路中间的冰脊,满脑子都是被自己从各家翻找出来卖掉的生铁炉子、处理的烟煤、扔掉的劈柴……扫雪的人里,不止他有上了年纪的娘,刚生下娃的媳妇,他不豁命干,还怎么有脸活人?没想到差点一命归西,竟让他的人气涨上去了,生子不光连任村主任,还上了电视,受到表彰,远近闻名。
当各路媒体相跟着离开妫村,小山村恢复平静后,生子发现了一件怪事,大白天的空街静巷,别墅虽好,罕有人声。媳妇说,天没亮大家就出村挣钱去了,都害怕背账。生子终于明白村民在忙啥,是在抓挠欠下的债。生子的心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揪起来,这债是我欠大家的,以前我只知道上传下达,欠也只欠村民一顿饭。现在,妫村率先完成新农村改造任务,上了报纸电视和广播,却让全体村民成了债务人,这让没有一分土地的山民,得还到驴年马月?生子啊生子,你欠下的是这世上最最难还的人情债啊!当生子奇迹般地路遇三姐,问起她出去一天挣多少工钱,三姐说,当小工一天十块,人家嫌我没劲儿,要给五块,五块我都去,欠钱背债,可不是人过的日子。人家城里人还房贷用工资,咱农民有啥,命?命没了,债还在啊!生子生生地把自己的梦搬来扣在全村老少的头上,那哪是履职、完成任务,何况任务真的完成了吗?
冶铁炉旧址前坐着的生子变了,讲究里面儿的生子不见了,他变成任何年龄任何模样任何性别去踏任何门槛,去求能求与不能求的任何人……他铁了心合着眼厚着脸皮去求施工单位把外包的苦累脏活交给村民干,人家不看他,听着都新鲜,工程质量谁负责?预算配套谁保证?生子从没啥缝隙的嗓子眼儿里发出的声音,就更含糊、哽咽、嘶哑了,字与字之间拉着血丝,再讲出话来,让人听着都疼。从此,妫村只要出工就按人头份算钱,修路挖沟,淘河打堰,砌井埋线……扛着植苗上山,垒起崖石护坡。一开始,有五十多岁的壮年不服,说自己干一天出的体力,哪能跟那些老弱妇孺得的钱一样?生子说,谁都有个老,谁不是打小时候过来的,谁没姐妹媳妇姑姑姨儿?各家的债在她们心里压着,那分量比爷们儿更大更重,像座山。生子求人求得说话都顺畅了。打那往后,只要生子求来活儿,全村老少个个都成了生子,跟紧生子,豁命干。
媳妇说,生子,你爱说话了。生子说,话总得有人去说。媳妇说,生子,姐姐们在说吃温居饭的事,按说这顿饭是为了今后主家日子过得好,她们想让咱妈攒局,咱家人在一块堆儿吃。为什么?生了问。媳妇面有难色地说,大家都搬进了新家,温起居来,一家得出四套份子钱。生子说,二姐做饭好吃……媳妇说,好些人请二姐去帮厨,二姐也应下了约她做饭的人家的温居饭。再说,生子,咱家还好说,跟街里街坊咋回说呢?已经有好几家要先给咱家温居,咱总不能不给人家预备饭吧?
有饭,咱全村一起吃这顿饭,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妫宴。生子说。到时候,把咱村嫁出的闺女都接回来,好好团圆团圆。
把全村人叫到一起吃“妫宴”的事,一安排下去,大家可高兴了,都觉得这是好事,省了这一百多户你请我、我请你,再说都盖了新别墅,这得请吃多少饭?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何况,那些为盖房已经家徒四壁的,正愁没钱请客、回礼、出份子呢。
妫宴终于做得了,小胳膊长的蒸面鱼也上桌了,生子举起酒杯,嚼着烧茄子浮头撒的生蒜瓣,刚要下令——开席!三姐夫风风火火地说,快着,收文玩核桃的车,被拦在南边坳口了,说话就要打起来了。
生子知道三姐夫是个闲不住的人,不用说别的进项,单说他倒腾鸡心核桃,就是一招鲜。可今天有人挡了他财路,他当然着急,让生子想不到的是,三姐夫接下来说,有人在南边坳口拉起横幅,怕车往山里来,客人都到咱村吃饭,路一通他们的财路就断了。那是妫村进北京城最近的道儿,几百上千年来一直没打通。生子愣了半晌,憋在心里的话终于说出来,光盖他奶奶卷儿的房不成啊?客人到了家门口,咋不请人家进门来吃饭啊,路不通,进不了城,咱坐在山底盆里,是山民,不是市民。
生子,这不能怪你,谁让咱村自然灾害多发,年年一下暴雨,村干部都往山上跑,就怕山洪不是好来,谁敢修路啊,水一过来,还不是得冲垮?老书记说。
现在不一样了,周边的治理都完成了,出山的路可以修通了,走!咱把路修通,把客人请进来,再开宴!生子说罢,已经欢着双脚走起来。
生子,修路得先有规划,按手续来。老书记说。
咱妫村今儿就出山了,有问题,我负责!生子大步迈过设宴的村南文化广场,村民纷纷离席,闻声而动,你追我赶,浩浩荡荡,人们同时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同频共振。这时,母亲的电话打过来,没有称呼,没有问候,就说,你大姐回来了。生子像是突然醒了,嘴唇鼓了鼓,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生子记得,大姐很早就挣钱,她跟着父亲到货运火车站干活,原本站上是不用女工的,可家里实在需要钱,生子的大姐从小山上地里干活,皮肤黝黑,没什么胸,身板干瘦,跟个小子差不多。父亲姓妫,到了站上大家都叫他妫爷,见没人肯跟她一组,就留下她,也为照顾她,让她跟自己一组,从货车厢里往下卸货。大姐跟生子一样不爱吱声,倒是听老二(也是生子的二姐)说新买的鞋下水一洗,布鞋面就抽了,她乐了。心想,在家她是老大,可她个子矮,脚也小,没穿过新鞋,倒是老二长势凶猛,家里总是给她买新的,她穿小了再往下传,老大就被老二硌过去,穿得实在不入眼。从这天起大姐就惦记洗抽了水的新布鞋,她看着老二把鞋放在鹰不落的南院墙垛子上,天没亮她光脚抱着那双半湿的新布鞋上站,跟在父亲身后蹚过妫水河,往脚上一套,就发现鞋大了。这时走在头里的父亲已经拎起一人多高的长撬棍,准备去捅车厢底板上的铁销子了。那铁销子上方是平的,下面有弧度呈半圆形,从左向右捅,捅差不多了,还打不开,因为一节车厢有好几组呢,得两组一起捅开,车厢距离地面有一人多高,他们各自手持长撬棍向上捅铁销子,随着一对对铁销子被捅开,车厢里的煤瞬间喷涌,下面的人得手疾眼快,赶紧往前跑,因为车厢里下来的不是一块两块煤,是几吨、几十吨瞬间倾泻,所以不光专心,还得腿快,稍不留神,就会出事。这时,大姐脚上那双不跟脚的鞋,使她落在父亲身后,父亲见她没跟上来,稍一走神的工夫,便被山洪一样的煤给淹没了。
大姐对父亲的死很是内疚,她故意嫁到口外,远离京城,大概她死也要死在见不到父亲的地方吧?生子想到这里,仿佛重新回到大姐离开妫村的那个姐弟俩路口相遇的时刻,年幼的生子大口吃着热火勺夹鸡蛋,大姐空着肚子看着他,委屈、伤心、无助,他记得,他全记得!
生子昂首走在出山的行列里,邊走边修,边开边平……明媚的阳光普照,村民们挺直了腰杆,当如火如荼的洪流像刚出炉的铁水奔涌到坳口,鼓荡的风像大姐伸出的双臂一下子抱住了众人。这是从北京城里吹来的风啊,生子说。

陈渔,本名陈民。至今已发表作品 300 余万字,包括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本等,多次荣获省部级以上一二等奖。北京作协、中国金融作协、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北京影视艺术学会等会员。曾出版小说、拍摄剧集多部,包括长篇小说《爱并痛苦着》《踱城》 《金汤》《汉白玉》、 四十集电视剧《京西汉白玉》等作品。
责任编辑 吴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