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的码头
杨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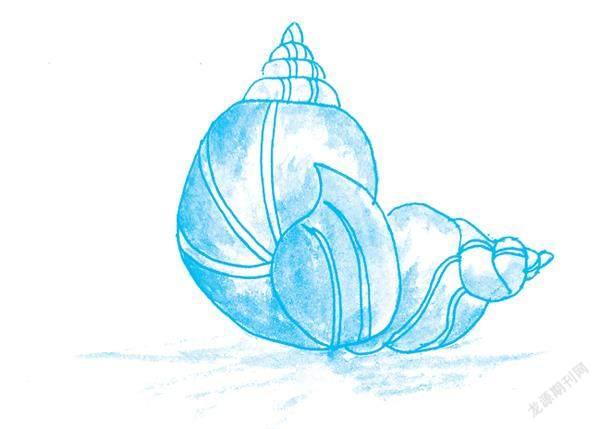
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这几天总是梦到我家的老屋。老家的屋后有一个池塘,有大半亩地的面积,小时候的我,管它叫水库。在没有自来水之前,我们一家人吃的都是这里的水。
为了吃水方便,祖母搬来几块青石和橡树桩,搭建了一个小小的码头,方方正正的,很是精致。
因为年龄小,祖母不让我靠近那个码头,生怕我掉进水库。但我对水有着极强的亲近感,几次贸然找来木滑板,然后抱着从码头上跳下去。没想到的是竟然就这样偷偷地学会了游泳。有一次被父亲知道了,他二话没说,拿走滑板,一脚将我从码头踢了下去,自以为会水的我在那一刻却毫无章法,命若悬丝,最后是被祖母捞上来,然后倒吊着沥水。那次以后,祖母给我讲玩水的危险性,但对死亡一无所知的我并不能体会那种可怕的情景。
夏天时,每当下过暴雨,池塘的水就会漫过码头。有些欣喜若狂的鱼会从码头跳到岸上,这是那时的我经常盼望的场景,收获多的时候可以达到满满一大桶。但我并不知道这是因为水里缺氧,只是以为那些鱼跟我一样高兴,所以就跳了上来。
有时候我会假装勤快,帮家里做些家务,比如淘米、洗菜。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心灵手巧,每次淘米都会淘出一码头的米,由于淘过米后的水是浑的,也看不见米,所以觉得无伤大雅。没想到每次都会被祖母发现,然后被骂做事草率。待她骂完后我去码头看个究竟,原来掉出的米,在水底看得这么清晰,于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再浑浊的水,也有澄清的时候。
等我稍大了一些,偶然一次洗手时发现,码头上爬满了田螺,又大又圆。独自捞上来一个,它立即躲闪的样子让我怀疑它为什么如此害怕这个世界,看到它如此紧张,我便将它放了回去,不一会儿它又冒头了出来,我才感到一点点安心的赎罪一样的喜悦。
没过几天,码头上的田螺越来越多,大小不一,偶尔游过来一只虾,将虾钳伸过去,试图捕食,没想到反而被田螺夹住,吓得到处逃窜。码头上的田螺,竟然多到影响洗菜,祖母就拿了滤网,捞了一盆,做了一道爆炒田螺。这道菜,我至今都甚是喜欢。
一天傍晚,祖母趴在码头上叫我,她一脸慌张的样子,衣袖已经完全湿透。我问其缘由,原来祖母洗碗时不小心掉了一个下去,捞了半天无果。我立即脱了外套和长裤,下水捞上了碗。我记得,那是深秋的季节,水温微寒。
码头边长着一棵很老的常青树,眼看要横跨码头,这使得总会有一些不知名的虫子从树上掉到码头,影响水质。特别是到了深冬时,树叶掉到水里,就会生出一层黑绿的膜,覆盖整片池塘。于是,祖母每年又多了一道重活,为了让码头干净,她开始不定期地修剪树枝。
1998年,我们全家搬进了城,留下了那个码头,从此,再也不见修剪那棵常青树的人。
现在,那个池塘已经长满了蒿草,常青树也抵达了池塘的对岸,码头早已塌陷,只剩下几块青石,上面布满了黑绿色的青苔。
看到这个景象,我想到一本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祖母是很低的碼头。
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让我立刻热泪盈眶。
(和风朗月摘自《中国妇女报》2022年12月8日 图/雨田)
———浅析数列与其他知识的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