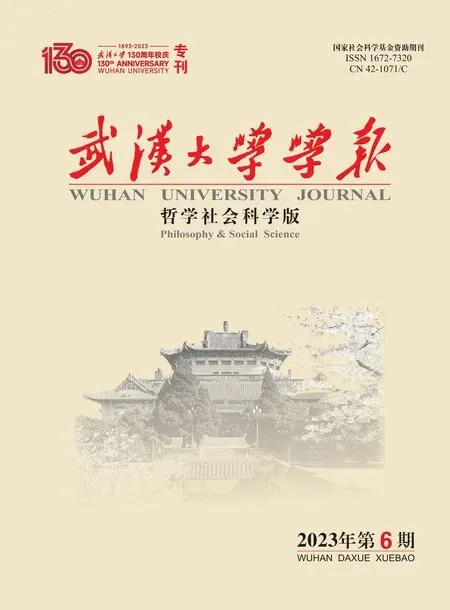武汉大学章黄学术的百年传承
于 亭
“小学”由秦汉之时童蒙识字之学,发展为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乃围绕古代书写文化,以汉字记录承载的汉语为中心,有形、音、义三分之说,遂有文字之学、音韵之学、训诂之学。时与地有古今南北,古书古语,难知其义。字与音有更革转移,字形变异孳乳,正俗异构,界限不明;语音变迁,唇吻侈弇,难留痕迹,淆若棼丝;语义为形、音所归,然而指事所在,会意所摹,引申假借,线索显隐,难言其详确。小学形义、形音、音义之间牵连复杂,虽有䚡理,而表面漫无条统,人难知其内外,古来号称难治。
中国学术,自明末风气由议论转趋征实。顾炎武(1613-1682)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1](P58),以为阳明心学近禅,束书不观,而欲改弦更张,又谓“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1](P73),由宋明儒学中考核一端,抽出全新的学问理念,揭举新的学术法则。至清中期,考文知音已成学问康衢,学者治学,率由“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可以通经”云云取径[2](P1)。戴震云:“夫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故训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3](P45-46)故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3](P140)。清代中期学术完成了语言主义的转向和向经学“本经”的会归,朴学考实成为显著的学术风气。戴震谓:“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3](P146)对于“本义”和“本经”的坚定追求,一者表现为小学蔚为大观,以古音学为中心,小学兴盛,独成一枝;一者表现为“汉学”之揭起和校雠之关怀。二者齐归于周秦之经籍旧文。可以说,清代朴学之精神追求,一为经学之本,一为小学之体,而以秦汉书本之校雠、周秦语言之音义为终始,所谓“以小学说经,以小学校经”[4](P148),清儒之稽古右文,名为复古“汉学”,实则求是责实,近代学术已造形萌现。章太炎、黄侃之学,承清学之余绪而有进一步的跃升转化。
一、章黄学术之内涵
民元之初,章炳麟(太炎,1869-1936)、黄侃(季刚,1886-1935)师徒二人,集清儒汉学之大成,以其学术转化,成为清学的现代总结者。章氏讲学不辍,门人各有所树立,其中黄侃以天资之胜,治学之矜,入堂奥而踵襄之,所得闳深,展廓独大。其门庭径由,再经黄门数弟子的传习充实,逐渐形成“章黄之学”。
章太炎、黄侃早年皆曾投身排满革命,倡言古学,以激动种族,以为国本。章黄继承清学之求是,又实之以民族主义和时代意识,积淀承受,转出新义,正如黄侃所说:“我辈学问,以汉学为表面,以申韩为骨子。”[5](P5)于旧学主传承,以恪守师承为治学第一义,认为“凡研究学问,阙助则支离,好奇则失正,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亦必如此,方有真知灼见。韩非有言:变业无成功。此可为吾人讲学之鉴”[5](P1),而其实,则不肯主奴清儒,不愿寄人篱下,务为前人所不能为,有鲜明的现代特色。可以说,章黄学术是在中国旧学基础上深造自得,圆融自成,师法特色鲜明的本土转型学术,其学以保守旧学为面目,以小学为体,以审音发明为骨里,在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与时偕行,自成一脉,并日渐产生重要的影响。章黄学术以旧学为体,虽不画地为牢,但要以经学小学为根基,期以大成之道,虽多受批评,被斥为守旧不化,自我矜异,却能在西学对中国学术全面重塑重造的大潮中自成而彊立。章氏学问体大恣肆,黄侃谓其集清儒之大成,阐晋唐之遗绪,实命世之大儒[6](P31),特精经学、小学,及于周秦诸子和释氏之书之思想,其言谓“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7](P328),可见其学旨趣之一端。章氏晚年讲习,谓“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又说“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8](P6)。黄侃踵之,谓“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一无可通”[5](P5),遂发扬光大,坚卓精锐成一家之言。
黄侃个性短于谐俗,不能与时俛仰,乃以教授自安,一生治经学、小学、文学,皆有得,尤精小学。章太炎说他“学问精嫥,言必有中,每下一义,切理厌心”[7](P327)。其说经称义,以为古说醇笃可倚,守之不轻移易,尤不以傀异为说倚魁自矜,“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9](P293),则近于清代惠栋之尊闻。章太炎谓其“自幼能辨音韵,壮则治《说文》《尔雅》,往往卓跞出人虑外,及按之故籍,成证确然,未尝从意以为奇巧,此学者所周知也。说经独本汉唐传注、正义,读之数周;然不欲轻著书,以为敦古不暇,无劳于自造”[10](P1),故其身后,章太炎谓之“清世说制度者,若金氏《求古录》,辨义训者,若王氏《经义述闻》,陈义精审,能道人所不能道,季刚犹不好也”[10](P1)。黄侃以敦古之殷,盛年遽逝,著述殊少,其深造小学、经学、文学之得,未能充分展现。从其鲜少的学术孑遗来看,他最精闳的贡献,在于传统语言文字之学的继承和转化,其门弟子日后自造传扬,也多以语言文字研究名家。
黄侃承章太炎之学之教,在清代小学成就的基础上,提升锤炼,精思凝聚,有理论的提升和转化。如他说:
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11](P2)
由此,他衍释“小学”内涵,谓形、音、义“三部虽分,其实同依一体:视而可察者,形也;闻而可知者,声也;思而可得者,义也。有其一必有其二,譬如束芦,相依而住矣”,进而申说“小学”名义,重新以新义建构转化,称“小学者,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也”,说:
小学者,即于中国语言文字中研究其正当明确之解释,推求其正当明确之来源,因而得其正当明确之用法者也。[11](P1)
他又说声韵、文字、训诂互相为用,曰:
音韵者何,所以贯串训诂而即本之以求文字之推演者也。故非通音韵,即不能通文字、训诂,理固如此。然不通文字、训诂,亦不足以通音韵,此则征其实也。音韵不能孤立,孤立则为空言,入于微茫矣,故必以文字、训诂为依归。然则音韵虽在三者为纲领,为先知,而必归于形、义,始可为之锁钥也。[11](P149)
周秦之际,有古书传记,有训诂之事,后有训诂之学。关于“训诂”之名义,唐孔颖达谓:
《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独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释言》则《释诂》之别,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释亲》已下,皆指体而释其制,亦是训诂之义。[12](P269)
清马瑞辰推说之,曰:
盖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导之,此诂与训之辨也。[13](P5)
黄侃暗承孔颖达“解释之义尽归于此”之说,言之曰:
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11](P181)
他又分“本有之训诂”和“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和“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小学训诂”)和“解文之训诂”(“经学之训诂”)诸义,表述训诂构成的方式和原理为互训、义界和推因,等等[11](P181-192),超越了历来说训诂不离随文训释之株拘,从而建构起新型的“训诂学”的语言语义观念和话语体系,全新地解释了训诂构成的内在原理。他总结清代小学的进步,说“一知求本音,二推求本字,三推求语根”[11](P12),其实是他自己的学问抱负加诸前代学术所抽绎出的内涵。黄侃的《声韵略说》《声韵通例》,一改清儒说音论韵涂辙,由归纳改为演绎,由具体考说而变为普遍论述,发凡起例,层层䌷绎释之。《音略》会通宋以来治古音之成就,以为古今相挟而变,古今声韵兼赅,以“悟发声之由来”,以知分合之的证,定今声41类,古声19类,今韵23摄,古韵28部[10](P62-92)。合古今打通,赋予《说文》《广韵》以中心地位,引出他以音韵学为基点,进一步超越清学语言主义训释的传统,超越“本经”“本义”的语境文本关怀,进而探寻汉字之“字原”、汉语之“语原”,求系统之解释。他说:
往者古韵、今韵、等韵之学,各有专家,而苦无条贯。自番禺陈氏出,而后《广韵》之理明,而后古韵明;今古之音尽明,而后等韵之纠纷始解。此音学之进步,一也。
声义同条之理,清儒多能明之,而未有应用以完全解说造字之理者。侃以愚陋,盖尝陈说于我本师;本师采焉以造《文始》,于是转注、假借之义大明;今诸夏之文,少则九千,多或数万,皆可绳穿条贯,得其统系。此音学之进步,二也。[10](P94)
诸语虽若总结过往之进步,实则创制新路,可谓有语言文字学现代转型的理论建立之功。又如其论字形之创制、字音之起源、声韵之机制和关联,以及字之变异和孳乳条例,都踵武章太炎而有提炼提升,并为后来其门人弟子对中国古代语言学传统的学理阐释建立了框架和基础。
二、黄侃与刘赜、黄焯之师受
黄侃曾辗转南北,历应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之聘任教。1919年至1926年间,他执教武昌,是他任教生涯中最长最稳定的一个时期。武汉大学的中国语文研究传统的奠定,基始于任教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黄侃,完成于黄侃及门弟子刘赜和黄焯。刘赜、黄焯在武汉大学,谨守师说,著述授业,逐渐塑造了武汉大学语言文字之学的研究风貌。
刘赜(博平,1891-1978)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师从时在北大任教的黄侃,受文字、音韵、训诂之学。1917年后游学日本,在东京拜入章太炎门下受业,章氏称为“再传弟子”[14](卷首),归国后再次追随黄侃研习小学。1929年受黄侃推荐,聘入武汉大学执教,前后垂50余年,终老于珞珈山。刘赜曾长期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于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黄焯(耀先,1902-1984)为黄侃从子,以弱冠赴武昌谒叔父,从此相从侍学15年,先在武昌中山大学修业,毕业后受黄侃之招赴南京中央大学任助教,侍其左右,直至黄侃下世。1939年,黄焯自重庆中央大学,受聘乐山武汉大学,从此亦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终老。20世纪50年代,武汉大学中文系有“五老八中”之盛,刘、黄人称博老、耀老,居于“五老”之列。
刘赜、黄焯同出黄侃门下,相与共事40年。黄侃为学尚专门,不骛泛滥,务精习,极重精读书,所谓“扎硬寨,打死仗”,特崇师法,尊笃古说,不轻驳前说,不轻改古人。他说:“所贵乎学者,在于发明,不在乎发现。今发现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5](P2)表达了坚尊旧学,读根柢之书,温故知新,而不以材料求新、方法出奇、套路好用而取胜的为学理念,丝毫无视“执守泰笃”之讥。这些风格,对刘赜、黄焯治学影响至钜。黄焯自述从侍黄侃之后为学次第,从《困学纪闻》《日知录》以窥治学门径,继受文字声韵大要,又因清黄以周谓学问文章皆宜以章句为根基语,以黄侃所说“研究章句即为研究小学”[5](P4-5),遂起而治《毛诗》,并禀受黄侃之语,谓毛传为一切经学根本,遂以毛传为宗本。他曾记黄侃之读书,曰:
先生阅书,必施圈点,虽卷过数百,必点完始已。殁前一日,吐血盈盂,以《唐文粹补遗》末二卷未毕,犹力疾圈点讫,始就榻。尝言:“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遍数。”(戊辰五月三日日记)焯窃观先生圈点书,数当以千计,经史子文诸专籍无论已,即以《四库全书总目题要》、《清史稿》两书论之,即达七百馀卷。至于能背诵之书,不止如先生所述《说文》、《文选》数部而已,如杜工部、李义山全集,几皆能上口,即词曲中能吟讽者亦多,博闻强记,盖兼具所长。[15]
笔者尝闻之于本师宗福邦、陈世铙,谓耀老于《十三经注疏》了然于心,出口成诵。黄焯晚年尚回忆拈出黄侃“读古书当潜心玩索文义,而不可骤言通假”之语,加以申说,呵段玉裁、王引之误解古书,牵就己说之失[16](P267-270)。可见黄侃读书为学对黄焯一生的深切影响。
在刘赜、黄焯的传承、授业之下,武汉大学章黄学术根殖萌蘖,尤其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刘、黄二老虽经颠沛摧折,仍有建树,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系统整理师说;文字声韵之学和章黄语言文字之学的理论化、系统化;经学训诂;传统小学典籍之整理研究。
(一)黄侃师说之整理
黄侃学术渊深,为学矜持谨慎,读书精勤过于常人,批注朱墨烂然,而不言著述。章太炎尝数与言,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催其从事著述,黄侃对之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但黄侃不幸年五十而中酒死[9](P293),其学术实践戛然而止,未及丰完。黄侃生前与弟子坐论讲习,门弟子辄记录其论学之语,也经常借阅过录黄侃批读过的书籍。黄焯随侍黄侃最久,亲其謦咳,还曾受命守护其藏书,所见既多,过录黄侃读书批识亦最多。他晚年萃精力,或取多年过录,或多方借钞,有意识地整理和保存黄侃的学术遗产,又以耄耋,倾力油印或出版,以宣扬师说。据其所撰《黄季刚先生遗著目录》[16](P278-290),黄侃生前发表的长短学术作品,以及未发表的遗著、各种读书批注笺识、学术手稿、诗文稿等约90余种,黄焯据以过录整理即40余种,再通过誊录、油印、出版等加以流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黄焯集中自己所有精力和有限的财力,通过不懈努力,使得保存在黄侃手稿、读书批注中的原创学术思想和学术遗产实况,得以为学术界所寓目,进而传播发扬。黄焯自述其整理黄侃遗著的情形,说:
焯犹得将书中笺识编辑成帙,如《说文》则抽写为《说文同文》《字通》《说文新附考原》,《尔雅》则编为《尔雅音训》,《文选》编为《文选平点》,《广韵》则武昌徐孝宓家有迻录本,据以编为《广韵校录》,其点校十三经白文本,展转于北京历史博物馆中求得,俱由古籍出版社印行。而先生手批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及焯早岁迻录诸书笺识,共得十种,合编为《量守庐群书笺识》,虽存什一于千百,俾来者得视犹医之针砭,或济川之舟楫,应无不可。[17](P1)
经黄焯整理面世者,如《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尔雅音训》《说文笺识四种》《广韵校录》《文选平点》(以上六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字正初编》《量守庐群书笺识》(包含笺识10种)、《黄侃声韵学未刊稿》(上下册,包含音韵表稿14种)(以上三部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蕲春黄氏文存》(油印本)等,较为系统地展现了黄侃学术的取径和风貌。尤为重要的是,黄焯之爬梳、抽绎、编次和整理成书,乃由一生于黄侃学术浸润涵泳和晚年识断精审的造诣而成,他在保守、展示黄侃学术遗产原始风貌的同时,将黄侃学术条理肯綮而有意识地系统化了。因此,黄焯不仅是记录者和整理者,实乃所谓述而不作,温故知新,斟酌因损之,而转出精义,令黄侃学说发扬光大。我们更应将其视为黄侃学术的合作者和继承者[18](P97-102)。
(二)章黄语言文字之学的系统化
刘赜、黄焯一生勤治小学,精于音韵,治学祖祧章太炎的学术意识,严遵黄侃的学术路线,不越雷池,而精义出新,更上层楼。如刘赜精研《说文》,撰《说文古音谱》,黄焯撰《古今声类通转表》12卷,材料对象虽异,乃皆模仿从学之时所见其师黄侃之所为而成。如刘赜述之,曰:
曩在北京大学,见先师蕲春黄君散《说文》九千余文,分隶其所定古本韵二十八部及古本声十九类为表,以今隶书之。余以为徐楚金之韵谱,不过便于检阅而已,又自来言古音者,或乖或合,无能窥其全部音值。此则以先秦本音系统贯穿形义,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虽事属假定,而三古遗言咸能拟测,文字亲属于焉可寻,洵小学之奇觚,当代之创制也。后归武昌,教学有暇,遂默识而仿造之,并依篆具载许君说解,名曰《说文古音谱》,朝夕䌷绎,粗谙音义相关之理,久之,又渐悟推寻音义相关之术,又久之,渐悟音义相关之用,并深感前人之治许书者,即病在支离破碎,不能贯穿全书音义,以上探语言之本真。观古人之遗象,致使无双绝学,神旨莫宣。[19](P1)
《说文古音谱》之书,以语音经纬,依黄侃所定古本韵28部、古本声19类等,将《说文》九千文散录,分隶为表格,以䌷绎音义相关之理,而推寻音义相关之术,进而悟音义相关之用。黄焯自言其《古今声类通转表》之作,曰:
焯往岁随侍先叔父季刚先生,见其披阅古籍,凡于文字声音之相通或有变转者,每加意及之。曾命焯录《说文》声母字之有重音者为一帙,其一字而有异声者则规识其旁。焯因是旁搜诸经传,凡可为声音通转之证者,类聚而分列之,计分喉舌、舌喉、喉齿、齿喉、喉唇、唇喉、舌齿、齿舌、舌唇、唇舌、齿唇、唇齿十二类,其喉舌、舌喉实可并为一类,喉齿、齿喉诸类视此,实则可分者,止六类而已。惟此六类中,亦多有互通者,是又未可过严其畛域也。经史子文可备甄采之资料至夥,中年以前屡经丧乱,未及遍搜,今老矣,又以昏眩疾不任寻检,徒据旧稿类次写定,成为《古今声类通转表》十二卷……[20](P5)
《古今声类通转表》首列《说文》形声字之声子、声母异声者,重文、读若之异声者附见其中,次列《经典释文》《玉篇》《类篇》之异声诸字,次列经传子史之异文异音者,再连缀以《易》《书》《诗》、三礼三传等群经、屈骚、史汉等史传、庄荀诸子、汉晋赋、《尔雅》《方言》《说文》《广雅》《玉篇》《广韵》《集韵》等小学书中之连语,资料采撷广博,去取精严。其表所列,以《说文》为基要,博蒐经籍文字,以见语词声音通转之关系和条件。
章太炎作《文始》,以文字变异孳乳、声韵通转以推摹汉字汉语之系统起源、形成内在的音义理据,从文字起源意义上,以《说文》为古形古音古义之书,举出“初文”“准初文”之例,以为基始,于字之分合,言变异、孳乳,于音之缌理,言对转、旁转、正纽、旁纽、变声等,以此交织,探求汉字声义之原。他说:
余以颛固,粗闻德音,闵前修之未宏,伤肤受之多妄,独欲浚抒流别,相其阴阳,于是刺取《说文》独体,命以初文,其诸省变,及合体象形、指事,与声具而形残,若同体复重者,谓之准初文,都五百十字,集为四百五十七条。讨其类物,比其声均,音义相雠,谓之变异;义自音衍,谓之孳乳,坒而次之,得五六千名,虽未达神恉,多所缺遗,意者形体声类,更相扶胥,异于偏觭之议。[21](P176-177)
刘赜毕生研治《说文》,祖述章氏《文始》之思想,撰《初文述谊》,将章太炎和黄侃的汉字形义思想进一步推进,他说:
凡《说文解字》所载独体象形、指事之文,名为初文,合体及变体省体象形、指事之文名为准初文。此二者为所有汉字构成之基本点画,亦即一切文字音义孳生之本原,今分类辑录以阐述其形体旨趣及其音义之关系。[22](P1)
《初文述谊》之书全从初文角度归辑䌷绎,将《说文》初文、准初文一一辑出,凡四百二十三文,依黄侃古本韵28部,古本声19纽加以类组,逐字阐述形体之本原和其中的音义关系。其藉由语言音义之表里,以求语原,与夫语音、形义之生成关系,进而推求字原、语原之本源联系,与章太炎、黄侃二人小学学术的内在理脉一脉相承。
刘赜、黄焯对于章黄学术特有贡献之处,还在于将章黄一系的小学思想,尤其是黄侃生前讲论的文字、音韵、训诂学思想,系统整理和阐发,将黄侃之治学独造,发为宏论,成为时代学术的重要内容。刘赜于1932年撰《声韵学表解》,1934年以“国立武汉大学丛书”之一种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黄焯则于20世纪70年代末,整理出版了《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此二书成为章黄学术体系中重要而成系统的现代理论著作。如刘赜说声韵之要,曰:
昔人分语言文字之学为三,一曰形体,一曰训诂,一曰音韵。其实三者虽分,仍同一体,譬之束芦,相依而住矣。三者之中,又以音为之关键。盖先民之世,文字未作,以音表义。书契既兴,始依音义而构字形。形体已具,犹以音为主,故音同者恒相通用,不必书其本字。后世概谓之假借,窃以为未达其原。然则音不明,形体即无由憭。故声韵学者,通语言文字之阶路也。[14](卷首)
其言始于袭黄侃之语为说,而有所进之,解释之当,明晰透彻,析说古代文字语言音义关系,其精畅更具现代学术风格。刘赜认为治音韵者,莫盛于清代,自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等清儒以来,递相阐发,后出者愈发精密,音韵之学“至今日遂炳焉为完全独立之学科”,但社会教育实际的状况是“然或偏于考古,于审音之道有所未详。或陈义简深,非初学之士所能窥晓,欲求一沟通古今,宜于入门之作,不可得也”,故规摹师授而作《表解》:
本师蕲春黄君承余杭章君之业,集古今音学之大成,海内言声韵者,莫不以为圭臬。余以愚昧,得闻绪言,年来教于上庠,恒据其说以为讲义之资,诸生闻之,靡不欢悟。兹复引申排比,参合众家之论,立为表解。[14](P1)
其书分上下二篇,上篇明今音,下篇明古音,方法与理论并重,以言语言之构成,与夫音韵之流变,而对于繁琐具体的考辨之言、异同之论,无当于音理者,概不阑入,以晓初学,立语言文字之始基。《声韵学表解》吸收了西方普通语音学的观念和描写方式,解释声韵、清浊、双声、等呼、通转等传统音韵之学的概念,而以黄侃今音41声类、古本声19纽、古本音28部为本体纲目,说授语音的本质构成,中古音韵格局及其正变,而推及求古音之资料和方法,声韵条理和通转的条件等,似旧而与时俱进。
黄焯整理,题称黄侃述、黄焯编次的《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对于黄侃学术的理论阐发和升华意义最大。1976年,黄焯以“焯曩侍先从父季刚先生,从受文字声韵之学,退以所闻录寘箧衍”,而以所录数百条编为《文字声韵学笔记》,“今无力刊行,唯付油印,以与国内之治斯学者共览之”[23]。1978 年,黄焯又以“先从父季刚先生尝为学子说训诂学,录为《训诂述略》”,“今会稡所说,复旁搜清儒及近世章、刘二君之语,而以己意附列其中,编为《训诂丛说》”[24],自费油印行世。1983年合为《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重为缮写,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小学学术中,训诂为最终旨归,清学于校雠和训诂为最长,清儒于声音之道、训诂之理尤精熟,但仅以征实考索为能事,博极群书以证一义,说理片段,有例而无论,缺乏理论的总结和阐发。就中国训诂学的现代转型和理论建构来说,黄侃可谓第一人,也是最重要的起点[25](P36)。
论者认为传统训诂之学因循而封闭保守,“眼睛向后看,只强调乾嘉学风,强调小学专著的研究,强调资料的积累。在这个领域里几乎没有出现过学科理论思维的巨匠。黄侃最有条件成为这样的巨匠,但英年早逝,‘他的较成熟的著述都还没有来得及写出’”[26](P567)。黄侃早年讲习训诂法则与条理,为门人潘重规所记,以《训诂述略》为题,发表于章氏国学讲习会所办《制言》半月刊1935年第7期,粗有结构,但规模未具。所以,从1976年开始,黄焯所编次的《文字声韵学笔记》和随后的《训诂丛说》,对于系统阐发黄侃学说,推动开展中国语言文字之学的本土理论建设,以及促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训诂学理论话语建构、学科平台和研究队伍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黄焯的经学训诂
黄侃门下弟子,多习治小学,鲜有传治经学者,盖时代风潮,鄙薄以旧贯治经。但黄焯独勇者不惧,信而不疑,抱守经学径由以治《诗》,积年所得,析撰为《毛诗传笺平议》《诗疏平议》《诗说》三书,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所独具。
周秦之际,《诗》在口耳讽诵,经秦火而得存。《诗》之经学,汉初以下,分古文毛传和今文齐、鲁、韩三家,四家各有师说家法。东汉末,郑玄“注诗,宗毛为主,其义若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12](P269),虽曰宗毛,然与毛义有未合,则从己意,或参取三家说之,致使《诗》郑笺本谓宗毛、申毛,实与毛传相异同牴牾。而郑笺混一古今,淆乱家法,《毛诗》仅存,传笺駮互,无复知齐、鲁、韩《诗》本经及师说之原详。《毛诗》又有序,传为子夏作,为后人所疑。至宋,疑经,废《诗》序,朱熹《诗集传》出,以为后世场屋圭臬,而汉唐注疏几废。清儒稽古反正,回归六经,又宗举“汉学”,尊尚贾服许郑,《诗》毛传郑笺引为正宗,以为醇古可贵,而《诗》语简奥,名物独多,古音天籁,成为清学训诂、审音、考古之绝佳材料,《诗》之经学大盛,说《诗》之作辐辏,名家频出。陈奂(1786-1863)尤其注意到:
固作笺之旨,实不尽同毛义。及至魏晋,郑学既行,虽以王子雝不好郑氏,力极申毛难郑,究未得毛之精微。唐贞观中,孔冲远作正义,传、笺俱疏,于是毛、郑两家合为一家之书矣。……近代说《诗》,兼习毛、郑,不分时代(毛在齐、鲁、韩之前,郑后四百余载),不尚专修(毛自谓子夏所传,郑则兼用韩、鲁),不审郑氏作笺之旨,而又苦毛义之简深,猝不得其崖际,漏辞偏解,迄无钜观。二千年来,毛虽存而若亡,有固然已。[27](卷首)
故此,他认为:
窃以《毛诗》多记古文,倍详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训,或通释,或文生上下而无害,或辞用顺逆而不违,要明乎世次得失之际,而吟咏情性,有以合乎诗人之本质。故读《诗》不读序,无本之教也,读《诗》与序而不读传,失守之学也。文简而义赡,语正而道精,洵乎为小学之津梁,群书之钤键也。[27](卷首)
陈奂治《诗》,上承其师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的意见,又秉持戴震以来之师说,谓“小学明,而经无不可明矣”,作《诗毛氏传疏》30卷,仍《毛诗》之旧,置去郑笺而疏毛传。
黄侃说:“治经之法,先须专主一家之说,不宜旁骛诸家。”“学问贵能深思,得其条贯。果能如此,虽笃守一经,亦能自立。”又说:“治经须先明家法。”[5](P6-7)黄焯治《诗》,承自陈奂、胡承珙,而对师说守之不移,能于清儒治《诗》有所去取,认为陈奂《诗毛氏传疏》专依毛传而不及笺,又偏详训诂名物,于辞义或少推究。其他或驳朱熹,或兼取毛、郑,不一而足,或病辞义迂塞,或病勇于改古,不可为训。黄焯说:
经学训诂与小学训诂有异。先从父尝云:“小学之训诂贵圆,经学之训诂贵专。”盖一则可因声义之联缀而曲畅旁通,一则宜依文立义,而法有专守故尔。清世高邮王氏父子深于小学,以之说经,实多精闢之义。乃承其业者,少究故训之原,而动言通叚,凡于经义之难明者, 云某与某通,某为某借,名为通经,实则改经乱经。时至今日,而其弊滋甚。余曩从先从父受声音训诂之学,愧未能竟其业,徒记其论治经一二语,期守之勿坠焉。[28](P6-7)
故自畅其旨,进而言之,曰:
治经不徒明其训诂而已,贵在得其词言之情。戴震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实则有训诂明而义理仍未得明者。要须审其辞气,探其义旨,始可明古人用意所在尔。朴学诸师,间有专治训诂名物,而短于为文,致于古人文之用意处不能识得谛当。夫经者,义之至粹,而文之至精者也。可由训诂学入,不可由训诂学出。治之者识其本末终始,斯得矣。[28](P6-7)
其谓治经不徒明其训诂而已,可由训诂学入,不可由训诂学出,超越了清学考实主义和语言主义的面向,有所取法而超乎其上,可谓至论。为“明《诗》之道,不笃守序、传,则准的无依;不深玩《诗》辞,则其义不著;不详稽载籍拟之以意,则其辞莫由通焉”[28](P2)。故说经一以毛传之义为主,《毛诗郑笺平议》申毛传以难郑笺,“纠其不与毛合而有违《诗》义者”,以去郑笺“揅之过深,思之过当,致有求合而反离、求密而反疏者”[28](P3-5)之病和驳杂之非;《诗疏平议》则针砭孔颖达,以为孔疏凡于毛、郑有异同者,辄多左毛右郑,而于郑笺宗毛为主之本意,忽而不察,导致分疏毛、郑之时,“于郑笺引而未发之奥,必曲折以达其义。若毛传有难明者,弗能旁引曲畅,辄以传文简质一语了之”,或意在申毛,而每非毛旨,而于郑笺或申毛或直下己意之处,又误解误释。《诗说》则总释《诗》学之大要。黄焯《诗》学三书,尊序宗毛,谨守旧学,其一也;取师法之精醇,不立门户之见,其二也;具学术史之时代理解,剖析精当,其三也。其眼光与其所得,取径于陈奂、胡承珙等清儒,而有过之,于20世纪经学衰废之学界,可谓一人而已。如《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逑,匹也。”郑笺:“怨偶曰仇。”《毛诗郑笺平议》曰:
大凡郑易毛之处,多本三家。其所以取三家者,必据经与序为说,顾往往不自知其立义之拘泥也。至毛训逑为“匹”、郑训为“怨偶”者,当由郑所见本逑作“仇”。又缘误解篇义“无伤善之心”之语,遂援左氏“怨偶曰仇”之文。据《列女传》之说,以仇为“仇怨”,以好为和好之“好”耳。惟仇本为“仇匹”义。此诗言“好仇”,犹言“好匹”。左氏言“怨偶曰仇”,则专言恶匹。好匹、恶匹,其匹则一。左氏所云,实非仇之本义。郑援以易毛,亦非也。[28](P2-3)
《诗说》曰:
《关雎》言君子好逑,《兔罝》言公侯好仇,逑之与仇,实为一语。《关雎》传训逑为匹,笺所见本作仇,故从《左传》“怨耦曰仇”言之。然无论嘉耦怨耦,而仇之为匹则一也。《兔罝》与《关雎》之所以异者,在其所指之人不同。《关睢》言后妃,好仇犹言嘉耦;《兔罝》言武夫,好仇犹言良弼、贤佐耳。郑笺偏执仇怨之文,而忽其仇膺、仇对之义,故解二诗均未合也。[29](P52-53)
其说甚审,则郑玄所见三家异本为“仇”字,本可各尽其辞,而郑误解序意,牵连释之,又于训诂有偏,误释“逑”为仇怨之“仇”,“好”遂为和好之义,以曲合序“无伤善之心”之语,遂致胶轕,而毛传义亦晦。
(四)传统小学典籍之整理
黄焯撰《经典释文汇校》一书,成为章黄之学与时代学术发展交织的伟业。陈、隋之际陆德明所作《经典释文》30卷,体大思精,汇集魏晋六朝经师所作经籍音读、训诂,勒为一编。千年而下,清徐乾学据明末叶林宗从钱谦益绛云楼藏宋本影钞本刻入《通志堂经解》,其后又有卢文弨抱经堂本。《经典释文》如文府宝库,旧音、成训、古经说、古经异文以万千计,为清儒所惜爱宝重,但鲁鱼豕亥,讹舛不堪,惠栋、段玉裁、臧庸、顾广圻、卢文弨等清儒多加校勘,迭所修订,但无论是通志堂本还是抱经堂本,都出于明叶林宗影钞本,叶本脱误已夥,绛云楼一炬,所藏宋本灰飞烟灭,终清之世,《经典释文》都不得善本以见旧貌。而唐代以至于宋代,《经典释文》内容亦在传写刊刻之中,为省便计而被刊落删削不少。黄侃谓“治经必以《经典释文》为锁钥”[5](P8)。黄焯自1931年起即蒐集资料,曾过录黄侃所藏自吴梅处过录的《经典释文》,有志于校雠之业。20世纪60年代,他得知北京图书馆藏有清内府藏宋元递修本,为天壤间所仅有,两度北上,赴北京图书馆借阅宋本,以通志堂本为底本对勘,“复旁及唐石经、唐写本、影宋本,并以清儒及今人黄季刚先生与吴承仕所说附列其中,他如卢氏《考证》、阮氏《校记》亦间采入”[30](P4),终于1977年76岁之际,撰成《经典释文汇校》30卷,集清以来诸家之大成,又得善本相覈,其功至钜,为学者所宗。《经典释文汇校》并非仅以校勘异同、是正文字为事,更以音理、训诂疏通理解,区别文献传写讹舛与语言机理有征之别,以察名实,别异同,决嫌疑。仅举一例明之。《诗·周南·关雎》“参差荇菜”,陆德明注“荇”字,曰:“衡猛反,本亦作莕,接余也。沈有並反。”此处本无异文,而黄焯出校语,曰:
吴承仕云:衡、有异纽,篇韵所列各切无有与沈音相应者,疑有字误。黄云:此喻、匣相通,《切韵指掌图·检例》所云“上古释音多具载,当今篇韵少相逢” 者也。又云:案喻切匣母,多是三等字,依陈兰甫分喻为二类,当云匣、为相通,今且仍旧说。焯案为纽古与匣一类,六代之音犹然(详余所撰《古音为纽归匣说》)。吴氏未之知,故有此疑尔。[30](P46)
此处引黄侃读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笺识之语为说,而加以证发[17](P316)。以音理之精微细察,区别孰为文献问题,孰为语言问题,说理坚卓,定谳确凿,人所不能及,非其人不能为之。
三、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对章黄学术之承传
刘赜、黄焯二老秉承师训,坚守不移,辉光之余,蕃士作育,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古汉语研究,开始形成鲜明特色。1975年,《汉语大字典》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亲自批准下启动编纂,四川大学徐中舒任主编,武汉大学李格非、四川大学赵振铎任副主编,川鄂两省多所高校上百位专家参与编写,湖北省指定武汉大学为本省牵头单位。武汉大学集中汉语研究骨干力量,组成编写组,投入《汉语大字典》编写工程,除了字形、字义的梳理、研究和撰写之外,还发挥研究传统和特色,全面负责审音工作。《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历时十年,全书收录楷书汉字约56000个,总字数2030万字,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收集汉字单字最多、释义最全的大型汉语学术字典,以释义准确,义项丰备完善,例证典范,一举改变了大国小字典的文化窘境,体现了当时汉语汉字历史研究和语言描写的最高水平。
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自觉地继承章黄学术的优良传统,不断地在传承中薪传、转型和发扬壮大的,是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以下简称“武大古籍所”)团队。武大古籍所的前身,是武汉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室,黄焯曾任研究室主任。1983年,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委会”)成立,武汉大学在原字典组骨干教师团队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武大古籍所,成为古委会直接联系和指导的实体研究所,首任所长周大璞,随后由宗福邦接任,副所长萧海波。周、萧二人曾为刘赜门下弟子,毕生从事古汉语词汇和训诂研究。宗福邦1959年自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0年被选派参加丁声树等主持的音韵学讲习班,从此走上音韵学研究的道路。他曾以《关于广州话阴平调的分化问题》(《中国语文》,1964)和《论入声的性质》(《音韵学研究》第1辑,1984)等学术论文,首次提出广州话阴平调已分化为两个独立的调类,广州话入声韵的四个调类等系列新观点,奠定了学术声誉,曾任《汉语大字典》编委和武汉大学编写组组长。古委会成立之后,要求直属的各大学古籍所确立和建设自己的研究特色和研究方向,而武汉大学既承章黄学术之绪,宗福邦的师辈和同事中有好几位是黄侃门下和再传弟子,古籍所自成立起,就与章黄学术有着密切的学术渊源。因此,宗福邦执掌古籍所之后,将传统语言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作为主要建设方向,主动继承和发展章黄学术的研究传统,萃集团队,深耕音韵训诂研究、汉语音义研究、古代小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经过持续建设,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宗福邦等更继承黄侃之学术构想,开展有组织的大型科研攻关,两代学人前后相继,纂辑巨制。
清代乾嘉诸儒稽古右文,推扬汉学,在复兴和回归汉学的旗号下,就古音以求古义,训诂明而古经明,搜辑考辨不遗余力,古经解、小学之书,辑佚纂集,其功至勤。阮元(1764-1849)在浙督任上,鸠集硕儒经生,编成《经籍籑诂》,汇辑汉唐经籍之训诂,有“经典之统宗,诂训之渊薮”之誉。古经音读之纂辑亦间有作,如《经籍籑诂》编成之前,洪亮吉(1746-1809)即撰成《汉魏音》四卷,辑录汉魏诸儒传注中之譬况说音凡数千百条,其自序云:“夫求汉魏人之训诂,而不先求其声音,是谓舍本事末。今《汉魏音》之作,盖欲为守汉魏诸儒之训诂之学者设耳。”[31](卷首)体现了乾嘉诸儒治经莫重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故训音声相为表里的主张。章太炎门下弟子吴承仕(1884-1935)于20 世纪20 年代,博采汉魏至唐初之经籍旧音约百有余家,按《经籍籑诂》的体例,撰成《经籍旧音》25卷、《序录》1卷。吴氏认为《经籍旧音》比之《经籍籑诂》,“一则集雅诂之大成,一则综音声之流变”[32](P77)。其书当时“伦脊已具,犹待补苴”[33](P50),可惜战乱起而作者逝,其稿飘零。黄侃曾读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批注其中疏误数百事[17](P313-416),又提出校补《经籍籑诂》的主张,他说:
清世阮元有《经籍籑诂》,为小学家常用之书,惜其以《佩文》韵分编,又载字先后毫无意义;至其蒐辑,亦有不备者。今若能通校一过,暂用《字典》编制法编之,次为补其遗阙,此业若成,则材料几于全备矣。又《经籍籑诂》间亦载音(如其引《字林》即载其音),究于汉后唐前之音多所漏略。今宜更纂一书,曰《经籍籑音》。以后编字书音时,即取此等全部列入可也。[11](P15)
1985年,武大古籍整理研究所创建不久,即依黄侃辑补《经籍籑诂》之构想,着手编纂《故训汇纂》一书。1997年《故训汇纂》编纂垂成,团队同仁又追踵黄侃更纂《经籍籑音》的构想,议为《古音汇纂》,以当《故训汇纂》之姊妹篇。自1985年到2019年,以35年持续不辍之功,不事声华,精诚合作,相继编成《故训汇纂》《古音汇纂》《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等巨纂。《故训汇纂》(2003)1300万字,16人历18年编成,纂辑了自先秦到清末的训诂资料,全面超越了清代阮元《经籍籑诂》,学界誉之为“诚自有训诂之书以来所未有”“博雅精审,足以取信今日后世”,可与《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相提并论。《中华大典·音韵分典》(2013)1000万字,11人历8年编成,是一部徵引繁浩、体大思精,充分反映古代音韵学成就的大型类书,学界认为“在资料的占有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古音汇纂》(2019)1300万字,8人团队历时22年打造而成,全面汇辑了自先秦至清代的音读资料,超越了黄侃辑录“汉后唐前之音”的构思,勒成一部收录完备,源流并重,音义互见,上起秦汉,下迄清代的历代汉字音注资料汇编,成为该领域的首创巨制。
《故训汇纂》《古音汇纂》之编纂,继承了中国古典学问中纂集一派的优良传统,更继承清学下迄章黄对于汉字、汉语音义关系探究关注之眼脉。清学至于章黄学术,其卓荦超拔者,在精研小学以为根柢,以小学治经乃至于一切学问。惠栋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34](P269),章黄进而正确地探识和阐发了音义相关的本质,及其相谐通转的关系,以声音为枢纽,明其䚡理,形、音、义互相求,声音之道明,而训诂之道明。作为后学者,我们亦进而意识到,语义之训诂固有赖于声音之道,语音脱离了语义和语境,也不可能获得合理的解释。如音义书以训诂为务,与韵书不同,其注音侧重于因音辨义,注音即所以表义。经师之读书音,有自然语言之因素,实亦包蕴着经史训诂解释的特有音读和规约语境,离开了经史群籍的语义环境,往往无法合理地理解和解释众多的音读现象。因此,《故训汇纂》和《古音汇纂》把完整、准确地标示音读、训诂所在的语境作为一条重要的编纂原则。《故训汇纂》《古音汇纂》作为姊妹篇,都上起秦汉,下迄清代,一以训诂为中心,按照成训建立注项,可谓“集雅诂之大成”;一以语音为中心,围绕说音建立注项,可谓“综音声之流变”。《故训汇纂》所收之典籍训诂,与《古音汇纂》所收之典籍音注,起到互见的效果。另外,例如,《经典释文》作为唐以前经籍音读训诂的集大成之作,其所迻录的汉晋六朝众家经师之音读、训诂、异本异文和陆德明所作之音注,价值之高,无有其匹。《故训汇纂》《古音汇纂》在黄焯《经典释文汇校》成就的基础上,对于《经典释文》材料进行了巨细靡遗的穷尽采录。这都是对于章黄学术理念的继承、致敬和践行发扬。
四、章黄学术之本土特质及其在武汉大学之赓续
综上,清代中期以来,学者皆知“故训音声相为表里,故训明,六经乃可明”[3](P153),小学有形有音有义,而又各有古今,形音义互相求,古与今互相求,可以得古义,䌷绎其义以至于无穷,进而得古经之义[35](P187-188),而“本经”“本义”之所在,无非以声音为枢纽,就古音以求古义,破假借,其理易简,知其同条共贯,则可以提纲挈领[36](P1)。清代小学蔚为大国,其枢纽在于以《说文》《尔雅》为根基,《说文》《尔雅》互相求,由探求周秦古音分合,唇吻音声之同通近转,而推求本字本义,又因声求义,说以假借。又初以声音之理申言转注之说,或缀联双声叠韵,渐生字族词族之观念。又以《广韵》为中心,剖析反切,系联声韵,以明系统之说。章太炎、黄侃师弟在清代小学成就的基础上,由考古之殷,进一步发展了审音的系统思维,扩而张之,以《说文》为根基,所谓“《说文》一书,于小学实主中之主也”[11](P6),以《说文》为可信不疑的材料,从字形、说解、解析、理据等入手,从文字之系统(初文、变异、孳乳诸说)、声韵之系统(古本声、古本韵、今声、今韵、通转条例)和训诂之系统(互训、义界、推因之方式①此黄侃说。章太炎称之为直训、界说、语根。和求证据、求本字、求语根之递进次序)等[11](P186),统而系之,出以条贯,虽三者各有畛域专说,实则旁通交糅互相求,言文字,进而说语言,在理论上加以集成的阐发,探求实现本土旧学的现代转化,有别于清末民国以来取法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中国语言学学术建构,从而自成一系,而在实践上特色鲜明,概括之,则为“明语原”“见本字”和“一萌俗”[8](P7)。章黄学出于清学,祖述取法而不稍移易,而能取乎其上,又断不寄人篱下,不肯俯首为清学之臣,实事求是评价清学优弊,以相争竞。如黄侃说自己于音韵之学,凡所祖述诸家,有宋郑庠,明顾炎武,清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严可均、陈澧及“亲教大师”章太炎,谓“幸生诸老先生之后,开其蔽矇,而获得音学之定理。施于政学,或足以释疑定纷”[10](P63),但又能看到“清人治学之病,知古而不知今。明人治学之弊,知今而不知古”[5](P4),又说:
有清一代,治学之法大进,其于小学,俱能分析条理而极乎大成。然亦间有剽掠古书,以为自媒,别为臆说,自我作古者,是则不足论耳。又清代小学,音韵最盛,盖喉唇之学,不烦左证。不知喉唇主于虚,而必证之于实,如射之有侯,载之有车也。故徒主于虚,亦异说之一途耳。[11](P2)
从章太炎到黄侃,学说有扬弃,有递进,如黄侃秉从章太炎根重《说文》的理路,但并不全信从章氏最所自矜的《文始》,认为:
近时若章太炎《文始》,只能以言文字,不可以说语言。如羊,祥也。火,燬也。以文字论,先有羊、火;以语言论,而祥、燬实在羊、火之先。故《文始》所言,只为字形之根源,而非字音、字义之根源也。[11](P199)
同时,黄侃对于《文始》中成均图之对转、旁转的条例,也有自己的意见,说:“古音通转之理,前人多立对转、旁转之名;今谓对转于音理实有,其余名目皆可不立;以双声叠韵二理,可赅括而无余也。”[10](P63)隐然表达批评抗衡之意。黄侃尤能以现代思维表达对清学以来学术转型的构划和思考,将清代小学考据方式由具体而抽象,由纠牵于文本语言之具象而上升表述为普遍学理,由旧学之凡例条例之说而展开学科转化,所作《说文略说》《音略》《声韵略说》《声韵通例》《反切解释上编》、其所讲《训诂述略》《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等,已经由根柢而衍绎条理,述以学理层次,由术及道,表述方式和建构具有了学科形态。
章、黄二氏于社会持激进民族主义,文化上则秉保守主义,学问尚专精,重师法,传习尤恃赖天资和勤奋兼备,学术理想呈现出浓厚的保守色彩。如黄侃说:“无论历史学、文字学,凡新发见之物,必可助长旧学,但未能推翻旧学。新发见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断不能推倒旧学说。”又说:“治中国学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佛经云依法不依人,即此义。”[5](P3-4)刘赜之撰《声韵学表解》,自言曰:
语言文字为吾人日用所不能须臾离之物,世人误以音学为攻治故籍之专业,往往心声心画鄙夫孺子能言其音,而士人不能举其字,有能举其字者又不能籀其义,且误读其音。吾实罕见学人能读数十字之文辞而音读不惝怳者,遑问其能知假借理故训哉。行见文言日以分驰,而俱即于鄙倍呰窳而已。今之言发扬民族或整理国故者鲜知及此,可不谓忘其本实耶。[14](P2)
此种由学术承守而发为文化保守之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学术、文化西来大潮之下,不仅不获理解,和者鲜寡,而且为新派学人多所议抑。在疑古思潮弥漫,国故新变,西方近现代科学方法、新史学和普通语言学方法、社会科学实验和田野调查手段等重建中国学术的风气进程下,章黄所守门径和知识陈述,一再受到严厉的学术批评和文化否定,例如强调师法,一尊师承被认为是旧学余孽;如谓其崇古封建,袭旧术语,缺乏现代科学形态和普通语音学的面貌;发明之意过于证实之可能,无论是以古证古,还是以古证今,不能免于穿凿,效颦者更易流于荒谬;过信《说文》,死守其形体和形义之说,不能得文字赋形取义之真;章氏“名原”“字原”“音原”之说关系牵杂,不能清晰地析分文字系统和语言系统及其各自内涵的关系;黄侃训诂原理之说似是而非,粗疏失要,不能推明古人立名的精意等,凡此种种,认为章黄学术显得不够科学而不切现代,乃至于视其尊经复古的学术取舍,就是要维持封建制度和否认社会进化。加上章黄之学专门,积累为先,艰深难进,浅习难窥精华,逐渐声华不彰,传习亦稀。不过,21世纪以来,当中国人文学术舶来有穷,凿枘扞格,研究方式引起反思,本土旧学传统又重回眼域,尤其是传统文献学的文本思维和辨章别白之法则,小学考竟文字音义、故训是式的古典语言解释方法及其实践、经史结构和注疏诠释思维,渐受重视,人文学研究开始出现“古典转向”,这一研究转向并非改移对象,而是乞灵方法。就中国语文研究来说,章黄学术的内在价值开始重新浮现,其学术理念之邃密合理,学术想象之超前,学术实践之卓荦渐被揭示和理解,尤其是章、黄祖述之善,师法之醇,考古之殷,审音之精,读书之勤,求证之矜与夫学术之精的内在关系,愈发受到同情之理解和诠说。
从1893年张之洞创建自强学堂,设汉文门始,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武汉大学人文学术,由黄侃之师授奠基,经由刘赜、黄焯开辟耕耘,经过漫长的发展递嬗,形成了章黄学脉色彩浓厚的中国语文研究特点。其中,既有继承章太炎、黄侃学术一脉相承的问题意识,遵循黄侃“小学必须专治一书,始不同乎肤论”的治学要求[11](P12),而有专精具体的传统语文学研究,如刘赜之《说文》研究,黄焯之《诗》之经学训诂研究、《经典释文》校雠等,又有笃承师说的理论建设,如刘赜之音韵学讲义,黄焯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实参以己说,以融合出之的《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等。及于当代,在武汉大学,章黄学术醇乎师法的传统固曾有断裂,但学脉未绝,学术领域、学术建设、传授培养未尝灭弃,同时保守了较具风格的学术特色。我辈学人在扬弃旧学眼界藩篱的基础上,远绍清儒、章黄,承接刘赜、黄焯的学术实践,有薪传,有开辟,其体现,一是音韵训诂领域研究不辍,一是传统语言学典籍的整理研究和辞书编纂持续建设推进,而所继承发扬的学风,则是绝学传承和黄侃推倡的“扎硬寨,打死仗”“变业无成功”的治学方式。
章黄学术在武大基始奠基和传承发扬,不绝如缕,历历数之,已有一百年的历史。黄侃说:“治学须知二事,一曰治学之法,一曰持论之方。”又说:“人类一切学问,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德。”[5](P1)这是章黄学问的底蕴,是武汉大学人文学术百年传承的优良传统,也是我辈后学所欲缵续光大的学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