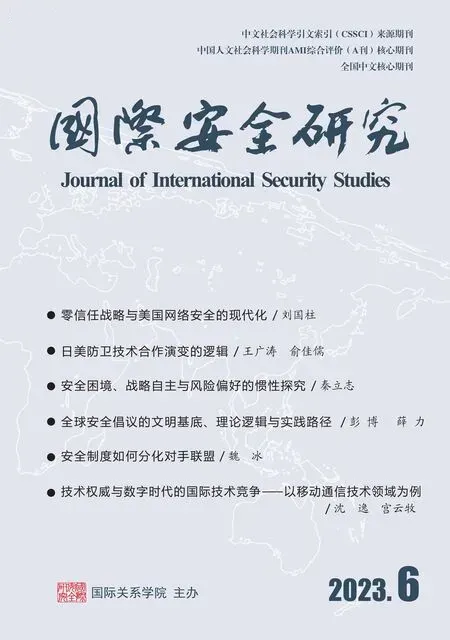安全制度如何分化对手联盟∗
魏 冰
【内容提要】 分化联盟是改变国家间实力对比的一种重要方式。现有研究围绕“楔子战略”这个概念系统论述了分化对手联盟的方式和机制,并提出了“奖励型楔子战略”和“强制型楔子战略”两种主要类型,两者均强调借助物质力量进行分化,可统称为“物质型楔子战略”。除此之外,由于联盟以竞争性安全理念为内核,而部分国家基于避免冲突和降低成本的考虑会在特定时期偏向合作性安全政策,因此分化国可以将差异化的合作理念作为切入点,即以“理念型楔子战略”实现对对手联盟的理念分化。理念型楔子战略旨在通过影响和改变目标国的安全理念来削弱其对联盟价值和功效的认知,从而间接促使其疏离联盟。当分化国对目标国不构成严重威胁,分化国在目标国关心的安全议题上具有较强的话语权,且目标国与部分第三方国家在该议题上持相似的政策立场时,分化国以理念型楔子战略为手段分化对手联盟。安全制度是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的主要平台,分化国可以利用安全制度提出合作性安全倡议,或者提出解决目标国重视的安全问题的合作性方案,以此为目标国提供联盟之外的替代性安全手段,进而削弱联盟对目标国的战略价值并降低对手联盟的合作水平。苏联在冷战时期提出的欧安会倡议是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的一次具体实践。
引 言
构建联盟和分化联盟是塑造国际体系均势形态的两种重要方式。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指出,国家可以通过内部手段和外部手段实现均势,其中,外部手段既包括增强和扩大自己的联盟,也包括削弱和缩减对手联盟。①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18.关于国家因何构建联盟,国际关系学界已经进行了充分探讨,大体上提出了“制衡威胁”(Balancing Threat)和“资源交换”(Concession-Extraction)两种解释模型。②Alexander Lanoszka, Military Allianc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22, pp. 25-35.关于如何分化对手联盟,学者们围绕“楔子战略”(wedge strategy)这个概念也已经建立起了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
现有研究主要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楔子战略,分别是“奖励型(reward)楔子战略”和“强制型(coercive)楔子战略”。前者指通过向目标国提供正向激励来吸引其疏离盟友;后者指通过向目标国采取持续的强硬措施来加剧与盟友的战略利益分歧,从而破坏对手联盟合作。③“奖励型楔子战略”和“强制型楔子战略”是泉川康弘(Yasuhiro Izumikawa)的划分方式,蒂莫西·克劳福德(Timothy W. Crawford)将两者分别称为“选择性安抚”(selective accommodation)和“对抗”(confrontation),两种分类方式不存在本质区别,参见Timothy W.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p. 160-164; Yasuhiro Izumikawa, “To Coerce or Reward? Theorizing Wedge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 22, No. 3, 2013, pp. 500-501。还有学者基于分化国对敌对联盟不同成员采取的不同手段做了更进一步的划分,参见韩召颖、黄钊龙:《楔子战略的理论、历史及对中国外交的启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6 期,第64-65 页。这两种战略均强调物质力量在分化对手联盟过程中的重要性,可统称为“物质型楔子战略”(material wedge strategy)。
然而,国际政治中还存在一些楔子战略实践无法归入上述两种类型的情况。例如冷战时期,苏联曾试图通过倡议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来分化美国与其西欧盟友,④Marie-Pierre Rey, “The USSR and the Helsinki Process, 1969-75: Optimism, Doubt, or Defiance?” in Andreas Wenger, Vojtech Mastny and Christian Nuenlist, eds.,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System: The Helsinki Process Revisited, 1965-7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pp. 68-70.这一过程既不涉及对西欧国家的物质奖励,也不存在对西欧国家的强制措施。实际上,欧安会代表的是一种区别于物质型楔子战略的新的楔子战略类型,旨在通过差异化的合作理念分化对手联盟,可称为“理念型楔子战略”(concept-based wedge strategy)。鉴于联盟建立在竞争性安全理念基础上,国家在分化对手联盟的过程中除采取物质性楔子战略外,还可以借助以合作性安全理念为核心的安全制度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
一 文献回顾
分化对手联盟的思想智慧和政策实践自古有之。在中国历史上,《孙子兵法》中提出的“亲而离之”策略,战国时期秦国针对六国实施的“连横”策略,其核心理念都是从内部分化瓦解对手联盟。①刘丰:《亲而离之:分化对手联盟》,《世界知识》2013 年第5 期,第56 页。在西方历史上,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法国以及俾斯麦时期的普鲁士等都曾通过分化对手联盟而取得实力优势。②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Stacie E. Goddard, “When Right Makes Might: How Prussia Overturned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3, 2009, pp.110-142;刘城晨、翟新:《战略调适与联盟瓦解:分化联盟的实践路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 期,第53-79 页。但对楔子战略的理论研究直到21 世纪初才有明显的进展,围绕楔子战略的概念和机制,学者们已经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此外,由于联盟本质上是国际制度的一种类型,而国际制度竞争会对竞争双方的实力对比产生影响,因此回顾国际制度竞争的相关文献同样能为楔子战略的研究提供启发。
(一)关于楔子战略的现有研究
楔子战略的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三个方面。首先,对楔子战略的概念化。对于如何界定楔子战略,不同学者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蒂莫西·克劳福德(Timothy Crawford)将其定义为“国家以可接受的成本阻止、分化或破坏威胁性或围堵性联盟的手段”。③Timothy W.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 156.凌胜利将其界定为“联盟(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或次国家行为体基于阻止潜在的敌对联盟形成或分化、破坏、瓦解已经形成的敌对联盟的目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资源,采取对抗或调适等战略手段来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艺术与科学”。④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7 期,第73 页。尽管措辞不同,但学者们对楔子战略的内在目标存在基本共识,强调其核心是破坏其他国家针对自己的联盟行为。
关于楔子战略的类型,除奖励型楔子战略和强制型楔子战略外,学者们还提出过进攻型(offensive)楔子战略、防御型(defensive)楔子战略、①Timothy W.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p. 175-187.强化型(reinforcing)楔子战略、抵消型(countervailing)楔子战略、②David A. Baldwin, “Power Analysis and World Politics: New Trends versus Old Tendencies,”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2, 1979, pp. 162-163.示范型(demonstrative)楔子战略和颠覆型(subversive)楔子战略③David Wallsh, Andrew Taffer and Dmitry Gorenburg, “Countering Chinese and Russian Alliance Wedge Strategies,” CNA Corporation, 2022, https://www.cna.org/reports/2022/05/Countering-Chinese-and-Russian-Alliance-Wedge-Strategies.pdf.等其他类型,但这些类型化方式的标准是实施楔子战略的动因和对象,其形式和内容与奖励型楔子战略和强制型楔子战略没有实质区别。
关于楔子战略的具体手段,刘丰区分了合作性战略、对抗性战略和观望战略三种类型。④刘丰:《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机制与案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1 期,第53-57 页。凌胜利从语言类、经济类、政治类和军事类四个维度进行了基础性划分。⑤凌胜利:《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的楔子战略》,《当代亚太》2016 年第1 期,第15-21 页。克劳福德提出奖励型楔子战略的手段有绥靖(appeasement)、让步和补偿(concessions and compensation)、担保(endorsement)三种。⑥Timothy W.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p. 167-175; Timothy W. Crawford, The Power to Divide: Wedge Strategies in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10.除此之外,垂直场所转移(vertical forum-shifting)、⑦Kristen Hopewell, “Balancing, Threats, and Wedg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Origins and Impact of the Sino-Indian Alliance at the WTO,”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32,No. 141, 2023, pp. 369-385.冲突促进(conflict promotion)、⑧Robert P. Hager, “‘The Laughing Third Man in a Fight’: Stalin’s Use of the Wedge Strategy,”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50, No. 1, 2017, pp. 15-27.军备控制(arms control)、⑨Timothy W. Crawford and Khang X. Vu, “Arms Control as Wedge Strategy: How Arms Limitation Deals Divide Allianc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6, No. 2, 2021, pp. 91-129.混合干预(hybrid interference)⑩Mikael Wigell, “Hybrid Interference as a Wedge Strategy: A Theory of External Interference in Liberal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5, No. 2, 2019, pp. 255-275.等也被认为能够起到分化对手联盟的作用。
关于楔子战略的目标,克劳福德认为从易到难可以分为四种,分别是联盟分化(disalignment)、联盟预阻(prealignment)、联盟解除(dealignment)和联盟重组(realignment)。①Timothy W.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p. 164-167.韩召颖和黄钊龙在此基础上补充了联盟冲突(inter-alignment conflict)作为第五种目标,即通过使用楔子战略使目标国与其潜在或实际盟友陷入冲突。②韩召颖、黄钊龙:《楔子战略的理论、历史及对中国外交的启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6 期,第64 页。
其次,对楔子战略的理论化。围绕奖励型楔子战略和强制型楔子战略的实施条件和起效条件,学者们提出了不同观点。克劳福德认为,分化国在多数情况下会倾向于使用奖励型楔子战略,因为强制型楔子战略容易加剧目标国的威胁认知,从而使对手联盟变得更加团结。③Timothy W.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p. 160-164.在此基础上,分化国的奖励能力以及目标国对分化国的战略重要性会共同决定分化国对于楔子战略的选择,分化国对于楔子战略的目标预期及其自身所受的联盟约束状况会影响战略效果。④Timothy W. Crawford, The Power to Divide: Wedge Strategies in Great Power Competition,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9-25.泉川康弘则认为,分化国的奖励能力和对手联盟的安全依赖程度共同决定了分化国的选择。⑤Yasuhiro Izumikawa, “United We Stand, Divided They Fall: Use of Coercion and Rewards as Alliance Balancing Strategy,” Ph. D. Disserta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2001; Yasuhiro Izumikawa,“To Coerce or Reward? Theorizing Wedge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 22,No. 3, 2013, pp. 498-531.在泉川观点的基础上,玄珠柳(Hyon Joo Yoo)进一步补充了目标国改善与分化国关系的意愿这一因素的影响。⑥Hyon Joo Yoo, “China’s Friendly Offensive Toward Japan in the 1950s: The Theory of Wedge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ian Perspective, Vol. 39, No. 1, 2015, pp. 1-26.钟振明基于能力、利益和手段等不同维度,揭示了奖励型楔子战略和强制型楔子战略的实施条件。⑦钟振明:《报偿分化、强压分化及联盟政治中的楔子战略选择》,《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6 期,第20-29 页。黄宇兴将研究对象限定为不对称联盟,提出联盟成员间相互依赖的对称性是影响楔子战略成效的决定性因素。⑧Yuxing Huang, “An Interdependence Theory of Wedge Strategie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3, No. 2, 2020, pp. 253-286.
最后,对楔子战略的经验分析。除了广受关注的历史案例外,学者们对当下的现实案例也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评估了中俄两国在2014—2021 年间分化美国联盟的六个案例,他们发现中俄两国会优先选择奖励型楔子战略,只有在失败后才会转向强制型楔子战略或颠覆型楔子战略,相比之下,奖励型楔子战略更加有效。①David Wallsh, Andrew Taffer and Dmitry Gorenburg, “Countering Chinese and Russian Alliance Wedge Strategies,” CNA Corporation, 2022, https://www.cna.org/reports/2022/05/Countering-Chinese-and-Russian-Alliance-Wedge-Strategies.pdf.马泰奥·戴安(Matteo Dian)和安娜·基列娃(Anna Kireeva)分析了2012—2020 年间俄日两国对对方集团实施楔子战略的情况,发现由积极的经济和政治激励与有限的强制相结合的楔子战略比纯粹的奖励或强制更有效。②Matteo Dian and Anna Kireeva, “Wedge Strategies in Russia-Japan Rel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5, No. 5, 2022, pp. 853-883.还有学者分析了俄罗斯如何分化美欧联盟,③Mikael Wigell and Antto Vihma, “Geopolitics versus Geoeconomics: The Case of Russia’s Geostrategy and Its Effects on the EU,”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2, No. 3, 2016, pp. 605-627.中国在“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如何分化澳大利亚、东盟等与美国的关系,④Tommy Sheng Hao Chai, “How China Attempts to Drive a Wedge in the U.S.-Australia Allian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4, No. 5, 2020, pp. 511-531; Ruonan Liu,“Reinforcing Wedging: Assessing China’s Southeast Asia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China Review, Vol. 23, No. 1, 2023, pp. 277-306.以及美国如何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朝鲜等竞争对手实施楔子战略。⑤阮建平、林一斋:《美国分化中俄与中国的预应思考》,《边界与海洋研究》2020 年第2期,第59-72 页;王晓虎:《“统一预阻”:美台安全合作的楔子战略视角》,《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3 期,第39-48 页;钟振明:《美朝之间强压型互动的联盟分化逻辑——一种楔子战略的分析》,《教学与研究》2018 年第11 期,第50-58 页;王晓虎:《美国楔子战略与亚太联盟预阻》,《国际展望》2017 年第3 期,第58-77 页;凌胜利:《双重分化: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楔子战略》,《东北亚论坛》2017 年第5 期,第46-57 页。
整体看来,现有研究对楔子战略的概念、机制和效果等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但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研究,都建立在奖励和强制这种类型化方式的基础上。一些研究声称提出了第三种楔子战略类型,但本质上只是楔子战略发挥作用的不同路径,而没有关注到楔子战略在内容和手段上还存在其他形式。
(二)关于国际制度竞争的现有研究
从广义上看,联盟是国际制度的一个子集。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国际制度是“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一整套相互关联并持久存在的约束规则,这些规则规定行为体的行为角色,约束行为体的行为,并塑造行为体的预期”。⑥Robert Keohane,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 Perspective on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Keohane, ed., Institu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 Westview, 1989, pp. 1-20.联盟无疑符合国际制度的一般性特征。
国际制度竞争被普遍认为是推动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动力。李巍和罗仪馥指出,国际制度竞争存在四个基本维度,分别是规则之争、机制之争、机构之争和秩序之争。其中,秩序之争是最高形式和最终目的,崛起国和霸权国都试图通过国际制度竞争来构建对本国有利的国际秩序。①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4 期,第28-57 页。贺凯和冯惠云则认为,当前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制度竞争策略,并且由于制度竞争的强度相对较低,因此中国崛起的进程会比普遍预期更加和平。②Kai He and Huiyun Feng, “Leadership Transi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Role Conception,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the AIIB,”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2,2019, pp. 153-178.
就国际制度竞争的具体表现而言,学者们分别对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制度竞争策略进行分析。朱杰进认为,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分为替代、叠加、转换和偏离四种类型,霸权国的制度否决能力与既有国际制度的弹性空间是影响崛起国选择制度改革路径的主要因素。③朱杰进:《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6 期,第75-105 页。陈拯关注霸权国的策略,认为霸权国存在谈判改制与退出制度两种基本策略,是否具备有吸引力的退出选项以及改制的谈判成本是影响其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④陈拯:《霸权国修正国际制度的策略选择》,《国际政治科学》2021 年第3 期,第33-67 页。
考虑到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体系是当前国际秩序的基石,现有研究大都将国际制度竞争与国际秩序转型直接联系起来,强调崛起国和霸权国改革现有制度和创建新制度的行为会通过影响双方的国际话语权而影响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除了这种直接路径,崛起国和霸权国还将国际制度作为分化对手阵营的工具,通过削弱对手实力间接影响国际秩序的转型过程。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种间接路径,他们发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制度吸引了部分美国盟友的加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国联盟的内部分裂。⑤Lars S. Skålnes, “Layering and Displacement in Development Finance: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4,No. 2, 2021, pp. 257-288; Kai He and Huiyun Feng, “Leadership Transi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Role Conception,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the AIIB,”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 12, No. 2, 2019, pp. 153-178;赵洋:《中美制度竞争分析——以“一带一路”为例》,《当代亚太》2016 年第2 期,第28-57 页。这表明国际制度在客观上可以发挥楔子战略的功效。
可见,国际制度竞争的研究在某些方面能够与楔子战略的研究进行有效结合。然而,现有的相关研究仅仅关注到国际制度在提供物质资源上的作用,因此仍然局限于奖励型楔子战略和强制型楔子战略这种强调物质分化的传统类型化方式,忽视了安全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类型国际制度,其理念价值对于分化对手联盟的作用。
二 安全制度与理念分化
为使研究过程更加清晰和顺畅,对理念型楔子战略的讨论将在两个限制条件下进行。第一,楔子战略的目标为分化联盟,即降低对手联盟的合作水平,这是其他层级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础,瓦解对手联盟或阻止潜在对手联盟成立往往伴随着其成员之间关系的降级和疏远。第二,楔子战略的对象是联盟(alliance),①关于联盟与其他安全合作形式的区别,参见Thomas S. Wilkins, “‘Alignment’, not ‘Alliance’—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ward a Conceptual Taxonomy of Align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8, No. 1, 2012, pp. 53-76。相比伙伴关系等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形式,联盟更多以外部威胁为动力,竞争性和排他性更强,因此更便于识别理念分化。
(一)“物质型楔子战略”与“理念型楔子战略”
楔子战略的作用机制与目标国对联盟价值的评估密切相关。一般而言,联盟的价值是由联盟带来的收益和参与联盟的成本共同决定。当收益过低或者成本过高时,意味着联盟的价值较低,此时成员国疏远盟友和退出联盟的意愿相对更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楔子战略的本质就是通过降低联盟给目标国带来的收益,或者提升目标国参与联盟的成本,以此削弱目标国维持联盟合作的意愿。
现有研究对楔子战略作用机制的阐述与此相符。克劳福德指出,奖励型楔子战略的核心机制是交换(exchange),即分化国向目标国提供物质奖励来换取后者调整联盟模式;②Timothy W. Crawford, The Power to Divide: Wedge Strategies in Great Power Competition,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10.强制型楔子战略的基本逻辑则是通过持续施压加剧对手联盟内部的利益分歧,从而促成其分化。③Timothy W.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p. 161-162.其中,奖励型楔子战略会降低目标国的联盟收益,因为分化国提供的物质奖励会弱化对手联盟对其形成的共同威胁认知,并且削弱联盟固有收益对目标国的相对价值,从而使目标国感受到联盟收益下降。①Timothy W.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 161.强制型楔子战略则会同时降低联盟收益和增加联盟成本,因为利益分歧一方面会削弱联盟可靠性,使目标国获取盟友安全支持的预期下降;另一方面则会提升联盟协调的难度和联盟困境的风险。凌胜利从战略环境、战略目标和联盟关系三个层次分析了楔子战略的作用机制,认为其核心在于影响目标国的联盟利益认知,使其对是否应该结盟和是否应该履行联盟义务等问题的认知发生了有利于分化国的转变,从而实现分化对手联盟的目标。②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7 期,第75-81 页。联盟利益认知与对联盟价值的判断在内涵上基本一致。泉川康弘认为,强制型楔子战略的主要作用机制在于通过提升对手联盟的“被牵连”风险而破坏对手联盟合作。③Yasuhiro Izumikawa, “To Coerce or Reward? Theorizing Wedge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Security Studies, Vol. 22, No. 3, 2013, p. 503.而“被牵连”风险是成员国参与联盟所面临的主要成本。刘丰基于对联盟瓦解条件的分析提出,楔子战略成功的机制有两条,一是国家趋利避害的倾向,二是联盟困境带来的风险平衡意识。在这两条机制的作用下,楔子战略可能导致对手联盟无法给成员国带来额外安全,同时使成员国在潜在或实际冲突中负担较高成本,进而导致对手联盟的分化乃至瓦解。④刘丰:《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机制与案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1 期,第57-59 页。
奖励型楔子战略和强制型楔子战略主要通过物质力量改变目标国对于联盟价值的认知,从而实现联盟分化。这两种手段的着眼点在于联盟的物质属性,即成员国基于共同或互补的安全利益而将各自的战略资源进行汇聚,以互相提供安全支持。因此,这两种联盟分化战略可以统称为“物质型楔子战略”。
然而,除了物质属性外,联盟作为一种安全合作形式,还具有理念属性。相比联合阵线(coalition)、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和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等其他形式的安全联合(alignment),联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排他性和对抗性。⑤Thomas S. Wilkins, “‘Alignment’, not ‘Alliance’—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ward a Conceptual Taxonomy of Align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38, No. 1, 2012, pp. 59-72.国家选择建立联盟的主要目的是借助盟友的力量与第三方行为体竞争,通过提升相对实力来获得安全。这种安全手段反映的是一种竞争性安全理念,即以零和思维看待自我与他者的安全状态,认为他者安全水平的上升意味着自我安全水平的下降。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竞争性安全理念指导的政策实践必然会加剧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正如格伦·斯奈德(Glenn H. Snyder)所指出的,为展示联盟团结而采取的行为会被对手视作更大的威胁,后者为维护自身安全将采取类似的行为进行回应,由此导致双方的敌意螺旋式上升。①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1984, pp. 477-479.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之间爆发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也更大。
战争固然是国家实现利益的可选手段,但其成本过于高昂,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国家的优先选项。对中小国家而言尤其如此,这类国家承受战争后果的能力相对更弱,因此,除了涉及核心利益冲突的情况,中小国家在多数时候会更倾向于合作性安全理念和安全政策,即以正和思维看待自我与他者的安全状态,认为他者安全水平的上升或下降会导致自我安全水平出现相同的变化。考虑到这一点,“理念型楔子战略”可以成为分化对手联盟的可用选项。
与物质型楔子战略相比,理念型楔子战略的风险更小。理念型楔子战略旨在通过影响和改变目标国的安全合作理念来削弱其对联盟价值和功效的认知,从而间接促使其疏离联盟。从作用机制来看,理念型楔子战略的核心在于使目标国意识到,除了以竞争性安全理念为内核的联盟外,还存在成本和风险更低的以合作性安全理念为内核的替代性安全方案。如前所述,中小国家在多数时候倾向于合作性安全理念和政策,但在现有联盟的约束以及自身实力的限制下,这类国家很难将其付诸实践。在此背景下,如果分化国能够主动提供一种基于合作性安全理念的有效方案,将对这些中小国家形成较强的吸引力。
在所有物质型楔子战略中,强制型楔子战略无疑风险最大。克劳福德和泉川康弘都承认,强制型楔子战略可能强化对手联盟对分化国的共同威胁认知,反而可能加强对手联盟的合作,甚至导致冲突。从历史上看,一战前夕,在协约国与同盟国相继形成后,协约国内部曾围绕是否应该对奥匈帝国实施强制型楔子战略进行过讨论。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明确表示,任何企图将奥匈帝国从德国身边分离出去的行为都将导致德国为维护荣誉而不惜一切代价,最终会把欧洲拖入可怕的战争中。②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37-338.德国此前曾在两次摩洛哥危机中试图对英法联盟实施进攻型楔子战略,但最终反而导致后者因恐惧加强了合作,并推动了一战的爆发。①姜鹏:《从属侧施压:同盟强化还是同盟瓦解?——“进攻性楔子战略”成败的政治条件及其类型化研究》,《国际安全研究》2021 年第3 期,第39-46 页。
奖励型楔子战略的风险则在于,一方面,分化国无法确保战略效果,分化对手联盟一旦失败,那么向目标国提供的奖励将反过来提升对手联盟的相对实力,从而恶化自己的处境;另一方面,提供奖励可能被目标国视为分化国发出的示弱信号,由此导致目标国提出更多要求,使分化国面临严重的沉没成本。②Timothy W. Crawford, The Power to Divide: Wedge Strategies in Great Power Competition,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11.
不论是提供奖励还是施加压力,物质型楔子战略都需要直接作用于目标国和对手联盟。在这种情况下,目标国盟友可能寻求通过捆绑战略(binding strategy)来维持和增强盟友对联盟的忠诚。③Yasuhiro Izumikawa, “Binding Strategies in Alliance Politics: The Soviet-Japanese-US Diplomatic Tug of War in the Mid-1950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2, No. 1, 2018, pp.108-120; Chengzhi Yin, “Logic of Choice: China’s Binding Strategies toward North Korea, 1965-1970,”Security Studies, Vol. 31, No. 3, 2022, pp. 483-509.与楔子战略的传统类型化方式类似,捆绑战略通常也被划分为强制型捆绑战略和奖励型捆绑战略。当目标国盟友选择使用奖励型捆绑战略时,其与分化国将陷入针对目标国的“竞价战”,分化国实施楔子战略的成本将由此上升。当目标国盟友选择使用强制型捆绑战略时,如果战略成功,那么目标国受其盟友控制和约束的水平将进一步上升,分化的难度也将更大;而如果战略失败,意味着对手联盟内部将出现分裂和不团结。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的研究发现,联盟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变得更加好战,从而提升外部战争的可能性。④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理念型楔子战略则不需要直接作用于对手联盟。基于合作性安全理念的替代性方案,从形式上看并不构成对对手联盟的挑战,新方案既不强制要求目标国参加,也不会改变对手联盟内部的实力结构,因此不会直接冲击对手联盟的凝聚力。实际上,理念型楔子战略的基本逻辑在于使目标国主动将原本投入到联盟中的精力和资源转移到替代性方案中,以此降低对手联盟的合作水平。由于无需与对手联盟产生直接关系,理念型楔子战略的风险因而也更小。
理念型楔子战略的实施条件有三个。第一,分化国对目标国不构成严重威胁,只有在威胁认知较弱的前提下,目标国才会有足够的意愿开展合作。第二,分化国在目标国关心的安全议题上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只有在此背景下,目标国才会认为分化国提出的方案具有可行性和可信度,也才会主动寻求参加。第三,目标国关心的安全议题受到部分第三方国家的关注,并且双方在该议题上的政策立场相似,只有满足这个条件,分化国提出的方案才能具备更强的合法性,其所面临的阻力也才会更小。
理念型楔子战略和物质型楔子战略能够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达成分化对手联盟的效果,国家在实践时既可以选择其中一种,也可以对两者进行综合运用。但需要注意的是,理念型楔子战略只能与奖励型楔子战略同时使用,因为分化国在使用这两种战略时都需要向目标国示好,两者的叠加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对对手联盟的分化效果;与之相反,强制型楔子战略与分化国向目标国发出的威胁信号相伴而生,无法与理念型楔子战略同时存在。考虑到理念型楔子战略的着眼点在于提出新的安全方案,因此安全制度是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最理想的平台。
(二)安全制度分化对手联盟的机制
安全制度是国际制度在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依照合作的基本动力来源和制度化水平,安全制度在广义上可以区分为联盟、军事联合阵线、安全组织和安全对话机制四种类型。①魏冰:《地区安全制度扩员的机制与动力》,《当代亚太》2021 年第4 期,第73-78 页。鉴于理念型楔子战略的实施重点是基于合作性安全理念的安全方案,因此安全组织和安全对话机制这两种基于内在合作动力而建立的安全制度是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的主要平台。
安全制度之所以能够成为理念型楔子战略的实施场所,是因为其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较弱的约束性。安全制度的建立通常与成员国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相关,国家参与安全制度的主要目的并非对抗某个特定国家的威胁,而是与其他国家一同讨论和应对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正因如此,安全制度在吸收新成员的问题上也更加开放和包容,只要是面临类似安全问题的国家,都具备成为新成员的资格。不仅如此,安全制度对成员国行为的约束也相对较弱。制度化水平较低的安全对话机制更多是作为一种交流平台而存在,几乎不会对成员国施加任何限制,其决议的履行情况通常由成员国自行决定。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安全组织由于有自身长远的发展规划,因此会要求成员国遵守和履行决议,但决议的制定过程相比联盟更为平等,即使是中小国家往往也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因此对成员国行为的约束也相对较弱。②魏冰:《地区安全制度扩员的机制与动力》,《当代亚太》2021 年第4 期,第77-78 页。
安全制度的强包容性意味着即使是处于竞争乃至敌对关系中的国家也可以共同参与,这就使其能够成为分化国与目标国合作的平台;弱约束性则有助于降低目标国对参与制度的顾虑,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标国盟友的危机感。对于目标国来说,安全制度的多边性有助于强化其所关心的安全议题的受关注程度,并通过引入其他国家的力量加速解决问题的进度。
安全制度主要通过两个机制促进对手联盟的分化。第一,分化国以安全制度为平台提出合作性安全倡议,以此推动目标国调整以联盟为核心的安全战略。联盟一经形成,通常会成为成员国安全战略的主要工具,而合作性安全倡议能够在两个方面转移目标国对联盟的战略依赖。一是成本—收益计算。参与联盟伴随着较高的物质成本,还要承担被盟友牵连的风险。当所面临的安全环境较为恶劣时,国家通常愿意接受这些成本;而当所面临的安全环境较为宽松时,国家对联盟成本的容忍度也将随之下降。合作性安全倡议则是一种成本更低的安全方案,它不要求成员国投入太多物质资源来提升安全水平,而是通过不断的交流和协商来增进战略互信,消除彼此之间的进攻性意图。合作性安全倡议通常更容易被普通民众接受,从而对目标国领导人形成观众成本,出于维持政权稳固的目的,目标国可能不得不接受倡议。二是在对手联盟内部制造分歧。弗雷德·伊克尔(Fred Iklé)在分析国家间谈判时指出,邀请敌对集团中的某个成员开展谈判的倡议可能产生一种离间效应,因为没有被邀请的成员会担心自己的利益在谈判中受到损害,从而与受邀请的成员出现分歧。①Fred Iklé, How Nations Negotiate, New York: Praeger, 1964, p. 57.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分化对手联盟。考虑到分化国与目标国盟友之间的竞争关系,即使分化国提出的安全倡议向任何国家开放,目标国盟友通常也不会主动申请加入。不仅如此,它还可能极力阻止目标国加入,从而导致目标国与盟友之间的分歧和联盟分裂。
第二,分化国以安全制度为平台提出解决目标国重视的安全问题的合作性方案,以此降低联盟对目标国的战略价值。联盟合作通常围绕如何防范和应对外部势力的进攻而展开,尽管成员国都期望能够享受到“联盟光环”效应,即在联盟条约规定的事项之外得到盟友的支持,②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56-359.但这并不属于联盟义务的范畴,这就意味着除非成员国关注的议题涉及其盟友的利益,否则后者介入的意愿相对较低。即使目标国所关注的安全议题属于联盟义务的范畴,或者盟友愿意在该议题上提供支持,所产生的后果也不一定符合目标国的利益。联盟的介入可能增加冲突爆发的可能性,①李冲、漆海霞:《盟主国声誉、安全依赖与冲突爆发》,《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 年第2 期,第29-32 页。而目标国是冲突成本和后果的最直接承受方。基于此,即使目标国将联盟视作威慑对手和保护自己的主要手段,联盟框架下的对抗手段也可能并非解决目标国问题的首要选项。
相比之下,以协商和谈判为主要手段的合作性方案具有以下优势:首先,可以缓解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其次,分化国作为第三方加入协商和谈判,也有助于推进谈判进程,尤其是分化国能够影响目标国对手的对外政策时。最后,安全制度的包容性和非约束性使目标国在接受合作性方案的同时,能够继续将联盟作为维护自身安全的最后防线。然而,将合作性方案作为首要应对手段,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转移目标国对联盟投入的精力和资源,如果合作性方案的效果较好,目标国与分化国的关系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由此将造成联盟合作水平的相对下降,从而达成分化对手联盟的效果。
从以上两个机制可以发现,理念型楔子战略的实施过程和效果会受到目标国与盟友关系的重要影响。当目标国与其盟友本就存在矛盾时,目标国追求自主的动力将会上升,由此将为理念型楔子战略的实施提供额外的动力;相反,当目标国与其盟友的关系较为稳固,或者后者主动加强与前者的捆绑时,理念型楔子战略的实施难度将会上升。事实上,这是不同类型楔子战略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三 欧安会与苏联的理念型楔子战略实践
1975 年7 月30 日至8 月1 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被称为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缓和”(détente)的顶峰,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33 个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共同参与了此次会议,会议通过的《欧洲安全与合作最后文件》(又称《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提出,所有参会国“认识到欧洲安全具有不可分割性,并且它们在推动全欧合作的发展上有共同利益”。②OSC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Final Act,” August 1, 1975,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5/c/39501.pdf.自此,以对话谈判为主要安全手段的“赫尔辛基进程”(Helsinki Process)正式开启,并在塑造欧洲地区“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观念和区域安全共同体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①朱立群、林民旺:《赫尔辛基进程30 年:塑造共同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12 期,第16-20 页。苏联是欧安会倡议的最早提出者,事实上,苏联倡导召开欧安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试图通过强化欧洲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对美国与其西欧盟友进行分化。
(一)欧安会的背景与历程
欧安会倡议是在1954 年1—2 月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首次提出的。②Martin Russell,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A Pillar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September 2021, p. 2. 关于欧安会倡议的详细历程,可参见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Public Statements and Documents, 1954-1986,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1986;瓦日芒:《缓和的幻想》,丁世中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124-134 页;陈须隆:《区域安全合作之道——欧安会/欧安组织的经验、模式及其亚太相关性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年版,第15-58 页;刘馗:《美国对欧安会的政策研究(1954—1975)》,华中师范大学2016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57 页。苏联在会上提议召开欧洲安全会议和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主张所有欧洲国家在《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指导下缔结一份欧洲集体安全条约。1954 年11月,苏联单方面召开欧安会并向包括美国在内的23 个国家发出邀请,但最终只有7 个东欧国家出席。1955 年7 月,苏联在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上再次提出将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作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并制定了一份更为详细的方案。但在这一时期,由于两大阵营在以德国问题为核心的一系列欧洲安全问题上没有形成基本共识,因此西方国家对苏联提出的倡议持坚决反对和拒绝的立场。再加上联邦德国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实现了再武装化并加入北约,而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建立华约进行回应,两大阵营的对抗态势正处于发展期。苏联逐渐意识到此时召开欧洲安全会议和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不可能取得预期成效,因此自1956 年开始也搁置了欧安会倡议。
进入20 世纪50 年代后期,两大阵营之间的竞争与对抗愈发白热化,相继爆发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出于对核战争的恐惧,美苏双方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开始加强合作,在东西缓和的大环境下,苏联再度将欧安会倡议提上议程。1966 年7 月,华约组织布加勒斯特会议发布了《关于加强欧洲和平与安全的宣言》(又称《布加勒斯特宣言》),提出通过召开全欧会议来讨论和解决欧洲安全与合作问题。这份宣言成为日后召开的欧安会正式会议的议程基础。③陈须隆:《欧安会的起源:主意的产生(1954—1969)》,《欧洲》2001 年第2 期,第87 页。尽管1968 年8 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对其国际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但美苏关系缓和的趋势并未因此而中止。1969 年3 月,华约组织布达佩斯会议发布了《华约成员国向欧洲所有国家的呼吁书》(又称《布达佩斯呼吁书》),呼吁召开欧安会的前期准备会议,以确定正式会议的议程。
在这一时期,美国对欧安会倡议仍然保持怀疑和警惕,但接受度却在上升。一方面,尼克松上台后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调整,重视与苏联开展合作;另一方面,美国的许多欧洲盟友对欧安会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在此背景下,美苏两国领导人于1972 年5 月在莫斯科举行首脑会谈并发表联合公报,就召开欧安会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同年11 月,欧洲33 个国家及美国和加拿大召开了欧安会的筹备会,各方就会议议程、己方立场和观点、议题详细内容等进行了深入讨论,筹备会一直持续到1973 年6 月,并拟定了《赫尔辛基最后建议蓝皮书》。
欧安会的正式会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3 年7 月3 日至6 日,由各国外长参加,会议批准了《赫尔辛基最后建议蓝皮书》;第二阶段是1973 年9 月18日至1975 年7 月21 日,由各国派出专家代表讨论具体议题,并拟定《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第三阶段是1975 年7 月30 日至8 月1 日的首脑会议,各国领导人正式签署《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至此,作为一项合作性安全倡议的欧安会最终确立下来,并在1995 年更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简称欧安组织)。尽管欧安组织的效力受到诸多质疑,但其成员数量仍在不断增加,时至今日仍然是讨论欧洲乃至全球安全问题的重要平台。
总体上,冷战时期苏联对欧安会的宣传大致可以分为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和60 年代中期至70 年代初期两个阶段。虽然苏联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不同,但其对欧安会的宣传却隐含着相似的意图,其中分化美国与其西欧盟友是苏联考虑的一个重点。
(二)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的欧安会宣传
苏联之所以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积极提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有四个重要的现实背景。一是德国分裂加剧了欧洲地区的冲突风险;二是北约的成立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提供了合法性来源;三是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加强了欧洲反共产主义的力量,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四是赫鲁晓夫上台后调整了苏联的对外政策,主张与西方和平共处,推动局势走向缓和。①时殷弘:《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1 期,第128-129 页。
在国际安全局势变化和国内政治环境调整的共同影响下,苏联寻求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并以此作为分化西方阵营和提升相对实力的突破点。1954 年年初,四国外长会议在英国首相丘吉尔提议下召开,旨在讨论如何解决德国问题和奥地利问题,德国问题是重中之重。苏联主张先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然后在此框架下逐步解决德国问题。为此,苏联建议欧洲建立一种集体安全机制,以期实现两个目标。第一,阻止西方国家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苏联在倡议中提出,各国应按照主权独立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加强合作和维持地区和平,阻止建立直接针对欧洲其他国家的集团,并建议签署欧洲集体安全条约,条约成员国不能加入任何军事联盟。第二,将美国排挤出欧洲事务。苏联在倡议中明确提出,欧洲集体安全条约只对欧洲国家开放,美国和中国可以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其中。①关于苏联倡议的详细内容,参见“General European Treaty on Collective Security in Europe,”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2-1954, Germany and Austria, Volume VII, Part 1, Conference files, lot 60 D 627, CF 197, No. 517, Proposal of the Soviet Delegation,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2-54v07p1/d517。由此可见,这个倡议一旦落实,将对西方阵营产生明显的分化和削弱作用,有助于苏联在欧洲地区确立主导地位并构建对东方阵营有利的均势结构。实际上,这也是冷战期间苏联欧洲政策的长期目标。②“Working Material for the Preparation of a European Security Conference,” October 10, 1969,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PA AA: MfAA C 367/78,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0082.
然而,美国明显察觉了苏联的意图。美国政府在对苏联参会目标的分析中提出,苏联意图是阻止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以及阻止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成立,同时认为苏联的重点策略是通过与法国达成安全合作来破坏欧洲防务共同体和拆散北约。③“Briefing Paper on Prospects for Berlin Conference,” in FRUS, 1952-1954, Germany and Austria, Volume VII, Part 1, PPS files, lot 65 D 101, “S/P Papers—Jan.–Feb. 1954”, No. 339, Paper Prepared by Jacob Beam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2-54v07p1/d339.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会议前也曾表示,此次会议可能是苏联破坏西方联盟和西欧安全的最后一次重要尝试。④“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81st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ursday,January 21, 1954,” in FRUS, 1952-1954, Germany and Austria, Volume VII, Part 1, No. 343,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2-54v07p1/d343.此外,与苏联相反,西方国家认为欧洲集体安全问题应当以解决德国问题为前提条件,并提出了解决德国问题的“艾登计划”。①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八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版,第206-207 页。因此,当苏联代表在会议上提出倡议时,美国、英国和法国一致表示反对。②“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at the Berlin Confere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in FRUS,1952-1954, Germany and Austria, Volume VII, Part 1, 396.1 BE/2-1154: Telegram, No. 451,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2-54v07p1/d451.
在1955 年的日内瓦首脑会议上,苏联为了争取西方的支持而对欧洲集体安全倡议进行了四点主要调整。一是同意美国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加入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二是同意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以独立身份加入。三是提出了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两个具体步骤:第一步是实现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和解,寻求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上达成一致;第二步是在此基础上解散两个军事集团,并签署新的欧洲集体安全条约。四是补充了成员国之间加强经济与文化合作的内容。③“General European Treaty on Collective Security in Europe,” in FRUS, 1955-1957, Austrian State Treaty; Summit and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s, 1955, Volume V, Document 251, Proposal of the Soviet Delegation, CF/DOC/6,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05/d251.尽管如此,西方国家对此仍然持反对态度,核心问题在于调整后的倡议在德国问题上没有根本性突破,苏联仍然寻求将德国问题放在欧洲集体安全问题的框架下进行讨论。
此刻正值东西方对峙与竞争的态势逐渐加强,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国家对苏联的威胁认知程度较高,对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需求较弱,对其前景也持怀疑态度。与此同时,美国加强与其西欧盟友间的合作,进一步提升了苏联通过宣传欧洲集体安全倡议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的难度。最终,西欧国家没有接受苏联的倡议。
对苏联而言,虽然这一时期的欧洲集体安全倡议在国家层面没有得到西方的正面回应,但在一些国家的国内层面却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越来越多的西欧和美国民众开始支持两大阵营之间的缓和。④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Western European and American Opinion Relating to the Four-Power Conference,” July 9, 1955, p. 3, https://www.proquest.com/governmentofficial-publications/western-european-american-opinion-relating-four/docview/1679067349/se-2.在国内社会的倒逼之下,西方国家政府也不得不开始重视欧洲集体安全问题,美、英、法和联邦德国还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后成立了专门研究和讨论相关事宜的工作组。这也为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开始西方世界接受欧安会倡议奠定了基础。
(三)20 世纪60 年代中期至70 年代初期的欧安会宣传
从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开始,冷战局势在三个方面出现了重大变化。一是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美苏开始加强双边合作,欧洲和全球安全形势逐渐走向缓和。二是欧洲各国寻求摆脱阵营束缚,西方阵营的法国和联邦德国,东方阵营的罗马尼亚等国纷纷开始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些国家之所以追求自主性的提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美苏双方在实现缓和后推行“越顶外交”,通过双边渠道协调欧洲事务,从而威胁它们的国家利益。①安德烈亚斯·温格、丹尼尔·莫克利:《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地区合作的模式》,载沃伊切克·马斯特尼、朱立群主编:《冷战的历史遗产:对安全、合作与冲突的透视》,聂文娟、樊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第193 页。除此之外,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也降低了西欧国家对其安全保障的信心,因此西欧国家希望通过缓和与东方阵营的关系和加强欧共体建设来维护自身安全。三是经济形势的变化。西欧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持续推进而步入经济复兴期,美国和苏联则因军事负担过重而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美欧双方还在关税和贸易等问题上不断产生摩擦。
在美苏缓和进程不断发展而西方阵营内部因经济矛盾和对外政策分歧等原因出现松动的背景下,苏联再一次掀起了召开欧安会的宣传浪潮。这一阶段苏联的宣传方式出现了三点变化。首先,前一时期的宣传围绕签署欧洲集体安全条约展开,后一时期仅强调召开欧洲安全会议。其次,前一时期主要由苏联通过多边渠道向西方国家进行宣传,这一时期更加重视双边渠道的宣传,并充分发挥东欧国家的作用。如在苏联的鼓励下,仅匈牙利就在1966—1970 年间相继与13 个西方国家就欧洲安全会议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磋商。②Csaba Békés, “Hungary, the Soviet Bloc,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CSCE Process, 1965-1975,”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8, No. 3, 2016, p. 119.最后,前一时期主要是在国家层面进行宣传,这一时期则深入到西方阵营国内,如通过欧洲共产党会议等政党间渠道争取西欧国家民众对欧安会的支持,以及鼓励一些跨国组织发放宣传册和组织共产主义者、左翼活动家和东西方的和平主义者共同参加讨论会。③Michael Cotey Morgan, The Final Act: The Helsinki Accor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85.
相比第一阶段,苏联在第二阶段的目标更为具体。第一,以欧安会为平台,通过签署国际条约的形式为二战结束画上一个象征性的句号,以最终实现和平。第二,在象征意义的基础上,利用多边渠道维持由二战、欧洲分裂和苏联主导东欧所构成的领土现状。第三,确定此后维系欧洲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第四,建立长期的泛欧对话机制,一方面加强与西欧国家的制度化联系,另一方面潜移默化地分化美国和西欧国家,并掌控欧洲事务的主导权。第五,通过与西欧国家和解来争取与西欧国家的经济合作。①Marie-Pierre Rey, “The USSR and the Helsinki Process, 1969-75: Optimism, Doubt, or Defiance?” in Andreas Wenger, Vojtech Mastny and Christian Nuenlist, eds.,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System: The Helsinki Process Revisited, 1965-7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pp. 68-70.苏联的这些意图集中反映在两份文件中,即1966 年的《布加勒斯特宣言》和1969 年的《布达佩斯呼吁书》。
尽管苏联在这一时期加强了对欧安会的宣传力度,但会议召开的过程仍然一波三折。首先,东方阵营内部就如何召开会议存在较大分歧。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更加重视欧安会的安全价值,希望通过承认领土现状来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而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则更看重通过欧安会加强与西方的经济联系。②“Budapest Appeal by Warsaw Pact Nations to All European Countries, March 17, 1969,” in United State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Documents on Disarmament, 1969, August 1970,pp. 106-108.为此,两派成员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布达佩斯会议上就如何设计会议议程展开激烈的争论,直到布达佩斯会议结束才勉强达成一致。除此之外,苏联国内的不同政治力量也存在争论,外交部坚定支持召开欧安会,一些党的机构则表现出不情愿的态度。③Marie-Pierre Rey, “The USSR and the Helsinki Process, 1969-75: Optimism, Doubt, or Defiance?” in Andreas Wenger, Vojtech Mastny and Christian Nuenlist, eds.,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System: The Helsinki Process Revisited, 1965-7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pp. 71-75.
其次,西方阵营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歧。美国尽管乐于与苏联展开接触与合作,但在两个方面仍然对欧安会存在担忧。第一,美国担心欧安会的召开可能导致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下降和西欧国家的自主权增强,加剧北约内部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矛盾,并对北约的稳定性和军事实力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产生负面影响。④“Factor Analysis Concerning the State of Preparation for a European Security Conference,” September 25, 1971,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PA AA: MfAA, C 368/78,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0096.第二,美国认为苏联新一轮的欧安会倡议相比前一时期并没有根本性变化,仍然寻求先解决欧洲集体安全问题,然后解决德国问题,并且缺乏实质性内容。基于这两点原因,美国直到60 年代后期仍然抵制欧安会。⑤范军、包文英:《苏联与欧安会》,《今日苏联东欧》1991 年第1 期,第22 页。
与美国相反,西欧国家对欧安会的热情却非常高涨,法国尤其积极。1966 年12月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Aleksei Kosygin)访法期间,与法国总统戴高乐就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相关事宜展开了讨论。①John van Oudenaren, Détente in Europe: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 since 1953, 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76.接替戴高乐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上任后延续了戴高乐对欧安会的支持立场,并主张加强东西方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希望以此在两大阵营之间培养共同的价值理念。②Nicolas Badalassi, “‘Neither Too Much nor Too Little’ France, the USSR and the Helsinki CSCE,” Cold War History, Vol. 18, No. 1, 2018, pp. 3-4.联邦德国也支持召开欧安会,事实上,勃兰特规划的长期政策目标就是通过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来确保欧洲的和平秩序。③Kristina Spohr Readma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Power of ‘Language’: West German Diplomacy and 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1972-1975,”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9, No. 6, 2006, p. 1078.挪威、丹麦和比利时等同样主张召开欧安会,它们相信这次会议能够推动缓和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则因国内民众的支持而避免表现出对欧安会的负面态度。欧洲的中立国也普遍支持召开欧安会,认为欧安会能够成为它们参与管理欧洲事务的平台,有助于打破两大阵营的垄断。④申红果:《论西方联盟各国对欧安会的态度及其意义》,《历史教学》2011 年第24 期,第55-56 页。加拿大则将欧安会视为展示其对欧洲安全承诺的机会,因此也表示支持。⑤Michael Cotey Morgan, “North America, Atlanticism, and the Making of the Helsinki Final Act,” in Andreas Wenger, Vojtech Mastny and Christian Nuenlist, eds.,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System: The Helsinki Process Revisited, 1965-7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34-36.
与之相对,荷兰和希腊等国与美国立场一致,认为欧安会对西方不利。英国虽然同意欧安会可能产生负面后果,但也意识到这样一场会议很难避免。英国人相信,如果西方拒绝欧安会,那么苏联就会以此为借口在国际社会上大做文章。因此,英国积极参与了欧安会的准备工作,并最大限度地为西方争取利益。⑥申红果:《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看英国对东西方缓和的态度》,《世界历史》2010 年第3期,第92-102 页。
在欧安会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使西方阵营内部在1969 年4 月的北约部长会议上爆发了激烈争论。最终,来自西欧国家的压力以及越南战争的负担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变对欧安会的立场。基辛格表示,“如果美国寸步不让,我们就可能在联盟中陷入孤立,把欧洲推向中立”。⑦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陈瑶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520 页。因此,美国到1969 年下半年正式同意召开欧安会。但为了避免会议进程完全由苏联主导以及由此带来的自身利益受损,美国确定了四个会议前提条件。第一,美国和加拿大以正式成员身份参会。尽管苏联在第一阶段后期的宣传进程中已经同意美国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但在第二阶段前期又重新表示欧洲安全会议应当仅限欧洲国家参加。第二,将解决德国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延续了西方阵营此前的方案。第三,开展共同均衡裁军谈判(Mutual and Balanced Force Reductions, MBFR),美国希望以此扭转因越南战争而导致的不利处境,并为欧安会的讨论补充实质性内容。第四,讨论人权问题。尽管基辛格等美国重要官员强调应当通过对苏联的行为施加约束来实现缓和,但在国内压力之下,美国最终选择将人权问题纳入欧安会议程。①Ronald E. Powaski, The Entangling Alli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Security, 1950-1993, Westport: Greenwood, 1994, p. 113.
然而,美国与其西欧盟友在裁军问题上却产生了矛盾,尤其在是否应该将裁军问题与欧安会进行联系以及如何联系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总体上,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和联邦德国支持将欧安会与裁军问题联系起来,法国则持明确的反对立场。但鉴于美国在联盟中享有霸权地位,并且能够直接与苏联进行谈判,因此裁军问题的谈判进程主要由美国掌控。②Helga Haftendorn, “The Link between CSCE and MBFR: Two Sprouts from One Bulb,” in Andreas Wenger, Vojtech Mastny and Christian Nuenlist, eds.,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System:The Helsinki Process Revisited, 1965-7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237-254.有学者提出,欧洲国家和美国对欧安会及缓和进程的看法存在明显的不同,欧洲国家将两者视为弥合两大阵营意识形态鸿沟的手段,美国则将其用于打压苏联集团。虽然双方的目的都是安全,但欧洲国家强调合作,美国却倾向于对抗。③Michael R. Lucas, “Creative Ten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ederal Republic in the CSCE,” in Detlef Junker, 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 1945-1990: A Handbook, Volume 2: 1968-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3.
由于苏联对欧安会的需求更为强烈,因此选择接受美国提出的这些条件。1969年10 月,在华约组织外长会议上,东方阵营正式承认了美国和加拿大具有同等的参会权。1970 年8 月和12 月,苏联和波兰分别与联邦德国签署了《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苏、美、英、法四国也在1971 年8 月召开了柏林会议,并于9 月签署了《关于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1972 年美苏首脑会议期间,双方就裁军问题达成一致。人权问题也被纳入欧安会的最终议程中。
随着欧安会日期将近,美国确定了参与欧安会的预期目标。1971 年年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四项目标:一是避免会议议题导致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分裂;二是避免缓和气氛给北约带来挑战;三是将美国的欧洲国家身份和东西方对话参与者的角色进行制度化;四是向东欧国家提供帮助。①“A Conference on European Security,” in FRUS, 1969-1976, Volume XXXIX, European Security,Document 76, Paper Prepar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39/d76.
经过长期的协调和争论,欧安会最终顺利召开,但东西方对这次会议的评价却截然相反。西方世界普遍将欧安会视为对国家利益的出卖,而苏联却将其称为外交的胜利,②Richard Davy, “Helsinki Myths: Setting the Record Straight on the Final Act of the CSCE,1975,” Cold War History, Vol. 9, No. 1, 2009, pp. 1-2.苏联宣传部门将其誉为“欧洲千年史的转折点”,是欧洲缓和与安全的里程碑。③丛鹏:《浅析“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外交学院学报》1987 年第2 期,第40 页。由此也可以看出苏联对欧安会赋予的意义和期望。
这一时期,美苏双方在经历了多次危机后主动走向缓和,两大阵营对彼此的威胁认知程度随之下降,西欧人民对于结束冷战的呼声也愈发强烈。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西欧国家对苏联提出的欧安会倡议展示出了高度的热情,欧洲许多中立国家也持相似的立场,由此提升了欧安会倡议的合法性。与此同时,西欧国家为避免自身利益受到美苏双边合作的影响而加强了自主倾向,与美国在经济和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也出现了争端,这两个因素为西欧国家接受苏联提出的合作性安全倡议提供了额外的动力。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西方阵营中积极支持欧安会的国家之一,联邦德国对欧安会的最大兴趣在于德国问题。勃兰特曾明确表示,“如果德国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没有首先得到解决,联邦德国参加欧洲安全会议将毫无意义”。④Petri Hakkarainen, A State of Peace in Europe: West Germany and the CSCE, 1966-1975,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1, p. 1.而联邦德国支持苏联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方均将德国问题与欧洲集体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尽管在具体方案上存在不同看法,但是基本理念是一致的。因此,勃兰特才明确表示愿意支持勃列日涅夫加快欧安会谈判进程,以推动德国问题的解决。⑤Christian Hac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erman Question,” in Detlef Junker, 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 1945-1990: A Handbook, Volume 2: 1968-199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1.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理念型楔子战略的第二个机制。
从分化效果来看,欧安会倡议的提出确实引起了美国与其西欧盟友在裁军问题、缓和政策等方面的矛盾,美国也表现出了对于被分化的担忧。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欧安会对美国联盟的分化效果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意识到了苏联的分化意图,并主动加强了与西欧国家的绑定。然而,这并不影响苏联通过欧安会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的意图。
结 论
分化对手联盟是国家提升相对实力的一种重要手段。现有研究主要发展了奖励型楔子战略和强制型楔子战略两种物质分化手段,而忽视了以欧安会为典型的理念型楔子战略这种新的分化手段。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前文提及的两条机制外,安全制度作为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的主要平台可能还存在其他作用机制。例如,有学者在分析冷战时期美苏等级间竞争时发现,削弱对手合法性等“羞辱”(shaming)手段能够降低对手等级体系中附属国对主导国的忠诚度。①Jeff D. Colgan and Nicholas L. Miller, “Rival Hierarchies and the Origins of Nuclear Technology Shar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3, No. 2, 2019, pp. 310-321.而安全制度是国际行为合法性的重要授权来源,国家可以借助安全制度的平台对竞争对手实施去合法化,从而降低其盟友的忠诚度,最终实现分化对手联盟的目标。
理念型楔子战略在当下的国际竞争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从理论上看,物质型楔子战略需要直接作用于目标国和对手联盟,因此风险和成本都更高;相比之下,理念型楔子战略把改变目标国的安全理念作为目标,将提供联盟之外的替代性安全方案作为手段,不需要直接作用于对手联盟,因此风险和成本都相对更低。从现实来看,国际制度是当前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平台,会对国际秩序转型产生直接影响。如何利用国际制度推动国际环境朝着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是大国国际制度战略的核心考虑。当前有关国际制度竞争的研究集中于如何通过提升国际话语权来获取优势,但实际上,作为一种特殊国际制度的安全制度可以服务于通过削弱对手实力而获取优势的目标。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基于合作性安全理念的方案,目前已经得到了全球八十多个国家和组织的认可和支持,其中不乏与美国存在紧密安全合作关系的国家。在美国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全球安全倡议”能够作为中国对美国盟友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的平台,但分化效果取决于中国在双边互动的进程中能否缓和后者对其威胁认知,以及倡议的落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