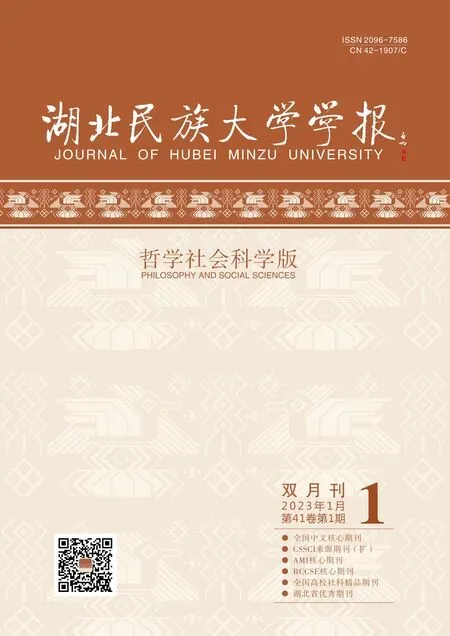自我的表征与社会的隐喻:“自我民族志”析论及反思
刘海涛
一、自我民族志:“中国版”实验民族志的一种新尝试
从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学科视角来看,“田野”既是一个与“此地”相分离的异域地理文化空间,也是人类学学者生产关于“他者”的专业知识的工作场域。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此地”与“彼地”越来越密不可分,“我者”与“他者”日益相互杂糅在一起。在当下全球一体化、网络一体化的社会条件下,如何界定“田野”以及从事“田野工作”已经成为一个需要不断反思的学术问题。“在这个时空日益被媒体和交通浓缩的世界上,所谓的‘田野’更像是一种怀旧,一种对于文化杂糅的遮掩”(1)潘蛟:《田野调查:修辞与问题》,《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第51-53页。;“当下,由于流动成为社会生活常态,田野工作也渐渐向‘多点’(multiple sites)发展”(2)范可:《在野的全球化——流动、信任与认同》,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64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人类学理论的不断引入,尤其是受到西方反思人类学“解构”思想和后现代实验民族志实践的影响,中国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面临着由传统叙事范式向现代叙事范式转换的学术转型。如何进一步将西方理论方法与本土学术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对日益受到现代性影响、不断流变的“中国田野”做出新的描述与分析,构建中国特色人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学者新的探索方向。
2011年以来,在《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再论“主体民族志”:民族志范式的转换及其自明性基础的探求》《三论“主体民族志”:走出“表述的危机”》《“三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微型实验——一个白族人宗教信仰的“裸呈”及其解读和反思》《事·叙事·元叙事:“主体民族志”叙事的本体论考察》等系列论文中(3)朱炳祥:《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第12-24+108页;朱炳祥:《再论“主体民族志”:民族志范式的转换及其自明性基础的探求》,《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第60-72+124-125页;朱炳祥:《三论“主体民族志”:走出“表述的危机”》,《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第39-50+124页;朱炳祥、刘海涛:《“三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微型实验——一个白族人宗教信仰的“裸呈”及其解读和反思》,《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第58-71+125页;朱炳祥:《事·叙事·元叙事:“主体民族志”叙事的本体论考察》,《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第40-53+124页。,以及《他者的表述》等专著中(4)朱炳祥:《他者的表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了“主体民族志”概念,给出了“主体民族志”实践路径,为超越后现代实验民族志开辟了新的方向,推进了实验民族志在中国的发展(5)刘海涛:《主体民族志与当代民族志的走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2-6页;刘海涛:《民族志理论与范式专题学术研讨会综述》,《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第110-116页。。
2018年以来,在“主体民族志”思想的整体观照之下,朱炳祥教授又出版了两部新的具有前后接续关系的“中国版”实验民族志专著——《自我的解释》《知识人》。
《自我的解释》,如朱老师所言,“践行的是主体民族志‘三重主体叙事’理念”(6)朱炳祥:《自我的解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5页。。因此,《自我的解释》首先是一部“主体民族志”,为进一步推进“主体民族志”的深入探索而不断注入新的理论元素和田野素材。此外,它还是一部解释自我的民族志,是民族志自我书写的范例。它以日记体的形式“裸呈”(直接呈现)了朱老师本人的69则日记,其间穿插着朱老师个人的一些理论评注,其写作意图和主旨“并非在于个人生活史的叙事,更不是自传,而是希望通过作为他者的‘自我’来叙述并论述个体的‘生性’‘个性’‘文化性’之间的关系,进而回应既有的相关理论”(7)朱炳祥:《自我的解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
《知识人》缘起于对研究目的的怀疑、对研究客观性的怀疑、对叙事原罪的认知等三种研究中的困惑,其直接的问题意识则来自“我(朱炳祥)自1987年以来30多年的高校教师生活中对于‘知识人’的‘群体自我’的生长过程、存在状态、学术追求等问题的思考”(8)朱炳祥:《知识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页。。在叙事风格上,《知识人》延续了《自我的解释》的“日记体”叙事风格,“裸呈”了一位父亲对孩子成长的记录,一位初中生、一位高中生、一位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日记,一位女大学生的情感日记,一位博士生专业化训练自述,其间同样穿插着朱老师个人的一些理论评注,分析展示了知识人之所以成为知识人的历时性过程,在此基础上构建出知识人的“生长的逻辑”(9)朱炳祥:《知识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前言”,第2页。。
在朱老师看来,《知识人》可以看作是继《自我的解释》的续篇:在《自我的解释》中,叙述的是个体的“自我”;在《知识人》中,叙述的是群体的“自我”。(10)朱炳祥:《知识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前言”,第1页。
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在《序言:〈自我的解释〉读后意见》中,曾对《自我的解释》有一个评析,认为《自我的解释》开拓了人类学写作的多重意义,其中的突出成就表现为聚焦个体、自我镜像和民族志哲学三个层面(11)徐新建:《序言:〈自我的解释〉读后意见》,朱炳祥:《自我的解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5-6页。;在《自我民族志:整体人类学的路径反思》一文中,则从整体人类学路径反思的角度对人类学的多维表述与个体转向、自我民族志何以可能、自我民族志表述范式的建构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12)徐新建:《自我民族志:整体人类学的路径反思》,《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第68-77+125页。笔者是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曾与徐老师就相关问题有过直接的交流和互动。在此对徐新建老师深表感谢!,指出“《自我的解释》可被视为一类堪称自我民族志、具有开创意义的实验作品,代表着民族志写作的一种创新发展”(13)徐新建:《自我民族志:整体人类学的路径反思》,《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第68-77+125页。,为深入解读《自我的解释》提供了新的理论反思途径。
若将《自我的解释》和《知识人》放到一起来看,一方面,这两部民族志都蕴含着一定的“主体民族志”思想,是在“主体民族志”思想的整体观照之下完成的;另一方面,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民族志逐渐显露出以“自我”为核心研究取向的另外一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型实验民族志——“自我民族志”——之底色与亮色。它们直接指向和叩问“个体自我”和“群体自我”双重维度的“自我”,初步彰显“自我民族志”所蕴含的独特理论价值:通过聚焦“自我”这一研究主题,民族志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我者与他者的视界融合、个人与社会的视界融合、社会事实表征等,能够得到更为鲜明的聚焦式集中反映和新的阐释,对于“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之后民族志如何前行”这个问题场域有着新的扩展意义。本文将结合国内学者的一些相关评论,尝试对此进行深入揭示,以进一步推动民族志范式和理论的更新、发展与反思。(14)作为朱炳祥教授的晚辈,我与朱老师从相识到密切交往,缘起于朱老师将有关“主体民族志“的稿件投稿给《民族研究》。朱老师把主体民族志首次系统完整地展示,他选择的是《民族研究》这个平台。作为《民族研究》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板块的初审编辑,我有幸成为“主体民族志“的第一位读者和首位评议者。之后,我与朱炳祥教授的交往日甚一日,成为主体民族志实践中的一员,成为“实验民族志之后民族志如何前行”问题讨论中的一员。上述林林总总,既归因于《民族研究》刊物的品质,也归功于朱炳祥教授在民族志领域的贡献。本文将再次以一个近水楼台的受益者的身份讲一下对朱老师新作《自我的解释》《知识人》的粗浅认识。事实上,自朱老师发表主体民族志相关论文和论著以来,包括《自我的解释》《知识人》这两本新作在内,留下了很多重要的有学术研讨价值的问题线索,有必要也有可能循此来进一步展开研究。
二、自我民族志:我者与他者的视界融合
自20世纪初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民族志诞生以来,传统人类学一般将异文化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由此型构了我者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我者与他者的视界融合问题亦应运而生,我者如何认识他者的讨论相伴而来。二战后受到后现代思潮影响而出现的后现代实验民族志认为,民族志描述的他者文化,并非他者文化本身,而是我者建构出来的有关他者的文化表征(cultural representation)。写出来的文化(writing culture)并非原汁原味的文化本身。写出来的文化与原汁原味的文化本身是一种换喻关系,而非隐喻关系。由此,如何实现我者与他者的视界融合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很多人类学学者的关注主题,他们为此贡献了不同角度的解题思路。
实现我者与他者的视界融合,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如何认识及如何处理“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主观性”。北京大学蔡华教授指出,当代科学民族志通过自身严密有序的不因人而异的公共客观的“铁的”方法论体系,可以将研究者的主观性排除在外,生产出客观科学的民族志知识。(15)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48-63+124-125页。意大利米兰大学马力罗(Roberto Malighetti)教授认为,彰显他者的主体性,向他性(otherness)开放,并不意味着客观中立性,也很难基于方法的客观性来消除研究者自我,一个人的偏见是其视域的构成要素,而人类学家正是从他的视域出发阐释事实,因为事实本身都是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如此,自然科学事实概莫能外。(16)马力罗著、吴晓黎编译:《时间与民族志:权威、授权与作者》,《民族研究》2014年第5期,第49-61+124页。清华大学张小军教授强调,研究者与当地人之间的经验互动,是理解当地人的关键,研究者的主体性不应夸大,但也不应当祛除,它反而是理解当地人的重要条件,因为民族志揭示的是一种与明确的科学事实不同的、充满歧义的、基于研究者与当地人之间互经验(inter-experience)之上的文化事实。(17)张小军、木合塔尔·阿皮孜:《走向“文化志”的人类学:传统“民族志”概念反思》,《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第49-57+124页。美国哈佛大学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教授认为,人类通过感官获取知识的方式决定知识本身具有不完美属性。知识是打破原有分类的事实,它会出现在人们意识到自己观点存在缺陷的时候。人类学家必须打破原有的认识和分类体系,这也是在异文化中进行田野调查的重要价值所在。人类学家应当认识到知识的有限性,有限性也在变化,无法也不必追求确定性。承认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事实。与其说文化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科学或社会科学,还不如说社会科学在普遍和具体双重层面上展现了一种制度性文化,这种制度性文化完美展现了文化的不确定状态。“文化亲密性”(cultural intimacy)指的是在每一种文化环境和制度下的一种对比,民族志写作者就是要从“局内人”和“局外人”两方面来理解这种“文化亲密性”的环境,本地语言通常是获得“文化亲密性”的钥匙。(18)丁岩妍:《“社会科学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成为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第120-122页。
朱炳祥教授提出的“主体民族志”思想在认识、处理“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主观性”以及实现我者与他者视界融合问题上给出了新的解题思路和新的贡献:“主体民族志”承认田野调查与研究中三个主体的存在,他们都是主体,通过“互镜”又都互为主客关系。三个主体分别且同时在场的叙事方式,要求“主体民族志”给予田野对象即“第一主体”“充分”的话语权,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第一主体”的主体性;同时,重申民族志者即“第二主体”的理论建构责任,认可由之而来的“第二主体”的主观性,并利用各种方式(包括“第二主体”明确交代研究背景、着重强调“第二主体”的自律性、展示评审者即“第三主体”对民族志知识生产的学术规范约束、展示“第一主体”对由“第二主体”记录和转写的“第一主体”自我讲述文本的修改意见和有关建议等)将这种主观性最大限度地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19)朱炳祥、刘海涛:《“三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微型实验——一个白族人宗教信仰的“裸呈”及其解读和反思》,《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第58-71+125页。“主体民族志”通过三个主体之间的“互镜”,借助“裸呈”这种叙事手段,以三个主体、两个“最大限度”的方式规避“研究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研究者的主观性”,由此实现我者与他者之间的视界融合。
《自我的解释》首先是一部“主体民族志”经验作品,具有如上“主体民族志”在实现我者与他者视界融合问题上的突出特色;同时,作为“自我民族志”的一种初步实验作品,它在实现我者与他者的视界融合中亦提供了新的理论建树及实践贡献。
朱老师已经出版的作为“对蹠人”系列民族志之一的《他者的表述》,应该是《自我的解释》的姊妹篇。若将《他者的表述》与《自我的解释》这两部民族志作品并置在一起,能够更为清楚地彰显我者与他者视界融合问题提出的逻辑依据和前提。正如朱老师在《自我的解释》这部“自我民族志”作品的前言之中所强调的:“‘人’的研究包括‘他者’与‘自我’,认识‘他者’与理解‘自我’,二者互为条件亦互为结果。对于‘他者’的研究只有在‘自我’研究中才能确定其位置并获得意义,对于‘自我’研究也同样只能在‘他者’的研究中才能确定其位置并获得意义。”(20)朱炳祥:《自我的解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页。
“自我民族志”要书写“自我”,再现“自我”,描述作为“他者”的“自我”,那“我者”(作为作者本人的“自我”)与“他者”(再现的“自我”)是同属一个视界,还是分属两种不同的视界?这其实是人能不能认识自己或者说人能不能认识不断变化发展的自己的问题,也是《自我的解释》所蕴含的深刻的人生和人性叩问。在《自我的解释》所“裸呈”的朱老师自己所写的69则日记中,朱老师通过展示自己社会角色的演变——知青、电灌站打水员、实习记者、军队中的基层连队战士、电台台长、作战参谋、高层领导秘书、高校行政人员、教师等,以及通过展示朱老师所观察到的诸多其他社会角色——汽车司机、离休干部、高校行政科长、一名想出国的大学骨干老师等,由此呈现多种叙事主体,呈现因多种叙事主体互为主客关系所形成的“互镜式”叙事,为“我者”(作为作者本人的“自我”)与“他者”(再现的“自我”)之间的视界融合问题提供了一种事实性呈现和解答。“作为人类学的‘自我民族志’作者,朱炳祥将多个不同的‘我’和‘她(他)’们作了跨年代和跨人物引申关联,把个人、文化和历史巧妙地连为一体。他向读者呈现的‘镜像’由此得到了与‘自我’合一的内在联系。”(21)徐新建:《自我民族志:整体人类学路径反思》,《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第68-77+125页。这种事实性的呈现和解答,远比哲学抽象讨论更富建设意义。而真正的话语解释空间则是留给了共鸣的读者(“主体民族志”中的第三主体),留由读者根据各自的哲学观对此给出开放性的评判。
《自我的解释》《知识人》这两部民族志也可互为姊妹篇。如前所述,在《自我的解释》中,叙述的是个体的“自我”;在《知识人》中,叙述的是群体的“自我”。小晨、小晨的父亲、中学生李文保、女大学生张春醒、女研究生山月朵,作为群体的“自我”被“裸呈”出来。与《自我的解释》一样,读者从《知识人》中获取的同样是群体生活中的个人生活、社会变迁中的个人生活,是不同的社会角色所型构的多种叙事主体以及由此型构的包括读者在内的多种叙事主体“互镜式”关系。《知识人》中的“互镜式”呈现,为“我者”(作为作者本人的“群体自我”)与“他者”(再现的“群体自我”)之间的视界融合提供了另一种事实性呈现和解答。
三、自我民族志:个人与社会的视界融合
根据费孝通先生的有关论述,徐新建老师曾对自我、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给出了一个清晰的总结:个体由生物人和社会人两个层面组成,自我是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体”,其特征主要有如下方面:其一,对于社会而言,“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其二,社会可以限制个人却泯灭不了自我;其三,自我不只是社会细胞,更是具有独立思想和感情的行为主体,社会实体的演进离不开个人的主观作用,也就是离不开具有能动性的自我主体;其四,自我难以摆脱具有超生物巨大能量之社会实体的掌控甚至同化,同时也会在本性力量驱使下抵制社会、反抗社会。(22)徐新建:《自我民族志:整体人类学路径反思》,《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第68-77+125页。无论是《自我的解释》还是《知识人》,虽然都未专门从理论上对个人与社会的视界融合问题进行详尽论述,但这两部民族志作品所提供的实践路径为自我民族志何以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视界融合提供了重要探索方向。
《自我的解释》这部民族志取材于朱老师本人所写的69则日记,但它并不是单纯的个人生活史呈现,而是一个以个人生活史片段为线索,通过截取并展示个人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在作者看来有意义、值得书写的特殊的社会事件,绘写出一种宏大的、流动的、活态的社会生活变迁场景,将中国一定时期的社会变迁淋漓尽致地描绘展示出来。在此意义上讲,作者所截取的与其说是个人生活片段,不如说是社会生活片段。个人的所思、所想、所为镶嵌在社会问题之中,个人被置放在宏大社会变迁之中,个人被置放在群体生活之中,“自我”由此得以充分彰显。“炳祥老师为了替无疑辨识自我的一代人找到了一个锚定自我的依据,引入了‘生性’的概念,这是一种为自己、也是为一代人自我安慰、自我拯救的学术努力。”(23)高丙中:《序言:“生性”的再发现》,朱炳祥:《自我的解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因此,“自我民族志”中的“自我”本身就是个人与社会视界融合的产物。
《自我的解释》这部民族志首先在于对自我的书写和描述,因此它首先关注的是个体内在的心态研究(24)徐新建:《自我民族志:整体人类学路径反思》,《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第68-77+125页。;但是,其目的诉求并非仅仅在于描绘出一种“自我”形象,而是基于“自我”形象的建构展示一种超越“自我”的集体表象,描绘一幅活态的如清明上河图那样的宏大社会生活广角。借助这一社会广角,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社会是如何一点点地悄然转型为今日中国社会的,跃然纸上。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社会与当今中国社会的差异,应该是打动包括民族学人类学专业读者在内的广大受众(即主体民族志中的第三主体)驻足欣赏、引起共鸣的地方。这部民族志所提供的鲜活材料,也会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中不亚于一手档案材料的原始基础材料,其材料价值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加弥足珍贵,会发挥更大和更为长久的社会影响力。因此,“自我民族志”中的“自我”本身就有超越自我的深刻社会意涵,是审视个人与社会视界融合的极佳维度。
从个人与社会视界融合的角度来讲,《自我的解释》所表征的“自我”与朱老师本人之间首先应该是一种隐喻关系,但同时也是一种换喻关系。
《知识人》的叙事策略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视界融合上,同样是成功的。在《知识人·天工开智》一章中,朱老师以20世纪80年代从幼儿园老师和中小学老师那里收集到的日记为材料,以一种儿童的视角来展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来展示那个时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关系。通过阅读这些生动鲜活的日记材料,不同时代的读者会有不同的反应。1977年底出生的小晨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不管他现在从事何种工作,不管他现在有着怎样的生活,当他作为“主体民族志的第三主体”看到这些日记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个人认同?对于在网络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读者而言,对小晨的儿童生活会有怎样的群体认同?这些共鸣的产生,标志着个人与社会的视界正在逐步融合。
“作为知识生产的学术论文的写作训练,应该是一种独创性的自主训练,虽然这种独创性有着各种因素的共同扶持,存在着知识生产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研究生的自我主体性是贯穿全部过程和各个要素的主导要素。”(25)朱炳祥:《知识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41页。这原本是博士生山月朵学位论文写作中得出最重要的个人学习经验,是山月朵个人自我认知飞升的重要条件,但同样也是当代研究生群体可以共同分享的论文写作箴言。由此,《知识人·蝉变》一章与其说是女研究生山月朵个人对其研究生生活的一种自我认知,倒不如说这是研究生群体的一种自我认知,“山月朵”变成了“山月朵们”。
小晨日记对其初中生活的描述,李文保日记对其高中和大学生活的描述,女大学生张春醒日记对其大学生活的描述,女研究生山月朵对其研究生生活的描述,是以自我认知,即发现和认识自己为线索展开的,但读者却能够看到群体的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生活。
总之,《知识人》通过独特的“自我民族志”叙事,将“片段”的“个体自我认知”整合为“整体”的“群体自我认知”,由此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视界融合。
四、自我民族志:社会事实表征
自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提出“社会事实”概念以来,学界对作为“物”的社会事实的捕捉就一直在进行之中。(26)王铭铭:《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第25-38+123-124页。从后现代的视野来看,社会事实与被表征出来的社会事实是两回事,是一种“换喻”关系。事实上,社会事实与被表征出来的社会事实的确不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说,“表征”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对“事实”存在的一种“反讽”),但是,社会事实与被表征出来的社会事实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应该是一种“隐喻”关系。这种“隐喻”关系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重要之一则为社会事实与社会生活传统之间的关系,即被表征和建构出来的社会事实应该是一种由碎片化的社会事实整合起来的社会生活传统,对作为“物”的“社会事实”的捕捉应该是对这种社会生活传统的展示。具有概述和细节描述功能的民族志叙事不啻为捕捉“社会事实”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整合碎片化的社会事实、揭示特定时代特定群体特定地域的社会生活传统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即,基于民族志在地研究,通过细节描述和一定程度的概述,可以相对容易地对碎片化的社会事实进行整合,展示某时代某群体某地域独特的社会生活传统。这也是民族志叙事所特有的重要功能之一。(27)这只是个人结合田野经验与理论阅读的一种并不成熟的拙见,可供学界批评。徐新建老师在《自我民族志:整体人类学路径反思》则认为,无论《萨摩亚人的成年》《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还是《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考察报告》,其中呈现的都只有被叫作萨摩亚人、航海者、赫哲族和苗族的抽象整体和模糊群像,这种样式的描写把人类学引向只关注抽象的“社会”和“文化”。因此,需要从仅关注中观群体的民族志陷阱中走出来,回归联通个人与人类两端的人类学整体。参见徐新建:《自我民族志:整体人类学路径反思》,《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第68-77+125页。
“自我”,包括“个体自我”和“群体自我”在内,是贯穿《自我的解释》《知识人》这两部主体民族志的主线索和核心关键词。它们围绕“自我”展开,无论是问题、方法、材料、观点,都建基于“自我”之上。《自我的解释》《知识人》通过对事实的描述(以各种叙事主体的日记的形式来“裸呈”)与对事实的解释(穿插朱老师个人的一些理论评注)的结合,基于“个体自我”和“群体自我”的特殊呈现,将碎片化的社会事实整合为一种社会生活传统,由此达到揭示社会生活传统的目的,实现对作为“物”的社会事实的捕捉。
《自我的解释》对“自我”的描述,不仅仅是个体自我“生性”的再现(28)高丙中:《序言:“生性”的再发现》,朱炳祥:《自我的解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4页。,也是一种社会生活传统的再现。通过阅读《自我的解释》《知识人》,读者能够知道和了解中国的人类学家是这样成长的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是这样悄然进行的,即知道和了解与西方世界所不同的另外一种社会生活传统。这种社会生活传统,源自“个体自我”和“群体自我”;这种社会生活传统的再现,也是通过作者(朱老师)的笔写出来的,究竟能不能得到认可,取决于读者(尤其是那些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读者)的共鸣与评判,其启示意义会随着时间的延续和时代的发展而逐步显现。这应该是《自我的解释》《知识人》这两部民族志作品作为“自我民族志”所体现出来的重要特色之一,也是“自我民族志”所独具的特殊贡献之一。《自我的解释》《知识人》为社会事实表征提供了一种特殊呈现方式,其贡献亦蕴含在这种特殊呈现方式之中。
“个体自我”和“群体自我”的特殊呈现,按照朱老师的思路和见解,主要通过“自我”(“个体自我”和“群体自我”)的表征来实现对社会的隐喻。
在朱老师的笔下,“自我”存在三种状态:我“在场”,是事件的“主角”;我“在”,是旁观者和目击证人,是事件的“配角”;我“隐形在场”,即通过叙事策略和修辞手法,如传统民族志所采用的叙事策略和修辞手法一样,将故事的讲述者看到和听到的“转换”为我们(即读者)看到和听到的,将“我”——故事的讲述者——隐形。我“隐形在场”,即在叙事上看不到“我”在场,但其依然是一种“事实在场”,而非“小说虚构”。在“自我”的这三种存在状态中,“自我”有时是事件的主角,有时是参与者,有时又仅仅是旁观者和记录员。朱老师将这三种类型的“自我”集中在民族志中展示出来,其理论价值在于,完整系统地揭示“自我”的真实存在状态。各种主体参与民族志是以这种实实在在的“自我”真实存在方式来完成的,在此意义上讲,各种主体参与民族志,事实上参与的是社会生活,多种主体以及多重身份得以在一种独特的社会生活传统中展示出来。我们既是社会的创造者,也是过客;我们既存在于时代,也逃匿于时代。自我民族志中的“自我”,既不是社会事实的完全的参与者,也不是社会事实的完全的旁观者,而处于一种特殊的多层面、多色带的“中间状态”。这是“自我”的一种真实生存状态。通过描述、展示和研究“自我民族志”中的“自我”——这种特殊的多层面、多色带的“中间状态”(这种真实的社会存在状态),碎片化的社会事实被整合起来,社会事实被表征出来,某时代某群体某地域独特的社会生活传统被展示出来。由此,作者变成“我”,读者变成“你”,主题变成“我们”。(29)徐新建:《自我民族志:整体人类学路径反思》,《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第68-77+125页。
无论是《自我的解释》中“裸呈”的“个体自我”,还是《知识人》“裸呈”的“群体自我”,都是一种“自我”的心路历程再现(represent)和建构(construct),体现了现实的“自我”与被表征的“自我”视域融合的过程;同时,这种“自我”,是被不同叙事主体以“互镜”的方式表征(represent)和建构(construct)出来的,“自我”被表征和建构的过程,也就是个人与社会视界融合的过程,“自我”被隐喻为社会的过程。由此,《自我的解释》《知识人》这两部自我民族志所传达出来的更进一层的理论意涵在于:从各种叙事主体“互镜”关系的角度讲,表征的社会事实与社会事实之间是一种隐喻的关系;从通过建构超越自我的集体表象的角度讲,表征的社会事实与社会事实之间是一种换喻的关系。
五、小结
《自我的解释》《知识人》通过展示“自我民族志”的特殊实践路径和理论旨趣,揭示“自我民族志”在“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之后民族志如何前行”问题场域中所特有的新的扩展意义,同时也彰显中国学者在此问题场域探索中的特殊地位。
人认识自我,需要从他者来反思自我,也需要从作为他者的自我来反思自我。以自我民族志来推进主体民族志的发展,是朱炳祥教授对“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之后民族志如何前行”问题的新的思考和新的推动。
作为“中国版”实验民族志的一种新型实验,《自我的解释》《知识人》与其他主体民族志作品一样,共同推进了实验民族志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也充满了超越后现代实验民族志的新的探索精神,为中国民族志争取了更大的国际学术话语表达空间。(30)朱炳祥、刘海涛:《“三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微型实验——一个白族人宗教信仰的“裸呈”及其解读和反思》,《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第58-71+125页。正如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指出的,“与其说《自我的解释》为认知中国社会添加了人类学家的个体案例,不如说另辟了人类学写作的自我镜像,并由此促进对民族志的方法论思考”(31)徐新建:《自我民族志:整体人类学路径反思》,《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第68-77+125页。,这种回归个体、回归自我的“自我民族志”是整体人类学路径反思的重要维度之一(32)徐新建:《自我民族志:整体人类学路径反思》,《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第68-77+125页。。
《自我的解释》《知识人》既体现出主体民族志的关怀与拓展,也展示了自我民族志的底色与特色,体现了“中国版”实验民族志的不断延续与新的尝试。这种新的尝试,主要体现在自我民族志的实践探索以及田野叙事上,因此也期待朱老师将来能够为“自我民族志”提供更多理论论证上的新贡献。
在《自我的解释》中,承蒙朱老师热情邀约,笔者不揣浅陋,曾给《自我的解释》写过一个简短的序言。(33)刘海涛:《序言:超越自我——朱炳祥教授〈自我的解释〉的启示》,朱炳祥:《自我的解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1-23页。本文延续了笔者为《自我的解释》所写序言中的问题分析进路来完整解读《自我的解释》《知识人》,揭示这两部民族志作品逐渐显露的“自我民族志”的新的研究取向,意在说明这种新的取向不仅代表着“主体民族志”的不断拓展,而且在发挥超越“主体民族志”视野范围的新的学术影响,并由此进一步促进对“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之后民族志如何前行”这个根本问题的深入理解。
本文从“自我民族志”的若干(并非全部)理论意义出发对《自我的解释》《知识人》所做的粗浅评述和解读,是在阅读欣赏《自我的解释》《知识人》中萌发出来的,是在朱炳祥教授“主体民族志”“自我民族志”学术思想的“照耀”下生产出来的,期待它们能够成为朱老师这两部新作留给学界的重要启示。以上浅见难免以偏概全,难免有误解作者和误导读者之处,敬请朱老师以及《自我的解释》《知识人》等“对蹠人”系列民族志的多种主体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