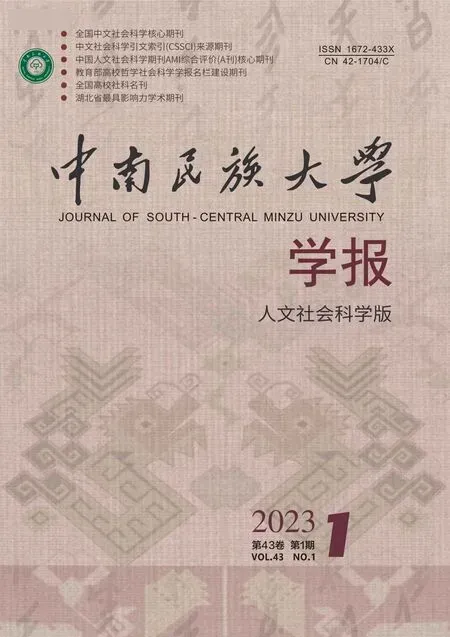《韩非子》序跋的韩学史意义
马世年 马群懿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宋代以来,《韩非子》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为数众多的序跋,这些序跋对于深入认识《韩非子》有着重要的作用,在韩学史研究方面具有特别的意义,是韩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当中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关于此问题,学术界已有关注,譬如,清代陈梦雷、蒋廷锡的《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韩子部”,辑录有关韩非子的史料、目录、书序、评论、艺文、杂录等各种文献资料40则(篇)[1];此后,陈启天的《韩非子参考书辑要》,辑录纪载、序例、考证、评论等55则(篇)[2],陈奇猷的《韩非子新校注》,附录有关韩非子记载、旧刻本序、考证、旧评等65则(篇)[3],而张觉的《韩非子校疏》则附录包括历代序跋在内的相关材料约200则(篇)[4]。这些都是对《韩非子》序跋的文献整理,充分体现出学界对此类材料的重视。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论及《韩非子》序跋的学术价值。早在1930年代,陈千钧在《历代韩学述评》及《历代韩学述评续》中,将序跋作为评论韩学成就的重要材料,来反映历代韩学发展的样相[5]。其后的陈启天、郭沫若、陈奇猷、梁启雄、郑良树、周勋初、谭家健、张觉等学者[6],都不同程度论及《韩非子》序跋的文献价值、思想意义及文学评价等问题。近年来,宋洪兵的《韩学源流》在讨论宋、元以后的韩学发展状况时,对序跋予以特别重视,如其论元代韩学的发展时即围绕何犿《校<韩子>序》来谈[7]。此外,拙文《诸子学史视野中的“新子学”研究——兼论现代韩学史建构的四个维度》与《韩学文献整理研究的构想及意义》等文,在讨论现代韩学史建构的思想史、文献史、文学史、研究史四个维度时,也对《韩非子》序跋有专门论述[8]。
不过,学术界对于《韩非子》序跋的研究还是较为单薄的,特别是对其韩学史意义的专门考察,目前还没有系统的论述。这也是我们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讨论的主要是从南宋到晚清所产生的各类《韩非子》序跋,属于“古代”的范畴。至于民国时期的序跋,与古代序跋已有较大区别,尤其关系到现代韩学建构的问题,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赘述。
一、宋元旧序:韩学低潮下《韩非子》的再发现
在宋代儒学兴盛的大背景下,“严而少恩”的法家思想俨然成为儒学的对立面,自然很难受到时人的青睐。宋儒为了阐述自己的思想立场,往往将批判法家作为彰显儒学的重要手段。元代统治时间短暂,社会矛盾尖锐,文化事业全面受到破坏,有“元代不文”之说,《韩非子》与整个法家学说亦遭压制。因此,整体来看,宋、元时期韩学的发展处于低谷。然而,在整体的低潮阶段,韩学也有其光芒之处。考察南宋乾道本《韩非子序》与元代何犿的《校<韩子>序》,可以看出宋、元时期人们重新发现了《韩非子》的价值。
(一)乾道本《韩非子序》的发轫意义
乾道本《韩非子序》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韩非子》序文。不过,从文本看,它几乎全部是对《史记·韩非列传》的摘录: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其本于黄老。其为人吃口,不能道说,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为不如。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干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病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廉直不容于邪枉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难》五十五篇,十余万言。[9]
前人或将该段文字与刘向的《韩非子书录》联系在一起,认为是刊刻者过录《韩非子书录》而成,也就是“以史实为序”。不过,这种看法受到现代学者的普遍质疑。根据武秀成先生考证,该序在节录本传之外,文字润色还参照了《资治通鉴》[10]。这样看来,该序当是刊刻者据本传删改而成(乾道本此序之后有“乾道改元中元日黄三八郎印”,也说明了这一点)。后来辑录刘向《别录》者如严可均、姚振宗等,又将此序看作是《韩非子》的旧本所传,从而当作了刘向的手笔。
该序较之于本传,主要出入有两处:一是序文将本传中“韩非疾治国不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改为“韩非病治国不务求人任贤”;二是将韩非本传当中《说难》的选段删去。这样,韩非重视运用游说之术、揣摩君主人心的方面略去了。整段的核心在于国家现实急需求人任贤,现有的局面却是“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相较于本传,该序文更加鲜明地突出贤才无所用,而对韩非思想的否定性评价只字不提,比如司马迁所说的“其极惨礉少恩”。这也反映出:宋代除了批判韩非思想的声音外,也有一小部分人对韩非的思想表示接受。
然而,宋代人对韩非思想的接受有时会出现特别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宋代积贫积弱的现实需要富国强兵,需要韩非课名实、尊法治、因时而变的思想主张。尤其北宋后期,内生奸佞,外患不绝,真正到了“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的局面,以韩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有其实际功用。另一方面,宋代以文治天下,儒学地位空前提高,他们极力站在儒学的立场上批判法家,认为法家一无是处,甚至对韩子客死于秦也没有丝毫同情,其游说之学也令人不齿。欧阳修对法家的评价就集中体现出这种矛盾性:“法家者流,以法绳天下,使一本于其术。商君、申、韩之徒,乃推而大之,挟其说以干世主,收取功名。至其尊君抑臣,辨职分,辅礼制,于王治不为无益。然或狃细苛,持刻深,不可不察也。”[11]可见,欧阳修虽知法家的实用,但仍在儒家的立场上,认为法家严而少恩,从而严厉批判。乾道本序对此类状况无疑有着纠弊作用。
此外,因为乾道本对明、清时期《韩非子》的刊刻流传影响深远,故而其序也流传甚广,影响甚大。此后源于乾道本的诸种《韩非子》,大都保存了该序,如清代张敦仁影抄本、吴鼒仿刻本和钱曾述古堂影抄本《韩非子》,便是如此。
要之,乾道本序并未站在儒家的立场对韩非及其思想进行道德批判,而是对其予以正面评价,对于韩子客死秦国也抱有同情。这篇写定于南宋乾道年间的序文也成为宋代韩非思想接受的另一个侧面。它也表明:尽管宋代韩学处于低谷,但《韩非子》的救世价值依旧受到有识之士的认可。
(二)何犿《校<韩子>序》对韩子精神的再发现
何犿的《校<韩子>序》是元代最为重要的《韩非子》书序,也是他向元顺帝进献《韩非子》一书时的上书,存于明万历年间刊刻的《韩子迂评》中。何犿,《元史》无传,由《校<韩子>序》中可知,其人曾为元代奎章阁侍书学士,而其献书在至元三年秋。元代使用“至元”年号的皇帝有两位,一位是元世祖忽必烈,另一位是亡国之君元顺帝。《四库全书·子部·法家类》存目《韩子迂评》:“考元世祖、顺帝俱以至元纪年,而三年七月以纪志干支排比之,皆无庚午日,疑‘子’字之误。奎章阁学士院设于文宗天历二年,止有大学士,寻升为学士院,始有侍书学士,则犿进是书在后至元时矣。观其序中称:‘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废,所少者韩子之臣’,正顺帝事势也。”[12]其说甚是。另据陈奇猷考证,文中“谦”为许谦,元代金华人,字益之,晚号白云山人[3]1221。据《元史·儒林传》,许谦卒于至元三年(1337年),享年六十八,何犿序中既称“与臣谦考雠,略加傍注”,则其献书必在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时无疑。何犿结合韩子思想在该序中献书言志:
臣犿窃谓人主智略不足,而徒以仁厚自守,终归于削弱耳。故孔明手写申、韩书以进后主,孟孝裕亦往往以为言,盖欲其以权略济仁恕耳。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废,所少者韩子之臣。伏惟万几之暇,取其书少留意焉,则聪明益而治功起,天下幸甚。臣犿不胜惓惓,昧死上。[13]
“徒以仁厚自守,终归于削弱”,这已是何犿顾及顺帝颜面的委婉之辞。事实上,元代到顺帝时积弊已久,国运岌岌可危。据《元史·顺帝纪》载,至元二年(1336年)至三年(1337年),地震、暴风、饥荒频发,“是岁,江、浙旱,自春至于八月不雨,民大饥”[14]。朝廷四面救灾,疲于应付,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各地起义不断。更为致命的是,至元三年四月,元顺帝颁布诏令:“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军器。开诏令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郡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人、色目人。禁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此举进一步激化了蒙、汉之间的矛盾。面对如此深重的社会危机,何犿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说“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废”,如再不谋求富国强兵,不求修明法治,天下大势只会更加恶劣。
尽管王朝已经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但是朝堂之上,依旧权臣当道,气焰嚣张。据《元史·伯颜传》记载:“伯颜自诛唐其势之后,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伯颜屡行悖逆之事,出行带领诸卫精兵。相比之下,元顺帝身边的仪仗反而寥若晨星,伯颜目无皇帝如此。此外,伯颜还构陷郯王彻彻笃,未经顺帝同意,他居然矫诏行刑,将其处死。此后,伯颜又故技重施,贬黜宣让王帖木尔不花。
所以,何犿所说的“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废,所少者韩子之臣”,显然是有所指的。他希望元顺帝能用韩子之臣,以法治国,励精图治。在他看来,国家的弊病须用《韩非子》这剂药方可医治。因此,他劝谏顺帝读《韩非子》,并将其用于政治实践,以挽救危亡。何犿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将《韩非子》视为治道之要而重新提起,以期君主励精图治、挽救国祚,其本质就是对《韩非子》救世精神价值的再发现。
陈千钧感叹元代是韩学的“大厄”时期,但从何犿的《校<韩子>序》来看,韩学的思想价值与精神内涵并未因此“中绝”,而是代有传承,不绝如缕。这种对韩子精神的充分肯定也是后来韩学发展中所不可或缺的。
二、文学视域与思想观照:明代《韩非子》序跋的意义
按照陈千钧的看法,明代处于韩学的“复兴时期”,该时期“上焉者则儒法兼用,学者亦儒法兼治;下者亦模仿其文,学其犀利之笔”[5]82。受明代文学领域复古思潮的影响,文人纷纷把先秦古文作为文气革新的标准。《韩非子》作为战国诸子文章的代表,自然进入到明人的视野,从而涌现出许多评选本和节录本。这些本子在校勘方面或无足称道,但作为文学读本,体现了明代人对《韩非子》文学性的认识。随着明代政弊的日益显现,学者们不再仅仅着眼于《韩非子》的文学层面,而更多关注其思想价值。《韩非子》因而广为重视,反复刊刻,《韩非子》序跋也集中产生。其中严时泰《重刊<韩非子>序》、张鼎文《校刻<韩非子>序》、门无子《刻<韩子迂评>序》、陈深《<韩子迂评>序》、茅坤《<韩子迂评>后语》、赵用贤《<韩非子>书序》、孙鑛《<韩非子节抄>序》、王道焜《重刻<韩非子序>》、庄元臣《<韩吕弋腴>自序》、沈景麟《<韩非子>小序》等,在诸多序跋中最具代表性。
(一)文学体认与文章价值
《韩非子》不仅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它也是战国文章的杰出代表。宋儒对韩非进行激烈批判时,忽视了对《韩非子》一书文学价值的肯定。明代则不然,比如,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就对韩非文章之“奇”作正面评价:“余读韩非书,若《孤愤》《五蠹》《八奸》《十过》诸篇,无论文辞瑰伟,其抉摘隐微,朗如悬镜,实天下之奇作也。”[15]明代的《韩非子》序跋也体现出对《韩非子》文学性的特别关注,尤其是在文学复古的思潮下重审《韩非子》的古文价值。更为可贵的是,这些序跋明确了思想和文学的分野,在思想的批判中揭示了《韩非子》的文学价值。
1.重估《韩非子》的文章价值。明代《韩非子》序跋有许多关于《韩非子》文学的评论,这与文学领域的复古思潮密切关联。明中叶以后,台阁体诗文日益走向僵化,文学领域追求改革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文人将目光投向秦汉古文,以“前、后七子”“唐宋派”为中心,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复古风潮。弘治、正德及嘉靖初期,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率先拉起复古的旗帜,提出所谓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要求一扫啴缓之弊,转为雄健之风。《明史·李梦阳传》载:“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李梦阳的这一号召,“有如长夜中出现的火炬,士流群起相从”[16]。这股复古的文艺思潮使得湮没已久的先秦古文重新获得关注,文坛倡导学习先秦古文的风气已开。其后,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虽然提出反对“文必秦汉”的主张,但是为了重造文统,他们追根溯源,仍然崇尚秦汉古文。嘉靖后期,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的“后七子”接过“前七子”复古的大旗,继续师法先秦古文。前后七子以复古为革新的主张,他们在此过程中重新发现了先秦古文的文学价值,把时人的眼光引到对先秦古文的关注上。
茅坤作为“唐宋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韩非子》是先秦散文的“擅场”之作。“擅场”一词,语出茅坤《<韩子迂评>后语》:“先秦之文,韩子则擅场矣。”意为“压倒全场”。《<韩子迂评>后语》是茅坤假托与“客”的讨论。文章开篇,“客”对《韩子迂评》一书的刊刻提出质疑,认为《韩非子》一书不流传于世已经很久了,现在又刊刻这部书,没有什么必要性。茅坤对此予以回应:“顾先秦之文,《韩子》其的彀焉。”其所写内容无所不包,“纤者、巨者、谲者、奇者、谐者、俳者、唏嘘者、愤懑者、号呼而泣者”,细小、庞杂、奇诞、诡谲之事俱在撰述之列,谐趣、轻肆、唏嘘、愤懑的情感包藏其间,这与陈深所言“上下数千年,古今事变,奸臣世主,隐微伏匿,下至委巷穷闾,妇女婴儿,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脏”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陈深此语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难逃韩非犀利冷峻的眼光,而茅坤认为,韩非所写,“皆自其心之所欲为,而笔之于书”,其思想或出自荀卿,但其文实为韩非内心情感的迸发,“未尝有所宗祖其何氏何门也”。因此,茅坤说韩非之文,是先秦散文的标准,实是通过肯定《韩非子》缘心而发,不囿于师承,来反对当时散文创作的拟古风气。
2.思想与文学的分野。明代的序跋尽管依旧存在以儒家立场批判韩子思想的现象,但将《韩非子》的思想性与文学性予以区分,在思想与文学之间有着明确的分野。这其中以严时泰《重刊<韩非子>序》和张鼎文《校刻<韩非子>序》为代表。
严时泰《重刊<韩非子>序》引《论语·卫灵公》说:“君子不以人废言。”他认为,韩非的思想和《韩非子》的文学性应该分开来看,不能因为排斥韩非的思想就否定其文学性。严时泰序文一开始即表明对韩非思想不认同,但“其书未可黜焉”,“苟略其理而论其文,不无可观者”,并非无可取之处。严时泰对《韩非子》文学性的肯定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史记·韩非列传》里讲,韩非、李斯同游于荀卿门下,非尤善著书,斯自以为不如。但南宋文章大家真德秀《文章正宗》中收录了李斯的上秦始皇书,却未收韩非之文,这是不合常理的。之所以如此,“则以体制不同,或全书不容有所简择故而”,只是因为《文章正宗》的体例所限。第二,吕本中、李性学等人都称赞韩非的文章,“其鉴别文字亦不在景元下也,而皆尝称许其书”,可见《韩非子》的文学价值也是值得肯定的。
张鼎文的《校刻<韩非子>序》在评价《韩非子》的文学成就时,体现出了极高的见解:“其文则三代以下一家之言,绝有气力光焰!”认为韩子之文出自三代,载古人事多奇崛,其“气力光焰”正是当下疲弊文风需要借鉴的。“学士选其近正者读之,未必不如更帜易令,登陴一鼓,以助三军之气也。”在他看来,革除一代文风之弊,非韩子之文不可。
此外,门无子《刻<韩子迂评>序》、陈深《<韩子迂评>序》、茅坤《<韩子迂评>后语》、赵用贤《<韩非子>书序》、王世贞《合刻<管子><韩子>序》、陈箴言《<韩非子>序》、沈景麟《<韩非子>小序》和庄元臣《<韩吕弋腴>自序》等其他序跋都充分肯定韩子文章的文学价值。譬如王世贞序所说“其于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者也,能以战国终者也”,也对韩子文章予以充分肯定,因而多为后世论者所引用。
比较而言,严时泰序全篇以重视《韩非子》文学性为中心,代表性更加突出;张鼎文序所论《韩非子》的文学价值,看法更为超拔。这两篇序在时间上也早于明代其他序跋,因而更具有标志意义。
(二)思想观照:批判与认同
明代的《韩非子》序跋,绝大多数都关涉韩非思想的评价。按其思想倾向,可分为批判与认同两个方向。
就批判一类而言,以张鼎文、严时泰序为代表。张鼎文的《校刻<韩非子>序》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道德批判,认为韩非专意刑名,思想主张尽显“刻核(礉)”。他甚至认为韩非、李斯虽言智术,却或“止于狱死”,或“遂至车裂”,皆不得善终,“为法之弊,反中其身,非、斯则同,特后先而!”严氏《重刊<韩非子>序》认为《韩非子》一书“不甚行于世”、流传不广的重要原因是韩非“喜形名法术之学,惨刻少恩”,不讲忠厚仁义。这种对思想的批判甚至影响到对韩非其人的评价:“非乃如彼,是诚吾道中之罪人,百世所不囿者。”甚至比之于“虎豹之猛”“蛟鳄之暴”,其论调纯为儒生立场,见解固无足观,而其情绪之难以自已,亦颇可玩味,流露出鄙儒对法家思想的偏见。
相较于宋代几乎一边倒批判的局面,明代则更为开放一些,认同韩子思想的声音多方涌现。由此也显示出明代对韩非思想由批判走向认同的态度。门无子《刻<韩子迂评>序》与王世贞《合刻<管子><韩子>序》即是其中特别的一类,其对于韩子思想的认同,与对宋儒的批判是联系在一起的。
门无子序云:“夫言期于用,言而无用,言虽善,无当也。众人皆以为然,而吾亦以为然者,六经也;众人皆以为然,而吾独以为不然者,宋儒也;众人皆以为不然,而吾独然者,韩子之书也。”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宋儒,而特别强调自己对韩子之书的认同。这就关系到对《韩非子》思想价值的认识:“韩子之书,言术而不止于术也,言法而不止于法也。纤珠碎锦,百物具在。诚汰其砂砾,而独存其精英,则其于治道,岂浅鲜哉?”认为韩子之书,实是思想之精英,治世之要旨,宋儒对此认识不清,反而批判韩非持论刻薄,因而是不对的:“以韩子为刻而不可用者,宋儒之言也。夫宋儒之言,密如猬毛,刻则刻矣,以试于用,则如棘刺之母猴。”
王世贞《合刻<管子><韩子>序》也对宋儒做了激烈批判:“儒至宋而衰矣……宋儒之所得浅,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辽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宋儒一味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对韩子进行批判,而忽略了其中的富国强兵之术,这也是宋儒不能积极面对现实,缺乏时代责任的体现。由此来看韩子的学说,就别具现实意义:“非子之所为言,虽凿凿,衡名实,推见至隐,而其技殚于富强而已。”富强的指向,的确是一语中的。此外,王世贞对于韩非的命运也给予理解和同情:“秦并天下之形成,亡所事非,而非以并天下说之,欲胜其素所任之臣而自功,则机不合;机不合,非不得不轻。”“机不合”也就是机缘条件未备,这也是认识韩非人生悲剧的一个新路径。
门无子和王世贞都试图通过指摘宋儒之弊,借古讽今,来发掘韩非思想的现实意义,从而为革除社会弊病提供一种新思路,这也是其认同韩非思想的深层动因。他们更多是结合韩非子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政治现实来接受韩非子的。
不同于门无子和王世贞,陈深的《<韩子迂评>序》和周孔教的《重刊<韩非子>序》则从另一条路径表达对韩非思想的认同。陈深认为,理解韩非的思想,首先要结合战国的时代背景,离开历史条件无端指责,是对韩非思想误读的开始:“战国之时,诈欺极矣。纵横之徒遍天下,而以驰骛有土之君,以至君畏其臣,臣狎其君,而篡弑攸起,诸侯是以不救。此皆上下浮謟而怠慢纾缓、不振于法之效也。于是申、韩之徒出,而以名实之说胜之矣。”[17]应运而生的申、韩名实之说破除了此浮淫之说。同时,陈深对秦用韩非之说而亡的观点也予以驳斥,认为是“所遇”君主自身的问题,“使其遇圣主明王,与之折衷,被之以封疆折冲之任,则其治功岂可量哉?……使其遇始皇、二世,直丧亡之雄耳”。这就是“物有受也,人有器也”。事物都有一个接受的程度,人主也一样,不同的君主接受韩子之说的程度和方式也各有不同。一句话,秦之亡,根本在于始皇、二世,是韩子所遇君主不明的缘故。这就涉及到对秦亡原因的探讨了。还需提到的是,陈深特别强调韩非犀利的洞察力,所谓“上下数千年,古今事变,奸臣世主,隐微伏匿,下至委巷穷闾,妇女婴儿,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脏”,显然是对韩非思想的另一种理解。
周孔教则特别强调韩非思想的政治功用与历史实绩,一针见血地指出:“《韩非子》之书,世多以惨刻摈之。然三代而降,操其术而治者十九。”他一反“惨刻少恩”的批判,认为“法令之行,自亲贵始,则疏者贱者日凛凛守法令惟谨。不敢以疏越亲、贱凌贵”。他进一步指出:
今天下愉愉怌怌,其为浮淫之蠹,盖极坏而不可支矣。使太史氏而生今之世,其焦心蒿目,必急欲起韩非,而为之一藻刷者。倘得是说而存之,庶几哉!分职修明,而颓波或可挽乎?是书之刻,又乌可废也?[18]1288
周氏借此序表达对万历种种乱象的担忧,希望以韩子之说挽救朝政之疲弊。因此,他刊刻此书的目的就是“取其言之适于用,且深有概于中矣”,表现出浓郁的经世情怀。
三、清代序跋:“发现”宋本与经世治用的新指向
传统韩学在清代进入总结阶段,在文本整理与版本流传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既有对此前所流传善本的刊刻翻印,又有对文本的考据校订。前者如钱曾述古堂影抄宋乾道本、张敦仁影抄乾道本、吴鼒影刻乾道本、二十二子本、汪氏编印韩晏合编本等,还有上述明代以来所刻各本的翻刻重印;后者如卢文弨《韩非子校正》、黄丕烈校并跋述古堂影抄本、顾广圻《韩非子识误》、王念孙《读书杂志·韩子杂志》、俞樾《诸子平议·韩非子平议》、孙诒让《札迻·韩非子某氏注》、于鬯《续香草校书·韩非子校书》等。及至晚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博采诸家,详加注解,遂为集成之作[8]57。特别要说的是,有清一代,韩学研究表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韩学研究更为集中于文本的校勘;另一方面,也密切关注现实政治与国家治理。而《韩非子》在清代实现全面校勘,与清人对宋本《韩非子》的发现有密切的关系。与此相应,清代序跋直观反映了清人对宋本价值的认识,以及对《韩非子》做全面校勘的状况;而产生于清末的序跋,则流露出浓郁的经世情怀。
(一)宋椠价值的新发现
南宋黄三八郎所刻乾道本《韩非子》元、明两代未得重视,直至清代,宋椠的价值得以发现。总体来说,清代流传的宋本《韩非子》主要有三种:一是清初钱曾述古堂影抄宋本;二是嘉庆年间,张敦仁借得李奕畴私人收藏的乾道本《韩非子》一种,张氏据此影抄一部,延请顾广圻校勘文字,但未能刊刻流布,影响有限;三是宋乾道本的仿刻本一种,此本乃吴鼒据李奕畴所藏乾道本影抄后刊刻而成。
据顾广圻、黄丕烈、吴鼒三人所作序跋,嘉庆年间,李奕畴(字书年)收藏有南宋黄三八郎所刻乾道本《韩非子》,并且借与吴鼒、张敦仁、黄丕烈等人。吴鼒序云:“翰林前辈夏邑李书年先生好藏古书精椠,而宋乾道刻本《韩非子》尤其善者。”他深知宋本之珍,故而嘉庆十六年(1811),“鼒以后进礼谒于途次,求借是书”,未成想借书心愿六年后才得以达成。吴鼒非常重视乾道本《韩非子》,于是他“属好手影钞一本”,并延请校勘名家顾广圻校刊,这便是吴鼒仿刻本《韩非子》。更加可贵的是,顾氏也十分重视乾道本《韩非子》的价值,仿刻本校刊完毕后,将自己数十年校韩的成果《韩非子识误》三卷附刊其后。诚如吴鼒序所说:“宋椠诚至宝,得千里而益显矣。”
清代的另一种《韩非子》即述古堂影宋抄本,黄丕烈所藏此本是顾广圻推荐所购,但顾广圻最先拿到书,于嘉庆七年(1802)七月十二日为之跋,对此本源流、基本面貌和版本优劣作基本的交代。顾广圻摩挲数日,于嘉庆七年(1802)中元日送至士礼居,黄丕烈见此书,欣喜之下,当日也作一跋。黄丕烈跋讲述购得述古堂影宋抄本《韩非子》的前后,与顾广圻跋相呼应。顾跋讲自己劝黄丕烈买书的缘由,而黄跋又从自己的角度来说购得此本的经过,都是对购书一事不同视角的描述。当然,黄丕烈作为该书的主人,他的跋显得更为详尽,除了交代购书的经过之外,也对成人之美的顾广圻多加称颂。顾广圻为清代最具影响力的校勘名家,黄丕烈为清代最著名的藏书家,二人的深厚友谊在此二跋中可略见一斑。
就在黄丕烈得到述古堂影宋抄本《韩非子》后不久,黄丕烈得知尚有宋本,即李奕畴所藏乾道本《韩非子》流传于世。他见到此本后,又于嘉庆七年(1802)八月六日作跋。如跋文所言,黄丕烈得到述古堂影宋抄本《韩非子》后,深觉此本精良无可比,平生所见书中几无优于此本者,遂打算用此本校明人赵用贤所刻《韩非子》。恰好钱塘人何梦华来拜访,见此本后亦以为珍。后黄氏从何梦华寄来的书札中得知,张敦仁(字古余)处有一部宋刻的《韩非子》,遂前去拜谒张敦仁,希望能够借书一观,未果。后又借张敦仁友人夏方米的关系,才如愿以偿。这样,李奕畴所藏乾道本的《韩非子》由张敦仁转借至黄丕烈处,黄氏遂将此书与自己手中的述古堂影宋抄本精心比勘。
由上可见,黄丕烈、顾广圻、张敦仁和吴鼒等人都亲见李奕畴所藏宋本《韩非子》,并且都将其奉若珍宝。诸家所作序跋也都反映出宋本《韩非子》在清代的流传。李藏宋椠出现后,衍生出张敦仁影抄本和吴鼒仿刻本,并均由清代校勘名家顾广圻手校。此外,黄丕烈也将其所藏述古堂影抄宋本和李藏乾道本《韩非子》精心比勘,足见宋椠乾道本《韩非子》的重要性。至此,除张敦仁本因未刊刻,未受重视外,述古堂影宋抄本和吴鼒仿刻本为后面实现《韩非子》的全面校勘奠定了基础。
(二)《韩非子》校勘的新突破
清人对宋本《韩非子》的重视,推进了“校韩”事业的全面进步。这种全面性体现在清人对宋、明以来各种版本的《韩非子》进行校理。顾广圻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所作《<韩非子识误>跋》:
《韩子》各本之误,近又得其二事。《外储说左下》两云“孟献伯”,“孟”皆当作“盂”。盂者,晋邑,杜预云“太原盂县”者是也。献伯,晋卿;盂,其食邑,以配謚而称之,犹言随武子之比矣。《说疑》云“楚申胥”,“申胥”当作“葆申”。葆申者,楚文王之臣,极言文王茹黄狗、宛路矰、丹姬事而变更之,下文所谓“疾争强谏以胜其君”者也,见《吕氏春秋》,高诱注曰:“葆,太葆,官。名申。”又载《说苑》:“葆”作“保”,《古今人表》同。“葆”“保”同字也。[19]
跋文对《外储说左下》的“孟献伯”、《说疑》的“楚申胥”两处文字的校勘特作说明。所涉问题很具体,跋文专门提及似乎过于细碎。但如果考虑到此时距《韩非子识误》刊成(1817)已近两年,则不难想见顾氏对《韩非子》一书所做的艰苦工作,“时已刊成,补识于后”,正可见其校书之用心。从《韩非子识误》初作到最后刊刻,中间经过十余载(1)尽管《韩非子识误》的序作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但该书实际上早在嘉庆十年(1805),顾广圻为张敦仁校勘影宋抄本时已经写好,这件事可以在顾广圻为张敦仁影宋抄本的跋文中互见。但顾氏并未就此写定,而是“携诸行箧,随加增定”。直到嘉庆十九年(1814),在扬州得遇吴鼒所收精善宋椠《韩非子》,并拟重刊时,才决定将自己的《韩非子识误》三卷附此书刊行。。十年之间,顾广圻携带《识误》三卷,推求弥年,随加增订,其校书之热忱、态度之审慎与精益求精之精神,足以为后世法。
顾广圻《韩非子识误》是其广校众本的成果,清代序跋多载校勘《韩非子》各本诸事。如同治年间,李慈铭校汪氏编印韩晏合编本《韩非子》,他在跋文中不仅评价该本,而且简评韩非思想:“韩子得失,前人论之已详。然在周末诸子中,已不能自成一家,言与申商异矣。其意主于尊上用威而设术太多,往往自穷其说。至引证古事,每有复出,亦多相抵午,则后人传写之伪,其所称一曰云云者皆出校,读者附记之语。”并指出他的校勘原则是“惟求不爽原椠毫发”。
此外,明刊本的《韩非子》校理也很盛行,如吴广霈校万历六年(1578)刻《韩子迂评》,他在跋中指出该本上源为元何犿所校残本《韩非子》,后据赵用贤刊本将此本补足,成《韩子迂评》补足本。而他“并获其先后印本,因为照补《内储说》脱文及《和璧》《刼杀》篇上下佚文各半,削牍而增修之殊,失原书之式,故一仍其旧云”。
翁同书则对明刊赵用贤《管韩合刻》本《韩非子》进行校勘,校毕有跋文如下:
是编系二十卷足本,虽明刻,实善本也。去年以卢抱经先生校一过。既又得全椒吴山尊学士重刊宋乾道本,乃得夏邑李书年先生所藏本影钞顾涧苹为精校而墨诸板,附以校语。予因取而再校之,甫动手而克瓜洲,携至浦口改。勤之饿辄临实之。迨校毕,孙城亦克矣。千载而下,其尚珍此军中再校本也。[20]
该本在翁同书校勘前一年,卢文弨已经校过一次。翁氏在得到吴鼒重刊的《韩非子》后,重校此书。颇具意味的是,翁同书校书全是在战火中进行的,一波三折,殊为不易,故而感叹:“千载而下,其尚珍此军中再校本也。”
除此之外,黄丕烈、方功惠、戈襄、王渭、韩应陛等在明刊《韩非子》上也有校跋。这些校跋大多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校勘的经过,并且将校理《韩非子》的重要成果简洁道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集体反映出清代前中期《韩非子》校勘的丰赡成果。
(三)经世治用的新指向
清末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刊行,其兄王先谦遂作《<韩非子集解>序》。其时正当甲午新败,在国家危难的特殊时间整理、注释这部两千年前的法家经典,《韩非子集解》便有了特别的意义。王先谦序对此有着充分的体认。
王先谦指出,彼时韩国处于存亡之秋,一方面,王室的责任,爱国的心情让韩非对操持国柄、无所作为的浮淫之徒痛心疾首;另一方面,韩非面对屡屡以空言游说韩王,沽名钓誉的奸猾之臣束手无策。于是,他怀着悲愤的心情著书明志。故而韩非之作,缘现实而发。王先谦说:“其情迫,其言核,不与战国文学诸子等。迄今览其遗文,推迹当日国势,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无可为治者。”[18]1279后人一味诟病韩非惨礉少恩,不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本身便是对韩非及《韩非子》的误解。在此基础上,王先谦肯定韩非言刑名法术的思想主张。他认为孟子以仁义、王道引导君主,造成的结局是“世主亦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18]1279。事实上,君主夙兴夜寐的不是孟子所讲的仁义,而是富国强兵,一统天下;天下的游士满口仁义,也不过是迎合君主对“仁义”的虚假兴趣,所图不过名利而已。因此,王先谦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反对韩非亡秦的谬说。他认为韩非出使秦国时,秦国的统一大势已然形成,其以法治国的基本方针经商鞅变法后早入人心,韩非并非秦法的推动者。而且,韩非一到秦国,没来得及施展才华就陨落秦狱,何谈秦行韩非之说?相对来讲,王先谦更肯定韩非为韩身赴强秦,最终为韩国宗社而死的精神。王氏为此深感悲切。
王先谦对《韩非子》的肯定,与清末乱象有莫大的关联。他对韩非的理解之同情,也寄予了自己的现实情感,因而表现出浓郁的经世特色,这与明代中后期诸多序跋中体现出来的经世情怀一脉相承,更有其特定时代的历史感喟。
总之,从南宋一直到晚清的《韩非子》序跋,反映了不同时代韩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宋、元序跋重新发现了韩非子的思想意义和精神价值;明代序跋则从思想维度和文学视域两个方面,表现出对《韩非子》的特别关注;而清代序跋则在清人全面校理《韩非子》的基础上,集中体现宋本的“发现”与经世治用的新指向。就韩学发展的外在形态来说,文献、思想、文学、接受四个维度,在《韩非子》序跋中都已基本形成。传统韩学的转型与现代韩学的建构,就是依照这四个维度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