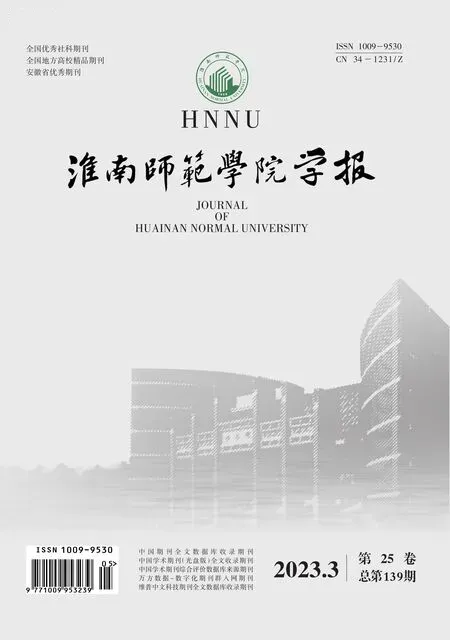李商隐《公子》(外戚封侯自有恩)考论
李昌平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冯浩《玉谿生诗笺注发凡》:“义山官秩未高,事迹不著,史传岂能无讹舛哉。”[1](P2040)学者对李商隐诗歌的编年以及释读时往往会模糊不清。李商隐有两首《公子》,一为五言古体诗,一为七言绝句,文章所论即为后者,诗曰:
外戚封侯自有恩,平明通籍九华门。金唐公主年应小,二十君王未许婚。
这首诗歌在李商隐诗集中并不突出,历代诗论家对其创作时间和创作意图鲜有论述。鉴于此,本研究将结合现世文献、出土文献等相关材料,以李商隐生平事迹为对照,分析各家之评说,并推断此诗的大致创作时间,对诗旨进行推测。
一、《公子》一诗的创作时间考证
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清代诗论家如屈复、姚培谦、冯浩、张采田等皆未言明,现代刘学锴、余恕诚两位先生在《李商隐诗歌集解》中也将其归入“未编年诗”中。叶葱奇先生《李商隐诗集疏注》将该诗定为唐宣宗大中二年(848)作,邓中龙先生在《李商隐诗译注》中亦将之归入大中二年,其依据是唐宣宗大中二年为万寿公主择婿一事。《新唐书》载:“万寿公主,下嫁郑颢。”[2](P3672)唐宣宗选中的驸马是郑颢,郑颢是郑絪之孙,《新唐书·郑絪传》载:“(絪)擢进士、宏辞高第。张延赏帅剑南,奏署掌书记。入为起居郎、翰林学士,累迁中书舍人。”[2](P5074)宪宗即位后,“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门下侍郎。”[2](P5075)官至宰相。郑颢在其影响下也多有长进,“举进士,以起居侍郎尚万寿公主,拜驸马都尉。有器识,宣宗时,恩宠无比,终检校礼部尚书、河南尹。”[2](P5076)然此等国婚,并非郑颢本意,《新唐书·白敏中传》载:“初,帝爱万寿公主,欲下嫁士人。时郑颢擢进士第,有阀阅,敏中以充选。颢与卢氏婚,将授室而罢,先衔之。敏中自以居外,畏颢谗,自诉于帝。”[2](P4306)叶葱奇先生据此将《公子》一诗系于大中二年并进行释读:
起二句乃调侃语,意思说郑颢不必满怀怨恨,成了外戚之后,通籍宫门,旦暮自由出入,肯定还有封侯锡爵的恩赐。三句,“年应小”乃曲笔诡词,所以不用“犹小”。而故用疑问之词。诗里不用禁脔等典故,是避免太明显,惟末句则明指阻拦郑颢就婚卢氏而言[3](P183)。
然细读此诗,却又和郑颢与万寿公主之事多有不合。诗中“金唐公主”,应为“金堂公主”,“唐”与“堂”在古时相通,《册府元龟》亦作“金堂”,屈复言此为“传写之误”,程梦星、姚培谦、冯浩、张采田等人皆认为“金堂公主”无误。也有可能是为尊者讳,将“堂”写作“唐”。查阅两《唐书》,穆宗八女中义丰、淮阳、延安早已出降,清源公主于文宗大和年间逝世,义昌、安康两位公主曾出家为道士,饶阳与金堂同时出降。唐敬宗去世时其三位公主尚年幼,不在婚嫁之列,文宗之女亦然。若“金唐公主”虚指某一位公主,则只有金堂公主和饶阳公主。金堂公主为唐穆宗第四女,《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记载:“金堂公主,始封晋陵。下嫁郭仲恭。薨乾符时”[2](P3670),可知金堂公主嫁给了郭仲恭。据新旧《唐书》记载郭仲恭为郭钊之子,郭暧之孙,郭子仪之曾孙,其余事迹不详。2010 年9 月至2011年2月,陕西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南郊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东兆余村北清理了汉代至唐代共三十座墓葬,其中M2为唐乾符二年(875)郭仲恭及其夫人金堂公主的同穴合葬墓,该墓虽已被严重盗掘,但还是出土了两方比较完整的墓志,分别是《唐故驸马都尉、将作少监、赠殿中监郭公墓志铭并序》(简称《郭仲恭墓志》)与《唐故金堂长公主、赠凉国大长公主墓志铭并序》(简称《金堂公主墓志》),现依据两方墓志对《公子》一诗系于唐宣宗大中二年之说进行辩误,并确定其创作时间。
《郭仲恭墓志》记载:
公讳仲恭,字德卿,其先华之郑人也,自祖及公四代,□将相公卿,世有明德,虽汉之金张氏,无足比焉。曾祖子仪,有大勋于王家,为中书令二十余载,封汾阳王,位称尚父,赠太师。祖暧,拜骑省左常侍,尚升平主,为驸马都尉、赠左仆射。父钊,策司空、兼太常卿、赠太尉。公即太尉第五子。太夫人沈氏,驸马都尉、兵部尚书宇之女[4](P299)。
郭仲恭出身太原郭氏,其曾祖郭子仪于安史之乱中平乱,功勋卓著。郭暧是郭子仪第六子,尚唐代宗爱女升平公主,生四子一女,郭钊乃郭暧次子,郭钊的妹妹是唐宪宗之元妃、唐穆宗之母懿安郭太后,“太尉君女弟入宫,封章帝之后,尊居国母,凡四叶,位称太皇,实公之姑也”[4](P299),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地位尊贵。在这样强大的外戚背景下,郭氏一门与李唐皇室之间多有姻亲联系,郭暧次女嫁给嗣许王李昭,第三子郭鏦娶唐顺宗女汉阳公主,第四子郭銛娶唐顺宗女西河公主,郭钊之子郭仲词娶唐穆宗第六女饶阳公主,郭仲恭娶唐穆宗第四女金堂公主,郭钊作为唐穆宗的亲舅舅,其在穆宗即位过程中也有拥立之功,其本人虽未尚主,然其正妻沈素乃唐代宗第八女长林公主之女,睿真皇后沈氏之侄孙女,吴兴沈氏也是江南大族。自郭暧尚升平公主始,以懿安郭皇后达到鼎盛,郭氏一门以勋功和外戚双重加持下,成为中唐时期声名煊赫的大族,《郭仲恭墓志》云:“姻连帝戚,内外一同。华毂朱轮,寰海无比。”[4](P299)以郭仲恭的身份,更符合“外戚封侯自有恩,平明通籍九华门”之意,因此屈复、冯浩、张采田等皆将“公子”认定为郭仲恭无疑。郑颢虽出身荥阳郑氏,其祖父郑絪也官至宰相,但其家族声望远不如郭氏。
此外,据《郭仲恭墓志》记载:
以会昌四年八月廿一日寝疾,薨于京师长兴里之私第,享年卅一[4](P299)。
会昌是唐武宗李炎年号,会昌四年即公元844年,郭仲恭病逝于此年,终年三十一岁。因此可以推测,郭仲恭生年大约在唐宪宗元和九年(814)。
《金堂公主墓志》记载:
三十年间,岁时出入禁中。入则为天子姑,姉妹尊重优渥;出则俭静,无贵游勋戚之态。呜呼! 可谓贤明德度,有母仪矣。乾符□年二月二十六日薨,享寿六十四[4](P307)。
金堂公主在郭仲恭逝世后寡居三十年,未曾再嫁,由此可以明确金堂公主薨于唐僖宗乾符二年(875)二月二十六日,可推知公主约生于元和七年(812)。又据《金堂公主墓志》记载:“文皇友爱,慎择配尚,以开成二年十二月降归我将作少监、驸马都尉、赠工部尚书郭公讳仲恭。”[4](P307)知两人成婚时间为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成婚时金堂公主约二十六岁,郭仲恭则二十四岁。若将《公子》一诗定于大中二年(848),此时郭仲恭已去世五年,而金堂公主虽尚在世,也已三十七岁,李商隐断然不会以此去影射郑颢之事。另外,据周腊生《晚唐状元驸马郑颢家世生平考》,可知郑颢生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卒于唐懿宗咸通元年(860),享年四十四岁。大中二年(848),郑颢与万寿公主成婚时,郑颢已经三十二岁,与“二十君王未许婚”不符,因此此诗系于大中二年之说有误,且这首诗应该专指郭仲恭与金堂公主之事。邓中龙先生又认为,若此诗专咏郭仲恭与金堂公主,则应在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长庆年间郭仲恭与金堂公主都没到十五岁,此说又不符合“二十君王未许婚”之意。大中二年之说与长庆年间之说皆是未看到郭仲恭与金堂公主的墓志而进行的错误推测。
那么此诗作于何时呢? 《金堂公主墓志》中可找到一些线索,墓志记载:
凉国以长庆元年初封晋陵公主,开成中改封金堂[4](P307)。
长庆元年(821),唐穆宗即位,时年十岁的公主受封晋陵公主,开成中又改封金堂公主,“开成中”应是开成二年(837)婚前改封,唐代公主在出降前要进行册封礼。诗中又有“未许婚”之句,郭仲恭与金堂公主于开成二年十二月成婚,则此诗只能作于开成二年。
开成二年对于李商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他在这一年终于进士及第。开成二年正月,李商隐第五次前往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并成功及第。刘学锴先生《李商隐传论》言:“商隐于是年三月二十七日动身东去济源,省谒住在济源的母亲。”[5](P91)而返回长安的时间“最迟在同年夏秋间”[5](P93),即六、七月间。至十月,“正当选人期集,商隐在长安候选时,令狐楚急召商隐驰赴兴元……大约在十月下旬,商隐赶抵兴元……到十一月八日,(令狐楚)病已危殆,……并命李商隐为之草遗表。”[5](P94)令狐楚于十一月十二日去世。“十二月,商隐伴随令狐兄弟护送令狐楚的灵柩自兴元经大散关、陈仓一路返回长安”[5](P96)。“从兴元回到长安,已是开成二年十二月下旬”[5](P97)。公主与勋贵子弟联姻是轰动长安的大事,若李商隐远在济源或是汉中,中间音书阻隔,信息传达不便,只有在长安期间他才能知晓此事,比如《寿安公主出降》一诗的创作。《旧唐书》载:“(开成二年六月)丁酉,以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为驸马都尉,尚寿安公主。”[6](P570)《新唐书》中记载内容则较为详细:“庭凑死,其次子王元逵袭节度,识礼法,岁时贡献如职。帝悦之,诏尚绛王悟女寿安公主。元逵遣人聘阙下,进千盘食、良马、主妆泽奁具、奴婢,议者嘉其恭。”[2](P5961)此诗应是李商隐在长安期间亲眼看见王元逵迎娶公主而所发的对朝廷讨好藩镇的感慨。由李商隐在开成二年的行迹来看,他有三段时间待在长安,一为正月至三月在京应试之时,二为六月至十月初在京等待候选时,三是十二月下旬至年末,由整首诗可以获知李商隐作此诗之时公主已经由晋陵改封为金堂以及郭仲恭与公主还未完婚两个信息,而郭仲恭与金堂公主于十二月完婚,则改封之事定在十二月之前,且据《通典·公主出降》记载,宗室女在出降之前要举行册公主与公主受册礼,至婚嫁之日还要经过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繁琐步骤,以上为婚前礼,之后还有正婚礼,时间跨度至少在一个月左右,若没有特殊事件发生,是不会耽搁太久的,以玄宗寿光公主为例,据《唐大诏令集·册寿光公主出降文》可知寿光公主于天宝五载(746)八月十三日受册出降,又据《大唐故寿光公主墓志铭并序》记载赐公主汤沐邑,筑馆别居,不久才与驸马郭液成婚,则从受册至成婚差不多在一两个月之间。由此可知若李商隐在年初应试期间作此诗,则金堂公主婚礼时间跨度最少差不多八个月,这不符合实际。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若是按照正常流程,金堂公主的婚礼当在十一月完成,为何会拖延到十二月? 当是因为十一月岐阳庄淑长公主病逝,而岐阳庄淑长公主是唐穆宗胞妹,金堂公主亲姑姑,出于服丧的礼制,才将婚礼推迟也是合理的。由此李商隐作此诗的时间当在开成二年六月至十月间。
二、《公子》一诗的诗旨推测
关于此诗,历代诗论家仅将写作对象指向郭仲恭与金堂公主一诗,而对于其诗旨则莫衷一是,主要分为三种说法,一是如姚培谦云:“见恩宠之渥也”[1](P1714),盛赞郭氏一门的荣耀;二如冯浩所言:“《旧书·传》:郭暧年十余岁,尚升平公主,主年与暧相类;暧子鏦尚德阳公主,鏦与公主年未及冠。则此诗所云似少迟矣,故咏之”[1](P1715),认为此诗是戏咏郭仲恭与金堂公主晚婚;三如屈复评此诗:“意言生来富贵,不用读书,如我辈之十载寒窗,至今穷困也”[1](P1714),认为此诗是对那些不学无术的勋贵子弟靠门荫和姻亲取得高位的讽刺。李商隐有两首《公子》,另外一首为:
一盏新罗酒,凌晨恐易消。归应冲鼓半,去不待笙调。歌好惟愁和,香浓岂惜飘。春场铺艾帐,下马雉媒娇。
《文苑英华》卷一九四“乐府三”中收有此诗,题曰《公子行》。屈复评此诗曰:“凌晨饮酒,归必半夜,忽然而去,不待笙调,性情无常也。歌愁和,不学无才也;香不惜飘,骄奢也。七八禽荒也。通篇写其醉生梦死,一无所知也。”[1](P1717)李商隐此诗旨在讽刺勋贵子弟骄肆荒淫,不学无术,其中也暗含着自己空有才华而沉沦下僚、不得施展抱负的无奈之叹。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说:“唐人《公子行》皆形容纨绔子弟之无知,但务享乐而不知稼穑之艰难,一旦得祖父余荫,出仕朝中,安得不举措乖方,殃民祸国!”[7](P333)唐人《公子行》大多也不出此种寓意,皆是以富贵公子为描述对象,或写其骄奢的生活,或写其与艺伎之恋情,而《公子》(外戚封侯自有恩)一诗则无此种寓意,从前二句“外戚封侯自有恩,平明通籍九华门”中“自有恩”可以看出,李商隐对于郭仲恭这样的外戚并不反感,太原郭氏在中唐时期于国家安全与朝政稳定上都有很大的贡献,自郭子仪之后,郭家子弟也都很上进,郭仲恭的父亲郭钊在穆宗即位过程中多有辅助,文宗大和年间,南诏攻掠蜀地,文宗诏郭钊领西川节度使,平息叛乱。郭钊治蜀有方,“政在简肃,德惟慎重,择贤用谋,蜀人畏安”[4](P262)。仲恭也秉承先辈之遗风,但他选择弃武从文,《郭仲恭墓志》云:“公特秉五行之秀,为马氏之良,代袭簪缨始以为文,孝廉上第,释褐为率府胄曹,转礼寺协律,又迁东宫詹府丞,在官谨慎,雅尚素风……公生而富贵,长于珠玑,而守廉洁之风,无贵骄之色。”[4](P299)“孝廉”是唐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郭仲恭并没有以门荫授官,而是走的科举之路,因此李商隐此诗绝非在讥刺郭仲恭,屈复之说不足取。
李商隐此诗涉及两个人物,“公子”郭仲恭与金堂公主,开成二年时郭仲恭二十四岁,金堂公主二十六岁,李商隐二十五岁,年龄相仿的三个人如何在这一年串联起来,是理解此诗的关键。李商隐未第时对于政治抱有极大的热情,往往就时事或含蓄表达,或直抒胸臆,如《韩碑》《有感》《重有感》《寿安公主出降》等。《公子》涉及皇室姻亲,又时逢李商隐进士及第,他定然想通过此诗表达什么,如张采田所言:“或当时有所指斥,殊难定解。”[1](P1715)
(一)以金堂公主的婚姻经历暗喻朝政之变化
《唐会要》记载:“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8](P1529)开成二年,公主与郭仲恭成婚时已二十六岁,其时郭仲恭二十四岁,在当时属于晚婚,相比于仲恭的祖父郭暧与叔父郭鏦、郭銛尚公主的年龄来说确实很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可以从金堂公主成婚前的人生经历来发现端倪。
初唐时期,朝政稳定,除个别公主外,大多数都能正常出嫁。到玄宗开元十九年(731)于崇仁坊设置礼会院,宗室女出嫁皆在此处成礼。安史之乱后废置,宗室女们也不能按时出降,唐德宗曾经感慨:“故公、郡、县主不时降嫁,殆三十年,至有华发而犹丱者,虽居内馆,而不获觐见十六年矣。”[6](P4046)唐宪宗时集中处理宗室女出降问题,“时十六王宅诸女,久不将嫁,德音初下,人感叹焉”[8](P72-73)。然自宪宗之后,朝政动荡,皇位更替频繁,对于公主的婚事也无暇顾及。金堂公主生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暴崩,太子李恒即位,是为穆宗,改元长庆,金堂公主于长庆元年(821)封晋陵公主,这一年她十岁。史书并未记载此时公主是否有婚约,或是有世家子弟请求尚公主,至开成二年与郭仲恭成婚时也没有记载说金堂公主为改嫁。长庆四年(824)正月二十二日,穆宗因服食丹药暴崩,这一年金堂公主十四岁,已到谈婚论嫁的年纪,她的婚事因此耽搁。同年太子李湛即位,为唐敬宗,仅在位两年,于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初八,为宦官刘克明等所弑,朝政变动,自然无法顾及公主婚事。文宗即位后,将公主许婚郭仲恭,但是在大和五年(831),仲恭之父于西川节度使任上病逝,仲恭依制丁忧三年,而在大和九年(835),发生“甘露之变”,文宗铲除宦官势力的计划失败,事变之后文宗被囚禁,朝政由宦官集团把持,而至开成二年,金堂公主才与郭仲恭履行婚约,因此“二十君王未许婚”并非指皇帝不想履行婚约,实为局势所迫。或许,李商隐意在以金堂公主晚婚的婚姻经历暗寓自宪宗末年至文宗大和末年动荡的时局。
(二)李商隐以此诗自遣
李商隐在《上崔华州书》中言道:
凡为进士者五年,始为故贾相国所憎。明年病,不试。又明年,复为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间,未曾衣袖文章,谒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识其面,恐不得读其书,然后乃出[9](P441)。
李商隐的应举之路可谓坎坷,自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又有大和六年(832)、大和七年(833),三年三试,皆不中,大和八年(834)因病未能参加考试,大和九年(835)再次应试,为知贡举崔郸不取,开成元年(836)未应试,开成二年(837)在令狐綯的极力推荐下,被主考官高锴录取。
在开成二年六月至十月,李商隐于长安候选,但是在十月令狐楚病重,急召李商隐驰赴兴元。令狐楚死后,李商隐与令狐绪、令狐綯兄弟扶灵柩从兴元返回长安安葬,到长安时已是十二月下旬,因此李商隐错过了选调的时间。定《公子》一诗作于开成二年六月至十月间,似乎与李商隐在等待调选时焦急的心态有关。“金堂公主年应小”中“应”字有猜测之意,但实际上金堂公主还要大郭仲恭两岁,并不存在因为年纪小而不能出嫁的问题。李商隐作此诗也是感慨郭仲恭与自己相同的命运,与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只差咫尺,只能焦急地等待。只不过郭仲恭最后还是娶了公主,而李商隐则错过了选调的时间,于是在开成三年(838)春他又应吏部博学宏辞科试,本已录取,拟授官职,却被某中书以“此人不堪”而落选。
(三)戏咏皇室姻亲
与皇室联姻本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但是中晚唐时期尚公主却成为烫手山芋,避之不及。中唐以后,由于朝政格局的变化,皇帝择婿的对象开始向士族子弟偏移,唐德宗时“十宅诸王既不出合,诸女嫁不时。而选尚皆繇中人,厚为财谢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慎择人。江左悉取名士,独近世不然。’帝乃下诏皆封县主,令有司取门阀者配焉。”[2](P3717)唐宪宗时为岐阳公主择婿,“因诏宰相于士族之家选尚公主者”[6](P4381),然而“初于文学后进中选择,皆辞疾不应,唯悰愿焉”[6](P3984)。唐文宗对这种重门第择婿的现象十分恼怒:“民间修昏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2](P5206)于是文宗下诏宗正卿在世家子弟中为两个姑姑临真公主和真源公主选择佳婿。此时的士族子弟更倾向于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与皇室联姻固然可以荣升贵戚,提高家族的地位,但对于有经世抱负的读书人来说,此等荣誉就会成为束缚自身发展的枷锁,其实驸马与公主之间名为夫妻,实与君臣无异,且公主们大多恃宠而骄,不修妇礼,《金堂公主墓志》云:“先是国家富有六合,卑视汉魏。主第或恃大宠,宣骄炽横,朝庭百吏不敢问,士人畏惮羞薄,难肯议婚姻者。”[4](P307)故而士族子弟多“不乐国婚”。除了少数能出嫁外,大多数公主或入道清修,或至死未及出嫁,而金堂公主在其中是幸运的。
金堂公主与妹妹饶阳公主能够嫁入郭家,其背后的推动者与郭太皇太后有很大关系。《唐故江华县主墓志铭并序》记载:“(江华县主)洎乎成人,乃教文宗曰:‘我女贤丽,当选才夫。擢于吾门,尤叶吾志。’先帝于是诏有司曰:‘朕与江华等郭氏孙,况祖后赐旨,其敢疏忽!’”[10](P316)或许金堂、饶阳与江华皆于开成二年十二月嫁入郭家。金堂与饶阳同为穆宗之女,江华为绛王李悟庶女,但她们都是郭太皇太后的亲孙女。同年六月时,嫁给成德节度使王元逵的寿安公主,是绛王长女,被文宗嫁给藩镇,成为朝廷与藩镇博弈的牺牲品,李商隐《寿安公主出降》即是讽咏此事。郭太皇太后有子二人,长子唐穆宗李恒,于长庆四年(824)驾崩,次子绛王李悟于敬宗宝历二年(826)在宫廷政变中被杀,女一人岐阳庄淑公主,元和八年(813)下嫁宰相杜佑之孙杜悰,文宗开成二年(837)十一月病逝,郭氏的子女先后离自己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对于自己的孙辈必定格外留心,与其嫁与藩镇成为外姓人,不如联姻郭氏亲上加亲,对于重振郭氏荣光、稳定朝局也大有裨益。因此李商隐《公子》一诗可为《寿安公主出降》之注脚,看似戏咏,实则别有深意,是对朝廷和亲藩镇的讽刺。
三、结 语
由于史籍对李商隐的生平事迹记载不详,其诗歌又多晦涩难解,解读其诗虽是一件不易之事,但却能乐在其中。元好问就曾论其诗:“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李商隐的这首《公子》(外戚封侯自有恩)是一首七言绝句,在其诗集中也并不出彩,对于其编年和诗旨也少有人提及,主要在于诗中涉及的“公子”郭仲恭及金唐公主的生平事迹,史籍记载不详,对这首诗的解读也就无从下手,2010年新出土的郭仲恭及其夫人金堂公主之墓志成为解读这首诗的关键。藉由墓志之记载,基本可以确定这首诗作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再结合这一年李商隐在京之经历,可将范围缩小至六月至十月间。诗中所涉及的三个人物——郭仲恭、金堂公主和李商隐都在开成二年迎来自己人生中的大事,李商隐 在这一年终于进士及第,而郭仲恭与金堂公主也喜结良缘。再结合这一年发生的历史事件,对其诗旨作喻朝政变化、商隐自寓与在戏咏皇室姻亲中暗含对和亲藩镇的讽刺三种推测,正如张采田所言:“或当时有所指斥,殊难定解。”由于相关资料阙如,文章只能依据现存文献对之进行推测,只待来日有更多文献古籍被发现,对这首诗进行更为精确的释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