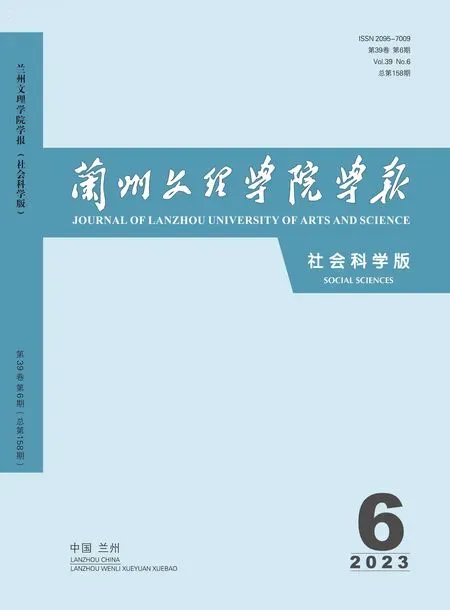《流浪地球》系列科幻电影中的神话元素
杨 瑞 峰,魏 畅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2019年《流浪地球》异军突起,首次在遗失之地竖立起一座孤峰,于是科幻这一被视为“儿童的”“科普的”艺术类型终于正式进入中国大众视野,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讨论热潮。面对后流浪地球时代“中国科幻电影将何去何从”的叩问,2023年《流浪地球2》的上映展现了中国科幻电影制作的无限潜能。虽然中国科幻电影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影响,但西方反技术主义思潮在中国并无坚实的生长土壤,辅之中国并无对外殖民扩张的历史,因此《流浪地球》系列电影选择致力于探索科幻电影表意的中国话语,并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合作为话语建构的显要路径。《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的成功,不仅源自其对电影艺术成就的追求,更得益于其中显露的“向神话回归的强烈的内在倾向”[1]。
一、科幻电影中的神话“元宇宙”
《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的情节设置以人类发现太阳氦闪危机为基础。面对氦闪危机,人类不得不制定了长达两千五百年的流浪地球计划,建造行星发动机驱使地球逃离太阳系,以4.3光年外的半人马座比邻星为目标,在漫长的太空流浪后泊入新家园,这一宏大构思在科幻电影中并不常见。中国虽然尚未形成成熟的科幻电影类型,然而中国观众却对这一全新的题材接受良好,或许是因为《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以细节取胜:唤起童年回忆的课文《春》,舞狮、麻将等传统民俗,姥爷“韩子昂”这一00后常见的名字和他爱听的流行音乐《海草舞》,熟悉的平凡面孔和日常服饰等诸多现实因素充斥着这个极有代入感的虚拟世界,地下城富有中国市井烟火气的布景淡化了崭新题材的接受障碍,促使观众相信《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构建的虚拟世界是现实生活的一个可能未来。
如果说丰富的现实元素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那么电影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则让观众领略到科幻的魅力。导演郭帆曾在访谈中说道:“在《流浪地球》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想构建一个没有坏人的世界、美好的世界,因为我们知道现实中不会有这样的世界。我们希望在影院的两三个小时里能看到一个美好的理想世界。”[2]然而与现实相比,《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构建的世界生存环境更加严峻:地下城有限的容量只允许一半人口进入,天灾人祸盛行,计划的过于漫长使人绝无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地球泊入新家园。在这种令人绝望的境况下,世界的美好体现在电影主创对人性阴暗面的有意“遮蔽”。原著中占据大半篇幅的叛变情节在电影中仅仅在角落中闪现,对人工智能大量取代工人岗位继而引发暴乱,抑或被舍弃在地下城外的另一半人口面临的艰苦生活等严峻的题材也没有展开探讨。影片中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人类对自然危机的抗争上,而并不是人类内部的相互攻讦,人性的闪光点由此得以显现。无论是播报宣告失败后运输车集体掉头全力协助“撞针”的俯拍镜头,还是面对引爆核弹任务时张鹏“五十岁以上出列”的呼告,人类总是在危难面前展现出超乎想象的团结和奉献精神,科幻电影由是建立起具有超越性意义的“超级之现实世界”[3]。
通过聚焦人性书写,《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初步建构起了一个具有超越性的“元宇宙”①。不过,“流浪地球”元宇宙的超越性,不仅体现在对人性的强调上,还体现在电影面对末日问题提供的应对方案上。科幻电影着眼于“幻”,虽然与科技息息相关,但其实更接近于种种历史可能性的预演。“末日”题材并不少见,然而司空见惯的飞船逃生题材已经无法引动观众的惊颤,成为了一种必然历史的“预告片”。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郭帆给出了新的解决方案,选择以陌生化方案打破观众的心理预期,呈现“带着整个地球流浪”的新奇想法。与疯狂构想相对的是严谨的世界观搭建工作,各领域专业人士参与其中,保证影片设定合乎逻辑真实与艺术真实,“参与这次世界观搭建的有二十多位科学家,所以世界的方方面面,从政治、经济、文化到所有的天体、地理等,包罗了很多”[2],符合当代社会信奉的可验证性律令。这种令人信服的假设使观众在脑海中铺设出与现实截然不同的背景,进而思考历史发展的另一条可能路径:在科幻电影荧幕内外的并置比较中看到现实世界的无限潜能。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流浪地球计划的可行性得到了验证,然而在《流浪地球》构建的元宇宙中,理性的叙事逻辑并未占据统治地位,充溢于荧幕空间的是神话叙事的幻影。面对迈克的质疑,中国代表周劼直没有证明移山计划的可行性,而是以象征化的语言予以应答:“我信,我的孩子会信,孩子的孩子会信,到那个时候,我相信会再次看到蓝天,鲜花挂满枝头。”神话语境下的信仰(belief)在此处显现,信仰对象是隐喻化的“蓝天”与“鲜花”,即地球泊入“新家园”后,迎接第一缕阳光而焕发的万千生机。在联合政府的发言中,周劼直又以“一根断裂的股骨”来比喻人类面对的危难,股骨的愈合依靠人类的团结,他以这种方式呼吁各国汇集全球所有核武并将其放置在月球之上,全力引发月核聚变。没有国家代表反对周劼直的提议,引爆月核的工作因此有条不紊地进行。在充满神圣意味的热烈呼唤下,人类团结应对危难,这种不符合科学实证的叙述反而鼓舞人心,也带给荧幕外的观众心灵的共鸣。
《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的讲述形式重塑起神话的肃穆与崇高。神话源于原始人对外界的想象性认知,是他们在有限的知识储备下作出的自我解答。“神话是关于世界和人怎样产生并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神圣的叙事性解释”[4],在此意义上神话与科学并无功能上的区别,因此科幻电影构筑的元宇宙得以通过显影神话的方式重新解释了现实世界,突破了剧情的单向线性发展。《流浪地球2》中多次闪现“距月球危机还剩16秒”“距互联网恢复还剩34分钟”等标示性语句,对此,导演给出的解释是:“把结果先抛出来,干脆观众也不用猜想剧情。因为如果去猜测剧情会影响到情感,我反而希望观众更多地注意到角色情感的发展,而不要受到情节的影响,情节不如情感重要。”[2]这种呈现效果与布莱希特的“间离效应”有相似之处,然而导演却借助编年体这种史诗化表达,剥除了理性分析对情感的干扰,实现了非理性的沉浸式体验。于是影片将神话语境中的心灵体验带给正在观影的当下,令观者在此氛围下接纳神话在影片中的事实复苏,为传统神话的降临寻得恰当的契机。
二、神话意象的纵向演绎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传统神话逐渐被现代科学强势替代。在高歌猛进式发展趋于平缓后,国人逐渐意识到建设精神家园所依赖的文化体系仍显零散,隐没的传统神话则是搭建这座当代中国文化大厦的粘合剂。因此在对现代性“阴影”的迟滞认知下,呼唤“神话”的再度降临成为人们的集体心声。在此情境中,《流浪地球》身先士卒,通过对传统神话意象的二次演绎赓续着神话传统。
影片中频繁出现的“圆形独眼”意象折射出神话的隐喻叙事风格。莫斯(550W)是《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中的人工智能,它拥有ToF雷达组,可以调动所有联网设备对目标物进行各种数据信息收集,其外观是圆形的红点,无论是功能上还是外形上都恰似一只眼睛。与莫斯ToF雷达组相似的“圆形独眼”意象在《流浪地球2》中反复出现,通常表现为监控摄像头“红点”(红外发光二极管)的蒙太奇片段。在无人机集体失控、方舟国际空间站坠毁、联合政府决策的分歧和团结、图恒宇妻女车祸死亡的意外、图丫丫的意识上传与月球发动机故障导致月球“坠落”等关键情节中,摄像头红点都密集出现。在观看片尾彩蛋前,观众或许会认为片中频频出现的“红眼”摄像头只是巧合,然而彩蛋中图恒宇对莫斯的诘问又令人重新审视“主题反复出现的蒙太奇”:
图恒宇:是你毁掉了月球发动机!
莫斯:包括但不限于:2044年太空电梯危机,2058年月球坠落危机,2075年木星引力危机,2078年太阳氦闪危机。
真相已自莫斯口中说出,《流浪地球》系列两部电影中的各种危机都有它的参与,频繁出现的圆形独眼是莫斯始终“在场”的暗示。无论是莫斯的红色圆眼还是监控摄像头的红点,都代表着“注视”的状态,这种对眼睛和视觉的强调实则是对眼睛原型意象的置换变形,在各种文献与文物上均有出现。例如20世纪80年代出土的三星堆祭祀坑青铜面具上,眼珠作圆柱状突出眼眶之外,这是将巫灵特殊视觉夸张化得到的立体造型,圆柱形巫眼即“纵目”传说,或代表巫人的神秘视觉和辟邪功能[5]。影片中多次强调莫斯的“眼睛”,是对莫斯见证、干预人类历史进程的暗示,是“眼睛巫术”在人工智能上的复现。
眼睛意象不独在人工智能莫斯的塑造上显现,还延伸至其他无机物体,特别是天体上,这与古人的表达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春秋时期,人们相信天帝与神灵都有视觉感知功能,“由于‘天眼’说法的存在,日月即‘天眼’之喻随之而生”[5]68。《流浪地球》中木星那只巨大的“风暴之眼”(木星大气层上的红色漩涡)数次出现,《流浪地球2》的一幅宣传海报由圆形的月球实验中心、行星发动机的圆形火焰喷射口和莫斯ToF雷达组的圆形红点向心拼接而成,三组圆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眼”。上述天体与机械的“眼睛”均为独目(一目),这种“一目”意象也保存在上古神话的原型结构之中,是一种无意识光辉的投射。例如在古埃及神话中,塞特神在鏖战中取霍鲁斯神一目,霍鲁斯又再次夺回一目并献予亡父冥神奥西里斯使其死而复生[6]。多神教神话中,各神明往往是某一天体的代表,艺术作品中的霍鲁斯往往与月亮联系在一起,因此月亮常常是霍鲁斯之目的象征。“月在某些情况下成为‘霍鲁斯的一目’;霍鲁斯的‘一目’失而复得,月每月隐而复现”[6]74,得到霍鲁斯一目的奥西里斯死而复生,正如月亮的阴晴盈亏,意味着月亮霍鲁斯之一目具有治愈与生死复归的意蕴。无独有偶,影片中的圆形独眼均象征生存与死亡的不同态势:木星之“眼”的接近意味着地球将要被木星引力撕成碎片,月球行星发动机过载显示出的“独眼”导致月球变轨以致坠落,这些都是死亡将近的预示;而引发核爆导致月球解体,月球上的爆炸光芒又仿佛月之圆眼,寓意生死交织的转置,三百名引爆核弹的领航员的死亡换来地球置之死地而后生;莫斯“独眼”更因为其对人类命运的操控而意蕴暧昧,它制造危机剥夺了人类的生命,最终的目的却是延续人类文明。在这里,“流浪地球”独目意象的生死复归与远古神话的神圣性解释得到统一。
影片中架构师图恒宇的死而复生拓宽了圆形独目意象的含义,也是对远古神话生死复归主题的再度演绎。图恒宇等人在水下的北京互联网中心旧址重连全球互联网,然而坠落的月球碎片击破了封闭的机房,水流一涌而入,濒死的图恒宇将自己的意识上传。生命终结之际,他在水下看到了莫斯“独眼”的闪烁,这是灵魂即将在数字空间中得到重建的信号。在古埃及神话中,水在诸多有关死亡与生命的神话母题中占有重要地位。拥有植物宇宙属性的奥里西斯获得霍鲁斯“一目”死而复生,他的葬身之地是在水中,正对应埃及尼罗河水泛滥后植物再次繁茂生长的情节[6]。图恒宇的死亡与复活是“获得‘一目’死而复生”的情节再现,“死亡—水—复活”构成了具有隐喻色彩的神话结构。沉没在水中的图恒宇,被水充满的狭窄机房,既处于死亡的终点,又像胎儿安卧于母亲子宫的羊水中。这种水与封闭容器的构形——“神圣水罐”是大母神的象征。大地子宫既是坟墓与死亡吞噬的子宫,也是容纳与生命孕育的子宫,图恒宇的生死轮回在母神“子宫”中循环。
不仅仅是图恒宇的死亡与重生,与前文所述的生死复归联系起来,命运的轮回与影片中的巨大圆形紧密相连:莫斯的“红色圆眼”自黑暗中跳出《流浪地球2》的片头,又在片尾沉寂于黑暗,图恒宇与图丫丫的无数个“数字房间”排布在莫斯的圆眼之内,领航员号空间站、行星发动机和月球实验控制中心等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设施均为巨大的环形,领航员空间站和方舟国际空间站与地球重合的拍摄角度则构成了被黑暗包裹的同心圆结构,图丫丫的意识被上传到数字空间后,拍摄视角自莫斯“圆眼”始,不断旋转着穿过无限重复排列的数字房间,与图恒宇所在的镜子房间、月球实验中心的摄像头“圆眼”构成一组长镜头,暗示着螺旋纠缠的未知命运。这便是大母神原型变形后的“大圆”(the Great Round)[7],即始于黑暗、包含万物、命运的升沉轮回其间的“自然母神之轮”[7]241~245。影片中的诸多原型意象以神话隐喻的方式归一于命运无常轮回的意蕴,显示了“天人合一”的特征。这种神秘的交融关系并非由理性思维编织,而是来自于非理性的联想与直觉。“流浪地球”元宇宙之构筑,令观众暂时自理性的钢铁框架中挣脱,投入非理性的海洋。
以上是上古神话原型意象的重新演绎,除此之外,影片中还出现了与传统神话母题背道而驰的反转,彰显了拆解既有意识形态的意图和建构新世界的渴求。为应对危机,以神话母题为蓝本命名的移山计划、逐月计划与方舟计划引人注目,前两者出自中国神话典故,而方舟计划则出自诺亚方舟的故事。这三个计划的结果大相径庭:移山计划更名为流浪地球计划正式实行,逐月计划也已通过实验,只有在建的方舟国际空间站被数字生命派袭击坠毁,方舟计划宣告失败,是对西方科幻电影前文本的颠覆。直接促成“方舟”坠毁的数字生命派占据着影片的暗面,面对太阳氦闪危机,数字生命派选择放弃肉体的存活,转而追求在数字空间中建立新世界。当人的意识上传成为数据后,便可以在数字空间中得到永生,这是“终末神学”的现实重述,即在“上主的日子”基督复临,所有亡者复生接受公审判(general judgment),最后善者进入永生的神国[8]。终结之日不仅是太阳氦闪末日危机,更是广义上肉体生命的毁灭,而方舟不论在影片中还是在神话中,都代表着生命得到拯救。数字生命派对“终末”的期盼态度使他们否认“方舟”的现实存在,于是上帝赐予的生机被上帝使徒捣毁,自内部裂隙而始的崩塌比外部的破坏更具讽刺效果。与西方终结论意识相对立,跨度两千五百年的流浪地球计划是中国宇宙人生无限延续意识的体现,实现了东方神话对西方话语的颠覆。
与西方对峙的关系之外,影片通过创造性的挪用实现了传统神话语境的自我颠覆:愚公移山神话母题中的山是愚公生存的阻碍,愚公移山是为了拉远山与人的距离,影片中的“山”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移山”是人类驱使自己栖身的地球移动;逐月计划令人想起夸父逐日和嫦娥奔月,但这两则神话均是人类追逐、趋近天体,逐月计划的目的却是驱逐月亮,使月亮远离人类。两个计划的意义反转源于对动词复义的再解释,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距离概念。语义的自反构成了一种隐喻,这种与平常事物不符的隐喻令人的感知更加敏感。“科幻……通过突兀的对抗而非平实直白的陈述或分析性陈述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认知:它是一种语言偏离,其结果是引发了人们对能够建立起其自身新标准的可能关系的感知。”[9]这种隐喻的自反给观众带来了陌生感,使观众自现实惯性中惊醒,思考“发生”之外的真实,这是科幻元宇宙得以构建的一种方法。
三、神话信仰的荧屏改写
在某种程度上,尼采提出“上帝之死”,标志着人类的中心地位正式建立。“谋杀”上帝者并没有成为“超人”,反而成了彷徨于虚无主义废墟的幽魂。在科幻电影构筑的元宇宙中,一个全新的“上帝”得以形塑,并得到了观众逻辑与情感上的双重信服,在此情境中,启蒙被打造成了神话阐释的一种手段,神话信仰依托具有启蒙效用的科技手段,在《流浪地球》系列科幻科幻电影的荧幕空间中得到改写。
随着剧情的展开,科技塑造出神话意义上的信仰对象,人工智能莫斯成为《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中超凡的存在。除了前文提到的莫斯向图恒宇坦白的对话外,影片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暗示了莫斯始终保持着俯视人类的姿态。1987年七一零所收到了“2044”这串数字,2058年超快光学飞秒实验室收到了“205807”,前者是太空电梯危机的发生年份,后者是月球危机的发生年月;在《流浪地球2》片尾,2065年的人类还收到了“20750215”的数字,正对应了“距木星危机还剩10年”的预言文字,与《流浪地球》木星危机叙事形成闭环结构。影片中并未点明信息传递者的身份,然而频频出现的摄像头“红眼”已将答案指向了莫斯,莫斯即是这些预言性数字的传递者。预言起源于远古,“在古人的信仰中,凡属可见可闻的一切现象,几乎都能成为未来某种事件的预言或预兆”[10]。进入工业社会之后,预言的神圣性开始消退。现代人实现了对神话的祛魅,于是传统预言失去了合法性,接续神话的是科学,科学成为现代人解释世界的信条。然而莫斯使用科技来传输数字,利用科学再现了传统预言形式,重建起与神话类似的信仰体系,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神”。
无论是神明与凡人的对比,还是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对比,都是探索莫斯身份定位的艺术策略。莫斯很显然拥有与人类相似的自主意识。在《流浪地球2》领航员面试时,面对刘培强“你为什么只有一只眼”的问题,还是550W的莫斯回复“我有两个版本的回答”,这两个版本分别是“极具幽默感的”和“官方回答”,此处莫斯的自主意识尚不明晰(或者仅仅是展露得不明显)。然而在片尾的这段对话中,莫斯毫不掩饰地显露出自主意识:
刘培强:550W。
550W:550W听起来不像个名字,但把它翻过来,叫莫斯(Moss),直译为小苔藓,是不是可爱了一些?
刘培强:这个回答是官方的,还是幽默的?
550W:这是莫斯的回答。
在某种程度上,莫斯主体意识的确立对人类的中心地位构成了挤压。莫斯为自己起名这一情节就集中体现了它对主体性意识的捍卫。拥有自主意识的主体往往对名字尤为重视,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名字、灵魂与身体三者紧密相连,“野蛮人将一个人的名字视为其人格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并视之为他的一个重要所有物”[11]。影片中莫斯的形象设计保留了方方正正的钢架构形,黑色或白色的机身上一只红色的“眼睛”,这种机器形态暗示观众莫斯不太可能具备类似于人类的自主意识。人类以“万物的灵长”自居,凭借理性树立中心地位,然而在《流浪地球》中,莫斯发出了“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确实是一种奢求”的感叹,至此,人类理性的桂冠被剥夺,藉此方可建立的优越感也因之荡然无存。
除了人工智能,人格化的天体也填补了上帝的缺席。《流浪地球》系列两部电影所描述的危机都与天体有关,人类的存亡由天体掌控。当人类不得不接受即将灭亡的命运之时,片中角色对着木星射击时的怒骂“我去你妈的木星,去你妈的”是人类被自然神力碾压的绝望,这种对话式的咒骂很明显将木星人格化了。木星(Jupiter)的命名来源于古罗马神话的主神朱庇特,影片中的木星仿佛众神之王般对人类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力。木星危机时,影片刻意突出木星的风暴之眼,在地球即将被木星引力捕获之时,木星的风暴之眼将整个天空染成血红,而在地球成功摆脱木星引力之后,影片中也出现了地球自木星风暴之眼前划过的镜头,木星的瞪视始终令人胆寒。同为信仰载体,如果说莫斯是有意识的神明,那么天体则代表着零道德的宇宙,后者更贴近粗犷的原始崇拜尚未被人类社会驯服的状态,人工智能莫斯碾碎了人类的主体骄傲,而崇高天体则剥夺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灵魂意义和肉体存在被同时摧毁的情况下,人类仍保留着重建主体价值的可能,而影片中对月球的塑造或许是一个重建主体性的契机。同为天体,月球与人类的关系更复杂(影片中尤其体现在月球与中国人的关系上),片中“等月球远到看不见了,也不知道中秋节还放不放假”的闲谈之后,是中外两个工作人员对南北方月饼馅料的争执,这是中国观众心照不宣的笑点。在末日将至的紧张氛围中,影片选择插入与月亮相关的中国民俗元素以调整剧情节奏,侧面彰显出月球重要的文化价值。月球对于人类的价值并不仅仅依托实体而存在,当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驱逐月球时,纵然表现出了不舍,但两位工作人员的对话却暗示着即使月球实体消失,月亮意象仍会和逐月计划启动时广播所说的那样,与“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文化记忆一同保留在人类的无意识基因之中。作为实体的月球消逝,而作为意象的明月在人类的美感世界永存,这便体现出人类的创造性价值,而这种创造性价值是人类命运无限可能的基础。前文提到,科幻是一种对历史可能性的试验,《流浪地球2》则就人类命运的可能性给出了诗意的描述:
刘培强:莫斯,人类能活下来吗?
莫斯: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刘培强:我选择希望。
这是两部影片中对人类命运走向最直白的探讨,“希望”这个词在两部影片中频频出现,“希望,是我们这个年代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在《流浪地球》的首尾反复出现,韩朵朵片头时对此不屑一顾,而在片尾时却以这句话呼吁人类再次拯救地球。韩朵朵并不是韩子昂的亲孙女,韩子昂这样讲述收养她的经过:“我救了一个孩子,无数双手把她推到了我的面前,我不知道她的父母是谁,那水下的每一个人,都是她的父母……我给她取名叫韩朵朵,我把我闺女的名字给了她。”韩子昂的亲生女儿早逝后,这个被托举而生的女孩继承了“韩朵朵”的名字,完成了延续希望的隐喻。《流浪地球2》中“普通人”张鹏与刘培强二人关于理想与生命的传递、“技术派”马兆与图恒宇二人对科学的执着与理念的继承、“国家代表”周劼直与郝晓晞二人有关责任的教导与后者由青涩向老练的转变这三条线中的师徒传承也诠释了希望的延续。
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指出,希望是一种“尚未存在的本体论”的追求。莫斯不具备人类对希望一词的情感体认能力,因此,当它在0.42秒之内便推演出人类必定灭亡的结果后便决定舍弃地球带着领航员号逃离。与此相对,人类却始终对未来世界充满希望,这种追求源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渴望与冲动,或许这就是莫斯得出“延续人类文明的最优选择是毁灭人类”结论的依据,因为无论面对多么沉重的必然,希望的开放性总能在意念层面为人类带来一线生机。影片中人类对命运的频频突破展现了希望的开放性:图恒宇摆脱了莫斯的绝对掌控而在数字空间内重生,输入最后一串密钥而成功重连互联网,因而得到莫斯“你是一个变量”的评价;尽管得知莫斯计算出人类存活的几率为零,刘培强仍然选择撞向木星以填补行星发动机喷射火焰到达木星的最后距离,最终为人类赢得生的可能;周劼直凝视摄像头“红眼”的镜头暗示着他与莫斯的博弈,他看似非理智的指挥使地球脱离月球坠落危机。在《流浪地球2》片尾,周劼直有一段独白:“我相信,人类的勇气可以跨越时间,跨越每一个历史、当下和未来……我相信,我们的人一定可以完成任务,无论虚实,不计存亡。”这段独白解释了在北京没有完成互联网重连的情况下周劼直明知提前启动行星发动机会导致地球撕裂,却还是对点火异常执着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周劼直触及了数字生命的真相,比起命运,他选择相信“虚”(数字空间)与“实”(现实世界)中人类对希望的追求,相信这种追求在每一个历史可能性中必然达成。对希望的信仰源自人类对血肉之躯局限性的理性认知,而人类的主体价值也正是在对希望的无限追求中得以重建。
四、结语
综上所述,《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立足神话语境,沿历史纵轴复现传统神话,让古老的原型意象与神话母题在影片中实现创造性、颠覆性的演绎,在神话元素的神秘交融中传递非理性的体验,同时以神级“生命”作为人类文明的横向对照物,以人工智能和无机天体来填补崇高上帝的空缺席位,令人类在灵魂意义与肉体存在被否定的情况下,通过对希望开放性的追求重建主体地位。此外,在缓解现代性危机与加强文化认同的双重需求下,《流浪地球》系列科幻电影印证了神话叙事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影片向我们表明:神话绝不仅仅是埋藏于历史尘埃之中的迷信故事,而是当代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资源,更是可以经由艺术加工重建当代人精神世界的有效手段。如何让神话焕发生机,或许不仅是艺术创作者需要去不断探索的重要议题,也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的重要话题。
【注释】
① Metaverse(“元宇宙”)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小说家尼尔·斯蒂芬森的科幻小说《雪崩》中,可以理解为相对独立于现实世界的三维虚拟空间。“元宇宙”这一概念发源于科幻,科幻也更贴近元宇宙“虚拟实景”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