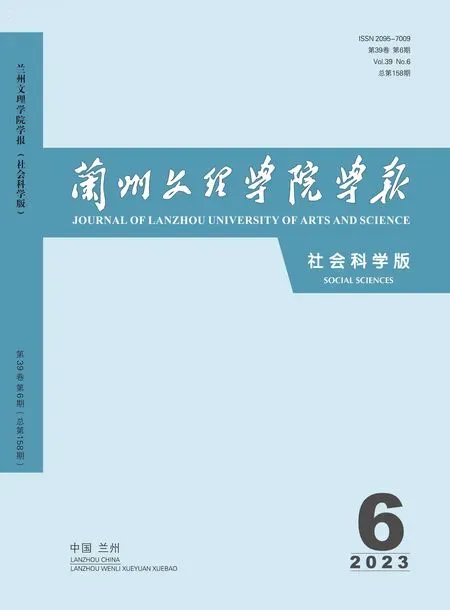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张慎言酒泉纪行书写
赵 钰 飞,万 雨 萌
(西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部,甘肃 兰州 730030)
张慎言(1577—1645或1646),字金铭,号藐姑山人,山西泽州阳城县(今山西省阳城县)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张慎言的仕途,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直至弘光,从知县、御史直到吏部尚书,一路坎坷,三遭贬黜。天启五年三月,已离京三载的张慎言被诬私盗库银,于次年谪戍肃州。作为明代晚期山西文坛的代表,张慎言的最高成就当属谪戍酒泉时的游草,是为《酒泉诗稿》。这部诗集对明末酒泉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作了精彩展示,更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新的文学地理内涵。
一、张慎言酒泉书写的“外层空间”
张慎言此行由天启丙寅年(1626)秋获罪启程始,至崇祯戊辰年(1628)春得赦还归终,历经酒泉四时。作为现存可见记录汉人王朝在河西边塞生存斗争现实的最后一部诗集,张慎言的《酒泉诗稿》不仅记述了边地的自然风貌,其地的风土人情乃至日常生活也被一一叙写,将明末边地的外层空间还原为一幅幅生动的地理图景。
明置九边,甘肃镇是明代西北防御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人言“四时皆防”“兵马奔驰殆无虚日”[1],而肃州地处甘肃最西端,自嘉靖七年(1528)“关西七卫”丧失殆尽,便成为国境之西边,直接暴露于军事冲突的最前沿。张慎言到时,酒泉形势已呈现出同明王朝相类的颓态。《酒泉诗稿》中的诗,真正以酒泉自然风物为描写对象的很少,但其诗歌构建起来的地理空间,无不以自然环境为其外层组成部分。“南山积雪”是肃州八景之首,“遥峰积雪流青烟”[2]正是张慎言初见酒泉的新奇印象。夏季来临,雪峰依旧,刚得安顿的逐臣偷闲远眺,积云环抱的祁连卧雪发出清亮的光彩:“霞文摇积雪,明灭夏云端。云峰既缅杳,雪意亦波澜。流景何难掬,清晖真可餐。”[2]酒泉名“泉”,自然水系丰富,城周有讨赖(来)河、红水河、丰乐川等多条河流,不仅立春时节有“东郊泉水澹潺潺”[2],春末上巳更是“烟泛汀洲花气然”[2],大小河流争相奔涌,不仅为肃州地理贡献了“清河夜月”“来河绕野”“红水穿碉”等胜景,更为塞上农牧业提供了丰沛水源。边塞军民为了更好地运用水资源,兴修水利,城内外筑渠坝数十,张慎言即有《坐黄草渠》《夏日黄草渠看雪》两诗专以水渠命名。此“黄草渠”最晚建成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龙口起于肃州城西南讨赖河,尽于城东北水磨渠。坝宽一丈,深三尺五寸,长六十余里,千户曹斌督修”[3],正是肃州水利建设的典型,在山水景观之间凿刻出人文痕迹。
除了景观、实物形式的文学地理要素,张慎言的诗歌还将边地的社会百态填充其中,构建起一个血肉丰满的外层地理空间。水利建设为农牧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民族交融和屯垦政策则贡献了实在的人口和丰富的人文空间。为避战乱,包括关西七卫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部落东迁至肃州乃至甘州,定居于祁连山下的肥美牧场。秋冬时节,“寒汀衰草见穹庐,南北杂居羌与胡”[2],明末边塞的危局之下仍上演着多民族友好共存的和谐场景。“牧儿奔返照,锄唱爱余曛。”[2]得益于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民族关系,农牧业都呈现稳定局面。但这种稳定,事实上只停留在诗人的心境里,在现实的地理书写中,《老圃行》一诗将内地移民的屯垦之苦真实展现出来。万历丁卯秋初,张慎言至酒泉已近一年,闲余拜访了一位七十岁的老翁。明初甘肃初定,为配合边地的民屯政策,大批内地移民辗转来到河西,而山西正是移民的重要源地,洪洞大槐树的故事至今流传。“兼闻我语似里閭”,老翁听到乡音,这才与我亲近,相近即言之肺腑:“良久渠云苟生活,少壮犹可老崎岖。阿妻衣破露两肘,鬓毛垂领衰过渠。对我拉儿摩其顶,但恐舍此委沟途。乡音剌剌不可已,滂沱涕泗沾襟襦。”[2]同乡人异地相逢,亲切之意溢于言表,也将边地屯田的现实苦难呈现出来。天启四年(1624)甘肃巡抚李若星奏云:“辽东、甘肃止设卫所,不设府县,以数百万军民付之武弁之鱼肉。”[4]张慎言访谈式的创作,把平民视角的民屯之苦付诸书写,为酒泉的人文地理空间补上了关键的一角。
作为军事前哨,“止设卫所”的肃州自然也不乏军事景观。防务闲暇时,“短衣射虎随飞将,野火椎羊傍健儿”[2],游缰射猎颇见东坡豪气;军情告急时,“登台面面尽黄埃,边气胡阴惨不开”[2],敌军压境,诗题《登城北最高处,三面皆虏,才东走张掖一线尔》更直观地展示出边境战局的危急形势。作为破阵锐士,“刀环血渍摩挲看,昨卖胡奴新髑髅”[2],边军的战意之盛恍惚间似有汉唐军威;而作为体制中的一员,士兵们一面遭受着“此物近来良减价,公移简勘又经年”[2]的低效官僚政治的剥削,一面又参与在“马首归悬三四级,居然明日长千夫”[2]的腐败现实中,而更多的普通兵士,实际仍无助地处于“武弁之鱼肉”的境地。据载,崇祯元年(1628)陕西欠饷138万两,各级军官克扣下级粮饷,士兵不堪其苦,乃至多生哗变[3]210。《清代通史》更统计明末农民起义之情形云:“曰叛卒,曰逃卒,曰驿卒,曰饥民,曰响马,曰难民。”[5]六类人中,兵居其半,足见明末军人待遇、遭际之恶劣。张慎言笔下的边疆并不似前朝边塞诗中所写的豪情壮阔,他以普通军民的视角,展示了明末时代背景下真实的酒泉地理空间。
以往诗歌的地理空间书写都是写“有”以填充之,但围绕酒泉的节物特色,张慎言还做了一些写“无”的尝试。丁卯夏末,张慎言在终日寂静中悲伤地发现,《酒泉无黄鸟兼无蝉》:“蝉响莺鸣寂不喧,朝烟晚霭静谁翻。”[2]郁闷之余只能发出“方怜节物良如此”的无奈感叹,可与《琵琶行》“终岁不闻丝竹声”的“从无”写法相比类。早在两晋张俊的《东门行》中,就有“鸠鹊与鹂黄,间关相和鸣”[6]句,唐代陈子昂记录由张掖至居延海一路见闻的《居延海树闻莺同作》中也有“边地无芳树,莺声忽闻新”[6]82的描写。同处河西,甘凉二州尚有莺鹂,一过酒泉便销声匿迹,区域比较之下,后者的荒凉恶劣变得愈发形象可感。写“无”的地理书写不仅使外层空间的形象系统更为明确具体,相较写“有”的填充意义,其更隐射着文学内层空间至关重要的心灵缺失,为进一步的精神探源提供了明确导向。张慎言的地理外层空间书写还特别体现出虚实相生的特征。他一方面在时空跨度上搭建起异质空间的比较体系,如“汀州草色果何如,遥忆芳莲碧水波”[2],春仲犹寒,酒泉的水滨尚无花草,诗人于是从回忆里拉来了异质空间的“芳莲”填充其间,在幻想中映画出一副“同时间而异空间”的文学地理图景。另一方面,他还尤其善于以梦境介入时间流动,在一固定的空间里填充入未来时间的景象,这类诗在《酒泉诗稿》中很多。如《春仲移居,宅西偏有桃李》“酒阑颜热时相讯,刻日先开故国花”[2]句,诗稿中分明有《春仲水滨,拟往踏青,寒甚,斋中作》的诗题直言“寒甚”,桃李又怎么可能“刻日”开放呢?相近时分的《立春夜作》也有“戍客酒酣犹未醒,春光已度玉门关”[2]句,反用王之涣“春风不度玉门关”[6]84的诗意,同样嫁接了虚构的情形,在这片苦寒的土地上“预支”了节物风光,以“同空间而异时间”的时空组织法向心灵的内层空间开拓出一片春色。
山水节物、军民生活,张慎言以普通人的视角,全面展现了酒泉的文学地理样貌。《酒泉诗稿》抓住景观、实物、人物、事件等显性要素,既写“有”以填充,又写“无”以留白,不仅形象勾勒出明末酒泉的外层地理空间,更为突入内层空间、展开精神探源开辟了路径。尤其是他从“无”处着笔的尝试,或将为文学地理学提供新的理论萌发点。
二、张慎言酒泉书写的“内层空间”
作为军事和商业的重要隘口,河西同样是文化输入的重要通道。中国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史上,唐代边塞诗派可谓举足轻重,在气象恢弘的大唐盛世,多少渴慕功业的志士策马河西,留下了不朽的诗篇。《唐诗别裁》载名家论唐诗之压卷,李攀龙推王昌龄之“秦时明月”,王世贞推王翰之“葡萄美酒”,王士祯则并举“王维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龄之‘奉帚平明’、王之涣之‘黄河远上’”[7]四者,西北边塞诗竟逾其半。这片土地上时空交叠,历史在地理的版图上留下它的凿刻,一个个古老的民族在这里流转,一代代人在这里交锋、定居又离去——从汉匈、唐蕃到明军胡虏,都用各自的故事填充了河西的地理空间,而酒泉堪称其间内涵最丰富者。张慎言作为最后一批见证汉人王朝与北方部族在河西走廊激烈冲突的诗人,对于酒泉人文地理空间的精神内涵是具有总结和补充意义的,而其游草中对于精神世界的书写,也确实深刻体现了这一价值。
酒泉的自然地理决定了它冷峻肃杀的气质。南临雪峰,北接沙漠,尽管水系丰富,但深居西北内陆,干燥的气候和近半年的寒季还是令中原人备受折磨。初到此地的戍客或许会短暂惊叹于西边胜景,但稍后真正直面恶劣的现实生存状况时,心中的愁苦和对故土的思念便会相继袭来。《酒泉诗稿》中耳目新奇的描绘型诗篇很少,只以诗句形式间或出现,尤见于入陇途中。天启丙寅(1626)九月,张慎言途径华阴,登临华山,满目胜景:“翠流丹壑秀难名,云响青崖白有声。”[2]但耸立的崖壁、缥缈的白云乃至滔滔东去的黄河,很快就变了模样:“三峰秀色愁将堕,万古黄河咽不流。”“心留峡里云空白,气暗关前紫不浮。”[2]不久夜宿铁牛峡,又有“云涨丹崖厚不收,秦川陇树淼难求”[2]的书写,直至洮河,秋意如刀,仍是“汀树愁将失,峰云寒不流”[2]。水“不流”、气“不浮”、云“不收”,寒气似乎遏制了水流又凝固了云海,满眼的地理景观尽管没有被寒秋杀灭生机,但万物一派郁结,同样倒映出诗人的浓重愁绪。不同于以往悲秋诗中的肃杀惨景,张慎言笔下的“秦川陇树”依然多如“淼”、美逾“秀”,仅作白描的地理意象观照仍不失为胜景,但正是这多到厚重、美到浓郁的景观结构,几乎填满了整个外层空间,与之相应,诗人的内层心理空间也被种种情绪拥堵乃至挤压着。张慎言是作为阉党乱政的受害者谪戍西行的,而彼时“众正盈朝”[8]的天启朝已然在如曹珰“劾四御史如承蜩然”[9]的倒行逆施下变得乌烟瘴气,“永戍”[10]的判决完全可能成为现实,在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双重绝望中,浓重郁结的愁绪自然满积胸臆。但“为诸生时,裹粮樸被,遍游吴越名胜,虽牵丝入仕,神明寄托,恒在山水间”[11]的经历和精神指向,似乎也冲淡了绝望的愁情,一路胜景,让不幸的张慎言得到了些许安慰,因此他笔下的景致并无秋气肃杀的颓貌,只在这渐趋寒冷的地理空间里填充着秦陇的疆界。
张慎言抵达酒泉后,真正面对塞外的地理景观,直言“登台切莫向西看,节物风光黯不欢。幸尔远峰开晚气,萧然积素送深寒”[2]。初雪之后的肃州恰如其名,在“深寒”的气候中,万物肃杀凋零,诗人的情绪也难以振起。酒泉的冬天很长,春日的节令却只有满眼冬景,《立春夜作》《上巳水滨眺雪看花》都只有借酒借梦才有诗人眼中的花开场景:“风光乍传烟摇曳,雪魄花魂愁欲眠。花间流波碧新软,光气与之俱近远。春色茫茫撩客愁,愁随春色为深浅。秋风凄紧春风缓,气缓客愁仍自满。”[2]“雪魄”中“花魂”愁眠未发,节物的惨淡催动诗人心绪,一诗连用七个“愁”字,把“永戍”之人的悲痛书写地淋漓尽致。
除了自然地理环境的恶劣,酒泉作为军事冲突的前线,三面临敌,激烈的战事也为这里增添了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张慎言是作为平民出戍肃州的,尽管彼时获罪戍边的旧臣“哪怕没有职务,也因他们先前曾在朝廷供职而具有一定的影响”[12],但在彼时自顾不暇的边事危局中,他初到时也只能“寓禅室”“三时缺起居。寒温烦琐细,眠食颇萧疏”[2],几无特殊待遇。但即便在这样的境遇中,张慎言却也逐渐注意到了新环境中丰富的军事景观。“塘传虏帐驻飞狐,士马宵奔偷杀胡”[2],矫健的勇士们闻风而动,策马偷袭敌阵,构成了边塞的靓丽风景线。“淋漓血渍染鞍鞯,酒债新偿五十千”[2],杀敌归来,血染马背,军士以军功换饷钱,又以之抵偿酒家,一幕幕场景丝毫不减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的豪情。在如此气象的军事场景的感染下,已“五十初度”的张慎言也不由发出“五十从军仍未迟,撊然韎韦尚堪驰……当时早署千夫长,总角诗书奚以为”[2]的慨叹,诗人内层空间的愁情似乎被边地建功之志一扫而空。来往家书中,“拟元夕后,向地主以一二队弛关外,臂鹰牵犬,幸得黄羊野马,割以佩刀,炙用野火,生嚼流血,良亦快事”[13]的狩猎计划更印证了诗人被军事景观深深感染的精神世界。
军事景观的积极意义是显著的,但久戍边关,其对诗人心灵空间的消极意义也日益显现出来,伤亡的阴影、生死的反差和实践的煎熬成为游子思归的催化剂。这不是酒泉的专属,但恶劣的外层地理空间更加剧了这一倾向。从出行途中即写下的“微尚当修夜,萧萧故国愁”[2]到初春有感于节物不欢的“刻日先开故国花”“乡路五千知近远,青青不断度黄河”[2],张慎言对于故乡的思念是持续加深的,最平凡但在酒泉地理空间里却难得在春日见到的花花草草成为诗人思乡之情无形蔓延的投影。稍作比较,其实不难发现,围绕边地的军人、军情,唐代边塞诗中也不乏以思乡为主题的作品,这类作品多以军人或军属为主人公构建文本空间;而明代边塞诗中此类诗篇在数量上大幅缩水,在文本空间的搭建过程中则更多以自身的经历和幻想入诗,由第三视角转变为第一视角。这一现象或与明代边防主要为防守而非如唐代主动进军的基本方针相关,前者征调、后者屯戍的边军构成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在截然不同的战争激烈程度和将士生存状况下,明代相对和平的军事地理景观对无论仕宦还是谪戍至此的诗家都未造成如前代般激烈的心理冲击。尤其得益于可携带家属至此的军屯、民屯政策,明代边地的军民失去了“思乡”这一集体心理的人文地理条件,而使这一心理缩小到流寓此地的少数人中间。
关于明代的这个少数人群体,历史是有记忆的,“因贬谪、巡抚、仕宦、漫游、从军等原因出塞到河西走廊的将吏文士较多,如丁昂、牟仑、张楷、郭登、陶谐、陈诚、岳正、徐廷璋、朱维均、郭绅、戴弁、赵锦、赵载、陈棐等”,乃至形成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文学团体。他们“舒忧觅笑,或唱或和”,在文学活动中排遣彼此的乡愁,且正是由于这一团体的存在,酒泉成为了“明代西部边塞文学、贬谪文学的创作中心”[12]。但值得注意的是,张慎言是被诬陷而获罪谪戍的,他离开故土时,不仅双亲乃至祖父祖母都已去世,且因戴罪之身,他一面遭遇了为报私仇的安伸“竟刺其臂”[9]92的迫害,一面“一时亲友及地方官有不唾弃而避之若凂者,几何人”[14],政治上、感情上,可以说张慎言此刻都面临着最大危机。因此抵达酒泉后,张慎言的孤独是无奈的,不同于唐代边塞诗人和同时期酒泉的文学团体,他思乡,但这份情感却几乎无处着落,仅有的一首宴饮诗《赠贺二府归里,贺贤者以左官去》,抒发的仍是“尔我荣枯”[2]的命运感叹。“悲欢皆昨日,穷老付余年。”[2]在孤独中,他思怀的仍只能是过去的家乡,他的孤独在时空两端都无比纯粹,面对历史和未来,面对整个世界,他拥有的都只有无尽的孤独。除了写给儿子和挚友的几封家书,他的思乡大多都真的只能指向“家乡”这样一个笼统的概念,但他的孤独,因为家乡这一概念的存在,又显得更加激烈和具体:戍途中望雪,他望见的是“孤光与积素”[2];初抵时恰逢五十诞辰,他“醉来时倚孤台望,边气黄云白发前”[2];春到酒泉,他“挥杯惟劝影,听鹊恨空啼”[2];当真正习惯了新环境,却依旧“斜阳半壶酒,孤影劝相怜”[2]。面对南山积雪、夕阳西下和戍所堡垒的塞外胜景,他的心理空间满满只是孤独。“塞上健儿那解愁,醵金贳酒醉无休。”[2]尽管他学着样子打猎、野炊、酗酒,但未醉和酒醒的时分,他的孤独依然极尽纠缠。当然,尽管孤独如此,思乡难付,最终在外层和内层空间中排遣此情的,仍是故乡,而寄托乡情的地理意象,是一株老槐。
《倚树作》有“槐老空庭枯欲尽”[2]句,这株树是长在张慎言新得的庭院中的,空寂的小院,半百的老人,垂老的枯槐,在他赖以生存的外层地理空间里构成一幅凄凉晚景。然而槐树并非简单的拟人寄托,它本身就是家乡的慰藉。张慎言爱树,爱植树,尤爱种松,在他分别记录归省和落职生活的《虎谷诗集》和《泊园诗集》中,就有着如《种松》《除日种松》《泉侧种松》《憩虎谷松下》等近十首专以松树为题的诗歌,以上四首歌咏的正是他故乡的松。虎谷是他故乡的别称,即今天的山西省阳城县润城镇屯城村,《偶成》有“山取虎谷名,松疑汉以前”[2]句,足见虎谷种松数量之多、历史之悠久。作为土生土长的松下儿郎,张慎言自然深受其感染,于特定时节种松的爱好便逐渐形成。作为自然界中傲霜斗雪的勇士,松树赋予了张慎言同样坚韧顽强的品质。不仅如此,《种松》的诗句还很好地诠释了诗人与松的感情:“笑似老翁生稚子,稚子老翁俱没齿。情知稚子不相待,学语弄髯差可喜。我令种松颇似此,盖偃涛翻吾老矣。”[2]诗人对初种的松树视如己出,倍感欣慰,对一纯粹的地理意向本身产生如此亲密的拟人情感,这在诗歌史上都是不多见的。爱松如此,张慎言也对其寄寓着乡情,《邸中有怀故园》中便有“两岁如在里,栽松又百株”[2]的感慨,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满植松树的地方就是故乡。谪戍酒泉的日子是艰辛的,但庭院里的老槐,以松树的形象,为爱松的游子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酒泉诗稿》中的组诗极少,而《庭前老树欹斜偃,蹇月徙倚,逐书触目》便是之一,其一云:
庭前老树半离奇,浸月饕霜人不知。尔我相依休谩诮,支离臃肿各多时[2]。
不同于翁稚相对的欣慰,在环境恶劣的外层地理空间里,张慎言与斜卧的老槐紧紧依偎在一起,如同手足兄弟,尽管树支离、人臃肿,但彼此扶持,诗人心中便有归属感。不如松树,不甚挺拔,困境之中却依旧顽强地活着,人与树的命运在故乡的投影里重合,文学地理的内层和外层空间在诗人的文本世界中融为一体。
组诗有共三首,首首精彩,其三云:
夜静星阑鸟不栖,空余缺月挂枯枝。半边老树探春信,早晚春过小月氏[2]。
老槐枯败,缺月如钩,寂寞夜分幸有春意爬上枝头,诗人在残破光景中抬眼凝望,夜光晦暗,但裹挟着希望的春天终将拂过肃州关山。小月氏是自月氏部落西迁后,当地人对其在祁连山下的遗民的称呼,这里即以人代地。诗人在残破的外层空间里开拓出一方温暖明媚的精神世界,支离的老树承载着故土的思念,跨越时空,送来希望满怀。这是一种地理纬度上的嫁接,从第一首的相依为命,到第三首的未来可期,槐树以松树的形象,在诗人的精神空间里投影下来自故乡的暖阳。张慎言《酒泉诗稿》中对这株槐树倾注了大量的笔墨,乃至多年后,这株树也仍在他的诗歌中活跃着。《报国寺松》中有“二十年来此再逢,怜仍拥肿对龙钟。支离待我胡箕踞,偃蹇题君曰不恭”[2]句,面对久违的松树,诗人心中浮现的仍旧是“支离”对“拥肿”的酒泉旧事。可见在彼时的塞外穷边,庭中老槐当之无愧扮演了张慎言精神世界的南天一柱,以故乡的温存慰藉了游子的心。
《酒泉诗稿》是记录汉人王朝在河西边塞生存斗争现实的最后一部诗集,对汉唐以来的酒泉地理空间书写作了积极的总结和补充,乃至在思乡主题的精神世界构建中实现了突破。
三、张慎言酒泉书写的精神超越
河西是汉唐军人激烈战斗的地方,滋养过无数边塞诗家,历代的酒泉地理书写也不断丰富着这篇土地的精神空间。张慎言的到来,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新的文学地理内涵,而这一精神世界的超越,是通过“陇首云”这一经典的地理意象实现的。
地理意象是“可以被文学家一再书写、被文学读者一再感知的地理意象,它们既有清晰的、可感知的形象,也有丰富而独特的意蕴”[15],河西作为边塞诗派的摇篮,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意象系统填充其间,而“陇首云”正是这一地理空间中的经典意象。最早关注到这一意象的是南朝的徐陵,其作于凉州的《关山月》中即营造出如此的诗意空间:
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星旗动疏勒,云阵上祁连。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6]52
关山月,乐府横吹曲,《乐府诗集》解题为“伤离别也”[16],前两联即通过实写与想象突出了这一主题。尤其精彩的是第三联,巧用对仗与双关,同步构建起塞外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空间,尤以“星旗”“云阵”为妙,借自然意象写活了“战气”的压抑紧张。由此,以云喻战争的传统便逐渐形成,至今仍有“战云密布”这样的词语在广泛使用。
唐代边塞诗蔚为大观,以“陇首云”为地理意象入诗者也不乏后继,从继承的角度来讲,约可分为两脉:一脉继续夯实以云喻战的形象类比逻辑;一脉则循着南北朝山水诗的创作逻辑,专注于描写云作为自然地理景观的形态美。唐诗的意境熔融扩大,情景如一,就“陇首云”而言,后者这类专写景致的诗相对较少,但也不乏名句:如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6]84,气象阔大堪当压卷;又如李白《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6]124,笔写边塞壮景;王维《出塞》中也有“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6]102的狩猎情景书写。前者以云喻战,更有颇多名句: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6]92句当居其首;皎然《塞下曲(二首)》其二以“旄竿瀚海扫云出”[6]161喻指唐人全歼敌虏、净扫西边的军事胜利;岑参《送张献心充副使归河西杂句》中“花门南,燕支北,张掖城头云正黑”[6]153、钱起《送张将军征西》中“战处黑云霾瀚海”[6]156则明确以黑云喻战事之危急,尽管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书写对象是北境之势,但用意相类,足见“黑云”已走出陇上的地理空间,走入了经典意象的行列。当然,唐代诗家的继承只是一部分,他们也以卓越的创造力,赋予这一意象以新的情感内涵。其实说“赋予”也是不甚准确的,自祁连云阵作为意象出现在徐陵《关山月》中开始,陇上的云就已经与离愁间接地挂起钩来,唐人则极复热情地歌咏了这一内涵下的“陇首云”。卢照邻《送郑司仓入蜀》中有“别忆还无已,离忧自不穷。陇云朝结阵,江月夜临空”[17]的书写,诗语直白地将“离忧”和“陇云”联系起来,并将“陇云”和“江月”并举,在时空两端的维度上坐实了其与思念之情的关系;贺知章《送人之军》有“送子成今别,令人起昔愁。陇云晴半雨,边草夏先秋”[18]句,诗人送友入戍,遥想陇云边草,不由满心离愁;刘长卿《鄂渚听杜别驾弹胡琴》中也有“不解胡人语,空留楚客心。听随边草动,意入陇云深”[19]句,诗人与客居他乡的蔡文姬在胡琴声中共情,眼前浮现出陇云边草的荒凉景,游子的离愁自然愈发浓郁。这些诗句突出了“陇首云”的形象特征——“结”是为郁结,“晴半雨”是为阴沉,“深”是为浓重——恰如离别的心绪,使得陇上的云以形象类比逻辑与离愁紧密结合起来,乃至沈佺期和钱起直以其入挽歌。随着“陇首云”意象的愈发成熟,其内蕴的愁绪也横向扩展,逐渐挣脱了伤离别的限制,“陇云愁”成为一稳定的诗歌语料,仅唐一代便有沈佺期、武元衡、薛能、温庭筠、高骈、孙光宪等诗人相继以之入诗。唐以后,宋人也以之入词,柳永即多次使用“陇首云飞”语,徐铉也有“陇首云随别恨飞”句,尽管他们不少已引申作“山头云气”解,但其以云喻愁绪的内在意蕴却愈加稳定下来,张慎言也有“率尔同酣陇首云”句,故该意象在此即以“陇首云”冠之。
明代边塞不如汉唐攻势之盛,整体比较安定,但进入统治末期,边势也渐趋紧张。以地域比较,甘肃镇在天启年间交战12场,占到彼时九边总战争数的2/3;以时间比较,天启间甘肃镇的年均战争数达1.71场,居明代历任之首[20]。谪戍此间,作为后来者的张慎言充分发挥了“陇首云”这一地理意象的丰富意蕴。《己巳元日回忆酒泉》是诗人记忆中的肃州,“天过穷石无芳草,云到西方是美人”以陇上白云为对象,直写其美,却更衬出边塞的满目荒凉。《城南野望》有“回首不堪斜日尽,白云尽处是康居”[2]句,康居是汉初西域的古国,唐时仍存在,一度俘获唐玄宗欢心、乃至风靡长安的“胡旋舞”相传即源于此。诗人以云为引子,将地理概念的史话内涵演绎为现实乱象,嫁接时空,在“不堪斜阳尽”中抒写对奸臣惑上、朝政混乱的深深忧愁。在《酒泉杂咏(二首)》其二中,张慎言更是直发“闭阁难终日,看云若易怚。有时仍自问,吾道竟何如”[2]的命运感慨,“怚,宗苏切,音租。剧也”[21]。一字即写尽陇首云的悲愁意蕴。对其军事喻义,张慎言则有《登城北最高处,三面皆虏,才东走张掖一线尔》:
登台面面尽黄埃,边气胡阴惨不开。有客只宜东向望,白云片片尽西来[2]。
北、西、南三面俱有胡军压来,无奈何东遁张掖,诗人心有不甘,盼望朝廷驰援军马若白云片片叠涌西来。云在天,高而明洁;尘在地,低而混浊,在外层地理空间里绘出一幅天地相争、明虏对阵的壮丽图景。诗人东向遁去,白云西向涌来,白云者,即譬诗人所期盼的闻警驰援的后方明军旅阵,是冲破“胡阴”的希望所在。此间“白云”亦实亦虚,既以之为自然景观与“黄埃”对举,又反用以“黑云”为敌军阵的意象用例,喻以新义,堪称妙笔。
同唐代诗家一样,除了对传统的继承,张慎言还以自己的生命光彩,为“陇首云”赋予了新的精神内容。《酒泉诗稿》中有诗名《坐黄草渠》:
袖书临远水,书倦即看云。雁字不可读,鸥波良易群。牧儿奔返照,锄唱爱余曛。我亦携书去,翛然何所欣[2]。
云舒云卷,鸥雁翔空,君子乐书,农牧繁荣——诗人笔下的酒泉形象在此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原本荒芜苦寒、民屯凋零、边军闻警的地理空间一转而为军民安居的塞外乐土。这并非梦回汉唐,而是诗人心绪的大转变,不仅拿起了书本,精神世界也变得淡泊适意起来,“书倦即看云”,如此心境,苦寒之地竟写出了桃花源的气象。就“云”的意象内涵而言,陶渊明、王维等一批诗家早已为其注入了清远隽澹的文学内蕴,但在肃州,作为愁气郁结的“陇首云”,如此彻底的转向是难以想象的。而这样的变化,是以张慎言的精神转向为契机的。在他的文集中有《酒泉寄贲闻札三首》,其一云:“仅借得《史记》,求《汉书》不可得。若马角未生,当以次读《尚书》、《礼记》。去留都未可知,亦渐有‘此中乐,不思蜀’之意。”[13]信中全无丧气语词,许是本着报喜不报忧的初心,但字里行间的旷达之气是真实可感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得斋“快雪”之后,张慎言对读书展现出极大的热情,酒泉期间,他奋而著《悔草》,在《悔草序》中,他痛定思痛:
《悔草》者何?是不肖言追往者之不知学、不闻道,痛自刻责,无人可控,无地可容,不得已,自泣自诉,而乃为是草,用志悔也。悔固也,而必为是草者何?茫茫然如穷人无所归,圣贤之言如饮食焉,朝斯夕斯,彷徨于胸臆手口之间,恍惚而冀一遇也。又人之有病,百体无恙而先见于脉,故医者得而医之。虽讳疾忌医,而切者已不言而知之矣。余既悔矣,方寸之病,余方不自觉,而庞杂之症脱于手口者,毕见于笔楮,无毫发可遁。有爱我者而赐之药石,将庆更生焉。此余志也。噫!悔晚矣,何嗟及矣!虽加一日,不愈于已乎![13]
张慎言本进士出身,学养深厚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即便怀才如此,他依旧痛悔“往者之不知学、不闻道”,乃至以《悔草》为名,奋而治学。但是,获罪永戍,归期渺茫,他治学又为了什么呢?非只感于“圣贤之言如饮食”,亦非仅为医“不闻道”之病,这是一个儒家士大夫的坚守,身处绝境,他满心挂怀的仍旧是家国天下。《酒泉诗稿》中暗刺朝政的诗歌不在少数,《老圃行》题下的“诗作于丁卯秋初,戊辰新正乃敢脱稿”[2],《乙丑即事》题下的“作于乙丑,爱我者促令焚去,附录于此”[2]都直观地反映了彼时政局的黑暗。据《三垣笔记》载,天启六年“曹钦程以一主政纠四御史”致使“三人皆死镇抚司,惟慎言戍”[22],《国榷》亦载曰:“曹钦程之诬陷诸君子也,俱下诏狱死,独张侍御就讯抚按。”[14]5321作为同批被陷害的四位御史中唯一的幸存者,张慎言愈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他在深深的悲痛与无奈中振作起来,誓以充实己学,重整朝纲。于是,谪戍酒泉在他的心目中变成了“圣主原教霜淬斧”[2]的历练之旅,他一面怀着神圣的使命感,感叹“如许乾坤容七尺,悠悠寥阔易为心”[2],一面藐视苦难,心态渐趋平和,乃至生出了“绝境耳目古,闻如得所求。朴真如我意,简寂自生幽”[2]的道隐气质。
面对困境,张慎言似乎也曾有过皈依佛、道的倾向。一方面,他少时读书所在的“海会书院”本就是佛寺,刚至酒泉时也曾“寓佛寺”并作有《善积寺老衲索题所摹藏经》,晚年在芜湖也是“寄食萧寺,繙经礼佛”[11]654~655;另一方面,他入陇途中曾有“早识数穷能至此,喜从令尹御青牛”[2]的感慨,崇祯朝再遭贬谪时,也曾忆酒泉云:“倘侥离伍投戈日,便是长林丰草时。”[2]但就他留下的现存作品和史家遗笔来看,抵达酒泉后,张慎言的儒心坚守是始终如一的,而正是在守望责任的日子里,他以儒家士大夫的中庸持志,抵达了淡泊宁静的境界。因此,他诗中的隽澹气象并非皈依或入道后的弃世,而是儒者宽厚胸膛中真正的心怀天下。可以说,正是张慎言的到来,使原本填满苦寒或壮景、兵气与乡愁的西北边地生发出恬淡适意的云气,更使这片土地的内层空间内蕴了儒之大者的精神内涵,乃至幻化出道家式的隽澹气象,这是张慎言对酒泉地理书写的珍贵赋予,更是对河西内层空间地理意义的精神超越。
四、结语
谪戍酒泉是张慎言生命中遭遇的最大危机,但也正是他的苦旅,为文学史留下了汉人王朝河西风云的最后剪影。酒泉地理书写的丰富文学内蕴磨砺了他的诗艺,更振发了他作为儒家士大夫的家国之心,“岁月君恩深未酬”“不知何以答君王”[2]的儒心坚守不仅反过来赋予了酒泉地理空间以新的文学特质,更实现了文学地理意义的精神超越。酒泉的谪戍历练,也使他的儒者心胸在坎坷的仕途中愈发深稳博大,终助其成长为南明国柱,在风雨飘摇中保护了汉人王朝的火种,史有“令其受事熙朝,从容展布,庶几乎列卿之良也”[8]4651之赞。而作为一刻骨铭心的地理符号,酒泉也变成了张慎言精神世界里的力量源地,每每遭逢逆境,它便流出笔端,重新以精神高地的形象,赋予张慎言以坚守的勇气,即便身染沉疴,他也在酒泉回忆中生出满腔壮气:“丹霜碧水休仓卒,待我扶笻登陇头。”[2]这是人与文学地理深刻羁绊的写照,是酒泉地理书写的宝贵精神遗产。
——酒泉晋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