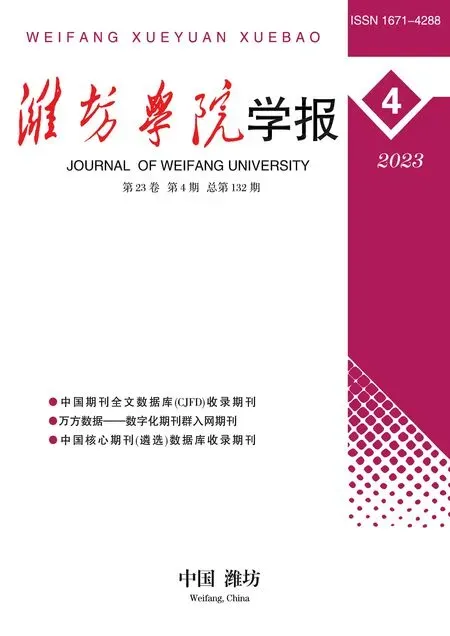论《蛙》和《个人的体验》中主角救赎的异同
杨仲友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大江健三郎是继川端康成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在日本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他数次来到中国,为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尤其是南京大屠杀)道歉、反省和赎罪,并和莫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个人的体验》作为他的代表作,以他的亲身经历,加上在广岛考察后的切身体会书写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救赎小说,主要讲述主人公“鸟”对新生的遗弃、拯救再到自我救赎的过程。莫言的《蛙》也是作家以自身经历书写的一部反思生命与灵魂救赎的小说。它以四封书信,加上一部九幕话剧组成,书写在我国计划生育背景下,主人公姑姑万心对新生的接生、毁灭再到自我救赎的故事。自我救赎作为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个别作品中的题材、情节、人物、母题和主题,而是不同作品中,同一题材、同一人物、同一母题的不同表现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主题学经常研究同一题材、同一母题、同一传说人物在不同民族文学中流变的历史,研究不同作家对它们的不同处理,研究这种流变与不同处理的根源。”[1]《蛙》和《个人的体验》都以生命救赎为主题,既有相似,也有不同,异同背后的根源值得挖掘。
一、救赎的相同之处
(一)原因的相似性:新生的毁灭
《蛙》和《个人的体验》中的主人公都对新生进行了毁灭。《蛙》中姑姑因为国家计划生育给孕妇引产,导致2000 多个腹中胎儿未见人世。《个人的体验》中,“鸟”因为向往非洲去过冒险刺激的生活,也不想要被婚姻家庭羁绊,而遗弃自己刚出生且患有脑疝的残疾儿。
《蛙》中的主人公姑姑万心原是公社的妇产科医生,由于接生技术高超,被十里八乡的人称为“活菩萨”“送子观音”。但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中,姑姑却不近人情,人性扭曲,利用国家公器对孕妇喊话攻心,围追堵截,并对多个孕妇进行强制性引产,酿成2000 多个婴儿不能顺利出生的惨剧。为了坚定执行国家政策,当发现自己的侄媳妇王仁美超生时,不顾亲情伦理,毅然决然到王仁美的娘家,大动干戈地把她引出来流产,导致王仁美大出血惨死在手术台上。后面为了让王胆把孩子打掉,已经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她说不把王胆肚子里的孩子做掉她饭吃不下,觉睡不着。责任心强到了这种程度,你说她还是个人吗?成了神了,成了魔啦!”[2]150最后王胆为了保护孩子躲进自家竹筏,混入其它卖桃子的村民的竹筏中溜出去时被姑姑发现,在展开追逐的过程中,王胆受到惊吓难产而死。
《个人的体验》中主人公“鸟”是一位预备学校教员,本来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却觉得自己的婚姻不幸福,所以向往去非洲过冒险刺激的生活。同时,自己的孩子出生就带有残疾,患有脑疝,更让生活本不如意的他神情沮丧。“一旦妻子生下孩子,我就要幽闭进家属的牢笼里去了。”[3]6为了能够去非洲旅行,也为了摆脱婚姻的束缚和乏味的生活,他决定遗弃自己的残疾孩子。在院方打电话通知他去医院,得知自己的孩子头部异样后,他根本没打算救治孩子,反而询问医生如何“正确”地处理掉孩子。在医生给了他相关的建议后,他决定停用孩子的牛奶,让医生把牛奶换成糖水,以便让其器官衰竭,自然死亡。后面院方告知他孩子还存活,是否需要动手术时,他再次拒绝了院方的合理请求,在自己情人火见子的建议下,把孩子送到火见子的一个做人流的医生朋友那里做掉。
(二)过程的曲折性:人性的复杂
《蛙》和《个人的体验》中主人公在进行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没有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人性的犹豫、沦丧、挣扎和反复,救赎的过程也是内心善恶的天平不断摇摆、斗争和博弈的过程,人性的复杂可见一斑。
《蛙》中姑姑在执行国家政策时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经历“青蛙”事件后,她精神恍惚,被迫通过捏泥娃娃的方式进行救赎。然而,当自己的侄媳妇小狮子不能生育,借陈眉的肚子生下孩子后,姑姑却不思悔改,人性再次沦丧,帮小狮子抢夺了陈眉的孩子。事后她又良心发现地说到:“也许我们把孩子还给她,她就好了呢?母亲和孩子之间,那是可以产生奇迹的……”[2]337这句话透露出她内心的犹豫和挣扎。最后,姑姑想要通过上吊轻松死去却不得。“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力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2]339她想上吊,却被人救了下来,在忏悔和救赎里反复煎熬……
《个人的体验》中,“鸟”在自我救赎时同样经历了内心的挣扎和煎熬,体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和反复性。首先,“鸟”在遗弃孩子时丧失人性。当意识到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是残疾儿时,他出于对平淡生活的厌恶和对非洲寻求冒险的向往,认为残疾儿是自己前往非洲路上的绊脚石,所以主动让医生把喂养孩子的牛奶换成糖水,加速其灭亡。其次,当他想要通过酒精和性交来麻痹自己时又流露出人性的挣扎。在和火见子宿醉时,他总是担心院方会打电话过来告知孩子的近况,当和火见子外出时,他脑海里不时闪过自己残疾儿的情景,说明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孩子,内心矛盾犹豫。再次,不愿做伪证时又体现他正直的一面。当他因宿醉而即将被校方解职时,学生劝说他做伪证以避免失去工作,他却一口回绝了学生的好意,没有以人性的恶去欺骗以带来更深的恶。最后,当他和菊比古交谈,被菊比古嘲讽时,内心的善恶不断进行博弈又体现出他救赎时的反复。
(三)动机的一致性:灵魂的救赎
《蛙》和《个人的体验》中的主人公在寻求救赎时的动机上都是一致的,在尘世生活里把丢失的人性美捡回来,形成健全的人格,以完成人性的复归和灵魂的救赎。
《蛙》中姑姑退休那晚,经过一片洼地,看到无数只青蛙对着她呱呱大叫,不仅跳到她身上撕咬她的肉体,还要吞噬她的灵魂,以致她晚年噩梦不断,精神恍惚,时常放声大歌。这些在旁人看来反常的行为,只有她自己知道,是她背了良心债的结果。为了偿还良心债,为了能够正常生活,也为了灵魂得以救赎,姑姑只能嫁给泥塑大师郝大手,通过捏泥娃娃的方式来让自己手中的2000 多个“冤魂”得以安息。只有他们都安息了,姑姑的罪孽才算洗刷完成,灵魂也才得到救赎和安息,自己才能轻松地死去。姑姑的自我救赎,本质上是为了把丢失的灵魂找回来,让灵魂复归肉体,自己才能身心健康,正常地生活。
《个人的体验》中“鸟”对现实平淡生活的不满,向往非洲寻求刺激来麻痹自己,让灵魂暂时解脱。但生下残疾儿后,为了逃避残酷的现实,他又开始酗酒,并通过和火见子有违道德规范的性交来麻痹懦弱的神经,加速灵魂的堕落。对残疾儿的遗弃,也是他人性缺失、灵魂丧失的一大体现。所以,当他拒绝给孩子手术,并把孩子送到其它地方打算做掉的时候,为了逃避良心的谴责,他决定和火见子去菊比古酒吧买醉来麻痹自己。正是在这个酒吧和菊比古的交谈中他逐渐意识到,他之前丢失的责任、担当、勇气和魄力正在复归,如果不去面对现实,拯救孩子,菊比古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他的灵魂也将一直沉沦下去。无论他走到哪里,人性的缺失和灵魂的游离都会伴随着他,后半生也会在痛苦和煎熬中死去。所以,与其说他拯救孩子,不如说残疾儿的出生给了他自我救赎、走向新生的契机。他通过对残疾儿的救助,间接地完成了对自我心灵的重新塑造,人性中缺失的责任担当等美好的东西也随之复归,灵魂得以最终救赎。
二、救赎的相异之处
(一)救赎的性质:被动改变和主观醒悟
《蛙》和《个人的体验》虽然均为关于主人公的自我救赎,但其性质却大相径庭。《蛙》中姑姑万心若不是因为退休那晚经历青蛙的洗礼,导致她晚年噩梦不断,失眠不绝,她也不会捏泥娃娃进行救赎。因此,《蛙》中的姑姑在进行自我救赎的性质上是被动的、消极的改变。而《个人的体验》中“鸟”却不同,他开始选择自我堕落的方式麻痹自己,经过菊比古事件的刺激后幡然醒悟。所以,他在进行自我救赎的性质上是主动的、主观的醒悟。
《蛙》中姑姑因为挟国家政策之法理,以公器之雷霆手段对高密东北乡的已婚男女进行强制性结扎引产,所以无所畏惧,自然也不会为那些未出世的婴儿感到内疚。但在生命伦理方面,她却用双手扼杀了2000 多条无辜的生命,造成了一些人家一尸两命,家破人亡的惨剧。且在计划生育的执行过程中,过于偏执,人性扭曲,为了任务不顾人命,已经触及犯罪。所以,经历“青蛙事件”的洗礼后,她才悔悟所犯罪孽深重,被动进行自我救赎。此外,得知小狮子借腹生子后,如果她主观醒悟了,就不会帮助小狮子去抢夺陈眉的孩子,加重自己的罪恶,但她却用行动表明,她的自我救赎是无奈的,是被动进行的改变。
《个人的体验》中,“鸟”刚开始用酒精和性交来麻痹自己,逃避现实。但经过和菊比古的交谈,他回忆了自己之前的勇气和担当。对于曾经对菊比古半途而废的厌恶和遗弃,如今却被菊比古借此来嘲讽自己,他内心受到了屈辱。同时他也发现,自己因为有担当才走了上坡路,而菊比古因为选择逃避走了下坡路,菊比古觉得“那时要不是一个人走的话,也许我也能换一种生活方式吧。”[3]122如果他现在和菊比古做同一个选择,那么菊比古的现在就是他的未来,他在菊比古身上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影子,最终痛改前非,不再做一个兜圈子逃避责任的男人,主观醒悟去面对现实,拯救孩子,迎接新生。
(二)救赎的行为方式:供奉泥娃娃和拯救残疾儿
《蛙》和《个人的体验》在自我救赎的行为方式上,截然不同。《蛙》中姑姑为了拯救自己,通过供奉泥娃娃的方式,让泥娃娃的生命得以安息。而《个人的体验》中“鸟”为了真正拯救自己,拯救自己的残疾儿,最终给他动了手术。
在《蛙》这部文本中,姑姑和泥塑大师郝大手结合,通过她脑海里清晰的回忆,生动形象地给郝大手讲解每个婴儿的父母是什么样子,以便泥塑大师能准确地捏出孩子的样貌。然后等这些泥娃娃烘干后,就把他们供奉起来,进行祈祷,幻想让他们的灵魂得以安息,生命通过投胎转世的方式得以再生。自己以为也能在这过程中不断洗刷自己的过错,忏悔自己的灵魂。当把最后一名亲手扼杀的未生婴儿捏完之后,姑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已经完成了灵魂的救赎,不再经受生命的煎熬,能轻松地死去。
《个人的体验》中,“鸟”经过菊比古事件的启发,终于认清了只有拯救自己的残疾孩子,才能够拯救自己。所以他不顾情人火见子的劝阻,毅然回去要给孩子动手术,不管手术结果如何,他都能坦然面对。同时,他也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做了规划,在小说最后一部分,他决定听从学生的建议,给非洲来日本的游客做导游,养家糊口。最后,他还在友人赠送他的巴尔干半岛小辞典里查“忍耐”一词,表明在面对平凡的日常生活,他需要“忍耐”。只有这样,才能熬过生命的低谷,迎来人生的曙光,最终实现自我救赎。
(三)救赎的结果:失败与成功
《蛙》中的姑姑认为自己没错,供奉泥娃娃也是被动改变,最后救赎失败。而《个人的体验》中“鸟”经过菊比古事件的刺激,幡然醒悟,最终救赎成功。
《蛙》中姑姑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在面对结婚对象叛逃时,她曾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所以在执行党的政策时不遗余力,坚决落实党的指示。在执行相关政策时,她内心并不认为自己犯了错误。面对晚年的精神错乱,她把希望寄托在泥娃娃身上,以为通过外在的行为能忏悔内心的罪恶。在小说最后一部九幕话剧里,姑姑以为帮助小狮子抢夺本属于陈眉的孩子是在为自己赎罪忏悔,却“以赎罪的方式酿造了更深的罪恶,以阻止悲剧的方式制造了更大的悲剧。”[4]结尾处自杀未遂,这条道路也没有走通,表明了她自我救赎之路的彻底失败。
《个人的体验》中“鸟”善良的本性和柔弱的人性之光,在关键时刻帮助他完成了救赎。他曾经也是一个优秀青年,后来因为人生变故而丢失了善良本性。如何处置残疾儿的犹豫体现了他还残存的善良本性,“在厌弃、羞耻的本能之外,‘鸟’也有着身为人父的怜子之情和不曾熄灭的人性之光。在他挣扎逃跑的过程中,自由与责任、邪恶与良知一直在他内心剧烈地争斗着。”[5]最终经过菊比古的刺激,他终于认清了现实,进而承担起了应有的责任。在同岳父交谈的过程中,他已经做好了面对残酷现实的心理准备,去当导游来赚钱养家,抚养孩子。岳父都认为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鸟”了。小说结尾,在友人赠送他的“扉页上题写着‘希望’的那本词典,他想找的第一个词语就是——‘忍耐’。”[3]126表明他最终完成了人性的复归,成功地进行了生命的自我救赎。
三、《蛙》和《个人的体验》中救赎异同的缘由
《蛙》和《个人的体验》写的都是自我救赎的主题。两部作品在自我救赎的原因、过程和动机上相同或相似,但在自我救赎的性质、行为方式和结果上,又产生了巨大差异,表明它们和作家的文化背景、个人经历和文本功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文化背景的不同
著名学者韦斯坦因认为,“作家对题材的选择是一种审美决定,观念性的观点是结构模式的决定性因素,信息是媒介中固有的。”[6]莫言和大江健三郎国家不同,文化背景方面也存在着差异。莫言作为我国的乡土作家,他的作品打上了“乡土”的记号。从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丰乳肥臀》到后面的《檀香刑》《生死疲劳》直至本部作品《蛙》,大多写他故乡的风土人情、民俗风貌、生离死别。他生于斯长于斯,对乡土的变迁和小人物的感受特别敏感。《蛙》写的是计划生育背景下个体生命在国家政策和生命伦理两难的情况下的艰难选择。姑姑被迫毁灭孩子,并非她主观恶意。她选择捏泥娃娃也是由于晚年失眠,噩梦不断让她被动屈服,需要给婴儿忏悔以寻求灵魂的救赎。由于非心甘情愿,姑姑的救赎之路就变得犹豫、动摇、反复,以致最后并未完成生命救赎。
大江健三郎生于日本,虽然日本和我国一衣带水,也保留了我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但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向西方学习,近现代也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江健三郎作为二战后日本有影响力的作家,其作品依然带有日本作家的细腻和深刻。在《个人的体验》这部作品中,他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来展现主人公内心的所见所想。同时,他还受到西方尤其是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积极通过文学创作来干预生活,干预社会。个人存在的意义不是荒诞的,虚无的,而是现实的,可期的,这点是他对存在主义的超越。《个人的体验》中“鸟”自我救赎的过程就写得非常细腻。而他选择主动拯救孩子,迎接新生的圆满结局,也符合大江健三郎干预生活、未来可期的写作理念。
(二)作家经历的相异
《孟子·万章》下篇写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的“知人论世”说,“涉及要了解作品,必须先了解作者”。[7]一部作品的生成,与作家个人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蛙》即是在计划生育背景下,莫言以自己在高密东北乡的亲身经历创作的一部作品。正因为如此,莫言在写姑姑的自我救赎时,非常地真切自然,仿佛作品里发生的一切已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了一般。同时,莫言作为农民作家,他的写作对象自然离不开自己土生土长的高密东北乡和那里的乡民百姓。莫言自己在不同的场合都强调过,他不是为了老百姓而去写作,而是作为老百姓去写作。因此在《蛙》这部小说中,姑姑用捏泥娃娃这样的方式去赎罪,没有切实的农村经历和真实的乡土体验,是写不出这么接地气又符合我国传统祈祷祭祀礼仪的小说。
《个人的体验》也是大江健三郎以他的亲身经历,加上在广岛考察后的所见所感而书写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大江光,先天性头盖骨缺陷,抢救后成为残疾儿。这个不可抗力的悲剧让他深深体验到作为父亲的不易,该经历成为他创作《个人的体验》的一大来源。怀着苦闷的心情,1963 年大江健三郎去广岛考察,回来后他把在广岛考察的所见所感,写成了随笔《广岛札记》予以发表。因此,《个人的体验》既融合了他自身家庭的经历,也结合了他去广岛考察后的感想反思。“他从广岛人的生存理念中深深地感到,他们那种立足于现实,敢于同命运抗争到底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敢于承担责任,能够确立自己人生坐标的生存方式,才是对人生真谛和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最好诠释。”[8]广岛人民面对核辐射仍然坚毅地生活下去,给了大江健三郎巨大的勇气和鼓励,他最终明白了人生坐标的生存方式。投射到作品上,则是“鸟”主动去拯救孩子,生命的自我救赎也在拯救孩子时得以完成。
(三)文本功用的差异
虽然都是关于自我救赎的主题,但《蛙》和《个人的体验》分属不同国家、不同作家、不同的文学体系,其文本功用也会存在差异。“对于人生短暂而自然却永恒长存的感怀,对于自我的认识和对于人生的领悟,对于理想的追求与破灭等都常常在完全不同的文学体系中以相同或不同的形式得以表现”[9]。在《蛙》和《个人的体验》两部作品中,《蛙》中姑姑自我救赎的失败,让人冷静和反思;《个人的体验》中“鸟”自我救赎的成功,让人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
在国家政策和生命伦理不能两全时,姑姑的一生,注定是悲剧的一生。《蛙》中姑姑“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代表着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受外在制度威压精神受到扭曲而无法依照本性生活的一群人。”[10]她想洗刷灵魂而不可,忏悔过错而不行,救赎生命而不能,自我救赎从根本上就不可行。莫言的“他人有罪,我亦有罪”已经表明,他在借用姑姑救赎的悲剧的一生来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来的影响和后果。“莫言用文字为生命潜心搭建神龛,在神龛前他自省、忏悔、祈祷。他敬畏生命,他救赎生命,他反思生命。”[11]
大江健三郎把个人的不幸体验和核辐射给广岛人民带来的身心创痛结合起来,书写普适性和普世性作品。正如作者在《我在暧昧的日本》一书中写到:“我在文学上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联系起来。”[12]《个人的体验》中,大江健三郎把“残疾”这一边缘性话题和“救赎”这一人类终极性主题相结合,表达核辐射给人类带来不幸时,需要振作起来,积极主动,忍耐现实,才能找到人生真谛。作品美好的结尾,即是作者给予世人的独特体验:人的一生并非轰轰烈烈,而在于把握好日常的平凡生活。像“鸟”一样,敢于面对残酷的现实,勇于承担家庭的责任,并积极努力去行动,人生就会充满希望。
结语
生命的自我救赎,是现实生活中人们难以逾越的一大鸿沟,同时也是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上述两部作品通过以小见大的手法书写个体的生命际遇,反映了普遍的人生困境和自我救赎,具有普适性和普世性。莫言在《蛙》中对姑姑万心这个人物形象倾注了无限的深意,姑姑不仅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也是一段民族的烙印。她承载着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对人性的思考,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大江健三郎在《个人的体验》中通过“鸟”这一人物形象,向世人说明,人生或多或少会掺杂苦难与不幸,抱怨生活,逃避现实或怨天尤人都是没有意义的。与其在自欺欺人中如行尸走肉一般地苟活,不如勇敢地面对现实,重新构建自己的人生坐标,寻找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忍耐并充满希望,生命就会在有意义的流淌中完成自我救赎。通过对上述两部作品主题的比较,挖掘其中的异同点并分析其背后的根源,一方面能深化文学创作中自我救赎的主题,另一方面也能从中汲取精神养料来指导现实生活。生命的自我救赎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人类不断挖掘自身、反思生命的无尽宝藏。